杂货店珍姐
王宝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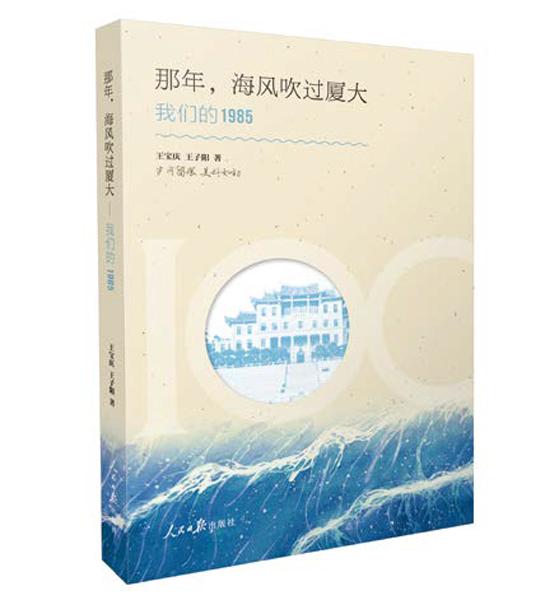
当年的厦大生活,曾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东边社2元钱一局的台球,吸引了多少厦大男生,在昏暗的露天灯光下专心致志打得不亦乐乎;块八毛的冰镇鹭江啤酒,又让多少壮志不言愁的大学精英热血沸腾。
那时,按照各自籍贯地域,厦大学生里有一批雄性激素超强、最调皮捣蛋的学生,心照不宣地划分出地方部队。
第一支部队,是来自北京的正黄旗小分队,直言快语,横冲直撞,在厦大留下不少豪横的故事。正黄旗队员们个个人高马大、玉树临风。特别是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儿,说起话来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似的,因此极有权威。
上海小分队有些悲剧,因为除了自己,他们把全国所有地区都看成乡下。但他们忘记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是农村包围城市。上海小分队的队员们痛苦地发现:无论自己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摆道理,头顶上永远有一支叫“北京小分队”的中央军。自己不管怎么火力全开,和中央军对起阵来,每次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后索性“闭关锁国”过小日子,只求正黄旗们别来打扰自己。
四川因为有重庆、成都两座大城市,因此号称“双枪小分队”。
蜀军队员们之前提起北京,觉得那里都是古老建筑和或许最早可追溯到辽金元时期的烤鸭,等见到桀骜不驯的北京学生,这才明白首都原来还盛产豪横不可一世的“鞑子”。
沿海人提起西北,总觉得那里没水喝,于是看见晋陕甘的学生,总会想到白城海边的水淹七军,动不动涛声依旧地就海边约架,占尽地利;贵州人提到东北和江浙,觉得这些地方都是未知的不发达地带;湖北小分队“惟楚有才”,但提起山东,就立即想到水浒,再加上企管系岿然屹立着那位能“辟邪”的山东猛男隋建人同学,因此对齐鲁联军也就多了几分忌惮;江浙人提起大连青岛,像进了美女博物馆,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除了“大长腿”和“皮肤白”这几个词儿,其余的话都说不利索了;而福建人提起北方,总觉得那是大老爷们儿豪情壮志的乐园。
“粤军”们考入厦大,曾经一度觉得,除了自己,中国所有地区都是北方憨大。等见到北京小分队气吞天地的谈吐和锐不可当的凶猛,白云山小分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家鸭庄和北京烤鸭不可同日而语——厦大里见多识广的正宗燕京“鞑子”们,敢情这么不好惹。
因此,机智的粤军立即制定避险规则。
平日里,白云山小分队对正黄旗小心翼翼避其锋芒。白云山小分队常在芙蓉楼几个杂货铺神出鬼没,队副是广州“富豪”阿雁,队长是朋友遍厦大的阿天,后者因为嘴巴大,又名“南霸天”。
前些日子,远在深圳的原白云山小分队队副阿雁给我打电话。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时,他嬉笑怒骂谈笑风生之间,忽然问起:“你还记得芙蓉十小店的老板娘珍姐吗?”
我们聊着,一个30多岁、开口就笑、快人快语、十分消瘦的典型闽南女子,渐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珍姐的小杂货店,就开在厦大芙蓉十下面的铁皮房里。这个小店老板娘,性格直来直去,颇有些侠气。当年厦大那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子,一到晚上就饥肠辘辘,很多人在她那里赊过账——尤其是白云山小分队的队员们。
对厦大那么多男生的赊账,她从不拒绝。那时的学生,一旦家里汇款到了,第一件事就是去还债,没赖账的。
珍姐常说,这些都是千里萬里离开爹妈的孩子,再说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秀才郎,毕业后都是国家建设的顶梁柱,能为国家作贡献,所以赊账、欠账,就是不还钱也无所谓。“10年之后,这些调皮捣蛋的坏小子,都是顶梁柱!”她每次都这么说。
现在想想,当年多少厦大学子身无分文、饥肠辘辘时,午夜悄悄跑到珍姐的小店敲门,难为情地叫一声“珍姐”,然后要了方便面就走。
她忙不迭追出来,给满脸通红的学生又递过一包榨菜、一包花生:“榨菜花生白送,阿姐请客!”曾有那么多的芙蓉学子,都受过她的恩惠。
珍姐瘦得如一片丝绸、一面窗帘,可胸怀却像宽阔的白城沙滩一样。她记忆力极好,能叫出很多学生的姓名。这种记忆水平,一定比厦大教务处的一些领导都更显得深入群众。
阿雁和我谈到这里,唏嘘不已。
我也记起,当年入学后,第一次和阿雁到珍姐的小店去买东西。她仰起头问:“你们北京男孩长这么高,你是不是国家篮球队的?”
我身高一米八,但要真在国家篮球队,算是名副其实的矬子,当即笑得前仰后合。
珍姐“砰”地打开一瓶汽水:“来,国家篮球队,阿姐请客!”我纠正她浓郁的闽南口音:“汽水儿!”珍姐努力学我的北京话:“汽——碎——而!”她学卷舌音,累得直喘,最后终于学会了:“气儿——碎!”
过了一会儿,她哈哈一笑,用闽南话对阿雁说:“太个歹学(太难学)!”
顺便说一句,阿雁这个家伙厉害,来厦大上学不到一年,居然能说比较流利的闽南话了。粤军领袖除了家境殷实,智商也不是白来的。
他和珍姐用闽南语聊来聊去,听得我云山雾罩。看着阿雁不停地抖动的嘴唇,在一阵羡慕嫉妒恨中,恨不能把一罐香菇肉酱直接倒进他嘴里。
“你叫什么?”她问。我想逗她,于是神秘地看看四周,然后低头附耳对她说:“我姓穆,叫铁柱。”正在兴高采烈的阿雁闻言一愣,心想这来自北京的胡人,真能胡说。珍姐努力思索着:“穆铁柱?好熟悉。好像在电台听过!”她欣喜万分,觉得见到了名人。
以后见面,她都叫我“小穆”,每次都逗得我哈哈大笑。凭着“穆铁柱”的名声,居然也在珍姐那里多次赊账。
有一次,珍姐夫妇在店铺前和我还有阿雁聊天。珍姐丈夫为我们切了西瓜,又不停地问,为什么北京学生都长得这么人高马大?珍姐也一个劲儿地追问。
我问珍姐和她老公:“你们是吃什么长大的?”珍姐说:“我们从小爱喝稀饭,过节时家里会买地瓜和油条,然后切碎放到稀饭里边吃。”我打趣说:“我们在首都有特供的,每天吃馒头、猪头肉和酸奶。肚子里的料不一样,当然重量就不同。”
记得那次当着珍姐丈夫的面,为了显示力气,我一下把珍姐抱起来,然后扛在肩上,扭头对她丈夫说:“我把你老婆扛走啦!”
把珍姐扛上肩膀,我晃晃悠悠向芙蓉十通往生物食堂的石阶走去,又扯开嗓子,大声开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呀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珍姐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到了北京吃猪头!
在粗犷嘹亮的歌声和一大群学生的哄笑声中,又顺原路把她扛回来。珍姐在我肩上拼命挣扎,红了脸说:“穆铁柱,不要这样!你们都是秀才,不能扛我这样一个小百姓!穆铁柱,不要啊!”
当时就想开玩笑,没想到珍姐被我一扛,竟一下扛到肩上。我心里一愣,心想珍姐一个大活人,身体怎会如此之轻?现在回想,那时艰苦落后的生活水平,让很多家庭不得不节衣缩食,人们无法达到应有的身高和重量。
唉,一个钢镚儿掰两半儿花、从嘴里省吃俭用,我们曾经历过多么艰难的岁月!珍姐丈夫感慨道:“难怪铁柱们个子高大,原来都是吃馒头奶、酸猪头长大的!”
慢慢地,珍姐家买了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就摆在柜台上。
有一次和阿雁去买东西,珍姐恼怒地看着我。我忙问:“珍姐,怎么啦?”珍姐手指着电视说:“我以前听广播,搞不懂;昨天看电视篮球比赛,终于知道谁是穆铁柱啦!你究竟叫什么名字?”阿雁一看机会来了,一本正经地向珍姐说:“他哪里叫穆铁柱?他真名叫西门庆。”
阿雁每月生活费200元,花钱多,赊账也多,还账能力强,是珍姐最大的主顾,因此颇得珍姐信任。
不过,珍姐这次还是有些纳闷儿:“怎么还有姓西的?外贸系有个阿西,总在这里买烟酒,他应该也不姓西。”我开玩笑地说:“怎么没姓西的?西王母,是不是姓西?”“厦大也有叫什么‘西的,原来和西王母是一家!”珍姐感慨厦大名人多,而且能和神仙沾亲带故,真是门第显赫。
她又仰起脸问:“如果有姓西的,那也就有姓东、南、北的啦?”我信口开河:“历史上有东汉、东胡、东吴、东晋,女婿叫东床,太子叫东宫;北嘛——北郭、北岛,天上指南的星星叫北斗;南,就更多了,南霁云、南怀瑾,对,还有南霸天!”珍姐笑道:“南霸天也总来我这里,替阿雁买东西。”
阿雁正在大笑,闻言忽地一愣,心里想,我从没叫阿天来买过东西呀!他是队长,哪有队长给队副跑腿儿买东西的道理?
再想下去,脑袋忽然大了——不好,有套路!
阿雁逗趣说:“珍姐,这世界还有姓‘妈的,你信不信?”
珍姐哈哈大笑:“哪里有这个姓!”
“妈祖,是不是‘妈开头的?”珍姐顿时双手合十,也终于放了心:“那好,以后我就叫他西门庆啦。”
我笑嘻嘻地道:“珍姐,你也要改个名儿,以后我叫你金莲姐。”她欣喜地说:“这个多不好意思。不过,‘金莲蛮好听的,一听就是正经人家的女子!”
叫了一阵“金莲姐”后,阿雁偷偷向珍姐提供了《水浒传》的情报,珍姐终于知道了发生在潘金莲、西门庆和悲惨的武大郎之间的三角爱情故事。
她听得目瞪口呆、柳眉倒竖,有一天趁我不注意,拿了一块西瓜皮,狠狠塞入我的后背衣领。阿雁也趁机对我开战,笑嘻嘻地把半包儿碎花生皮,一点儿不剩地倒入我的衬衫。
唉,這就是粤军的诡计多端。
说回白云山小分队。
那时芙蓉八下面有两兄弟开的一家小店,店主是一高一矮的兄弟俩。虽是一母同胞,却长得相差十万八千里。哥哥高个子,偏瘦,面容严肃,眼睛特别明亮,长得颇像电影《兵临城下》的男主角裘德·洛;弟弟中等身量,圆头圆脑,像一只可爱的胖猫,生起气来也像在笑。
这家小店的哥儿俩没受过什么教育,记忆力和计算能力似乎都不怎么行,再加上听、讲普通话都要先在脑子里费力地翻译一遍,因此被白云山小分队钻了不少空子。
只要买东西超过三样,裘德·洛哥俩就算不清楚。白云山队长阿天第一个发现和了解到这个战场规律。
“老板,买一包大重九香烟,六包火柴,两瓶芬达汽水,三瓶菠萝汽水,还要两包鱼皮花生,四罐香菇肉酱,五包方便面!”
胖猫弟弟顺手把大重九香烟扔了过来:“等一下!慢慢说,我记不住这么多。”
阿雁又凑过来:“老板,四罐香菇肉酱,五包鱼皮花生,六包……不,七包方便面!还有八罐香菇肉酱。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再加六包火柴!”
最后一算账,一包鱼皮花生、两包方便面、三包火柴,其他都买一送二了。
裘德·洛哥俩卖东西不累,可算起账来,立马昏头,累得头昏眼花。大脑似乎供血不足,因此一到晚上倒头就睡。
这天凌晨,又被一阵猛烈敲击铁门的声音惊醒。胖猫弟弟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地说:“不卖东西了,太晚了!”
阿雁带了一帮粤军队员大叫:“老板,快开门!”
“不卖了,已经睡觉了!”
“要买大物件,大买卖!”
裘德·洛迷迷瞪瞪踹了弟弟一脚:“大买卖,快去开门!”
胖猫弟弟挣扎起床,愣头愣脑地打开铁皮门,问:“什么大买卖?”阿雁嘻嘻一笑:“买一包两分的火柴。”
胖猫弟弟怒骂,然后慢腾腾转身去拿火柴。等回过头时,柜台上煮熟的两只鸡蛋,已经被小分队顺到了口袋里。
白云山小分队就是这样,围点打援、声东击西,获得不少战利品。
当然,里面也有立场不坚定的“叛徒”,专门到珍姐那里抄后路,让队副阿雁防不胜防。
“珍姐,拿一包香烟、三包方便面,是阿雁让我来买的,记在他的账上!”
“珍姐,两包饼干、一瓶芬达汽水,记在阿雁账上!”
……
阿雁防不胜防,后来怒火中烧,暴跳如雷。付清别人的欠款后,向珍姐郑重声明:除非本人亲自来买东西或当面赊账,否则以他的名义来购物赊账的,自己一概不认。
有一次,粤军们吃喝过头,一下子把半个月的生活费花光了。几个人瞬间意识到自己成了丐帮,大家面面相觑,发愁明天到哪里去找饭辙。
凌晨时分,白云山小分队在队长、队副带领下,为摆脱没吃没喝的悲惨命运,蹑手蹑脚悄悄摸上芙蓉八的裘德·洛兄弟店铺。趁着夜黑风高,偷偷地拿走铁皮屋外的十个空酒瓶,然后卖到珍姐的杂货铺。
珍姐不明就里,收了瓶子,当即给粤军将士们点了现金。
粤军将士贼不走空,又趁乱哄哄人多,从珍姐店外再顺走几个空汽水瓶子,第二天拿到裘德·洛兄弟商店去卖。
一次得手,再来一遍。
一来二去,芙蓉八那家裘德·洛小店的哥儿俩终于发觉不对了。
这天夜里,白云山小分队又有两名队员悄悄摸了过去,一看四周漆黑无人,竖起耳朵听铁皮屋内鼾声如雷,立即撸起袖子,抬了空酒瓶箱就走。
猛听铁皮屋内传来声震屋顶的怒吼,仿佛晴天霹雳。接着大门爆开,胖猫弟弟变身咆哮猛虎蹿出。与此同时,不知哪里又钻出手拿木棒的哥哥裘德·洛,用钢铁般锐利的双眼冷冷怒视粤军。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裘德·洛兄弟二人一前一后,铁塔般堵住白云山小分队队员的去路。
粤军队员见状,魂飞魄散,扔下箱子就跑。
其中一人,自恃常胜铁军,忘乎所以,这次大意穿了拖鞋,无可奈何之下,眼睁睁叫声“苦也”,被逮个正着。
他被困在铁皮屋内,满头大汗,不停地向怒气冲冲一言不发的裘德·洛两兄弟道歉、忏悔。
阿雁听到消息,急忙领了珍姐过来。
珍姐大步上前,一把推开裘德·洛,然后拿了10元钱塞给他,嘴里问:“够不够?”
胖猫弟弟不依不饶:“要20块!”
珍姐厉声道:“马上到我的小店去拿!另外我关店三天,让利三天给你,只让你一家做生意,够不够?”
她看了一眼那个垂头丧气的学生,叹口气道:“都是没计算好吃喝的孩子,可不可以原谅他一次?”
回到芙蓉十楼下,珍姐突然怒气冲冲,转身打了那个男生一巴掌,骂道:“你们是秀才,不是丐帮!”
她横眉立目:“钱不够,到珍姐这里来借!吃不够,到珍姐这里来赊!还不起,就说一句,算珍姐白给你,阿姐请客!你们是天上的文曲星,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切切不可去偷空瓶!”
她叉着腰,站在那个队员面前:“你也拿过几次我的空瓶子,我都没有讲过!你是要做文曲星,还是要做地贼星?”
那男生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一下子就哭了。一个堂堂的粤军大老爷们,羞愧得上气不接下气。
事后,阿雁从家里寄来的生活费里,拿了20元钱给这位广东“难友”,算是周济,也一次性替他还了欠珍姐和裘德·洛兄弟杂货店的钱。
接着,阿雁又替其他粤军队员还债,总计一百七八十元。
之后一个月,阿雁天天去吃宗阿伯的稀饭咸菜。大概因为膳食结构不合理,营养失衡,据说吃粥到月底,走路都打晃儿了。那个月一定是吃粥吃伤了,所以现在的阿雁,虽然目如朗星,却是头顶锃亮,当年肯定是伤到头发根儿了。
那名哭成泪人的白云山小分队队员,后来则成了羊城的著名商人,为人处世极其诚实守信。据说当年的粤军队员们毕业后,再回到厦大珍姐和裘德·洛的商店,都是不问价钱,随便买一堆,东西也不拿,然后放了厚厚的钞票就走。有良知、有良心、有情怀,粤军铁军,名不虚传。
毕业多年后,阿雁已成为南方某著名企业的老总。有一次他到厦门出差,走在镇海路的骑楼老街上,一家路边小杂货铺的老太太奇怪地看着他。他没在意,带着秘书和一群下属,继续大步流星向前走。
瘦弱的老太太忽然颤巍巍上前一把拉住他:“阿雁,你回来啦?”她站在自己的小铺前,慈祥地端详着阿雁,然后爽快一笑:“这20年过得怎样?成国家栋梁了!来,喝瓶冰镇汽水,阿姐请客!”
西裝革履的阿雁,定睛看着面前的老太太,顿时热泪长流……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那年,海风吹过厦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