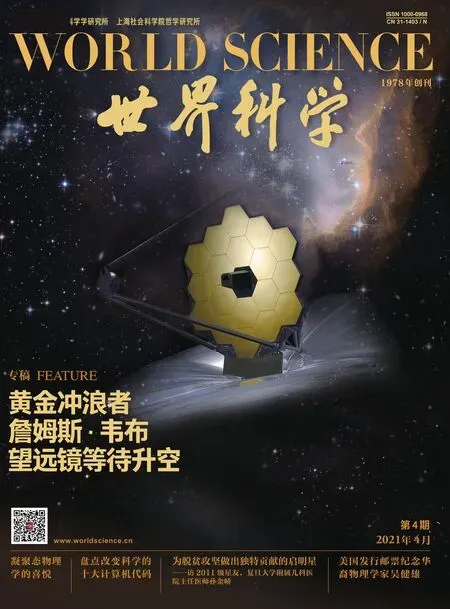福岛事件十年,核能何去何从
编译 李军平

2020年中国工业展览会上,参观者通过增强现实头盔观看核反应堆模型
10年前,威力巨大的地震与海啸摧毁了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引发了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
此次事故发生时,人们对新一轮核能技术以及它们在实现低碳未来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抱有新的希望和未经考验的乐观情绪。事故发生后,人们重新认识到核基础设施的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脆弱性,以及在设计、管理和操作这种复杂系统时的易错性。
灾难发生十年后,尽管气候危机越来越近,但这些严重问题依然存在。
许多学者认为,如果地球要限制全球变暖,核能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是,鉴于可能产生的环境及社会问题,许多人对核能非常谨慎,甚至持反对意见。在2018年发布的全球变暖特别报告中,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承认,核能在遏制全球气温上升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又强调,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在促进或阻碍投资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
安全与成本是核工业面临的主要挑战。虽然新的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新型反应堆可能在21世纪中叶方可实现商业化。但这个时间太过久远,随着太阳能与风能(加上储能技术)等竞争技术的兴起并占据优势地位,届时这类新的核技术很可能过时。
我们认为,一个更大的问题迫在眉睫,即核部门长期以来做出技术和政策决定的不透明、不对外和不公平的方式。因此产生了两个关乎核能未来的关键问题:第一,核工业能否克服公众的反对意见?第二,其收益是否超出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与成本?
核工业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向前发展。这将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观念,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更负责任和更具前瞻性的核工业。
为何会发展至此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核能发展势不可挡。政策制定者与开发商预计,核能将“太便宜而无法计费”。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三里岛(1979年)和切尔诺贝利事故引发了强烈的反核情绪,加之施工成本上升和政府补贴减少,核能投资急剧下降,发展势头长期停滞。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世纪70年代预计:到1990年,核能将达到430 GW的发电量,或世界发电总量的12%;到2000年,核能将达到740 GW~1 075 GW的发电量,或全球发电总量的15%。实际上,到1999年,核能仅达到预计(2000年)的1/3,为308.6 GW。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核能复兴的期望开始出现。到2010年之前,兴起了一股核能建设热潮。
福岛事故为这股热潮泼了冷水,加之其他经济与政治因素,导致许多国家的核工业综合体解散。福岛反应堆事故4个月后,德国议会投票决定逐步淘汰核能设施,以2022年为最终期限。瑞士内阁也紧随其后,要求国内5座核电站退役。事故发生时,日本共有54个在运反应堆,有12个随后永久关闭,目前共有24个处于关闭状态。
福岛事故后,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审查了核电站的运行情况。虽然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安全问题,但美国仍在继续使用核能。一些国家开始重新使用核能或制定重启计划。
目前,有16个国家正在建造约50座核反应堆。中国的数量最多,共有16座核电站在建,印度与韩国紧随其后。根据《世界核工业现状报告》,截至2021年2月底,全球32个国家共有414个核电反应堆在运行,占世界发电总量的10.3%。总体而言,核能一直在缓慢发展,但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许多人认为核能是解决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该观点的核心是新技术在持续发展。以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为例,每个机组的发电量不到300 MW,足以为20万个美国家庭供电。这一发电规模减少了发生灾难的可能性,而标准化的设计将大幅降低成本。
目前,美国一些水冷式SMR在接近商业应用。2020年,俄勒冈州蒂加德市NuScale公司的设计方案率先接受最终安全评估;第一个SMR发电站计划于2030年在爱达荷州建成;其他公司正在开发更高效、更安全的新一代(第四代)反应堆,其中大多数依赖于冷却剂而非水制冷。但第四代技术距离实现商业化仍有较长时间。

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社会参与
核能的发展历程波澜壮阔,但是,核能的支持者仅强调其技术与经济特质,忽略未解决的道德伦理问题。支持者未能考虑:核技术的利益与风险在当地、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分配不平衡;他们也未能考虑,谁被排除在核能建设的决策过程之外,谁受核问题的影响最大。
例如,全球近3/4的铀产量来自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的土著社区或附近的矿场。这些矿场在使用后未得到修复,污染土地、毒害人民,并颠覆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由于核废料的长期储存库通常远离核电受益的社区,核废料的处置同样会产生权益不平衡问题。考虑到现有的技术解决方案,核工业经常提出废料储存问题。对于核废料在哪里和如何储存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国家提出了“绿色新政”,明确了对财富再分配、社会公正及环境公平的渴望。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出现了相关讨论,公众对核能的支持参差不一。
核工业一直未能针对这类问题与公众进行有意义的接触。这种不接触的做法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的风险心理学研究认为,公众在风险评估中易情绪化、不够理性且无视概率。因此呼吁核工业,要么接受公众的风险意见并按此设计,要么为公众提供核能教育。
核工业选择了后者,即通常只在工厂监管的最后阶段让公众参与,并使用业内的风险观点对公众进行教育。这是一个将灾难与后果概率相乘的简单方程,但忽略和忽视了公众的视角。例如,许多人愿意接受自愿或熟悉的风险——如飞行、吸烟或开车——而非不熟悉和无法控制的风险。对于非自愿风险活动,大多数人往往不强调概率,并要求保障其舒适性和安全性。
核工业与公众接触的模式导致了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对立和分歧。例如,福岛事故在公众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核工业一直在淡化这场灾难的后果,强调其未造成任何直接人员伤亡。事故的确未直接造成人员死亡,但民生、社会关系的损坏和生态系统不可逆转的破坏是巨大的。据估计,有16.5万人流离失所;10年后,约4.3万居民仍无法返回家园。行业风险评估仅强调这类问题的经济影响,但却无法估计其对人们生活和环境造成的难以量化的损害。
公民需要参与从铀矿开采到废物管理的全过程,而非简单地说服。
不同的道路
当然,不平等的环境与社会负担问题绝非核工业独有。例如,利用可再生技术开采锂矿和回收电子产品也涉及这些问题。但其他行业在公众参与方面做得更好。其他工程领域早已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例如,太阳能电池板开发商一直聚焦于终端用户的真正需求,这样的讨论导致半透明的太阳能电池板——使农民可以在下面种植作物,开辟“农业光伏”新领域。
核工业在推行技术民主化的过程中面临特殊障碍。大型核反应堆并不适合社区所有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模式。不过,不要低估人类思维的创造性。例如,2019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反应堆创新中心一直在研究可能拥有先进反应堆的地方社区如何看待风险。
新一代的设计者——包括一些受美国能源部核能办公室资助的初创企业——一直在了解公众支持什么类型的反应堆。福岛事故殷鉴不远,这种交流有助于设计者以创造性和定性的方式思考安全与风险问题。一些设计者声称,已经发明了不会使堆芯熔化或释放大量放射性的反应堆。
我们并非要求公众成为核反应堆的共同设计者。但在前期设计过程中,外行人对风险的认知应当为反应堆安全系统、应急计划程序以及复杂系统中人类机构和临时处置的作用提供信息。当然,公众在决定在哪和如何建造反应堆等问题上必须有发言权。
更为包容的未来
长期未能与公众进行有意义的接触也导致了“监管俘虏”的出现,即管理机构更倾向核工业的利益。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这种情况只在制度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地方都存在这一现象,只是程度不同。
例如,人们普遍将日本核安全局被核工业“俘虏”视作福岛事故的制度原因。即使是在被视为核工业发展典范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制定商用核能战略规划的私人实体也可以向该国的核监管机构提出建议,这显然构成了利益冲突。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几个拥有成熟核工业的国家正在成为全球核技术的供应国。在治理薄弱的国家(包括尼日利亚、越南和沙特阿拉伯)推行核计划应谨慎从事。我们并非在质疑这些国家是否有权发展核能,而是质疑其是否做好了准备。支持这些国家发展核能应当以制度建设而非签署技术销售合同的形式提供支持。不幸的是,监管机构往往缺乏关注和资源。
在全球各地,核能立项决策往往由小部分政治精英做出,他们未进行任何真正的需求评估,不了解核能如何适应国家的整体能源政策,也不考虑公众对核技术及其风险的意见。核电企业通常认为,新的核电采购国不会投入资源进行技术研发,也无意如此。因此,核能的采用似乎是人为的,是核工业渴望获得利润和市场主导地位的刺激,而不是集体应对气候变化等社会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
若使核能在深度脱碳事业中发挥关键作用,排除在设计、开发和决策过程之外的公众意见必须拥有一席之地。
资料来源Nature
——数字反应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