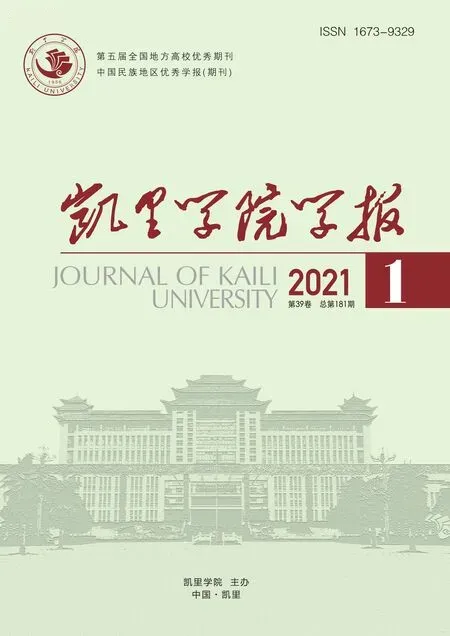论感觉作为历史人类学的新路径
——以贵州东南的“盐香”与酸辣为例
(凯里学院,贵州凯里 556011)
在人类学的第一个百年(1870-1970)里,历史是缺位的,尽管也有着埃文斯-普理查德等人类学家在呼唤历史。20 世纪70 年代前,人类学集中研究“冷社会”,这些社会保持着千百年不变的传统,当地人的过去与现在“大同小异”,外加史料、文字的缺失,均是造成人类学家历史缺位的可能因素。20 世纪70 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人类学家关注的“冷社会”被发掘殆尽,人类学开始转向关注“热社会”,后者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激烈的变化,甚至传统意义上的“冷社会”也因为全球化而发生激烈变化。那么,历史或变迁就成为人类学家不容忽视的研究维度。20 世纪80年代历史人类学滥觞,“人类学如何切入历史”随即成为历史人类学探索的方法论命题。
以中国为例,至今历史人类学切入历史的方法至少有两种。第一是正史。与西方人类学的语境不同,中国有着一个强大的历史记录与史料研究传统。从正史文献切入,是历史学家的强项,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田野必不可少的一环。第二是民间文献。中国不仅有着强大的正史传统,更有着强大的文字传统。民间文献(如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等)就是后者的体现。历史人类学家遇到这些历史材料,如何呈现其“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上的意义”[1],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承袭宏观、整体的视野;另一方面要更加贴近历史主体的生活与实践。在清水江耕耘20 载的张应强教授倡导: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历史中不同个体和群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agency);另一方面要将人类学擅长的田野调查和历史学擅长的文献解读辩证结合:在田野中解读文献,在文献中深化认识田野[2]。
感觉作为历史人类学切入历史路径的可行性,在于感觉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推进。自20世纪70年代起,Walter J.Ong等学者就开始注意到民族志在方法和书写上的视觉中心主义(visualism)倾向亟待反思[3],这一反思提醒人类学家从视觉之外的其他感觉去认识自己的田野调查和书写路径。1982 年,Steven Feld 带来了第一部感觉研究的民族志文本——Sound and sentiment(《声音与情感》)。该书的研究对象是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丛林中的Kaluli 人因为视觉范围的限制,听觉高度发达。作者从听觉去理解该文化的审美、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乃至世界观[4]。1997年,Constance Classen 发表Foundations for an 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5](《感觉人类学的根基》)一文,标志感觉人类学正式成为人类学的重要视角。Sarah Pink 留意到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感觉转向”(sensory turn),倡导人类学家将感觉带入到民族志实践中来[6]。中国学者同样也注意到,视觉之外的感觉在我们的实践中往往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如朱晓阳提醒我们,到在讨论社会空间的时候,“不可以忘记声音是十分重要的‘世界看法’,没有这些叙说声音的存在和弥散,小村人的生活世界和社会空间等将无法获得真正实现”[7]。
以味觉为例,既有研究已经足以表明其关联到人们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Harris Solomon通过印度孟买比萨的制作与消费发现口味和食物的选择不仅关乎人群的分类,而且关乎政治,造就出一种所谓的“肠胃政治”(gastropolitics)[8];Viktoria von Hoffmann 通过法国近代早期的儿童教育的分析,认为味觉与美学、原罪(sin)、教育和进食礼仪纠缠在一起,共同对儿童的身体(body)进行规训[9]。张文义通过景颇鬼鸡的民族志呈现出,景颇人和我们能都体验到的酸辣口味的鬼鸡,但在景颇人那里,“鬼鸡是性别和年龄分化的标志,也是人神的分界和连接”,景颇人吃鬼鸡吃进了“一个世界的想象”[10]。肖坤冰从福建武夷山的景观入手,分析了当地“正/外”的想象空间结构,后者是建立在味觉、环境、历史、身体、生计和市场等互动基础上的[11]。总之,可以味觉不仅仅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我们可以借其探讨“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合一”[12]。
从感觉切入,不仅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文化,还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历史。日本学者井口淳子①井口淳子等人从听觉书写了西北杨家沟的文化和历史,参阅(日)井口淳子,深尾叶子等:《黄土高原的村庄——声音、空间、社会》,林琦、朱家骏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中国学者陈春声②陈春声从樟林人的“份”的感觉解读了当地的信仰与社区历史的演变,参阅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杨念群③杨念群对于感觉与历史的探讨更为深入,可参阅以下文章:杨念群:《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读书》,2007年第4 期;杨念群,雷天:《“感觉”历史——杨念群访谈录》,《博览群书》2007 年第8 期;杨念群:《提倡“感觉主义”的若干理由》,《中华读书报》,2007-05-16。等人探索,均表明了从感觉切入文化及其历史这一路经的潜在价值。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本文旨在结合感觉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探索味觉和历史的关系,以此为基础阐述感觉作为历史人类学切入历史的可能路径之一。
本文的田野材料来自贵州东南,主要的田野点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南加镇柳霁(又为柳基)村,位处清水江中游。柳霁一带是汉苗侗杂处的区域,历史上这一带还是“生苗”与“熟苗”的交界之一。乾隆元年(1736 年)清廷在柳霁设县丞,隶天柱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撤柳霁分县。2013年7月至2015年10月,笔者在柳霁累计完成了13个月的田野调查。
一、“盐香”:味觉里的历史
在我们的味觉体系里,盐之味非常特别。稍增一分会被冠之以“咸”,稍减一分则谓之“淡”。一道美食,一般情况下盐之味应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一旦其被品尝者提出来,那就意味着该食物的美食身份将遭到严重质疑。但是当盐味总是被贵州东南的人们提及而且是以“盐香”①凯里学院研究苗语的唐巧娟博士认为:“苗语中找不到直接表达‘咸(味)’的词,而是通过ghangb xid(香盐)或dliut xid(味重)来曲折表达。可见,于苗族而言,‘咸’本身就是一个陌生的味觉概念,是盐传入后,随之产生的味觉概念。注:苗语中,dliut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味觉词,泛指一切较重的味道,也可以表香甜味,也借用来表咸味。”的形式提及时,就颇值我们的思考了。其至少提醒我们留意盐味在当地文化甚至历史中的特殊性。在贵州东南,与盐味相对的味觉是酸。历史上,酸在这一区域扮演着盐的替代者角色,同时它又可以用作为人群划分、价值取向的“区划者”(如后文提及的“酸汤苗”)。也就是说,从“盐香”与酸汤交织与纠缠中,我们可以重新窥探贵州东南(由于贵州苗疆大部位处贵州东南,后文会根据具体的语境在“贵州东南”和“苗疆”之间切换使用)的文化与历史。
在今天贵州东南汉语方言的日常用语里,“盐香”“盐咸”是一个餐桌上的惯用词,“咸不咸盐”“香不香盐”(即“盐咸不咸”“盐香不香”)是当地人们评价一道菜的重要指标。今天柳霁人的饮食仍以“盐重”著称。
2015年6月23日傍晚,柳霁北门,七八个人坐在房东家小店外“款门子”(闲聊)。他们无意间扯到吃盐这个话题上来,于是谈到了一位嗜好独特的人——新台(柳霁邻村)已故的龙家大爷。其“(生前)每餐吃肉的时候要拿到盐碗里像蘸白砂糖一样蘸盐吃”,去世的时候80多岁。
龙家大爷的案例毕竟是极端,但现在柳霁40 岁以上的人,每天的食用盐量依然比较突出。在我的田野过程中,我和房东夫妇共3人,平均不到1周就要1包盐(250克)。“平时我和你大哥两个人在家吃饭,一包盐才够吃七八天”。房东太太春桃说。但若以此量化每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并不可取,因为每餐剩下的汤菜会有相当一部分倒在猪的食槽中。对于饭菜的口味,柳霁人常说“辣子要辣,盐要咸,药要苦”。就连春桃自己也觉得柳霁人“吃盐多,口味重”。当我在其他村(包括汪泽、新柳、芳武、天培等村)吃饭时,主人家首先问的往往不是饭菜的味道如何,而是问“咸盐没”,生怕盐放得不够!
甲:“那些年(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菜里盐不够,会被人拿来开玩笑。款门子(闲聊)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在某家吃饭,盐都舍不得放。”
乙:“老一辈人缺盐缺老火了,说‘要想吃上盐,除非过大年’。不像现在,随便你吃。”
丙:“那个时候(民国)吃的是颗颗盐,就像现在的冰糖块一样。丢在锅里煮菜,菜吃完了盐还在。”②2015年6月23日,田野日记。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历史上所有的柳霁人都像这般嗜盐。仅仅是那些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人们(经历了从极度缺盐到盐充裕低廉的时代)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共餐),会对盐之味有特别嗜好。在新中国成立前,即便大户人家,这样对盐味的嗜好是不会被容忍的。“以前要是一家都像现在这样吃盐,用不了几年(家)就败完了”,参与闲聊的“老八”说。
今天年轻一代开始接受来自电视、手机等媒体和医生的建议——少吃盐才是健康的饮食方式。房东家的大女儿婷婷在贵阳医学院求学,假期回家每天都会帮着准备一家人的饭菜。“每次我下盐的时候,婷婷都会伸手来拉我,让我少放点(盐)”“盐吃多了真的不好。”春桃说。但其实有几次在用餐的时候,我看到婷婷的父亲偷偷往菜里加盐:“菜要香盐,吃了才有力气干活。”他解释说。
柳霁老一辈的人们对于盐味的偏好与盐在贵州的历程密切相关。至少是在1949年之前,盐对于苗疆乃至贵州来说,一直都非常缺乏。
历史上,贵州几乎不产盐。之所以言“几乎”,是因为一些材料显示,贵州并非完全不产盐。如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贵州曾发现了几处盐井,并开始“试煎”。“贵州……至于盐井,共得数处,现试煎一井,已有微效”[13]185。
台湾学者姜道章的研究也显示,贵州有一些零星的产盐点,但没有盐场[14]5。很可能是贵州盐的产量微乎其微,因此相当一部分研究盐的学者都直接断言“贵州素不产盐”。而历史上贵州交通又极其不便,使得盐味的缺失在苗疆的味觉地图里格外突出。
18 世纪30 年代,西南的封疆大吏鄂尔泰对此就深有体会。后来在其主持编修的(乾隆)《贵州通志》中载:“黑苗在都匀之八寨、丹江、镇远之清江、黎平之古州……艰于盐,用蕨灰浸水。”①(清)鄂尔泰等修:《贵州通志》(乾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卷七,苗蛮,十四。
大约20年之后,时任贵州巡抚爱必达在撰写《黔南识略》时也留意到,在苗疆,无论是苗人还是侗人,饮食里几乎没有盐,“(思州)府南有洞人,约五六百户,……饮食避盐酱”②(清)爱必达:《黔南识略》,道光二十七年罗氏刻本,卷一八,思州府条,五。“高坡苗……食蔬菜少用盐,以草灰滤水代之”③(清)爱必达:《黔南识略》,道光二十七年罗氏刻本,卷二三,开泰县条,八-九。。
19 世纪70 年代,随着湘军进入贵州镇压咸同苗民起义的徐家幹,也见闻“苗人席地而食,菜不加盐”[15]的现象。
尽管今天清水江两岸盐的供应早已不是问题,但曾经(新中国成立以前)盐的稀缺依然存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并具身化到(embodiment)经历了从稀缺到充足的两三代人的味觉偏好甚至身体中。或者说,文化将这一历史过程“烙”在人们的身体部位、口味嗜好中。最极端的例子是20世纪50 年代以前,盛行于这一区域的地方病——“大脖子病”(俗称“大颈瓜”,患者不少,一度成了生苗的习惯病[16]132)。尽管这一病变在今天贵州东南已经匿迹,但仍可以视为缺盐的历史嵌入当地人身体的一种极端体现。这也意味着,历史可以从其身体及其具身化现象中被解读出来。
历史上,4种盐分别从4条路线入黔:最早是西路滇盐。滇盐主要沿着滇黔驿道进入黔西,这一路盐对苗疆的影响甚微。北路川盐主要沿赤水河至遵义、贵阳、都匀等地,后在清代又流入贵州东南的镇远等地;东路淮盐在明代入黔,主要沿长江逆流而上进入贵州东南。道光《大定府志》载:“我朝定鼎以来,(大定府)分食淮盐川盐,惟康熙中普安有改食滇盐之举,旋即复旧。……贵州各府,近湖广者食淮盐,近四川者食川盐。”[17]
此外还有一条被忽略的盐路:南路粤盐。其主要沿着珠江上溯至都柳江,行销于古州(今榕江)一带。粤盐入黔相对较晚,规模相对川盐淮盐要小得多:雍正十年(1732年),广西巡抚金珙奏请官运粤盐至古州丙妹、三角屯试销[13]244。粤盐入黔的尝试随即展开:“粤西委效力吏目刘士龙押运生息食盐五百包赴古州试销,是年九月又奉拨粤东盐一封,委运商俞文耀领运古州试销。”[18]雍正十一年(1733 年),黎平府知府滕文炯在古州(今榕江)丙妹、来牛、三脚屯三处设盐埠。粤盐自此进入苗疆。
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苗疆川盐、淮盐、粤盐三足鼎立。民国时期的剑河县(原清江厅)可谓其缩影。(民国)《剑河县志》记载如下:
在抗战前,本县食盐供给有三路焉。
一来自榕江,名为西砂,係由粤西贩运,故又名粤盐。其盐杂质太重,非经煎熬或沉淀不能食,且味不甚咸。
一来自湖南洪江,名为东砂,有远运自淮水者,故又名淮盐。色微红质洁净,其味高出西砂一等。
一来自平越鸡场,为川盐,因其状成块如石,又名岩盐。味较东西砂为最,苗胞尤酷爱之,倾销最广。年约销六十余万觔④阮略纂修:《剑河县志》,民国三十四年,卷六,党务志,四九,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
盐进入苗疆后却长期稀缺。伴随盐的稀缺加剧了人们味觉上的紧张关系,这种张力反过来,会赋予盐不同的社会身份或社会生命(见后文),甚至卷入到帝国与边疆的关系当中。换言之,当盐的味道随着市场和人群流入到苗疆后,国家权力也随之逐渐渗透进苗疆人群的味觉中。这还意味着,当缺盐的苗疆与中央王朝关系紧张时,控制于中央手中的盐就会成为帝国的一张王牌。
我们知道,不到万不得已,国家一般不会使用外显的暴力来彰显其统治,而是通过一些微妙的控制来实现这一目的。在清代苗疆,这种微妙性一度体现为对盐的控制。农业中国的统治者很早就发现人类味觉对盐的依赖性,他们将皇权、赋税与人对盐味的依赖捆绑在一起。因而,盐的生产与运销一直为中国历代王朝国家所悉心经营。其关乎民生,更关乎国本。在苗疆,外来的可被控制的盐一度被统治者尝试转化为统治利器,以彰显皇权的在场。
雍正三年(1725年),开辟苗疆的前夜。贵州巡抚石礼哈数次上疏雍正皇帝,请求将苗疆纳入帝国版图。石礼哈的策略是:先调集军队,镇守苗疆通道和关卡;再禁止盐流入苗疆,以盐为武器,从味觉上让苗疆的人们体皇恩,知帝威。一二年后,若苗疆仍不归顺中央王朝,必因盐的缺失导致苗疆内乱,此时再挥军围剿,武力征服。①石礼哈的策略被雍正归纳为:“先调兵驻防,堵截前后去路,并禁通盐货,断绝必须之物……一二年后,不受招抚,则调集四路兵丁,捣其巢穴”,并问询云贵总督高其倬的看法。(见(雍正)《殊批谕旨》第45 册,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高其倬奏折)
在清王朝的贵州巡抚石礼哈的眼里,盐是一种武器,可以用来威慑“山野小民”,可以赁其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导致不被统治的山民的味觉紊乱,并促成其内乱。尽管他的策略被暂时否决,但其思路却从未被忘记。而在其后各次大规模的苗民起义中,清王朝均在试图禁止盐流入叛乱区域,“以加速苗民起义运动的失败”。与此同时,“叛乱者”也在极争取私盐的进入和寻求盐的控制权②咸同苗民起义时,张秀眉攻下清江厅后,最先采取的策略就是恢复清江厅市场,拉拢汉人盐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贵州省编辑组编:《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三)》,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正如姜道章指出的,盐从来都是“革命人士、土匪及不满分子组织的直接目标”[14]1。
贵州巡抚石礼哈的提议,是试图把盐当作王牌,尝试在味觉里征服苗疆。但在今天看来,他似乎并未考量到历史上苗疆人群的味觉体系及其能动性(agency)。
二、酸与辣:味觉塑造的历史与文化逻辑
历史上,面对无盐的困境,苗疆的人们一直在寻求盐味的替代方案,并形成了独特的味觉文化。一种策略是以辣味代替盐味。这一策略是在明代辣椒传入中国之后才开始践行的。康熙时期编纂的《思州府志》也有类似记载:“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19]乾隆时期撰写的《黔南识略》载:“海椒,俗名辣子,土人用以佐食。”③(清)爱必达:《黔南识略》,道光二十七年罗氏刻本,卷一,总序,十六。在《四川盐法志》中,贵州少数族群不仅通过辣味来代替盐味,还有酸味。
黔省地瘠民贫,夷多汉少,夷民食盐在可有可无之间,家道稍丰者向商贾买盐以资食用,其穷夷则概食山菜所酿辛酸之物,或曰辣子,或曰酸菜,竟不食盐。④光绪《四川盐法志》,卷10,《转运·元展成疏略》。
辣椒是晚近才传入中国的,因之,味觉里以辣代盐也是比较晚近的事。那么,在辣椒传入中国以前,贵州的“山野小民”因应缺盐的策略是什么呢?
“以酸代盐”。在辣椒传入苗疆后,出于调味的需要,苗人逐渐发展出了以酸辣为主的饮食风格,后者以“凯里酸汤”为代表。侗人的饮食风格也有酸辣的特色,如“启蒙酸菜”、腌鱼(又称酸鱼),此外还有以“瘪”(以牛或羊的粉肠肠液、胆汁调制出的侗族特色饮食)为代表的饮食。历史上的贵州东南的汉人移民,在盐的稀缺这一问题上,也并不比周边的少数民族好太多,因此他们也会食酸。田野调查中我的房东太太(汉族)每年春季采来的野菜,出去鲜食部分,都会用来腌制成酸菜。
每年春季到坡上采集野菜,主要有蕨菜、鱼腥草、水芹菜等。以蕨菜为例,将新鲜蕨菜洗净,放入开水锅中煮至半熟,取出冷却后切成合适大小,以糟辣椒搅拌均匀(也可根据个人喜好放入生姜片、煮半透的稀糯米等),盛入坛罐中密封。二三日之后变酸即可食。此外她还会腌制酸青菜。每年冬春交替时,园子里种植的青菜长出菜薹之时,将其整株采回洗净后切碎。加入炒熟的糯米,野生“小苦蒜”的根部、新鲜的生姜片和辣椒面等,以双手用力搓揉至充分,晒至半干后盛于陶罐中,密封1个月左右即可成酸。类似的做法在嘉庆年间的《黔记》中有记载,区别是后者用的是白菜:“黔人好食臭腐物,每岁三月,洗白菜,铺巨桶中,加以小米,层菜层米,满则以巨石压之。至五月始开,气极恶,沸汤食之,颇以为美也。其汁治泄泻痢疾甚效。土人呼䤃菜。”[20]
对于高坡的苗人来说,他们制作的酸则显得尤为独特:蒸饭之前以较多的冷水煮米至水开,然后控米——用筲箕或其他器具滤下米汤;将半生的米转入甄中开始蒸饭后,滤下的米汤放置降至常温,然后倒入用于专门酿制米酸的坛罐中,加盖密封,经过三四天的发酵,即可食用。储酸的坛罐尽量不要摇晃,不可倒入热水。每餐可以将冷却的米汤加入,以保持常年食用。若不满意味道,可将储酸罐清洗重做。烹制酸汤之前先将适量的清水倒入锅中,然后从罐中舀入适量的米酸(使用的瓢忌油腥)调味至自己喜欢的酸度。往锅里放入自己喜欢的蔬菜,如豆芽、莲花白、小白菜、嫩瓜、嫩豆、“毛辣果”(樱桃番茄)等,最后放入些许木姜子再一次调味即可。因为是以米汤作为酸汤的主料,其又被称为“米酸”。前文提及的“凯里酸汤”即属此类。
相对而言,“米酸”应该是较早的“苗疆酸”。明清以后,番茄和辣椒传入中国西南,苗疆开始制作“毛辣酸”和“糟辣酸”。
毛辣酸:挑选合适的“毛辣果”(樱桃番茄),洗净后捣烂,放入干净的坛罐中,加入适量散装的白酒,密封保存,发酵月余即可。因为这种酸汤相对于米酸颜色鲜红,故人们又将其称为“红酸”,而将米酸称为“白酸”。在黔东南有这样一种说法,“白苗红侗”。苗家喜“白酸”,侗家爱“红酸”。
糟辣酸:每年秋季红辣椒采收之后,将红辣椒处理干净切碎,与糯米、姜丝一起舂,最后再将洗净的“毛辣果”(樱桃番茄)放入舂烂,混合充分后装入干净的陶罐,然后密封。根据气温,快则七八天,慢则半月即可发酸食用。
除了蔬菜可以䤃制成酸食之外,苗疆的少数族群还会将鱼、牛等肉食䤃制成酸食。今天黎(平)、从(江)、榕(江)一带的侗族尤爱䤃鱼,并以此为待客上品。腌肉的做法可以追溯到鄂尔泰主持编修的(乾隆)《贵州通志》:“(仲家)歛牛、马、鸡、犬骨,和米糁和之,作醅至酸臭为佳,称富积者,则曰贮䤃桶几世矣。”①(清)鄂尔泰等修:《贵州通志》(乾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卷七,苗蛮,十。
20世纪30年代,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做田野调查时,就发现了苗家“以酸代盐”的现象。
苗人的喜食酸味,当非生性好酸辣,或因……无盐……在无盐的时代,只有多食酸辣以促进食欲,累世相传,至今虽有盐,但仍保存好食酸的特性[21]。
此后,民国遵义人郑珍编的《荔波县志稿》中也持此观点:“诸苗……鲜食盐,淋灰水浸肉而食,或以牛豚等骨用水浸,俟其酸臭以当盐。”②郑珍:《荔波县志稿》,(见贵州省文献委员会编《贵州文献季刊·第5期》),1949年,第11页。酸、辣与盐味的关系展现了感觉(或味觉偏好)贯穿了一段历史并呈现在当下。兵燹、灾害、迁徙等因素会导致当下的人们在其集体记忆中找不到过去,但是感觉却跨越了人的主体性呈现出主体间性的特质——它在不同时空下不同的主体之间流动。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可能摆在了我们面前:用感觉来架起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桥梁。凌纯声、芮逸夫、郑珍“以酸辣代盐”的观点得到了后世学者的普遍认同。但“辛以代盐”“以酸代盐”绝非是苗疆人群因应无盐的全部策略。
另一无盐的因应策略是以蕨灰或木灰代替。清代贵州的地方官员和文人留下了不少记载,如余上泗《蛮峒竹枝词》①余上泗《蛮峒竹枝词》:“银圈压项耳垂琐,饭里团糯糯米香。盘有山蔬频苦淡,蕨根渍水代盐尝。”见〔清〕黄宅中修:(道光)《大定府志》(二)(收入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9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道光二十九年刻本),卷五十八,第130页。、蒋攸铦《黔阳竹枝词》②(清)蒋攸铦:《黔阳竹枝词八首》有“醅菜珍同旨蓄藏,无盐巧用蕨灰香”之语,见(清)蒋攸铦《黔轺纪行集》,附于贵州古籍精粹《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点校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7页。、毛贵铭《黔苗竹枝词》③毛贵铭《黔苗竹枝词》有“莫厌蕨灰少咸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语。后注“食少盐,以蕨灰代之”。见潘超,丘良任,孙忠铨主编:《中华竹枝词全编(七)》,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第71页、第72页。等均描述了这一因应策略。20 世纪40 年代,大夏大学的陈国钧仍见贵州生苗:“并不知道吃盐,只拾些山上的树枝烧成了灰,再加水使它沉淀,水内便含有咸味,这即是生苗代盐的方法,一直至今还有大多数人吃这种灰咸水。”[16]13020世纪80年代,翁家烈的《剑河县苗族调查》中仍有在新中国成立前,剑河苗人“用杉木灰汁做盐”④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调查(之四)》,1986年,第427页。的记忆。在今天凯里三棵树一带的苗人祭祀过程中,当人们烹煮祭品时,“拿盐来”往往表述成“拿木灰来”(Dad ghad hxud dax)⑤感谢王金元老师(凯里三棵树人,苗族,现任教于凯里学院)的分享。。这些材料存在着某种一脉相承的特征,或正好说明苗疆人群“以灰代盐”的因应策略。
在苗侗等少数族群的文化逻辑里,酸又有着别样的意义。酸是美味之源,在柳霁下游锦屏一带的侗家,流传有“酸鱼煮豆腐,菜好饭遭殃”的说法。其意是指酸汤鱼煮豆腐,特别开胃,让人饭量大增。酸是力量之源,汉人形容苗人“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其意是说苗人爱酸,三天不吃,路都走不稳。在苗族神话里,苗人的先祖姜央和雷公斗智,成功将雷公困在一个仓内。失去了法力的雷公在姜央外出后,便逗姜央的孩子玩,趁机央求孩子给他喝点家里的酸汤水:
Hxid maix eb wat dot, 看看有没酸汤水,
Mongx dad lol diot ghet, 若有给我拿点来,
Dad dax eb wat niat, 酸汤已经拿来了,
Dad dax diot ghet ngit。 拿来给公看一看。[22]
雷公喝了酸汤之后,立即重获法力,破仓而出。放眼苗疆缺盐的历史,苗人通过酸获得力量或许是一种历史的隐喻:没有盐,酸也可以调味。但苗人对于酸则有着非正面性的体验和判断。
苗疆的酸如此特别和突出,渐渐成为人群区分的标准(当汉人大规模进入后)。在柳霁下游的天柱一带,有群人因讲话汉苗夹杂难分,他们说的话被称为“酸汤话”,他们因之被称为“酸汤苗”。在清水江流域的汉语日常用语中的“酸”,有着微妙的意指。当我的一位苗族同事在天柱做田野调查时,当地的“酸汤苗”称他讲话“带酸”。这让他纳闷万分:“本来他们就是酸汤(苗),居然还说我讲话带酸!”他认为在黔东南,当人们说你讲话“酸”的时候,多少带有一分排斥、鄙夷的意味。而“酸汤话”,很可能就是在清水江频频流动的人群交往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凯里三棵树苗家的婚嫁观念里,有一种传统的理念,希望女儿嫁给“尤修”(yus xed)一类的男人,以免吹风淋雨过苦日子。yus 是指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xed 指老虎。特别不愿意让女儿嫁给那类被称为“巴虐欧修”(bad nios eb hxub)的男人,bad 是男人之意,nios 一般不单独使用,有“花脸”之意,eb hxub 即酸汤。yus xed 与bad nios eb hxub 直译分别为“虎男”与“酸汤男”。姑娘嫁给“虎男”,吃穿不愁;姑娘若嫁给“酸汤男”,则只能天天喝酸汤,甚至还要去为一家人遮挡风雨,意味着后半生的辛苦和操劳。①讲述人:王金元,苗文记录人:唐巧娟。时间:2017年3月4日,在此一并感谢两位老师。
在贵州东南少数民族家里做客,他们会在开餐之前谦虚地说“不好意思,拿酸汤来招待你”。在这一价值体系里,酸有代表着次级的、边缘的甚至是负面的价值取向。在黔东苗语方言里,这种负面性在一些日常用语的表述中更为明确:nenx hol leib ongt eb hxub ib like,其直译是“他像个酸菜坛一样”,意译为“他是个糊涂蛋”。②感谢凯里学院唐巧娟博士对该材料的分享,唐博士认为:“用最熟悉的具象概念来认识和表达抽象概念,是人类认知的普遍性规律。Hxub(酸)作为味觉词,在苗语中的隐喻义也极为丰富,如hxub hxid(心情不好)(hxub jenb 受惊)(ongt eb zas hxub糊涂人)等。”酸菜坛与人的属性的对应,是酸汤文化的体现,也是其建构价值观念的参照。总之,“酸”在贵州东南苗人的文化里兼具一种矛盾的价值取向。
一方面,酸在贵州东南的历史和文化里呈现出价值取向层面的矛盾性;另一方面,一酸对应的盐和盐味在贵州东南的历史和文化里则呈现出了别样的媒介物质和社会生命(sociallife)历程。2015年3月1日,南加镇上的一个汉族小伙将返迷(距离南加镇上游约两个小时的水路)的一位苗家女孩“拐”到家里(春节未归家)。过完春节后,小伙的父亲请了两个能说会道还能喝酒的朋友,租了一艘冲锋舟载着礼物(主要是一大桶米酒,需要两个人才能搬运,此外还有鸭两只,鞭炮若干),沿清水江逆流而上,前往女方家“讲信”③所谓“讲信”,是婚恋中男女恋爱后,未通过提亲等正常程序,男方将女方“引”到家里。男方父母请人到女方家报信并说情。(因为他们中的一人认识我,顺带捎上了我一同前往)。从江边到女方家还有一段距离,女方家也不迎接,以示自己的态度。好在小伙的父亲在女方村里结识了一个姓彭(村里唯一的一姓汉人,世代木匠,仅3 户)的“老庚”(兄弟),快到一半的时候由他前来引路。女方的母亲已备好酒菜接待(一锅炖肉、一钵酸汤、一碟蘸水和米酒),但女方的父亲为表示不满,象征性拒绝出场。男方父亲请求多次后,女方父亲方出场。酒桌上男方父亲又少不了赔礼道歉,双方你来我往地喝酒说笑,大约两个小时后,女方的父亲开始改口称男方父亲为“亲家”,并说到了“修舅公”(见下文)的事情,女方父亲指着餐桌上的蘸水自问自答:“亲家,你以为苗家的蘸水好蘸恺④“恺”是当地方言语气词,表示加强。啊?一点都没好蘸!”
所谓的蘸水,基本的配料是盐和辣椒。但在这个场合,它显然不是一碟蘸水那么简单。男方父亲显然也不太确定“苗家的蘸水不好蘸”的意思,微微一愣,他在村里结识的彭老庚立即解释说,女方的母亲有四兄弟(需要修舅公)。男方父亲“一点就通”,立即非常爽快地拿出了一叠现金交给女方父亲去“修舅公”,很显然他是有备而来(事后出村时他咨询彭老庚,说自己拿出4800,一个兄弟1200,是不是妥当。彭老庚连说“合适”)。男方父亲道:“修舅公这事就麻烦给亲家了,我们一起把这碟蘸水的味道调好。”女方父亲说:“亲家我也不是抠人,这钱我拿去,该杀牛杀牛,该杀猪杀猪,剩下的我一分不占,有多少我退你多少。”他也不数钱,直接收下。就这样,男方“讲信”之礼算是顺利通过了。
自清代国家权力正式进入这一区域后,就大力反对盛行的姑舅表婚[23],“皇帝”(国家的权力)和“舅舅”(婚姻中的舅权)在清水江两岸就人口再生产一事上不断角力。“皇帝”要求废除姑舅表亲,并将之定性为陋习,单边推进中原王朝认可的礼仪。三百年来,尽管舅权在该区域日益式微,但在今天的婚姻仪式中,舅权的草根力量依然存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婚姻程序中的“修舅公”,当女方家同意婚事后,男女双方要到舅公家告知舅舅,取得舅舅的同意并和舅舅家修好关系。
察看姑舅表婚中女性流动,不难发现这样的逻辑:两名男性甲和乙,甲男将自己的妹妹(一名女性)“馈赠”给乙男作为妻子;为了回礼,乙男将自己的女儿(一名女性)回赠给甲男的儿子做妻子。这是一次跨了两代人的“礼物”交换,而且是充满了男性中心主义逻辑的交换。也就是说,女孩的母亲是赠礼者(女孩的舅舅)“馈赠”给女孩父亲的一名女性。按照互惠的逻辑,受礼者(女孩的父亲)应当将他的一名女性(即其女)回赠给赠礼者之子。
而“讲信”意味着,女孩没有嫁回舅舅家。相当于单方面撕毁了两个男人(女孩的舅舅和女孩的父亲)之间女性交换的不成文约定,所以理应到舅舅家“赔罪”并修好关系。
“修舅公”意味着要送“舅公礼”。今天的舅公礼已经被淡化不少,但在历史上,“舅公礼”的礼金(又称“江钱”)是笔不小的数额。在清水江北岸高地的小广一带,一度“勒要江钱三十(两)五十(两)不等”①小广《永定风碑》(光绪十四年),该碑现立于小广环龙庵前。。碑文中并未交代“江钱”之外的礼物,也许是将礼物折入了“江钱”。在“江钱”之外的礼物里,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盐。根据小广王TH 的回忆,她的女儿姜TE 结婚时(1980 年),她就特别交代女婿和女儿在婚前到自己的兄长家去“修舅公”,“去时由男方家带2-3桌的肉、酒和9 块盐钱②2014年7月18日小广田野调查资料,访谈人:毛章舟、潘婷、黎成亮。翻译:杨梅玉。”。20 世纪80 年代初的9 块钱不是小数目,柳霁吴JX 等人至今还记得,“1985 年,1986年盐价才一角五分钱一斤,后来才涨到一角六,一角七”③2015年2月17日田野日记。。也就是说,9 块钱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最少能买60斤盐,足见盐的特殊性。
2015 年4 月,柳霁小潘娶亲(女方是苗女)。临行前母亲将一件件礼物考究地缠上红纸条交给小潘,礼物之一包括2包盐(共500克)。“现在盐便宜了,以前盐贵,带去的(盐)越多越有面子。”小潘的奶奶说。“以前苗家提亲的时候还要给‘盐巴钱’,或者拿‘盐巴钱’买盐巴,分给女方的叔伯家,还要给女方的舅舅送礼钱和盐巴。提亲回来苗家会抹你一身泥巴,送你一头小猪背着回来。到家后杀这头猪请客,大家凑钱给你。你还要买点盐送给自己的叔叔伯伯。”一位从南寨嫁来柳霁的苗家老人说补充道。
也就是说,准备结婚的苗家小伙子,需要用盐和三方面的男人(女方的舅舅们、女方的叔伯们、自己的叔伯们)来调和关系并宣示一个新的社会再生产单位即将成立(见图1)。其中最为紧张的关系是与舅舅家,而男方的叔伯们,更多的是在家族内宣告一个新的家庭即将诞生。

图1 婚姻中的“人际之盐”
盐之所以能扮演这一角色,需要联系苗疆味觉地图及其历程方能更好理解。或许我们可以说,婚姻程序中的盐,嵌入了一段苗疆独有的历史。过去的味觉历程通过现在的程序无意识呈现出来。
三、神灵的味觉:历史、仪式与感觉的互嵌
类似的历史无意识呈现不仅仅是在婚姻的程序中,在祭祀神灵的仪式里也同样存在。尽管当下,盐已是这一区域寻常百姓家最不起眼的日用品,但一段味觉的历史仍在仪式中若隐若现。
2015年10月4日,秋收基本结束。施秉菜花湾,苗寨。
每年秋收之后,菜花湾的一些苗民(主要是老人)会到10 里外的县城请仪式先生到家里做“保家神”的仪式。
下午3:40 左右,上一个做“保家神”的男主人将仪式先生和我引领到下一个同样举行“保家神”仪式的主人家。主人家仅仅是两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堂屋的角落的一根竹上串着用棉纸做的人形和铜钱状的东西(后来仪式先生说人形代表请到家里的兵将,铜钱代表的是金银财宝),有些已经有些时日,发黄了。吴大爷(主人家)说那是之前各年做的。
进门后,主人家立即往置于堂屋正对大门的供桌上摆放祭品:12 盅酒、12 元钱、12 条鱼(鱼苗,盛于碗中,碗里有半碗水),最前面放一碗蘸水,分别放有盐、辣椒、蒜瓣。供桌后置一凳,那是仪式先生所坐之位。他和男主人说一些准备的事情,老太太(女主人)在偏厅,配合准备物件。直到整个仪式结束,仪式先生走的时候,她才跨过门槛送先生离开。仪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肃,开始之前老太太还用汉语问我时间(他们一直都说苗语):“有没有8点了?”“才3点44”,我回应她道。“我这个钟坏掉了,看着快8点了。”
下午3:45,仪式开始,先生开始用苗语吟唱,语速较慢(后来他说这是在请兵将)。4 分半钟后,吟唱结束。男主人将准备好的鸭子拿到屋外去宰杀。仪式先生还是以快速说话的方式念词。大意是(其后仪式先生所翻译):
保主人家天天送金,夜夜送银;天天消鬼,夜夜消神。
保主人家没有:天灌(音)地灌八八六十四灌;天煞地煞八八六十四煞;天瘟地瘟八八六十四瘟。
保主人家没有:走路跌打死伤、打岩死伤、枪毙枪打死伤、吊脖子死伤、雷打火烧死伤、坐着死伤、站着死伤……
仪式很简短,前后约20分钟。然后仪式先生又到另一个村的苗民家主持仪式①2015年10月4日,田野日记。。
菜花湾的仪式引发我兴趣的是那碗蘸水。所谓“蘸水”,一些史料中又写为“占水”,一般以盐、辣椒等调味品和开水简单配成。清末到贵州镇远府任职的李祖章(1863-1929),很可能是在上任或某次旅行时,中途到一处山茅小店歇脚。店家招待他的是包谷饭和水豆花,外加一碟“占水”(李祖章特别记载了它的做法:“以水泡盐块加海椒”)。可能是受到了来自苗疆味觉上的“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李祖章用餐之后赋诗一首:
山腰茅店客停车,玉米为餐佐豆花。
淡食难堪增占水,海椒烧罢洗盐巴。[24]
恐是意犹未尽,李祖章在诗后又注释:“途中有包谷饭,菜多水豆腐,俗名‘豆花’,并无豆油,以水泡盐块加海椒(辣椒)调食。谓之‘占水’。缘黔中盐布最贵,有贫民生平少食服者。”[24]
1900年前后入黔任职的李祖章,或应感到满足,至少在山郊野岭处,餐桌上还有一碟“水泡盐块加海椒”的蘸水供其调味。如果说蘸水上了李知府的餐桌是情理之中的话,那么蘸水是如何堂而皇之地上了神灵的供桌并成为祭品的?在我们(也包括李知府)日常生活的餐桌上,蘸水处于从属地位。它让位于餐桌最中心的主菜,并被置于餐桌的边缘。盛放的餐具也明显不能与主菜的餐具相比,要袖珍得多。但在这样一个仪式里,蘸水却有着突出的位置。
笔者:“蘸水用来献神,以前的老人家有什么说法吗?”
主人家:“没有什么说法,老一辈的人就是这样做的。让他们(神)吃的时候(有)味道一点。吃好喝好了,就会好好保佑(主人家)了。”①2015年10月4日,田野日记。
这大约可以看作是一种人神之间的互惠逻辑。人向神灵献出祭品,祈求安康。神接受人的献祭并予以护佑。但在这个过程中,此岸的赠礼者“非常细心”地考量到了彼岸的受礼者(神灵)的味觉体验(如果神灵也有味觉体验的话)。也就是说,神灵并不在意盐和辣椒(它们本身并不是美食),而是在意其味道。
如果说最初在清水江两岸,盐仅仅是餐桌上的“调味之盐”(味觉之间的调和)的话,那么在婚姻中,盐已经上升到了“人际之盐”(人与人之间的调和);而在“保家神”的仪式中,它则是“仪式之盐”(人与神之间的调和)。而盐的这三种身份,都以其味觉的体验——当地称之为“盐香”——为基础。结合区域的历史与“盐香”在苗疆的历程,献祭仪式中有蘸水这一细节,或许是历史因一种对盐的味觉诉求而被隐喻或嵌入在仪式之中。尽管在当下,盐已在从稀缺品普及为最不起眼的日用品,并意味着它作为“人际之盐”和“仪式之盐”的社会生命的式微,但我们仍可以通过盐之味去重新理解这一区域和流域的历史。
四、结论与讨论
历史上当中央王朝试图通过味觉世界来树立自己的威权,开展自己的统治时,“山野小民”通过“辛辣代盐”“以酸代盐”“以草木灰代盐”等策略展现其主体能动性。300年后,他们的味觉实践留下的是苗疆人独特的饮食偏好和以凯里酸汤味为代表的特色美食。我们通常用“饮食习俗”来简单概括这些现象,但也掩盖了味觉里的历史和历史里的味觉。
贵州东南的个案探索表明,人类学尤其是历史人类学解读历史的路径可以是多元化的。人类学家当然需要积极学习历史学家解读历史的方法。从文献版本到典章制度,从时间定位到空间定位,人类学家都需要真正入门。但人类学或者说历史人类学的使命在于理解“人民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在这一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就发挥出了其自身的优势。毫无疑问,后者是学者贴近人民的生活和日常实践的不二法门。当我们面对田野中的民间文献,也就是历史人类学将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辩证结合的契机——在田野中解读文献,在文献里重新认识田野。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我们的田野调查点、区域及其历史。
将感觉作为历史人类学切入历史路径的原点,在于感觉是嵌合(embedded)在历史中的,历史也会具身化(embodiment)在感觉中。也就是说,感觉是历史长河中必不可少的一块拼图,是历史主体——人民的能动性和实践动力之一。与此同时,过去的经验、既有的政治经济环境,也会影响甚至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身体感觉中。因为人们的感觉是生物性与文化性的统一,是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统一,还是瞬间与历史的统一:“味觉既是瞬间性的,又是历史性的。”[25]一方面,人们的感觉会固然有各不相同的辨识度,另一方面,正如本文的酸、辣与“盐香”,这种感觉上的体验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无意识呈现。当一种所谓的习惯,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现象,还具有某种普遍性,成为一群人的倾向时,它就类似于布迪厄所说的“习性”(habitus),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传承性和时间性。正如民国和解放初期出生的柳霁人们嗜盐的习惯,乃是历史嵌入到了人们的身体嗜好里,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具身性(embodiment)或历史的身体化。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感觉“藏”有一段历史。这种感觉,不仅仅会呈现在仪式的某个细节(如神灵祭品中的蘸水)里,还会呈现在人群的某种嗜好中。
也就是说,感觉存在于历史中,历史也存在于感觉中。因而,这样一种特殊的感觉必须置于一段历史整体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同时,从感觉可以解读出一段历史。这就是我们结合感觉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从感觉去解读历史的理论基点。
综上,人类学解读历史的路径至少有三条,其方法也各有差异。

表1 历史人类学解读历史的三条路径
这三条路径及其方法并非各自独立,也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应当交叉运用,并积极探索更多的可能路径,才能更好地梳理出更加贴近人们生活与实践的“人民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