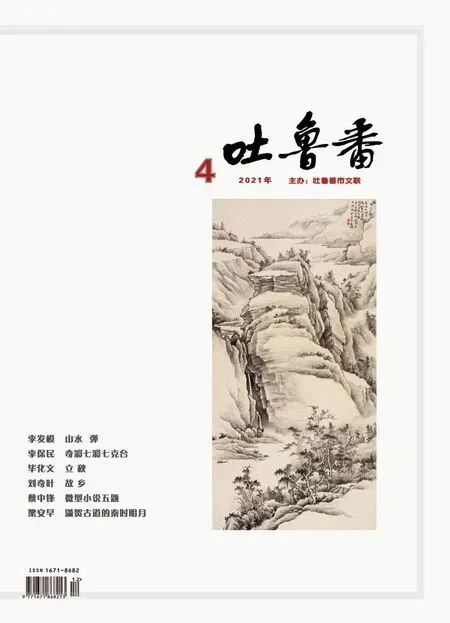路口
吕雪冰

春枝回来了。接到哥哥电话时,腊生正在上班。春枝是腊生的女儿,已有十几年没有回家。当 初离开家的时候,只有十三四岁。那年腊生的妻子夏草在外打工,和别的男人生了个儿子,也就不回腊生这个家了。春枝就是那年离家出走,不知到哪去了,腊生从没找过,只是回家看见哥哥的小孩才想起自己还有个女儿。春枝突然回来了,有些出乎腊生的意料。
她回来干嘛?腊生问哥哥。
带着一个小孩回来的,说是小孩要上学了,要把户口转走。
那就让她转吧。
转户口你不回来怎行?
我在上班呢,怎么回去?
上班不可请假?
请假要扣很多钱。
你说你,孩子那么多年没回来,你就不想见见?钱就那么重要?哥哥提高了嗓门。
又不是我不要她回来,真是的。好好,我去看看能不能请假。腊生觉得有些委屈,语调也提高了些。
不能请假你今天也必须回来。哥哥撂下电话的声音让腊生哆嗦了一下。
腊生在城郊的一个化工厂上班。那年,腊生从外地打工回来,在家窝了大半年,父亲只好求一个远房表叔帮他找了这份工作。主要在车间装卸一些生产原料,这工作很适合没有什么文化的腊生。腊生读过三年书,老师说,腊生读书用枪子都打不进去。老师用枪子打了三年,腊生还是在一年级,第三年的下半年,晕晕乎乎的腊生辍学回家了。腊生虽不会读书,手上的事还是会做,就是太懒,你得哄着他做。前几年在工厂,腊生的车间主任总是夸腊生能干,还说要帮他介绍女朋友,这让腊生在厂里工作得很开心。去年换了个主任,新主任看腊生,事事都不顺眼,总是批评腊生,多数时候是当着大伙面批评。现在腊生都有点怕见他,可哥哥的话又不敢违抗,腊生只好硬着头皮找新主任请了假。
首先看见腊生回村的是腊生家的大黄狗。狗跟着腊生的摩托车前后奔跑着,扭动着,讨好地叫唤着,身上的枯草和灰尘抖落了一地。
腊生支起摩托车,大黄狗就往腊生脚上蹭。腊生怕大黄狗弄脏自己的裤子。一脚踢开了它,滚一边去,癞皮狗,脏死了。大黄狗猝不及防,“汪汪”叫着,跳到一边,夹着尾巴不解地望着腊生。
瘦高个子的腊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门喜欢穿笔挺的外套和发亮的皮鞋,大背头也梳得亮光光的,光亮的头发下面是一张骨瘦嶙峋的脸。此时,腊生看见狗身上的癞皮,忽然觉得很像自己小时候腿上长的疮,记得那时自己没事总是坐在地上使劲挠,挠出了血就在地上抓把灰涂抹在上面。一想到这些腊生很不舒服。他又停下来,对着狗头一脚蹬去,还不快滚?大黄狗后退两步,站定,见腊生进了屋,它又跟过来,因为在这个家它比腊生待的时间还多。腊生只在过年或有事的时候回来。腊生住的是分家时分得的两间青砖瓦房。村里搞新农村建设,统一将房顶上加盖了树脂瓦,外面的青砖上刷了白色涂料,这一捯饬倒是有几分徽派风韵。更让腊生感到高兴的是,他家再也不会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了。平时腊生出门就在门扣上加一把小锁,两门之间会留下一些缝隙,腊生不在家时狗都是从门缝里进出,为腊生守着这个家。
春枝见腊生进屋赶紧站起来,爹,您回了。身边的小男孩直往春枝身后躲。
腊生放下头盔,扫视了一下屋内,屋内干干净净,显然被春枝收拾过。腊生很满意,坐在八仙桌的上位,望望春枝,又望望小男孩,欲言又止。
孩子要上学了,我想把户口转过去。春枝侧过身摸着孩子的头,来喜,快叫外公。
来喜又往后躲了躲,怯怯地叫了声外公。
细如蚊吟的声音,狠狠地咬着腊生的心,让腊生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腊生的手不自觉地伸向了口袋,摸出了一百块钱,送给来喜,来,拿去买糖。
来喜扭捏着不敢接。望着父亲手上的钱,春枝只觉一股酸酸的气流直往鼻子里钻,这是她做梦都梦不到的情景,在她的记忆里父亲是那种“烂泥巴扶不上墙”的人,姆妈经常当着春枝的面这样说父亲。春枝小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只知道烂泥巴不是什么好东西,长大啦,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春枝自然和姆妈一样瞧不起父亲。父亲倒是生活得自由自在,在家,姆妈不叫父亲做事,父亲永远不会主动去做,就像她们小孩玩的陀螺一样,不抽打永远不会自己动起来。父亲自然也不会考虑家里的开销,以至于姆妈叫他去买袋盐都必须先把钱给他,偶尔有找回的零钱,姆妈没及时向他讨回,多半会被花掉。在春枝的印象中父亲从未给她买过东西,更没给过钱。此时的父亲让春枝既熟悉又陌生。
春枝替来喜接过钱,向腊生鞠了一躬,谢谢爹。爹,这是我给你买的。春枝拿过放在条几上的烟酒。
我又不抽烟,也不喝酒。花这钱。呵呵。腊生用手拨弄着袋子,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爹,这几年你还好吧?
好,我好得很,有吃有喝的。
你头发都白了。
老了,不白?……我去买点菜,中午让你大妈帮着搞下饭。腊生有些不习惯春枝的关心,赶紧岔开了话题。
买了,放大妈家了。
你买的?
嗯。
那还差不多。要不然他们会不高兴。腊生用手指了指东头哥哥家。我每次回来,又叫我过去吃饭,吃点饭却给脸色我看。其实,有几次我是买了菜的,过年时我还给他孙子压岁钱。可他家孩子连一根烟都没给我买过。我也就不管许多了,反正回家就到他家去吃。腊生的表情生出了许多得意,仿佛他在他哥家吃饭让自己沾了很多便宜。
平时你就自己弄点饭。
我哪会弄?自从你姆妈离家后我就没开过火。
“汪汪!”大黄狗突然叫了两声。
你叫什么鸟?妈的,你自己瘦成这样脏成这样,能怪我吗?滚滚滚,滚出去!腊生和大黄狗在一起时经常这样吼。
大黄狗好像听懂了,不情愿地慢慢爬起来,慵懒地走了。
中午的饭菜很丰盛,大妈还特地宰了只母鸡。吃饭时,大妈不停地为春枝母子夹菜。
孩子,回家了,莫作礼,多吃点。大妈,我自己夹,你也吃呀,别只顾我们。
你这孩子十几年没有消息,这猛地回来,还带回这齐整的儿子,你晓得我和你大爹几高兴啵?我看着你们吃我都饱了。唉,要是你姆妈能回来就好了。春枝大妈语气低沉了下来。
大妈的哀叹汇成一股奇异的气流,在春枝体内快速地游走,片刻便触摸到了春枝埋在心里的那根脆弱的神经,气流就像毒蛇一样将这根神经紧紧地缠住,并死劲地绞动,痛得春枝端着碗筷的手无力地瘫放在桌上,同样无力的头,低垂着。“姆妈”,就像一根刺扎在春枝心里,想时,生生地痛,痛时,深深地想。可想着想着,姆妈的样子在春枝的脑子里就像暴露在室外的宣传画,日晒雨淋已变得模糊不清。有时,在梦里,姆妈和奶奶的样子会重叠,让春枝分不清到底是姆妈还是奶奶。此时,春枝依然想不起姆妈的样子,这让春枝觉得自己不可原谅。她甚至恨自己怎么记不起姆妈的样子。这突如其来的恨意使那游走的气流随着眼泪无声地滴落在碗里,继而化为丝丝柔软的热气飘散在空中。热气也带走了腊生吃饭的“吧唧”声。
腊生愣愣地望着春枝,夹着一块肉的筷子依然杵在盘子里。他不知道春枝吃得好好的,为啥突然哭起来。腊生觉得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吃,有了吃又何必考虑许多?腊生不会考虑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因为有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此时春枝的眼泪却让他内心有了一丝刺痛。
就你嘴多,尽说些无用的。搞得孩子饭都吃不安。大爹吼了大妈一句。眼睛却瞟向了腊生。
腊生“哼”了一声,将夹着的肉扔给了桌下的大黄狗,狗东西,让你也过下瘾。狗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春枝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赶紧笑着说,是我不好,那时我没手机,也没记住家里人的电话,就一直没联系。
这次回来就多住几天。看这孩子多可爱。大妈摸着来喜的头说。
来喜和大家一起呆了那么长时间,也已熟悉了。他边啃着鸡腿,边环顾四周说,我家也住楼房,就是没这么大。
来喜的话顷刻让气氛活跃了起来。
欢快的气氛让腊生好像又回到了以前和夏草在家生活的时候,久违的感觉,使腊生有些茫然,他想到了夏草,更想到了夏草和那男人生小孩。这些想法让腊生有些不知所措,如同一头鹿突然闯进一座漆黑而又空旷的房子里一样慌乱。
那男人和夏草一个车间,他总是变着法地买些东西到腊生和夏草租住的小屋,见了面总是“哥呀,哥呀”地叫个不停,叫得腊生春风满面,飘飘忽忽。当夏草告诉腊生,她怀了那男人的孩子时,腊生一声不吭,拿起桌上的水杯“咕咚咕咚”大口喝水,喝饱了,用袖子擦一下沾有水珠的下巴,走向门外。夏草望着腊生的背影哭着叫道,你这个闷驴,你倒是放个屁呀,你骂我打我呀。你跟我离婚呀。夏草的哭声在阳光照射下滴落在腊生的身后,留给夏草一个悲凉的背影。夜里腊生又回到了出租屋,他依然和往常一样吃饭拉屎放屁。
夏草的肚子越来越大,无法在厂里上班,她要和那男人一起回他的老家生小孩。当夏草跨出出租屋的那一刻,腊生有些站不稳,他忽然意识到夏草真的要离开他,他有一种恐惧感,恐惧感如电流般击打着他的身体,这并不完全因为他工资低无法生活(腊生不懂技术工资只有夏草的三分之一),而是由于他已习惯在夏草的庇护下生活,离开夏草,他的日子就瞎了。他颓废地瘫坐在椅子上,骂了一句,一个童子鸡跟一个老母鸡,不得好死!我呸!
第二天,腊生只身回到了家乡。
吃完饭,春枝到厨房帮大妈洗碗,大妈坚持要自己洗,春枝只好在旁边陪着说话。大妈聊着这两年家乡的变化,清澈的自来水将满满的幸福流淌到了大妈的脸上,这静好的幸福通过光亮的灶台折射进春枝的心里。春枝突然想起了奶奶家老式的柴火灶,还有烟囱上随风飘逝的炊烟。
春枝不喜欢炊烟,因为炊烟总是急不可耐地逃离自己温暖的家庭,那么高调,那么忸怩作态,那么无情。那天刚上小学的春枝放学回家,同村小美被姆妈牵着一蹦一跳地走向家里,春枝忧伤地望着奶奶的家,这时奶奶家的烟囱正爬出一股淡淡的炊烟,袅袅婷婷,春枝好像在炊烟中看到了爸妈的影子,一阵风过,炊烟消散在空中,爸妈也随风而逝。春枝觉得炊烟就像爸妈一样不喜欢春枝,将小春枝留给年迈体弱的爷爷奶奶,春枝不知炊烟争着抢着从烟囱爬出却又飘向了何方?也是在一个炊烟袅袅的傍晚,春枝见到了失魂落魄的父亲,知道了姆妈再也不要她了。从那时起,那缕炊烟就住进了春枝的心房,多年来,炊烟总会固执地裹着一丝痛苦从春枝的心房升起,春枝有时怀疑自己的心是否被这炊烟熏黑熏烂,烂得结了痂,炊烟在春枝心房升起时疤痕就会隐隐作痛,每次她只能如一只受伤的猫一样,蜷缩在异乡的某个角落舔舐着自己的伤口。而此时的疤痕却被刚刚涌入心里的幸福暖流轻抚着,暖流将笑容带回到春枝的脸上。
腊生用火柴梗剔着牙齿,来喜乖巧地依偎在腊生的腿上,逗着身边的狗。
腊生以前在哥哥家吃饭,速度都很快,吃完了兀自推碗出去。腊生大多数时候是到吴花家,吴花已六十岁了,老公在外打工,孩子自己做了房子在一边住。吴花也不用带孙子,日常也就是打打麻将。听说,吴花打麻将输多赢少,老公和孩子给的钱不够她输。村里有人说腊生的工资都让吴花吸掉了。腊生听见后会梗着脖子说,莫乱嚼,人家那么大年纪,你也不怕雷打头。可腊生依旧往吴花家跑。
一直没有夏草的消息?哥哥见腊生没有走的意思就问了一句。
没有。
你也不打听一下?
有么好打听的。
婚也不离,就这样拖着?你也不打算再找一个?
哪个看得上我?
你大嫂不是帮你介绍了一个?
带着两个小孩,都还在读书,也真是,帮我介绍的都是拖油瓶的。以后再说吧。腊生扔掉火柴梗,嘴里“吱吱”地吸了几下,吧唧几下后再咽了下去,舒适感顷刻布满了脸。
你以为你还找得到黄花大闺女呀,人家不是带小孩难,想找个人帮衬,谁看得上你?你还看不上人家。腊生的小眼睛翻动着,用余光瞟向哥哥,抖动不停的双唇发出悄悄声,见哥哥正盯着他,只好将声音和口水一起咽回肚子,即刻低下头用手抠着鼻子。
哥哥本想再唠叨几句,可望望对面的腊生那怂样,也就没有说的欲望,只是暗自摇头轻叹。
此时,春枝和大妈一起走出了厨房。
妈妈。来喜见到妈妈扑了上去,惊得大黄狗跳了起来。
孩子,小心别摔着。腊生赶紧起身抱住了来喜。来喜咯咯地笑,笑声包裹着春枝,裹得春枝鼻子发酸。父亲从未抱过她,哪怕是自己摔倒在父亲眼前他也会视而不见。为这事姆妈没有少骂他,你眼瞎了?孩子摔倒了,你也不拉下。挨了骂的父亲才会拉起自己,嘴里嘟囔着,走路也不好好走,起来起来。父亲对来喜的一抱让春枝感到无比亲切,这丝丝柔柔的亲切感恍若来自遥远的梦中,如奶奶那双青筋暴起的老手,轻轻拍打着春枝的后背,让她那颗一直在外漂着的心回到了自己长着坚硬外壳的躯体,并蹭蹭地向外散发着暖暖的亲情,这份温暖使春枝变得无比的轻松,轻松得如同一只随时都可以飞起的燕子。
春枝又想到爷爷奶奶,提出先到爷爷奶奶的坟上去上个香。
春枝的爷爷奶奶葬在村西头的一个山坳里,春枝不知道地方,腊生只好陪着去。一同去的来喜想自己走,腊生说,山路难走。就把来喜驮在肩膀上“打马架”,来喜一路咯咯地笑。春枝要去买些香纸爆竹和水果,腊生说,平日里上坟是不需要烧纸钱的。春枝不做声,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坚持将东西买了。
他们路过一片公墓,来喜叫了起来,外公,外公,你快看,那是什么?
公墓建在一个山坡上,呈半圆形,从公路到山脚修了一条宽敞的柏油路,路边移栽来的香樟树又已长出新枝,摇曳中发出喃喃细语。路至山脚下便是一级级台阶,约有六七级,往上是呈阶梯状的墓台,墓台上两棵一组的塔柏如守卫般守护着一个个墓位。台阶两边往上直到半圆的边上都栽有红叶石楠,有人说,到了秋季,远看墓地就像一颗镶嵌在地上的红心。腊生却没有这种感觉,他觉得葱郁的山坡上弄出这么一块水泥地,就像一个人头上贴了一块膏药。腊生搞不懂村里为什么要建公墓。以前村里人死了,各自找一个自认为理想的地方安葬,后代们都认为自己祖辈死后葬的是风水宝地,每年清明都拼命烧纸,乞求保佑,多好。不过,腊生的这些想法只是放在自己心里,他怕说出来别人笑话他,因为那天他就跟“麻杆”说了,“麻杆”说他落后,跟不上时代的脚步。“麻杆”从小体弱多病,尚未成家,因为家里穷,平时不大言语,大家也都不愿意搭理他,他常跟在腊生屁股后面混。因为是贫困户,这两年到“麻杆”家看望他的领导多了起来,腊生感觉“麻杆”鼻孔有些朝上,连说话的语气都变了。那天“麻杆”这样说腊生,腊生当时有些不高兴,不过转念想到“麻杆”病恹恹的样子,肯定是在为自己死后找位子,腊生内心就像在酷热的夏天流过一股清泉,带走了一切烦躁与不平,顷刻心里敞亮得如万里无云的天空。再说,自己有吃有穿,自由自在,干嘛要和“麻杆”那样的人一般见识?更没有必要辛苦地去跟上什么时代的脚步。
来喜不停地拍打着腊生的头,想让外公分享他意外发现这么漂亮地方的喜悦。
看到了,看到了。声音是从腊生鼻子里溜出来的。来喜依然饶有兴趣地回头张望。
腊生领着春枝拐进离公墓约一百米的一条山路,说是山路,却因许久没人走过已长满矮小的灌木,灌木丛里夹杂着一些荆刺,稍不留神就会划到手,或划破裤子。腊生把来喜抱在胸口。弓着腰,小心前行。紧随其后的春枝有些手忙脚乱,手已被划破两个口子。春枝并没有感觉到疼,她倔强而又坚定地往上前行,嘴里轻声地念着,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来了。越往上春枝的声音越哽咽,当她看到父亲在一个坟包旁站定时,她踉跄地冲过去,跪倒在坟前,放声大哭。来喜惊恐地望着母亲,继而也嗷嗷大哭起来。
腊生不知所措,只好把来喜放在春枝身边,春枝边哭边按着来喜的头,带着他不停地磕头。腊生捡起地上的香纸,想帮春枝点着,可找了半天,才发现自己忘了带打火机,腊生尴尬地杵在那里呆望着春枝母子。春枝哭声很大,仿佛要把这么多年的思念、委屈、痛苦……一股脑儿全发泄出来。
阳光被树枝剪成大大小小的碎片,碎片从树叶间散落下来,在地上绘制成梦幻般的图案。微风中,腊生的脸也变得迷离起来,就像川剧中的变脸。忽远忽近的哭声,忽明忽暗的光亮,将腊生的神志轻轻地牵出,恍惚中的他看见父母从棺材中坐了起来,静静地倾听春枝的哭诉,父母听着听着就从棺材中走了出来,在林中游荡,好像在寻找着什么,腊生的目光也跟着他们游走,却发现父母从未瞟过他一眼。腊生有些失望,他知道父母在世时对他是恨铁不成钢,可为什么死后对他还是如此冷漠?腊生抬手使劲地擦了擦眼睛,眼前,春枝仍在悲切地哭诉着,散乱的头发遮住了她已被眼泪和汗水弄花的脸,不规则的阳光碎片在她背上跳跃着。此时,腊生宛若在春枝身上看到了夏草的影子。他想从记忆里搜索孩子小时候的样子,或者是某一个可爱的动作,这显然是徒劳,这一切似乎在他的生活的河流中没有溅起一点浪花。此时,他意识自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无所作为的,甚至一无所知。这份愧疚感迅速在他体内膨胀,将他深藏心底的眼泪挤出了眼眶。泪眼中他又看见了父母,他们就站在自己的眼前,对他怒目而视。慌乱中,腊生死劲地咳了一声,随着咳声,父母不见了,春枝的哭声也戛然而止。腊生的皮肤猛地收缩了起来,好像有许多小针在扎,他赶紧捡了块石头将手中的纸压在父母的坟头上,再将香和爆竹整齐地摆放在坟前,接着就匆匆向山下走去,留下了春枝母子。
腊生慌乱而又快速地奔走着,直到看见大黄狗迎着他跑来,他才放慢了脚步。那一刻,他似乎感受到了勇气和力量。
整个下午,腊生都被父母在坟边树林游荡的画面困扰着。在镇派出所,春枝将没有自己名字的户口本递给腊生,发现他表情灰暗。春枝以为父亲是因为自己将户口转走而难过。于是春枝就说,我会常回来看你的。腊生接过户口本咧着嘴点了下头,随即转身走了出来。此时,太阳已走到了山顶,山顶上的几片浮云穿着红裙,轻轻地簇拥在太阳身边。腊生拖着长长的影子,茫然地望着前方。一种孤独从他的影子慢慢向上攀爬,一下子占住了他整个身体,他无助而又无奈地立着。春枝挽着腊生的肩膀,将他扶上车,腊生呆若木鸡。
春枝从镇上回来时带了点菜,决定在家做晚饭。大妈说,菜都准备好了,就在她家吃。春枝想在家多住几日,不好意思天天在大妈家吃,谢绝了大妈的好意。来喜可能是累了,到家就睡了。腊生到家依旧一言不发,那个困扰他的画面自出现后就像吸盘一样紧紧地吸在他的脑子里,更让腊生惊恐的是,现在脑子里出现的画面越来越多,就像一部保存完整的纪录片,在“吱吱”地播放。腊生不清楚自己连枪都打不进一个字的大脑怎么会装进这么多东西,他得想办法把这些东西从脑子里赶走,时间长了,一定会烧坏自己的大脑。找谁呢?大哥大嫂?不合适,他们会骂自己神经病,找“麻杆”?只会让他更瞧不起自己,对,去找吴花,只有她才不会笑话自己,有时还会帮着出点主意。
腊生去找吴花的时候,已是夜里十点多。星子如赶集似的聚集在空中,腊生担心哪一天天空一发脾气会抖落几颗星子下来。月亮悠闲地穿梭于群星之中,将清辉撒向村子,给寂静的村庄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吴花家在村东头,与腊生家隔着一里来路。腊生在吴花家的窗户上轻轻地敲了两下,吴花将门开了一条缝,腊生朝四周看了看麻溜地闪了进去。
你说你有么狗屁用,每次来都吓得一身汗。吴花取下一条毛巾扔给了腊生。
腊生没有擦汗,任由毛巾搭在肩上,低头不语。吴花走到腊生身边,拿起毛巾帮腊生擦着汗。今天手气真背,又输了好几百。
腊生没有吱声,用手隔开了吴花的手。
吴花愣了一下,旋即又将身子靠了过来。我没钱了,你能借点给我吗?吴花的声音甜软得像糖稀。我还没发工资,没有钱。腊生嗡声答道。
那你先帮我找别人借点。吴花轻柔地推着腊生。借不到。腊生语气有些不耐烦。
关键时候指望你是屁用都没有。吴花扭着屁股走到桌边,将毛巾扔到桌上。
你还用少了我的钱?腊生带着怒气的话如剑一般刺向吴花。
吴花像是被剑气点了穴道,僵硬在那里,傻傻地望着腊生。也许是剑气伤得不深,片刻吴花又恢复如前。
我说你就是个榆木脑袋,捧着金饭碗到处讨饭吃。吴花用手点着腊生说。
腊生不解地望着吴花。
你老婆在外面和别人生了小孩,又没跟你离婚。我问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他说,你可以告她重婚罪,她要不想你告,不就得给笔钱?吴花说完,将左腿架在右腿上,得意地晃动着。
我有吃有喝的,干嘛要她的钱?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提这个事,你还要提,一天到晚就是钱钱钱,你也不怕难为情。腊生直着腰板对着吴花吼道。
腊生的声音在夜间有着极大的穿透力,久久在屋内回荡。吴花没想到腊生敢如此大声地向她吼叫,她想用更大的声音压住腊生,可又怕邻居听见,就用低沉的声音咬牙切齿地说,我不要钱跟你这个烂男人?这声音就像是母狮向猎物发起进攻前的吼声。
我是烂男人,你不也是烂女人?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吴花,她扑向腊生,拽着他的衣领向外推搡。老娘是烂女人,你跟我滚出去,老娘再也不想看到你。慌乱中,腊生碰倒了门边的笤帚,笤帚将腊生绊了一个趔趄。吴花捡起笤帚砸向腊生跌跌撞撞的背影。
腊生走得漫无目的,嘴里不停地诅咒着吴花,老婊子,瞧不起老子,假的,他妈的,都是假的,不就是嫌老子没钱吗?突然,腊生的脚又被什么绊了一下,他吓得一跳,低头一看才发现大黄狗跟在他的身边,他不知道狗是什么时候跟来的,或许他一出门就跟在他后面。腊生骂了句,狗东西!大黄狗轻声地叫着,回应着腊生。腊生背着手走在前面,大黄狗欢快地跟在后面。他们来到村中间的水塘边,腊生坐在塘坝上,大黄狗蹲在他身边。
腊生头疼痛得厉害。如果说腊生的头是一台搅拌机,开始只是装有水泥沙子什么的,刚才被吴花加水一搅拌,现在每个角落都被水泥块堵得严严实实。腊生双手捧起一捧水,洗了把脸,又用手使劲地揉着额头,试着将堵在脑子里的东西揉开。这时他看见一颗流星从空中滑过,又有人要死了。一想到死人,下午在父母坟边见到的画面又跳了出来,随之出现的还有吴花鄙视的眼神,它们就像毒蛇在不停地对着他吐信子,腊生有些胆怯和悲观。人活成这样,真他妈窝囊,连吴花这个烂女人也瞧不起自己,太没意思了。腊生的头勾到两腿间。
夜,跟随月亮的脚步越走越深。塘边,腊生和狗并排坐着,静谧的月光里氤氲着月季花的香味。微风吹过,腊生感到一丝凉意,他回头望了眼不远处的家。来喜“咯咯”的笑声似在耳边响起,这笑声如春天破土小草,顷刻在腊生的心里长出一片绿荫。突然间他有了新的想法,他想多挣点钱,把日子过好点,他不想让人看不起,最起码不能让孩子看不起。他得找一份长久点的工作,因为自己年龄大了,过两年厂里可能不会要他了。他记起有个同事说过火葬场工资高,好像可以干到六七十岁。以前怕别人笑话,现在想到只要自己生活得好,管别人怎么说。
塘面微波荡漾。轻轻柔柔的水把腊生的烦恼漾得干干净净。此时,他无比轻松和愉悦。他决定明天中午去找下表叔,看看能否帮他在火葬场找份事做。打定主意的腊生伸了个懒腰,起身向家里走去,后面跟着摇着尾巴的大黄狗。
第二天,腊生上班时来喜还在睡觉,腊生临走时还是到房间看了一眼。天阴沉沉的,春枝提醒父亲是否带把伞。腊生说,车上有雨衣,叫她不用担心。腊生轰鸣着离开了家,留下了一股黑烟,久久不得散去。大黄狗追去很远,直到腊生骑车的身影完全消失在眼中。
路上,雨果真下了起来,腊生见雨不是很大,也就不想停下穿雨衣免得耽误时间,迟到了扣钱不说,还得被主任骂。雨飘飘洒洒地下着,腊生的车子也越骑越快,当他在一个路口发现那辆工程车时,已经刹不住车……
天放晴了,空气被雨水冲洗得没有一粒尘埃,只有腊生家的大黄狗一直守在村里的公墓里,守在腊生的墓碑旁,时常发出低沉的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