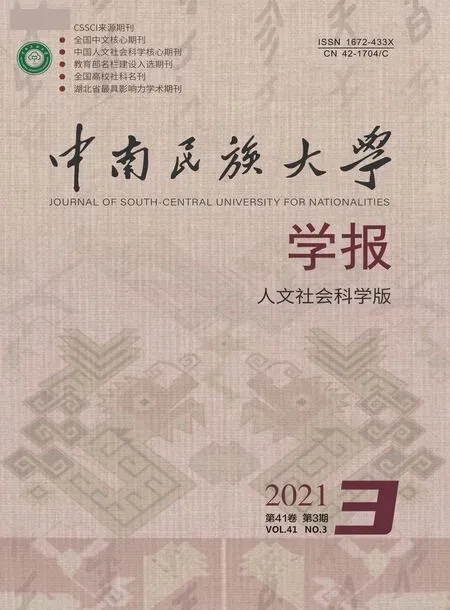诗歌,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
吉狄马加
就任何一种精神创造的成果而言,诗作一旦成为他者,或者说成为公众的读物,它就不完全属于原作者了,每一个读者都会对它进行属于自己的诠释,其实接受美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正因如此,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关心我的诗歌与读者产生了怎样一种关系,是否引起了必要的共鸣?因为作品一旦问世,它就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它的知音,也可以说这是在期待着一个又一个心灵的回声。能不能听到这样一些回声,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十分关心的。但是,今天这么多从事诗歌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相聚在中南民族大学,专门就我的诗歌写作及更广义的彝族文学进行讨论,的确让我感到内心不安。并非是出于所谓的礼貌和谦虚,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我所写的作品就足以劳动各位不辞辛苦在这里来开这样一个会。
需要说明的是,就当下彝族文学的现状来展开话题,还是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彝族现有900万人口,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现在从事写作的作家和诗人众多,这其中有用汉文写作的,也有用母语彝文写作的,许多作家和诗人都取得了足以让我们关注的创作成就,特别是一些更年轻的作家和诗人,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和天才的素质。在研讨会筹备之前,我就再三告诉会议的主办者,希望诸位把更热切的目光投向他们,因为他们代表了我们彝民族文学的未来和希望。
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已经走过了40年的写作历程。如果说诗人中也有幸运之人的话,那么我应该算一个。1985年我的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得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诗歌奖,那时候我不到24岁。1988年我的诗集《初恋的歌》获得第三届全国新诗诗集奖,也就是现在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前身,与我同时获奖的就有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北岛等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诗人,我来自于我所熟悉的文化,是这个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时代选择了我,也是这个让我的民族经历了千年不遇的嬗变的时代选择了我。
立陶宛伟大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在一个有关我的学术研讨会上,作过一篇题为“民族诗人和世界公民”的发言。他这样说道:“他公正地感觉到自己是生活在中国南方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儿子,是这个民族的代表和捍卫者,这一民族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民俗和传统,这一民族亲近自然,几乎与自然融为一体。这一民族保留了具有独特魅力的仪式象征体系、象形文字以及未被其他宗教和教义同化的泛灵论信仰。简而言之,她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对这种方式的认知,可以丰富我们关于整个人类的概念,也就是说,可以使我们更具有全人类性。这一生活方式的许多特征能教给我们很多东西,甚至可以为我们这个复杂化的、无限复杂化了的世界中每日出现的许多问题给出答案。”我不敢承受他给予我的这种褒奖,但我却把它理解为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在精神上的认同。诗歌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面对自己灵魂的独语,更重要的,它是我与这个世界进行对话的媒介。当然,这是一种经过创造后形而上的精神产物,或者说它是最具有个人性,而最终将获得普遍性的声音和密码。我认为,我所有的精神创造其实都是面对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头顶上无限光明的宇宙,引领我的祭司永远是无处不在的光;另一个就是我苍茫的内心,引领我的祭司同样是无处不在的光。他们用只有我能听懂的语言,发出一次又一次通向未知世界的号令,并在每一个瞬间都给我的躯体注入强大的力量,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肉体和灵魂才能去感知我获得的这一切。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想回应几个问题。
1.关于民族的文化历史对一个诗人的影响。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都是人类文明的儿子。这句话讲得非常深刻,也讲得十分到位,在我的身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彝族可以说是一个诗歌的民族,现在有九百多万人口。彝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的民族,大家知道,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达到了什么高度,其标志有几个方面:一是有没有自己的历法;二是有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特别是文字;三是有没有成系统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经典,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庞大的丰富的文化遗产,这其中包括了哲学、宗教、历史、天文、地理、文学等方面。熟悉文字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现有的原生文字里,最古老的就是汉文和彝文。彝文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从我们的先民创造使用这种文字到现在,它从未中断过使用的历史,直到现在它也是一个被继续使用的活态文字,据我所知,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特别是在今天的大小凉山,这种语言文字还在广播电视台、报纸、文学刊物上被广泛使用,今天到会的作家巴久乌嘎就是《凉山文学》的主编,这个刊物既有汉文版,也有彝文版,现在凉山州还有一部分作家诗人在用母语写作。另外,彝族有自己的历法——太阳历,在彝族古老的典籍里面就记载了这种古老的历法。历史学家刘尧汉和天文学家卢央也写过一本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书《彝族天文学史》,这本书从学术上第一次告诉了世界,彝族先民创造的太阳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何等的地位。作者在书中把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和印第安人古玛雅的十八月太阳历进行了比较,让我们对彝族古代太阳历有了一个更清晰更直观的了解。一个能在历史上创造了文字和历法的民族,可以肯定其古代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是令人赞叹的,毫无疑问,这都是我们写作者必须继承的伟大传统。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位诗人,那就是爱尔兰伟大的民族诗人叶芝,他虽然是用英语写作,但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历史感和文化感的诗人,那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古老的凯尔特神话以及深厚博大的爱尔兰民族的文化传统。正如叶芝本人所言,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的文化传统,他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的良心和代言人。而我作为一个诗人的写作,其文化传统既来源于我的民族,也来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当然我也深受世界不同国家优秀文化传统的影响。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
2.关于我诗歌创作的源头。我个人的写作有三个重要的源头。第一个源头是中华文化。我用汉文写作,如果没有屈原、李白、杜甫,没有唐诗宋词元曲,没有中国的现代诗歌,就不可能造就我这样一个诗人。第二个源头是源远流长的彝族诗歌传统。彝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也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其历史典籍基本上都是用诗歌的形式书写的。另外,彝族是世界上留存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彝族的英雄史诗、创世史诗就有十余部,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抒情诗,包括大量的民歌,共同构成了浩如烟海的诗歌遗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一伟大的诗歌源头,也不可能造就我这样一个诗人。第三个源头就来自于对世界优秀诗歌的借鉴和学习。我真正受到一个诗人的深刻影响,那就是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记得还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第一次读到一本完整的诗集,就是戈宝权先生翻译的普希金的诗,也可以说是因为阅读普希金的诗歌让我开始想成为一个诗人。现在回忆往事,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那本戈宝权先生翻译的普希金诗集,封皮已经撕掉了,等我如饥似渴地读到最后,才知道诗歌的作者叫普希金,诗歌的译者叫戈宝权,好在这本诗集的后记还没有丢失。
当然,我的诗歌写作,特别是我真正开始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我就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这一代诗人,都是中国现代诗歌写作的一种延续。如果从现代汉语诗歌来讲,对我影响最大的诗人就是艾青,这其中当然也还包括郭沫若、戴望舒、闻一多、穆旦等一大批人。他们都是现代新诗的先行者,无论从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而言,他们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今天再重写中国现代诗歌史,对他们的贡献都应该作出更客观公正的评价。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的,我的第一本获得全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写于那个时期。有研究者做过统计,它们都是我十九岁到二十三岁这个阶段写的诗歌。在我身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我的写作很像艾青他们那一代受外国诗歌的影响,我可能是中国少数民族诗人中最早受外国诗歌影响的诗人之一。我早期的写作主要是受到了黑人诗歌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美国黑人诗人麦凯、兰斯顿·休斯,另外,还有非洲诗人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马提尼克诗人埃梅·塞泽尔,等等。我和当时生活在西藏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经常在一起交流,我们完全是凭借一种直觉,还不能从理论上捋清其中的道理,就是为什么这些生活在亚文化地带的诗人和作家能影响世界,而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也都成为了被世界公认的一流的作家和诗人。这其中还包括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尤其是他们中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那个时候发现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福,完全是因为阅读他们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激动和欣喜。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最早在中国被翻译出版的《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真正的读者也不是太多的,而马尔克斯后来被中国文学界天天挂在嘴上,这已经是1982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事了。可以说,就是这些作家的写作给我那一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带来了颠覆性的飞跃。现在回想起来,我阅读诗人聂鲁达、洛尔迦、尼古拉斯·纪廉等人作品时,他们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真正通向世界的窗口,这种借鉴和文化上的受益无疑影响了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是优秀文学的价值判断。从大的方面讲,我们这一代少数民族作家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我的兄长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就深受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影响,回族作家张承志深受苏联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影响,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深受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等人的影响。我前段时间读一本非洲作家的创作谈,又再一次阅读了桑戈尔有关“黑人性”的理论文章,借此阅读机会我又把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为桑戈尔和埃梅·塞泽尔主编的《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写的序言重读了一遍,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作品在这个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上具有特殊价值的认识。桑戈尔后来不仅成为了一个誉满全球的诗人,他还是塞内加尔的开国总统,他是诗人中的大政治家,也是政治家中的大诗人。由于他对黑人诗歌的贡献,法兰西学院吸收他为院士,他还是第一个获得法国语言学博士的非洲黑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在大学时期的同学,同样是伟大政治家和诗人的埃梅·塞泽尔后来也被吸收进入法兰西文学院成为了院士,他过世之后,其灵牌也被请进了法国先贤祠,埃梅·塞泽尔对黑人诗歌和世界诗歌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
就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而言,我们这些人都是后来者。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是在前人创造的高度上进行写作,我在很多地方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中国现代诗歌头几十年的艰辛探索和实践,就不会有后来十分繁荣的中国新诗的局面。卞之琳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我多次去拜访过他,他明确地告诉我,郭沫若代表了中国新诗头十年的成就,不管后来有人怎么对他进行污名化,都不可能改变其经典诗集《女神》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他还告诉我,还在穆旦在世时他们就进行过这方面的交流。他们还认为就诗人的广阔和深厚以及对叙事和抒情的精湛呈现,艾青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这充分说明只要本着对中国新诗发展负责任的态度和严肃的学术精神,我们才可能对所有的诗歌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在这个方面我从卞之琳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受用终身的东西。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艾青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他作为一个伟大诗人所具有的高尚品格,还是他的诗歌所始终保有的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注,都对我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
3.关于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如何呈现在诗歌中的问题。我认为诗人的写作既是个人经验的表达,也要反映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经验,这就需要一个诗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具有人类意识,要通过个人的写作深刻地反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如何把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如何把个人经验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共经验,这一定是一般诗人和重要诗人的一大区别。我以为小诗人和大诗人的最大分别,就是诗人个体所书写的作品是否真正具有了普遍的人类意义。英国诗人塔德·休斯说过这样一句极为富有哲理的话,一个诗人如果把个人经验高水平地扩充入公共经验和社会经验,并因此获得更普遍的人类意义,那么这个诗人就会越伟大。他专门以爱尔兰诗人叶芝为例,认为叶芝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命经验,他还把古老的凯尔特神话和爱尔兰民族的反抗和复兴融入其中。正因为叶芝诗歌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叶芝毫无疑问就成为了爱尔兰民族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杰出代表。这种情况在20世纪并不是一个特例。
作为一个行动的诗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躲在书斋中的写作者。法国诗人雅克·达拉斯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一个行动的诗人,他认为行动的诗人在不同的历史上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让诗歌进入公众社会,与时代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文章中谈到了雨果,谈到了艾吕雅和阿拉贡,当然我非常愿意接受他对我作出的这样一个评价。在今天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中国真正开始举办高水平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与我的具体策划和组织是分不开的。还是20世纪末,我去哥伦比亚参加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从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歌大国,创立我们的国际诗歌品牌,我们一定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掌握我们的文化话语权和诗歌话语权。2006年我到青海担任政府的工作,这为我创办国际诗歌节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可能。2007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正式举办,由于诗歌节产生了广泛影响,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被世界诗坛公认为世界七大国际诗歌节之一。这七大国际诗歌节五个在欧洲,一个在南美洲,一个在亚洲,就是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现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大都与我有着特殊的关系,其中不少国际诗歌节都是由我策划主办的。什么是行动的诗人,我以为他必须把个人的文化理想和广泛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必须把个人的追求与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融合在一起,也只有这样,他的行动才是有价值的,他为这个理想和目标所奉献付出的一切,也才是有意义的。我力求像巴波罗·聂鲁达、阿拉贡、希克梅特、扬·里佐斯、勒内·夏尔这样的诗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一个诗人所负有的社会责任。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到这个现实中来走一遭,我们必须承担起人类所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生命本身或许是荒诞的,只有我们赋予了它意义,生命才会变得伟大而崇高。今天我们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来,真正把伟大的中国梦在文化中也变成现实。
我在很多地方说过,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也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未必在对外交流方面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只有在文化上成为这个世界的重要一极,并能在文化上真正影响这个世界,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国。有一个非洲作家告诉我,现在中国人的形象在全世界都很好,从来不去干预别国的内政,但中国人给他们留下的形象除了温良恭俭让外,更多的还是一个在经济发展上能影响世界的国家和民族,但我们的文化传播却很难形成与我们这个大国相匹配的地位。他还告诉我,我们今天与非洲有很多的经济合作项目,但文化上的合作项目却少而又少,也就是说,我们在当代文化方面对非洲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他还说:肯尼亚有个总统说过这样一句话,白人殖民了我们几百年,拿走了我们的资源,却给我们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本《圣经》,另一个就是殖民者的语言。他告诉我,虽然他们和殖民者之间有着复杂的情感和关系,但不可否认,今天的西方文化依然深刻地影响着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现实。他给我讲这些,主要是想告诉我文化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其他的影响更重要、更持久。不是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聚光灯已经打在了我们头上。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当然不是靠穷兵黩武,但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节点。我写《致马雅可夫斯基》这首长诗,实际上就是在回答人类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是诗歌的巨人,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在误读他,就像他在活着的时候被误读一样,有的诗人可能只存活在文本和修辞中,但马雅可夫斯基不一样,他会永远存活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记忆里。阿拉伯当代伟大诗人阿多尼斯就曾告诉过我,马雅可夫斯基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历史人物,他都要比他同时代的诗人更富有神奇的魅力,因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时代所留下的最深刻的痕迹。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我的诗歌《吉狄马加的诗》列入了“蓝星诗库”,有评论家对这本诗选中我二十五岁以前的作品进行了解读,他们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对彝族精神史的诗的阐释,特别是《自画像及其他》这一组诗,更能反映出彝族年轻一代在文化上的觉醒。这说明真正优秀的诗人必须既是诗歌文本的创造者,还是所置身于的那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
再次向诸位表示感谢,这么多朋友相聚在中南民族大学来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我真的感到有点受宠若惊。这绝不是谦虚,大家从四面八方过来,晓雪、李鸿然先生都已进入耄耋之年,还专门赶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令我非常感动。大家坚守秉持着严肃的学术精神,在富有成效的研讨中谈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聆听后深受启发,应该说收获是巨大的。当然我也感到有一点不足和遗憾,那就是谈我个人的写作比较多,而整体的谈当下彝族文学的情况偏少,我始终认为江山代有人才出,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彝族写作者都写得非常好。我在这里还是要提议,希望大家今后更多地关注彝族年轻作家和诗人的写作,因为他们代表着未来。特别是近20年来,彝族作家、诗人队伍扩展得很快,有很多人无论是在写作风格上、写作创新上,还是个性化书写上,应该说给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就我个人作品的讨论,我也感到有点遗憾,那就是大家肯定和表扬的成分多,而对作品提出的批评比较少。我原想能多听到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可能是大家出于客气,还没有真正完全做到畅所欲言。我想这只能在以后再召开研讨会时进行弥补了,特别是要有更多的研究者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研讨新人的作品上。俄国著名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对任何一个作家和诗人来说,批评家更容易看到另外一面镜子里的你。作为一个已经有40年写作经历的人,我认为,听取批评家和旁人的意见就更为重要,能认真聆听各方面的意见,这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见宛如苦口良药,对个人今后的写作既是一种启发,还会产生有益的深刻的影响。从创造的角度而言,伟大的诗人奉献给这个世界的诗句不是全部,或许仅仅是一部分,他们都是为这种神奇的力量所赋予的。
我想强调的还是那一句话,就是我非常希望听到更多的意见和批评,甚至那些激烈的批评,我也会视为一种宝贵的教诲。有人说我是当前中国被外国翻译最多的诗人,这是一个客观情况,这只能说明我们处在一个国际交流更为频繁和快捷的时代。我曾经给许多外国翻译家和出版机构说,不要忘记去翻译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那些优秀诗人的作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的作品很少被翻译到别的语言中去,比如说诗人闻一多、戴望舒和穆旦等人的作品。艾青的作品虽然已经有了许多译本,但真正高水平的译本还是不多的,过去他的译本大多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翻译出版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主要国家才开始翻译出版了他的部分诗集。作为一个重要诗人,他的作品无论是在翻译数量还是在翻译质量上都还远远不够。我的作品现在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已经出版了近九十个版本的外文诗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作为一个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诗人,毫无疑问我是幸运的,这最重要的是在我的背后有一个正在日益变得更加强大的祖国,那就是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中国母亲。
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来结束我今天的发言,这首诗的名字叫《或许我从未忘记过》:
我做过许多的梦
梦中看见过最多的情境
是我生长的小城昭觉
唉,那时候
我的童年无忧无虑
在群山的深处,我曾看见
季节神秘地变化
万物在大地和天空之间
悄然地转换着生命的形式
在那无尽的田野中
蜻蜓的翅膀白银般透明
当夜幕来临的时候
独自躺在无人的高地
没有语言,没有意念,更没有思想
只有呼吸和生命
在时间和宇宙间沉落
我似乎很早就意识到死亡
但对永恒和希望的赞颂
却让我的内心深处
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激
谁能想象,我所经历的
少年时光是如此美好
或许我从未忘记过
一个人在星空下的承诺
作为一个民族的诗人和良心
我敢说:一切都从这里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