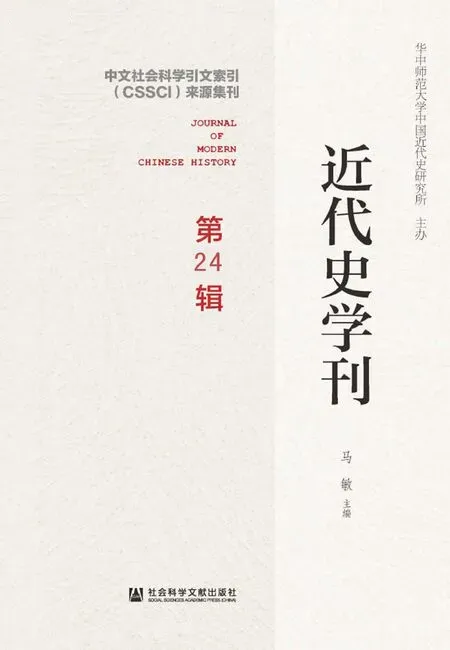近代更夫职业群体探析*
苏全有 王淑杰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重大转变,更夫职业呈现出濒危的生存状态。在经济收入低微,居住和穿衣条件十分简陋,工作环境极其危险,社会地位极端低下的种种因素下,更夫群体不堪重负,甚至许多人走向了死亡和犯罪道路。但作为历史阶段的产物,更夫不仅是民间的报时者、防火示警者、信息的传递者,而且是地方治安的维护者,承担缉捕盗贼之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夫更是近代消防、警察及巡逻保安的雏形。
更夫是指古代夜里靠敲更报时巡夜的人,在民间,更夫也被称为“打更的”。更夫虽然算不上近代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主角,但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在近代社会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近代更夫群体的兴衰诠释着这一时期社会地方治安的发展特征。随着社会环境的重大转变,更夫群体的职业功能与作用发生了变化,作为城市的边缘人、农村的守夜人,更夫收入低微、生活毫无保障,整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其生存状况及职业功能的作用值得我们关注。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学界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对下层职员、产业工人、苦力、游民以及个体生产经营者等群体的研究。但近代更夫群体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至今没有专著出版,相关著作仅有日本学者内山雅生的《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①〔日〕内山雅生:《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李恩民、邢丽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一书有所涉及,其中第三章第三节“打更与保甲自卫团”对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地区的打更与保甲自卫团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相关论文仅有所涉及,如姚俊香的《农村打更巡逻队的发展与完善》②姚俊香:《农村打更巡逻队的发展与完善》,《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多从农村治安管理角度出发提出打更巡逻队建立的必要性;李三汉的《打更巡夜员》③李三汉:《打更巡夜员》,《武汉文史资料》2016年第3期,第1页。对打更巡夜也只是简单论及。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更夫为视点,通过考察并梳理史料,探析更夫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职业功能和作用,以推动相关研究更加深入。
一 近代更夫的职业功能
更夫是一个古老的职业,起源颇早,早在《周礼》中就有一职官被称为“鸡人”,其主要职责就是报时。之后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时期。其名称的由来,则因古代习惯将一夜分为五更,这在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书证》就有记载。④程树德:《说文稽古篇(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57,第76页。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更夫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发挥着报时、巡更防盗、防火示警和传递信息等方面的作用。
(一)报时
更夫首要的社会功能是给世人报时,便于“作息推时”。在晚清之前,为了掌握准确时间,各府州县的更夫通常利用沙漏、烧香或水钟滴水来计时,同时要守着沙漏、滴漏或燃香,以便掌握住准确的时间。更夫夜里用更数表示时间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一更为戌时,时间是晚7时至9时;二更为亥时,是晚9时至11时;三更为子时,是晚11时至次日早1时;四更为丑时,是早1时至3时;五更为寅时,是早3时至5时。至此,也就到了通常所说的五鼓(更)天明了。⑤杜育群、刘辉雄:《警察巡逻综合执法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第30—31页。打过五更,读书上学的、出门经商的、开店经营的等等,就忙着起床生火煮饭,做各种准备,以免误时。乾隆末年曾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在讲述中国更夫时说:“更夫每天晚9点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5点。城里的街道笔直,夜里十字路口的大门要关闭。更夫巡夜从第一个门开始,直到他在中途遇到另一位更夫。他左手拿着一个竹筒,右手拿着一个梆子。从晚9点开始,每隔半个小时,就要敲打竹筒记时。”①刘潞、〔英〕吴芳思编译《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71页。晚清之前,更夫打更报时其实是一种较为粗糙、欠缺客观性的报时方式,其过程中对时间的掌控几乎完全依赖于更夫自身的经验,并非十分精准。
晚清之后,钟表的精准计时功能逐渐显露出来,在许多城市里,更夫的梆子依然会响起,但是更夫所用的计时工具已经被钟表取代,在某些广场及城市公共空间中更夫的报时功能开始衰退。如“晚清时的上海、福州、宁波等通商城市,公共大型建筑上通常都装有计时的大自鸣钟。民国时期,常熟、长沙等内陆城市也都相继在城市中心建筑物上安装钟表……随着现代市政建设的开展,南京、广州等大城市不但多在市中心建有大型钟楼,就连马路灯柱上也开始安装了进口的时钟”。②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23页。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生活节奏缓慢,钟表尚未普及,人们的生活起居仍然依靠更夫打更报时。如河北蔚县大部分村镇从立冬开始到翌年清明这一段时间,均雇用更夫数人,每晚轮流在全村范围内传街过巷,打更巡夜。此时蔚县农村尚无钟表报时,人们耕作劳动,生活起居,都是昼间靠响,夜里靠更。就连书塾里的青年学子,夜读经史,也称之为“三更灯火五更鸡”。特别是一些脚户、磨房等每天都要起五更,唯有打更报时,给人们提供了司时的方便,更夫成为最古老的“自鸣钟”。③河北省蔚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94,第133页。更夫精确的报时有助于人们时间观念的养成,进而促使人们对自己的活动和行为进行细致规划,达到更加合理安排生活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钟表普及,打更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时间的要求,更夫的计时功能自然而然地逐渐消失。
(二)巡更防盗
更夫的第二个社会功能便是巡更防盗,维护地方居民安全。晚清时期,由于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落后,街道没有路灯,一般使用煤油灯,光线昏暗,夜间行人常常会遇到不法之徒利用夜幕进行偷盗和抢劫。为了安全,地方政府大多雇用更夫夜间巡逻,除了打更报时外,还兼巡查盗贼等职责,发现可疑情况,协同地甲一同捕获。据1892年1月9日《申报》报道: “积窃某甲前晚三更时,在大东门外郎家桥地方东张西望,更夫见其形迹可疑上前盘问,甲飞步奔逃,更夫追至桥北将甲扭获,搜出锁匙、锁子、铁凿、铁柄等共二十余件及自来火一匣、当票三十余张,一并交十六铺地甲,由甲解至中局,请讯局员蔡蓉卿二尹升堂提讯。”①《更夫获贼》,《申报》1892年1月9日,第3版。1901年3月10日, 《申报》又报道:“去秋本城西门内,二十二铺尤姓家被窃,投上海县署报请缉查,迄今日久未获,前晚三鼓时,更夫某甲击柝至彼处,见一小偷伏处墙隅,执而搜之,则身畔藏有小刀及贼具甚多,遂协同地甲解送巡防局禀请讯究。”②《更夫获贼》,《申报》1901年3月10日,第3版。可见更夫所起到的维护社会治安作用其实比传达时间更为重要。
更夫巡夜防盗,冬季尤为重要,因为冬季是盗贼易发时节,所以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往往选择在冬季雇用更夫。据1902年12月13日《新闻报》载:“苏垣元和县金调卿大令,以现届冬令宵小繁多,诚恐各图司更难以照料,因自捐廉俸雇有强壮丁役一十五名,每图各派一人专司更柝,各图副役轮流司巡,如果获有盗贼,定必从重给赏,以示鼓励,说者谓大令此举,真为当务之急哉。”③《雇役巡更》,《新闻报》1902年12月13日,第9版。更夫在巡更治安过程中,如有功绩,地方当局会给予奖励。1897年10月19日,苏城高师巷崇义庵被宵小者盗得法器、法衣等物,为更夫所见,当即呼唤栅夫帮同捉获,翌晨解交北路总巡局,经局员胡大令提讯,饬责数百板,枷号示众,给更夫钱一千文以示奖励。④《更夫获窃》,《申报》1897年10月19日,第2版。同时,更夫失职也会受到相应的责罚。1894年8月6日《申报》载,保甲总巡叶临恭司马率勇甲按段梭巡时,见地方栅栏未闭,立传该更夫诘问,展喝笞四百板以儆将来,并将该铺地甲严行申斥,谕令嗣后更夫如有疏忽,惟该铺地甲是问。⑤《更夫受责》,《申报》1894年8月6日,第3版。
民国以来,更夫的社会职责已不单是击柝报时,巡更报警,以防盗贼。尤其是近代以来在通商口岸设立的租界,更夫职业已经逐渐转变为具有巡警职能的武装警察。从某种意义来说,更夫职业具有近代巡捕及警察的雏形。如上海租界后来有名的巡捕就是从更夫演变出来的,1845年的《土地章程》规定允许租界招募华人充当更夫,当时租界内的更夫职责极其简单,无非负责夜间巡逻,有事击鼓报警,无事打更报时,以防宵小。又规定“雇用更夫由洋商与华民妥为商定,其姓名由地保、亭耆报明地方官宪查核。更夫条规应予订立,其负专责管领之更长,由官宪会同遴派”。①姚远:《上海租界与租界法权》,上海三联书店,2016,第224页。1854年,新《租地章程》签订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民间自助式的更夫被职业化的籍外警务机构——巡捕房所代替。②姜龙飞:《上海租界》,文汇出版社,2014,第89页。然而,更夫职业的现代转型在民国时期仅存在于诸如上海租界等较大的通商口岸,在其他地区更夫仍为传统意义上的“敲竹报时,巡夜报警”之人,未与武装警察相关联。如1924年甘肃警务报告:“本厅前据调查员魏炳南条陈,以现当防吃紧之时,每入深夜各区警士等各守岗位,自有一定地点,稍一大意,防务上即有疏忽之虞,兼以今岁米珠薪桂,无业游民更较往年为多,饥寒所迫在堪,虑似省桓防务较之往年尤为重要,拟请查照从前办法,训令各区通饬各街甲长、牌长人等,于冬防期内务各雇用更夫多人,每夜沿街梭巡作警察之声援,以期周密庶资保卫等情,昨业经处长批准,令行各区署遵照实施矣。”③《本省警务实录:厅令各区认真规复各街市更夫》,《甘肃警务周刊》第54期,1924年,第19页。此时的更夫仍然承担着巡夜防盗的职责,政府筹添更夫是为辅助警力之不足,以便维护地方治安。
除此之外,在广大农村地区,更夫巡更防盗的职能也有所变化,一般分为两种形态。一是由村民共同负责轮流打更,二是由村民委托更夫来负责村内警卫。以华北地区的沙井村为例,民国初年,实行的是更夫负责的“夜间巡逻”,但在1940年之后,人们再次去调查沙井村时,发现打更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每天治安好的时候5个人左右去打更,不好的时候10—15人按地轮流打更。④〔日〕内山雅生:《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第103—104页。沙井村的打更由专人负责变为村民轮班负责,这样的变化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将打更与组织保甲自卫团同等看待的结果,以便加强地方治安。
(三)防火示警和传播信息
除了报时、巡夜防盗外,更夫还具有防火示警和传播信息的功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一个历代沿用的“喊火烛”的消防习惯,这也就是更夫的防火示警功能。临近冬季黄昏时刻,更夫通常会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关好门窗,小心火烛”,以此警示百姓注意防火安全。晚清时期,更夫在防火示警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894年,“金陵水西门外草屋极多,距正街各店不远……前夜有人持火绳燃,某姓茅屋因雨后茅湿,火不易燃,泼以洋油,正欲燃着,适更夫蹲暗处大解,突起擒之,大呼放火,四邻并起烛之,素不识面,问何仇至,此亦不答,地甲带回拷以私刑”。①《放火被获》,《申报》1894年4月16日,第2版。1903年1月21日前晚一下钟时,沪城大南门内,货店披屋内忽然失火,霎时轰轰烈烈,势若燎原,远近更夫见之,立即鸣锣报警。②《沪南火警》,《申报》1903年1月21日,第3版。1911年,更夫防火示警的功能仍然存在,据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的文件记载: “前夜二句钟,伪督署失慎,数处消防队驰往,施救不及,即掩灭无余烬。诚有多数水夫之臂助,收效当为尤速。拟请嗣后夜间如有火警,无论警署得知与否,希饬更夫鸣锣遄报,俾获登时出笼,庶几星星之火易熄;更烦代促附近有力居民,群起灌援,敞处定即量予筹资,以慰劬劳。”③赵志飞主编《中国晚清警事大辑》第1辑,武汉出版社,2014,第27页。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防火宣传和管理往往无人过问,消防常识很不普及,就连国民党警政局也不得不承认:“惟是我国未臻普及,消防知识,更属缺乏。一般民众,平时未能合理之预防,偶一失慎,则张惶失措,施救无术,轻则丧失财产,重且伤及生命。”④陈文贵、吴建勋、朱吕通主编《中国消防全书》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第10页。由于民众消防知识的缺乏,各地消防设备的短缺,此时全国各地仍然依赖更夫打更达到防火目的。如湖北嘉鱼县的鱼岳、簰洲两镇均设有更夫,夜间敲竹梆,提醒“小心火烛”。⑤湖北省嘉鱼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嘉鱼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99页。新兴县每到秋冬季节的晚间,城乡均设有更夫过街串巷巡行,敲响竹筒,报时防盗,呼喊“提防火烛”的防火警语。⑥新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新兴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478页。衡阳县各城镇配有更夫巡逻,鸣锣提醒人们注意防火。⑦衡阳县志编纂委员会《衡阳县志》,黄山书店,1994,第411页。更夫防火示警,作用不可低估。
除此之外,更夫还可以传达一些消息,起到通知的作用,如传达县衙、县府号令指示。更夫在打更时通常喊道:“大老爷吩示,天气亢阳,小心火烛。”“各路团总即刻到县府去,县长有事交代。”①邛崃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邛崃文史资料》第14辑,2000,第171页。到了抗战时期,这种警示和传播的功能作用,为动员群众和通报敌情搭建了一个特殊的平台。《涪陵人民抗战纪略》一书记载了抗战时期涪陵县更夫的抗日行动:“更夫每晚走街串巷,提醒人们小心防盗,敲梆打锣唱更报点拖长声音的唱词:‘月黑头,惊醒些,日本人,把我欺。东三省被占去,还占北平和天津,现又占去上海和南京……’”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涪陵区委员会编《浩气福州涪陵人民抗战纪略》,重庆出版社,2015,第320页。更夫所唱使人难安枕席,不忘国难,使得城乡群众的抗日热情甚是高涨。同时,也有利用打更传递情报。1942年,为了保护淮南津浦路西至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北线交通,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和中共皖东工委在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开展抗日斗争。“交通线上游击区的群众积极支持配合,各保甲以自然村组织打更队,以敲梆子、点火把、吹牛角、插红、栏杆为信号,只要敌伪顽军一出动,群众就发出信号,交通站便一站接一站传递情报,使我区、乡政权和武装能迅速行动起来,研究对策、打击敌人、保护交通线。”③安徽省邮电管理局编《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淮南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6,第70页。新中国成立后,更夫就成了历史,但是“打更”仍然被用作宣传工具。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乡村政府常在晚上组织小学生“敲更打鼓”搞宣传,一边敲一边喊“穷灶头,富水缸,防火防偷不能忘”“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婚姻要让儿作主,奉劝长辈莫包办”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④沈成嵩:《江南乡村民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第122页。
近代中国的更夫不仅是民间的报时者、信息的传递者,而且是地方治安的维护者,承担缉捕盗贼之责,从某种意义来说,更夫更是近代消防、警察及巡逻保安的雏形。
二 近代更夫职业的生存镜像
随着近代社会环境的重大转变,更夫这一职业呈现出濒危的生存状态,但至民国年间,时钟尚未普及工农家庭,广大百姓仍以听更知时辰。打更是一个劳动时间长、收入微薄且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职业,并且整日挣扎在生存线上,与人力车夫、粪夫、苦力等相差无几,其生存镜像值得我们关注。
(一)更夫的收入
就更夫的经济状况而言,其收入极其低下。近代中国的更夫,除了受雇于地方当局的更夫领有薪金外,一般由地上的街坊、店家和地主等集资雇用,多由失去劳动力的孤苦老人担任,这类更夫收入比较微薄,他们的薪资一般以月计算。如从1903年江西省颁布的《江西详办罪犯习艺所章程》中可见,处于社会上层的各级官员,收入颇高,月薪一般在几两到几十两不等。如督办、提调、驻所专管,每人月薪水银36两;知府为正办,月薪水银20两;司事月薪8000文;监工月薪4000文。而杂役的工资,则因行业不同而有区别:听差、把门、管厂管号等杂役工资,每人月薪2000文;厨役、火夫、皂役、更夫工资每人月薪1600文。①范佑先主编《江西省司法行政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232页。清末支付工资多用银两、铜钱,按照1903年时江西的银钱比例标准——1两银子换制约1600文铜钱来计算,②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江西省志》第43卷《江西省财政志》,1998,第76页。作为杂役中收入最低的更夫,其工资收支大体能够相抵,维持基本的生存。但这部分更夫毕竟是少数,并非每个更夫都能达到。如清末成都地区更夫的月薪为500—600文钱,③《成都之百工价目》,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第500—508页。可见收入之低。
民国时期,社会动乱,物价起伏不定,更夫的工资仍旧是各行业中较低的一种。此时的工资支付一般使用银元、铜元及法币。如1931年,赤峰街内各职业的月薪大约是:工役8元、厨役6元、更夫4元、店员5元、成衣工15元、老妈子33元、马弁8元、车夫7元,苦力工4元、司机30元。④赤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赤峰市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第2228页。1933年,湖北枣阳市月薪标准仅6元,⑤湖北省枣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枣阳志》,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第546页。北平更夫的月薪标准仅3元;⑥菁如:《北平的更夫》,《大公报》1933年12月25日,第13版。1935年,四川威远县更夫的月薪标准仅5元,并实行八折支付工资;⑦四川省威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威远县志》,巴蜀书社,1994,第581页。内蒙古宁城县更夫的月薪标准仅6元。⑧吴殿珍主编《宁城县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第984页。由于更夫归地保管辖,一般由地保向各住户收钱,每家每月1—2角不等,需视住户贫富而定,按住户所纳的更钱,足以赡养更夫有余;但由于层层的盘剥,民国时期的更夫月薪水平只在3—6元,堪比苦力工,收入十分低下。总体来看,更夫收入微薄,经济拮据,生存状况极其艰难。此项收入尚不足维持个人最低的生活,如果再有家庭之累,更夫将陷于极窘困的地步,所以他们多半除打更之外,另有兼职,如倒秽土及其他出卖劳力的工作,以补足生活。
在广大农村地区,更夫甚至没有工资,其生活主要靠逢年过节时地方上凑些钱或米粮给予资助,很是艰辛。以民国时期四川临邛镇为例,临邛镇的更夫除了为村里居民帮办红白喜事、驱赶乞丐的骚扰,获得几吊钱的酬金外,在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来临之时,便手持罗盘沿街挨户讨取赏赐,一般是3文或4文;遇到卖肉的,屠家会给一小块肉。另外,在冬天卖炭火也是更夫的生活来源之一,卖炭火一般在黄昏时,通过给人家火笼里添炭火赚点钱,一笼火卖3—5文不等,视火笼大小而定。卖火之后接着去打更,其辛劳可想而知。①《邛崃文史资料》第14辑,第172页。
(二)更夫的居住与穿衣
近代中国更夫群体在夜间为他人提供服务,并没有因为勤奋的劳作换取幸福生活,而是彻夜劳作,却仅能糊口养家,其生活水平堪称极端低下。首先,更夫的居住条件极为简陋,他们居住的更房或更棚,是各乡镇商民为保障财产安全,集资雇用更夫设立的。在城市,更夫一般携带家眷居住于更棚,其住所“约板为之,仅容坐卧,规制狭小,聊蔽风雨”。②《更夫多事》,《申报》1884年7月19日,第10版。更棚规制狭小,环境极为简陋,曾因其弊病一度被废除。晚清时期由于直隶地区各州县的四路捕快吏治十分腐败,“包赌窝娼,恣行乡里……转招盗贼,以为收赌、规敛盗费地步……甚至与贼坐地分赃”,政府大力裁减差役,并规定“各州县旧设窝铺、更棚以及四路捕快,如详一概革除,仰即通饬各属遵照办理,仍责成巡警认真责缉,以靖地方”。③《文牍录要:臬司详请札饬各属裁革窝铺更棚及四路捕快文并批》,《北洋官报》1906年第1010期,第4—5页。此项措施,使得直隶地区裁减差役冗员、除弊安良的步伐得以加快,但对于打更者来说无疑是噩耗,仅能遮风避雨的场所也不复存在了。在农村,更夫所住的为“更房子”,或筑村头,或垒高处,空间皆狭小,仅一灶一炕间有一矮墙而已。①周惠民:《风情开原》,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第229页。条件更差者多居住于寺庙。1936年《申报》所载之文描述了打更者的居住状况:“打更的是一个矮小的老人,他有一对厉害的近视眼,我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起就做了这行业的。而且镇上人对于这行业也从来就没有看重过。他没有打更的月费,也没有一所可以避风雨的更楼,让他孤独住在土地祠里。”②《打更者》,《申报》1936年12月26日,第15版。可见更夫的居住条件之简陋。
其次,近代中国更夫的穿衣,十分破陋。1925年《寒夜里的更夫》一文描写了更夫的衣着之旧:“他于是鼓着精神,将绳子把他的短破衣好好缚住,脚上拖了一双破皮鞋。头上戴了一顶旧毡帽,上面更加上一个斗笠;点了灯笼里的火,携了竹筒和木棒,预备去到那凄凉的街头,过他的‘柝、柝、柝’的生活。”③何雍然:《寒夜里的更夫》,《婴宁月刊》1925年第6期,第4—5页。更有甚者,是任何御寒之物都没有。1933年的《大公报》上记载了北平更夫的生活状况:隆冬之际,更夫在夜间打更巡夜之时,“除了自治区发给一件单背心,上面缀以‘□□区□□坊更夫’以外,任何御寒的东西都没有,自己随便穿着破布夹着败絮的棉袄,就那样与寒风相奋斗”。尽管“去年自治区会为了给他们买皮袄,向住户捐去了许多钱,然而,迄今也没有看见更夫穿上皮袄,中国官场内的黑幕,委实令人不堪尽言”。④菁如:《北平的更夫》,《大公报》1933年12月25日,第13版。于此可见,更夫生活十分艰苦。
(三)更夫的工作状态
就工作环境而言,更夫经常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尤其是在近代社会动乱时期,土匪、强盗、打家劫舍的盗贼颇多,更夫工作环境之危险、生活环境之恶劣是其他职业不能相比的。由于近代治安制度和道路设施尚不完善,更夫夜间在各街道打更敲柝时,往往成为盗贼攻击的首要目标。作为一种高危职业,更夫被盗贼打伤、打死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的报刊常报道此类事件,如1900年8月15日更夫遇贼被伤:“芜湖税务司公馆于本月15日之夜,突有梁上君子乘机溷入,毁楼下浴定之门,更夫陶选华闻声来视,贼出怀中小匕首,迎面猛刺,致左耳被削几堕,耳后及太阳穴亦划破甚深,痛极狂呼,惊醒诸仆,贼急奔逸,踪影杳然,遂禀知税务司墨贤里君,函请当道严缉。”①《更夫遇贼》,《申报》1900年1月26日,第2版。更夫丧命的情况时有发生。1908年9月8日更夫被匪溺死:“杨树浦祥泰木行,更夫二印人,被匪击伤一人,拔去一人。其拔去之人当被抛入浦江,前日午后尸身在桥畔浮起,缚有麻绳,由捕捞起送入验尸所,昨由西医会同英领事验明候殓。”②《更夫被匪溺死》,《新闻报》1908年9月8日,第18版。1924年5月11日更夫被人谋毙:“麦根路看守石子滩之更夫通州人冯实实,于前晚被人谋毙,昨晨,经陈姓工人所见,报告新闻捕房,饬探沈寿章协同西探前往。查得死者鼻中流血不止,颈中系有撕碎布衣,遂将尸体移入虹口斐伦路验尸所,候报请公共公廨中西官莅验。”③《更夫被人谋毙》,《申报》1924年5月11日,第15版。
就工作职责来看,夜间打更者如若未尽职责,不仅会受到责罚,可能连本职工作也要丢去。如1880年1月7日,漳江巡局办理冬防时规定:“各段栅栏二更后即须封锁,各管段员并查察,遇有未即遵奉者,皆惟更夫是责。”④《更夫遭殃》,《申报》1880年1月7日,第2版。此令一出,更夫固然不敢不按时封锁栅栏,但差役、家丁、游民、无赖往往三五成群,横行无忌,偶为阻拦,势必动拳。所能禁止的只有商人及居民而已。但无论何种缘由,皆是更夫受责,可见政府对这一职业的苛刻。1894年8月6日便有更夫受责的报道:“保甲总巡叶临恭司马督率勇甲按段梭巡,行经八铺书锦牌楼地方,见栅栏未闭,司马大怒,即传栅夫究问,栅夫诉称未打三更,是以未闭,司马曰刻已一点半钟,何以不打三更,立传该更夫诘问,更夫供小的已打三更然后回去,司马怒其狡,展喝笞四百板以儆将来,并将该铺地甲严行申斥,谕令嗣后更夫如有疏忽,惟尔是问。”⑤《更夫受责》,《申报》1894年8月6日,第3版。1900年8月25日便有更夫被革职的报道:“前晚二十三七铺更夫李元春所居栅栏,不戒于火,熊熊之势几肇燎原,幸即汲水狂浇得以扑灭,局员盛雨村二尹查悉情形,以更夫漫不经心,咎难宽恕,立命提案斥革,易人承充,以儆疏忽。”⑥《更夫宜革》,《申报》1900年8月25日,第3版。
就工作时间来看,打更看似简单,实则很辛苦。更夫每夜按规定的线路巡视,更次的间隙可以打个盹,同时要守着滴漏或燃香准确掌握时间。有一首诗形象地再现了更夫整夜巡更的情景: “他敲打着寂静,背负着黑暗,行走着,那像一颗萤火虫的,是他手里提着的灯,它给夜行人一线光明,敲着,敲着,他敲着,第一个先知——雄鸡,终被他敲醒,于是破晓之歌升起,他不声不响沉默地去休息,让那些万物去拥抱黎明。”①其:《更夫》,《燕京新闻》第15卷第7期,1948年,第1页。
三 近代更夫职业的社会现状
(一)更夫的社会地位
近代中国更夫群体处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底层,拥有很少的权力,普遍处于一种“地位低下”的状态。晚清时期更夫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是“为庸人中之一尤,为庸人中最辛苦,最轻贱之服务”,②灨一:《更夫娶小姐之奇谈》,《时报》1915年6月4日,第15页。而且更夫多为汉人。1907年8月,清政府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将军为旗民另谋生计。在变通旗制的过程中,清政府基本上是依据“旗丁授田,俾之归农,辅之以兴办实业和教育”这一原则来安排旗人生计,以此保障旗人生活。③郑师渠、史革新、刘勇:《文化视野下的历代中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第474页。此谕着眼于全体旗人的整体利益,对于满人而言,即便是衣食无着的败落户也不大可能以更夫为职业谋生。故考察更夫之身份,可以推论出晚清从事更夫职业的多为汉人。就中国传统的社会职业分工来看,更夫的职业地位极端低下,再加上有清一代汉人的地位,更夫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民国时期,更夫的社会地位亦是如此。以北京典当行为例,当铺更夫除夜间围绕库房打梆巡更以外,并管帮厨、杂勤、扫地、生火、开门、上门、打发饭(伺候人员吃饭)等杂役。他们与—般伙友待遇是不一样的,被看成仆役,在考勤账(记载工资待遇的簿册)上,一般成员都是记名的,独有更夫只记某姓,如李更、赵更等,并且排列最后,降低一格书写。在经济待遇上,除工资差别外,零钱等项亦不同于一般成员。④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23辑,北京出版社,1985,第219页。这都表现了封建等级观念。在一些散文中亦可以看到对更夫职业的描述:“更夫执业之微贱者也。且多庸懦无能之徒。以之查拿鼠窃狗偷则可,以之防御大盗则不能。”⑤焕新:《更夫之廿载繁华梦(上)》,《齐塘月刊》第5卷第4期,1930年,第62—64页。
同时,更夫的政治地位也很低下,这与该群体的涣散性有关。近代中国从事打更职业的人员虽然数量很多,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组织性、纪律性的更夫群体组织。尽管早在1929年7月开始,《时报》上便发布通告成立黄埔商轮更夫工会的消息,提倡工人自治,①《黄埔商轮更夫工会成立》,《时报》1929年7月12日,第5页。但最终还是被撤销。1929年10月30日有报道曰:“查该黄浦商轮更夫工会,向各船户违法勒索更费,查明有据,且与本市工会注册暂行规则之规定相违,业经将该工会执照图记缴销,并将其所设各支部停止活动在案,准函前由。究竟是否该工会仍复违令勒索,抑有匪人借名敲诈,均应查明依法究办。”②《黄浦商轮更夫工会》,《申报》1929年10月30日,第16版。更夫工会在维护更夫权利、救济更夫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作为。
(二)更夫的身心状态
经济收入微薄、工作环境极端危险、生活条件极其窘困、社会地位极端低下等种种因素相互叠加,可能导致更夫身体功能的衰退甚至走向死亡,或者不堪心理的重压走上犯罪道路。
迫于长期的劳累、物质匮乏的折磨,加上夜巡的危险性高,更夫患病的现象极为普遍。如《神州国医学报》载,广东更夫郑纪耀患有怪病,“大便闭塞,竟有匝月未曾排泄,虽则服药疗治,迄无效验,因此腹大如五石瓠,涨闷难堪,怨愤填胸,突于十九日下午八时,由家走出投浦自杀”。③《更夫患怪病投浦》,《神州国医学报》第3卷第10期,1935年,第21—22页。也有更夫出于精神和身体的压力,选择死亡。如1933年3月1日《新闻报》载:“大昌绸缎庄更夫浦东人王景初,年五十九岁,在该庄任事已久,王平日勤俭无奢好,忽于昨日上午二时许,在该庄后门内楼梯栏上自缢身死。”④《大昌绸庄更夫自缢》,《新闻报》1933年3月1日,第14版。1948年7月3日《新闻报》又载:“永安公司屋顶花园更夫高邮人周仁,四十一岁,近因物价上涨,不堪生活高压,忽告神经失常,昨晚七时一刻,身穿汗衫黑短裤,突自六层楼饭厅平台上纵身跃下,跌自南京路浙江路口马路边,脑浆迸裂,肢体骨断,当场毙命,由警将尸车往验尸所候地检处派员检验。”⑤《永安屋顶花园 更夫跳楼殒命 受物价刺激神经失常》,《新闻报》1948年7月3日,第4版。更夫这一职业整日挣扎在死亡线上,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不但经受着缺吃少穿的折磨,还要忍受着身体折磨和精神的压力,其生活状况堪称极端低下。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更夫自身生活的需要,再加上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他们很容易行为失当走上犯罪道路,影响社会的治安。《新闻报》曾多次报道更夫犯罪案件,如1926年9月6日,更夫窃取油行大批桐油。①《请究更夫串窃商货》,《新闻报》1926年9月6日,第9版。也有因犯罪判处徒刑者。如1934年7月2日,某公司华更夫王铁甫,上月串同张叶氏,将邓王氏之十六岁女银弟,诱往沪江旅馆,至午夜同睡一床,乘隙将银弟奸污,翌晨女返家,据情告知乃母,遂投报榆林路捕房,女送广仁医院验明属实,嗣经华探目李鹏飞密往按址将王逮捕,判决王有期徒刑三年六月。②《强奸少女 更夫判处徒刑》,《新闻报》1934年7月2日,第15版。
由上可知近代更夫的生存镜像,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在近代中国早期城市化的背景下,更夫虽然算不上社会治安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角,但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更夫不仅是民间的报时者、示警者、信息的传递者,而且是地方治安的维护者,承担缉捕盗贼之责,从某种意义来说,更夫更是近代消防、警察及巡逻保安的雏形。同时,更夫是一个劳动时间长、收入微薄且社会地位极端低下的职业,并且整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与人力车夫、粪夫、苦力等相差无几,其生存镜像值得我们关注。从近代社会群体而论,更夫是一个很好的视窗,一面很好的镜子。晚清之后,中国社会在外力刺激和推动下,被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城市里的更夫逐渐转变为巡捕或警察,其社会功能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治安条件差,警察很难下乡巡逻,再加上农村地区钟表并未完全普及,以及受到传统风俗的影响,更夫仍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钟表的普及,更夫职业逐渐消失。更夫职业的消失有一定的必然性,符合社会城市化的进程。从定义来看,更夫本指旧时打更巡夜的人,显然,“旧时”把“更夫”一词的运用给限定了。查阅《现代汉语词典》,1965年《现代汉语词典》(第二版)中有“更夫”一词,1996年的《现代汉语词典》 (第三版)中已无该词,原因便是社会的变迁。如今,“打更”已经成为历史,但更夫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忽视,其所反映的不仅是近代城市及乡村基层社会的图景,也有中国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