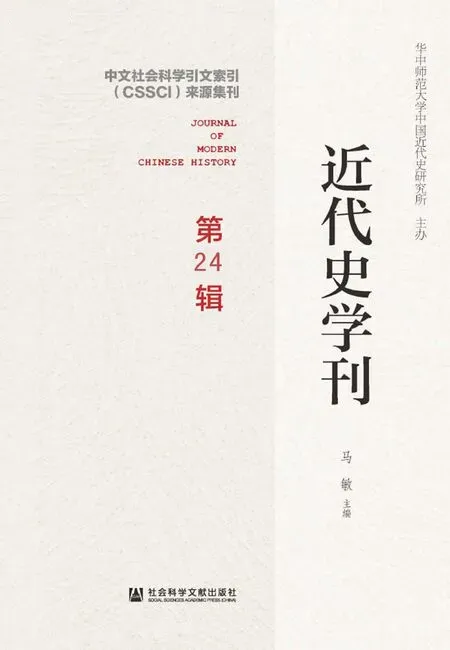权势干预与学术独立
——以周天健入职史语所为中心
张 辉
内容提要 1942年因日寇入侵而辗转播迁于大后方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不拟招人、违反院章的情况下,被迫吸纳仅有高中学历的周天健为助理员。此事过程异常曲折,名义起初由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分发为助理研究员,然后变相操作为该院院长戴季陶私人推荐。对于处理此事的态度和方式,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之间分歧严重。在权势干预下,最终史语所不得不妥协接纳。这看似平淡不惊的人员入职事件,其实背后暗潮涌动,引起的往还纷争不仅隐含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而且牵涉学术机关下的学人群体在权势干预与学术独立之间、社会现实与学术理想之间的两难抉择。
向以“拔尖主义”招选青年后进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借助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吸引了众多学有专长的学界精英汇聚一堂,在民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至今犹为人津津乐道。该所的发展历程曲折艰辛,其中人才招选便时常受到外界或大或小的干扰。相对于考试的公平公正而言,个人推荐就不免掺杂各种人事关系和人员取舍标准等问题,遇权势干预时,更是难以抉择,处理不好就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影响学术机构的走向甚至生存。
1942年刚刚辗转播迁于四川李庄的史语所立足未稳,即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考试院铨叙部①铨叙部为民国时期考试院的附属部门之一,为最高铨叙以及公务人员人事主管机关,负责任免、升迁等事项。分发高考及格人员周天健(1922—1995)至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 “指令”派至史语所任职助理研究员。考试院此举属行政分派,而向来主张学术独立的史语所是接受还是拒绝?此事在史语所所长傅斯年(1896—1950)与中研院院长朱家骅(1893—1963)之间引起了纷争,过程复杂曲折,焦点集中在铨叙分发与高中学历上。本来此时史语所限于经费紧张、职位饱和,不拟招人,①《董作宾致王献唐》(1942年8月10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李3-2-11。但迫于权势干预,最后还是妥协接纳了周天健为助理员。
此事台面上看似风平浪静,其实背后暗潮涌动。此中不仅隐含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与身份认同诸问题,而且牵涉学术机关下的学人群体在权势干预与学术独立之间、社会现实与学术理想之间的两难抉择。对此事件,目前还没有见到相关的解读分析。所以本文借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档案、广东省档案馆档案,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力求深入内幕,究明真相。
一 周天健入所始末
1942年7月16日,考试院铨叙部分发高考及格人员周天健至中研院,“指令”派至史语所工作。18日接到公函后,中研院秘书长刘次箫(1888—1950)认为事属紧急,迅即致信总干事叶企孙(1898—1977)商讨。23日,叶企孙回复如下:
十八日惠书敬悉,铨叙部十六日来函似可照下意答复:本院聘请研究人员时,向例由各所长根据工作方针及预示情形拟定人选,向本院之院务会议或人事管理委员会提议,经审查资格与本院所定规程(可送一份去)符合,然后由院长核准。又本院之研究人员及事务人员一律不铨叙。经高等考试及格者,其学识谅已有相当程度,其中有愿来本院担任研究工作者,自可由贵院向本院推荐,并请以履历、考卷、考分及考作送本院,以便发交有关之所长照规程审查。倘其学历及研究成绩合乎规定,本院当可照聘或照任。至于用分发手续,则因本院与其他政府机关性质不同,似非所宜。又助理研究员之资格见本院《研究所组织通则》第十一条,请注意高考选择个人时,所注意之点与本院或有不同,不敢不慎重考虑。尚祈贵部原谅为荷。上拟之覆文,大意是否妥当,敬恳转请院长指示。陶傅两先生处是否宜先征求意见,亦祈请院长决定专覆。①《叶企孙致刘次箫》(1942年7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
此复函透露出三点信息。第一,考试院铨叙部分发高考及格者周天健至中研院,拟任为助理研究员,此属行政强制行为。第二,中研院的人事有很大的自主空间,不是考试院的下属单位,故不受其节制。而院内聘请人员,有一套例行标准和规则,向由各所所长推举至院,经院务会议或人事管理委员会商讨,由院长决定。第三,铨叙分发人员至中研院,与院章不符,②《研究所组织通则》第十一条规定,研究所职员的任免权由各所所务会议决定。参见刘桂云、孙承蕊选编《国家图书馆藏国立中央研究院史料丛编》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7页。不予接受。但可私函推荐,备齐资料,以备审查接纳与否。
本来如此回复,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又顺水推舟给考试院一个台阶,可谓两全其美。但是,报告送至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处后,他于28日批复:“可将戴先生致孟兄书大意,电孟兄征求意见。戴先生甚知本院情形,且极重视,故其致孟兄函,须私人性质。高考及第者,无论如何可等于大学毕业。仅一助理或研究生应予照办,否则恐与本院前途影响太大也。”由此可知,朱家骅避而不谈铨叙分发之事,而是单方面视此为考试院院长戴季陶(1891—1949)的私人推荐,应予以接纳。指示仅以大意而非原函或抄印件告知孟兄,可以想见铨叙部原函③遗憾的是,笔者经过再三寻找,还是未找到铨叙部原函。但从叶企孙小心谨慎的复函,可以想见原函内容之大概。的官方语气及朱家骅的考量。他还有意拔高道:“高考及第者,无论如何可等于大学毕业。”此等自说自话实难令人信服。但亦不能不承认此为“大局”着想,不意因安插“一助理或研究生”而累及全院,“否则恐与本院前途影响太大也”。
接到批示后,刘次箫遂即附上叶企孙拟函,并将铨叙部公函大意函知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字孟真),即上信中所提“傅先生”“孟兄”。傅8月7日回复如下:
奉复敬悉。覆铨部信,弟与叶总干事意见相同,叶总干事陈兄信,弟觉可用,似可加二事:一、即告院研究人员与大学之教授助理情形相等。若以分发手续办理,恐机关与分发者皆感不便,仍请斟酌。二、大学部毕业,若干年中,本院对之薪额至微,固实为学习性质,与荐任或高级委任之待遇薪额不合。
我公一而对铨叙部表示不能接受分发,一而对周君只好试用。以若戴公私人介绍,而其措词姿态如此客气也。但请兄向周君言:①我们可按照戴公私人之介绍,非按铨叙部之分发。②把《章程》给他看,他只能作助理员,不能作助理研究员(除非寄有相关著作来,审查合格)。③为求学业,此间甚好,弟等当尽力助之。④为求资格,本所殊无此资格,因本院人员皆无铨叙也。⑤荐任待遇,乃二百数十至四百数十元,但彼在本院之资格是为助理员,即仅百余元,此须牺牲者也。
总之,为学问可以来,即愿牺牲其他。不能牺牲其他,以为学问,来恐后悔。此须说明在先,以免后论也。戴公之信,何以至今未寄来?甚怪矣。若措词如兄所示之大略,则也客气,而无分发之恶影响。
明晨派人去宜宾,奉复一长电。
明日中午开所务会议(今日雨天,济之不能上山),若决议与此不同时,当再电达,自当以决议为正。若无电,即无更动矣。专此呈写。
此信兄转呈或以大意转陈院长知悉。此函外抄两附件,一呈院长,一呈叶总干事。
附件 照章:一、研究员、副研究员、编纂、技正、技士、技佐分别由院长聘任或函任之。二、助理研究员、管理员、事务员、书记均由所长推荐给院长函任之。三、助理员及研究生均用考试方法选拔之。(事实上,聘任人员亦由所长推荐于院长核准聘任之)
眉批:戴先生公给之高考毕业生速由史语所任用为要。①《傅斯年致刘次箫》(1942年8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274。
由此可知,傅斯年的意见与叶企孙大同小异:因与院章抵触,拒绝铨叙分发;为免不必要的麻烦,可以考虑接受私函推荐,但申明“大学部毕业……只能作助理员,不能作助理研究员(除非寄有相关著作来,审查合格)”。薪资微薄的助理员虽属较低阶的实习性质,但偏重于学术研究,与积累政治资本无涉。且根据章程,“助理员及研究生均用考试方法选拔之”。这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暗示无论是铨叙分发还是私人推荐皆有不妥,院内之愿意接纳以私人推荐名义,亦属权宜之计。次日上午,史语所紧急召开所务会议商讨对策,根据会议记录可知,其他同人亦持同样观点:“建议于院长,本院未便接受铨叙部之分发高考及格人员。但周天健君可不以分发论,试任为本所第一组助理员。”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十一年度第四次所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274。当天下午,傅斯年即致电中研院总务处主任王敬礼、刘次箫,告知以上详情。②《傅斯年电王敬礼、刘次箫》(1942年8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刘次箫接电后,随即致信告知朱家骅:
关于戴院长所介绍之周天健君,孟真已电复如下:“周事如作戴先生个人介绍,不作铨部分发,可请其即来;但请告彼:到此治学甚便,而资格仅合助理员,非助理研究员,待遇甚薄,当为学问牺牲。”除已由职经函周君外,谨此报告,恭请钧察。至周君之任函,宜俟其到所后,由所函报到院,再行填发,特并陈明。③《刘次箫致朱家骅》(1942年8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
当日朱批:“戴先生函声明:私人介绍,并非分发。且周亦言不计地位,只求得一研究机会。应速照派为要。”可见,此时戴季陶、朱家骅二人已互通音信,由铨叙分发改为私人推荐。至此,中研院及史语所在对周天健其人无甚了解的情况下,仅凭戴季陶一纸私函,均想赶紧接纳,免生事端。
本来此事至此已可结束。然而,平地起波澜。考试院负责的考试分为高等和普通两种,前者招录的是大学毕业生,后者招录的是高中毕业生。两者均须通过考试,由铨叙部作为拟任公职人员报批政府同意后,再分发任用。④王传敏:《戴季陶与南京考试院》,《文史天地》2013年第3期。此时中研院才把周天健为高中学历的“实情”告知史语所,不仅违反“助理员应为大学本科毕业且已取得相关研究成绩”的院章,⑤刘桂云、孙承蕊选编《国家图书馆藏国立中央研究院史料丛编》第1册,第12页。对于招人“无时不力求其标准不至劣下”的史语所来说,①《傅斯年致吴定良》(1933年2月11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340页。也实难接受。这深深触动了“为人极易冲动,冲动之时如火山爆发”的傅斯年。②《丁文江致董作宾信》(1935年4月24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黄山书社,1994,第253—259页。于是,对国民党老辈人物向无好感的他据理力争,③“至于国民党老辈,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人。” 《傅斯年致胡适》 (1938年6月20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675页。当日长函朱家骅,洋洋洒洒说了七点,除申述前见外,亦表其不满:
……⑤周竟不将戴函寄来,似先要求满足,而后肯缴此至宝者。此则所谓“鸡毛掸子作令箭”,开头先不给人以好印象。……⑥助理员之资格规定甚明白,彼非大学毕业,何以处理?如以为高考可与之相当,则最好付此解释于院务会议,此固办不到。若发付人事会议或由院长先加以暂解释,而俟将来院务会议之追认也。总之,敝所绝不敢与院章之外有何举动,绝不作使院章成具文之事。故,如次箫兄第一书言及其非大学毕业,则弟等日前之决定,或有所不同,更当求兄之谅解矣。……⑦至于兄批此事关于本院甚大云云,弟微觉不同。若戴公为讲理之人耶?则彼不应见怪,若其不然,亦无法使其不见怪,如怪则怪在弟耳。故鄙意以为此事关系本院甚小,以其至多是弟一人之事也。惟既承剀命,弟两度派专使往宜宾发电,连川资二百元,周天健尚不知为如何之人,而弟已事之如上神,此则为国家学院一叹矣。④《傅斯年致朱家骅》(1942年8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
由此可见,让史语所无法接受的是,事情已经快要接近尾声时,才提及周天健仅为高中学历的事实,这与“助理员之资格为大学毕业生”的院章相抵触。这也是周天健迟迟未将戴季陶的推荐信寄给史语所存案的顾虑。此前以个人推荐的名义接纳,已属勉强之举,此则又横生波澜,有意隐瞒,故傅斯年感到戴季陶等人以势压人,且一直被蒙在鼓里、被耍弄其中,于是将郁积心中的愤懑倾泻而出。然而,当朱家骅接到此信时,尽管颇为难堪,但次日仍回电重申前议,希望尽快将此事翻篇。傅斯年当然无法释怀,于是再电刘次箫,进行申辩:
江函敬悉,周天健既非大学毕业,其可任为助理员否,仍须请院长对《组织通则》第十一条加以解释。本所未敢擅改,此事似当嘱周将戴院长函,连同详细履历、著作等先行快函寄此审查。未便遂亦[随意]决定,恐其程度太差,来所无益,或起争论也。乞陈院长。①《傅斯年电刘次箫》(1942年8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
并当即公函院总办事处:“周天健一人系贵处交下,其办法已详历次敝所傅所长致贵处刘主任函,并请其代呈院长函。近又发现该员并无大学毕业资格,与《组织通则》第十一条不符,应如何解释及办理,仍请院长决定。……敝所本年原不拟添人员,且目下若添,纵可敷衍一时,明年加薪又是问题。此时局面,人少事省,人多事多。敝所已深感其苦。”②《史语所致院总办事处》(1942年8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由此可知,他仍然抓住“高中学历”一事不放。此事若是别人做来,可能早已大事化小、不了了之了。但是对于“为人率直,不眉上不傲下……在学术上或公务上从不苟且,必认真探讨以致争辩”的傅斯年来说,③马学良:《历史的足音》,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第864页。是行不通的。少负才名的傅斯年自视甚高,常“目空天下士”,能入其法眼者,实属寥寥。对此等借私门请脱、行不合规章之事,他向来嗤之以鼻。所以他希望以正义的坚守来对抗权势的压迫。如他自己吐露道:“此时热心一件事业,真是愚公移山耳……然人类的进步正是如此!天下事是傻子办的。”④《傅斯年致胡适》(1945年10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243页。愈显学人的坚守和不屈风骨。
然而,朱家骅认为院章之事应“活学活用”,立即复电傅斯年:
次箫兄转来尊电敬悉。周天健事,季公致兄函,言之甚详,且极诚恳。周君虽未大学毕业,但既经高考及格,至少亦可等于大学毕业,因高考亦以大学毕业为限。周君有其他资格可援,故得参加高考,今既及格,在国家法令之解释,可说已超过大学毕业资格。今以助理员位置,当无不妥。
另有眉批:
彼之事,弟详加考虑,似未倾以院之规程拒绝之。因法律须活用,若情理苟置不顾,则恐不能为人原谅,与院之前途实转增困难也。如此,似希斟夺[酌],示复为幸。①《朱家骅电傅斯年》(1942年8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
由是可知朱家骅对此事的重视及思虑,但他还是故调重弹,牵强地认为高考及格者,“可说已超过大学毕业资格”,此等掩耳盗铃之辞,不过希望勉强从法理上说明此事之可通融性。且“若情理苟置不顾,则恐不能为人原谅,与院之前途实转增困难也”。用意主要还是避免引起戴季陶的不满。由是督促傅斯年不要拘泥于“小节”,应考虑人情和全院的发展,也是对傅斯年的执拗不满。
但是,傅斯年仍然无法释怀。即使违反院章一事不说,至今仍未见戴函和周个人履历、著作等,对于向有“识人之明”的傅斯年来说,怎么可能糊里糊涂地接纳陌生者周天健呢!从上面的往还信件可知,本为铨叙部公函分发,只是朱家骅起初批复以戴季陶私函看待,遂造成后来许多误解。但若直接告知行政分发而非私函介绍,仅此一点,恐怕向以标榜学术独立的史语所更不会接纳了。
既然傅斯年如此坚持要审查周天健的个人履历及著作,中研院亦不得不致函索要。周天健“两奉手示”后,于8月17日回函寄来履历:
渝城趋访,快聆尘教。两奉手示,并文口来电,均谨诵悉。多承关照,铭感。奚当天健在校受训卒业,遂戴院长之嘱,先分发考试院工作。一俟入所研究事洽妥,随时前往。现在校一切摒挡收毕,拟于二十日左右入城,自当走访也。谨将履历及著作抄寄傅所长外,谨函奉复,敬请著安。①《周天健致刘次箫》(1942年8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
由其履历表可知,他高考及格后仅在中央政治学校受训党化教育半年,并未受过高等教育系统专门的学术训练,也没有严肃的历史、语言方面的学术著作,仅有些诗文随笔。这与史语所招选标准——“助理员应为大学本科毕业且已取得相关研究成绩”相去甚远。
中研院将其履历及著作转至傅斯年手上,仍希望史语所尽快吸纳为助理员为要。事情至此地步,中研院方面认为傅斯年太过拘泥于细节不放,而史语所方面认为不应以权势干预、强行安插不合格人员,双方僵持不下,都有一股怨气待发。其实此间傅斯年已与院里闹得不可开交。事因中研院越过史语所,直接聘请陈寅恪为专任研究员,且准许其领全薪、暂不赴所,而任教于广西大学。②张少鹏:《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0期。现在接踵而至周天健事件,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傅斯年力争无效,反成众矢之的,身心俱疲。所以于8月21日以病为由,上了辞职信,并言已在办理交接手续及安排以后的生活,颇为决绝。③《傅斯年致朱家骅》 (1942年8月21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992—993页。虽然绝口不提周天健事件,但是抗争的用意至明。朱家骅再三挽留,但认为周事仍应及时办理。傅斯年知势不可违,只得再次进言三点:第一,“弟当遵命同意任周为助理员”。第二,指出“周来后问题必多,助理员位低,彼必不满。彼必无专门之根柢,如何治学?……且彼至今不曾将戴信寄来,使弟心中生一颇不良之印象……本所职员皆无铨叙资格,以后重入仕途,又吃亏了”。第三,“任周只凭戴函(私人介绍),本院似绝不便承认铨叙部之分发。……此例一开,后患无穷……本院与考试院铨叙部之关系,似绝不可更进一步”。④《傅斯年致朱家骅》 (1942年8月25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994—996页。可知,傅斯年只能妥协接纳,而对周天健仍未“将戴信寄来”耿耿于怀,实则是对中研院的处理方式表示不满。
其实傅斯年还未放弃,仍在竭力做最后的抗争。9月21日由史语所公函院总办事处,告知:傅斯年将于双十节至重庆与朱家骅面商周天健到所之研究工作,并限周君于10月5日之前到所。①《史语所致院总办事处》(1942年9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面对傅斯年的执拗,正在青城休养的朱家骅亦露不悦,②《傅斯年致朱家骅》(1942年8月8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984—985页。于10月3日批复道:“周天健资格问题院章已解释,俟下次院务会议开会再行报告,傅所长业已完全同意,可即照任,并催周天健速往李庄报到为要。”他希望周天健尽快入所任职,成为既成事实,再多争议均于事无补。傅斯年见状,只好作罢。此后便是程序化的问题:10月8日中研院发聘函给周天健,③《史语所致院总办事处》(1942年10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9日发聘函至史语所,④《院总办事处致史语所》(1942年10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周11月1日正式到所工作。⑤《史语所致院总办事处》(1942年11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至此,该事才算画下句号。
二 几人之间相互缠绕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知晓周天健曲折的入所过程、中研院人员的态度转变、朱家骅的变相操作、傅斯年自始至终的坚守和无奈妥协。不禁令人疑惑:何以朱家骅必欲助成之?何以傅斯年不惜以辞职力争不可?其实这不仅牵涉权势干预下学人的坚守和妥协问题,而且内中隐含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
此事因考试院铨叙部分发而起,由朱家骅推波助澜而成,所以有必要先对戴季陶的权势地位以及戴、朱、周三人复杂的关系做出分析。
身为国民党元老、蒋介石与张静江结拜兄弟的戴季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之位达20年(1928—1948)之久,几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始终。作为屹立政界的“不倒翁”,其隐含的政治权势可想而知。他与朱家骅是浙江同乡,二人的交谊启于辛亥革命时期,那时朱身先士卒、勇于革命,深得戴的赏识。而且朱的哥哥在张静江创办的公司任账房,以此因缘,二人的交往更加频繁。⑥曲凯南:《朱家骅传》,《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1926—1930年,二人共长中山大学,由于戴身兼多职,未能经常驻校视事,所以校务由朱实际主持,颇有劳绩。此后二人长相往来、共进退,戴一直是朱的政治依靠,①朱家骅:《追念戴季陶先生》,王聿均、孙斌合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第736—740页。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庇荫制关系”。②萧功秦:《中国转型期地方庇荫网形成的制度因素》,《文史哲》2005年第3期。所以朱对周天健事件极为重视。这不仅是对戴个人恩情的回馈,亦是身兼组织部部长的朱对戴工作的支持,因分发任职人员均须征得国民政府组织部同意。其实,这也透视出“公”与“私”二者常常处于难分难解的关系,在抉择时后者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民国时期国家体制的运行中,个人交谊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是其体制不健全的一种体现。
而周天健髫龄学诗,少有才名,被辛亥老人陈赓笙称为湖口四才子之一。③《王一民文集》第1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第361页。“曾受知于戴季陶先生。年十五,即有诗集问世,见者无不惊为异禀神资也。”④周天健:《不足畏斋诗存·屈万里序》,自印本,1990,第1页。“一时他的大名传遍了当地。……文人雅士莫不目之为神童。”⑤薇芳:《诗童周天健》,《申报》1937年3月23日,第11版。早岁授彭泽县知事,辞不赴任,后在江西盐务管理局工作数年。1940年通过考试院组织的高等考试,随即送至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原中国国民党党务学校)受训,⑥《高考初试录取名单》,《大公报》(桂林)1941年11月28日,第3版。据参加过当时高考的石兴邦回忆:“此时的高考与现在的高考一样……相对于正规大学,以培养政府行政人才的中央政治学校好考得很。”石兴邦:《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陕西师范大学,2013,第43—46页。次年分发至考试院任职。⑦《高考再试及格人员 呈准分发任用》,《大公报》(重庆)1942年8月5日,第3版。平时与戴季陶以师生相称,往来密切,因为“在中国社会,除了家庭关系之外,最重要的无疑是师生关系”。⑧Ch’i Hsi-sheng,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37.此外,父亲周欲苏(1880—1944)在政界的关系,亦是他能与戴接近的缘由。⑨《史语所致院总办事处·附件直系亲属调查表》(1942年11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3)。因了这几层关系,平生“锐志于学”的周,想借机至中研院做学术研究,⑩《史语所致院总办事处》(1942年1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60。所以才有此事之由来。
尽管戴季陶没有事先对朱家骅明说此事细节,一生游走于政学两界的朱家骅亦深谙个中情由。权衡各种利害关系后,只能选择妥协接纳,以求全院整体和长远的发展。所以其言行虽有牵强之处,背后亦有不得已的苦衷。而傅斯年何以如此抵触?这不能不提他与戴的渊源以及他领导下史语所的学术理念与身份认同问题。
傅斯年与戴季陶的接触始于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时期。1926年戴季陶、朱家骅甫任中大正、副校长。是年底傅斯年刚一留学归国,便就任中大文科学长,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对教务贡献甚大”。①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王聿均、孙斌合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741页;《傅斯年致石坦安》(1927年5月2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020-002-0095-021。可以说,中大的两年是其归国后学术人生的开始,大展拳脚的首个舞台。而在此之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校向傅斯年伸出了橄榄枝,但最后均告落空。为此他“感著[觉]极为苦恼,‘茫茫如丧家之狗,亟亟如路旁之鱼’”。②《傅斯年致罗家伦》 (1926年11月9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70页。若不是中大伸以援手,恐有陷于“野鸡教员”之境,③《傅斯年致罗家伦》 (1926年11月9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73页。所以他起初对中大、戴氏、朱氏是颇为感念的。但是随着戴在中大实行党化教育,傅斯年与他渐行渐远。因其理想是创建一个不受政治干扰的学术社会,然后“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的解决”。④傅斯年:《青年的两件事业》,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7,第456—461页。而且当时校内派系倾轧严重,各方忙于争权夺利,傅斯年斥之为“一群败类”。⑤《丁文江致董作宾信》(1935年4月24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363—375页。当时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使不少无故学生入狱,傅斯年为处理这类事件与广州特别刑事法庭有多封往来书信,颇使他焦头烂额。参见广东省档案馆藏,020-001-0093、020-003-0025。尽管没有明指戴季陶,但对其校长领导的不满不言而喻。他们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傅斯年只好退而求其次,加快离开中大的步伐。
1934年,两人又不期而遇,不同的是此次两人并未谋面,但傅斯年对戴季陶的观感进一步恶化了。事因该年戴奉令至西北考察,4月11日突然公开发表“真电”给时任中研院院长蔡元培(1968—1940)、教育部部长王世杰(1891—1981),要求“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毫无疑问,锋芒所指为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及北平研究院考古组。两机构均有公开回应,对其荒唐言论予以驳斥。①时人熊梦飞摘录各方信件,对事情原委有辛辣的评述,参见熊梦飞《冢中枯骨作祟——我亦参加戴季陶与蔡孑民、王世杰、徐炳昶诸先生之笔战》,《文化与教育》1934年第17期;《冢中枯骨作祟(续)——我亦参加戴季陶与蔡孑民、王世杰、徐炳昶诸先生之笔战》,《文化与教育》1934年第18期。涉及切身利益的傅斯年,亦及时在报上公开声援,对其荒唐言论进行驳斥。②《傅斯年谈发掘工作》,《申报》1934年4月15日,第10版。而1933年,虔信佛教的戴季陶拜九世班禅为师,并授法号,在处理公文政务之余,时常诵佛抄经。傅斯年对此更是嗤之以鼻,常以“阿弥陀佛”代指。③《傅斯年致罗家伦》 (1936年12月10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575页;程沧波:《再记傅孟真》,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第98页。
由此可知,傅斯年对戴季陶的观感由起初的感念,逐渐滑落到鄙夷嘲讽,所以无论对其主持的铨叙部分发还是私函介绍,均颇为抵触。人是有感情的,史语所“大家长”傅斯年个人好恶的变化,亦影响到史语所的人员进出。尽管他宣称史语所招人不会“以我等之接触及情好为断”,④《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致蔡元培、杨铨》(1928年5月5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93页。但对厌恶之人所推荐的不符要求者,他是不愿欣然接受的。无数事例证明“成功不取决于你知道什么,而取决于你认识谁”,⑤Ronald S.Burt,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of Competition,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0.因为“有时‘说句话’在组织决定是否吸收一个人的过程中具有特定的分量”。⑥Nan Lin,Social Capital:A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and Ac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0.而史语所人员结构已比较固定,据笔者对史语所学人群体结构与社会关系(1928—1949)的统计分析,其第一代多是志同道合的同辈,第二代几乎均是第一代人及其同好的亲朋故旧或学生,史语所群体的封闭性颇为明显。⑦参见张辉《近水楼台:史语所学人群体结构与社会关系(1928—1949)》,《安徽史学》2021年第3期。其人员大多来自相同场域的同质分子,长此以往便“产生某种预期的乘数效应……进入了自我维持状态”,⑧Mark Granovetter,Getting a Job:AStudy of Contactsand Career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133.“从而加强内群吸引与外群排斥,导致‘我们’与‘他们’的区别”。⑨Dominic Abrams and Michael A.Hogg,Social Identifications:A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Taylor Francis e-library,2006,pp.16-21.而“‘我们’与‘他们’……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谁是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这是显而易见的”。①Zymunt Bauman,Community: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12.所以傅斯年对“他者”戴季陶推荐的异质分子周天健颇为排斥,便不难理解了。
此外,傅斯年通过履历表对尚未谋面的周天健亦无好感。生于江西、长于舞文弄墨及以前的工作主要属于行政性质,这均与史语所招人“惯制”相违。据笔者对史语所(1928—1949)全体职员中151名研究人员的籍贯统计,自始至终来自江西的仅有2人,而来自傅斯年故里山东的则有16人,位居前列且呈逐年增加之势。此次同时顺利入所的逯钦立(1910—1973)、屈万里(1907—1979)②身为山东巨野人的逯钦立,本科、硕士皆就读于北大,为傅斯年的及门弟子,毕业后旋即入所[《史语所致院总办事处》(1942年8月11日);《史语所致院总办事处》(1942年9月22日);《院总办事处致史语所》(1942年10月9日);王汎森:《逯钦立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第773—782页]。身为山东鱼台人的屈万里,仅有高中学历,由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和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的衍圣公孔德成联合推荐入所[《孔德成、王献唐致傅斯年》(1942年7月25日);《董作宾致王献唐函》(1942年8月10日)、《傅斯年致王献唐、孔德成》(1942年8月11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李3-2-12;《傅斯年致屈万里》(1942年9月15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李3-2-18;屈费海瑾:《屈万里先生的治学与史语所》,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第899页]。均为山东人,确如俗语有云“一把雨伞遮一乡人”“公章不如老乡”。从中亦可看出“中国人重乡谊,严省界”的传统,③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第270页。因为“地理距离产生主题距离”。④Mei hui Yang,Gifts,Favors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in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28.尽管有些人认为傅斯年用人“无分畛域”,但持异议的声音仍不绝于耳。恐怕还是身为山东人的史语所所员杨志玖的话较为公允:“傅先生也不免有门户之见,对有些人他看不起。”⑤杨志玖:《回忆傅斯年先生》,《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38页。“对于他瞧不起的人,他往往出之于极度傲慢的态度和尖刻的言语。”⑥傅乐成:《时代的追忆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第200页。如早年在批评出身浙江的鲁迅兄弟为文尖酸刻薄之后,傅斯年说道:“仆虽不才,尚是中原人物,于此辈吴侬,实甚不敬之。”⑦《傅斯年致罗家伦、何思源》(1928年3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29页。似此不经意之言,颇能代表他真正的心声。所以,对出身古之“南蛮”的周天健不甚待见,却同时欣然接纳两位同乡后进,亦不奇怪了。
傅斯年主张史料实证,对传统士人文化充满敌意,呼吁摒弃文人文化。他认为“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①《傅斯年致胡适》(1920年8月1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0—11页。“文人一旦做到手,‘人’可就掉了。”②傅斯年:《随感录》,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1卷,第278页。1941年,他对刚入所读书的四川大学才子王叔岷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③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第48页。当时四川大学文史学风还是比较偏重实证,④罗常培:《蜀道难》,王均主编《罗常培文集》第1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第170页。此与史语所的提倡不谋而合,所以傅斯年不担心王叔岷无法迅速融入史语所团体。而对于“不废吟咏”的才子周天健来说, “无专门之根柢,如何治学?”且他所爱者,是傅斯年所恶,谈何接纳?此外,史语所为学术机关,强调为学术而学术、远离政治。⑤“他是一身正气的政治家,但回到史语所,却绝不谈政治。……据知情人士说,‘上边’曾有指示要所内人员集体入党,文件被他扣下了。” (杨志玖: 《我在史语所三年》,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第789页)胡厚宣回忆:“因在学术上求名利,所以脱离政治……受胡适、傅斯年影响……死读书,不谈政治。”(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第377页)而周天健以前的经历均与政治、行政分不开,曾受训的中央政治学校便是“专以培养党员为职”。⑥舒芜、许福芦:《我眼中的国民党大员“同事”》,《湖南文史》2003年第2期。正如傅斯年辞退其他所员的说辞:“非谓先生不能做学业,乃谓先生能做而擅长之事,不与本所之工作相合。”⑦《傅斯年致刘学濬》 (1932年6月29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307页。所以傅处处表示顾虑,担忧其以后“重入仕途”。
三 权势干预下傅斯年的两难抉择
以上分析了几人之间的关系渊源,以及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之学术理念与身份认同问题,从中可以略窥民国时期制度设置与运行之间的脱节,传统社会人情影响下因人设职的老路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潜行,更加说明传统力量的根深蒂固和民国社会的过渡性质。当然此中更为凸显的是政学两界的交织难解,政治权势对学术独立的干预。傅斯年自谓“平日任气使性,不知人情为何物……平日素志,断无与政客接近之理”,①《傅斯年、罗家伦致段锡朋、许德珩、陈剑修、黄日葵》(1919年6月2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8—9页。然而他由坚决拒绝到逐渐妥协接纳周天健,其中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戴季陶背后强大的政治权势。尽管在此事件中戴几未现身,但因其“握权甚大”“所居职位实是号召一部分潜势力”,②《李济致丁文江》(1934年5月13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8册,第111—112页。其权势像一张无形的手,是决定此事件最终走向的力量。
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大夫的身上。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从中心滑向边缘,中国便并存政治和文化两个轴心。③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第6期。在近代中国,两者的关系常常是剑拔弩张、对立紧张。一些相信学术文化优于政治的人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相信学术的发展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④Wang Fan-sen,Fu Ssu-nien:Alife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3-4.傅斯年正是其中的代表,他主张“总当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来”。⑤《傅斯年致胡适》(1945年10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240页。“照着我们的主义,一点也不屈挠的做下去。”⑥《傅斯年致顾颉刚》(1919年4月20日),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7卷,第13页。但是,受到政治危机的不断干扰,这几近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正如胡适所言:“想造成一个不受政府支配的学术机关,此是甚不易做到的事。……今研究院的组织法第一条说‘国立中央研究院直接隶于国民政府’;第三条云‘院长一人特任’;经费来源每月由财政部颁给;其中全无一点保障可以使政治势力不来干涉。”⑦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第5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第652页。颇具吊诡意味的是,这群自由主义学人想造就一个不受权势干预的学术社会,但又不得不借助政治的力量来达成。他们始终处于保持学人独立自主地位与疏通政府关系的两难之中。因权势有时是一种助力,有时是一种阻碍,其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实难平衡。实际的结果常常是权势干预难以避免,学术独立挥洒的空间仅止于让这种干涉降至最低限度而已。
作为“学林霸才”的傅斯年,颇具马克斯·韦伯所言的具有超凡的、革命的卡里斯玛式权威性格,强调对现有混乱秩序的破坏作用,与官僚型的支配呈尖锐对立。①〔德〕马克斯·韦伯《韦伯选集Ⅲ:支配的类型》,康乐编译,台北,远东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9,第68页。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亦不得不忍气吞声。因为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势之间天然的紧张关系,似乎存在托马斯·库恩所言的不可通约性。尽管常常交织在一起的二者追求的目标不同,后者对前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机制,前者对后者的依附性却非常强。尤其身处那样一个学术资源有限、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政府的年代,学术领袖与政府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政府拨款的有无、多少。自诩为“拉账第一人”的傅斯年,②《傅斯年致李济》(1935年6月26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503页。亦无奈道:“弄钱乃是大费工夫之事,决非一纸公文,安坐可得者……今日全院之局面,实与政府失却联络。……似此局面,不知何时出岔子。”③《傅斯年致任鸿隽》(1940年2月26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810页。其意不言自明。所以,傅斯年的转变与其说是在权势高压下的妥协,不如是为了史语所乃至整个中研院的前途所做的策略性改变。然而,正如他的自我解剖:“在这两难之中,自己变动了自己的约定,而心中不宁,不必说也。”④《傅斯年致林语堂》(1929年8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262页。“一人心识,分成两片,非特本人大苦,而且容易成一种心理上的疾病。”⑤《傅斯年致蔡元培》(1920年9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14页。颇似埃里克森所说的,这是“真正的生命存在”和“为了达成目的的自我否定”之间的两难抉择。⑥Erik H.Erikson,Young Man Luther: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New York:W.W.Norton&Company Inc.,1962,pp.52-53.这不仅是傅斯年个人的无奈,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哀,所以他哀叹:“‘学院的自由’、‘民主的主义’,在中国只是梦话。”⑦《傅斯年致胡适》(1940年8月14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832页。
尽管如此,把“史语所看作是他的命”的傅斯年还是竭力抗争,至少将周天健由铨叙分发改为私人介绍、由助理研究员改为助理员,这当然是坚守学人风骨却又难以言述的“苦涩胜利”。但“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⑧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华书局,2016,第490页。尤其像傅斯年等少数精英分子,不会甘做权势任意摆布的玩偶。其实傅斯年的抗争亦不仅仅在于此事,更是在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对权势干预学术独立强烈不满,希冀此类事件不再重现。所以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学术的权威对抗政治的权威,试图使政治家沦为外行,从而使自己“处于元话语地位”。①〔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英〕罗杰·夏蒂埃:《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53页。“一切历史经验证明了,若非再接再厉地追求在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②〔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77页。正如孟子所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创始一个学术建制,招募人才是最基础的工程。③潘光哲:《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9—10页。而人才的招募与培养关涉学术机构的发展前景,关乎其在学界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傅斯年如此不屈不挠地力争学术自由。但是,在那样一个人才征募的方式还在摸索中的时代,权势干预与人事关系对学术独立的侵蚀在所难免,尤其是不得不委曲求全于具有无限笼罩力的权势威权之下。若不如此,仅“拘于学术圈中,局外不作布置,则学术本身工作有时竟不可通”。④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资料文物选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第201页。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不是故纸堆,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如何能够切实做到三者之间良效互动、相得益彰,仍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不是要讴歌傅斯年们在学术领域里的丰功伟绩,而是希望通过此一小事件,窥探政治高压下学人风骨的坚守、学术机构在乱世中的艰辛历程,以及20世纪中国学术延绵不绝的精神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