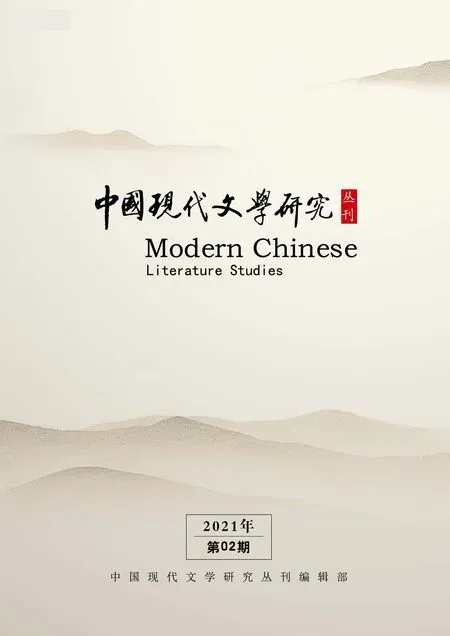脱域写作与新时期以来城乡题材小说的新变
内容提要:198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和城市小说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无法再以纯粹的“乡土文学”或“城市文学”进行划分。现代化与全球化一方面带来空间等级秩序的日趋明显,另一方面也带来空间的同质化现象。而在文学写作中,脱域写作的出现是极具症候性的表现形态,其中所涉及的身份认同危机和自我救赎命题凸显出浓厚的空间政治意识。某种程度上,空间权力对人物的生产和规训,构成了80年代以来城乡题材小说写作新变的内驱力之所在。
引 言
现代化进程被视为贯彻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而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明显具有加速趋势,与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耦合在一起。这一多层次进程的重叠和耦合所带来的巨变在空间上表现为空间流动的加速和单向度位移,在时间上,则表现为多种时间形态的并存。文学写作中,脱域写作的出现就是极具症候性的表现形态。
之所以提出“脱域写作”,是为了跳出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分法论述框架。“脱域”这一概念,原由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中首次提出,意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之后该理念为后殖民主义所借用,特指流散的主体离开家园文化进入宿主文化时身份的暧昧。而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和城市小说之间的界限已日益模糊,很难用纯粹的乡土文学或城市文学加以框定。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已无法被界定为乡土——毕竟孙少平和高加林们的足迹是在城乡之间移动,他们的出生地虽在乡土农村,也一度生活在农村,但他们表现出的“走向城市”的决绝和悲壮使文本超越了单一的乡土文学的维度。这与50—70年代的《创业史》(柳青)、《香飘四季》(陈残云)、《卖烟叶》(赵树理)等乡土小说显然不同。这些小说尽管也写到城市(包括县城),写到徐改霞(《创业史》)和许细娇(《香飘四季》)们走向城市,但她们的这一意向和趋向却是被作为否定的、“不安分守己”的对象加以表现的,此类文本所推崇的是扎根农村、安心农业生产,城市则作为乡土的他者而出现。比如,赵树理的小说《卖烟叶》中,农村知识青年贾鸿年不安于生产,“投机倒把”,最终触犯了法律,赵树理本人也因为塑造了这样一位不够正面的农村青年形象而备受抨击。然而80年代开始,这些不安分的青年农民却摇身一变,成为被肯定和被赞美的对象。浩然的《苍生》中,田保根的形象完全可以说是贾鸿年的某种复刻,只不过原先的“堕落”却被视为“先进”,“保根这样的新人物的出现,压根儿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类似的人物,还有贾平凹《腊月·正月》中的王才,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以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由这些小说开始,走向城市,渐渐成为农村青年显示其价值和实现其人生目标的表征。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于内部被进行了翻转,乡土开始作为城市的他者而出现。如果说城市化进程催生了城市与乡土的二元对立结构,那么现代化进程则使得这一结构中空间的差异性和不对等性一步步凸显。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经将现代性比喻为一种“液化”的力量,这一力量使“旧有的结构、格局、依附和互动的模式统统被扔进熔炉中,以得到重新铸造和形塑”。新的空间等级秩序中,乡土与城市、小城市与大城市,地方性城市与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与全球化中心城市等构成了一系列子对,而乡土无疑是作为子对中的低端而存在的。“社会关系的主体及其行为摆脱了空间直接作用与互动的地域性限制,不确定地在时空维度上联结和延展,造成社会交往的时空错位与异时空套嵌,导致社会关系的空间重构”。越朝向或靠近中心城市的空间,其等级就越高。但这里的格局与其说是差序格局,毋宁说是等级格局。这样一种格局中,空间的流动呈现一种单向度的发展,基本上总是从低一级的朝向高一级的流动。与这一空间流动趋势有关的写作,不妨名之为“脱域写作”。
一 脱域写作与空间等级秩序
所谓“脱域写作”是对新时期以来属于城市或农村题材,但又与传统城市文学或乡土文学不尽相同的部分小说的概括。脱域写作在题材和主人公的塑造上属于城市文学或乡土文学,但它所蕴含的新变,已不再单纯适用于城市文学或乡土文学的定义。此类作品中,主人公们的不安分和他们不停的流动所显示出的,是一种特有的社会过程:“社会关系‘摆脱’本土情境的过程以及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轨迹中‘再形成’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正处于一种加速发展状态,“由现代性所引入的时空分离过程加速进行,脱域为其关键因素”。“脱域”(disembeding)是与“嵌入”(embedding)相对应的,城市文学或乡土文学都基于一种嵌入式表达,而新时期以来,这两种表达方式间的彼此渗透则正是由脱域所带来的。
传统的“乡镇写作”虽也涉及城乡之间的空间流动,但其流动带有双向可逆性:乡镇既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中转站,也是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对立冲突的缓冲器,乡镇作为中间地带的性质决定了乡镇写作嵌入式的杂糅特征。脱域写作则不同,其空间上的跨域不限于城乡之间,而囊括乡土、乡镇、城市等多个层级时空。脱域写作中的乡镇只具有暂时过渡的性质,主人公总要经由乡镇走向城市,从地方性城市走向中心城市,带有悲壮的不可逆性。就主题而言,乡镇写作多偏重于象征功能和隐喻色彩,最具代表性的是余华的《兄弟》,以及迟子建的《群山之巅》。脱域写作表现的则是主人公在从低一级时空向高一级时空的无法停止的跨域过程中的挣扎、困惑、迷惘、矛盾、绝望乃至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Edward Soja)指出:“人从本质上就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文论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也在其《空间的诗学》(La poétique de l’espace)中引用诗人阿尔诺(Noël Arnaud)的名句来说明空间的重要性:“我就是我所在的空间。”空间虽然是人类行为与社会关系的产物,但其自身同样是社会的生产者。空间与空间的区隔制造出了一种生产机制,会影响、改变,甚至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无论是生活空间的设置,还是地理空间的位移,都将直接影响人的身份意识与主体诉求。某种程度上,空间等级秩序的存在决定了脱域写作的层次性特征。
表现城乡之间流动的“半脱域写作”所蕴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小说和乡土小说无法企及的。这一类小说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人生》为代表。“他内心为此而炽热地燃烧,有时激动得象打摆子似的颤抖。他意识到,要走就得赶快走!要不,他就可能丧失时机和勇气,那个梦想就将永远成为梦想……哪怕他闯荡一回,碰得头破血流再回到双水村来,他也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聊以自慰了。”孙少平对城市的向往呼应了整个80年代中国“走出去”的时代主题,虽然路遥小说中的人物们均未能走远——孙少平无法属于省城,《人生》中的高加林也止步于县城,然而,他们的努力虽暂告失败,走向世界的决心却不可动摇,一旦时机成熟,又将再发。至于表现地方性城市和中心城市之间单向度跨域的区域性脱域写作,即通常意义上的“新城市文学”,因其所聚焦的问题与当下息息相关,作品中主人公的困惑也是前所未有的。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根本相关,毫无疑问,它比时间带来的焦虑更甚”。王刚的《月亮背面》《福布斯咒语》,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和文珍的《第八日》,均体现出空间改变带给人们的身份认同焦虑,及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更复杂的层级,则是表现跨国界间的“新移民写作”,比如说査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韩东的《中国情人》,阎真的《曾在天涯》,林那北的《峨眉》和徐则臣的《王城如海》等。主人公在全球中心城市之间的跨域一方面涉及国族认同,但更大意义上则涉及文明认同或文化认同,“资本的这种空间生产虽然是全球性的、同质化的,却又是割裂的、分离的、不连续的,包容了特定性、局部性和区域性,以便能够驾驭它们……”全球化过程中,空间生产所带来的包容性和矛盾性被一一呈现。
脱域写作的多层次,决定其构成上的繁杂,以及阐释上的复杂性。就构成部分而言,脱域写作具有超越题材分类的特点,大部分所谓的“底层文学写作”均可划归到这一类中。按照福柯的说法:“空间是任何权力行使的基础。”而底层之苦难或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在跨域的过程中,因物理和伦理空间的挤压而被人为地生产出来。8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小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浩然的《苍生》等——都是对空间生产的书写。“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脱离“土壤”的农村青年们陷入城市的钢筋水泥中,失去自我的身份和重量。而当代反映农民工和蚁族的作品也可归入此类,如孙惠芬的《民工》《天河洗浴》《后上塘书》,关仁山的《麦河》《日头》《天高地厚》,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贾平凹的《高兴》《极花》,东西的《篡改的命》等。此外,京漂系列,上漂系列,包括知识分子题材,也可纳入这一范畴。就历时性而言,脱域写作涵盖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众多小说创作,具有广泛的概括性。由共时性层面来看,脱域写作涵盖截然相反且互为表里的两个主题,一是单向性流动的决绝和义无反顾;二是精神上的无根和返乡冲动。前者聚焦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流动,主人公们义无反顾地从乡村走向城市,由中小城市走向大城市,又由大城市走向中心城市。然而,伴随主人公们单向度的义无反顾感而来的,不仅是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体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迷惘、困惑以及无家可归的挫败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返乡构成了脱域写作的重大主题。但这一主题也有其层次性,或围绕乡土作为背景存在的理想化的原乡想象,或围绕乡土消亡后的无根感。两种对乡土的不同表现,也体现出脱域写作的不同精神指向。
脱域写作的出现,与城市化进程及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朝向城市的单维流动不断加快,乡土农村却一再萎缩。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书写已不仅仅是表现乡土青年农民走向城市,小城青年走向中心城市,还同时表现一种单向流动后精神返乡的可能性的缩减。对于脱域的流浪者,乡土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伊利亚德所说的“神圣空间”,“神圣空间的揭示使人们在均质性的混沌中获得一个基点、一个方向成为了可能”。然而乡土的消逝,直接带来神圣空间的坍塌和毁灭,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返乡的无所依傍,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即成必然。
二 象征标识的设置与脱域写作的阶段性演变
脱域写作的表征张力,往往被凝缩为某种象征标识(symbolic tokens)。“象征标识是交换媒介,它具备标准价值,因而在多元场景中其指代意义可相互替换”。比如说《平凡的世界》和《人生》中,书本就充当了时空转换的象征标识,其功能体现在为不同空间进行想象性关联的建构。蜷缩在看似模糊、抽象且具有象征性的城市面前的乡村,是经由书本打开了一扇窗户、建立了一座桥梁,让乡村知识分子在一种“想象性的共存的秩序”中,构筑起自己同城市的“想象的共同体”身份,从而使乡村中的知识分子最早萌生了走向城市的念头。贾平凹《极花》中的高跟鞋,即是一种象征标识,通过高跟鞋的意象,女主人公建立起了同城市的想象性关系,义无反顾地走向城市。正如贾平凹所说:“严格地说,人和物进入作品都是符号化的。通过象阐述一种非人物的东西……只有经过符号化才能象征,才能变成象。”作为一种媒介,象征标识容许个体自行建构其主体性,并同时与外界空间生成一种秩序分明的等级关系。当主人公藉由象征标识重新打量自身的现实处境时,必然发现并认识到乡土农村的落后和贫瘠,迁徙和流动便随之而来。就象征标识的意义而言,书本与高跟鞋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之处,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预示了乡村青年进城的两种迥异的路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还有诸如“铅笔盒”“发卡”等。《哦,香雪》正是通过火车所带来的铅笔盒和发卡构建起乡村少女同世界(以城市为代表)的想象关系的层次性。火车的出现使乡村与城市间有了连接的可能,火车带来的象征标识物也促使香雪对自己熟悉的环境进行了“再辨识”(re-cognition)。“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的山谷”。铅笔盒和发卡令香雪第一次脱离了共同体,而在意识层面上出现了个体化、实体化。铁凝自己在谈到这部小说时提到:“它在我整个创作中不是价值高或低,分量轻或重,而是它本身具有一种不可替代性,后来的小说在叙事上更成熟,更像一个自觉作家的写作,但《哦,香雪》焕发出来的对人生,对情感,对生活,对希望那种透明的激情是不可替代的。”恰恰也是“对希望那种透明的激情”在敦促着香雪们走向外界,而这些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的入口正是铅笔盒与发卡——知识与商品。
一部分乡村青年通过铅笔盒所象征的知识走向城市,刘震云的《塔铺》和贾平凹的《商州》均属于此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与《人生》也可视为其变体。然而,一直鼓舞激励着中国广大农村青年们的知识神话体系却在近年的另一些小说中被彻底摧毁,如宋小词的《倒立行走》。“铅笔盒”被彻底祛魅,城乡二元对立的深刻矛盾则被推到了时代前沿。孙频也在《同体》中令我们看到,农村青年通过知识改变的往往只是自己的职业和户口关系,他们作为次一等存在的农民文化身份却是根深蒂固和无法改变的。从文化角度探讨城乡对立关系的新视角,也使得长期以来建构的知识神话被打破。金耀基曾借用勒纳(Daniel Lerner)的“过渡人”(people in transition)概念描述中国“过渡人”处于中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价值的困窘”。这一概念对于“边缘人”(marginalized groups)也同样适用。知识不再是金手指,经由知识走向城市的农村青年发现他们无法再度通过知识去改变“兼具身份”,他们被卡在了夹缝里,既不是农民,但也无法成为真正的市民,终至沦为主流社会空间以外的边缘人。
脱域写作展示了城乡空间互动背后的权力运作模式,城市作为异质空间在物理、文化、心理等层次被一一铺展、一一剖解。“空间并非空洞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住所。人借助外在的空间去激活关于空间的回忆,从而将外在的命运赋予内在的意识,进而认识自我”。空间通过权力运作,直接成为人类主体意识构成的重要媒介,离开故土的农村青年们试图打破空间秩序、书写自我身份,但其主体性却一再被外部空间所否定、所排斥,致使他们徘徊在边缘人的位置上,无力起拔。
当知识神话坍塌后,“发卡”则为农村青年提供了另一条路径。通过发卡——这一既是生产品,也是消费品的双重内涵象征,铁凝的《哦,香雪》预设或建构了农村青年同城市间的两种关系,商品生产者以及消费者。1990年代末以来,数量众多的打工文学正是前者的代表,农村青年更多是充当商品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如曹征路的《问苍茫》、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和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等。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村青年男女而言,他们与城市的关系反而是通过消费者的身份得以建立的,因为城市的魅惑无疑正是体现在消费的丰裕上。“……通过控制消费从而全面控制了日常生活,获得了新的活力,却将人类推进了一个消费被控制、欲望被制造、满足与匮乏交替循环的符号化消费时代”。假如青年农民首先以消费者的身份建构同城市的关系,则会立刻面临巨大的匮乏感,继而一败涂地——贾平凹的《极花》便是如此。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以一种浪漫性的想象关系走入城市时,便被城市所吞噬(被拐卖)。此处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青年女性被城市消费品的繁华所炫动,而心甘情愿让自己的身体以商品或消费品的身份出现在城市男性消费者眼里。这一类小说有关仁山的《麦河》,孙惠芬的《天河洗浴》《吉宽的马车》和钟求是的《零年代》等。脱域写作中,乡土青年农民不论是作为消费者或生产者出现,其重塑自我身份的渴求大都换来了悲惨的结局:男性带着身体上的残疾(工伤)回到家乡或葬身城市,如《高兴》中的五福,付秀莹的小说《陌上》等,女性则一步步堕落,走上不归路——如《麦河》《吉宽的马车》《天河洗浴》。
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是一个特例。小说中的黑娃借助照相馆里的相机和布景(包括电话道具),在想象中建立起了中国农民同美国和美国总统间的相互关系:中国生产的羊毛卖到美国,美国生产的相机被中国消费者使用,彼此都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种身份存在,因此,黑娃并不需要走向城市,也没有出走的动机和渴求。同样,东西的《伊拉克的炮弹》中的主人公,则通过电视机这一象征标识,建立起了同伊拉克的民众的想象性移情和平等,属于空间秩序上的并列空间,因而也不构成空间的迁徙。在当代中国,以上作品并不多见。对于大多数表现空间关系的小说,象征标识的意义都在于建构空间的等级关系,而不是对等关系。唯有建立起等级,主人公的跨域和迁徙才被赋予内在驱动的巨大张力。
尽管如此,也有一部分小说并不特地为空间等级的联结而构建象征标识。推动小说主人公在空间中迁徙的不再是强烈的能动性,而是一种无意识或盲目性的行为。例如东西的《篡改的命》,小说主人公汪长尺的城市梦和身份焦虑,表面看来是没有考上大学(其实是被掉包)所造成的心结,实际上是被父亲汪槐自杀所激起的农村人的“原罪意识”,以至于他不惜以生命做代价,去“篡改”儿子汪大志的命运。“汪长尺不想重复他的父亲汪槐,就连讨薪的方式方法他也不想重复,结果他不仅方法重复,命运也重复。”黑色幽默的背后,展现的是历史潮流的暗涌,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对立,在于长期以来经济结构、文化政治等方面相结合形成的空间等级,以及人们对其价值排序的判断。从这个角度看,《篡改的命》与孙频的《同体》等小说有一脉相承之处。
三 身份认同危机与脱域写作的时间构型
一般的城市小说(包括城市改革小说和市井文化小说)中,空间通常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譬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陆文夫的《美食家》、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刘心武的《钟鼓楼》等,文本中的空间虽有私人和公共之别,但却缺乏真正的变化,时间的流转带来的是空间上的自我循环运动。《美食家》中,城市空间一度变得充满张力,甚至显现出不正常,可一旦“文革”结束,这一空间又恢复其原有的样貌。时间既是异己的变动因素,同时又具有修复力量。在这一时间的笼罩下,城市小说中的空间往往成为一种隐喻,而很少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同样,对乡土小说而言亦复如此——如汪曾祺的小说,废名的小说与沈从文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自然时间的循环往复决定了空间上的相对停滞。乡土改革小说的情况相对复杂,其中涉及空间关系的变动,以及空间中人与人关系的变动,然而无论怎样变动,主人公的活动区域都主要局限在乡土,如贾平凹的《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浮躁》,叶辛的《在醒来的土地上》《基石》《拔河》,蒋子龙的《燕赵悲歌》。乡土的变动来自外来非自然时间(或者说“工业时间”)的进入,乡土空间有了变化,不过变化仍旧被限制在自然时间的框架内。外来非自然时间尽管带来了空间关系的变化,但只是一种视角,而不是基础,起主导作用的仍旧是自然时间,以时序的循环为标志。
相比城市小说和乡土小说,脱域写作是一种在双重或三重时间的变动和交织中表现空间关系的立体书写,时空关系呈现为一种动态结构。“所有的‘主体’都被安放在某一空间中,这个空间是他们必须认识他们自身,或失去他们自身的地方……”空间关系的变动,迫使主人公们在全新等级秩序中去构建自身,或最终失去自身,从而带来多重时间形态的并立交织。《苍天》和《平凡的世界》中,自然时间与非自然时间构成了双重交织,而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和文珍的《第八日》,则把“同时期的不同期性”的区域性时间、全球性时间和永恒精神时间交织在一起,复杂的三重交织正是由社会的加速发展造成的。互联网和技术革新一方面带来时间的均质感,大家都处在同一水平上;另一方面又因为空间上的不平等关系,令人们清晰地体验到时间的不同步。时间感与空间的密集度成正比,在全球化大都市中,时间是加速发展的,而地域性空间中的时间则相对缓慢,这种对比使超越时空限制的永恒时间(或精神时间)作为一个主要命题被提出。譬如说《耶路撒冷》中的耶路撒冷,所象征的正是精神性时间的存在。五位主人公均因儿时伙伴景天赐的死亡而背负上道德阴影,“到世界去”成了他们逃脱过往的出口。“(世界)意味着机会、财富,意味着响当当的后半生和孩子的未来,也意味着开阔和自由”。然而,由于这本质上是一种逃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和追寻,所以他们始终是“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自赎的历程中,耶路撒冷成为意识时间的永恒标地,尤其对于初平阳而言,本可以拯救天赐的十分钟是他不停回归的类似告解室的“空间”,也正是因为“还有忏悔、赎罪、感恩和反思的能力”,他得到了以色列大学教授塞缪尔的赞赏。而最后四人一起集资成立的“兄弟·花街斜教堂修缮基金”,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斜教堂成为信仰存续的具象化,一种超越了过往和区域性的永恒时间的矗立。
双重时间或三重时间的交织,又进一步决定了脱域写作中认同危机和自我救赎主题的浮现。时间的交织,带来的是空间上的流动,认同危机就在这种空间流动中生发。“经典的现代的身份确定是按照相对经受得住时间变迁的方式建构的,并且因此只要是在变化和变革受到一定的阻碍的地方,它就是建立在人生的连贯性和连续性基础上的。”对一个社会而言,空间流动性越小,其认同就越稳固,相反,空间流动性越大,认同危机就会产生。弗洛姆认为,现代化造成了人的焦虑、不安和无归属感。乡土中国遭受破坏或坍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乡民的身份模糊与价值困窘,例如沈从文的《边城》。当认同危机难以缓解时,就会出现自我救赎的必要。以贾平凹和王安忆为例——贾平凹的《高兴》和《商州》中的主人公始终是在抽象意义上的乡土和城市间跨域,认同危机的存在和解决都与这种空间移动有关,基本不存在自我救赎的必要;而像王安忆的作品则始终以全球化大都市上海作为背景,文本中的主人公欲在空间的秩序中确立自身,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就是寻根——如《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天香》等,要么就是放逐(被放逐或自我放逐)或逃离——如《遍地枭雄》《匿名》《红豆生南国》《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的主人公虽身为上海人,但却并不以上海人的身份而感到自足,进一步说,正是因为这一身份才促使他们格外向往繁华大世界,从而进行永不停息的物理与心理跨域。“人的生存一旦不再依托一个固定的空间,他的家园感、安全感也受到威胁,他的同一性也就被不断流动的空间所解构、重构”。然而在被不同空间划分出的等级格局两端,跨域者都是不折不扣的他者,物理和心理空间的痛苦流放导致一种永远在路上、缺乏归属感的生存方式。这种被空间生产出的阈限性 (liminality)使人终日挣扎在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中,难以找到合适的自我位置。“位置”既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伦理意义上的,“阈限的实体既不在此、亦不在彼”。主人公在空间中行走的精神路径赋予他们的是一种明显的存在的空缺,以及因空缺而产生的自我救赎的冲动。
身份认同危机和自我救赎的命题,在“发卡”和“知识”所代表的两类脱域写作中,其意义和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就发卡所代表的脱域写作而言,其主人公一般是不存在身份认同危机的——即便存在,也只针对那些“新生代农民工”,如东西的《篡改的命》,主人公汪长尺即属于迥异于父辈和同辈的那一类农民工。他首先关注的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他需要改变的是自己的农民身份,是“身份政治被遗忘”的匮乏感,而不是财富或金钱的获得——尽管后者是他的大多数同辈乡村青年的梦想,例如,与他同乡的那位妓女,就以在城里买房入户为荣。而在孙惠芬的《后上塘书》和关仁山的《日头》等小说中,主人公们如果在单向度的空间迁徙中失败,他们面临的主要是物质上的生存问题,而非精神上的身份认同焦虑;而一旦他们通过非正常手段,或带有原罪的方式获得了成功,则更为需要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而非构建主体感的身份书写。
与此相对,在经由“书本”这一象征标识走向城市的脱域写作之中,主人公们所显示的是另一维度的问题,即精神上的荒芜及还乡冲动。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当主人公义无反顾地走向城市时,精神返乡也就在同时沦为了一种姿态,家乡其实与外面的世界一样,都是荒芜并充满变化和危机的,“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得慢而已”。因此,只有处于未完成状态时,精神返乡才具有意义,一旦进入现实,美梦必将破灭——《高老庄》中的子路逃也似的离开了家乡。这一点也为许多作家所意识到,当他们的主人公产生返乡冲动时,并不会真的回到家乡,而是选择另一个替代品,如《耶路撒冷》中的耶路撒冷这一意象就带有虚幻性,仅仅停留在想象和未完成状态,而当初平阳面对花街出现的“匪夷所思的混搭”,感到的也是荒唐和悲哀。本应成为永恒时间、精神寓所的耶路撒冷只是一种虚构;而故乡也不复存在,跨域者不得不沦为故土上的异乡人。现实的两端都指向驱逐和异化,“我可能在哪儿都难有生根发芽之感。这可能是常态,在哪里你都无法落实。惟其如此,此心不安处,非吾乡者亦吾乡。只能如此”。而像文珍的《衣柜里来的人》和杨则纬的《于是去旅行》中,主人公则会选择一场前往拉萨或丽江的旅行以缓解内心的焦虑。脱域写作中,旅行常常是精神流浪者们缓解内心焦虑的重要方式。
不难看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是脱域写作中普遍涉及的主题。对于《哦,香雪》《平凡的世界》《人生》等小说而言,它们的主人公同城市之间是一种想象性关系,还只处在走向城市或被城市所召唤的过程中。而当农村青年真正走向城市后,危机也就浮出水面,一方面要承受来自现实的强大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感到与城市的格格不入。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宋小词的《倒立行走》、马小淘的《毛坯夫妻》中。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也可体现在那些既说不上成功,但也不失败的主人公身上,如文珍的《第八日》,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甫跃辉的《巨象》等,然而这却代表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危机,异己感与其说是来自外界的打击,毋宁说来源于自身的无根感。这些从小城、乡镇或农村来到北京和上海的青年,不得不亲身验证超一线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显示出的令人可畏的凝聚力和排斥力。两种力量的并存撕裂了主人公们,使他们的存在也呈现出分裂状态——现实中决绝悲壮的坚守与执着,和精神上茫然无措的惶惑焦虑。
结语:反向跨域与新出口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加速发展,一方面带来空间等级秩序的日趋明显;另一方面也带来空间的同质化现象:世界越来越像“地球村”,使得身处全球化大都市或中心城市的人们往往产生出一种逃离或自我逃离的冲动,形成“反向跨域”:从中心城市逃向荒山或深山——如鲁敏的《奔月》和王安忆的《匿名》。她们的主人公试图从中心城市逃离(或被逃离)到偏远山区、穷乡僻壤,尝试一种重新陌生化的生活。但当生活从全然陌生逐渐变得熟悉时,人们最终发现边地与中心城市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之处。逃离显示出了虚妄的色彩。此时,只有不停地奔跑(《奔月》),或者让自己沉于水底(《匿名》),才是灵魂的最佳归宿。拥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和“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等诸多积极品质的现代人,同样也是一群在精神上无故土可归的人。同质化的空间已然使人们无处可逃、逃无可逃。
由此来看,近些年出现的“反向跨域”的脱域写作显得别有深意。如王安忆的《匿名》《遍地枭雄》等作品,作家试图通过一种全然陌生的语境以激活主人公的人生体验。然而这是一种“再符码化”的过程,《匿名》的主人公通过重新识字和说话而完成的,是再度文明的过程,究其根本不过是一次再循环、再启蒙而已,个人的精神危机并不能得到解决。钟求是的《零年代》则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小说在一个喧嚣的时空背景下讲述一个“慢煮时间”的故事:主人公赵伏文和云琴来到(回到)被遗弃的乡村,这样一种返回带有双重意义,一是从城市向乡土的撤退(云琴),一是对被遗弃的乡村的重建(赵伏文)。赵伏文和云琴在城市空间和空心村之间的跨域显示出的是对社会加速发展的某种批判。社会的加速发展带给人强烈的异己感,赵伏文不再能找到自己在城市的位置,城市也直接带给云琴肌肉的无力感。“无力”是人们面对日益快速发展的社会时最切实的感受。他们只能回到被遗弃的空心村才能凝聚或重建自己的气力,及其身份认同。与钟求是的困惑相似的是张忌的《出家》,主人公从农村走向城市后发现,回到农村已变得不再可能,但城市却又让人产生一种深切的空虚,无法着陆的感觉使主人公最终选择了出家。出家以其处于所有世俗空间外的过渡状态,或许构成了脱域写作中一种新的身份重建,及对主体性思考的新出口——“空无”。
脱域写作既是一种空间书写,也是一种身份书写,其构成与内涵复杂多变,并还在不断生成新的表达方式。其中所涉及的身份认同危机和自我救赎命题凸显出浓厚的空间政治意识,而在某种程度上,空间权力对人物的生产和规训,构成了80年代以来城乡题材小说写作新变的内驱力之所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