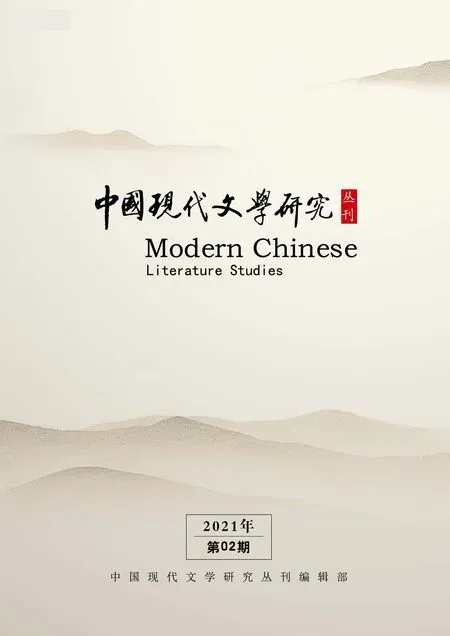彭燕郊研究:回顾与前瞻※
——纪念彭燕郊诞辰一百周年
内容提要:学界基于彭燕郊人生历程和写作生涯形成的三个“三十年”的研究视角,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现这一“跨越现当代文学阶段的人物”的形象内涵。纵观数十年来彭燕郊诗歌的接受状况,总体上不够均衡。不少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一个“‘被低估’的文学史形象”,这预示了彭燕郊诗歌研究的较大空间和相关评价可能达到的高度。同时,彭燕郊相关文献总量繁巨,近年来已有较多工作进展,若在文献整理、全集出版、版本校勘、传记写作等方面持续推进,则彭燕郊的重要性能得到更全面的呈现。
对彭燕郊相关文献的整理出版而言,2008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此前所出版的彭燕郊作品集多是诗文,所展现的主要是彭燕郊作为一位诗人的形象,最主要的作品集即是2006年年底出版的《彭燕郊诗文集》,分三卷四册,诗歌卷分上下册,散文诗卷、评论卷各一册。2008年彭燕郊逝世之后,相关文献的出版呈现更为丰富的态势,先是三卷本“彭燕郊纪念文丛”出版,其中包括首次结集的回忆文集《那代人》(2010年)。随后,则有大学课堂的“诗歌研究”课程讲稿(《彭燕郊谈中外诗歌》,2011年)、书信集(《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2012年)、日记选录(《溆浦土改日记》《“文革”日记选录》,2013年)、谈话录(《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2014年)等多种样式。由此,彭燕郊形象有了更为多元、也更富历史价值的内涵。如今,时至2020年——彭燕郊诞辰百年,《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和《风前大树:彭燕郊诞辰百年纪念集》先后出版,前者共录两人书信660余封,跨度达24年(1983—2007),体量相当宏大;后者仿作家研究资料集的体例,分作家自述、相关印象记与回忆文、相关研究与阐释以及包括研究综述在内的相关文献辑存。此外,《彭燕郊年谱》已经完成了初步撰写,《彭燕郊陈实往来书信集》即将整理完成,《彭燕郊书信集》(分去信和来信两种)也在编选之中。与此同时,部分彭燕郊文学资料以捐赠的形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馆。随着百年的到来,彭燕郊文献的出版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一时间节点,对相关情况进行回顾,同时,对一些症结或可待深入之处予以前瞻,对彭燕郊以及相关话题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一 作为“跨越现当代文学阶段的人物”的彭燕郊
回顾既往的彭燕郊研究,有两种比较突出的思路:一是“七月派”研究框架;二是地域文学(主要是湖南文学)的视角。这对彭燕郊的名声多有提升,但对其诗歌个性的认识实际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妨碍。也有人认为,不少研究“常常只是彭燕郊诗歌的某些部分和方面”,缺乏对于“彭燕郊诗歌艺术的全景”的整体把握。
纵观彭燕郊八十八年的人生(1920—2008),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其人生可大致划分为三个“三十年”,每一个“三十年”人生的转折都跟国家命运、时代风云紧密相关:从1920年至新中国成立,近而立之年的彭燕郊已在血与火之中淬炼了青春期;从1950年直至1970年代末期,又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精神炼狱;再往后,直到2008年逝世,又一个三十年,彭燕郊获得新生,不仅再一次迸发出强大的诗歌创造力,在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的译介出版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也产生了积极的效应。阶段性特征如此之明显,提供了深入讨论的基础。
实际上,彭燕郊的身份其实远非“诗人”所能涵盖。“诗人”固然始终是彭燕郊最为主要的身份,但弱冠之年入新四军,写诗,在桂林、重庆、香港等地参加文学活动,从事编辑工作,直到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参加第一次文代会,这已算是有多重身份。1950年从北京到湖南之后,学者(教育工作者)、民间文艺工作者身份日益凸显,又遽然沦为“胡风分子”和街道工厂人员。及到新时期之后,在写诗——不断探索诗的新风格的同时,又因花费大量精力来筹划、组稿乃至主编外国诗歌的译介而被称为“文艺组织者”,再加上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代之后,其作为历史当事人、文学青年导师、大陆与港台文学活动的联络者等身份也都累积了比较丰富的内涵。
彭燕郊身上所交织的诸种身份自是各有其历史效应,但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其中有着“现代”与“当代”交集的复杂蕴涵。在现代中国,彭燕郊有过十余年的写作历史,在《七月》等刊物发表过较多作品,出版过五种作品集,已有比较突出的写作风格,聂绀弩在为其诗集《第一次爱》所写序言中,曾赞誉彭燕郊“不但对于我们常见而漠然了的东西发生兴趣,还能从大家共见的东西上看出我们所不能看见的东西来”,并作了一种类比,“杜思妥耶夫斯基写完了他的处女作《穷人》,别林斯基对他说:你的年龄应该还不懂得他写得如何地真实。如果别林斯基的话是对的,彭燕郊也应该不懂得他自己的诗篇的沉重”。这一判断可谓是非常敏锐地发现了彭燕郊的写作才能。总体视之,现代阶段彭燕郊的诗歌写作与文学活动与冯至、卞之琳、艾青等前辈诗人或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有其独特之处,已然具备了可堪讨论的重要意义,这应是毋庸置疑的。
在第二个“三十年”里,彭燕郊的人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有两点尤为突出:其一是地理的挪移,彭燕郊本有机会在北京立足,但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他来到了陌生的湖南长沙,且从此定居下来。其二是人生志向的转变。学历较低、从未在大学任教的彭燕郊接受了湖南大学中文系聘书,据称,时任中文系主任谭丕模“想把湖大中文系办成鲁迅艺术学院式的系”,希望和彭燕郊“共同办好这个系”。彭燕郊本人也希望到湖大“可以带学生下厂、下农村,搞创作”。初到湖南,彭燕郊确实经历了带学生下乡的阶段,不过是与“高等学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直接相关,而难以实现“鲁艺式”中文系的设想。种种资料表明,彭燕郊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份工作之中,先后到益阳、溆浦等地参加土改,有详细的土改日记;有相关创作,如《高兴大妈》等;同时,利用这个机会采集了7000余首歌谣,随后从中选取部分辑成《湖南歌谣选》出版(1954年)。1977年,钟敬文有诗《喜燕郊北来》,其中有句“相期完胜业,万里骋飞轮”。所谓“胜业”,指的就是关于民间文学的编集和研究。如果说,1950年在北京与钟敬文一起编《光明日报》“民间文艺”副刊的经历确立了彭燕郊对于民间文学的兴趣,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民间文学乃是彭燕郊的“胜业”。
因全国院系调整,彭燕郊在湖南大学短期任教之后,又曾到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但1955年,此一时段的教书生涯因“胡风事件”而中断。“胡风分子”成为彭燕郊的一个重要身份。二十一个月的关押、被开除公职、闲居在家,之后则是二十余年的街道工厂经历。新时期初期,彭燕郊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街道工厂“工作很轻,搞油漆,业余时间较多”,二十几年来“一直没丢掉专业,仍然热衷于买书,读书,写作”。写作方面,1967年5—6月的日记曾整理刊行。其诗作,日后在编选“潜在写作作品集”时,曾辑成《野史无文》(2006年),而稍早的《夜行》(1998年)也收录了不少标注为此一时期的作品,但和学界对于“潜在写作”有所质疑的情形相似,彭燕郊此类作品的写作时间也可再估量。总的来看,无论是人生际遇还是写作状况,此一时期的彭燕郊均有新的阶段性特征,也具备了较多可堪讨论的内涵。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一直没丢掉专业”的彭燕郊进入人生的第三个“三十年”。大学教师生涯得以赓续,只是换作了湘潭大学中文系;“专业”工作也有了更大面积的展开。概言之,彭燕郊晚年的诸种文化身份之中,更为突出的是文艺组织者、七月派或“胡风分子”和民间文艺工作者,但细加缕析可发现,彭燕郊还是进行了比较明显的文化抉择。民间文学工作始于新中国初期,1979年参加第四次文代会的专业身份也是民间文学,至1980年代中段,相关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而从胡风这条线索下来,非常明显地凸显了彭燕郊的“七月派”或“胡风分子”身份,新时期之后,特别是1985年胡风逝世之后,纪念性文字乃至《胡风传》的写作,是彭燕郊本人明确意识到的——同时也是其他“胡风分子”赋予他的一项重要任务,相关话题显示了一名“现代作家”如何在当代文化语境之中展开历史认知与自我辩诘,其间带有强烈的思想史或文化史含义,但此方面写作只实现了很小的一部分,有着明显的未完成性。相较而言,源于新时期初期的文艺组织——更确切地说是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方面的工作,彭燕郊投注了更为持续的精力,一直到去世之前仍“以老牛破车自况”,并与友人商谈外国文学丛书的出版构想。代表性的书刊即有“诗苑译林”丛书、《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等,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充分显示了彭燕郊在新的文化语境之中所做出的文化抉择”,其中蕴含了“藉助译介活动来推动当代文艺发展的自觉意识”,标识了彭燕郊作为一位“当代文学人物”的属性。
藉由如上勾描,一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彭燕郊的人生与写作有着非常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国家命运、政治局势、时代语境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彭燕郊之于时代有过积极的投合,时代之于彭燕郊的人生抉择、写作与文学活动也有着明显的激发作用,“七月派”、地域文学以及民间文学、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组织工作等方面内容在此都能得到解释。另一方面,在与时代交集的过程中,彭燕郊的个性特征、艺术能力与专业精神也一直在发挥作用,并最终占据上风。彭燕郊身上有一种特别的韧性,这使得他历经困境而不屈——转换为写作,则是对于诗、对于文学艺术的“沉迷”。彭燕郊早年诗与“七月派”的总体风格有关联,但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而其晚年也始终坚持诗歌写作——始终葆有诗艺探索的激情,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衰年变法”。当然,学界对其诗歌艺术成就的评价可谓见仁见智,但彭燕郊“晚年写作”的形象孑然独立于当代中国作家之中,应无疑义。至于其他方面,如在民间文学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在新时期初期即敏锐地把握文艺发展的新动向并且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的文艺组织工作,均非短期行为或随性为之,借用彭燕郊致友人信中的一个词汇,均可说是一种“专业精神”使然。
由此来看,较之于之前的研究,三个“三十年”的视角兼具阶段性与整体性、时代性与个人性,应该是更为全面的视角。再进一步看,依据时代转折而划定的三个“三十年”明确了彭燕郊作为“跨越现当代文学阶段的人物”的形象内涵,这也有文学史的独特意蕴在。纵观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群体,从现代到新中国,再到新时期,跨越不同阶段的作者也不在少数,而彭燕郊算得上非常典型的一位,三个阶段均有足够的长度和较多可堪讨论的内涵,可说是完成了从“现代作家”到“当代作家”的转换,显示了一位写作者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这也是衡量一位写作者是否重要、能否称得上是大诗人(作家)的主要标尺。
二 “彭燕郊现象”或“‘被低估’的文学史形象”
当然,彭燕郊被人们所认知,更主要的还是作为一位诗人。对于彭燕郊诗歌的阅读,始终还是重点所在。文学编辑、批评家韩作荣曾写过一篇《彭燕郊现象》。在他看来,“诗歌史中曾经走红一时、声名显赫的诗人未必是当时最好的诗人”,“文学史上的一些名著,初现时大都没被世人普遍接受”,用以举例的包括杜甫、布莱克等著名中外诗人。而彭燕郊“是一位似被忽略、却对诗有着深入、精到理解、卓尔不群的真正的诗人,却没有得到重视和应有的评价”,“他对诗之深入理解与永不枯竭的诗之敏感和天分融于一体,才有了中国新诗中鲜见的‘彭燕郊现象’”。此前评论界有类似呼声,也有过同名文章,界说的涵义不尽相同,但韩作荣在彭燕郊逝世四年之后所发出的声音再一次凸显了对于彭燕郊的阅读与评价的问题。
就彭燕郊作品的研读而言,目前最为精深的可能是陈太胜。在他看来,“彭燕郊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诗人!”彭燕郊的诗歌和散文诗均可属于“最好的作品之列”,彭燕郊早期诗“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与文学史所强加给‘七月派’的那种单一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的总体风格的不相吻合。他早期诗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可被列入新诗史上最好的作品之列”。“彭燕郊具有一种惊人的把现实变成想象的诗的能力,与那种夸张的强制性的语言暴力完全不同,这是节制的更为有力的声音,在此,诗确证了诗自己在人类文明中独特的作用和力量,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一种呼吁,同时也是娱乐人的带有甜美声调的音乐。”“彭的诗,在某种意义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诗与音乐的关系。这一点在他的晚期(1979—2008)诗作中似乎尤为明显”,“彭的诗既是某种哲学,又是某种音乐。他的诗的语言赋予了思想以音乐的境界”。“作为一个长期被忽视,至今其写作成就没有得到应有和公正评价的诗人,彭先生的散文诗写作也遭受到了相类似的命运,还只为少数人所看重。事实上,依我个人的判断,彭先生是中国现代继鲁迅之后在散文诗这一文类的写作上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作家。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研究的彭先生的散文诗写作,恰恰体现出了其写作的丰富性与实验性,或者说是先锋性。”这类判断基于对文本的细致研读以及关于现代诗、现代散文诗的相关理论,是其讨论新诗现代性这一总体思路的一部分。而这,固然并不完全是空谷足音,但到目前为止,并未得到充分应和。
一个被认为是“最好的”诗人为何会被忽略呢?究其原因,自然有诗歌文本、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因素,阅读的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21世纪初期的一种为彭燕郊呼吁的声音指出:“彭燕郊是我们时代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但是“在我们众多的文学史教本和大学课堂里却是一个空白”。这里重提,倒不关乎辩护,而是试图继续引向彭燕郊作品的阅读与评价的问题。上述观点认为阅读是一大关键,“让人们读到较为全面的彭燕郊作品集,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必须尽力让更多的人阅读到他的那些在中国新诗史、文学史上极为独特和卓越的作品”。事实上,囊括彭燕郊最主要诗文作品的《彭燕郊诗文集》在2006年即已出版,这确乎引发了一些阅读,上述两位作者即是在读了该套诗文集而展开论说的;随后,也有学者据此称彭燕郊为“‘被低估’的文学史形象”。但以“文学史”的视野观之,彭燕郊的名字多半只会出现在关于“七月诗人”和“归来诗人”的一连串诗人名字的罗列之中,而不会展开进一步的介绍或评述,典型的处理方式即如严家炎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所示。也有的文学史,如朱栋霖版《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5—2016(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其名字见于“归来的诗人”部分,但未见于“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部分。可以说,一二十年来,在大学的文学史教本以及大学课堂上,相关情势自然是在缓缓改变,却也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但关于阅读,如下关于选本的材料或许会提供一些相异的观点。我们曾做过关于彭燕郊诗歌(含散文诗)的选本统计,所称选本包括两类:一类是彭燕郊本人编订的(包括自印诗集),计17种;一类是由他人所编选的,为不完全统计,目前是177种。时段为1942—2019年,其中绝大部分为新时期以来的选本。入选频次最高的为21次,有两篇,即《雪天》《家——给一个在动乱中失掉家的人》,入选频次在10次以上的(10—14次)有《小牛犊》《冬日》《读信》《敲土者》《檐滴》《影子》《明霞》《一朵火焰》《宽阔的蔚蓝》《落叶树》《混沌初开》等。入选频次和篇目或已超出一般的印象,与彭燕郊本人的选择也不一致,这显示了作品接受的差异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关于彭燕郊的选本不能说是少,其中有比较多的年度诗歌选本,也有《中华诗歌百年精华》《二十世纪中国新诗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二十世纪中国经典散文诗》《中国新文学作品选(上)》《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新诗卷》《新时期文学二十年精选·诗歌卷》《鱼化石或悬崖边的树:归来者诗卷》等重要选本,这至少意味着在不同时期“选家”(也可以说是专业读者)的视野中,彭燕郊是一位值得选入的诗人——基于较多的选本量,很难说彭燕郊是一位被忽视的诗人,只是受重视的程度该如何考量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2007年以来,以彭燕郊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17篇,数量不算少,其中对于彭燕郊与西方诗歌、绘画艺术、音乐的关联研究,以“文学活动”为中心来探讨彭燕郊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关联,文献学视野下的彭燕郊研究等,显示了年轻的研究者的活力、锐气以及值得称许的文献能力。不过,17篇硕论中有15篇来自湖南的四所高校(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湘潭大学)及陈太胜所在北京师范大学,相关指导教师何云波、陈太胜、赵树勤、易彬等人,或为彭燕郊的学生或为重要的彭燕郊研究者,均可说与彭燕郊本人有着明确的关联。这自然可说是一种薪火传承,但也昭示了相关影响的某种限度;而且遗憾的是,从目前所获知的情况来看,相关工作多半也就是止于此,缺乏进一步的进展。
综上,彭燕郊并非一个完全不受重视的诗人,在部分研究者那里,彭燕郊获得了非常高的认同度,且有很大力度的推介,但在文学史著之中遭遇冷淡,在普通读者中也可能遭遇某种阅读障碍。放诸作家作品的接受史,这也算得上是比较奇异的景象——若韩作荣等人所谓“彭燕郊现象”是可信的话,那还可以适当细化,即彭燕郊在部分研究者与更多的研究者、普通的读者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反差。
反观韩作荣、陈太胜这两位不同年龄层次的研究者(读者),其与彭燕郊的“相遇”可说是有着独特的蕴含。两人都与彭燕郊有过交道,但都是到了很晚的时刻。韩作荣只是因为2006年来长沙参加诗歌活动,“一天晚上在田汉大剧院看演出时”与彭燕郊有过一面之缘,他当时“读过的彭燕郊先生的诗并不多”,但“最早关注彭燕郊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诗,而是他参与或主编的几套书”,即1980年代的“诗苑译林”丛书等。待到2007年3月收到彭燕郊寄赠的诗文集,才“深入了解、结识彭燕郊这位诗人”。陈太胜认识彭燕郊稍早,见过两三次面,有过一些书信往还,是彭燕郊在晚期阶段非常器重的一位研究者,但陈太胜认识彭燕郊“最初与他本人的诗人身份并无关系”,而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博士论文确定以梁宗岱诗学为主题,需要查询相关资料,而彭燕郊在筹划“诗苑译林”丛书的时候,与梁宗岱有过交道,又协助其晚年伴侣甘少苏撰写回忆录《宗岱和我》,掌握了包括梁宗岱手迹在内的不少资料。两人交往始于2001年,但陈太胜真正研读彭燕郊诗歌已是2007年,《彭燕郊诗文集》已出版、“《彭燕郊诗文集》出版暨创作研讨会”将召开之际。迫于参会的压力而阅读,没预料“读彭先生的诗,却让我深感震惊。一上午和一下午,彭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似乎完全变了——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诗人”。
可能并非是巧合,韩作荣、陈太胜这两位研究者知晓彭燕郊的名字,首先都是因为其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在比较长的时间之后才真正进入彭燕郊的诗歌世界——对照陈太胜对于年轻学生的告诫,最终是“文学的经验”发挥了效应。这样的故事听起来非常美妙,显示了彭燕郊的专业工作和诗歌写作的总体效应。
三 文献、版本、传记等:若干可堪深入之处
从目前情形来看,彭燕郊相关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确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因为某些文献的不足,彭燕郊人生的一些重要阶段至今晦暗不明——有两个时段的文献匮乏尤其严重,一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之前,大致即早年阶段;二是1950年代中后期到1979年代后期。早年阶段缺乏家族方面的讯息,也少有旁述类文献,目前多依据彭燕郊本人所撰写的简略的年谱以及晚年的回忆文。后一阶段属特殊的政治时代,公开文献少,相关回忆不多,能被采信的有效文献有限。综合考量,前一阶段或已难有更多文献,而后一阶段,若能获得档案材料,当能有效充实;口述历史的采集也是一个重要途径,但目前还只是偶有出现。
至于其他阶段,相关文献虽说是比较丰富,但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清理。比如,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到1950年代中期,彭燕郊诗文的发表总量不小,且发表的地域比较广泛,日后搜集有不小的难度,以致至今仍没有比较完整的目录。彭燕郊晚年曾托一些友人查阅早年资料,也自编过一个很不全的发表目录,但相当部分作品被遗落在《彭燕郊诗文集》之外是可以想见的。当然,有些作品未收,也是彭燕郊本人有意汰选的结果。我们所编《彭燕郊年谱》,得益于发达的数字文献检索系统,对此阶段的文献多有发现,但也有不少原刊尚未找到。至于新时期之后彭燕郊作品发表的情况,有原始书刊和数字资源数据库并用,已不是难题;但其他的文献,特别是文艺组织方面的文献,当初多半是书信、文稿,而未见诸公开发表的书刊,随着时间流逝、当事人远去,相关历史与话题有被湮没之势。
总体来看,目前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是文献的不平衡,即如我们所作的《彭燕郊年谱》显示,某些人物、某些阶段的文献更密集、篇幅更大,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与某些人物之间的交往更深、某些阶段更为重要,而是受限于实际搜集到的文献以及文献本身所包含的信息量。以书信为例,彭燕郊在各时期,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与各方文艺界人士多有书信往还,足可称得上是一位勤奋的书信家。友朋来信得到了彭燕郊的较好保存,但彭燕郊的去信所见不多,较大规模的集拢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到目前为止,那些通信量比较大的对象,除了梅志、陈耀球、陈实之外,完整掌握的仅少数几位,如给木斧、卢季野、陈梦熊、李振声、陈太胜等人的信,其他的人多半还只是一些零散的材料,如可知施蛰存与彭燕郊1981—1999年有大量通信,但目前仅见1981—1982年彭燕郊的9封去信,以及施蛰存1990年代的来信和1980年代的少许来信,计有30余封。这样的状况势必会导致文献不均衡的局势。其二是主题文献的梳理与历史的辨析。以彭燕郊所从事的文艺组织工作为例,“诗苑译林”丛书显然得到了更多关注,包括《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在内的其他书刊则缺乏系统梳理。而彭燕郊的“专业精神”确是值得称道,他对现代以来外国文学译介的总体情况非常熟悉,很多“在一般人的视野之外”的译作都了然于心,但此中也有一个状况,那就是他并不通外语,与新时期以来同样从事类似工作的同时代人如袁可嘉、绿原等人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缺陷,由此,相关工作或许也需作进一步的估量。
对于彭燕郊而言,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文献来源,那就是他那堪称繁巨的遗藏。彭燕郊自认是一个连一张纸片都舍不得扔掉的人,其遗藏之中还有大量可堪利用的文献,至少还包括数以千计的书信和明信片,逐年记录的日记,所搜集的成捆的民间文艺资料,所搜集和保存的友人手稿、作品剪报,各时期的纪念册、证件、票据(比如,参加文代会的代表证、购买粮油的证明之类),等等。最近借着一次《寻找彭燕郊》纪录片的拍摄机会,我们得以翻阅了彭燕郊很小一部分遗藏,也是多有发现。举两例,其一为1950年4月2日谭丕模、杨荣国给彭燕郊的一封短信,其中写道:“桂林一别,又已多年;近闻在光明日报工作,至为欣慰!兹者:湖大之中文系拟请先生为副教授,担任‘现代诗歌选’‘文艺学’诸课程,如蒙俯允,敬乞电示为荷!”前面提到从北京到湖南是彭燕郊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而这是目前所见关于彭燕郊来湖南任教的唯一的原始文献。其二为一张题为“红星积木”的设计图纸,上有“长沙市城北区钢铁人民公社玩具厂”的字样,厂址在砚瓦池正街24号。这与彭燕郊的街道工厂经历有关,此一经历前后超过20年,回忆资料显示,大约从1970年之后,彭燕郊开始在长沙阀门厂做翻砂副工和油漆工,但关于此前的工厂,只有一个含混的说法,即“街道工厂”,工厂名称、地址均不得其详。彭燕郊遗藏中的这份图纸,包含了明确的信息。相关遗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仅有少量被整理出来,而要全部清理好并整理出比较完备的目录或出版相关文献专集,显然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基于新文献而展开研究,自然是一种常见的思路。以书信为例,新近出版的《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体量宏大,对新时期以来彭燕郊各方面的情况有比较全面的呈现,对文化语境,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译介方面的信息也多有涉及,当值得深入研读。而随着部分彭燕郊文学资料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的公立机构,更多的读者将有机会接触到他的手稿、作品集等文献,相关研究工作应该也会逐渐展开。
也有研究基于新发现的油印本彭燕郊诗集《消息》展开。在彭燕郊诗歌的传播过程中,有一类比较独特的现象,即存在较多非正式出版的油印本、打印本,其中还包括一种中英对照本。这可能是自印,限于出版条件或出于交流的目的,也可能是他印,《消息》即是熟悉彭燕郊的人士所编,但仅署“编者”,未署姓名。这些之于彭燕郊写作历程有着独特效应的文献自然值得细致勾描。《消息》出现于1980年夏,当时正是“归来之歌”方兴未艾之际。在研究者看来,诗集“包含了某些读者对于彭燕郊这位‘别具一格’的诗人的期待”,“不同于那些在政治与社会话语之中确认自我的‘归来诗人’,彭燕郊从自然、艺术之中发现自我作为‘人’的存在的勇气与价值,写作了一批‘美’的、‘轻松’的诗篇”。也即,同为“归来诗人”,彭燕郊有着不一样的姿态和声音。但是,“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学界对于彭燕郊诗歌的总体评价并不在这个方向,彭燕郊本人对此也有犹疑”,由此,研究者认为,“历史评价的差异,写作者观念的演变,对于某些题材与风格的汰选,均可进一步辨析”;而在这样的辨析过程之中,“关于彭燕郊的整体阅读与研究的更大空间”也能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作家的经典化,须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基于全面的文献搜集而编选作家作品集,是经典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仅有三卷四册《彭燕郊诗文集》和若干作品集单行本,这意味着彭燕郊的整体形象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呈现,比较完备的彭燕郊全(文)集的编选是未来一段时间亟待进行的工作。前段时间,我们曾应某出版社要求,列出一部《彭燕郊文集》目录,包括诗卷、散文诗卷、评论卷、散文与随笔卷、回忆录卷、访谈卷、书信卷、土改文献选、讲课录、民间文学卷以及附卷,共19卷。这自然只是初步分类,卷数尚不能完全确定,卷名也不尽合宜,但体量之宏大、编选之难度已在其中。而彭燕郊作为诗人、作家、评论家、文艺组织者、大学教师(诗歌教育家)、民间文学工作者等方面的形象和业绩,由此将得到全面的呈现。
构想中的《彭燕郊文集》,诗歌有三卷到四卷,这一方面是因为彭燕郊诗歌数量较大,尚有较多诗作遗漏在2006年版《彭燕郊诗文集》之外,有待辑佚。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版本的考虑。彭燕郊是一位不断求新求变的诗人——因其对作品有过反复修改,也可将他归入中国新诗史上对写作最为苛求的作者之列。彭燕郊的诗歌往往有着多个版本。综合来看,彭燕郊的写作修改行为主要发生在新时期之后,其修改作品的驱动力主要并非外在的时代因素,而是个人对于写作的不断苛求,即如论者所指出的,彭燕郊“将诗歌作为最高境界和价值意义上的艺术品(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进行虔诚的打磨,为此,不惜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几遍、十几遍甚至几十遍地修改一首诗(如《罪泪》《岳阳楼晚眺》《湖滨之夜》乃至《妈妈,我,和我的歌》等,都有多种版本或极大的修改时间跨度)”。2006年版的《彭燕郊诗文集》,即经过了彭燕郊本人长达数年的反复修订,其中有筛选,也有对于作品的全面修订,是彭燕郊的最终改定本——回忆文不在此列,但从当时已经大致编订,但到2010年方才出版的回忆文集《那代人》来看,也有相当程度的修改。
作家晚年对于作品进行审订与汰选,编成比较完备的个人作品集,这也并非孤例,艾青、卞之琳、徐迟、昌耀等人都曾如是为之。研究者对此或有非议,但写作者并非为文学史或研究者而写作,自有修改作品的权利。从作品的版本谱系来说,这意味着定稿本的出现。对研究工作而言,则意味着又多了一重考察的维度。为了更好地展现彭燕郊写作的历史面貌、提供更精确的版本谱系,构想中的《彭燕郊文集》即打算以汇校本的形式呈现。我们目前已在着手进行这一工作,但其中的烦琐和困难不难想见。
运用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知识理念对作家作品展开研究,目前在学界已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基于彭燕郊作品比较复杂的版本状况,版本批评、批评性校读都有其必要性。学界对此也有过关注,但还很有限,其中有赞誉,也有明确的问题指陈,比如,李振声即曾批评《生生:多位一体》的修改本,“诗作本该具有的博大与丰富,是从一开始就已经被诗人自己的设定所削弱或消解了的”,改定本的跋语“里边随手援引了国际政局中刚发生不久的一个事件,用以诠释诗的题旨和写作动机。这不止牵强,也大大缩小了诗义的涵盖度”。但也有一些研究以《彭燕郊诗文集》为对象来统摄彭燕郊各时期的写作,实际上造成了论者所谓因“版本的互串”而有损“批评的精确”或导致“阐释的混乱”。在日后的研究之中,宜树立精确的版本意识。
传记工作也亟待开展。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彭燕郊年谱》,字数超过30万,包含了很多新的信息与线索,而一部更为翔实的彭燕郊传记也有必要。此前有过《认识彭燕郊》(苏正军,2000年)、《彭燕郊评传》(刘长华,2008年)两种,在总体上偏于论述,所运用的生平文献比较单薄,不少重要阶段未能得到深入、有效的透现。与传记写作相关,口述历史的采集以及对于作家生活史、文学地理等方面的田野调查与文献搜集工作也亟待展开。使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是因为《寻找彭燕郊》纪录片的拍摄,拍摄者为肖振锋、张雷等年轻人,来自彭燕郊当年工作过的湘潭大学,他们在湘潭、长沙、广州、桂林、北京以及彭燕郊家乡福建莆田等地采访了很多人物、拍摄了很多素材。这实际上也是文化抢救的过程,所采访的人物之中,就有彭燕郊在湖南大学的学生和湖南师院的同事、现已93岁高龄的汪华藻老先生。而就我所知,相关场景的拍摄却是遭遇了一些困境,突出的一例就是现位于长沙市城区的彭燕郊1970年代工作过的长沙阀门厂旧址(现为雨花区红花坡路30号)。2018年年底,我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到过此地,拍下了数十张旧厂房的照片,后来搜罗多种历史文献,写过一篇短文,名为《红花坡路30号,彭燕郊当年刷过油漆的地方》。2020年9月领着拍摄组再来此地准备取景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被改造成为一个文体生活园,除了标有“长伐 1976”字样的井盖等还保留原样之外,门窗、墙体、屋顶等都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造,墙上的标语、告示基本上被清除或被新的油漆覆盖。随着阀门厂的痕迹被有意抹掉,长沙又将失去一处跟彭燕郊有较长关联的场所——在更早的时候,彭燕郊的旧居已经随着湖南省博物馆的扩建改造而消失。城市变迁仍在普遍发生,寻访其他跟彭燕郊相关的地方已有了特殊的紧迫性。若能摄制相关影像或图片,并有针对性地钩沉相关文献,则能积累彭燕郊传记素材;而这本身也将成为独特的历史文献,为未来的历史书写提供感性的参照。
结 语
同时代人牛汉曾赞誉彭燕郊为“默默者存”。“默默者存”典出《汉书·杨雄传》,在牛汉看来,这是“民族的传统”,今人之中也有不少继承了这种品质:“近五十年来,有沈从文、丰子恺、晚年的孙犁、上海的施蛰存和湖南的彭燕郊,等等,他们‘默默者存’,清苦,自在。”后辈学人李振声也曾谈道:“燕郊先生的诗,尤其是他晚近的诗作,始终维系在一个很高的精神高度上。我虽不便说,它们的存在,是如何在不时地提示和警醒着人们远离那些足以致使人类精神矮化的种种场景和事物,但我心里清楚,它们的存在,是怎样在延缓着我个人精神生活的退化和萎缩的。”这些声音显示了彭燕郊评价可能达到的高度。站在一百周年这一特定的时间节点往回看,尽管彭燕郊的接受与传播呈现复杂的或者说不均衡的态势,一般性的研究成果不算很丰硕,文学史著的认可度还比较有限,普通读者也可能存在某种阅读障碍,但也还是有足够的理由对研究前景抱以期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更多文献,特别是比较完备的作品全集的出版,会有更多批评者的加入,会打开更大的研究空间,而彭燕郊的重要性终将得到更为全面的显现。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