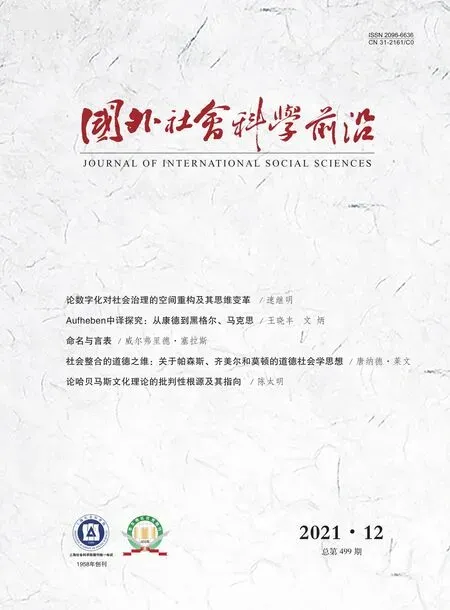论哈贝马斯文化理论的批判性根源及其指向 *
陈太明
众所周知,韦伯认为社会合理化过程乃是与哲学社会科学对整个世界的祛魅过程重合的。韦伯的观点为社会系统论承袭,按照著名的系统论学者卢曼(Niklas Luhmann)的观点,现代社会经历去神秘化后由“块状分化”向“功能分化”转变。在块状分化的视角下,我们从不同的、有形的团体(比如家庭、部落、民族等等),来理解社会运作;在功能分化视角下,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具有自己特殊的功能并分别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些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包括宗教、教育,等等)。1参见尼可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0页。但是,这三个子系统的地位是不同的。随着社会不断走向完善的合理化过程,政治系统逐渐成为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因而政治系统获得了高于经济系统与文化系统的地位。三个系统虽然各有侧重,但就主宰其运行的理性模式来说,它们都是工具理性的。这就加剧了韦伯早已有所意识的意义和价值丧失的问题,即现代社会在系统论理解下“其功能已经凌驾于我们大部分的日常理解。这些系统按照工具合理性进行运作,而悬置了人类价值和意义问题”。1Jim McGuigan,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179.通过哲学的追问找回丧失的意义和价值,遂成为哈贝马斯追问文化之作用的问题意识。本文拟将哈贝马斯的文化理论界定在这个问题视域中,并通过揭示其文化理论何以具有批判性为基础,进一步推论出其批判维度的两个指向。
一、有效性要求与文化的规范结构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的发展乃是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综合过程,不应局限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和政治中心控制力的提升。相应于系统论的三分法,对应经济系统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对应政治系统的是权力的增强,而对应文化系统的则是规范结构的提升。承袭了工具理性思维的系统论分析模式是有缺陷的,如其所言:“如果我们把社会理解为系统,就不会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现实性在于虽然得到公认,但往往是虚拟的有效性要求。”2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6页。这种有效性要求,哈贝马斯用语言予以解释,它指的是行动者在用语言进行人际交往过程中所暗含的承诺或保证。语言交往者用语言进行沟通以实现交往目的时必然会指涉不同的世界,如果言说者指涉的是外部世界必须满足真实性(truth)要求,如果言说者指涉的是人际关系的社会世界必然需要满足正确性(rightness)要求,而言说者表达的是内心的意向性整体的内在世界时则要满足真诚性(truthfulness)要求。诸有效性要求被哈贝马斯看作是客观的、超越一切语境的,因而任何以达至理解、获得共识为目的的交往活动都必须以这样一些在语言使用中得到承诺的有效性要求作为最终保障,舍此任何语言上的有效沟通和成功的交往都是不可能的。
很明显,哈贝马斯于此已经表露出透过语言预设的有效性要求反驳系统论的意图,“交往行动概念以相互理解为机制协调行动,它反事实地假设行动者的行动趋向于有效性要求,这也就要求其对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具有一种直接相关性。”3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 William Rehg, Cambrigde, Mass.: The MIT Press, 1996, p.17.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种在语言有效沟通中获得承诺的有效性要求究竟与何种社会子系统产生关联。就经济系统而论,经济进步的核心在于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经济总量之提升,当然,这里面主体的创造力、科技的进步程度都会对其有影响,但是其主要的判定标准依然在于资本的增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消费在量上的提升,而不去考察背后的价值理念与规范要素,因而简单来说它是金钱导控的。而就政治系统来说,政治系统的进化过程在于各个行政部门合作效率的提升,它要求在最短时间内、用最低成本做到上传下达,并将其控制能力提高到最大范围,因而它是权力导控的。显然,哈贝马斯于语言中证成的这些有效性要求具有显著的无法科学量化的规范结构,它们并不存在于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子系统中,也不是其进步与否的评价标准。这一点哈贝马斯的如下说法能够证明,如其所言:“如果把生活中文化再生产结构中的有效性要求,诸如真实性、正确性等,理解为控制媒介,并且把它们和权力、金钱、信任以及影响等放到同一个层面上,它们就会失去其通过话语而能够得到兑现的意义。”1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7页。哈贝马斯在此表明两层意思:一是有效性要求与系统论所说的文化这个子系统相关联,二是这些有效性要求决定了文化不能与经济和政治适用同样的工具合理性标准。社会系统论对此并未有正确认知,由此造成文化系统成为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附属的结果,而社会系统也随之失去了规范性基础,由此而受到工具理性的货币和权力之单向导控。
与之相反,哈贝马斯认为,各个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之间的影响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此认为文化仅仅受到工具理性支配则与文化本性相悖,哈贝马斯主张,“在任何一种系统中,规范结构都必须和有限的物质基础区别开来。”2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7页。整个社会的发展不惟建立在对自然(包括社会)的征服上,在此过程中人的内部自然也会得到改造。同时,人是社会性存在的存在者,他以社会为前提和载体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人际关系,并通过相应的社会规范稳定彼此的行为期待,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过程,也充分显露着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哈贝马斯进而指出,“社会系统的理想价值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价值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系统整合非规范要求的产物;在理想价值中,社会生活的文化定义与系统论对于生存命令的重构是相互联系的。”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8页。这即是说,以有效性标示的社会交往过程以及在交往中促成的社会进化需充分重视文化的规范作用,这是文化区别于经济和政治的核心特质。
然而,规范结构本身乃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在系统论的三层区分中我们可以将其笼统地理解为文化,但其又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化这么简单。因为规范结构在笼统的文化定义下,实际上隐含的是其纠正系统这个单向理解模式的内部力量。系统论将政治系统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中心,在这个系统之中权力获得了绝对有效的指挥权力。可以说,在这种理解模式下,文化系统成为最受忽视的一个子系统,其造成的结果必然是韦伯早已揭明的意义和价值的丧失。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发展需要一种精神性动力,他把这种精神性的动力比喻为社会进化的起搏器,“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是社会进化的起搏器,因为新的社会的组织原则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这些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使现有的生产力使用或者新的生产力的产生,以及社会复合性(Komplexität)的提高有了可能。”4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25页。职是之故,哈贝马斯理解的交往其根基是一种精神性的沟通概念,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基于语言沟通上的相互理解而达成的共识,而他所理解的文化则是基于这种精神沟通之上而得来的人类思想成果,以此便不难理解文化的“起搏器”所具有的规范性功能。
显见,与马克思将社会整合建立在物质性的生产力基础上不同,哈贝马斯将社会整合的根本建立在语言性的相互理解所预设的有效性要求上。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整个社会的发展建立在一个匿名的规则系统之下,由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了文化的上层建筑。大体上,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这个观点表示了赞同,但是他同时认为,文化作为以经济基础为根基的上层建筑并不像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被制约的精神性因素。如其所言:“文化始终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尽管文化在向新的发展水平过渡时似乎发挥着一种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迄今所认为的还要重要的作用。”1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页。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理论尤其推重文化要素的规范效能。正是基于对语言交往中的有效性要求之揭明,哈贝马斯获得了一种解释社会进步的视角,其基本思路是以语言沟通揭示出的有效性要求为文化的规范性潜能进行奠基。
二、生活世界引导的范式转换
为了扭转工具理性主导的系统论的社会理解所造成的规范结构的缺失状况,哈贝马斯借用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通过在语言中证成的有效性要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虽然已经揭示出了交往理性这个与工具理性相对立的理性模式,并已表露出通过重建文化批判功能以反对系统论所理解的社会整合的基本路向,但是这并不足以深刻揭明系统论在理解社会整合上的核心缺陷,只有深入语言沟通的前理论层面才能挖掘出现代社会文化要素的批判潜能。由此,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基于金钱、权力、价值、规范等多种整合因素之下的整体,不能仅从因理性而来的主题化知识寻求支撑,不管这种知识是基于工具理性的还是交往理性的。这样,交往行动理论要想进一步揭示文化的批判潜能就需要生活世界这个“补充性的”概念2参见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Two: Lifes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o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homas MaCarthy, Boston: Beason Press, 1987, p.119.,因为“交往理性潜能首先必须在现代生活世界形态中释放出来,才能让获得解放的经济亚系统和行政亚系统的命令回过头来对遭到破坏的日常生活实践施加影响”。3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67页。
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是作为批判科学危机的概念而引入的。胡塞尔所面对的问题是,自然科学以异化的理想化前提来解释世界,并以之为世界解释的唯一金规则从而剥夺了哲学这类反思性科学的社会建构意义。为了扭转这种与事情本身相背离的世界认知,胡塞尔强调日常生活实践的非科学的偶然性之于科学世界观的前理论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世界概念提出的目的正是反对科学的理想化和武断化。虽然哈贝马斯借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以为社会的规范结构提供进一步说明,但是他同时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有一个盲点,即他并未认识到生活世界本身也是具有理想性质的。而究其原因则在于,“由于语言主体间性构成了主体哲学的一个盲点,因此,胡塞尔也未能认识到,日常交往实践本身就是建立在理想化前提上的。”1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75页。可见,与通常对胡塞尔未走出主体性的意识哲学范式的批评一致,哈贝马斯也认为胡塞尔因其囿于意识哲学的独白式言说方式而未能澄明语言沟通的主体间性结构。这就造成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未能揭明保障语言沟通的理想化前提,而这恰恰是语言所言说世界之有效性要求得以兑现的前提性条件。通过言说,生活世界的前主题性知识成为主题性知识,它们在各自所突出的主题中要求各自的有效性要求。
生活世界引入社会分析以抗衡系统论使哈贝马斯获得一种新的视角。由此,主导系统论的是基于工具理性的宰制而来的系统整合(systematic integration)的路线,而哈贝马斯坚持的则是与之对立的生活世界的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路线。对于两者之区别,哈贝马斯曾有明确论述,兹引如下:
社会整合涉及的是具有言语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在社会化进程中所处的制度化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被看作是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指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的特殊的操控性能。社会系统在这里是指通过掌握多变环境的复杂性而维持其边界与持存的能力。2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homas McCarth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80, p.4.
显见,哈贝马斯并非不承认系统论对社会系统的一般性认知,但是对系统论所说的各子系统通过自洽逻辑维护自身边界的观点予以驳斥,因为这事实上造成强势的经济和政治系统对于文化系统的导控,生活世界的自身特性恰好可以纠正文化在经济和政治系统强力侵入下逐渐式微的趋势。哈贝马斯说:“我们也不能把生活世界的这些因素理解为相互构成周围环境的系统”3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5页。,生活世界本身并不是一个与其他系统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系统,它不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并列,当然自身也并不产生像货币与权力这样的调控媒介。换言之,生活世界并不在系统论所划分的经济、政治、文化这样一套系统之中进行自我表征,文化作为生活世界的一个结构要素并不是如系统论所界定的那样与其他系统具有清晰边界的子系统,毋宁说它只是统一在生活世界的背景下,并与系统的货币和权力共同维护整个社会的进化与发展。
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生活世界概念进行革新。生活世界并不是主体以自己的独白意识独断地构建起来的一种先验意识,而只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模式或者说一种存在方式。正是因为生活世界不同于意识哲学的解释范式,因而它才能超出系统论从而克服其缺点,因为生活世界本身乃是背景性的,不具有任何超然的地位。这个解释模式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转向,一方面它是在文化传承意义上来讲的,生活世界具有优先于系统的地位,“因为生活世界中文化传统的改变,因而系统只能是历史地出现的。”1John Sitton, Habermas and Contempora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03, p.62.而生活世界是以语言为基础获得其背景知识之地位的。2参见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Two: Lifes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ounctionalist Reason, p.124.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以语言中的沟通因素导致了相互理解作为人际关系调节的基本目标。而生活世界的背景知识之明确性、总体化力量以及其整体性则构成了其作为以语言为基础的理解的基本背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便使得文化与语言之间产生了直接的关联关系,“语言与文化,既不与参与者在交往过程中对它们的境况进行界定的形式的世界概念相一致,它们也不表现为某种归属于内部世界的东西。语言与文化对生活世界来讲是建构性的。”3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Two: Lifes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ounctionalist Reason, p.124.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与文化具有直接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并不建立在两者共同归属于外部世界、社会世界抑或内部世界,而是因为两者都源于深层次的生活世界,语言与文化一方面建构起了生活世界,一方面当行动者用语言对世界中的某种物进行言说时其又必然与生活世界的背景知识相一致。生活世界在概念设定上经过主体间性的对话式转换已经把语言与文化勾连在一起,这个概念由此隐含地肯定了整个社会中文化系统的重要作用。这是问题得以推进的一个基础性步骤,要想深入分析基于生活世界理念的社会认知模式在何种意义上维护了文化的独特地位,就需要对生活世界的形式构成进行剖析。
三、生活世界的形式构成
如前所论,历史性的、背景性的、未产生经验分化的生活世界具有一种奠基于语言沟通模式之前反思层面的结构,这个结构也就是生活世界的形式构成。既然如此,那么生活世界就像语言沟通模式的形式要求一样,在其内部秉持的是沟通意图下的共识这一基本原则。延续这个思想,哈贝马斯在其经典之作《交往行动理论》中遵循帕森斯(T. Parsons)已得到公认的三分法,他认为生活世界乃是一个现象学的而非实体化的世界,因而其构成并非系统论式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只是一种现象学层面的形式结构。这种形式结构包括三个形式化要素:文化、社会与个性(personality)。4参见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Two: Lifes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ounctionalist Reason, p.134.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对之做出了更为明确的界定,他说:“文化知识表现为符号形式,表现为使用对象和技术,语词和理论,书籍和文献,当然还有行为。社会表现为制度秩序、法律规范以及错综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实践和应用。个性结构则完全表现为人的组织基础。”(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就文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来说,文化首先是一个知识的储存库,“这个知识储存库为社会成员提供没有问题的、一般的背景信念”。5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Two: Lifes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ounctionalist Reason, p.124.这即是说,文化作为知识储存库在一般意义上构成了处于该文化语境下的行动者先行承受的传统。换言之,文化体现在占有文化的人对于传统的继承上,任何参与交往的行动者在进行交往之初便已经在这些伽达默尔所说的“前见”的基础上提出其有效性要求,这些“前见”作为一般性的背景信念在具有共同语言、共同风俗习惯和共同文化传统的人看来乃是不成问题的,至少在没有新的经验产生前不会经受理性拷问。当然问题还有相反的一面,即这些被传统所固定的背景知识具有某种悖论性质:一方面,它在某些方面是固定不变的,与生活世界的形式特征密切吻合;另一方面,这些至少在近代科学主义视域下不成其为知识的知识又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一点又与生活世界的历史性相吻合。而后者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再生产问题。正是通过生活世界的形式结构之分析,文化分别与社会和个性这两个形式要素间产生相互影响,从而使文化能够在历史性的生活世界背景之下得到保存和更新。文化与社会、个性的相互关系,可作如下两方面分析:
首先,就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来说。社会的各项制度包括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伦理规范等都是与文化传统一道形成的,两者具有相互渗透的交互关系。文化的归属感无疑在同种语言中更易确立,但是经过历史流传而得到固定的文化模式,往往会超越语言共同体的狭义语义学限制。对此,哈贝马斯曾说:“文化传统超越了集体和语言共同体的界限,只要存在,它们就不会受到社会认同或个人认同的约束。”1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4页。正是文化具有的这种跨越时空的关系,才使得文化知识作为知识的储存库能够被具有认识能力和行动能力的参与者所认同。文化超越了某个共同体的狭隘视域而得到传承与更新,文化更新并建立新的认同的过程为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也为具有这种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确立集体认同的基础。所以说,作为生活世界形式结构的文化和社会本来就是两个互相促进的因素,文化的超时空性质使它一方面必须承受社会的检验,一方面经过检验的文化又能够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就文化与个性的关系来说。文化与个性结构的形成同样具有直接的关系。就逻辑上来说,在讨论文化与个性的相互关系前,需先行讨论社会与个性的关系。对此哈贝马斯接受被普遍接受的社会先行于个性的观点,“自我的同一性只能在一个群体的占统治地位的同一性中形成。”2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8页。通过与他者的协调从而形成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同一性,浸淫于文化中的个体因为文化的先行承受关系而形成自身的个性也即个体同一性。在此过程中,个体要接受文化传统的教化,并在自己与文化的接触中更新文化的内容和维度,如哈贝马斯所睿智地指出的,“文化传统的内涵永远都是个人潜在的知识;如果不是个人从解释学的角度占有和继承了文化知识,也就不会有什么传统可言,即使有了传统,也无法流传下来。”3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6页。个体处在一种诠释学语境之中为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不是个人单独享有的一种资源,因而不是个体作为主体承当文化传统,而是文化传统通过主体更新自身。每一个文化传统都是文化对个体的教化过程,但与这种诠释学的教化观念一样,它并非对主体天生具有的自然天赋的开发,而是具有典型的走出自身又回到自身从而获得新的内容的辩证过程。1哈贝马斯在此无疑受到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深刻影响,按照诠释学的观念,教化并非对自身天赋能力或素质的开发或提升,而是与社会政治意义具有深刻关联,对此伽达默尔曾说:“在教化中,某人于此并通过此而得到教化的东西,完全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2页。)具体到文化上,不难推知哈贝马斯是将文化视为一种重要的因教化而获得的东西,个人通过文化的教化使自身成为有文化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文化的教化所导向的个性结构乃是一个不断更新但无终点的提升过程。所以说,在个性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在个体不断的学习进程中,这种文化观念不断地深入到个体的人格结构中,并成为个体在社会中进行自我确认的一种能力。
生活世界的三个结构要素具有相互间的输入和输出关系,但并非系统论意义上的外部关系,而是诠释学意义上的辩证关系。正是基于生活世界中三个要素的辩证关系,生活世界才建构起以行动者的互动为中心的一个具有弹性范围的背景性共识。哈贝马斯以一种抽象的哲学思考批判了社会理解的工具论导向所导致的文化强制,并意图通过交往理性的批判意识使被扭曲的文化交往回到交往的本真状态。文化作为生活世界中的一个知识系统,它包含背景知识,同时也包含对有效性要求有所承诺的主题化知识,这些知识不仅能够构成交往参与者的行动资源,也构成了其对文化进行更新与再生产的契机。当然,如果要重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所揭橥的因工具理性之强势所导致的价值与意义之丧失,则要进一层考察作为符号的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批判性。
四、文化之批判性的根源和指向
依韦伯之见,西方在其独特的文化模式之下诞生出了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但西方近代以来的合理化路向则并不在于自古希腊以降的理性主义哲学思考,也不在于数学、经验科学、技术以及艺术的合理化过程,真正的根源是新教徒的自我约束精神,藉此,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下进入工具理性的合理化路向。韦伯的这个答案无疑将现代化进程置放到了意识结构层面上。虽说韦伯并非没有注意到社会合理化与文化合理化的不同指向,也确实意识到社会合理化过程与文化以及意识结构之间的关系。但是,韦伯仍然将文化合理化的进程之核心环节归结到“现代科学、后传统主义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以及自主的艺术”2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one: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p.178.这些层面上,而这其中最为核心、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特质的当属以现代科学进行表征的所谓工具目的之合理化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关于西方理性主义的普遍化过程中阐释出的普遍主义的工具理性结构存在着模糊性质,“韦伯一直在寻找一个参照点,通过它,韦伯把充满矛盾的社会合理化过程相对化为文化发展的特殊过程。”1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one: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p.179.哈贝马斯并不认同韦伯这种带有相对主义倾向的普遍主义表述。事实上,韦伯在这里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即他把目的合理性的控制理念作为西方理性传统的独有特色而带有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特色。现代化的特征根本不在于以某种特有文化所抽绎出的抽象原则去普遍化其他文化,因为“生活形式的多样性仅限于文化内容,并同时指出,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意识自觉’或‘抽象’程度,势必会共享世界的现代理解中的某些形式属性。”2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one: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p.180.普遍主义路向根本的目的是要揭示现代文化的一些普遍主义的形式特征,而不是以偏狭的中心为基点的文化内容的普遍扩充,因为即使“每一代人在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感知方式上都通过文化而与过去每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3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页。这也并不代表西方文化自身不需要经由哲学的反思和批判。
文化虽然是一个与真理、规范以及价值相关的传统因素,但是在哈贝马斯马斯看来,文化必须是沿着韦伯的合理化命题而能够得到独立的理性评价的,特别是其中的规范与价值因素。当然,就像其一直批判韦伯的文化合理化模式之工具向度一样,哈贝马斯同样认为文化虽然是一个理性的知识系统,但是其理性化方式却不是工具理性的而是交往理性的。在交往理性模式下理解的文化首先是一个抽象的、形式化的、具有特定意义结构的符号系统,以符号形式得到传承的文化本身具有解放的力量并负有批判责任。伴随着社会的“祛魅化”过程的必然是另一种声音的出现,即文化的整合性作用本身因为文化的分化而越来越增加了动力减弱的风险,如其所言:“在规范意义上具有重要作用的文化进程不断地暴露到崩塌的危险中。”4Habermas, The Liberating Power of Symbols: Philosophical Essays, trans., Peter Dew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25.这种现象恰如有学者所评价的一样,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个“文化区分化与符号差异化”5高宣扬:《文化区分化与符号差异化》,孙周兴编:《交互文化沟通与文化批评》,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的过程。笼统地说,现代社会的文化确实表现出各种差异,这种差异以符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文化的差异化绝不意味着评价体系的多元性以及相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通过符号论得到表达的人类文化在其合理性过程中依然能够找到其统一的、形式化的以及客观化的有效性要求作为自我规范的标准。
哈贝马斯在此无疑接受了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er)的文化符号论思想。在卡西尔看来,虽然人类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创建出了辉煌的、多样性的人类文化,但是究其根源,所有文化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文化本质上来说乃是人面向世界的符号,“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页。通过文化符号,人与人建立起基本的规范和价值认同,在符号化的文化中充斥着各种与人的精神具有直接关系的创造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与自然界发生关联的一切领域,不管它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都可以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部分。哈贝马斯放弃了卡西尔文化内涵中的非理性因素,认为符号化的文化形式内部保存的是一个理性的知识系统,这个系统完整性与解释力表现为知识不断完善的过程,因而不仅是科学技术领域,而且是道德与审美领域都走向了自己各自的合理化过程。与文化的差异化伴随着的是知识的不断分化,“世界观的合理化导致了文化的认知(cognitive)因素、评估(evaluative)因素和表现(expressive)因素相互之间的分化,因此带来了一种现代的世界理解。”2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one: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p.176.哈贝马斯进一步认为,合理化的过程提高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它不仅包括文化传统所具有的(严格意义上的)认知内容,而且包括了社会整合内容。它囊括了有关外在自然的经验—理论知识,社会成员的道德—实践知识以及个人关于他们自己的主体性或内在自然的审美—表现知识。”3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one: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p.177.由此可见,在哈贝马斯看来,作为知识储存库的文化其知识表现形式在三个向度上展开,分别是:关于外部世界的自然知识、关于道德实践的规范知识、关于内在自我的审美知识。实际上,在将生活世界的背景共识逐渐主题化过程中,文化使自身成为一个理性的知识网络,而文化之所以能够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发挥批判作用,究其原因,还是它本身的知识属性。
文化是共同体在有限的历史时间中理性构建起来的知识系统,它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承受文化的此在自我确认的传统,因而也是一种重要的交往资源。但是,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这是秉持启蒙意识的哈贝马斯的一个基本信条。文化本身内蕴反思批判性质。知识的一个基本特征乃在于它的可错性,而作为生活世界之背景知识的知识形式“根本不代表严格意义上的知识”4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p.22.。尚处于背景状态的生活世界知识根本不具有可错与不可错的区别,只有当生活世界的背景资源被行动者用来实际地维护人际关系以达成理解时才会转变为具有可错性的知识。哈贝马斯认为,“在某一特定点上,我们能够达到一种易错的知识的那些事物的领域,通过其绝对的必然性和直观的存在而从弥散的生活世界背景中分离出来。”5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Christian Lenhardt and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5, p.138.这些背景性的知识当用来表达不同世界形式内的事物时,就会在各自领域内表现出合理化的不同形式并因之发挥其批判和反思的矫正功能。
综上所论,哈贝马斯以韦伯的文化合理化命题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个问题意识展开文化批判性的理解。哈贝马斯秉持的基本逻辑是用规范性概念来重建文化的反思基础。但哈贝马斯于此并未采取意识哲学的先验路向,而是既尊重文化的经验特征,又不放弃先验论证的论证效力,以保证文化不被抽象化理解为空洞无物的纯形式。1哈贝马斯曾借助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经验考察论证其道德发展理论,其所采用的方式,笔者曾将其界定为“先验论证与经验确证”结合的方式(陈太明:《道德普遍性的先验论证与经验确证——哈贝马斯的一个独特视角》,《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按照科尔伯格,儿童道德发展先后经历三个层次,分别是“前习俗层次”(preconventional level)、“习俗层次”(conventional level)、“后习俗层次”(postconventional level)。对应于这三个道德意识层次上的行动者的行动动机被哈贝马斯分别表述为“普遍的兴趣和无兴趣”、“用文化来解释的需求”、“竞争性的要求解释”。(L.科尔伯格:《道德发展心理学——道德阶段的本质与确证》,郭本禹、何谨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176页。亦可参见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pp.123-125. )其中特别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与“习俗层次”相对应的动机——“用文化来解释的需求”。道德意识结构的发展在道德发展心理学下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不断趋向脱离内容的道德原则之过程。哈贝马斯用文化对应充满内容的习俗,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作为规范的文化需接受作为原则的道德之批判与反思。因而,文化虽然是一个相对来说已经定型的知识系统,但是其本身却是需要进行批判反思的,而且建基于人的认识的符号化本性之上的文化自身亦具有这种潜在的反思能力。所以,在哈贝马斯的文化理论中,文化的批判维度实际上具有双重指向。当处于同一文化谱系之下的得到该文化教化的行动者基于调节相互之间行为期待的道德需要时,那些传统的、造就了个性系统的文化就需要不断地被纳入批判意识的审查之中。另一方面,当文化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时,它并非被动地受经济和政治系统的单向导控,而是以自身的批判反思规范货币和权力从而决定了整个社会整合所具有的规范性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