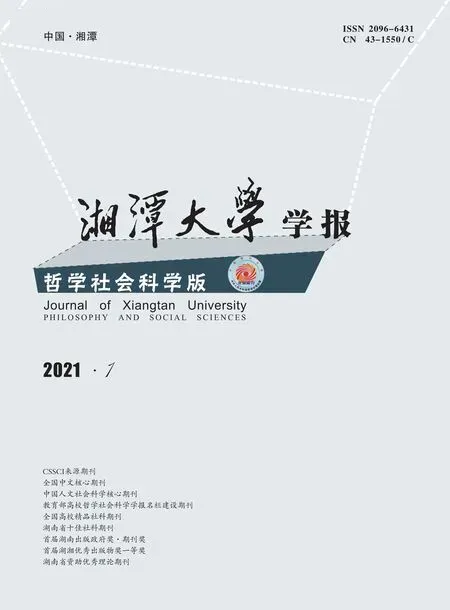理性认识美国外交转型与中美战略竞争*
温 娟,李海东
(1.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2.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 100037)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教育等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领域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全球地位,成为“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1]21。维持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首要地位,成为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谋求的全球战略目标。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的结构性危机不断暴露,其国内两极分化、种族冲突和社会分裂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不断侵蚀着美国霸权的实力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快速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在代表未来技术前沿的5G领域,中国的快速发展对美国的技术优势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维持自身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主动调整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不断塑造中美战略竞争态势。
近年来,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展开讨论:一是从权力转移的角度出发,讨论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构建国际秩序的影响,(1)参见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14-25页;杨原:《大国政治的喜剧——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彼此结盟之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第38-68页;朱锋:《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2页。预测中美战略竞争是否会走向“新冷战”或者是掉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2)参见[美]格雷厄姆·艾莉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2;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Daniel J.Lynch,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istory: Reviews of New Books, November 2, 2019, pp.164-166; Biao Zhang,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December 28, 2019, Vol.24 (4), pp.707-708.二是从国际制度的角度出发,讨论中美两国如何构建“制度均势”,从而在经济和安全两个领域实现机制化的相互制衡,达到中美之间的“协调共治”;(3)参见李开盛:《中美战略竞争管控的制度主义分析》,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4期,1-20页;汪海宝、贺凯:《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3期,第56-81页。三是从双边关系的角度出发,反思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预测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探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与可操作化路径。(4)参见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凌胜利、郦莉:《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历程、经验与启示——兼论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12期,第11-13页;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3期,第7-20页;张杰:《中美战略竞争的新趋势、新格局与新型“竞合”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2期,第1-20页;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96-130页;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Graham Allison, “Cou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e Rivalry Parterner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7, 2019.本文尝试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视角,探寻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路径,进而分析全球化时代中美战略竞争不同于历史上大国竞争的性质,最后在此基础上预估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
一、美国外交转型催生中美战略竞争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大体上遵循以“接触战略”为主的原则,即希望通过与中国就一系列的议题进行“接触”,使中国逐步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美国试图通过由其自身所主导的自由霸权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和制度,在经济上引导中国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政治上迫使中国转向西方的那套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从而把中国变成符合美国需要的国家。
然而,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持续分化,以及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国内从2015年开始进行了持续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对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接触战略”进行了反思,“美国决策精英正弱化以往对华接触与融合的政策基调,推动对华政策朝着挤撞方向发展”[2]9。“对华强硬”正逐渐成为美国新的战略共识,并不断塑造着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中美战略竞争态势。
(一)小布什政府与中美竞争性因素的缘起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其自身实力和价值观的普适性愈加自信。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把“扩展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在经历过一系列波折和起伏之后,中美关系在克林顿政府后期转向“建设性接触”,双方在1997年达成共同致力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3]307。但是,代表共和党保守派势力的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立刻抛弃了克林顿政府对中国“战略伙伴”的定位,转而把中国界定为“竞争者”和“地区性的潜在对手”。[4]
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突发,使得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遭遇双重挑战——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以“他者”的崛起而可能引发的权力转移为特征的传统安全威胁。其中,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本土安全构成了更为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因而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敌人,据此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反恐。随后小布什政府发起了以反恐为目的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然而,两场反恐战争不仅没能有效地根除恐怖主义的威胁,反而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沼。恐怖主义不仅消耗了美国大量的战略资源,成为侵蚀美国全球霸权的主要威胁,而且对美国全球首屈一指的军事能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为了寻求在反恐问题上的国际支持,小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淡化了对大国竞争的关注,转而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加务实的合作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重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实际上,在小布什政府的安全视域中,中国具有显著的两面性:既是一个需要严密提防的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手,又是一个需要在某些地区安全事务上与之合作的伙伴。”[5]154
由此可见,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战略虽然以反恐为中心,但也开始了对中美潜在的战略竞争关系的界定。在此阶段,美国尤其警惕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小布什政府在2006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是主要新兴大国中最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6]29
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同时安抚其他国家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忧,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主张,试图寻找到现代大国不与国际秩序主导国发生军事冲突而实现崛起的途径。2005年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中国知名政策人士郑必坚的一篇文章,文章写道“中国已经采取了超越大国崛起传统道路的战略……中国不走‘一战’时的德国和‘二战’时的德国、日本依靠暴力掠夺资源、争夺霸权的老路。中国也不会走冷战中大国争夺主导权的道路”。[7]22美国要求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遵守国际规范,承担与中国实力相适应的更多责任。
总之,小布什政府时期,虽然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但美国已经开始关注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了。中国主动采取了积极的建设性姿态,使双方能够有效地管控分歧,更多地聚焦于务实合作。
(二)奥巴马政府与中美竞争关系的形成
小布什政府后期,各种意外事件接踵而至,历史潮流进一步发生改变。2008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席卷美国,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久拖未决,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并成功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这些事件让美国精英开始重新思考美国对华战略的得失。但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初期展现出比较务实的对华合作姿态,把中美关系界定为“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8]12,在地区热点问题上愿意寻求与中国务实合作。
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开始重新调整其对外战略,强化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态势。一方面,奥巴马政府试图改变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安全与外交战略均被反恐战争主导的不利局面。奥巴马试图“使反恐政策成为美国安全与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进而将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应对经济危机,防范新兴大国崛起等重建美国领导地位的全球战略之中,但又要收到可以彰显的反恐效果”。[9]1为了改变美国因反恐战争而持续遭受损害的国际形象,同时尽量减轻反恐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掣肘,重塑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美国于2011年6月出台了《国家反恐战略》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奥巴马政府试图“使反恐战争既不主导美国人民的生活,也不影响美国更广泛的利益”[10]。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奥巴马政府于2012年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意味着美国开始将战略重心由中东的反恐战争转向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奥巴马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把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与亚太盟国的军事合作,扩大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伙伴关系网,对中国形成更加有力的制衡”[11]16。另外,奥巴马政府还试图优化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发展“新军事”概念和以技术上的优势抵消数量上的不足为核心的“抵消战略”,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亚太安全网络,同时,让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减轻美国的战略负担。
事实上,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已经将中国界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增强。美国对中国的关注重点由小布什时期对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增长的关注,转变为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综合国力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对周边地区外交政策变化的关注。
为了更好地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抓住发展战略机遇期,中国将“和平崛起”改为更温和的“和平发展”。2010年12月,中国负责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了一篇题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声明,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是符合世界发展形势和中国国家利益的长久政策。[12]奥巴马政府在加大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同时,也强调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竞争不一定导致对抗,要管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避免恶性竞争。[13]
总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由初期的强调合作转变为关注竞争,中方也承认竞争的存在,但双方都致力于开展合作,管控分歧,促进良性竞争。因而,这一阶段的中美竞争关系仍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方位的、战略性的。
(三)特朗普政府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激化
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面临的来自恐怖主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峻。特朗普政府继续打击恐怖主义,但对美国反恐战略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收缩美国全球反恐战线,将反恐重心聚焦于美国本土,将打击对象聚焦于“伊斯兰国”和“基地”[14]52。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化了的恐怖分子网络及其追随者,二是受到一些国家支持和纵容的恐怖组织,三是受到恐怖分子宣传与蛊惑的国内极端暴力势力。特朗普政府把伊斯兰激进恐怖分子界定为美国及其核心国家利益面临的“最危险的跨国恐怖威胁”,在此基础上,于2018年10月4日批准了一项最新的国家反恐战略报告,对2011年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战略进行了一次升级。新战略意味着“美国在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上的一个转变”。特朗普在序言中表示“该战略确立了新的反恐路径”,“新的反恐战略概述了美国抗击愈发复杂和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的方式。这一反恐战略涉及追溯恐怖主义源头,切断恐怖分子资金来源并升级打击恐怖主义的工具。该战略还专注于保护美国基础设施,打击恐怖分子极端化和招募活动,并加强与国际伙伴的合作。”[15]
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从反恐领域完全转移到传统的大国权力竞争上面,使大国竞争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其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的主流看法。报告开门见山地指出,如今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大国竞争,美国在当今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分别是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和亚太地区的中国;从长远来看,中国又是对美国构成全面挑战的主要对手。报告全文提及中国的次数多达30多次,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和“竞争对手”,并在经贸关系、地区角色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大加指责。[16]在美国看来,与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所构成的安全威胁不同,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所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现行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美国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就是挑战美国的在当今世界的主导地位。[17]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美国又做出了区别,“除了中俄两国不同的地理位置构成不同的地缘政治挑战以外,来自中国的挑战更加具有长远性和全面竞争性”。[16]
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自2014年以来的首份《国防战略报告》,该报告涉及中国部分的表述在基调上与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基本一致[18],都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修正主义强权”并“寻求建立一个与其专制模式相符的世界”。这份报告代表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性转变,“其重点将是优先准备打仗,尤其是为大国战争做准备”。[19]
总之,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全球战略开始把来自中俄等大国竞争的挑战列为首要威胁,置于恐怖主义所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上;同时,还把中美经贸关系纳入了国家安全范畴。这表明美国对威胁的感知和判断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美国感到其长期拥有的不容置疑的全球主导地位开始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而挑战的实质在于中国不断提升的全球竞争力”[11]17。中美关系的基调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快速崛起的中国已经被界定为美国的首要威胁,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日益凸显并相互交织,推动中美战略竞争朝着日趋激化的方向发展。
二、理性认识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
“中美战略竞争是两国关系进入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也是当下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从历史的宏观视野观之,中美战略竞争的大幕刚刚升起,这一个过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但是,“中美竞争的本质不是安全之争,而是经济社会之争”[20]96-130,因而全球化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历史上大国竞争的新特质,主要体现为竞争的非对称性、非零和性、非对抗性。
(一)非对称性
中美战略竞争的“非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中美“实力对比”的非对称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战略“攻-防”态势的非对称性。
尽管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两国绝对实力差距仍将长期存在。美国面临的只是实力的相对衰弱,而不是绝对衰弱,美国自身的绝对实力仍然在不断增长,只是增长的速度没有中国那么快。有学者预测,“到2023年,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可能赶上美国,但美国仍可保持明显优于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中国仍然无法全面超越美国”[21]19。在体现大国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人才、教育等方面,中国与美国之间也将持续地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可以从本国14亿人口中挖掘最优秀的人才,而美国可以利用全球70多亿人口中最优秀的人才。中国在吸引国际人才和技术创新方面,与美国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中国最大的优势来源于持续稳定的国内政治局势和不断增长的总体经济实力,但国内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以科技和创新力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力仍有待提升。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在总体实力对比上的非对称性,意味着当两国把各自的主要战略力量用于重点领域的关键性竞争时,双方可利用的战略资源是不对称的。
此外,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仅取决于彼此的综合实力对比,还取决于双方在全球范围内可供利用的战略资源和战略动员能力。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无论在整体实力还是动员能力上,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相比,都占据明显优势。在没有实质性盟友的情况下,仅凭借自身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力,中国很难在短时期内扭转战略竞争上的被动态势。
总体来看,中国整体战略实力明显弱于美国,并且中美实力对比在短时期内难以发生质变,因而中美战略竞争不是同一量级的主体之间的竞争,而是非对称性的竞争。
(二)非零和性
中美战略竞争的“非零和性”是指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既不同于传统大国对领土、资源的掠夺性竞争,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势力范围争夺,而是在一个多层次、多问题领域相互关联的复杂的制度和规则网络之中,展开的一场以“规则制定权”为核心的影响力竞争。这是一种趋于“软化”的战略竞争,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制胜,而科技和制度创新力的竞争是非零和性质的竞争,完全可以通过协调与合作的和平方式,取得互利共赢的结果。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权力主要来源于对人口、领土和资源等生产资料的优势性占有。但是,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这些传统的生产资料在一定时期内的总量是基本固定的,也就是具有“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的零和性特征,因而,战争就成了获取领土、资源和财富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主要来源于对新技术的控制和垄断,大国竞争的方式已经由以战争为终极表现形式的“硬竞争”转化为以创新力为核心的科技和制度的“软竞争”[22]51。一方面,科技和制度的创新带来了全球财富总量的迅速提升,国家可以通过科技和制度创新更有效地增加自身财富;另一方面,通过科技和制度创新增加财富的方式,减少了对人口、领土和资源的依赖,从而缓解了国家间围绕土地和资源展开的零和性竞争。
一部分悲观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国家必然追求权力,因而大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中国的崛起必将威胁亚太邻邦与美国,美国最适合的政策就是尽早遏制中国”[23]104。还有学者以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来预言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未来走向,同时,把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德关系相类比,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将使全球力量平衡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进而不可避免地落入“修昔底德陷阱”[24]5-11。但是,“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比较本质上而言是不精确的,甚至最精确的类比也不意味着当代人一定会重复前人的错误……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一战’之前欧洲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激烈的公众舆论不允许妥协。中美关系却不是这样。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25]511
(三)非对抗性
中美战略竞争的“非对抗性”是指中美在客观上存在战略竞争的结构性压力,但目前两国之间的竞争还没有互相威胁到对方的生存安全,双方的战略竞争还在可协调的、非对抗性的范围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明确地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但其中也提到“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是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冲突与对抗”。[16]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也阐述道,“这不是一个对抗的战略,而是一个承认竞争现实的战略”。[26]
首先,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之间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深度交融,双方都能从对方的稳定与繁荣中受益,而相互对抗的成本在不断上升。诸如核扩散、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中美双方在维持双边关系和全球体系的整体和平与稳定上,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大国责任。其次,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使得大国之间冲突与对抗的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和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这就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完全可以是非对抗性的。最后,中美两国要维持自己的竞争力,都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增强自身凝聚力。“中国劳动力正在老化……西方正进入紧缩时期,形势远比以前复杂……一个面对如此庞大国内任务的国家不太可能轻易(更别说自动)投身于战略对抗或追求世界主导地位。”[25]513-521“现在所谓的中美竞争,实际上是两个大国重新整合内部的一个赛跑,谁能先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谁就能赢得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权,进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27]5
此外,中美战略竞争由美国主动挑起,“中国虽然无法阻止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意图,但是中国可以通过努力控制战略竞争的边界,积极塑造一种良性竞争的战略互动文化”[28]8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战略文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以强调斗争为核心的“冲突型战略文化”,转变为以合作为核心的“合作型战略文化”[29]355。尽管目前美国呈现的依然是“冲突型战略文化”[30]107,其国家安全战略带有明显针对中国的进攻性意味,中国也在努力寻求改善现有国际体系中不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看,中国始终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以渐进的形式不断融入美国主导下的现行国际体系,谋求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地位。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在寻求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三、合理预估中美战略竞争的趋势
中美战略竞争本质上是“实力占优”的守成大国,对“趋势占优”的崛起大国发起的预防性战略施压。中国迅速崛起,美国相对衰落,中美实力对比朝着利好中国的方向发展,是推动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层次结构性因素;美国国内政治的持续分化与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是加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催化剂;全球突发性危机性事件,是点燃美国“霸权焦虑”、激化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导火索。因而,中美战略竞争既受国际体系层面的结构性因素的驱动而呈现出持续性常态化趋势;也受国内政治层面和领导人个人层面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阶段性高强度趋势;还受突发性因素的刺激,而呈现出某些领域高危化趋势。
(一)经贸、人文和科技领域的“脱钩”可能趋于常态化
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对利益目标的争夺和权力关系的转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结构性的,也是战略性的,因而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竞争过程。“实力占优”的守成大国面对“趋势占优”的崛起大国时,很容易产生“霸权焦虑”心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霸权焦虑”会越来越严重,因而往往会对崛起大国采取持续的高强度战略施压,以求“速战速决”;而崛起大国往往希望把竞争的战线尽量拉长,以求用“趋势优势”来争取实力差距的缩小。但由于整体实力对比的差距依然存在,守成大国往往拥有更多的战略主动权,崛起大国往往陷入被动应对的境地。
中美战略竞争是由美国通过不断调整外交战略的方式而主动发起的,中国并不寻求挑战美国霸权地位和推翻现行国际秩序,而是致力进一步融入和改善现行国际秩序,营造保持经济繁荣稳定的内外环境和争取在世界事务中应得的尊重。但是,中国无法阻止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意图与决心,因此,由美国主导的中美双方在经贸、人文和科技领域的“脱钩”可能将趋于“常态化”,“脱钩”的范围和力度,可能会朝着美国主导的方向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过去几十年里,经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发挥着“压舱石”和“推进器”的关键作用,中美在经贸领域的高度“相互依存”状态奠定了双边关系合作与稳定的基础。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以强现实主义的竞争型理念取代了自由主义的合作型理念;以“美国优先”为第一原则,特别重视美国的经济利益,采取了经济民粹主义立场,强调所谓“公平贸易”和相对收益,注重贸易逆差问题,“使得经济竞争上升为中美战略竞争中基础性、根本性和关键性问题之一,其中高端制造业和自主创新能力体系成为现阶段中美经济竞争中最为突出的领域”。[31]1-22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美国对中国不断施压,主动挑起并不断激化中美贸易战。从目前美国的政策导向来看,经贸关系将从“压舱石”和“推进器”转变为中美两国矛盾和冲突的源头。[32]22短时间内,中美经贸关系的内在矛盾性很难改变,美国可能进一步主动追求在经贸领域与中国“脱钩”。
在技术创新领域,美国自19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的科技实力是美国繁荣和安全的保障,美国未来的经济机会和国家安全都取决于其持续的全球技术领先优势。但是,近年来中国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华为在引领未来技术前沿的5G领域,对美国的技术优势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不断加大对华为的打压,升级出口管制清单,阻止全世界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代工厂给华为提供芯片,力图彻底绞杀华为。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在人文交流和科技领域,美国可能在现行基础上进一步更新对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出口管制清单,几乎所有尖端科技都将包括在内;中国的科研人员和留学生将越来越难以参与美国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前沿项目。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美国也很可能对中国持续施压。
(二)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中美围绕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将日趋激烈。现行国际秩序是美国领导下的自由霸权秩序,美国强大的国家实力是秩序创建和维持稳定的基础;现行国际秩序所包含的一系列制度、规则、规范、习俗、惯例等无疑体现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偏好。国际秩序的竞争,本质上是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它依然离不开权力政治的逻辑。制度并非纯粹“中立性”的场所,它反映了特权,是权力竞争的场所。[33]11
中美在全球经济治理和网络安全领域的规则制定权之争,将会越来越激烈。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不断增大,中国要求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与自身实力和能力相符的投票权与发言权,并且要求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国际制度创制方面,为加强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中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中国的这些举措被美国解读为试图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去美国化”的平行秩序或替代秩序,推行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
在网络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也将日趋激烈。美国及其盟友力图利用其传统军事优势,推动网络空间不可逆转的军事化,将《武装冲突法》引入网络空间,把传统战争和网络战争挂钩,认为“动网”即“动武”。中国和新兴国家则谴责传统军事强国推动网络空间军事化的行为,希望在“动网”和“动武”之间建立缓冲隔离带,以区别网络攻击和传统战争。美国是互联网的缔造者,凭借其领先的信息技术优势,在网络安全国际规则的塑造中掌握了主动权。中国在互联网发展中属于后来的新兴国家,与美国还有较大的实力差距。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的一些核心议题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34]25-54。“由于网络安全要素渗透性强、敏感度高,与中美贸易冲突其它要素相互交织叠加,进一步推升了贸易冲突的紧张程度。”[35]149
另外,在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时,中美围绕抗击疫情问题的认识和应对办法,出现了严重分歧,在国际舆论上针锋相对。在面临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时,中美在国内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规则方面的分歧不仅没有弥合,反而进一步加剧。未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领域的竞争与矛盾将更加激烈。
(三)军事安全领域突发高危事件的可能性增大
近年来,中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崛起被美国视为对其全球海洋霸权的挑战。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周边安全与稳定,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同时加快了军事现代化和信息化步伐。但是,在美国看来,中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在近海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策略和在远洋的军事活动给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带来全面而严峻的挑战。美国认为,中国海军在局部海洋正逐渐有能力和美国争夺制海权,因而,美国开始重新强调大国对海洋控制权的竞争。特朗普政府反复强调要加强美国军事能力建设,尤其是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这无疑将增加中美在海上安全方面的竞争压力。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口头上坚称对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海洋主权与权益争端不持立场,表面上关注所谓“自由航行”和地区秩序问题,实质上最关心的还是其海上主导地位,并对中美日益缩小的能力差距感到焦虑。[36]15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变得越来越具有挑衅性和威胁性,同时还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不断进行军事施压。2017年2月,美军“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巡逻;2018年5月,美军派两艘驱逐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此外,美国在拒绝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同时,鼓动澳大利亚在南海执行定期的“自由航行”,煽动英、法等国派舰进入南海巡弋,定期和日本举行海上军演,竭力营造多国海军力量介入和干预南海局势的事实,企图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孤立中国。“美国及其盟国的强势干预,客观上成为南海紧张态势难以缓和的根源。”[37]17
从战术上来看,美国尤其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以取得战术优势。2019年5月,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了一场以“未来战争:通过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实现战术优势”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认为“现代战争日益以数据为中心,国防部需要采取措施整合云技术,通过优化云技术和人工智能,在未来战争中获得战术优势”。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威廉·施耐德指出,“5G构成的威胁远超预期。中国的5G概念可以通过与百度系统的耦合,进而集成精确导航和瞄准功能”[38]。
总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持续衰败外溢到国际政治领域,美国很可能在经贸、人文、科技、军事安全和国际制度等领域,对中国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强硬举措,激化中美战略竞争,中国将面临美国持续的高强度的战略施压。对此,中国一方面要有足够充分的心理准备,保持足够的战略忍耐与克制,努力寻求良性竞争与协调共存;另一方面要针对可能发生高危冲突的领域,提前制定应对突发性危机的预案,尤其是在台海和南海等触及底线的问题上,中国要有坚决反击的意志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