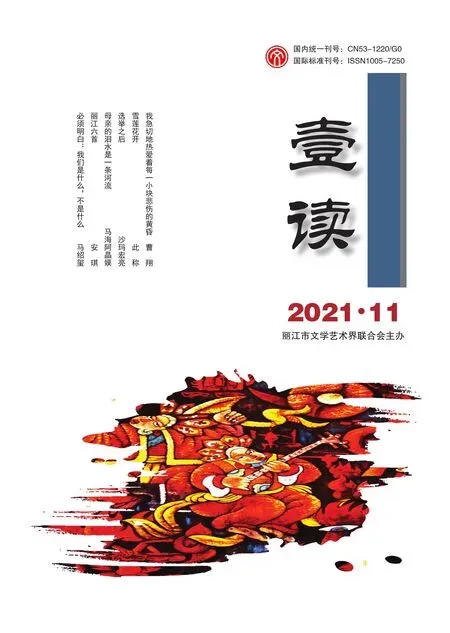丽江记忆
◆王丽
想起丽江古城,无端地,便感觉坠入了深潭——诗的深潭。绝对的山水诗。因意境深远,总难以自拔。
无论远观、近看,相隔千山万水或近在咫尺,其古韵清雅总是无遮无拦,扑面而来。那样的美,因时光打磨而旷远厚重,经岁月浸泡而延展通透。虽静默无语,却传递着可意会而难言传的诗情与画意。
散落的竹简、断弦的古琴、模糊的行书似乎都不足以让诗的意境留存,让城的灵魂依托。
最佳的载体非青花瓷莫属,却因青花易碎而不宜靠近,多了份距离;典雅高贵却不够温润,总少着点妥帖。
不知不觉中,便成就了一座城,一幅山水图。
一轴画卷,轻轻展开,徐徐滚动,一端便稳当地停伫于宋、元的古朴街衢;另一端却被时间的轴挟裹着一路向前,停不下,止不住;通向遥远,却总有留白。
一幅落于凡间的水墨丹青,沾了烟火,接着地气。因豁达而从容,因自由而不羁。因接纳而宽厚,因明彻而宠辱不惊。
无论平民百姓或达官贵胄,不分地域、民族,不看肤色;无论短暂歇息或长久相守;只要走过,遇见,留在画中;那一笔,或轻或重、或浓或淡、或直接或婉转,都成了不可缺。
行走于画卷,走出,走进;听故事,成了故事。
徜徉于山水,来来,去去;赏着景,成了景。
想起丽江古城,便想起:
四合院斑驳的墙上露着的土坯;沧桑的青瓦上住着的,喜欢在风中窃窃私语的枯草和小黄花;阁楼雕窗上弹指即破的棉纸;大门上谜一般的黄铜挂锁。
河边垂柳处。三五只鸭,随淙淙流水,顺河中水草,游向石桥,穿过木桥;不屑于身旁飘过的菜叶,一头扎进水底,追逐着鱼虾而去。至岸边,未抖净身上水珠,便被木锤声和溅起的水花惊走。
古城的路,四通八达。早起的商贩们为多挣些钱,天蒙蒙亮就推车、挑担涌进四方街。
五一街的十字路口是个砍价的好地方,有经验的纳西大妈们总能拦下来自龙山、南山的柴火、栗碳或是洋芋和土鸡。雨季时,还能买到五角钱一串的松茸、鸡枞。
卖完山货的人,手里数着毛票,便奔四方街而去。
男人们多聚集至大石桥边的茶馆里,茶馆外支着的铁壶一直添着柴,冒着烟,准备着为茶客们续水。
茶馆对面的汤圆店热气腾腾,糯米团子在锅中翻滚,膨胀。盛进碗里加入米酒,用勺轻轻一扒便漏出花生、芝麻馅儿,让人甜到心头。
上了大石桥,看桥头坐着的汉子手中架的鹰,眼神犀利、傲气,藐视众生;看负重的骡马小心翼翼地踏过青石板,最终却滑倒撒落一地货的狼狈;看人群里挤出挤进的竹筐中的小猪崽、鸡鸭和菜……
石桥向下至四方街的凉粉店藏于闹市中,是个歇脚的好去处。滑爽而有韧性的鸡豆凉粉在平底锅中煎黄,撒上火麻子盐、韭菜和绿豆芽,用小木勺浇上土罐里的油辣椒、姜蒜水和醋、酱油,一碗香辣诱人的热凉粉便要游走于舌尖了。最简单过瘾的就是一大片凉粉摊在手,抹上辣椒和盐,边走边吃。
四方街集市,人声鼎沸,简易的摊子排满了街,来自乡下或山里的货总是炙手可热,供不应求。
寻常小菜则干干净净,清爽诱人。
青绿的棕叶撕成宽窄不一的细条,简单的在菜上一绕,打上结,一把把水灵灵、绿油油的小白菜或小香葱便有模有样,惹人怜爱起来。
猪肉,甚至是鱼均成了棕叶的俘虏:一块被拴着的肉,一条被穿过唇的鱼,被人拎着穿梭于人群,游走于集市。木桶中泡着的豆腐则幸运许多,最后要躺在小竹筲箕里,成了饭桌上的“丽江煮豆腐”。
集市慢慢散去,街便清静下来。露出了理发店、新华书店和牛肉馆。
不大的书店总散发着新书特有的墨香,柜台上的小人书和春节前挂满墙的年画都是孩子和大人们的最爱。
挨近狮子山的牛肉馆里,长条凳已挤满了人,四方桌上的一盅酒,一碟凉片,外加些白水煮蛋、几碗面,能够让卖了好价钱的商贩们痛快地吃上一顿。酒肉的香气随风而散,飘满整条街。
不知不觉,夕阳西下,抬眼望去,已是一城金色,一城炊烟。
想起丽江,便想起郁郁古风中,有趣的城。
神秘的语言充斥着各个角落,所有交流均在奇特的词汇、音调里完成:熟人问候、小城轶事、讨价还价……听懂的便心领神会,不明白的则云里雾里,如解天书。
关于文字的解读,听过的最有趣的说法是:
因木氏土司的睿智和眼界(或许也仅只是因避讳),让丽江古城没有城墙。一个“困”字,意味深长。
和姓家族,是木老爷的长工,须辛勤劳作。所以“和”字拆解开,“木”上“一撇”代表毡帽,“口”字代表一背筐,形象而生动,身份一目了然。其他姓氏则散落于古城街巷,久居一处,彼此间不免盘根错节,沾亲带故,所有的渊源,皆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缘分。
曾有人戏谑:在丽江,男人负责琴棋书画,女人负责柴米油盐。如古城那些黎明即起,做豆腐、擀面条、搅凉粉、卖早点……辛苦忙碌的女人们和那些放鹰打猎、养花钓鱼、弹琴写诗的悠闲惬意的男人们。
也有人言:田间地头,皮毛店、缝纫社、铁匠铺不乏技艺精湛的男人们,都能养家糊口,闲暇时赏兰花、演古乐、读书写字,极尽风雅之事,是身后女人们的付出与成全。是披星戴月的柔弱肩头背起了生活的琐碎,日子从来就是这样,由古至今。
无论何种说法,均不妨碍丽江人的生活,该怎样过还是怎样过。
而记忆深处却总是那些:冬天河边洗菜的女人;黄昏时背着高过头的松毛下山的女人;背着大木桶、系着皮围裙、杀猪的女人。
有趣的城,自然也是特别有“仪式感”的城。
逢年过节祭祀时,供奉着对天地神灵的恭敬和虔诚及对祖辈的缅怀和敬意。
小孩满月,用红纸和毛笔郑重地写上吉言和“祖父赐名曰……”寄托着对新生命的期望和祝福。
春节时,四合院落里树枝上缠着的红纸和花盆上贴的“春”字,拴住了春天,也留下了春意。
甚至于中秋节前就开始准备的月饼——烤黄饼,也是充满了趣味。
碳火、猪油,豆沙、玫瑰酱一应俱全,等着主妇们大显身手。诙谐的人忙里偷闲也不忘调侃舍不得往面里多搁油的人:得多放些油呀!不然那饼会硬得从狮子山滚到四方街都不会碎。
想起丽江,便想起:
邻家大院——茶马古道上马帮歇脚的驿站,墙角破旧的马鞍、生锈的掌钉、废弃的油灯、历经百年的石臼。
裁缝铺里,祖父手中那常常行走于布匹上的滑石、剪刀;那随时需加碳倒灰的铁熨斗和那只尘封多年的豆青色的扁扁的鼻烟壶。
古城清冷的月光下,祖母的七星羊皮披肩里传递着的温暖和坠在耳上的碧绿的玉片泛着的温润的光。
街头偶遇的老先生,庄重、小心地抱着古琴缓缓离去的背影。
四合院高高的门槛上,静静坐着的纳西老奶奶手里拾掇着的小黄韭。
曾有人说,时间是一条直线,所有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均无法参与、重叠和预知;而在丽江古城,时间或许是个圆,走进伫立了近千年的城,总会让人迷失。
行走在古城,有人说,找到了家园;也有人说,失去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