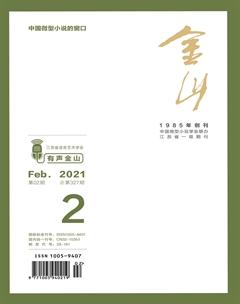二斤炒糖
马绍军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说的这佳节,并非重阳,而是春节。
春节后,元宵节前,是人们走亲访友的日子。上世纪六十年代走亲访友所携带的伴手礼,大多以点心为主。点心中又以炒糖、蜜三刀、开酥、羊角蜜为主,不像现在品种繁多,烟、酒、米、油……拿什么的都有。这只能说明,过去物资匮乏,生活艰辛。
带上二斤炒糖,走亲访友,很是寻常。炒糖大多都是用纸盒子封装的。装好盒,称好重量(每盒约1斤),在包制过程中,要在包装纸上面再放上一张宽约2公分,长约8-9公分的红纸,既美观漂亮,又寓意幸福吉祥。炒糖则经油炸、拌糖即成。装入盒中外面又加了层外包装纸,炒糖中的油还是会渗出外包装盒和外包装纸上,那层油光光的纸,让人禁不住垂涎欲滴,還令满屋飘香。碰上有些“要面子”的亲戚,自然得多备些礼,这也是人之常情。已经结了婚的小俩口,甚至还有些带着孩子一同去拜年,少说得备上8至12斤炒糖,再买些“礼肉”,这样才足够光鲜。在农村,回娘家拜年定会引来看热闹的人,借故看看新客拿了多少礼。临走前,姑娘、姑爷带来的礼品要回一半,外婆、外公还要给大人、孩子压岁钱。有些讲究的人家还要找上几个在村子里有头有脸、能说会道的人来家里,陪着姑爷一道说话、喝酒。
炒糖的形状,多以圆柱、方柱为主。其实,炒糖也是分三六九等的。用牙一咬,酥而蜜甜的是一等,价格也自然昂贵些;用牙一咬,微酥,稍微带点劲,不是蜜甜而是糖甜的算是二等,我总觉得这类炒糖极像是一名刚柔并济的铁血汉子;而那些用牙一咬,不仅咬不动,甚至连甜味也很寡淡的,则为三等,民间戏称这种炒糖为“跺脚咬”,价格也相对低廉。
二斤炒糖,礼尚往来。联结起了两个家庭之间的情谊,是古往今来恪守的传统礼仪,意义深远。一来彰显了孝道,体现了小辈对长辈人的爱戴;二来是适逢春节,以此探望一番历经了整个冬季的长者们,身体是否安然无恙。拜完年后,长者张罗着小辈们留下来共进午餐是很正常的。那时,要置办一些肉类得去较远的集市,很是不便。因为那时交通工具甚少,赶路全凭脚力,路况也不佳,道路大多坑坑洼洼,崎岖不平。但为了招待好前来拜年的亲友,主人早有准备,节前便早早去集市买了肉,煮熟,再码上盐腌入坛中,等着春节招待亲朋好友时取出。吃过饭,临了,主人还要把客人送来的二斤炒糖还回去一斤,这些事情大多由男孩子来完成,这都是礼数。另外,压岁钱也是少不了的。二分、五分、一毛……都可以,不像如今这般出手阔绰,甚至有的小孩过完春节就直接成了“万元户”。那时,多数家庭都有兄弟姊妹几个,各自在家里都有约定俗成的分工。一般父亲主外负责养家赚钱,母亲主内负责家务,几世同堂,尽显和乐。
二斤炒糖,礼轻情义重。在那日子清贫的年代里,亲戚朋友间那浓得化不开似炒糖一般的情感,是无法用物质来衡量的,那是赴汤蹈火,甚至用生命来维系的。不像现在,物质条件虽然好了,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似乎淡漠了许多。
二斤炒糖,走亲访友,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与回忆。现在想来,依然有种记忆犹新的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