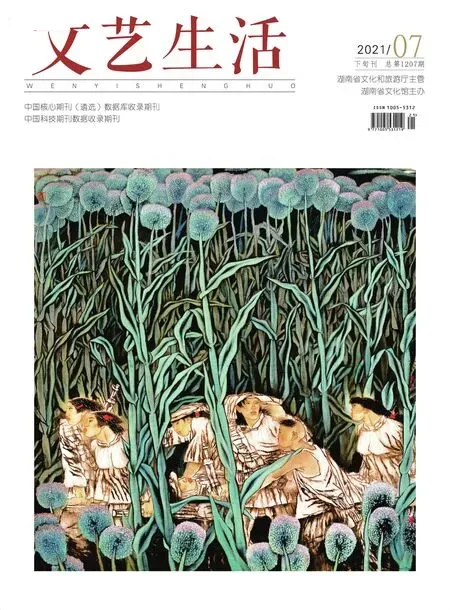俄罗斯17世纪巴洛克式文风浅析
王彬羽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一、前言
巴洛克式艺术起源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欧洲,是介于文艺复兴之后和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兴起之前的一种过渡性艺术形式,其表现形式及手法极为复杂多样,很难对其文学和艺术风格做出准确的界定。巴洛克式文学则是在文艺复兴的结束后,兴起于16世纪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随着彼得大帝的改革,这种纷繁复杂的艺术在17世纪中后期传入俄罗斯。美国比较文学之父雷纳·韦勒克在其著作《批评的诸种概念》中对欧洲各国巴洛克文学表现形式及影响进行梳理和研究后指出,巴洛克文学最重要的体现特征就是修辞手段,而这种修辞手段却又有可能适用于任何阶段和时期,[1]这可以看出对巴洛克文学做出准确的界定是十分困难的。德米特里·利哈乔夫也在其著作《思考俄罗斯》中多次强调,对于17世纪俄罗斯的巴洛克风格而言,重要的既不是对西方学者更为关注的艺术形式和修辞手段特点的分析研究,也不是对艺术派别和艺术类型归类掌握,而是这种艺术形式在俄罗斯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其对俄罗斯文学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影响。
二、巴洛克风格在俄罗斯的产生及其特点
利哈乔夫在《俄罗斯巴洛克风格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列举了三位对俄罗斯巴洛克文学风格研究的最为深入的专家。他指出,第一个谈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俄罗斯文学中的巴洛克现象的是俄罗斯著名的文学史家、哲学家列夫·蓬皮扬斯基,他在其《特列季阿科夫斯基与德国理性学派》一文中针对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某种现象首次使用“巴洛克”式这一术语,并进一步明确了与这种所谓的德国巴洛克式风格——西里西亚第二学派的关系;[2]此外,苏联文化史家和东方文学专家伊戈尔·叶廖明在其《西梅翁·波洛茨基诗体风格》一书中对俄罗斯巴洛克式文学风格进行了全面的概括与总结;最后,从理论角度提出俄罗斯17世纪巴洛克风格的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古罗斯文学专家斯维特拉·马特哈乌泽洛娃,她于1968年在布拉格举办的第六届国际斯拉夫学家大会上作了题为《17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巴洛克风格》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分析了俄罗斯巴洛克式文学起源以及这种文学流派对于俄罗斯新旧文学承上启下的关系等问题。然而,我们认为,第一个系统梳理巴洛克文学风格在俄罗斯文学史的地位以及这种风格对其发展进程之影响的,恰恰正是利哈乔夫本人。
关于俄罗斯巴洛克文学风格是否发源于俄国本土是各国学者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上利哈乔夫并不完全认同马特哈乌泽洛娃的意见。后者认为,在17世纪的俄罗斯有两种独立形式的巴洛克:一种是本土的巴洛克,它否定并怀疑旧的形式,具有解构性,是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之下产生的;另一种是由波兰-乌克兰引进的巴洛克,这是由学院派诗学培植和推行的、纯理性主义的、走向风格主义的巴洛克。[3]-[12]她认为,俄国古代文学的终点正是巴洛克式文学在俄国的兴起。然而,按照利哈乔夫的观点,巴洛克文学在俄罗斯的兴起基本上是外来因素的必然结果,如果存在“本土的巴洛克式”并且这其表现形式很强劲的话,那么外来的巴洛克式因素是不会轻易进入俄国境内并与本土的巴洛克式因素相融合与发展的。
接着,利哈乔夫进一步强调,由于俄罗斯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仅仅是存在一些“文艺复兴现象”,因此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巴洛克式艺术风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来自西欧(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的巴洛克式艺术风格通过波兰——乌克兰传入俄罗斯,使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具备了本国形式和本国内容,[3]-[17]因此,从这个角度也可将这种风格理解为西欧巴洛克风格的俄罗斯本土化。
如果我们认为俄罗斯17世纪的巴洛克风格是一种来自西欧的巴洛克风格与俄罗斯本土的文化、文学特征的一种“杂糅”,那么这种“杂糅”风格必定会给俄罗斯带来独特的且其他欧洲国家所不具有的特点与作用。如果从整体上将欧洲的巴洛克文学风格看成是介于文艺复兴运动与新古典主义运动之间的重要的文学思潮,[5]是一种向中世纪古典文学“回归”的话,那么17世纪俄罗斯巴洛克文学风格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回归”,只不过不是向古希腊、罗马传统和中世纪传统的回归,而是承袭自己的古罗斯式的传统并在这些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巩固、发展和创新。这种“回归”形式充分体现了古罗斯文学的主要特点,即风格上的矫揉造作、“辞藻堆砌”、热衷于固定的文学形式(如编年记事)以及所具有的社会教谕功能等。[3]-[5]
西欧巴洛克式文学风格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艺术思潮,也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学风格,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当代的文学作品中都积极地展现出自己的活力,[6]在17世纪传入俄罗斯以后,这种活力又体现在它能够迅速地融入俄罗斯本土文学之中,与俄罗斯古代文学特征相互照应,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西欧的、独具特色的17世纪俄罗斯巴洛克式文学风格,这种特点首先体现在它建立在官方和宫廷基础上的华丽和夸张,对人物的表现服从于总的辞藻华丽的情节与线索。3[6]-[7]就这一特点而言,西梅翁·波洛茨基是典型的17世纪俄罗斯巴洛克式诗人,同时也是俄罗斯第一位宫廷诗人和职业作家。波洛茨基的创作领域广阔,包括了步道文、专题论文、戏剧和诗歌等领域,他的创作目标是将所有领域的知识传授给读者,从而在俄罗斯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文化,[7]他的诸多诗作,如《俄国之鹰》(Орелро ссийский)、《悦耳的古斯里琴》(Гусльдобр огласная)等作品将这一巴洛克式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次,巴洛克式文学充分吸纳了俄罗斯古代文学的特质,在创作风格上体现了劝喻和启蒙精神,具有一种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般的性质。
例如,波洛茨基就竭力通过献词、颂词、赞歌和贺词等形式告诉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菲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理想君主应有的特点;17世纪另一位巴洛克式宫廷作家卡里昂·伊斯托明在其诗作中呼吁索菲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创办高校,传播科学。3[7]-[8]
最后,巴洛克文学作为一种向新古典主义文学的“过渡性”文学形式,它也逐渐具备了俄罗斯近现代文学的现实性与世俗性。利哈乔夫指出,俄罗斯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在为所创作的现实“收集”情节和题材,以便进一步描写生活,描绘生活的纯粹和奇妙,刻画人与人、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利哈乔夫注意到,17世纪俄罗斯巴洛克文学形式中出现了反映世俗内容的识字读本和诗歌,这也说明巴洛克式文学在推动着俄罗斯文学从整体上朝着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方向前进。
三、巴洛克式文学风格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在俄罗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短暂但又重要的一种文艺现象,它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俄苏文史学家也都有过相应的讨论。伊戈尔·叶廖明曾简略地阐述了17世纪下半叶由西欧传入俄罗斯的巴洛克式文学风格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发展进程中起到的作用,他指出由于俄罗斯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阶段,所以中世纪古典主义美学因素对于17世纪的俄罗斯来说并不“十分遥远”,因此俄罗斯能够较为轻松地吸收含有这些古典主义美学因素的来自欧洲的巴洛克式风格,这也是俄罗斯首次汲取来自西欧的风格[8]。苏联文学史家亚历山大·莫洛佐夫认为,来自西欧的巴洛克文学风格吸收了之前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优秀成果,在传入俄罗斯后对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巴洛克式在俄罗斯取代了文艺复兴。[9]
利哈乔夫在对17世纪俄罗斯巴洛克式文学特征充分研究后基本赞同叶廖明和莫洛佐夫的观点,他结合自己的理论对巴洛克风格在俄罗斯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发展作用作了总结性归纳。
首先,利哈乔夫赞同叶廖明在第四次国际斯拉夫学家大会上作的报告,认为由于东斯拉夫各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运动,从中世纪直接进入了巴洛克式时期,所以巴洛克式加快了俄罗斯新文学的形成,用新的主题、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段丰富了文学,出现了过去未曾有过的艺术创新的新体材和新形式—诗歌和戏剧。[10]
第二,被引入到俄罗斯并与俄罗斯本土文化相融合共生的巴洛克式风格与西欧的巴洛克式并不相同,它不是一种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文学的回归,而是一种面向自己古代文学的“影像”,一方面,通过这种镜像般的审视,俄罗斯古代文学创作的特点和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另一方面,通过西梅翁·波洛茨基、卡里昂·伊斯托明等诗人和作家的引介与翻译,来自西欧的新风格和新要素传入俄罗斯,这又构成一种对中世纪的背离,使巴洛克式成了俄罗斯文学从中世纪向近现代的一种过渡形式,具有明显的缓冲意义。
利哈乔夫进一步指出,由于俄罗斯没有文艺复兴运动,而是由巴洛克式承担了文艺复兴的功能,因此便可以理解巴洛克式那种乐观向上、肯定人的价值和启蒙的性质。3[10]正是这种对人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感叹以及对人的价值的理解构成了俄罗斯18世纪的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小说,乃至19世纪文学黄金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最重要和最核心的思想观念之组成部分。
最后,利哈乔夫又以自己多民族和跨文化的视角,表达了对整个欧洲的巴洛克文学现象独到的见解。他强调,巴洛克作为一种虽然短暂,但是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和艺术潮流,尽管它在欧洲各国家之间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存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这种潮流具有某种超越国界的整体性。它成了形式化很强的风格,能服务于不同的思想体系,能从一个国家传入另一个国家。17世纪下半叶的巴洛克式是没有国界的并能超越社会的壁垒。3[11]这一时期的俄罗斯诗人和作家翻译了欧洲各国的诗歌和文学并将其引入俄国,从而形成了某种“超越街垒”的(帕斯捷尔纳克语)、“具有国际性”的而非“民族差异性”的欧洲统一的风格爱好。
在对17世纪巴洛克式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与作用分析完后,理性的且具有批判精神的利哈乔夫还注意到,虽然不可否认巴洛克式文学对18和19世纪俄罗斯新文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应被夸大,应该被理性地看待。他强调,尽管17世纪的巴洛克文学形式为俄罗斯带来了文学创作中的个性解放、个性化原则加强、对人的关注以及文学世俗化和启蒙性质等具有现代意义的积极因素,但绝不能将巴洛克式视为俄罗斯文学发展之中绝无仅有的甚或是主要的作用。应当注意到,巴洛克式主要是对存在于社会上层和官方文学起作用的一种力量,它更像是一座桥梁,承载着其他重要的进步现象并与它们一起推动了18世纪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形成。3[17][18]笔者认为,利哈乔夫正是以这种国际性视野和对文学、文化领域跨民族、跨文化的思考模式和研究方法以及他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使他始终立于俄罗斯文化研究大师之林。
四、彼得一世与俄罗斯新旧文学
别林斯基在其写于1834年的成名作《文学的幻想》中为了突出罗蒙诺索夫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将其比作“俄罗斯文学中的彼得大帝”。[11]别林斯基从文学的视角高度评价罗蒙诺索夫,为其在俄罗斯文学中崇高的地位定了位,并在一系列文章中高度赞扬了他为俄罗斯文学领域的改革所做出的突出贡献。通过对罗蒙诺索夫的评价,我们也能理解这位俄罗斯西方派代表人物对彼得一世之于俄罗斯社会、政治、军事乃至文化和文学所起到的“转向器”般的作用。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化的反思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一是彼得一世改革是俄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分水岭,改革之后的俄国社会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二是俄国新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上层,尤其是与上层密切相关的知识阶层,他们代表了俄国文化的现实面貌和发展方向。[12]其实,无论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在18和19世纪的俄罗斯社会观念中,彼得一世的即位和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它改变了俄罗斯科学和文学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学之舵由教会转入世俗政府的手中,并通过行政命令使俄罗斯文学与欧洲文学靠拢。彼得一世倡导文学的“西化”,创办第一份报纸《新闻报》,派遣各阶层青年前往西欧留学,同时引入西欧的诗歌、诗律和文学视野,推广世俗读物、“传奇故事”和“爱情小诗”和政论体裁等文学形式。[13]不可否认的是,来自西欧的巴洛克式文学风格正是通过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之桥传入了俄罗斯,因为这种风格完全符合他所竭力倡导的理念,即热衷于启蒙和改革,喜爱巴洛克式“民主”体裁,喜好按照波洛茨基的巴洛克式劝喻精神来认识沙皇对俄罗斯国家及臣民的权利和义务。
利哈乔夫指出,彼得一世需要为自己在俄罗斯塑造一种民主的和公民的形象,他借此常常强调自己对俄国公民般的服务,热爱人民和科学,尊重个人价值,在他的改革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各种门类和各种形式创作中的个性化原则的发展。3[25]然而,利哈乔夫注意到,一方面,在17世纪俄罗斯引自西欧的巴洛克式文学中这种对个性化创作原则的尊重和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只是古罗斯文学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而并非是彼得一世文学改革的直接结果,因为早在14-15世纪的“前文艺复兴现象”中对个人的关注就已经出现在俄罗斯艺术作品之中,只不过由于俄罗斯没有过向近代文学转变的文艺复兴运动,取而代之的是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巴洛克式文学作品之中。另一方面,新旧俄国之间的鸿沟又恰是彼得一世亲手所造成的,因为他试图断绝包括文学和文化在内的与旧俄国的一切联系,为自己树立一种改革者先驱的神话。
彼得需要靠近欧洲,就说他之前的欧洲是相脱离的;他需要俄罗斯更快地发展,就说他之前的俄罗斯是保守的和静止的;他需要一种文化新风尚,就说旧的文化不值一提。于是,彼得之前整整7个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不断地遭到贬损和否定。[14]然而,关于彼得一世的改革是否真的为俄罗斯新旧文学建造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成为二者的分水岭这一问题,利哈乔夫给予的答复是否定的。他强调,俄罗斯古代文学和俄罗斯近代文学并不是一个突然中断、另一个突然出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而是一个统一的文学,3[19]一部统一的文学史。俄罗斯近代文学并非彼得一世欧化的结果,他机械地复制和掌握欧洲文化的经验是无法孕育俄罗斯的近代文学的。与此恰恰相反的是,正是来自西欧的巴洛克式文学在17世纪的俄罗斯境内的不断发展,创新出与俄罗斯本土文学相融合的、适合本土文学发展的新型文学体裁,培育出像西梅翁·波洛茨基、西而维斯特·梅德韦杰夫、卡里昂·伊斯托明等优秀的巴洛克式新型诗人和作家,才使俄罗斯文学向西欧的转变做足了准备,才能使俄罗斯有能力掌握西欧先进的文学经验。
不仅如此,利哈乔夫还提醒我们,在彼得一世改革将近百年之后的18世纪中后期,中世纪的文学体裁并未消失,依旧有人编写和阅读使徒行转,传抄就文集,阅读古罗斯优秀的文学作品。然而,新文学环境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在排挤俄罗斯古代文学:在文学传播手段上,打印机的出现了逐渐使传抄、手抄等方式消失殆尽;文学期刊、杂志、剧院、文学评论等近代文学环境的出现使这一时期的古文学对俄罗斯文学史的发展失去了意义,退居次要地位。
因此,应当理性看待彼得一世的改革对俄罗斯新旧文学产生的影响,不能将俄罗斯新旧文学割裂开来看待,而应以一种统一的文学史整体上加以研究和把握。
五、结语
通过对17世纪俄罗斯巴洛克式文学风格的产生、对俄罗斯文学史发展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通过文化背景的视角审视彼得一世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的分析,利哈乔夫指出,俄罗斯文学从中世纪文学向以注重个性化原则、尊重人的价值、关注人的命运为特征的近现代文学过渡和转变,是由14-17世纪这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里通过“前文艺复兴”现象和巴洛克式等艺术风格影响积累的结果,而并非直接源自彼得一世的改革,他的改革只是顺应并加速了俄罗斯文化整体上从中世纪类型向近现代文化类型的转变。彼得这位17世纪“典型的巴洛克式人物”只是俄罗斯文化转型的“加速器”,3[27]是这个过程的产物,而远非必要条件。
我国学者刘文飞教授将利哈乔夫比作“一位独特的西方派”,因为他强调俄罗斯文化的欧洲属性,强调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欧洲教养,强调西方文化较之于东方文化的某种优越性。[14]其实,就俄罗斯17世纪巴洛克式文学风格的作用而言,他不仅是一位“独特的西方派”,同时还是一位“独特的斯拉夫派”。他一方面对俄罗斯吸收西欧先进的文化经验,向西欧文学转型的转型表示肯定;另一方面,他又无限推崇和热爱俄罗斯古代文学。他坚持认为,西欧文学只有与俄罗斯本土文学相融合,而俄罗斯文学只有在继承、发展和创新本国古代文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欧文学的经验才能以更强劲的根基扎根于世界民族文学之林。利哈乔夫的这种辩证的观点似乎在当今的俄罗斯文学中应验了,在以后现代表现手法为重要特征之一的当今文学中出现了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维克多·佩列文等俄罗斯后现代派代表作家,他们借鉴了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和“重构”策略,以新思维模式和新叙事话语消解、颠覆、否定传统思维模式,却又继承了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传统——拒斥一切虚无主义,[15]并且试图找回俄罗斯文学中强烈的宗教感。从这一点我们似乎不难看出,作为文学史家的利哈乔夫始终高度关注着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方向,并为这种发展树立了两座“基石”,即来自西欧先进的文学经验与屹立在俄罗斯本土的文学传统,只有这种坐落在“经验”上的“传统”,才能充分推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使其在世界文学中拥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