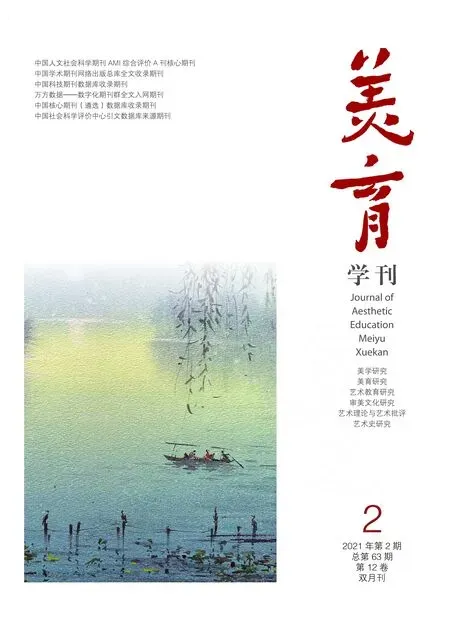“玩好”的初容
——基于先秦至两汉相关文献的审美文化考察
蔡志伟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0)
“玩好”,是古人对于各类审美精品的统称(1)有关“玩好”概念,学界目前存在两种看法。一种意见指出“‘玩好’指生活中的审美精品”,见[美]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文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另一种意见声称“玩好之物的概念与现代西方观念下世俗装饰艺术的概念大致相符”,见[美]乔迅(Jonathan Hay):《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刘芝华、方慧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8页。笔者认为,尽管前者较之后者略显模糊,但是更加符合“玩好”的历史实情,其在任何时期皆非仅与工艺品或装饰物相对应。本文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梳理、建构一个更为完善的“玩好”概念。,其在先秦、秦汉时期就已广泛使用,并在内涵不变、外延扩展的情况之下沿用至今。目前有关“玩好”的研究著述多将视野投向晋唐以降,尤其是明清之际,极少论及先秦、秦汉时期的具体情况。缘此,本文尝试以先秦至两汉相关文献为基础,通过考察字形词义,历史语境与社会反思三种维度,建构“玩好”的审美文化初容。
一、何谓“玩好”:三位一体的“物—审美”概念
作为一个始自先秦的古老概念,“玩好”是由两个动词叠加构成的一个名词。这种构词方式暗示,该词可能源自人们对于某些事物频繁做出的某种特定行为,在行为与事物屡屡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二者之间渐次形成了对应关系,于是前者就引申为后者的代名词。如此不妨暂将“玩好”的概念结构假定为:“物—行为”。延此假设,这里尝试通过溯源“玩”“好”二字,了解其中“物”与“行为”的原初情况,进而建构“玩好”概念的基本模型。
作为一种天然矿石,玉以其独特、珍稀的自然属性受到先民关注,进入社会生活。琢磨成器之后,常被用作身份财富的象征,以及巫、礼仪式的载体。随着制玉、用玉活动的不断深化,玉及其制器造型的形式美感更获凸显与提高;与此相伴,人们对于这些形式的美感认知相应更加自觉。于是,玉器在履行上述象征、载体功能的同时,也成为一种供人欣赏的审美物品。

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3]527
这里的“玩”已非动词,而是作为代指“白珩”的名词。综上所述,“玩”即“弄”,是一种开启诸种感官从事审美活动的动作,与先秦时期用玉、赏玉的社会风尚直接相关。由此,可以提炼出“玩”字中的两种结构要素:审美对象与审美感官。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先秦时期的“玩”亦有钻研分析的意义。《易传》:“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4]这是“玩”之意的再扩展,一方面将游戏心态的端详审视,移作严肃学问的探理考究;另一方面却又保留其中的审美属性,无论活动本身,还是活动状态,皆与感性直观与精神愉悦紧密相连。
再行考察“好”。根据段玉裁的说法,“好”(hào)由“好”(hǎo)引申而来。《说文解字》有云:“好,媄也。”“媄,色好。”段注写道:“好,本谓女子。”[1]618亦即专指女子的姿色不凡。已有研究指出,先秦女子以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眼睛明亮为美。这种女性审美观的成因,涉及对于女性能否胜任生育、劳作的现实考量[5]。一个有些敏感却又隶属事实的情况是,在早期男权社会中,美女与其他观赏物并无本质区别,她们曾被男性视为“足以移人”的“尤物”[6],也有所谓“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并提说法[7]328。
关于“好”的意义泛化,以及引申为“好”,段注写道:
引伸为凡美之称,凡物之好恶;引伸为人情之好恶。[1]618
准此可见,“好”在意义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了由人及物、由物及情的演变轨迹。由特指美女扩展为指涉一切令人愉悦的事物,最终衍生为标识感性判断的概念。另外,“好”不仅是对事物外观美、丑的甄别,而且含有表示偏爱、甚或沉溺的色彩。综上可知,“好”属于一种感性判断行为,乃是先秦时期女性审美语汇的意义引申。如是,可以提炼出“好”字中的两种结构要素:感性判断与审美对象。
若将上述“玩”“好”二字的结构要素相互叠加,就可得到“玩好”概念的基本模型——审美对象+审美感官+感性判断,也可简单表示为“物—审美”。通过“玩好”的最初对象与内在结构可见:其源自先民对于观赏玉器、美女活动的抽象概括,完整表述了审美活动的三种基本要素:对象、感官与感性判断。
先秦、秦汉时期,“玩好”虽然起于玉器与美女,但是包罗之物不限于此,所涉颇为繁杂:
魏王遗楚王美人……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8](《战国策·楚策四》)
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9]561(《谏逐客令》)
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9]717(《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这里与“玩好”并提的诸种事物,大体涉及自然产品与工艺制品两类,具备如下共同特征:它们既是生活物资,却又因原料珍稀且精美异常,而越出于一般生活物资的范畴,以悦目的形式与不菲的身价,成为王室贵胄的居处陈设,以及人际、国家之间的馈赠选择。
客观而言,“玩好”的出现与发展,是古代先民审美意识高度自觉的产物。说明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实用需求获得满足之时,尚有余力与意愿追求面向审美的专门事物,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把标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玩好”概念具有极强的扩容性,所含事物类别会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有所增益。这种现象的出现,完全符合“玩好”作为一个“物审美”概念的原始逻辑,一旦某物与“玩”“好”行为频繁对应,就会几乎为其照单全收。这种包容性暗示,“玩好”无孔不入,乃是古人构建审美生活的重要物品。当然,这种包容性同样存在基本限度,亦即某物可为个人进行事实占有。譬如,中国古人存有“玩月”一说,然则遥不可及的月亮并非属于“玩好”。
二、由“赠”说起:“玩好”与礼制的历史纠葛
《说文解字》有云:“赠,玩好相送也。”段注补充写道:“以玩好送死者,亦赠之一端也。”[1]280这些解释一方面显示“玩好”与交往活动存在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它与诸多生活领域关联,既主演日常美物的角色,也客串丧葬仪式的戏份。由此可见,“玩好”曾以广义“礼物”的身份存在,“礼”乃是其置身的一种重要历史语境。
相较文字释义提供的扼要信息,“玩好”与“礼”的实际纠葛更加曲折复杂:其在西周时期受到《周礼》“式贡”分配制度的规范与监督;随后则在礼制崩溃与生产力提升的社会变革之中,迎来蓬勃发展的时代机遇;同时,将之用于陪葬,既是礼制的组成部分,又是衡量死者生前是否勤俭的重要指针。
有关“玩好”最为知名的一则早期文献,无疑是《尚书》所载“玩物丧志”的历史故实(2)尽管已有研究指出,这段记述或为晋人伪托,但是正如下文相关论述所示,这段记载基本符合西周时期“贡物”“玩好”与礼制之间的历史实情,故而可以引援使用。梁江《先秦古籍所述及的美术鉴藏》一文亦持类似观点。见梁江:《先秦古籍所述及的美术鉴藏》,载《美术观察》,2000年第7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厎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曰:“呜呼!明王慎德,西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人不易物,惟德其物……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7]326-330
这段材料显示,外邦朝贡周王朝的物资,大体包括“服食器用”与“玩物”两类。前者属于“用物”,后者对应“异物”“远物”,亦即供于观赏的非实用物。太保告诫周王,若将贡物用于国计民生,则是王者德行的显著彰显;相反,如果沉溺耳目的欢愉,醉心其中的“玩物”,实属品行不端的失范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这番进谏并非单纯的道德言说,而是以制度规范为现实依据的道德发声。《周礼》明确规定:
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10]449
何谓“式贡之余财”?“式贡”是指周朝“大府”掌管的“九贡”“九赋”与“九功”,可以视为政府物资的总称。其中的“九贡”专指“邦国之贡”,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贡物;“九赋”“九功”泛指“畿内田野之税”与“万民职事之征”,亦即农业与手工业的税收,其在当时也属贡物范畴,唤作“万民之贡”(3)关于这种外邦贡物与国内税收在称谓方面界限不明的情况,李云泉的《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曾有说明。见李云泉:《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无须赘言,包含“邦国之贡”与“万民之贡”的“式贡”,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品质不一。故而,“大府”在敛收“式贡”以后,另会依据物资种类与品质优劣进行划分。经过这道分拣程序,一方面各种“式贡”的不同用途得以确定,另一方面其中的“良货贿”也从一般“货贿”之中脱颖而出。随后,归类完成的“式贡”则会转交“外府”、“内府”“玉府”分别掌管。
三府所掌“式贡”的种类、品质、用途以及物权所有互不相同。概而言之,进入“外府”的“式贡”主要是一般生活物资,“待邦之用”,物权归属国家;流入“内府”的“式贡”主要是高级生活物资,“待邦之大用”,物权亦属国家[10]467-474。分至“玉府”的“式贡”较为特殊,《周礼》记载: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齐,则共食玉。大丧,共含玉、复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第,凡亵器。若合诸侯,则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献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贿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赐,共其货贿。[10]451-467
如是可知,“玉府”主要掌管非实用性的奢侈品,“玩好”就是其中一员,专供君王在生活装饰、休闲娱乐、丧葬与赏赐等诸多方面的个人花销,物资权限完全听凭君王的个人旨意。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周礼》规定,“式贡”的分配必须遵循优先考虑国家之用,再行满足君王之需的基本原则[10]449;即先行分拨“外府”“内府”的公共开支,复次分派“玉府”的私人用度。上述这些分配方式与基本原则,就是所谓“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
在“国”与“家”、“公”与“私”矛盾不可调和的时代,《周礼》制定的“式贡”管理办法,能够确保政府物资不受君王意志的随意支配,合理用于国家运转的切实需求。其间,“玩好”的拥有与获得,被限制于一定尺度与特殊人群之内。同时,这种限制做法也使本就属于“良货贿”的“玩好”更显难得珍贵,为君王贵胄显示身份、炫耀财富提供着独特的物质资本。简而言之,这套“式贡”秩序,是“礼”的一种具体呈现,“玩好”则被置于“礼”的严格约束之下。
在理想状态中,一位心系社稷的明君,应当脱离私欲而胸怀天下,不去计较“玉府”的个人得失,全力确保“外府”“内府”的物资充盈。即使不能如此,也应严格遵循“式贡”分配的制度条陈,获得“礼”批准的私人享乐之资。准此,在“旅獒事件”中,引起太保进谏的原因,除了对于君王道德的理想诉求之外,抑或包括如下事实:周天子有意越过“式贡”制度的管控,而径将“贡物”纳为“玩物”。即使这只獒犬随后也将通过“礼”的分配成为“玉府”中的赏玩之物,但是这套制度流程必须得到切实执行。
然则,在礼制崩塌以后,作为其中组成部件的“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也就沦为一纸空文。这种约束失效的突出表现,并不在于权威旁落的周天子是否可以毫无顾忌地“玩物丧志”,而是在于随着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任何富有财力的阶层皆可随时购买、占有、享受“玩好”。一言蔽之,在失去礼制管控、获得物质生产助力的全新时代,“玩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兹举春秋至两汉的几则史料为例:
管子对曰:“……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3]230(《国语·齐语》)
吕不韦……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9]541(《史记·吕不韦列传》)
宛有富贾张汎者……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恃其伎巧,用势纵横。[11]371(《后汉书·党锢列传》)
如是可见,春秋以降,伴随“玩好”制售行业的蓬勃发展,其更加普遍地走进了权钱阶层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他们享受、互赠的时尚之物,甚至成为观测一地风俗的风向标与跻身上流社会的敲门砖。这些文献同样显示,“礼”对“玩好”的限制约束,绝非故作姿态的繁文缛节。这种悦人耳目的奢侈品,确实会给社会稳定与政权统治,带来意想不到的潜在危机。
在以“玩好”构筑日常享乐的同时,视死如生的古人还会用其陪葬,在阴间继续生前的物质生活,在墓中标识生前的身份地位。使用“玩好”作为陪葬品,最初既是“礼”的组成部分,也受“礼”的规范制约,荀子有云:
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襚,玩好曰赠,玉贝曰唅。赙、賵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故吉行五十,奔丧百里,賵、赠及事,礼之大也。[12]492
其后,随着“玩好”不再受到“礼”的约束以及迅猛发展的势头,其在厚葬风气之中成为尽显奢华的主力;而在薄葬之风获得强调以后,它的缺席则是体现墓主纯俭之德的标志:
爰暨暴秦,违道废德,灭三代之制,兴淫邪之法,国资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11]839(《后汉书·赵咨传》)
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时年三十。遗诏无起寝庙,敛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11]134(《后汉书·顺冲质帝纪》)
这些材料再次表明,“玩好”与道德礼法之间,始终存在不可化解的矛盾关系。如是描述或许甚为贴切:当时人们在感官欲望层面对于“玩好”甚为喜爱,却在道德律令面前对之忧心忡忡。在心怀天下、注重修养的诸子百家那里,作为物欲的凸状之一,“玩好”成为他们展开社会反思的材料与靶心。
三、不役于物:有关“玩好”的社会反思
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必须承认如下事实:尽管彼时涉及“玩好”的各家言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之视为社会蠹虫,但是更为公允地说,“玩好”并非如此不堪。诚如前述,“玩好”是文明进步的一把标尺,乃是先民审美意识走向高度自觉的相应产物。那么,这把文明的标尺为何屡遭口诛笔伐?
太保谏言周天子切忌“玩物丧志”之论,可以视作讨伐“玩好”的文化先声。其中涉及沉溺“玩好”的两重弊端:危及国家稳定,有损个人品行。随后,先秦诸子对于“玩好”展开的社会反思,大体仍旧延此推进。面对“玩好”日兴之势,他们对其威胁社会安定的斥责更为严厉,对其戕害道德修养的思考更加深刻。
上文提及,《周礼》规定“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的目的在于,防止君王为图私人享乐,而肆意侵占公共资源的现象发生。这种制度反映的基本精神,具有普遍适用意义,并不仅限某朝某代。可以想见的是,如果统治阶层屡屡无视这种资源调配原则,那么社稷国运必将处于危险境地。正因于此,先秦诸子再三告诫,国家必须遏制生产“玩好”造成社会浪费,注意避免搜罗“玩好”激起的社会矛盾:
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13](《管子·五辅》)
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14](《韩非子·亡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言论具有直击当下的现实品质,但是并未充分剖析人与“玩好”负面关系的症结所在——物欲的形成,以及尝试探索究竟如何克服之。严格来说,不是“玩好”,而是其背后的物欲导致着社会资源的不当消耗。故而,解决“玩好”引发的社会积弊,关键在于如何击破物欲。对此,儒、道两家作有正面回应。
概而言之,人、物之间存在两种关系:“役物”与“役于物”(4)《荀子·修身》写道:“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7页。)这里借以“役物”与“役于物”作为标识人、物关系的基本概念。,前者意味主体对客体始终保持着一种主动姿态,后者则是截然相反。不可否认,“役物”能力的不断强化是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由满足实用需求向非实用需求的推进,恰与“役物”能力渐次攀升的相互对应。然则,一旦物质生产到达一定水平,人与物的关系就有可能出现戏剧化的颠倒,卢卡奇(Georg Lukács)将之称为“物化”(Verdinglichung):
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5]
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玩物丧志”之说可以证明,先秦时期就有类似的“物化”现象存在,并且人们对之已有明确认知。
仅将物欲与沉溺“玩好”相对应,显然不够恰当与全面。这样理解更为适宜:物欲包含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无度追求,以及为了满足这种追求,而对社会地位、名利富贵等相关条件的过分争取;而痴迷“玩好”以及其他享乐活动,则是这一系列意愿的显性表征。有关于此,老子曾有一段经典论述: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16]
这里提及的“难得之货”多半是指以“异物”“远物”为主的“玩好”,“五色”“五音”“五味”云云,则是对于人们沉溺“玩好”以及其他享乐活动的客观描述。老子告诫时人,应当效法先贤“为腹不为目”的做法,在基本生活需求获得满足以后,不再无休止地追求额外的生活享受。
所谓“为腹不为目”实则隐含如是观念:注意“役物”的目的与尺度,避免由于过分“役物”,从而走向“役于物”的窘境之中。崇尚“道法自然”的老子,固然倡导“无为”的行为方式。然则“无为”并不代表全然放弃“役物”,亦即完全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这种能动性的适宜边界。具体来说,以生存为目标的“役物”不是“有为”,实属顺应天理的“无为”;但是超越其上的“役物”,就属出于巧智的“有为”,有悖“自然而然”的准则。一旦“役物”超出恰当边界,那么这种“役物”行为的对应产物,譬如属于“难得之货”的“玩好”,就会使人进入“役于物”的状态之内。究其原因在于:不同于生存层面的生理需求,享乐层面的生理需求并无上限。在人与“玩好”等享乐之物的交互活动中,耳目之愉始终处于被激发、再渴求的情形之中。若不加以有效克制,主体就会进入“目盲”“耳聋”的被动状态,成为“役于物”的物欲奴隶。
对于如何避免“役于物”的状态,老子提出应当“少私寡欲”“见素抱朴”,通过“涤除玄览”的精神修行,纯洁内心、洗刷物欲。庄子与其持有基本一致的观点,宣称“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17],同样发现充满巧智的诸多事物,对于纯真本性的笼罩与扭曲。其为此拈出“心斋”“坐忘”之说,要求祓除个体欲望,涤荡精神世界。
在某种程度上,老、庄提出的精神修行方法,有些过于玄妙而难以切实执行。一方面,人们的感官体验一经开发,实难复归先前的朴素状态;另一方面,这种复归是否确实必要,或许有待商榷;进而言之,在无法复归之时,是否存在更为可行的某种办法,对其加以必要约束?先秦儒家提出了一套抵制物欲侵袭的务实方案。
在这套儒家方案中,作为“礼”的内化,“仁”扮演着关键角色。《周礼》规定的“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包含如是策略:允许“玩好”的存在,然则必须服从“礼”的约束;作以延伸即为:承认个体感官享受的合法性,但是必须无碍集体实用需求的基本利益。这种策略的基本逻辑,在“礼”内化为“仁”以后,成为先秦儒家管理物欲的有效阀门。
孔、颜乐处,是一个典型案例。何种精神力量能够促使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超然于物质享乐与名利诱惑之外?无疑乃是其与孔子共同奉行的“仁”字。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修养方案中,作为个体准绳的“仁”,是支撑面向集体的“道”与“德”的基础;或言之,只有奉行“仁”的个体,才能作出对于集体有益的工作。其间,克制过分的自我诉求——物欲,乃是重要目标之一。朱熹明确解说:“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18]94儒家并未宣称彻底消灭物欲,而是采取以“仁”来管理、约束物欲的方式,使其无法肆意妄为、畅行无阻。
对于感官欲望及其有效控制的问题,孟子、荀子作有更为细致的解读与阐发。他们共同承认,诸如口、目、耳、鼻等感官欲望,是“性也”[19]393与“人情之不免也”[12]211;却又指出,与生俱来并不表示感官欲望可以放任自流,一旦任其妄行,个体就会陷入“蔽于物”[19]314、“为物倾侧”[12]102的境地之内。因此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依靠道德律令对其严加制约。值得引申讨论的是,物欲之所以被视为一种道德病症,是因为并不仅仅在于患者无度挥霍社会资源,更加在于患者丧失了不受外物所控的自由意志——那些看似肆意而为的选择,皆是位于物的外部操纵之下。无须赘言,这种情况在“玩物丧志”者不断索取“玩好”的欲望行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反思、化解物欲的同时,儒、道两家又以“游”的提出——“游于艺”“与造物者游”,而为人与“玩好”走向良性互动,预设了一张基本蓝图。诚然,先秦时期的儒、道之“游”与“玩好”并无直接关联。但是在思想传承的过程中,其对后世的“玩好”文化确有不可低估的塑造作用。朱熹曾经如是阐述“游于艺”:
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18]94
在此,“游”被解释为一种以“六艺”为对象的“玩物适情”活动。值得说明的是,这种说法并非是将“六艺”作为“玩好”,而是借此强调审美活动的价值问题,亦即要求通过审视具有人文历史价值的事物,进而陶冶道德情操、掌握客观规律。这种价值倾向,极为鲜明地体现在宋代文士“追三代之遗风”“补经传之阙亡”的金石玩好之中,朱熹就是当时知名的金石玩家之一[20]。同时,这里将“适情”作为“玩物”的尺度规定,意在点明人与审美对象之间应当保持合适“距离”,避免过度沉溺。
道家的“与造物者游”同样对于后代文士的“玩好”文化影响深远。一则,其中展现之亲近自然的审美视野,使得文士将奇石、花木等自然物引为“玩好”,用来点缀自己的壶中天地。二则,其中内蕴之道法自然的价值观念,使得文士在鉴赏诸多“玩好”之时,通常持有推崇天成、贬斥矫饰的趣味取向。其三,其中包含之澄明外物的修养心境,使得文士自觉报以“一赏而足”“寓意于物”的“玩好”态度,从而规避物欲的负面袭扰。
简言之,儒、道之“游”为人与“玩好”走向良性互动埋下了文化伏笔。
四、余论:“玩好”历史分期简述
概略来看,中国古代“玩好”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其一,先秦、秦汉时期。如上所及,这一阶段的“玩好”概以工艺精品与自然珍奇为主,讲求好异尚奇、雕镂繁缛的审美趣味。其二,魏晋、隋唐时期。由于文士群体的普遍介入,这一阶段的“玩好”在品类、趣味方面出现了扩展与突破。艺术收藏逐渐成为“玩好”中的重要一支,而与工艺精品、自然珍奇并肩鼎立。作为追求清雅人生的物质依托,“出水芙蓉”面貌的“玩好”更为文士青睐。其三,宋元时期,尤以两宋至为关键。在此期间,文士“玩好”成为整个“玩好”世界的主导力量,“佳物”“清玩”等专指文士“玩好”的概念相继提出;皇家宗室、市民阶层的“玩好”趣味,也向文人群体主动靠拢或相互交融。尤其重要的是:一方面,文士开始大量撰写有关“玩好”的诗文与谱录;另一方面,他们普遍认同“玩好”在形塑身份、提高修养、构建生活方面意义非凡;同时,“玩好”成为文士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阶层展开交往的重要媒介,广泛渗入社会生活之中。其四,明清时期,尤以晚明最为紧要。多部研究著述指出,在物质文化的席卷下,文士阶层既围绕“玩好”设置“文化区隔”,以凸显自我的身份与地位;又为商人、工匠等企图冲破阶层划分的群体,提供着效仿所为、与之交往的途径。以“玩好”为载体的审美生活全面展开,呈现出“早期现代”或“前现代晚期”的社会特质。
诚然,中国美学史研究可以继续进行自然物、工艺品与艺术品的分类考察。然而,如果站在“玩好”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古代的审美实践中,实则并不存在如此明晰的划分,而是倾向于将不同物品组合起来,共同构筑生活场域。故此,与其分而论之,不如视为一体、探其共性。如是,或许能够更加切近历史原境,也为美学理论提供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