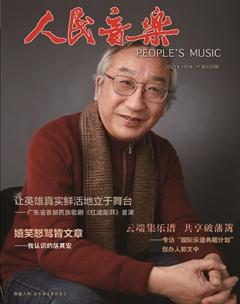试论音乐教育的双向交互研究范式
一、缘起
进入21世纪以来,音乐教育发展的步伐加快,这一趋势从最初的基础音乐教育延伸到高师音乐教育,并最终促发了后者的跟进改革,显示了中国音乐教育自上而下(从教育决策部门到广大基础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启迪路线以及自下而上(从基础音乐教育领域到高等音乐教师教育领域)的行动实践路线。这一进程是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那么,音乐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是否就带来了音乐教育实践及理论研究的显著进步呢?
一方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从世纪之交至今,音乐教育在中国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大量文献选题着眼于中国音乐教育在新时期的思想理念,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这些探索为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参考,理清或深化了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例如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及“学科本位”的旧观念,构建“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成为广泛期许。在现行课程标准里,“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等理念都已是各方所认同并强调的学术立场。在广大中小学,基于新的课程标准的音乐教学也在逐步呈现出新的面貌。
而另一方面,答案又是难以确定的。过去若干年来,音乐教育研究的主要成果都集中在思辨性研究方面,这一点通过浏览近年来音乐教育学方向的期刊论文及硕、博学位论文选题即可窥见一斑。不可否认,思辨性研究对于音乐教育价值、本质、方向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弥补建国以来音乐教育在思想导向上过于依附于社会政治运动的倾向,面对音乐教学曾出现的“非艺术化”“专业化”等现象,能够从思想领域、哲学基础上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深层反思。但遗憾的是,在不少研究中——其中不仅包括音乐教育的哲学研究,也包括音乐课程研究以及教材教法的探索等——往往呈现出实践性不足,甚至是脱离实践、脱离音乐、空谈理论的问题。与理论著述的层出不穷相对照的是,广大音乐教育实践者对于音乐教育研究中花样翻新的说法褒贬不一。而来自教育部发布的艺术学习质量监测报告中透露的信息,却以冰冷的数据呈现出近乎尴尬的现实:中小学生的音乐素养检测的结果与期望目标相去甚远。①音乐教育研究似乎处在一个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如何协调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关系,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反思
多年来,音乐教育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脱节一直为学界所诟病。不少音乐教育研究脱离音乐本身谈教育,脱离音乐教学实践谈理论,导致理论研究空洞化。进入21世纪后,课程改革的步伐虽然加快,但是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层面一直是混淆不清的,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倾向尤其值得关注。
(一)音乐教育研究的“泊来主义”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校音乐教育自20世纪初逐步形成以来,从最初“学堂乐歌”时期对曲调、乐器、乐谱、西式基础音乐理论以及现代学校教育模式的引进,到后来在音乐教育体系方法、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等领域的借鉴,一直是以向西方学习为主要特点的,这一特点甚至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延续。应当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西学东渐思潮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洋为中用”的文化政策以及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之社会背景的影响下,这一特点本身自有其基于特定阶段国情、历史语境的合理性一面。也必须要承认,在今后,“西方音乐教育理论、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仍然是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重要参照”②。然而吊诡的是,或许是由于这个“源远流长”的历史惯性,在“西方中心主义”已经被摈弃的当代,音乐教育研究却依旧表现出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围绕音乐教育基本理论以及音乐课程、方法的研究,我们所听到的各种新名词、新说法,只要稍做分析便可发现,其来源大多是转引自國外——特别是北美的相关著述,并且已经形成了习惯性的研究套路。
在任何时候,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其中的关键在于“扬弃”,音乐史上几次关于“中西关系”的讨论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学者所建立的理论和方法,其学科侧重点是以其自身背景和兴趣为基础并为解决其自身问题而建构的,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音乐教育之所需。“盲目套用西方理论和方法是被动的‘传声筒行为。”③历史是发展的,那些基于国外历史文化语境的理论在与中国国情、民族性格甚至特定阶段历史空间的磨合中是否可以全盘照搬,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不少热衷于宣传、“舶来”国外理论的研究往往易于忽视基本的一点,那就是到中国最普通的学校去,实地查看、体验,亲自检验甚至实践操作自己的或是别人的理论。“泊来主义”式的音乐教育研究,加上不少人的盲目跟风,仅仅堆砌了表面上的繁华,与真正做到懂教学、会教学、将理念与方法落实到实际教学中尚有一段距离。
(二)音乐教育研究的概念化
概念是思想和行动的工具,也凝结着人们认识和实践的智慧。④毋庸置疑,在学术创新或音乐教育的改革中是需要出现一些新的概念的,但是如果把创造概念当成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就是另外一回事。⑤前文所及,近年来,音乐教育以思辨性研究为显著特点。有研究者统计过,2000—2010年这一区间的相关成果中思辨、描述性研究论文占到了定性研究总数的90.6%。⑥笔者所统计的近十年间(2011—2019)以“音乐教育”为主题的论文也仍然是以思辨性研究为主要特点。特别是其中不少论文都是依托于某种理论基础,在与研究对象“对接”后稍作演绎,貌似要标新立异,实则避实就虚,缺乏原创性。围绕音乐教育改革,新的概念层出不穷,不少研究成果热衷于引介、追随、移植所谓新理论、新观念,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却往往捉襟见肘。概念化的研究倾向是造成音乐教育研究空洞化的原因之一。
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有时是难以避免的,但即便是高度抽象化的哲学也应当时时刻刻以现实世界为映照,否则就将成为空中楼阁。某种程度上,哲学研究是基于假设和想象的,也需要假设和想象,这也意味着需要实践来摆脱(或弥补)形而上学的缺陷。而众多的相关研究是基于前人研究的研究,而不是基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并没有以丰富的一手材料——音乐教育实践为基础,由此而形成的“问题意识”也许就成为假问题。即便是一些更贴近于现实的对音乐课程、教材的研究,其实也倾向于以逆向的方式对观念、哲理进行重复性叙述。如此的研究取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究者的懒惰,也日益显示出研究取向与时代精神的某种不协调。
例如,一个常见的模式是:首先设定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它往往是一个看上去“新颖”的工具性概念,继而在此基础上与某个不甚理想的教育现实作比较,当这一比较出现不协调时,比如某种教学现实不能达到某一理念的理想状态,这时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了,研究的结论自然是针对这一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同样是基于该理论(概念)的假设,至于它放在现实的教育情境中是否真的奏效,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已经是后话。毕竟,作为研究,似乎论文写完了,就达到了研究目的。
概念化的研究表面上可以做到逻辑推理的“自圆其说”,但实际上研究者并没有参与到真实的教育场景中,而是抽身于实践之外对其做旁观式的指导。⑦这样的研究自然很难获得教育主体的兴趣与认同,层出不穷的新话语也使他们“在认识和实践上深陷这种概念丛林的无奈和苦恼。”⑧
三、音乐教育研究的双向交互范式
在学术辩论中,一些相对主义的观点有时会被人以极端的措辞提出来,最终导致非此即彼、甚至是混淆是非的结果。笔者一直坚持认为,在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中应当倡导辩证思维,以避免过于偏袒一方而造成认识和实践的偏激,以科学态度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有助于不断完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身份的音乐教育思想观念。⑨音乐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其“舶来主义”“概念化”等现象,促使我们需要做出某种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要舍弃已经取得并且还需进一步探索的某些进展转而追随另一种研究取向,而是在研究中采取辩证的、统筹的态度。我们既不能离开理论家们基于逻辑假设与推理而得出的思辨性成果,也不能脱离教育教学实践第一线的鲜活案例与经验。音乐教育既要有书斋式的思辨性探索,也不能离开实践取向的田野视界。
(一)音乐教育需要哲学审视
创新是需要概念的,概念世界或理论世界为人类社会指明前进的方向。哲学研究以逻辑分析方法研究抽象的概念及命题,建立在广博的专业书本知识基础上,善于借鉴前人累积下来的理论成果,能够将认知建立在人类对过往历史知识的抽象概括之上,以宏远的哲学视野分析问题并对未来做出预判,这就是音乐教育研究的思辨范式(或理论范式)。它借助广泛的文献阅读,通过研究前人成果,归纳、演绎、推导出理想的蓝图并形成概念表达和解释话语。这一类研究注重对事物内部统一性的探求,但容易忽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或变动性。⑩从事哲理思辨的研究者并不一定从事基础音乐教学,一般很少或从不下基层,缺乏到中小学音乐教学的课堂去亲自身体力行的经历。因此,推崇人类学田野方法的研究者甚至将其称作“扶手椅上的研究”。
然而音乐教育仍然需要哲学研究。哲学指引着人类的方向,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状态。它可能是超现实的、超功利的,却能够为人类根本的价值与终极关怀提供思想资源。缺少哲学思考的音乐教育学,其理论思考与学术创新将无法突破形而下的局限,难以形成富有创见的视野与格局。因此,音乐教育不能没有哲学审视。但问题在于如何进行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是基于他者的历史,研究他者的哲学命题,然后再套在自己身上,还是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吸收借鉴他者的方法,研究关乎自身发展的哲学命题?
我们知道,不论贝内特·雷默、戴维·埃利奥特或是其他业已纳入我们视野的理论家们,他们提出的理论都是以各自所处的社会情境——比如西方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自律或他律的艺术思潮以及本国特定社会文化与政治气候等——为基础的。西方音乐教育思想观念的不同取向中,有的強调作为艺术的音乐,有的强调作为文化的音乐。不同取向的涵盖面有宽有窄,大都会基于各自的教育目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具有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意义。但是将其进行理论上的“站队”继而对立起来看待,体现的却是“二元论”的思维定势。
在日本音乐学家德丸吉彦看来,音乐都是具有民族性的。?輥?輯?訛音乐教育是“音乐”的教育,由此可见也是具有民族性的,而民族性则意味着特定的历史意涵与文化属性。如果剥离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属性,以他者的概念研究他者的哲学命题,所得出的概念就可能无法在自身的土壤上生存。西方理论和概念的经验基础是西方本土的教育经验与事实,?輥?輰?訛而儒家传统却有一种超越学术的强烈实践性和政治化倾向,?輥?輱?訛两者有着质的差异。将外国概念与中国实践简单对接,是一种把不同于西方的“局外人”假定为与西方学者相同并采取相应态度的界定。对此,周文中先生认为:“现在国内只讲西方,你讲西方时髦的东西他们(西方人)都懂,你讲中国的东西他们不懂,我认为中国音乐教育的态度要转变。”?輥?輲?訛周先生虽然身居西方却并不崇拜西方,一生保持着特定的民族文化身份,才使得西方音乐家有兴趣与之交往和对话。因此,在进行哲学研究时,需要立足于我们自身的传统历史文化,才能防止产生认知的错位。
(二)音乐教育亟待实践研究
音乐教育研究的实践取向,要求研究者“以具体行动的方式升华理论,以合作参与的方式介入实践”,?輥?輳?訛要运用感官的触角去倾听、观察、捕捉音乐教学的现场细节,以更具现实性的理论解释音乐教育现象,指导音乐教育实践。
将正在发生着的教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场域,是实践研究的重要特点。研究者在与教师的交往中掌握音乐教学的实际知识,不断丰富各地域、各层次学校音乐教学的感性积累,通过实地观察音乐教学实况、对师生进行问卷调查以及查阅有关学校音乐教学的历史档案和相关数据等途径进行经验材料的采集。研究者要了解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广大基层音乐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以及他们所采取的个性化的解决方式,要通过了解、参与基层音乐教学中丰富多样的教研活动和体验各具特色的教学案例反思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取向实际上早有先例。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晚年卸下职务,躬身小学音乐教学,以实际行动寻求音乐教育的解决之道。在国内,杜亚雄、王安国等前辈频繁深入教学一线,以实实在在的田野工作来践行音乐教育。
音乐教育研究首先是对音乐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对音乐的教育及其研究,脱离音乐的音乐教育研究是靠不住的。音乐教育的实践取向,既包括教育(形式层面),也包括音乐(内容层面)。音乐教育的目的是引导学生认识、表现、创作以及运用音乐,问题就在于什么是音乐?长期以来,我们将音乐的定义局限在“艺术作品”的范畴,音乐教师或多或少也都具有这样的学科背景。然而,我们所面对的音乐世界却并非如此单一,在现行音乐课程的叙述中,这种丰富性实际上也得到了体现。我们以何种路径来实现这一丰富多维而包容的课程理念?奥尔夫、柯达伊、达尔克罗兹、铃木等人所建构的音乐教学体系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践行着用音乐培养人、塑造人并进而服务社会的教育目标,都蕴含着朴素的音乐人类学理念,但也因其体系化、工具化而具有一定封闭性,尚未发展为充分的音乐实践。从事音乐教育及其研究应该建立在了解音乐的生成、维持与运作机制的基础之上,关于这一点,音乐人类学已经为音乐教育做了理论准備。
“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理念重视音乐的体验与感受,这与音乐人类学提倡的将音乐“作为音响体验”的观念其实是一致的。将“作为社会体验的音乐”和“作为音响体验”的音乐结合起来,既符合审美音乐教育的初衷,也与音乐人类学的学术立场吻合,不仅如此,也消除了课堂音乐教学与社会音乐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音乐人类学非常重视田野工作,而这一点也与音乐课程是内在地一致的。鼓励音乐实践(音乐课程基本理念之一)自然也包括了课堂之外的音乐实践,教师和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田野,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了解社会生活中的音乐。
结 语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很多专业都是借鉴西方理论框架建立起来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原有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已经有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音乐教育的现实困境及音乐教育研究所存在的“舶来主义”“概念化”等现象促使我们需要对现有学术体系进行反思。
音乐教育研究既要有思辨性探索,也亟待丰富扎实的实践研究,将两种研究旨趣有机结合、相互映照、彼此印证,这就是音乐教育研究的双向交互范式。倡导哲学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双向交互,不仅有助于将音乐教育哲学、教育学与音乐人类学及教学实践互相打通,以开放的视野借鉴他者研究成果,也有助于将研究基础建立在自身历史语境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以此寻求中国音乐教育研究更为恰切的学科定位与文化定位。
①姜澎《教育部:全国六成小学生、近七成中学生唱歌跑调!是天生的还是音乐老师没教好?》[J/OL]文汇网,2018年10月11日访问。
②李燕《音乐人生与音乐教育——王安国访谈录》[J],《人民音乐》2019年第6期。
③曹本冶主编《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④?石中英《穿越教育概念的丛林》[J],《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年第6期。
⑥王东雪《定性、定量和混合研究:中国音乐教育研究的三种取向——基于对CNKI(2000—2010年)论文的分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⑦吴原《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与教育创新》[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⑨严永福《艾里奥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探微”——兼论音乐教育哲学的中国视角》[J],《人民音乐》2014年第11期。
⑩彭荣础《思辨研究方法:历史、困境与前景》[J],《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第5期。
[日]德丸吉彦《民族音乐学》[M],王耀华、陈新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页。
戚务念《论中国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向》[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张振涛《中国学人的身份定位与“局内、局外”观》[J],《音乐研究》2018年第3期。
林菁《有感而发的创作──作曲家周文中访谈录》[J/OL],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VXMIdQnYNArd9QLdUyapxQ 2019年10月27日访问。
吴原《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与教育创新》[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严永福 博士,淮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刘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