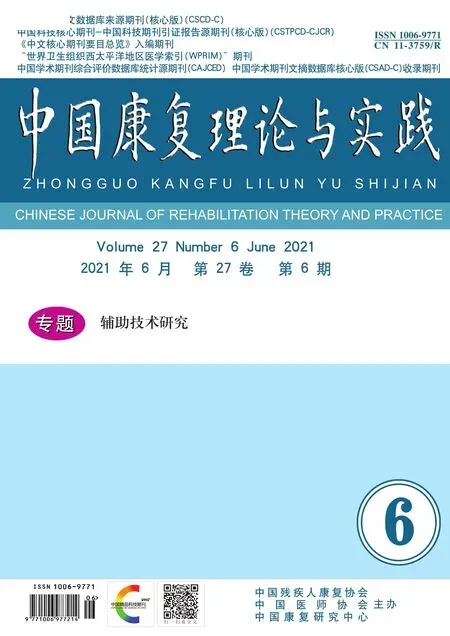三氧疗法在卒中后肺炎康复治疗中的潜在作用
张倩,席家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北京市100144
脑卒中对全球卫生保健系统和社会造成重大负担[1]。除神经功能缺损外,卒中后呼吸道感染和尿道感染等并发症也对患者的进一步康复构成障碍,并增加死亡风险[2]。脑卒中相关感染,特别是肺炎,与不良预后独立相关[3]。细菌性肺炎是最常见的并发症[4]。
1 卒中后肺炎的特点
微生物学数据显示,卒中后肺炎大多数为早期发作的医院获得性肺炎或社区获得性吸入性综合征。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革兰氏阴性细菌,如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杆菌或肠杆菌属等最为常见[5]。
患者的临床状况,如卒中严重程度、保护性反射受损、吞咽困难、机械通气及其他医源性侵入性操作等,影响卒中后肺炎的感染率。由于缺乏保护性反射,患者的误吸风险增加,并与意识障碍程度有关。大多数卒中相关性肺炎由吞咽困难和随后吸入口咽或胃内容物引起的。但临床上,约一半卒中后肺炎患者没有吞咽困难;同时,约一半健康成年人睡眠时发生误吸,但不会发展为肺炎[6]。这意味着还涉及其他机制,如脑卒中诱导的免疫抑制[7]、对感染的易感性和全身性抗炎反应[8]。
中枢神经系统通过自主神经系统感知体内炎症,并在发生全身性感染或受伤时产生强烈的反调节反应;这种反应本质上是抗炎和免疫抑制的,可以被认为是适应性反应,有助于遏制因感染和损伤引起的炎症。脑或脊髓损伤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炎性介质,或破坏神经免疫相互作用的控制信号,这两种情况均可能导致固有和适应性免疫系统下调;而在没有周围炎症刺激的情况下,这会导致人体防御系统严重缺陷,使宿主易受微生物侵袭[7]。
卒中后肺炎的治疗通常是经验性的,非插管患者可能难以获得下呼吸道培养物。目前除护理和功能训练外,预防性抗生素也应用于临床实践。系统综述表明[9],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可降低卒中后肺炎的风险,但抗生素治疗对脑卒中患者的死亡率没有显著影响。故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推荐急性脑卒中后常规预防性使用抗生素[10]。
2 三氧疗法
三氧(O3)是由3个氧原子组成的特殊分子,是氧(O2)的同素异构体,因特征性刺激气味,又名臭氧,具有极强的氧化性。三氧疗法基于医用剂量O3与体液混合后产生的各种生物学效应,目前用于50 多个病理过程的治疗。三氧疗法结合O2-O3混合物,具有不同的治疗剂量[11]。三氧疗法给药根据治疗目标和治疗部位而不同,目前常用O3自体输血(ozonated autohaemotherapy,O3-AHT),其优势是取预定量血液,经计算,可以注入精确的O2-O3混合气体。少量血液在体外与O3发生快速反应,产生各种生化产物后,输回患者。其他治疗方式包括通过肌肉、椎间盘内和椎旁直接注射给药。直肠注入是另一个常见的给药方式。经鼻、输卵管、口腔、阴道、膀胱、胸膜和腹膜腔灌气是需要慎重选择的给药途径[12]。
临床试验证明[12-15],O2-O3疗法在心血管、外周血管、神经系统、退行性病、骨科、胃肠道和泌尿生殖系统病理方面的有效性,包括多发性硬化症[16]、纤维肌痛[17]、糖尿病/溃疡[18-19]、皮肤疾病/伤口愈合[20-21]、传染病[12,22]、口腔科[23]以及骨髓炎[24]。
根据O3靶向相关分子机制,试图寻找这些过程是否与卒中后肺炎发病机制相关,以推定其治疗靶标,为卒中后肺炎中应用O3治疗进行理论准备。
3 三氧疗法作用机制
O3是一种三原子气体分子,在自然界中是由于射线与大气中的O2反应产生,性质很不稳定,极易分解成O2和氧原子(O),常温下O3半衰期为20~30 min。天然的O3能阻挡紫外线,保护人体免受伤害。人体也会产生氧化剂攻击入侵的病原体,除过氧化氢、超氧化物、次氯酸盐和O2外,还包括O3。人外周血分离的带有抗体的中性粒细胞,可通过水氧化途径催化O3生成,从而有效杀灭细菌[25]。O3有免疫调节和抗炎、抗氧化活性,有抗菌、镇痛、促进氧合和血管舒张作用等[12,26]。
3.1 免疫调节及抗炎
O3和其他医用气体,如一氧化碳和一氧化氮具有双重作用,具体取决于剂量和细胞的氧化-还原状态。O3很容易溶解在血浆的水中,并被亲水性抗氧化剂(如还原性谷胱甘肽、抗坏血酸和尿酸)作为牺牲性化合物而部分(20%~40%)淬灭,大部分与多不饱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PUFA)反应并由白蛋白运输[27]。治疗范围为10~80 μg (0.21~1.68 μmol)/ml,以产生精确微小的氧化应激,从而引起无毒性的功效。O3是一种前药,在反应过程中快速消失,产生两个重要产物:过氧化氢和脂质氧化产物(lipid oxidative product,LOP),最终以4-羟基壬烯(4-Hydroxynonenal,4-HNE,来自ω-6 PUFA)和4 羟基-2-己烯(4-hydroxy-2-hexenal,4-HHE,来自ω-3 PUFA 的反式)的形式存在[28]。
过氧化氢容易扩散到免疫细胞,同时也是信号转导中的调节步骤,促进多种免疫反应[29-30],特别是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和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的增加;IL-2 增加会启动免疫反应[31]。另外,过氧化氢激活核因子-κB (nuclear factor-κB,NF-κB)和转化生长因子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从而增加免疫活性细胞因子的释放,上调组织重塑。过氧化氢增强酪氨酸激酶活性,磷酸化IκB (NF-κB 的一个亚基)[32],介导NF-κB 作用。低剂量O3抑制前列腺素合成,释放缓激肽,增加巨噬细胞和白细胞分泌物,促进过氧化氢和一氧化氮水平,从而刺激IL-8 增加。IL-8还激活NF-κB。动物实验显示[33],使用O3可减轻和预防大肠杆菌诱导的肾脏系统炎症反应。
低剂量O3可促进单核细胞形成和T 细胞活化。当T 细胞抗原受体(T cell receptor,TCR)识别入侵者后,TCR 相关的蛋白激酶(70-kDa zeta-chain associated protein,ZAP-70)分子发生酪氨酸磷酸化反应,激活磷脂酶Cγ1(phospholipase Cγ1,PLCγ1)[34],产生两个关键的第二信使:肌醇三磷酸酯(inositol triphosphate,IP3)和二酰基甘油(diacyl glycerol,DAG)。IP3与其位于内质网膜上的受体IP3r 结合,导致Ca2+从内质网进入细胞质;细胞质中Ca2+升高激活钙调磷酸酶,从而使活化T 细胞核因子(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ed T cells,NFAT)脱磷酸化并将其转运到细胞核中。NFAT 诱导细胞因子转录,如IL-2、IL-6、IL-8、TNF-α 和干扰素-γ,同时还有DNA 上的免疫应答元件。这些细胞因子具有促炎和趋化作用,促进嗜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其他炎性细胞聚集、浸润,并增强其吞噬能力,以杀死局部病原体[33]。NFAT 也可以在其他细胞和组织中表达,自身也可以与DNA 结合。NFAT 与DNA 的结合主要通过核转录因子激活蛋白-1(activator protein-1,AP-1)共存诱导。AP-1 通过促分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途径激活,从而激活免疫应答[28]。过氧化氢是一种活性氧,可以充当O3的信使[35],诱导NFAT或AP-1激活,从而刺激先天免疫系统,帮助细胞免于损伤。
由O3引起的中度氧化应激会增加核因子-类胡萝卜素2 相关因子2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derived 2-like 2,Nrf2)活化,Nrf2 激活抗氧化反应元件(anti-oxidative response element,ARE)的转录,即Keap1/Nrf2/ARE 信号通路,调控抗炎基因表达,抑制炎症进展[36]。诱导ARE 转录后,各种抗氧化剂酶响应O3的短暂氧化应激,水平升高,如过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S-转移酶、过氧化氢酶、血红素加氧酶-1、NADPH-醌-氧化还原酶和热休克蛋白,它们与临床多种疾病的自由基清除有关[12]。
3.2 刺激氧代谢和调节血管
O3是O2跨膜流动的刺激物。三氧疗法继发细胞内O2含量增加,使线粒体呼吸链更有效[33]。O3-AHT 可增加红细胞果糖磷酸激酶活性,从而增加糖酵解速度,进而增加ATP 和2,3-二磷酸甘油酸酯(2,3-diphosphoglycerate,2,3-DPG),2,3-DPG 使血红蛋白解离平衡偏移,从而增加组织中O2的输送。再加上一氧化氮合酶活性增加,O3-AHT 刺激区域灌注明显增加[37]。反复治疗可产生足够LOP,到达骨髓,作为应激源,促进红细胞生成和抗氧化酶上调。O3也引起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减少,并协助氧化细胞色素C。
O3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以及向缺血组织输送氧气[38],增加抗氧化酶纠正慢性氧化应激可增加成红细胞分化,导致红细胞增加,即“氧化预处理”[39]。此外,O3诱导产生血管舒张剂前列环素[31],并通过血管内皮细胞刺激一氧化氮产生[40]。这些事件有利于微循环水平血管扩张,降低周围血管阻力。
4 三氧疗法应用于卒中后肺炎
卒中后肺炎的发生与环境(如患者所处空间及医源性侵入性操作)、病原体致病性、患者免疫与屏障功能受损相关。以下发病机制可能与O3治疗靶点对应。
4.1 免疫和抗炎作用
卒中后肺炎最常培养出的细菌为需氧革兰氏阴性杆菌和革兰氏阳性球菌,包括肠杆菌科(肺炎克雷伯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链球菌[6,41]。随着抗生素的滥用,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变得越来越普遍,也时常可以看到多重耐药细菌。念珠菌通常代表定植或气管受累[42]。与非卧床患者相比,大约75%危重患者感染革兰氏阴性杆菌[43]。在革兰氏阴性菌中,脂多糖似乎起了重要作用。
脂多糖与其主要受体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s,TLR-4)结合[44]。细胞内衔接蛋白(如MyD88)与TLR-4 结合并激活涉及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和p38 等多种细胞内信号级联反应;TLR 激活巨噬细胞,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包括TNF、IL-1β 和IL-6,协调局部和全身炎症反应。TNF 和IL-1β 依次激活局部内皮,诱导血管舒张,并增加血管通透性,使血清蛋白和白细胞募集到感染部位。此外,内皮上组织因子(也称“凝血因子Ⅲ”)增加,导致局部凝血级联反应,有助于防止微生物通过血液传播。IL-1β 和IL-6 一起激活肝细胞,产生急性期蛋白,这些蛋白质激活补体并调理病原体,以便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吞噬。这些信号的表达通过NF-κB途径激活[45]。
微生物病原体可以通过多种致病方式,使机体感染。大肠杆菌使用效应子逃避先天免疫应答。效应子之一OspG 与泛素化E2 蛋白结合,可阻止NF-κB 亚基-α (IκBα)抑制剂降解,从而抑制NF-κB 活化[46]。OspB 与OspF 作用,通过招募宿主因素改造染色质,降低IL-8 水平[47]。总体上,效应子减弱炎症反应,使细菌得以长期存活[48]。肺炎克雷伯菌免疫逃避策略的重要手段为阻止由NF-κB 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s)控制的TLR依赖性激活:克雷伯菌可劫持去泛素化酶cylindromatosis (CYLD)和MAPKs 磷酸酶MKP-1;在组织水平,克雷伯菌利用IL-10 的抗炎特性塑造局部微环境,通过限制炎症反应实施免疫逃避[49]。铜绿假单胞菌的鞭毛、脂多糖和4 型菌毛有高度炎症性,可被宿主模式识别受体(如TLR)识别,通过NF-κB信号通路引发炎症反应[50-51]。
动物实验证明,脑卒中导致与菌血症和肺炎相关的细胞介导免疫持续下降,如单核细胞失活、淋巴细胞减少、Th1/Th2转移,早期NK 细胞和T 细胞反应受损,尤其是干扰素-γ 产生减少,诱发关键性抗菌防御缺陷[52]。脑卒中患者T 细胞快速丢失和功能失常是常见变化,与脑缺血后免疫抑制一致。脑卒中后,细胞免疫应答降低、交感神经活动增加,与较高的感染风险相关[9-10,53]。
O3可增加巨噬细胞和白细胞分泌,增强粒细胞吞噬能力,促进单核细胞形成和T 细胞活化。过氧化氢诱导NFAT 激活,启动免疫系统;同时通过Keap1-Nrf2-ARE 信号通路产生抗炎作用。与野生动物相比,Nrf2-/-动物表现出更严重的炎症和组织损伤,推测Nrf2 信号传导途径在炎性疾病中具有保护作用[54]。激活肺泡巨噬细胞Nrf2,可对肺部炎症产生保护作用,阻止向肺气肿发展[55]。
4.2 改善血液循环和氧化预处理
O3改善血液循环和向缺血组织输送氧气的作用,以及2,3-DPG 水平增加、谷胱甘肽还原剂增加,我们推测O3处理可以部分改善因炎症受损的氧化代谢。O3通过增加Keap1-Nrf2-ARE信号通路中的抗氧化酶,纠正慢性氧化应激,增加成红细胞分化,导致红细胞增加,即氧化预处理。同时通过前列环素和一氧化氮的产生,改善微循环。
5 小结
三氧疗法可能对卒中后肺炎有效,减少抗生素使用。机制主要归因于免疫和抗炎系统激活,细胞抗氧化酶活性上调,血小板生长因子释放增强,血液循环和O2递送改善组织氧合,增强新陈代谢[25]。Nrf2-ARE、NF-κB、NFAT、AP-1 等是O3发挥作用的主要信号通路。这种疗法没有副作用[56-57]。可进一步通过临床试验证实其疗效。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