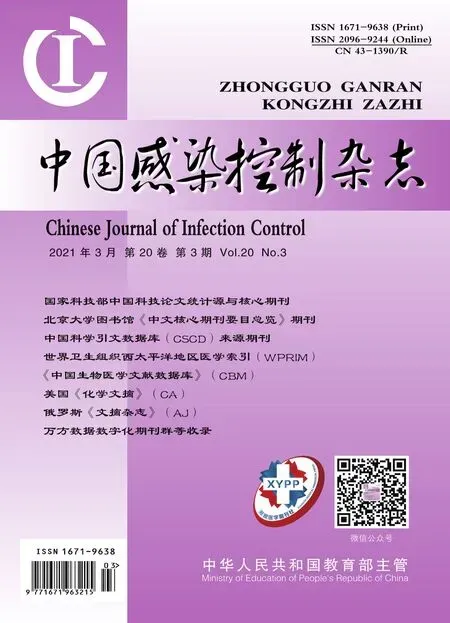智能机器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用探索
李少强,刘 浩,郭文亮,周圆圆,李时悦
(1.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广东 广州 510120; 2. 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16)
自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武汉暴发并在全国迅速蔓延,至2020年3月全国有3 019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1 716名确诊为COVID-19,其中存在大量职业暴露导致的感染[1]。COVID-19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医护人员在救治患者时,处于相对密闭的环境,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也可能通过气溶胶途径被感染,对患者进行呼吸支持治疗时,与患者近距离接触,尽管有标准的职业防护,但仍面临着较大的感染风险、工作负担和心理负担[2]。
如果有可以远程操控或者全自动化机器人替代医务人员工作,参与到COVID-19战疫之中,可减少医护人员与感染患者近距离接触的时间,以及暴露于空气中高浓度飞沫、气溶胶的时间,从而降低潜在感染的风险,减轻医务人员心理负担、工作负担,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减少医源性交叉感染的概率。面对疫情,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2月初,工信部发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协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倡议书》,促进、推动智能机器人更好地投入抗疫行动中[3]。庆幸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陆陆续续已报道有多种机器人参与到临床、护理、检查、生活工作中,如超声机器人、咽拭子采集机器人、消毒机器人、保洁机器人、物流机器人等,现将智能机器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用情况逐一介绍。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还将有插管机器人、支气管镜机器人、搬运机器人等投入使用。
1 治疗方面
目前,智能插管、吸痰等呼吸支持治疗机器人仍处于研发阶段,国内外较少报道此类智能机器人运用于实际临床。
1.1 吸痰机器人 2013年,日本ULVAC机工株式会社开发了不影响患者人工气道呼吸状态的自动痰液吸引系统,但由于操作不便,吸痰位置局限于人工气道口等,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均未能完全替代人工吸痰操作[4]。2015年,谭文君等[5]研发了智能吸痰机器人,采用机械臂和手的仿真转动模拟真实吸痰动作,在模型上可有效吸出模拟痰。该团队根据前期的实验,改良了吸痰机器人运动单元机械臂,机械臂吸痰操作过程中较前更稳定,送管成功率较前提高。
1.2 插管机器人 2010年,Tighe等[6]首次提出气管插管机器人概念,运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对人体模型完成气管插管操作,但此设备庞大昂贵,仅能在手术室麻醉状态的插管中使用。2018年,王新宇等[7]研发远程ETI,研发出小巧灵活和便携的远程机器人辅助插管系统(RRAIS),并进行动物实验,机器人系统在绝对数字上比人工直接喉镜插管获得了更高的首过率和总体成功率。
国内外研究通过人体模型或动物试验验证了吸痰、插管机器人系统的可行性和较高的成功率,但这些插管机器人仍处于半自动阶段,需要人工将机器和气管插管放入口中等操作,不能实现完全的、无人工干预的操作,在传染病疫情中使用价值有限。
2 护理方面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湖北各地疫情呈爆发式发展,当地医疗资源出现明显短缺。同时,湖北省武汉市的医护人员作为抗击COVID-19第一线的战士,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8]。种种因素影响下,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影响。在此情况下不禁思考,当今智能化设备种类繁多,关于医疗机器人也有报道,在抗疫第一线能否通过使用智能机器人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现将现有的医疗机器人介绍如下。
2.1 静脉穿刺机器人 通过静脉穿刺输送液体或获取血液样本是最常见的临床常规操作。医护人员往往依赖手工静脉穿刺技术,但其成功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者的操作水平和患者的生理表现,在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肥胖患者身上操作对操作者有更高的要求。2000年,Zivanovic等[9]报道其研发成果,一种自动采集前臂血样的机器人系统,并讨论了初步结果,证明该系统的可行性。2009年,Zivanovic等开发的采血机器人Bloodbot,根据不同的组织弹性,利用手臂静脉探测器,将目标静脉和周围组织区分开来,精确定位静脉穿刺点,但其需要医护人员调整扎针机器部件的倾斜角度。Richard Harris在2010年开发了一种采血机器人VEEBOT,采血准确率可达83%[10]。Balter等[11]研制的机器人静脉穿刺装置,采用近红外和超声成像技术扫描选择合适的注射部位,并采用9自由度机器人根据图像和力引导将针头插入血管中心,还开发了一种医疗设备,通过抽血和在护理点以全自动方式提供诊断结果,实现端到端的血液检测,将一个图像引导的静脉穿刺机器人与一个执行诊断分析的微离心和光学检测平台相结合。
2.2 配药机器人 配药是每个护理人员都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抗疫一线,由于病患多,医护人员紧缺,操作环境差等因素,工作隐患较多,其中在静脉输液配药过程中,往往存在保护不足,药物污染、空气污染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隐患。国内2017年周宏珍等[12]研究结果表明,与人工相比,智能静脉用药配置机器人的配液效率和精确率更高,且极大地减少了由于配药环节造成的职业损伤,但该研究存在研究对象较为局限,研究时间较短等缺点。
上海市仁济医院日间化疗中心尝试使用机器人护士进行配药,护理人员只要从电脑中调取患者需要的处方二维码并准备好药剂、输液袋等设备,机器人护士就会在完成扫描后立即进行配药,会按照设置确认每瓶药的定量配置,同时在上面完整的将患者信息、药品名称以及具体用法都标记清楚,整个过程仅花费1 min,快速且精准[13]。可见配药机器人的使用能够提高护士工作效率,减少药物残留和配药错误的发生;药液配制过程中人与药物完全隔离,减少护士暴露机会,减少医院感染发生;工作效率提高后,护理人员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患者的其他服务。
2.3 饮食护理机器人 早在1998年Mike Topping公司就已研制出第一款低成本商业康复机器人“Handy 1”,该机器人包括一个5自由度的机械臂和1个激光扫描系统,可用于多项任务,包括喂食辅助。
国内饮食护理机器人的研究相对落后,2006海军工程大学研制出可控式用餐机,同年哈尔滨工程大学研制出一款新型助餐机器人My Table,但是二者都需进一步完善才能实现产业化[14]。2012年李彦涛[15]提出助餐机器人样机研制及控制研究。尽管饮食护理机器人对于重症及残疾或老年患者能够提供必要的帮助,减轻医护人员负担,使得医护人员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临床工作中,但此类机器人存在一些缺点,如售价高,功能较单一,便携性和对不同使用环境的适应性不足等。此外,机器人的安全性有待提高。
2.4 其他 除上面三大类护理机器人,笔者还发现许多其他类型的护理机器人,这些机器人也具有应用于临床工作的潜力。如监控机器人不仅可用作家庭服务机器人,也可以用来减轻护士对患者的持续检查和生命体征的记录。尿液输出监测系统用于监测患者的尿液输出,在紧急情况下发出警告,并自动清空样本(Otero、Apalkov、Fernández和Armada,2014)。另外,2013年Kuroda等[16]提出了一种临床传感器网络系统,该系统可以代替护士完成输入数据的任务,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提高了护理过程的效率和安全性。Kangasniemi等[17]提到一种智能静脉泵,目前主要用于注射放射性制剂,可提高整体护理满意度。2019年国内刘文勇等[18]研究指出,目前有一家医院和两家护理机构正在试用护理服务机器“智能护理车”(intelligent care cart),该款智能护理车采用模块化设计,医护人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将其召唤到所需的房间,并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快速进行配置。可见现今关于护理机器人的研究繁多,成果显著,甚至部分护理机器人已经成功产业化。在疫情一线医护资源紧缺,医护人员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有效灵活地使用智能机器人具有缓解人员紧张情形,使得医护人员能把精力投入最需要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弥补护理工作不足等优点。
3 检查方面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投入抗疫战斗检查的机器人有超声机器人和咽拭子机器人。
3.1 超声机器人 超声检查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诊断工具,其具有非倾入性、价格便宜、可移动便携、不产生电离辐射等特点,被广泛应用在临床检查中。超声机器人还具有的以下优点:(1)可以将超声检查的时间提前,为危重患者的紧急治疗提供信息。在院前急救中,远程超声有助于实现快速检伤,可以增强医生的预诊能力,为抢救生命赢得时间。(2)可以实现无需出远门就在当地接受医疗专家的检查,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远程超声技术的实现,顺应了国家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补充了基层医疗资源,实现了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2018年刘延花等[19]比较超声机器人和传统超声检查的差异,检查42例志愿者的消化系统及泌尿系统,发现机器人法及传统方法的超声图像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机器人法较传统方法检查时间多6 min左右。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2020年2月全国首例5G超声机器人远程操作在浙江省人民医院成功实施,随后应用于湖北疫情一线[20]。
超声机器人在常规疾病诊断结果,以及获取的图像质量方面与传统超声检查有较高的一致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超声机器人具有对病人进行检查的应用价值。
3.2 咽拭子机器人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山大学对17例COVID-19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患者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不久即可在上呼吸道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载量[2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2]就将呼吸道拭子核酸检测作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重要的确诊标准之一,并且检测下呼吸道标本(痰或气道抽取物)更准确。
咽拭子机器人还具有以下优点:(1)采集简便、早期识别、易普及。上呼吸道拭子核酸检测只需30 s即可采集完成,无需借助任何仪器设备。在COVID-19此类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播时,对已有明显症状或重症患者进行下呼吸道样本核酸检测,其敏感性较强,而对早期发病甚至无症状患者进行检测,则其敏感性较差[22]。因此,呼吸道拭子核酸检测依然在基层排查和临床确诊工作中具有极高的优势和地位。(2)降低假阴性。尽管目前的学术观点认为鼻咽拭子的检测效能比咽拭子更高,但不同的病期、不同病情、不同部位患者病毒载量有所差异。研究[23]表明,同时采集鼻咽拭子和咽拭子并且增加采样次数能减少假阴性。另外,由于医务人员在采集咽拭子标本时直面患者口腔,担心患者飞沫和气溶胶会传播扩散病毒,容易在采集咽拭子时操作粗糙、或者取样时间较短,导致咽拭子假阴性[24]。若医务人员可与患者保持一定距离采样,能够更好地保护医护人员避免交叉感染,同时咽拭子智能机器人统一了采集的方式,势必能更加规范采样操作,获得更高质量的标本。(3)不良反应少,患者易配合。做鼻咽拭子时无法直视患者鼻腔、鼻咽内部,操作需要一定经验和手感,部分患者对鼻咽拭子耐受性差,不易配合,容易发生出血等不良反应,而咽拭子为可直视下操作,不良反应少,更容易让患者配合及接受。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首台咽拭子采样机器人由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钟南山院士团队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联合研制成功,并于3月开展了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机器人咽拭子采样可以达到较高的质量且受试者无不良反应[25]。
4 生活管理方面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病患人数激增,以及民众的恐慌心理等,疫情严重的城市存在医疗场所拥挤,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对于医院的管理难度也大大增加。介绍几类机器人,其能协助一线工作人员解决部分生活管理问题,同时降低工作人员被感染的可能性。
4.1 消毒保洁 消毒保洁是一项暴露风险高的工作,尤其在疫情期间,无论是在户外场所或医院,工作者都有极大的暴露风险。消毒机器人在突发不明原因疫情中的应用具有特殊优势,其发展历史较长, 技术更成熟。国内2003年急性严重呼吸综合征期间王立权等[26]曾报道了一款“护士助手机器人”,隔离病区以外的工作人员通过摇控图像信号遥控机器人,机器人到达隔离病区的任何位置完成垃圾处理并对相应地点进行清洁消毒,还可以运送医疗器械和设备,运送试验样品及试验结果,为患者送药品、送饭及生活用品等。据媒体报道,已有多款消毒机器人投入武汉一线使用,国产的多型智能化机器人如钛米智能消毒机器人,以及国外如丹麦UVD消毒机器人等[27]。同时,也有以往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无人机用于远程测温、空中喷洒消毒等[28]。智能机器人的使用,减少了医护人员与被污染物品和环境的接触,降低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可能性。
4.2 派发物品 早在1989年美国就开始使用一款移动式护理机器人“HelpMate”,负责将餐盘从餐厅送到护理站,其拥有避障和自主导航等功能,能有效完成医用物品等运送任务[29]。继而陆续有各种负责病房分配食物、药物以及取走垃圾等机器人诞生。这类机器人代替医护人员派发物品、食品、药品,使医护人员能将更多精力投入患者的治疗和护理。
4.3 搬运 在国内,患者的转运仍然沿用传统的方式,依靠医护人员或家属将患者抬、扶、抱到担架或轮椅车上,需要2~3名护理人员共同操作才可以完成。一方面,一些重症患者或者残疾患者在搬运过程中如果操作不慎,易引起患者的再损伤,甚至生命危险。另一方面,经常抱、抬患者,加重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长此以往也会危害到护理人员的背部骨骼和肌肉,发生腰肌损伤。2009年张西正等提及日本机械工程研究所开发的“MELKONG”护理机器人,专门用来照顾那些不便走动的患者,该机器人可以轻松而平稳地将患者从床上托起,并将其送往卫生间、浴室或餐厅[30]。还有一系列机器人,如机器人Robear可以将老人从床上带到轮椅上,为日常生活提供基本护理;SAM具有看门的功能,还可导航、监控、远程监测摔跤风险等[31],可以帮助患者传递物品,不仅方便了患者,还有利于医护人员将更多的精力从繁杂的事务中转移到患者的疾病恢复和心理关怀上。
5 疫情宣教与引导防控相关的机器人
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由于疫情的蔓延,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所以,加强有效的社会科普,能加深人民群众对疾病的认知及了解,减少社会的恐慌。以下类型的机器人用于疫情宣教与引导防控。
5.1 引导防控的智能机器人 2020年2月,阿里巴巴推出的客服智能对话机器人[32]与多个省市政府的卫健委合作,该类机器人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在线疫情知识问答”,无停歇地为所有咨询的用户提供全天候的准确回答,能有效缓解政府工作人员在抗疫期间的服务压力,提高全社会对疾病的认知,了解到最新的资讯,减少社会群体的焦虑。同样,随后投入使用的腾讯政务联络机器人也具有相关功能。
5.2 社区防控智能机器人 社区防控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环节,技术支撑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京东数字科技集团[33]与360金融分别在疫情暴发初期2020年2月已开发出智能外呼机器人、疫情问询机器人、良研问卷等智能工具,可对公众进行一对一的主动电话呼叫,用于排查、通知、回访,帮助疾控系统开展信息采集工作,大幅提高人工效率,包括流动人员排查机器人、本地居民排查机器人、特定人群通知机器人、政府工作上报和监督机器人定人群通知机器人、政府工作上报和监督机器人。
5.3 加强疫情宣教的智能机器人 加强全社会对疾病的认知有助于进一步的防控疫情,以往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无人机系统,疫情期间也在多个高风险地区进行疫情防控宣传教育[27]。如对不戴口罩、四处串门的居民进行劝阻,无人机将不戴口罩外出的居民劝回室内。
6 面临的困难与展望
诚然,智能机器人在疫情中应用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及挑战:(1)智能机器人应用成本仍较高;(2)智能机器人对网络技术要求高(5G/高速蓝牙等),不同地区网络技术存在差异;(3)医院应用涉及医院感染管理的要求;(4)医疗应用环境的复杂性等。
智能机器人可以减少医务人员工作量及交叉感染风险,面临的所有挑战都值得努力解决。未来,智能机器人智能化程度、远程操作的距离、精准化控制等将改进得越来越好。在满足医疗需求的前提下,智能机器人能更好地应用于治疗、护理、宣传。
7 结语
随着科技抗疫的全面开展,医疗与智能机器人的有效结合,深化应用于临床、护理、检查、生活管理、疫情宣教引导等,解决了很多医疗上难以突破的技术问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能带来1+1大于2的有利影响,值得重视以及推广。
致谢:感谢李时悦教授团队研究生蔡嘉慧、刘经伟、肖珠琳、郭祖源的调研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