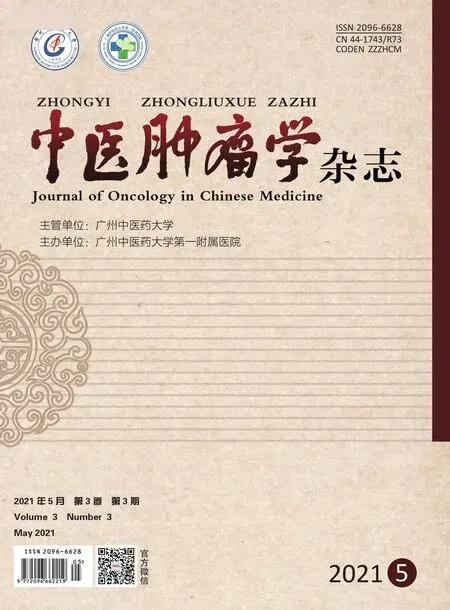在中医肿瘤学基础研究中运用系统生物学方法的刍议
王院春, 吴勉华, 惠建荣, 王希胜, 朱叶萍
1.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陕西 咸阳 712000
在20世纪生物医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美国科学院院士Leroy Hood[1]于1999年提出“系统生物学”的概念,并于2000年创立了第一个系统生物学研究所,他把这一学科描述为“研究一个生物系统中所有组成要素(如基因、mRNA、蛋白质及代谢产物等)的构成,以及在特定干扰条件下,如遗传、环境等因素改变时,所有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2,3]。系统生物学不是研究单个基因或蛋白质,而是利用高通量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平台,引入计算机科学、数学和统计学等方法,研究生物系统在遗传或环境等因素的干扰下,基因组、蛋白质组等各要素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同时,将这种变化的信息整合起来,建立以数学或图画来描述生物系统各要素及其关系的模型,从整体上帮助人们理解生命的逻辑和调控网络的秘密。系统生物学的核心特质是多变量的整合,力图实现不同干扰条件下对生物体从基因到细胞、组织、个体的多层次研究,从整体上解析生物系统的本质规律。中医学也是从先天、环境及社会等整体上研究人体和疾病,以联系的、运动的观点分析健康和疾病,辨证论治,与系统生物学在思维上有“异曲同工”之处[4]。有学者认为系统生物学的理念和方法可助力中医药学的研究发展,已有不少学者在此领域取得一定成果[5-7]。中医肿瘤学是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人类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类疾病的流行特点、学术沿革、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规律、辨证论治体系及预防康复等科学的一门临床学科[8]。相较于中医其它临床学科和现代医学的肿瘤学科,中医肿瘤学虽已具备理论体系、学术特征和诊治技术,但在医学日新月异的当下,其学术体系仍需不断完善,方法技术也需创新发展,笔者基于系统生物学思想与方法之考量,在中医肿瘤学发展方面略有浅识,兹述于下。
1 中医肿瘤学概况
1.1 发展历史概述
国医大师周岱翰认为中医肿瘤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医临床分科[8]。隋唐以前是中医肿瘤学的奠基时期。甲骨文中即有“瘤”之记载,《山海经》记载有治疗“恶疮、瘿瘤、噎食”等类似肿瘤疾病的药物,《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也奠定了中医肿瘤学形成与发展的基础,《难经》区分了“积”和“聚”,并对“五脏之积”的特点进行描述,《本经》记载治疗“癥瘕、恶疮、瘿瘤”等抗癌中药并沿用至今;《伤寒杂病论》创“六经”辨证体系、方证体系和抗癌方药,至今仍有鳖甲煎丸、大黄䗪虫丸等许多方剂应用于肿瘤临床[9];《诸病源候论》最早将癥瘕单独作为一类疾病设专候论述,并重视脾胃功能,注意顾护正气,为现代中医诊治提供了宝贵经验[10]。宋金元时期是中医肿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11]。这一时期病名、病因、发病、病机、证治、预防都有了新的发展,如提出了“癌”的概念,并认为“毒根深藏”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病因学说注意到“情志”因素,辨证论治逐渐形成;有官修方书载有大量方药,至今仍为肿瘤临床组方的参考;在治疗原则方面,易水学派、补土派强调养正,提出“养正积自除”的观点,攻邪派强调“达”“发”“夺”“泄”“折”五法,滋阴派推崇从痰论治等。明清时期是中医肿瘤学的成熟时期[12]。此时中医肿瘤学从病因病机、诊断鉴别、治则方药、技术手段等均已形成体系,许多医家在其专著中多有论述,如《外科正宗》等外科专著注重内外合治,已初具综合治疗的思想,《医宗必读》提出“初、中、末三法”分期论治,并明确攻补兼施用于治疗各类肿瘤,成为现今中医肿瘤学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渊源。晚清以来,是中医肿瘤学的现代化时期。如同中医学一样,中医肿瘤学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百年沧桑,但西学东渐也给中医肿瘤学注入新的血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肿瘤学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总结凝练、七八十年代的“减毒增效”,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医肿瘤学逐渐具备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学术体系、人才队伍和临床分科的实践基础,从中医内、外、妇、儿等学科中脱颖而出,成为现代中医学体系中一门独立的临床学科,结合现代科技,走上快速的现代化道路。曰其“古老”,确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曰其“年轻”,实因规矩方才,宏途肇启。
1.2 优势、特色与局限
中医肿瘤学具有绝对优势和鲜明特色,在当前肿瘤治疗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8]。首先,整体观念,强调人体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均是不同层次的“整体”,发生肿瘤均是由于不同层次“统一性”的破坏,如人体局部发生肿瘤是因为全身阴阳失衡,人与自然不相和谐会导致人群肿瘤患病率的升高,不同社会环境中人群肿瘤发病率也不同,在预防、治疗肿瘤时从整体出发,注重联系,调整、恢复整体的稳态或平衡。其次,辨证论治强调个体化、个性化治疗,主张“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需根据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等特点,结合季节、时令、地域、气候等各种特定条件确定治疗原则;还需根据肿瘤的类型、分期、证候等特点制定相应的治法、方剂和药物;近年还有结合现代影像、组织类型、分子检测等手段确定优势人群及选择特异方药等方法,也是辨证论治的具体体现。再者,中医肿瘤学具有以人为本的特色。诊断辨证注重正气,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治病”与“治人”紧密结合;疗效评价首先考虑人的生存状态和适应能力,如生活质量、生存期、心理健康等;在诊疗过程中注重医患之间的信息沟通,采用“望闻问切”等传统方法诊察疾病,通过药物、针灸、推拿、导引等方法治疗疾病,诊疗过程中充分调动患者的主体能动性,同时将医者的治疗目的、信息和能量传递给患者,这在针刺补泻中尤为突出。第四,道法自然的认识论强调世间万物都有其客观规律,认识生命和肿瘤都要遵循自然规律,以自然之理可以阐发生命和肿瘤的奥秘;由此而形成的“顺势思维”方法论强调在治疗肿瘤时要遵循邪正盛衰,顺势而为,如早期肿瘤,正气强盛,邪气尚弱,可强攻邪气,邪去正安;而晚期肿瘤,正气大亏,邪气鸱张,则需补养正气,扶正祛邪;又如,肝气以条达为补,胃气以和降为补,均需顺势而为[13]。
当然,事物总有其发展的局限性,中医肿瘤学也不例外。例如,中医肿瘤学的基础理论和经验方法均脱胎于中医基础及临床各科,理论的系统性有待完善[8],解释实践相对充分,但对具体实践的指导性有待加强;理论或经验方法多为定性,定量不足,精准不够[14],缺乏用现代科学语言如数据等描述界定的标准,可操作性还需提高;临床诊疗多为经验性,普遍接受或适用的规范体系尚未形成,包括疗效评价体系;科学研究不能体现整体性,缺乏系统性,中医属性弱化[15]。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唯有不断突破局限、完善自身,中医肿瘤学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与特色,实现新的蜕变。
2 系统生物学可为中医肿瘤学发展的借鉴和补充
相对于还原论为基础的研究体系,系统生物学更强调整体思维,注重各要素的整合,其研究思想、方法体系可以成为中医肿瘤学保持中医属性,发挥优势、特色,快速发展的借鉴和补充。
2.1 基因组学与中医肿瘤学
基因组学是对所有基因进行基因组作图、核苷酸序列分析、基因定位和功能分析的科学。检测肿瘤基因组的突变在预测肿瘤发生、选择治疗方案和判断预后方面意义重大。Brunner等[16]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对收集到的5例正常肝脏和9例肝硬化肝脏的组织样本构建出482个全基因组序列,发现肝硬化肝组织含有的突变数量是健康肝组织和肝细胞癌组织的两倍,相比于健康肝组织,肝硬化和肝癌组织中突变类型的多样性更大,解释了慢性肝病人群的肝癌风险增加是因为其中大量DNA损伤突变促进了有潜力癌变细胞的出现,对未来利用基因组学数据预测慢性肝病患者患肝癌的风险成为可能。WEDGE等[17]对前列腺癌标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whole genome sequencing,WGS)分析,新发现了5个编码驱动突变的基因,同时发现CDH12和ANTXR2基因的丢失与不良的生存预后相关。黄清洁等[18]基于二代测序技术(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对300例肺癌患者肿瘤组织中的驱动基因进行分析,发现EGFR可与其他驱动基因突变共存,这些突变与患者年龄、性别、吸烟史、组织类型等有关,还发现了一些低频突变的基因,改变了以往驱动突变独立、互斥等认识,对肺癌驱动突变的深入研究和临床治疗都有重大指导意义。
中医肿瘤学也从禀赋、体质、行为习惯等预测肿瘤的发生、决定治疗法则及判断预后等,如“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过饮滚酒,多成膈证”等。我们可借鉴基因组学的方法和技术,把中医学的禀赋、体质等概念进行结构化描述,赋予客观的基因组信息,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同一性,进而实现预测肿瘤发生、选择治法方药、判断预后等的客观可操作性。有学者论述基因组学技术已经在中医药基于体质的精准预防、个体化诊断等方面有较多应用,期待在中医肿瘤学领域将有更多深入的研究和应用[19]。
2.2 转录组学与中医肿瘤学
转录组学是研究细胞内所有基因转录情况和转录调控规律的科学[20]。基因的转录产物称为转录组,广义上指全部从基因转录的RNA总和,包括编码蛋白的信使RNA(messenger RNA,mRNA)和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ncRNA)。通过转录组学研究,可以揭示基因表达与生命现象的内在联系,解释基因调控机制和不同表达信息,对不同时间或环境条件下的生理病理现象提供基因表达谱的差异和调控信息。刘文琛等[21]通过高通量的转录组学检测和生信分析,发现急性缺血性中分阴类证、阳类证的lncRNA,miRNA,mRNA表达存在差异,并研究了不同类证的分子调控网络。王阶等[22]以冠心病血瘀证为切入点,采集312例患者外周血基因信息,运用转录组学研究技术,确立了冠心病血瘀证lncRNA-miRNA-mRNA 3个层面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构建了冠心病血瘀证miRNA-mRNA及lncRNA-miRNA-mRNA 2个水平的调控网络,基于差异基因和调控网络,对202例活血化瘀中药治疗前后共计400余人次的基因检测结果结合细胞实验,从基因-蛋白-功能3个层面揭示了活血化瘀中药干预冠心病血瘀证的基因调控网络机制。黄卉等[23]对小鼠脑肿瘤组织样本进行基因芯片检测,发现金龙胶囊组共有37个差异基因(倍数>2),106个拓扑基因,其靶点主要集中在细胞粘附和凋亡、免疫应答、神经发育等,金龙胶囊通过诱导神经细胞特有基因表达发挥抗脑肿瘤作用。
恶性肿瘤具有病史相对较长、演变复杂、异质性突出的特点,“证”的演变复杂多样,借鉴转录组学研究平台可探索中医肿瘤学病证联系规律、“证”的本质及演变调控规律,研究“证”的客观化或确定标志物,提供“证候差异、同病异证、同证异病”的分子依据等。转录组学研究还可以对中药复方、针灸等复杂体系的抗肿瘤作用机制研究提供技术支持[24]。
2.3 蛋白质组学与中医肿瘤学
细胞或组织的基因组所表达的全部蛋白质称为蛋白质组,相对于固定的基因组而言,蛋白质组因时间、地点和环境等各种条件的影响而呈动态变化,蛋白质组学[25]即是研究蛋白质组的构成、表达水平、功能和调控关系的科学,与中医学“整体观”和“动态观”趋同。蛋白质组是生物功能的执行体,其动态变化能全面反映生物体功能的改变。李晓亮等[26]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比较了人肺腺癌和癌旁远端正常组织的差异蛋白,发现癌组织和远端正常组织的蛋白质存在显著差异,并鉴定了14种肺腺癌相关的蛋白质,为肺癌的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奠定基础。丁峰等[27]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比较了肝郁证肝癌患者、非肝郁证肝癌患者和健康人唾液样本中蛋白质组的差异,发现3组人群唾液标本中蛋白质存在显著差异,以此建立了肝郁证肝癌特异的蛋白数据库,筛选出肝郁证肝癌演变可能相关的差异蛋白,为肝癌肝郁证证候本质及临床辨证提供客观证据。饶希午等[28]通过血清蛋白差异表达研究,发现益气养阴组与模型组差异表达的蛋白共116个,通过功能鉴定,明确这些蛋白与肝癌进展的多个环节和多条通路有关,确定益气养阴法的多靶点、多中心调控的作用。袁枝花等[29]学者认为蛋白质组学从整体研究的策略可显著提高中药作用靶点的发现效率,在中药现代研究中具有明显优势,并指出3种蛋白质组学技术在中药作用靶点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为中药作用机制的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中医学“司外揣内”的诊察方法有利于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但缺乏客观指标,我们可利用蛋白质组学的方法,以差异蛋白将外露的“象”与内在的“脏”之间建立客观联系,实现肿瘤的早期诊断;同一癌症不同“证”的演变规律对我们整体把握疾病、确定治则治法至关重要,我们可利用蛋白质组的整体性、动态性、多样性与中医学整体观、动态观、辨证观建立联系,对研究癌症病程中的证候本质和建立辨证体系很有意义;中医的治法治则多具有多靶点、多中心的调控作用,复方、针灸等的作用靶点非常复杂,蛋白质组学可以为治法治则、药物及穴位的调控靶点、作用机制研究提供思路借鉴和技术支持。
2.4 代谢组学与中医肿瘤学
代谢组学是从整体上全面、动态研究生物体或组织器官的小分子代谢产物的科学[30,31],主要关注基因调控、酶活性改变和代谢变化。代谢组学把研究对象看做整体,跳过体内具体环节,通过全面分析生物体或组织器官代谢物的种类、数量及动态变化,寻找差异,揭示生理或病理过程,发现其中的可能机制,具有活体研究、无创伤、与生理或病理过程相似等特点。江文俊等[32]利用代谢组学技术检测了中分化胃癌细胞系、低分化胃癌细胞系和正常胃上皮细胞系的代谢谱,发现了9种差异性代谢产物,有望成为胃癌潜在的肿瘤标志物,对胃癌的早期诊断和疗效评价具有重要的意义。巩振东等[33]运用代谢组学技术检测模型动物唾液中代谢物的变化,发现与正常体质组比较,肾虚体质组唾液中3种代谢物含量升高,肾虚证候组唾液中5种代谢物含量下降,与肾虚体质组比较,肾虚证候组唾液中1种代谢物含量升高,表明在“正常体质-肾虚体质-肾虚证候”的演变中,唾液中代谢物成分发生变化,这些物质可能成为肾虚相关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对阐明“肾虚”的实质提供客观依据,也有助于肾虚的早期诊断和防治研究奠定基础。方婷等[34]利用代谢组学技术比较了正常组、乳腺癌荷瘤组和乳腺癌荷瘤薏苡仁油治疗组小鼠的血清代谢谱,发现与正常组比较,荷瘤组小鼠有15种代谢物水平降低,1种代谢物水平升高,这些代谢物在薏苡仁油给药后均有显著回调的趋势,表明薏苡仁油可能通过调控体内花生四烯酸等4类物质代谢发挥抗肿瘤作用。
中医学素有通过“望、闻”排泄物与分泌物诊察疾病的方法,可以说是代谢组学诊察疾病的雏形,故可通过代谢组学技术对“望、闻”的内容继续延伸,建立中医肿瘤早期诊断和疗效评价的新体系;代谢组学技术还可助力确立恶性肿瘤及其不同阶段证候的生物标志物,赋予证候以代谢组学实质;代谢组学技术同样对研究中药复方、针灸等复杂体系的作用机制具有借鉴和补充作用。另外,代谢组学在发现新药[35,36]或新的治疗方法[37],预测肿瘤治疗效果等方面均已显示出优势,其对中医肿瘤学今后的发病机制探索、肿瘤预防和治疗、药物发现和机制研究等领域均有重大借鉴和补充作用。
2.5 多组学策略与中医肿瘤学
肿瘤是一类多因素、多环节、多阶段发生发展的复杂疾病,可能涉及到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等一个或多个水平的异常,且不同水平之间可能还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单组学研究对全面阐释肿瘤所涉及的问题具有局限性,多组学的研究策略可以从不同水平阐释肿瘤发生、演化、进展等复杂问题,现代高通量技术正好为多组学研究策略奠定基础,现代肿瘤医学已经开始实践[38]。通过多组学研究还可以发现药物的作用靶点、治疗起效的物质基础等,这种研究策略与方法正好同中医肿瘤学整体观念及复法大方治疗实践相吻合,借鉴这种策略和方法可以补充中医肿瘤学目前发展中的不足,启发新的研究思路,有助于学科快速发展。
多组学研究可以全面阐释肿瘤发生发展的具体机制。LI等[38]利用多组学分析不同类型非小细胞肺癌组织,发现在肺癌组织中丝氨酸羟甲基转移酶2表达上调,这一上调与染色体12q14.1位点的扩增有关,同时丝氨酸羟甲基转移酶2也与肺腺癌的转移和不良预后有关。苗华等[39]基于系统生物学整合技术挖掘发现细胞周期和增殖信号通路是结直肠癌发生中的核心通路,UBE2C和AURKA等11个基因是该通路的驱动基因。中医肿瘤病因病机的研究同样可以借鉴这种多组学策略或赋予多组学内涵。
在肿瘤诊断中,“见微知著”是中医诊断疾病的一种思维方式,多组学整合有望在“微”上实现客观化和定量化,有学者综述近年来多组学技术在口腔癌和其它肿瘤诊断中的优势和应用现状,提出多组学整合可成为口腔癌诊断的系统生物学研究借鉴,是实现口腔癌早期诊断的有效途径[40]。充分利用现代多组学高通量技术,赋予望、闻、问、切等诊查技术客观标准,是实现中医肿瘤学对高危人群早期诊断的有效途径,可使中医学“司外揣内”等诊察方法更具可操作性。
在疾病分型和精准治疗方面,国医大师王琦提出将系统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医体质学的研究,有助于从微观上探讨体质的本质,有利于建立量化的体质分类标准,同时为辨体治疗提供依据[41]。张继玲等[42]研究发现大肠癌患者最常见的体质类型为气虚质,其次为湿热质与气郁质,男性患者湿热质比例较高,女性患者气郁质比例较高,且体质分布情况与年龄及TNM分期密切相关。引入多组学技术有望实现体质、证型、阴阳、五行等疾病分类属性的系统化和客观化,也为肿瘤的现代中医精准治疗提供依据。
在研究中药、方剂的作用机制方面,多组学整合策略同样显示绝对优势。柳润辉[43]团队在国际上率先采用系统生物学的多组学方法进行中药方剂的多成分、多靶点作用机制研究,阐明麝香保心丸中药效成分之间的增效、减毒、维持血药浓度等相互作用关系,实现在分子水平整体阐明方剂的作用特点。半枝莲是临床最常用的抗癌中药之一,胡晨骏等[44]利用复杂网络算法筛选出与半枝莲最相关联的前100个基因、4个基因族和前10条KEGG信号通路,从系统生物学的角度挖掘半枝莲的潜在作用机制,并经过文献研究分析验证,相关结果与半枝莲的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高度一致,为研究人员利用多组学策略从整体水平研究半枝莲或其它抗癌中药的药理活性提供方法学参考。
此外,多组学研究方法还有助于中医肿瘤学的特殊概念客观细化、科学界定,对诊断、治疗的方法技术确定生物标志物、整体上阐明药物等的作用机制,对预后判断确定科学依据、便于临床操作。高通量的研究方法还有助于提高药物、腧穴等的筛选效率,发现新的治疗靶点。
3 结语
中医肿瘤学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在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预防康复观等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鲜明特色。然而,面对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生物医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医肿瘤学在理论创新、研究方法迭代、技术精准化以及与现代科学的相容性方面均表现出局限或不足,遇到新的挑战。系统生物学全面、动态的研究策略和方法体系与中医肿瘤学整体观念、动态变化、辨证论治等思维方式具有趋同性,许多学者将系统生物学引入中医学各领域的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应成果。借鉴系统生物学的研究体系可推动中医肿瘤学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现代高通量的组学技术有助于开展中医肿瘤学病因、病机、诊断、治疗、机制探索等多层次的研究,提供给中医肿瘤学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基因组学研究可为中医肿瘤学的病因与发病学说提供客观的基因组数据,指导肿瘤预防、治疗和判断预后,还为中医药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转录组学研究可助力中医肿瘤学发病规律研究、证候本质研究,为不同的中医证候确定生物标志物,阐明证候演变的调控关系,为同病异治和中医药预防提供转录组依据。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可帮助确定中医诊断信息的标志物,在肿瘤的早期诊断、预后判断、证候本质、中医药的作用靶点等研究方面均可实现客观量化,也为发现新的中医药疗法或治疗靶点、阐明中医药的作用机制提供支持。多组学策略完全适应中医肿瘤学整体观、动态观、辨证观的优势,在中医肿瘤发病机制、诊断辨证、肿瘤分型、精准施治、机制探索等各方面均可提供多层次的信息支持,并赋予中医肿瘤学新的科学内涵,实现现代化或与现代科学沟通、相融的基础。
尽管系统生物学的策略与方法已经在医学研究中开始应用,高通量技术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需克服以下几点:第一,组学分析将大量的数据进行整合,复杂的海量数据对生物信息平台的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况且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是对分析平台的考验;第二、组学技术产生的预测分析模型、诊断治疗方法和作用靶标距离在临床中实现中医药预防、早期诊断、精准医疗等还有很大的距离,还需不断地探索求证;第三,组学技术有利于全面实现中医肿瘤学概念、理论、方法、技术等的客观量化和机制阐释,但要保持中医学属性、强化中医学特征、发挥中医药优势仍然面临挑战;最后,系统生物学及高通量组学技术是一匹“宝马良驹”,对中医肿瘤学科队伍的驾驭能力同样提出挑战。当然,系统生物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多变量整合、整体解析,中医肿瘤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源于其自身实践。笔者认为,随着技术局限性的突破和分析平台的进步,大胆借鉴系统生物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体系,不断补充短板、发挥优势,将使中医肿瘤学取得更好的发展,在人类攻克癌症的道路上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