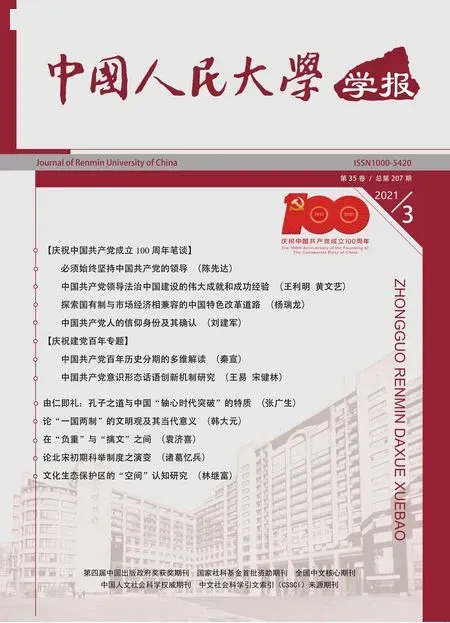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认知研究
林继富
近年来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举措,其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日益彰显。从2007年6月我国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开始至今,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走过14年的历程。2011年,《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强调,以规范编制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为引领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1)《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办非遗函〔2011〕22号),2011-01-19。参见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资料汇编》,73-76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同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原则,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制定专项保护规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2)《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六条。参见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资料汇编》,6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2018年发布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规定“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依托相关行政区域设立,区域范围为县、地市或若干县域”(3)《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2018-12-25,http://www.gov.cn/index.htm。,明确了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性“空间”设定的基本范围。截至2020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先后批准设立闽南、徽州、热贡等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19年12月,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探索实践和建设成果基础上,文化和旅游部进一步确立了7个文化生态保护区,以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4)《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中说明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关系:“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后一年内,所在地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的基础上,细化形成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经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审核,报省级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后发布实施,并报文化和旅游部备案。”本文主要使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表述。
当前,学界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践总结与理论探讨尚显薄弱。本文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为研究对象,深入讨论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的认知层次和功能特性,以期丰富和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建设和实践。
一、文化生态理论视角与问题的提出
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以人的生活“空间”为基本文化单位,注重特定区域内生态环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知识生产和传承保护。文化生态理论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践行动和理论建构的基础。
文化生态理论源于19世纪70年代德国生物学家E.H.海克尔主张的“生态学”,意在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1955年,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明确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认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特定生态环境与文化相互依存、平衡关系的学科(5)J.H.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载《世界民族》,1988(6)。,力图以文化生态“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6)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8-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斯图尔特指出:“它的主要问题是要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内部的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7)朱利安·H.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载《南方文物》,2007(2)。不同环境下产生不同形态的文化生态适应,自然生态的生物层与文化层交互作用,在特定区域内构成共生关系。他秉持文化变迁的多样性文化生态发展观,突破了以文化解释文化的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生态理论从单向度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逐渐朝向多元方向和互动性影响发展。美国人类学家罗伊·A.拉帕波特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等作为文化生态学分析框架,通过阐释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理解生态系统作用于文化生产的动力和发展规律。(8)罗伊·A.拉帕波特:《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人生态中的仪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文化生态系统是“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9)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1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也就是说,文化生态不是单一的自然环境,而是各种因素相互关联、作用、影响形成的动态有机系统,应重视自然环境与文化形态及其内部具体要素和类型之间存在的系统性关联,它们彼此影响,互相作用。文化生态理论着重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关联性,指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理想状态是均衡有序,一旦失衡,就会影响民众生活、文化生产和社会发展。(10)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文化生态理论从环境角度理解文化,认为山脉、河流、海洋、森林、草地等自然界的环境要素为人类知识生产和文化发展提供特殊的场域和情境,并从人、自然、社会等各种关系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的生产、传承和发展;强调生态环境影响特定文化空间内的文化特质,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文化生产的互动性,以及文化与环境动态关联的过程状态、文化生态系统内外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文化生态理论关于特定空间的生态系统、知识生产、文化变迁、文化生态场域等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文化生态保护区包含特定空间中多样的生活文化、多元的价值观念与多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生产传承,这就需要从整体共生、动态发展、和谐均衡的文化生态理论视角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我国启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以来,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包括:探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文化生态累积性、延续性与历史文化传承的因缘关系(11)张松:《文化生态的区域性保护策略探讨——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论析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历程及如何处理传统性与当代性、稳定性与发展性的关联,以促进文化交流互鉴(12)李晓松:《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研究》,载《民俗研究》,2020(3)。;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在羌族家园重建中实现整体性抢救保护和传承发展,为城镇化建设注入文化基因(13)林继富:《家园建设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等学理问题。实践方面侧重分析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申报与保护,类型、层级与范围,法规与机制,保护与发展的关系(14)宋俊华:《关于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几点思考》,载《文化遗产》,2011(3)。;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要注重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并突出其文化特色(15)马盛德:《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要关注的几个问题》,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指出科学评价文化生态保护区遗产资源的生存状态、社会作用、经济价值及保护效果(16)李山岗、仇斌奎:《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如何管理与评价》,载《光明日报》,2016-12-02。等操作性强的问题。上述成果从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与生态的关联性、互动性等方面研究了文化生态的整体性,肯定了在政策保障下从单一化、碎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推进到整体、系统的文化生态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文化生态保护区不仅是单纯的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而且涵括以人为中心的生活关系和文化关系。在整体观视角下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认知离不开科学的生态观,这也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最好实践。
然而,相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生活,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的层次性、类型性,及其作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生产和传承、整体性保护的价值和社会历史意义等方面均没有更为深入、细致的研讨,也较少对我国现有的23个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特定“空间”进行分类研究。因此,从文化生态理论的空间视角全面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与状态,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发展、融合,以及文化生态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生产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空间层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空间的整体性与区隔性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政府以“同一性质的区域文化”为整体,“选定传统文化保存得相对完整,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价值观、民间信仰以及诸多具体文化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点的人群聚居空间给予特别的关注,使这一特定地区传统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健康的传承”(17)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刍议》,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作为“同一性质的区域”“人群聚居空间”和“特定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对其“空间”的科学认知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生活性保护的前提,也是理解并推动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保证。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集中、存活良好、文化特色鲜明的区域。这个区域性“空间”有大有小,大的可以是跨越多个行政区划的民族聚落或文化传统区域,小的可以是一个村庄或社区。就目前我国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即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空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区隔空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的“结构空间”。三种“空间”具有文化表达和文化特征的层次性,彼此关联互动,构成以人及其活动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传承、发展的生活实践关系和文化生态关系。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传承、历史传统以及自身发展规律和整体性保护需要出发,形成区域明确、界线清晰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这种“空间”具体包括四种情形:(1)跨越省级行政区划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比如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包括四川省7个县和陕西省2个县(18)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包括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黑水县,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平武县,陕西省宁强县、略阳县。,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包括安徽省2个市县和江西省1个县(19)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包括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和江西省婺源县。。这两个文化生态保护区划定的“空间”着眼于文化生态的同质性和相似性,由此形成区域生活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形态、传承方式和发展历史的趋同状况。(2)在同一个行政省区,但包含不同市县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比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包括福建省3个市(20)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包括福建省厦门市、漳州市、泉州市。,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陕西省2个市(21)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陕西省延安市、榆林市。,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涉及湖北省2个市州(22)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山西省9个市区县(23)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山西省晋中市,太原市小店区、晋源区、清徐县、阳曲县,吕梁市交城县、文水县、汾阳市、孝义市。,客家文化(闽西)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福建省8个区县(24)客家文化(闽西)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上杭县、武平县、连城县、永定区,三明市宁化县、清流县、明溪县。,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重庆市6个区县(25)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重庆市黔江区、石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武隆区。,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河南省5个市县(26)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河南省洛阳市城区及孟津县、新安县、洛宁县、偃师市。。这些关涉到数量不等的市区县在内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制度管理上相对统一,并充分尊重立足整体关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历史和当代生活的特质,不过由于不同市区县在保护力度和方向上的差异,因而影响了整体性保护的一致性和协调性。(3)在同一个市州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比如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广东省梅州市,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在山东省潍坊市,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在江西省赣州市,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江西省景德镇市。这类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相对协调统一,出台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针对性强,且考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整体性和特色性。(4)以市县为单位构成文化生态保护区。比如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区在浙江省象山县,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在河南省宝丰县。此类文化生态保护区有利于从整体上保护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众独特的生产生活,保护空间具体明确,保护措施细致有效,能够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视角及时、准确地解决传承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划定的“空间”范围主要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和生活性出发,一些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建设在尊重特定文化空间的自然生态传统和民众的历史生活传统基础上跨越行政管理区划的界线,尽管这样可能带来管理的不便,但是,这对于地理上连成一片、文化生态一致的区域来说是科学合理的。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存活和传承情况而划定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充分考虑建设管理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但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传承发展才是保护的核心,其划定的“空间”边界不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障碍,“空间”的地方性是在多民族交流交往的生活中得以形成的。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不是画地为牢,不是利益圈定,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族群、人群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彼此欣赏,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传承,这就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理念,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规律。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蕴涵了人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发展历史,我们要礼敬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历史传统的人文性和情感性。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生活形态均有千百年的积淀,它们在交流中形成,不同区域族群、人群频繁交往,构成不同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空间”面相。这些“空间”既独立存在,又相互交融,如“表演空间”的戏台、剧院,“游戏娱乐空间”的公共性广场,“话语空间”的桥头、河边、树下等,以及将表演、游戏娱乐和话语等融为一体的“空间”,多样化区域以不同方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和传承的具体而富有情感的“空间”。这些“空间”统辖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空间”中,其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具有同质性和整体性。比如,武陵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建设的湘西、鄂西南和渝东南三个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和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具有重要意义,却给武陵山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产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传统呈现带来一些缺失。自古以来,土家族、苗族生活在武陵山区,互嵌互融的生活使他们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和传承上表现出交流性、交融性和共享性,这样既使三个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建设的行政管理边界明确,又令其文化边界难以完全切分。也就是说,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是交流的、生产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整体保护时充分考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和传承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传统性和生活性、独立性和关系性。同时,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生产及生活传承。武陵山区三个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管理制度、保护措施和“空间”内民众的生活关系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和传承,长此以往,武陵山区传统生态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和传统性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空间”设定应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传承的“结构空间”衔接,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区内不同“区隔空间”、文化生态保护区与非文化生态保护区之间的交流沟通,使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生产和传承从整体上继承历史、延续传统和着力发展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和传承的具体“空间”不是均质和同一的,而是存有多样态的“空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内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生活性以及资源分布、生态环境等情况划定了不同层次的“空间区隔”。比如,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根据环境承载力、文化类型、特征、遗产分布、价值特点等因素,按照整体性保护原则,在保护区内划定保护功能区,明确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及与之对应的保护措施”(27)参见四川省文化厅:《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四川)总体规划》,2013-10-16。。重点保护区包括汶川县绵虒镇以北、理县甘堡乡以东、茂县全境和北川羌族自治县。该区域集中保护区内90%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54%的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区空间结构与功能区划分为沿岷江形成的传统村寨保护区、大禹文化保护区、以北川新县城为中心形成的羌族文化复兴区。一般保护区包括汶川县绵虒镇以南地区,理县甘堡乡以西地区,松潘县、黑水县、平武县全境。一般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文化空间以传统村寨为主,羌族文化是主流文化。但由于与其他民族文化相邻,文化多样性和交融性突出。一般保护区内保护工作应以重点传承空间为主,突出特色,注重营造多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氛围。(28)参见四川省文化厅:《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四川)总体规划》,2013-10-16。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明确的“区隔空间”规定性,重点区域内有重点保护空间,一般区域内坚持实施重点传承的空间保护。这些“空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密集、传承状态良好,凸显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历史传承和鲜明文化特色。也就是说,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空间”被区隔为重点、一般或者重点、辐射和关联的区域(29)参见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成果稿),3-5页,2011-08。在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同仁县为重点保护区域,泽库、尖扎两县为热贡文化生态辐射与关联区域。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不同“空间”的保护存在差异,以同仁县隆务河谷为核心地区,包括整个隆务河流域,由多个民族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且包含多种文化元素在内的传统地域文化。,其差异主要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性、分布密集程度,以及与民众生活的关系度上。“区隔空间”的设立对于管理者来讲就是政策制定、实施方式和支持力度等方面有相应区别,这势必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样态。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展现出不同的生命活力,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传承为中心形成的系列“空间”与民众生活构成结构化的层次性。根据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质、分布特征和表现形式,其传承可以分为外在层次、中间层次和内在层次。外在层次即非物质形态或物化形式,包括生活形态、传承方式;中间层次是民众在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中形成的行为习惯,包括习俗礼仪、音乐舞蹈、神话传说等;内在层次包括由民众意识形态表现的家庭、婚姻、价值等认知及其他各种宗教和信仰。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的“结构空间”传承层次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承主体的关系而呈现的“空间”层次,其外在、中间和内在三个层次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构成谱系性的知识结构。
综上所述,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不同“空间”层次涵括保护区的整体性“空间”建设、保护区内区隔性“空间”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的“结构空间”生产。无论哪一种“空间”呈现的非均质性并不意味着哪一类或多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程度,而是表明这些“空间”生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众生活传统的紧密程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社会历史的关联程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创造力的基本面相。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活环境空间和社会历史空间,“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30)《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2005-12-22。参见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资料汇编》,1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这就是说,整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于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生成孕育、传承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包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物质载体及其空间,如家族的祠堂、村落的戏台、庙宇和传统村落、历史街区,以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提供动力源泉的自然生态环境等,这些均说明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层次”的历史发展和传统属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生产和保护是动态性的,关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结构的动态生活关系。保护不同“空间”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激活其内生发展动力,更好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联系,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人在特定场景下的生活态度和行为选择。文化生态保护区内人的生活、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空间的核心,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传承赖以存续的保障,反过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能力、传承发展的“区隔性”又凝聚成区域社会的集体认同和共同价值,并塑造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内民众的生活特性和整体性的文化特色。
三、空间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空间的传统性与建构性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文化生态作为“空间”分类的依据,建立在民众生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传承的共时性基础之上,保护区建设是在“空间类型”作用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与文化生态之间的关联而进行的保护实践。“空间”分类和“空间”层次映现了我国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特质。当前,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一方面与其所属的文化主管部门的整体考量和积极工作分不开,另一方面保护区以“空间”共同性作为保护类型,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谱系的文化特色和多民族生活特征。“分类就是把人、事物、概念、关系、力量等划分到不同类别中……分类对我们人类思考和认识这个世界、了解自己的生活空间以及其中的活动来说至关重要。”(31)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2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文化生态保护区将中国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及民众生活予以分类,充分尊重和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空间”中的社会历史传统、民众生活方式和地方民族文化,以“空间”为基础呈现民众的社会认知、生活观念、审美价值和行为实践。
文化生态保护区从整体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主体的生活进行概括和分类,其中蕴涵了包含和排斥的生活关系、文化关系以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边界的功能。涂尔干和莫斯在《原始分类》中认为分类就是“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32)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这种分类的基础是社会成员共享的集体意识、价值观念,社会文化充盈并构成和谐的人类生活空间,在同一种分类体系中人们共同分享同一种生活。涂尔干和莫斯对民众生活和知识的分类基于社会团结的功能性认知,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来讲同样重要。
我国23个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23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传承的多民族生活关系和文化关系,尽管不同文化生态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类型、传承空间多种多样,但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而分类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则着力于整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和传承。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生活就具有社会团结和文化凝聚的特性,具有多民族、多区域的生活认同情感,促进不同族群、人群的交流沟通,进而构成多民族交融互动的生活,也使文化生态保护区成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共同体建构的类型化“空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谱系生产的关系“空间”。
当然,文化生态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对于“空间”分类的社会文化认知往往以含蓄和潜在的状态表现出来。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文化空间类型、生活传统类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分类始终存在。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有些无法详尽描述,但是“空间”含义不会因此而不复存在,也不会因为分类否定这一特殊“空间类型”的历史延续性和未来发展。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在界定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类型”时,突出和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在性生活特质,并没有遮蔽民众历史生活中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空间类型”的逻辑。
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看,民众生活并不因为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空间”及其中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空间”而发生刻意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按照生活秩序和文化自身的逻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自我分类框架中。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空间”分类通常直接来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实践及其传承发展的规律,表现出共同性建构中的差异性。“人们常根据片面的理解去替各门艺术的分类到处寻找各种不同的标准。但是分类的真正标准只能根据艺术作品的本质得出来,各门艺术都是由艺术总概念中所含的方面和因素展现出来的。”(33)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分类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空间本质,以民众认知、命名和生活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为基础,其建构的“空间”分类框架源于个体经验、语言形式、文化传统、社会背景、物质环境等相互作用凝聚而成的集体认知,以及民众生活互动互融的关系转化。这就是说,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分类是基于特殊生态环境下形成的地方知识分类。比如,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玉树高原生态环境下藏族特有的地方知识基础上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玉树地区地处高原特殊地理与气候环境,千百年来生活在玉树的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生态知识和体系化的生存经验,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合理地利用和适应自然,精心呵护自然环境。至今充满活力的大量民间传统足以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玉树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河流域适于农耕、半农半牧、游牧、商贸集市等地区为传承区,分布较为集中,加之位于安多、康巴和卫藏三大藏语方言区地缘与文化交汇处,其文化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和鲜明的区域特色、民族特色。”(34)青海省文化与新闻出版厅:《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2016-12。玉树藏族的地方知识是以玉树自然环境、生态资源、历史传统等建立起来的关于生活、社会专属性的认知和应用体系。玉树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类型与玉树藏族的地方知识认知是一致的,与玉树藏族传统文化的分类是一致的。因此,现已划定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民众生活历史实践形成的传统文化区域具有高度一致的“空间”性质,这就不会因为“空间”分类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生产的生活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传承拥有一套源于民众生活的知识体系,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生产不断从民众知识谱系中汲取营养,不仅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土壤,而且保障民众生活的有序运转。当然,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生活中纷繁复杂的个体经验被分类为具有边界和标识的各种社会类别和不同“空间”类型也存在一定问题。“人们认识到世界实际上是多样化的,是各种繁多的实际与潜在的认知结果的主体,每一种分类体系不过是一种对整体性的秩序化的周遭世界的伪装。”(35)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3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空间层次”以文化特征为标准区分为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等,每个空间内的保护又倾向于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这就使传统“空间类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谱系的整体由于保护区的“空间”区隔化而被切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文化生态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生产动力。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分类并非机械性与结构化的,而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传承及其依附的社会结构逻辑基础之上,这样,其“空间”才具有生活实践的意义、情感表达的价值以及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虽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分类无法全部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保护区的社会组织体系中,以此映射文化生态保护的区域性,乃至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对于社会成员的规制,但是,文化生态保护区三种“空间层次”的划分无疑为理解民众生活方式、民间社会组织和民间知识生产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实践行动拓展广阔的视野。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分类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和传承,从生活整体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与民众对地方知识的分类并不矛盾。文化生态保护建设区域的“空间”分类与民众地方知识的“空间类型”,并没有否认民众生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流性、交融性。尽管因为行政区划的界线而使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具有明确的边界,然而,这种“空间”同样具有文化传统的整体性、知识生产的能动性和传承发展的动态性。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整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生产和传承的“空间”表现出非凡的张力与无限的活力。
四、讨论与结语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分类原则和标准是绝对的,具有排他性,但是,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其“空间”又是相对的,具有生产性、包容性和动态性,传递了政府和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认知。文化生态保护区呈现的“空间层次”侧重于共时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生产,“空间类型”则以社会历史为根本表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生活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通过传承实践和空间认知创造与建构的“空间”是生活性的,也是生产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生产根源于传承主体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既是实践性的,又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活方式的认识,目的是从整体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辨识、归置,更好地保护、传承、利用和发展。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将地理生态、行政区划和社会文化等边界融为一体,保护区内又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生活空间分为重点、一般和边缘等“区隔空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给予适当有效的“空间”归类,由此提供具体而有针对性的措施,但是,这种“区隔空间”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生产和传承多样性带来一定影响。
文化生态保护区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传统和人文生活形态,显示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共存和文化特色,发展为民众交往交流交融生活的凝聚力和认同属性,生活在同一“空间”内的多民族民众共享同一文化,进而形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谱系为核心的认同传统。
以人及其活动为核心构成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包括人的生产方式、生活行为、语言表达和道德观念等,与自然生态环境结构为相互作用的整体,具有传统性、发展性和体系性。文化生态保护区内不同“空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传承与文化生态系统之间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这种动态平衡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不断适应生态环境做出的调整,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修复生态环境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受的破坏和损失,从而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和传承发展的良好态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聚焦于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空间”,它由政府和相关文化主管部门同意,并设立建设区域、制定建设内容、确定建设目标,这就达成了“空间”建设人为属性、制度化规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实践的自在特质的有机结合。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速度的加快,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生产及其存续受到严重挑战,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的“空间”,进行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势在必行。在政府引导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科学认知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的整体性与区隔性、生活性与历史性、文化性与建构性,实施并实现以文化生态涵养和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内生动力的保护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