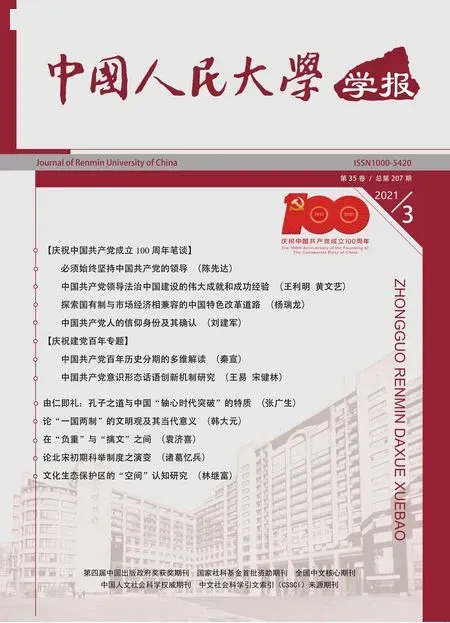中国百年科技转型历史轨迹的哲学反思
黄 婷
中国科技从传统到近现代的转型经历了怎样一个历程?其历史跨度如何界定?中国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是否有其自身发展逻辑?刘大椿教授提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主要是向西方现代科技模式转换,其历史分期为明末到清初的西学东渐阶段和清末到民国的师夷长技阶段。(1)刘大椿:《师夷长技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3)。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问:有没有必要把自鸦片战争后开始的“师夷长技”到西方现代科技模式在中国转换、生根、自立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特别是有没有必要把从民国时期西方现代科技体制在中国确立到当代科技体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否出现了根本性转折?
仔细梳理学界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民国以来科技转型历史轨迹的分析及哲学反思,或是基于民国结束前后的分期,或是基于科技体制方面的转型,或是基于以主题或学科划分的专门史,或是基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近现代转型,或是基于以上各类型的结合。刘大椿等著《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二卷):师夷长技》(2)刘大椿等:《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二卷):师夷长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对截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现代科技转型进行了以点带面的阐述和分析;朱世桂侧重研究农业科技体制的百年转型(3)朱世桂:《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12。;钱斌对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期中国科技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分析(4)钱斌:《新中国科技体制的建立和初步发展(1949—1966)》,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论文,2010。;姚昆仑研究了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时间跨度自古代始,囊括了民国至当代(5)姚昆仑:《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论文,2007。;孙磊基于科技职业伦理的视角阐释了民国时期的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发展历程(6)孙磊:《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太原,山西大学博士论文,2018。;张培富研究了在制度化的留学活动中产生的化学专业留学生对近代化学体制化的贡献(7)张培富:《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考察——近代留学生对化学体制化的贡献》,太原,山西大学博士论文,2006。。也有学者研究了科技近现代转型下传统科技文化的印迹和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呈现的效果。王前对经世致用等中国传统技术文化在近现代科技转型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8)王前:《“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王忠武基于传统文化的转型对功利主义科技价值观的演变进行了分析(9)王忠武:《传统文化转型与科技价值观嬗变——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科技价值观的建构逻辑与重构方略》,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3)。;李丽分析了百年来科学主义是如何中国语境化的(10)李丽:《科学主义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范铁权阐释了中国科学社如何形塑现代科学文化(11)范铁权:《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文化》,天津,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3。;彭国兴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众对现代科学社会功能看法的演变过程(12)彭国兴:《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关于科学社会功能的认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4。。以上研究为百年来中国现代科技转型的进一步哲学反思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本文拟在当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大视野和科技自身的发展脉络,对百年来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历史轨迹进行整体性的哲学反思,并追问这种整体性哲学反思之所以可能的条件。
一、从西学东渐到自主创新的历史顺轨性
从明末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与西方科技文化交汇之后,由于清代乾嘉学派对“西学东源”的论证,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失去了通过吸纳西方近现代科技来实现科技转型的可能,直到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兴起,国人才开始正视西方现代科技文化,承认技不如人,奋起直追。原则上,从晚清到民国约百年间,在“师夷长技”的总体思路下,中国完成了从原有科技发展模式向近代科技发展模式的转型,特别是实现了科技发展的体制化和制度化。但是,从现代西方科技模式在器物和制度区分的层面上,晚清与民国期间还是存在着较大区别。从科学文化主要包括的四个方面——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对“赛先生”的宣扬,才使科学文化从器物层面走向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科技体制的确立,使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也走向了制度化。而与晚清到民国之间科技转型呈现出的差异性相对的是,近代科技体制在民国期间确立之后,一直到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21世纪初,除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体现出来的制度优势,实则科技的体制化、制度化方面乃至科技文化都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民国科技体制化以来,西学东渐的外源性、追赶性的科技转型作为一个未完成状态持续至今,科学文化的四个方面——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在曲折中不断得到加强和内化;二是从近现代科技体制确立开始至今,并不存在一个先学习后自主创新的截然二分阶段,毋宁说,模仿基础上的科技创新和贡献从未中断过。
(一)尚未完成的“西学东渐”
近200年来,西方社会整体上发生了三次科技革命,前两次科技革命使科技文化从前科学时代转向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小科学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使科技文化转向以技性科学为特征、科技一体化的大科学时代。与之相应的是,对科技文化起支撑作用的西方社会形态也从传统型经现代型走向后现代型,或者用丹尼尔·贝尔的话来说,是从前工业社会经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13)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2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发端于欧美、渗透和扩散至全球的这三次科技革命、两大科技文化转型,中国都是以追赶者形象出现的。可以说,中国的近现代科技转型一直是一种外源性、追赶性的转型,尚未走到引领科技发展的这一步,直至最近才提出要“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14)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载《求是》,2021(6)。
从历史发生学视角看,中国的近现代科技转型有三个值得挖掘和省思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经过北伐战争的南京国民政府获得了难得的一段稳定的执政期,无论是政府的组织架构还是在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立,都为科技体制化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在当时的政治治理体制中,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海归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学教育和研究团体,呈现出专家治国的治理特色。在这“黄金十年”(15)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说法源于1951年美国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C.Wedemeter)将军在美国第82届国会报告:“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与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在这十年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见Paul K.T.Sih(ed.).The Strenuous Decade: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1927—1937.New York:St.John’s University Press,1976,p.26。发展期,智识阶层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路线“农工立国”之争也逐渐统一为一致谋求机械化、现代化,国民政府以现代化、体制化的方式推进着工农业生产、财税与货币改革。在科技教育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科研体制化进程的基本完成,职业科学家开始有了系统化的官方研究平台。高等学校的国立化、教会学校的去宗教化、基础教育的现代化和体系化、职业教育的规模化,使制度健全、接轨欧美的人才培养模式确立起来。这种科技教育模式即使在抗战期间也未因内迁流离而影响到其根本。这个时间段的主要成就是以德法英美为蓝本形成了基本的现代科技发展体制。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封锁,百废待兴,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彻底转变,中国科技发展的“求道”之路只能转向科技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面的苏联。通过对革命高校的升级、旧中国高校的接管和1952—1953年的院系大调整,新中国按照苏联单科性专门学院、多科性行业大学、文理科综合大学的模式彻底改造了高等教育体系。完成改造后,人文社会科学被限制,综合性大学比重降低,工科院校得到加强。这对于急需进行工业化的新中国来说,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样,通过接收和改造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留下来的大部分研究机构,新中国也建立起最高学术研究和管理机构。通过苏联的援助,我国工业化进程有所提升,特别是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大量苏联专家参与了中国的工业建设,主要进行设备、技术方面的援助和技术人才的培养。(16)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编著:《苏联对我国工业化的援助》,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次的“求道”之路戛然而止,特别是随着极左思想对科学活动的强力渗透,科技文化一定程度上走向扭曲,其影响延续至今。这个时间段科技发展外源性的另一个体现是,一批海外(主要在欧美)留学专家带着国际最前沿的知识和最先进的技术纷纷回国,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归国潮。1949年成立的“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和帮助了大量留美专家归国。这批海外科学家归国后,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构建起了新中国的学科体系和工业化建设体系。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从 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以后,中国在科技领域上与国际的交流开始慢慢恢复。1972—1977 年,中国先后向英、法、加拿大、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派出留学人员千余人。(17)苗丹国:《出国留学六十年》,1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批心系祖国的华人科学家纷纷访华,带来国际上最新科技资讯和成果,推动了中美之间的科技交流。而深受政治运动冲击、科技转型进程遭遇反复的中国科技界也急切期待着这些在国际上已功成名就的爱国科学家引领他们回到科技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科技转型之路再一次向欧美接轨。此时,西方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如火如荼展开,以科技一体化、产学研一体化、知识经济等为特征的新科技文化形态确立起来。因此,中国一方面要回归正常的现代科技体制,另一方面要适应新时期科技文化形态,进行体制创新。这个过程持续至今。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最近十年来,世界科技发展处在变革交汇处,科技文化与其他类型社会文化的联系和互动越发紧密和复杂,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先期完成工业化并步入后工业社会,在这方面呈现出的问题和实践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中国也利用新的一波留学归国潮,推动着科技本身的突破和科技体制的创新。
(二)一直持续的自主创新
从大的时间尺度上说,从18世纪末最早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到19世纪末第二次科技革命德国的后来居上,20世纪初美、日迎头赶上,西方(包括日本)近现代科技体制的产生和成熟并不比中国早很多。德国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直到19世纪初仍然是一个落后农业国,从1810年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的创立,到1873年建立国立物理研究所,1877年建立国立化学研究所,1879年建立国立机械研究所,到19 世纪末终于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美国到19世纪末仍没有几所像样的大学,但美国高等教育、科技研究与工业部门紧密结合,从1876年爱迪生建立门罗工业实验室、1900年通用电器公司实验室成立到1925年AT&T公司贝尔实验室成立,美国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完成了蜕变,20世纪20年代后逐渐成为中国学子留学的向往之地。
中国百年来的科技转型之路并非一蹴而就,但也不是亦步亦趋、一直落于人后。梳理历史可以发现,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科技体制成型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未缺少创新,整体上的后进并不能掩盖点状乃至片状的科技突破。在基础科学领域,数学、物理学从模仿到创新,从民国政府科技体制建立初期的零星突破到现在自己培育出国际一流人才;在与中国地理空间紧密相关的生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等领域,突破性的成就亦不少见;在与中国工业化进程息息相关的工程科学方面,中国用“两弹一星”、桥梁工程、三峡大坝、高铁项目等证明了后发劣势下进行自主创新的可能性;紧密依托工程技术等物质支撑的基础性科学,如航天工程科学、微观科学等领域在近20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而渐显优势。
在科技体制的创新上,民国时期并无太大亮点,但是学科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的建制化本身就是一个创举,开创了把植根于西方文化的科技体制移植到作为他者文化系统的中国这样一个过程。值得肯定的是,在多年的抗战中,国民党政府并未将科教战时化,而是勉力维持战时科教的常态化,因此也使得抗战期间科技知识分子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上都取得了不少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确立了科技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1956—1967年科技发展规划。通过对旧有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海外归国人才的改造和本土科技人才的培养,新中国科技体系较旧中国更加完善,“例如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射电天文学、石油化学、生物物理化学等等,在旧中国都是完全没有基础的,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相应的基地和培养了干部,并开展了研究工作”(18)聂荣臻:《十年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载《人民日报》,1956-09-27。。“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技体制改革先后经历了适应商品经济的改革、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等阶段,围绕着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科技政策体系,“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夏保华提出,基于社会技术转型的国家自主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英国为代表,是基于转轨性社会技术转型的,即开创全新的技术文明形态,开拓出人类社会全新技术范式、轨道和体制;另一类以德国和美国为代表,是基于顺轨性社会技术转型的,即把一种技术文明形态推进到新的阶段。(19)夏保华:《社会技术转型与中国自主创新》,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借用此“顺轨性”和“转轨性”的概念,可以说,自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在近代折戟,被迫走上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之路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之路是顺轨性的。自民国时期近代科技体制确立以来,中国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着顺轨性的科技模仿和自主创新,或者说是基于模仿的创新。只有明确这一点,社会主义文化引领下的具有制度优势的转轨性科技转型才能奠基于厚实的文化和历史土壤上。
二、中国科技发展之路的地方性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以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科技强国的主要标准,并对我们自己科技发展在世界版图上的定位模糊不清,甚至对诺贝尔奖一直无法取得零的突破耿耿于怀,由此引发出关于中国教育是否能培养出大师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但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追问,近现代转型之下的中国科技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科学实践哲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科学,因其自己趟出的一条“中国特色”之“路”而彰显其根本意义,其现在积累的成就和显露的问题是否可以从作为其汇入世界科技发展史大流之“路”的意义上进行理解和阐释?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地方性知识”,可以从科学实践哲学视野去观照。吴彤总结了吉尔兹阐述“地方性知识”的三个重要特征:第一,地方性知识是与西方知识形成对照关系的知识;第二,地方性知识是与现代性知识相对照的非现代知识;第三,地方性知识一定是与当地知识掌握者密切关联的知识。(20)吴彤等:《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107-10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这种对地方性知识的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挖掘处于劣势地位的地区性知识的意义,但是,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的提法具有强烈的结构主义特征,即普遍性与地方性之间的泾渭分明,使得“地方性知识”成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处于西方主流知识之外的、与普遍性知识对举的“概念”,因而在彰显其意义的同时也一并将其置于普遍性知识的附属和补充的位置,并没有根本地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幻象。
科学实践哲学把科学当作一种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而非现成的知识形态来看待,即持有一种实践优位的科学观。美国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通过解构普遍性而论证“从根本上说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它体现在实践中,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或独立于情境的规则”(21)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113、1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在劳斯这里,所谓普遍性实际上是地方性知识标准化后的表征,而所谓标准化则是“在前人留下他们的研究很久之后,又把这些先前的研究纳入可供进一步研究的素材中”(22)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113、1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即从一种地方性知识扩展到或改造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以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来探究科学活动,确实可以解释理论优位视角下被遮蔽的科技知识生产的过程性和非中心化特征。但是,劳斯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科学知识生产这种实验室(田野、诊所等)实践活动的地方性,而国内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来进行的研究,其案例亦多集中于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如中医学、风水、少数民族科学实践、民族植物学等(23)吴彤等的《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第十五、十六、十七章有相关案例研究。,科技发展之“路”的地方性并没有成为一个主题。
就中西方科技发展路线来看,“直到16世纪,两者之间并无交集,各属两个独立的科技规范,没有可比性”(24)刘大椿等:《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一卷):西学东渐》,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直到明末清初中西科技发生交汇,第一波西学东渐经历了16世纪末的酝酿、17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上半叶的式微。与之相伴随的是,西方社会自17世纪开始发生了科技革命,到19世纪,无论在物质成果上还是在精神成果上都把中国远远抛在了后面。痛定思痛的中国意识到“师夷长技是唯一选择”。近百年来,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之路经历了前述三大历史节点后,基本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潮流,走出了一条顺轨性的科技模仿和自主创新之路。这在两种意义上体现出科学实践的地方性:第一,在科学知识生产上,我们的自主创新多集中于跟中国情境高度相关的领域,如民国时期的考古学、地质学、生物学,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科学,改革开放后的工程科学,等等。实现中国气象科学数理化的第一人赵九章就气象学在中国的发展曾经说过:“从现代化的科学发展来看,气象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一方面联系着当地的具体地理条件,有它的地域特点;另一方面,则遵循着物理变化法则,而与数理科学有共同性。因此进一步揭示现代气象学的本质,必须广泛积累天气和气候的观测事实,利用现代新技术,更深入掌握大气物理现象的变化过程,运用现代科学的成就,进行分析研究……”(25)吴阶平、钱伟长、朱光亚等:《赵九章》,3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也就是说,这种看似边缘的学科领域,恰恰是我们后发劣势转为优势的地方。甚至在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也因为对经验科学方法的移植而多有突破。中央研究院自1928年成立后,陆续创建了包括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内的14个研究所,覆盖大部分现代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并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圭臬。然而,传统上被看作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却成长得最快,成果最卓著,以至成为中央研究院的招牌,其主要原因就是创所者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中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推崇。第二,由此出现的中国科技发展模式的地方性。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受功利主义科技价值观的影响(26)按照王忠武教授的理解,“与‘儒家文化→革命文化→现代文化’的历史转型发展相对应,中国传统科技价值观建构经历了‘道德功利主义→政治功利主义→经济功利主义’的历史嬗变 ”。参见王忠武:《传统文化转型与科技价值观嬗变——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科技价值观的建构逻辑与重构方略》,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3)。,科学实践中对基础科学重视不够,学术界对此也多有批判,其中诺贝尔奖的有无和多少成为我们判断基础科学够不够重视的重要依据。但是,如果承认科技发展道路的地方性和开创性,那么也就可以解释上述第一种意义上的科技知识生产何以展现出其典型的地方性特征。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科学家伍连德,1935年因在中国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而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的屠呦呦,突破的领域就是以现代科学方法所进行的中西药结合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在数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吴文俊,突破点不是产生于其早期专攻的拓扑学,而是以中国传统数学方法开创的数学机械化研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知识生产和辩护的特定情境,佐证了在科学实践哲学的视野下探究中国百年来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立场何以使得中国科技转型走出科技与实践紧密结合、与中国情境紧密结合之路的必要性。
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的走向,正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余音未消、第四次科技革命暗潮涌动的时刻,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看,如果一劳永逸的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成立,如果中国科技向现代的转型确实紧紧依赖于中国情境,依赖于标准化知识生产形式在中国的地方化,依赖于顺轨性转型的落地、生根和自主化,那么,中国如何在接下来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迎头赶上?这不仅仅取决于我们产出了多少科技知识,还取决于在哪些领域进行产出,并由此走出一条怎样的科技发展之路。在2019年11月29日举办的“中国工程科学高峰论坛”上,有学者提出中国工程实践对于原创性的要求迫使工程科学必须优先发展。(27)《中国工程实践高速发展要求加强工程科学研究》,见http://www.gov.cn/xinwen/2019-12/01/content_5457380.htm。这里的工程不仅仅是指水利建设、交通网络建设等技术工程,更包括生物工程、信息工程等,特别是涉及多学科交叉的会聚技术,将大大拓展对工程的定义。从百年来中国科技实践历程来看,以优先发展工程科学、反哺小科学意义上的“基础科学”的方式走上科技强国之路,是否真正把握住了中国科技实践的历史脉络?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挖历史,探查基于中国情境和地方性发展之路的合理性依据,从而为这条道路铺就更坚实的路基。
与之相伴的是,梳理百年来中国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探究西方近现代科技体制如何扩展到中国,呈现中国科技发展之路的地方性,也是为了探究科学实践哲学作为近年来流行的科学哲学思潮其解释力的限度和范围,实现科技发展史与科技哲学的互融。特别地,科学实践哲学产生的哲学背景是后现代思潮,在其三个重要的观点(实践优位、地方性知识、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关联)(28)吴彤:《实践维度的科学哲学在当代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5)。中,其对普遍性的解构和地方性的辩护这一点很容易走向误读和激进。因此,需要根据史料专门辨析中国科技转型之路的地方性是如何建基于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所维护的标准化之上的;关于知识与权力的关联方面,在何种意义上呈现为福柯所展现的内在关联,在何种意义上呈现为传统理解的外在关联,亦需要立足于史料进行辨析。而要理解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下科学之“技”的本质抑或说“技”的前提,也需要辨析是否可以用中国重“技”不重理和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进行解释。因此,对中医学、风水、少数民族科学实践等主流科学的边缘地带进行研究还远远不够。只有把近现代科技转型之下中国科技发展的复杂性、整体性样貌呈现出来,才可理解当前科技哲学一些新观点、新提法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三、中国百年科技发展社会历程的不可割裂性
如果说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必须把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之路作为一个整体来探究才能更加突显其地方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百年社会转型(29)尽管1949年前后,中国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转变,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今,中国总体上走的是从封建帝制转向以西方为鉴并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因此,民国政府现代化改革的成果经无产阶级改造后都为新中国所用了。体现在科技上,则是工业化成果和科技知识分子的“一技之长”成为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实力量。中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作为一个社会历程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可分割性。这种不可分割性主要体现在:在这百年间,国家意志、传统文化、实用主义、社会历史状况等外部环境对科技发展间歇性地长期持续产生着影响。
国家意志使得中国的科技转型之路打上了深刻的国家主义色彩,其正面的作用在于通过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科技发展紧紧围绕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运转。哪怕在国民党独裁政府时期,这一点也有所体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高层吸纳科技知识分子,力行专家治国。蒋介石认识到:“没有一个现代的工业基础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军队,基础性的、与军事相关的工业将作为国家工业生产能力发展的第一步。”(30)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110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1932年其直接领导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国防科技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地位之高,时人称为“无形内阁”。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受原子弹爆炸威力的冲击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也曾勉力推行原子弹计划和三峡开发计划,但由于政府的腐败和内战的爆发才不得已放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以举国体制发展国防科技和重工业科技,取得了重大成就。改革开放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等大科技工程有力推动了我国高技术的进步;“中国制造2025”宏大计划力图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制造业升级,提升工业化水平;以杂交水稻技术创新为代表的民生科技则“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都浸透着国家意志、国家需要和国家力量”(31)夏保华:《社会技术转型与中国自主创新》,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国家意志在促进现代科技文化的大众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虽夹杂“礼义廉耻”等传统价值观,但也致力于破除陋习,普及科技知识,倡导健康化和纪律化生活方式,推动社会有序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为了消除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指导下,坚持科技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针,开展了全民性、运动式的科普活动和科技精英下基层扩展科技应用的实践,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普通民众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促进了科技在大众层面的现代化转型。国家意志在科技发展中负面的作用则体现在,一旦失控则危害到科技发展的自主性。近现代科技转型的曲折多源于此。国民党政府时期个人独裁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党政名义控制科教体系,以党化教育之名压制了大学的自主权。(32)张守涛:《民国中央大学党化教育研究》,载《档案与建设》,2015(3)。另外,垄断阶层对权力的渴望始终高于现代化的追求,使得科技转型的效果往往只及于精英层面,难以下沉到普通民众。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党和政府的思路尚未从革命转向执政,一段时期内,科学技术被革命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科学“大跃进”扭曲了科技发展的正常道路,损害了科学自主性。其损失主要表现在:一是本已正常化、现代化的科技体制遭到破坏,很多留学归国的科技知识分子受到很大冲击,教学和科研被迫中断,造成了科技发展的阻滞和人才的断层;二是国家错失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机,科技作为生产力特别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没法发挥出来,使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现代化潮流中落后于很多国家。
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重人伦、亲族的儒家传统在科技的现代化转型中,一直或隐或显地产生着作用。一方面,重人伦轻规则的习惯使人情因素过度干扰科技自主性。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以蒋介石等掌权者为中心,根据亲疏关系形成了大小不等的人际圆周,在科技知识分子的选拔任用上,往往只看是否在某个圆周范围内,而不是依才干论。例如任鸿隽,他在20世纪30年代因蒋介石之邀执掌四川大学,实行国立化、现代化改革,成就斐然,后在其夫人与四川文化界产生龃龉时,为维护夫人名誉而辞去校长之职,蒋介石认为其意气用事而再未予以重用。又如,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时,由于门户之见,很多提名单位只推荐本单位的人,以致一些贡献卓著但为人低调者成为遗珠,而政府高官朱家骅等尽管早已不再有学术贡献,仍然当选。这种人治因素即使在当代,仍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科技发展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伦关系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作为整体性文化的科技转型过程中由个体的原子化带来的人际疏离,为工业化之后社会的伦理重建提供了文化土壤。特别是在太急太快的社会性科技文化转型和工业化进程中,如果占中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被甩出这个进程之外,那么这样的转型算不上成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近百年前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最近几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对土地承包责任制的长期坚持,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使科技文化以适合于社会承受性的速度扩展到基层,也为科技转型和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缓冲区和转圜空间。
实用主义是指美国19世纪末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真理观,即真理不在于语言符合观念、观念符合事实,而在于实践和经验上是否能够解决问题。随着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访华,胡适等人将其发扬光大,并发展为两个方面的诉求:一是讲究实用的态度,二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经验科学方法。实用主义理念指导下的中国科技发展之路,以经验的方法注重解决中国情境中的问题,产生了之前所述各方面的科技成就。以新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为例,当时参与导弹研究的中国科学家中,见过导弹的仅有钱学森一人,通过“总体设计”、大胆探索,最终实现了造出导弹的目标。但是实用主义在实践中也与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结合,与科玄论战之后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科学主义结合,甚至与意识形态相结合,被庸俗化为实效主义和功利主义,造成诸多问题:一则过度注重实效,科技被当作“有用”之学来处理,对于科学原理上的钻研和突破没有耐心,甚至被政治化为理论脱离实际;二则将科研当作实现政治目标和人生目标的手段,科研工作要么受“科学救国”“科技强国”的强力驱动,要么受个人名利驱动;三则只讲目的不讲手段,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今日之学术不端种种乱象多源于此。
从社会历史状况来讲,百年来的中国大致呈现出“乱(民国初年)——稳(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乱(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年)——乱(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稳(改革开放)”的W状动态进程,与之相应的是前述三个时间节点下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颇受社会稳定度的影响。一旦社会稍有稳定,充满家国情怀的科学家总有迫切的愿望将毕生所学施展出来。在所谓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中,习得西方科技知识和社会治理知识的归国者效德师美,对中国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仅600多人,科学研究机构也只有30至40个,不可能胜任重大的高水平的研究工作”(33)丁厚德:《中国科技运行论——科技战略与运用管理》,3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所产生的81位院士只有十几位去台湾,其余60多位都选择了留下来。而除了留在大陆的学人,更有一批正在国外进行访问讲学的科学家和接受学术训练的青年人才,迫不及待地赶回来建设新中国。据中国科学院估算,新中国成立前后,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有5 000多人,到1956年底,有2 000多名科学家陆续归国。“文化大革命”后期及改革开放前期,也有一批华人科学家回归祖国,带回了西方世界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科技运行方式。同样,在社会稳定期,科技体制的确立、改革、推进等也进行得比较顺利。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混战,虽有教育部等机构,但科技的体制化一直没有得到切实的推进,直到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以学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成立为标志,现代科技的教学与研究得以真正制度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现代科技文化的沉淀也都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环境。
自民国时期西方近代科技体制扩展和移植到中国,直至今日,上述这些因素历时性地共同发生着作用,并慢慢内化为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成为我国科技运行的集体无意识,因此,有必要分析这些所谓“外部因素”是如何形塑了中国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四、结论
研究历史往往是为了定位当下并为未来设立目标。从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大视野看,从科技弱国到科技大国再到科技强国,从以西方为鉴的顺轨性科技转型之路到“四个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引领下的转轨性科技转型之路,我们此时处在哪里?我们如何确立自己的科技文化自信?不经由对历史细致入微的剖析,把握其复杂性,理解其特殊性,总结出其内在一致性和规律性,则无以回答上述问题。形塑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可能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仅就科技之技来说,西班牙哲学家J.O.加塞特提到:“要警醒我们时代一种自发的然而不明智的倾向,即认为:根本说来,只存在一种技术,也就是现在的欧美技术。”(34)加塞特:《关于技术的思考》,载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282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在国内,夏保华提出,近代以来西方所领先的不过是一种“机器技术文明”(35)夏保华:《社会技术转型与中国自主创新》,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如果未来整个社会的技术转型真的要走向“心身—机器—生态技术文明”形态的话,如果中国的科技转型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在21世纪即将展开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后来居上,我们必须看看在科技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以为是先进的如何可能是误解,我们以为要抛弃的如何可能需保留,我们以为是劣势的如何可能是优势,由此,基于我们自身历史的反思,来确立科技文化自信。这就要在现在与过去之间进行永无休止的“之”字形回溯,以对已有的认识不断进行重新阐释,从当前的道路不断重新出发。因此,对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之路的哲学反思不是一个单一的封闭的问题,而是不断进行“之”字形回溯的极具弹性的话题。这个“之”字形回溯如果要设立一个起点的话,放在近代科技体制得以确立的百年前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点。对这段科技发展历程的哲学反思,既是“四个自信”在科技发展道路上的体现,是我国科技文化自信得以确立的史实支撑,也是“中国梦”在科技领域得以实现的思想前提。
因此,需要从哲学层面把握这段历史,对发端于西方的近现代科技文化在我国引入、生根、自立的过程进行再理解,特别是对近代科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后的整个科技发展历程进行再理解,以帮助我们合理地定位我国的科技发展在世界科技发展版图上的位置,确立科技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具有中国地方性)的科技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