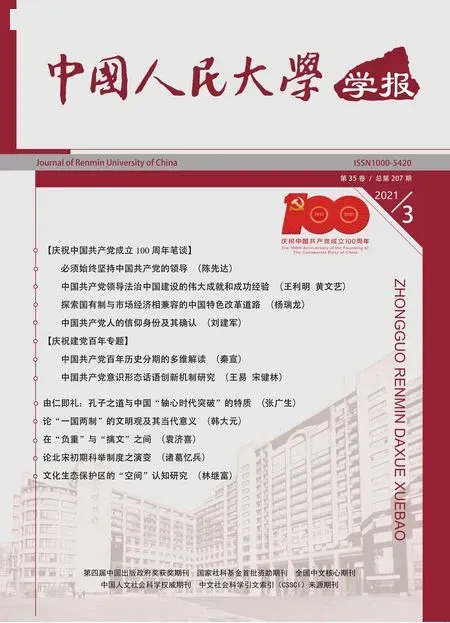从辉格史观到语境主义:柏克政党理论的阐释及其方法论反思
霍伟岸 朱 欣
不同的方法论对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问题会产生多大程度、何种性质的影响?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或许就是找到一个恰当的案例展开分析。本文聚焦于18世纪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通过对19世纪以来柏克政党理论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力图对此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意见。
一、辉格史观的影响及其批判
在西方政党思想史上,柏克的政党理论经常被看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例如,著名思想史家萨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在经典教科书《政治学说史》(1937年)中指出:“柏克力图重新振兴辉格党的努力,使得他比英国任何其他政治家都更早地洞见到了政党在议会政体中所具有的必要作用。”(1)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下卷),30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其实,萨拜因的这个论断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当时盛行的辉格史观的深刻影响。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占据主流的方法论是辉格史观,它把历史看作是不断进步、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专制走向自由的线性发展,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臧否都要放在这样一个目的论式的时间轴上去衡量。(2)关于柏克与辉格史观,参见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裴亚琴:《17—19世纪英国辉格主义与宪政传统》,第四、五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虽然今天柏克通常被解读为保守主义之父,但他的形象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3)张伟:《埃德蒙·柏克与英国宪政转型》,9-1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F.P.Lock.Edmund Burke,Vol.I:1730—1784.Oxford:Clarendon Press,2006,p.295。,这完全是辉格史观塑造的结果。在辉格史观的观照下,柏克的政党理论摆脱了前现代的反党派思想的束缚,预示了未来自由民主政体中通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因而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4)不过,这些早期的观点大都以评论文章的方式得到表述,或者在一本著作中附带提及,但是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证。参见John Brewer.“Party and the Double Cabinet:Two Facets of Burke’s Thoughts”.The Historical Journal,1971,14(3),Sept.,p.481 n11;在专著中表达的此类观点,见John Morley.Burke.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09,pp.53-54,该书初版于1879年。作为秉持辉格史观研究柏克思想的最著名学者,约翰·莫雷(John Morley)的另一本名著是Edmund Burke:A History Study.London:Macmillan and Co.,1867。中译本见约翰·莫雷:《埃德蒙·伯克评传》,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尽管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对历史的辉格解释提出重要的批判,但辉格史观对西方政党思想史研究其实一直持续发挥着重要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在其政党思想史研究著作《政党体制的观念:美国合法反对党的兴起1780—1840》(1969年)中精炼地概括了三种原型意义上的政党观,把柏克视为第三种政党观的首要代表,并充分肯定了他的重大突破:“柏克第一次打破了盛行的反政党论调,为政党原则和政党忠诚做出了辩护。”(5)Richard Hofstadter.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780—184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29.如霍夫斯塔德所言,他的这一观点主要受曼斯菲尔德的启发,但是在强调柏克政党理论的里程碑意义方面,以曼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施特劳斯学派不仅与辉格史观最为相似,而且更进一步。此外,霍夫斯塔德所概括的三种政党观原型显然带有辉格史观意义上的演进关系。意大利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政党与政党体制》(1976年)中对现代政党思想发展脉络做出了线索清晰的爬梳,在这个脉络中柏克占据了显要的位置。萨托利认为,柏克区别于以往理论家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率先“把政党视为既可尊敬又是自由政府的工具”(6)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辉格史观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随着巴特菲尔德对辉格史观的批判日益深入人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柏克研究热潮中,强调要从柏克写作的环境和意图的角度解释其理论的研究取向逐渐变成了新的主流。这种研究取向主张要评价柏克理论的贡献,一定要避免把我们今天的某些预设简单投射到柏克身上,或把某种后来的发展简单认为是柏克本来的目的而犯下颠倒时代的错误。恰当的做法是要着重考虑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他自己对形势和问题的评估,他所能运用的思想资源,他及其同僚或对手的直接意图与感受等因素。这种高度重视语境的研究取向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个不同的流派:第一是以曼斯菲尔德(Harvey C.Mansfield)为代表的施特劳斯学派(the Straussians)的“字里行间阅读法”;第二是以欧戈曼(Frank O’Gorman)、弗德(Archibald S.Foord)等人为代表的、强调政治史的政治语境主义;第三是以布鲁尔(John Brewer)、博克(Richard Bourke)等人为代表的、强调思想史的智识语境主义。这三个流派的共同点是反对辉格史观的目的论叙事,但在其他许多方面则分歧大于共识。三个流派争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第一,柏克是否是在为一个政党政府体制辩护?第二,柏克与博林布鲁克(H.J.Bolingbroke)的政党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二、施特劳斯学派的字里行间阅读法
说施特劳斯学派方法重视语境容易遭到质疑,因为施特劳斯是历史主义最著名和最深刻的批判者之一,而注重语境看上去像是历史主义的研究倾向。但是施特劳斯反对的是历史主义通过还原方法和相对主义来取消伟大理论的普遍意义的倾向,却不但不反对、反而十分看重从语境的角度解读文本含义的做法。(7)关于施特劳斯学派的研究方法及其与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之关系,可参见霍伟岸:《洛克权利理论研究》,7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施特劳斯那部著名的、也充满争议的《迫害与写作艺术》所提倡的、从伟大作家留下的显而易见的矛盾出发去探寻其理论表述的隐微教诲(esoteric teaching)的方法,就是基于一种从语境出发的假设:作者为了逃避环境对他的迫害而有意在显白教诲(exoteric teaching)中不表述自己的真实意图,但留下一定的线索供细心的读者去探究和发掘。(8)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施特劳斯学派方法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特别喜欢强调古今之争,而柏克被施特劳斯认为正是处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关键转折点上的重要思想家。(9)施特劳斯对柏克思想之于古今之争的意义的评述,可以凝缩为:“尽管柏克的‘保守主义’与古典思想高度一致,但他对于他的‘保守主义’的阐释却准备好了一种应对人类事务的方法,那对于古典思想而论,比之法国革命的理论家们的‘激进主义’甚至还要陌生一些。”见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3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有关评论见Steven J.Lenzner.“Strauss’s Three Burkes:The Problem of Edmund Burke in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Political Theory,1991,19(3),Aug.,pp.364-390。
以施特劳斯学派方法研究柏克政党思想最重要的著作无疑是曼斯菲尔德的《治国术与政党政府——关于柏克和博林布鲁克的研究》(1965年)。该书的核心观点是强调柏克倡导用一种崭新的政党政府体制,来取代单纯凭借政治家个人才能治国理政的传统做法。曼斯菲尔德认为:“柏克是第一位两党体制(或多党体制)的坚定支持者。”(10)Harvey C.Mansfield,Jr..Statesmanship and Party Government:A Study of Burke and Bolingbroke.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183.
柏克著名的政党定义 “政党就是基于他们都同意的某个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去促进国家利益的一群人的联合”(11)这个定义的英文原文是:“Party is a body of men united,for promoting by their joint endeavours the national interest,upon some particular principle in which they are all agreed.”见《伯克法国大革命前著作选》(Pre-Revolutionary Writings),187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经常被人们引用。但是,由于这个定义中的政党(party)和原则(principle)两个词都是单数形式,这就给它的解读带来了两种可能性,它既可以指由一个单一政党代表了唯一真正原则,也可以指同时存在若干个不同的政党,每个党都主张自己的特定原则。曼斯菲尔德持后一种观点,他给出的理由是:第一,有文本证据表明,柏克认为可以同时有几个政党合法并存;第二,考虑到当时英国的政治现状,柏克也不大会认为有可能由一个党吞并其余所有党;第三,柏克并未排除政党联合的可能性,但暗示政党联合不必试图消除政党纷争的根源;第四,在历史上,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竞争和对抗有助于英国宪制在统一之中保持多样性,而且这两党在宪制面临危机时通过光荣革命中的联合还拯救了国家,这说明柏克认为多党并存与仅有一党相比能够更好地捍卫自由。曼斯菲尔德强调说,柏克对政党的主要优点的阐发,“只有从一个政党体制的观察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政党成员的角度来看”(12)Harvey C.Mansfield,Jr..Statesmanship and Party Government:A Study of Burke and Bolingbroke.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183.,才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曼斯菲尔德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去论证,虽然柏克的《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以下简称《不满》)并未指明他的论辩对手究竟是谁,但这个人最有可能是活跃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著名托利党政治家和思想家博林布鲁克。(13)著名的19世纪柏克传记作家、自由主义政治家莫雷早在1879年就已经指出,柏克在《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中对忠于政党联合有何裨益的大胆论证,正是对博林布鲁克以政党为恶的观点的回击。参见John Morley.Edmund Burke:A History Study.London:Macmillan and Co.,1867,p.53。不过,莫雷并未对这个观点展开论证。曼斯菲尔德认为,正是在博林布鲁克的政党学说(14)关于博林布鲁克政党学说最重要的三篇文献《论政党》《论爱国主义精神》《论爱国君主的观念》,都被收录于David Armitage编:《博林布鲁克政治著作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的影响下,18世纪60年代英国政治舞台上的那个特定的政治派别(15)包括柏克提到的约翰·道格拉斯和布朗博士,也包括柏克用“许多其他人”来概括的、由曼斯菲尔德考证出来的欧文·拉夫海德、约翰·马里奥特爵士、托拜厄斯·斯莫利特、阿瑟·墨菲、托马斯·波纳尔、查尔斯·劳埃德、约翰·阿尔蒙和巴斯爵士等人。参见Harvey C.Mansfield,Jr.Statesmanship and Party Government:A Study of Burke and Bolingbroke.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p.86-105。才造成了朝野上下普遍不满的动荡局面。曼斯菲尔德指出,更重要的是,博林布鲁克的爱国君主论对乔治三世的影响很大,促使这位君主从登基伊始就极力推行那种无党派的、推崇个人德性的统治。博林布鲁克虽然比柏克更早为政党的政治正当性做过辩护,但博林布鲁克推崇的政党,其正当性来自它最终要消灭一切政党,使政治回归到爱国君主的德性之治的使命。这与那种渊源已久的、敌视内部分裂以维持政体的完整和谐的反党争思想传统,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与之相比,柏克则支持政党成为英国宪制中的“建制(establishments)”,政党竞争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利大于弊,有助于保持自由政体的健康稳定。在这个意义上,曼斯菲尔德认为,柏克才是西方反党争思想传统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批判者,也是把政党视为可敬的政治建制的现代政党观的奠基人。(16)不过,曼斯菲尔德也看到在博林布鲁克和柏克的政党理论之间存在更复杂的关系。曼斯菲尔德指出,博林布鲁克的爱国君主观念并不依赖于个人德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君主遵循特定原则(如“以有才具者代替仅靠家族背景的人,中止腐败,热爱和平胜于荣耀,以及促进商业等”)的意愿,这样,博林布鲁克也为以原则取代治国术的现代政党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博林布鲁克与柏克的政党观并不如初看上去相差那么远。参见Harvey C.Mansfield,Jr.Statesmanship and Party Government:A Study of Burke and Bolingbroke.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p.118-122。
曼斯菲尔德娴熟运用了施特劳斯学派的“字里行间阅读法”来解读柏克的政党理论,不但细致考察了柏克公开发表的著作和大量私人信件与手稿,还同样深入解读了博林布鲁克及其思想遗产继承者的有关文献,力求在两者的对比中凸显柏克政党理论的现代性。曼斯菲尔德认为,博林布鲁克的政党观与古典立法者的形象保持了一致,强调政治家的治国技艺;而柏克力荐的政党政府体制则可以避免对于不可多得的伟大政治家的依赖,以政党来矫治专制暴政危险,并驯化人民的自然激情,从而实现一种自由稳定的政治秩序,同时使得寻求最佳政体的古典政治思想的核心关切变得不再重要。因此,柏克的政党理论决定性地超越了博林布鲁克,体现了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背负了现代性的缺陷和弊病。
由于秉承了施特劳斯方法论区分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精神,曼斯菲尔德对柏克政党理论的很多阐发不免有过度解读的嫌疑,替柏克说出了很多他本来没有明确讲过的话。例如,曼斯菲尔德争辩说,柏克关于英国混合政体的概念不同于传统(如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因为在这个宪制中的每个要素(下议院、上议院、内阁大臣、国王)都以各自的方式“与人民相联系”“并从属于人民”(17)Harvey C.Mansfield,Jr.Statesmanship and Party Government:A Study of Burke and Bolingbroke.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158.,因此,从根本上说,柏克把英国政体视为一种民众政府(popular government)。根据曼斯菲尔德的解读,柏克对英国政体的这种观点非常接近于《联邦论》对美国联邦政体的看法,但柏克却从来没有像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James Madison)那样明确宣称其政体观的新颖之处。(18)麦迪逊对美国联邦政府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政制这一点有着极为自觉的认识,他说:“幸哉美国,我们相信:对整个人类而言,美国人民正在追求一种崭新的、更为高尚的事业。他们完成了人类社会编年史上一场无可匹敌的革命。他们编织出一个如网状结构般的政府,举世无双。他们设计出一个伟大联盟,使其存在,把改进和使之长存的任务,留给后继者。”见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9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曼斯菲尔德当然可以说,这正是他的研究发掘出来的柏克的隐微教诲,但多数历史学家仍然更愿意相信柏克对英国政体的认识并没有超出传统混合政体理论的范畴。(19)像许多典型的施特劳斯学派的作品一样,曼斯菲尔德这本关于柏克政党理论的研究专著在论证上颇为复杂曲折,多少沾染了所谓的隐微教诲的风格,因而不免遭到同行学者的诟病,见Kenneth Reshaur.“Review on Statesmanship and Party Government:A Study of Burke and Bolingbroke by Harvey C.Mansfeild”.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1966,32(2):pp.258-259。尽管遭到各种批评,但曼斯菲尔德的《治国术与政党政府》仍然是关于柏克政党理论的重要著作,而且许多解读颇具启发意义。
三、政治语境主义
与曼斯菲尔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欧戈曼和弗德为代表的政治语境主义方法强调要从柏克的政治职业生涯以及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情势的角度去理解其政治著述的确切含义。
欧戈曼认为,要恰当理解柏克的理论,必须将这一理论与当时引发其表达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解释。在他看来,柏克首先并且主要是一位政治家,他并没有后人一厢情愿赋予他的那种思想的体系性。也就是说,柏克从未提出过一种成体系的政治哲学,他所有的政治著述都是基于特定的政治情势,是受政治行动的需要而被激发出来的,而不是从某个既定的理论中推理出来的。由此,在政党宣传压力的影响下,柏克也会灵活地改变其理论基础,他在前后一致性方面出现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其实并不奇怪。柏克的理论创新也是因为“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政治思想的语言不再适合英国政治情势的现实了”(20)Frank O’Gorman.Edmund Burke:His Political Philosoph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p.12,p.33,p.15,p.34,p.34,p.35,p.35.。诞生于17世纪晚期、以洛克政治哲学为代表的辉格主义,在18世纪60年代的政治环境中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现实意义,柏克于是勇敢承担起重塑辉格主义的重任,他博采各家所长为己所用,包括洛克、博林布鲁克、新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主义者的理论资源,但并不超出传统哲学讨论的范畴,也未进行哲学方法的创新。出于这样的政治语境主义方法论,欧戈曼特别反对学者们脱离对当时政治环境的考虑而断章取义地引用柏克的话以求建构他的理论体系的做法。
从方法论出发,欧戈曼不点名地对曼斯菲尔德式的解读提出了批评:“事实上,我们应当避免受到这样的诱惑,即匆忙得出结论说柏克是在从一个政党体制的角度思考问题……柏克头脑中完全没有英国政治体制可能会迈向两党政府体制这样的观念。”(21)Frank O’Gorman.Edmund Burke:His Political Philosoph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p.12,p.33,p.15,p.34,p.34,p.35,p.35.欧戈曼的矛头所向除了曼斯菲尔德的著作之外,很可能也包括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对柏克所做的辉格式的解读。欧戈曼的批评理由之一是,柏克只是把政党当作解决紧迫的现实政治问题的权宜之计。欧戈曼进一步指出,柏克把政党视为一支相当保守的力量,政党只是用来解决冲突,恢复当时已经失衡的自由宪制,并不是用来促成像政党政府体制这样重大的宪制发展。即便仅就宪制恢复而言,柏克的着眼点也是落在使有德性的人通过政党这一组织工具团结起来进入政府从事公共服务,而不是使政党冲突制度化为政党体制。
欧戈曼研究了流行的政治语言在18世纪政治环境中发生的变迁,并从这个特定角度去看待柏克与博林布鲁克的关系,更加突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区别。换言之,虽然柏克并不是博林布鲁克的拥趸,但也从后者那里汲取了很多观念,包括“资产者要保持独立性的理想和他对腐败的痛恨”(22)Frank O’Gorman.Edmund Burke:His Political Philosoph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p.12,p.33,p.15,p.34,p.34,p.35,p.35.。欧戈曼指出,柏克当然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受到当时政治哲学的重大关切(如博林布鲁克同样关心混合政体失衡问题)的引导,他也没有开创新的政治哲学方法,而是在传统政治哲学语言的边界内既继承又改造旧的辉格主义。欧戈曼对柏克政党理论的创新性做出了重大限定:“他有可能是最伟大的、但绝非是第一个鼓吹政党的宣传家。”(23)Frank O’Gorman.Edmund Burke:His Political Philosoph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p.12,p.33,p.15,p.34,p.34,p.35,p.35.欧戈曼强调说,自17世纪晚期以来,为政党原则辩护已然形成涓涓细流,人们对政党的态度已经“从最初不愿承认其合法性慢慢发展到批判性地接受其宪制上的功能”(24)Frank O’Gorman.Edmund Burke:His Political Philosoph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p.12,p.33,p.15,p.34,p.34,p.35,p.35.。连博林布鲁克也承认反对党的正当性,并且能够容忍一个全国性政党的存在,因此,柏克着力阐发的罗金厄姆党(Rockingham Party)的原则,以及政党这一概念本身,“甚至在柏克之前就已经成为政治常识了”(25)Frank O’Gorman.Edmund Burke:His Political Philosoph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p.12,p.33,p.15,p.34,p.34,p.35,p.35.。如果非要强调柏克政党观的新意,欧戈曼认为那只能说柏克把一个“传统的妙策(nostrum)”用于解决当时面临的政治问题,是一种针对特定环境的解释应用上的创新。(26)Frank O’Gorman.Edmund Burke:His Political Philosoph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p.12,p.33,p.15,p.34,p.34,p.35,p.35.显而易见,这种意义上的创新是很难具有里程碑性质的。
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弗德的《国王陛下的反对党:1714—1830》是一部研究反对党的观念和制度是如何在英国得到确立的政治史名著。弗德对柏克政党理论的处理也是完全将其视为18世纪60—70年代英国的大政治环境和柏克本人所处的小圈子(罗金厄姆党)夹逼之下的产物。从柏克《不满》的写作过程来看,其主要内容和观点代表了罗金厄姆党的基本信条,具体的写作几易其稿,吸收了党内同僚的不少批评意见,因此其新意实在有限。从《不满》的观点意涵来看,弗德从那些看上去带有一般性的表述背后解读出罗金厄姆党人的实际意图:“他期待罗金厄姆党能够取得一场大胜,以便重建被认为是在乔治二世统治时期曾经具备的种种有利条件:伟大的辉格党人确保自己获得了关键的职位,获得了国王的信任,确保他们能够控制国王的影响,从而扩展他们的执政基础,足以使政府有足够的人可用,并且使他们的处境舒适自如。”(27)Archibald S.Foord.His Majesty’s Opposition:1714—1830.Oxford:Clarendon Press,1964,p.318.正是基于这个角度的分析,弗德才发现柏克政党理论的真实目的与博林布鲁克如出一辙:柏克的“诚信之士的政治联合”与博林布鲁克的反对党都将“终结对于反对党的需要”(28)Archibald S.Foord.His Majesty’s Opposition:1714—1830.Oxford:Clarendon Press,1964,p.318.。在弗德看来,柏克政党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用一种创新的方法和复杂微妙的论证重新表述了罗金厄姆党的基本信条:“在他的笔下,个人的行动变成了制度,政党策略的因素变成了原则,政治分歧变成了善恶之分。”(29)Archibald S.Foord.His Majesty’s Opposition:1714—1830.Oxford:Clarendon Press,1964,p.316.弗德指出,柏克在《不满》中表述的政党理论不过是对众所周知的老辉格党信条的一种重述,没有太多新意,当时著名的辉格党政治家贺拉斯·沃波尔(英国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之子)就称此书“太冗赘又太考究,让早知其事者厌烦,又让不知其事者难解”,见前引书,321页。把政治分歧变成善恶之分这一点,确实不由得让人想起博林布鲁克政党学说通篇充斥的善恶交战的道德语言。最后,从《不满》在现实政局中激起的反响来看,柏克的这本小册子其实远未达到罗金厄姆党的政治目的,可以说是一部失败的政治作品,时人只是把它看作反对党时常表达的老生常谈,柏克那些关于政党的可尊敬性的论述不过被视为罗金厄姆党为自己争取权力的借口罢了。从政治语境主义出发,弗德虽然承认柏克和博林布鲁克的著作都具有超越作者本人职业生涯的生命力,但他始终强调一定不能被其表述上的普遍性语言所迷惑,而误以为一个以真诚的方式自我表达的政党在政治上就真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纯良。
四、智识语境主义
与政治语境主义更加注重从政治环境的角度解读文本不同,智识语境主义关注的焦点在于定位文本所处的思想脉络,以及把文本视为作者针对特定时代问题做出的一种具有政治行动意义的回应。这种方法论一般被认为是由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波考克(J.G.A.Pocock)等人所开创。在关于柏克政党理论的研究中,下文将述及的两位秉承智识语境主义的学者布鲁尔和博克都有过在剑桥大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经历,他们在著述中也对自己的方法论有着高度的自觉,并多次引用斯金纳的方法论著作。
表面上看起来,智识语境主义与政治语境主义似乎都是要回到文本的直接历史语境中去还原作者本来的写作意图,但是两者之间其实还是有重要区别的,智识语境主义格外重视作者为什么要使用某个特定的政治论证,以及该论证与当时惯用的、围绕同一问题的其他论证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
布鲁尔从柏克写作《不满》的本来意图以及政治同僚对这本小册子的反应来界定柏克政党理论的性质,并对曼斯菲尔德的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在他看来,柏克的本意不是要为政党本身辩护,而是试图说服当时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各个派别进行一种特定的政治联合,柏克把这种在他看来具有政治正当性的联合称为政党活动。无论是罗金厄姆侯爵(the Marquis of Rockingham)本人,还是罗金厄姆党的其他成员,甚至当时流行刊物上的评论文章,都没有把柏克的这篇政论文看作是在倡导一种政党政府,他们认为柏克只不过是在倡导成立一个联合起来的反对党。而且,如果柏克真的是在提倡一种政党政府体制,那么这种倡议的结果几乎必然会是分裂议会中的反对党,并疏远那些不属于任何党派的独立议员,这样的结果与柏克写作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如果柏克并未意图倡导政党政府,他也就不可能试图预言英国的宪制发展。”(30)John Brewer.“Party and the Double Cabinet:Two Facets of Burke’s Thoughts”.The Historical Journal,1971,14(3),Sept.,p.495,p.491.
布鲁尔起初确实致力于淡化柏克政党理论的新意,不过他并不完全同意弗德把柏克与博林布鲁克的学说混为一谈的做法。布鲁尔认为,虽然柏克有可能持有一种关于反对党的末世论看法,却并不适用于政党,柏克眼中的政党在取得权力之后仍会继续存在,并不会一劳永逸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柏克寻求将一切形式的政治联合都看作正当,也不意味着他把政治视为(具有同样正当性的)相互对立的政党之间的一种有益的对话。”(31)John Brewer.“Party and the Double Cabinet:Two Facets of Burke’s Thoughts”.The Historical Journal,1971,14(3),Sept.,p.495,p.491.柏克一直坚持政党与派系之间有本质区别,政党是一种致力于实现国家利益的具有正当性的联合,而派系这种不正当的政治联合则在追求狭隘私利的过程中不惜牺牲公共利益。不过很可惜的是,布鲁尔指出,柏克一贯坚持的政党与派系的区分,以及他关于政党与自由政府密不可分的观点,在18世纪60—70年代已经是一种老生常谈,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布鲁尔表明,从18世纪30年代起一直到柏克1770年发表《不满》之前,有不少著作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尔作为例证举出的那些著述的发表时间都晚于博林布鲁克的《论政党》(1733—1734年,其中同样区分了政党与派系的不同,并强调了自由宪制之下政党的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柏克政党理论相对于博林布鲁克的创新性又大为降低了。(32)John Brewer.“Party and the Double Cabinet:Two Facets of Burke’s Thoughts”.The Historical Journal,1971,14(3),Sept.,pp.491-492.布鲁尔在这篇文章中认为,柏克政党理论的创新性只是在于他“扩大了具有正当性的有组织政治行动的范围”,因为罗金厄姆党作为一种小型的受人尊重的政治联合体,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辉格党或托利党,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党。
有意思的是,布鲁尔几年后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承认自己先前的文章对柏克政党理论的创新性估计不足。布鲁尔在一篇对包括欧戈曼著作在内的两本新著的长篇书评中更新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批评欧戈曼低估了柏克理论的新意。布鲁尔比较了乔治二世和乔治三世时期两位国王对待政党的不同态度,以及反对党相应地必须采取的不同策略:乔治二世统治下,辉格党长期占据政治主导地位,是因为他们能够说服国王相信辉格党与托利党具有本质区别,要想维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坚持由辉格党来主导政府,这样一来,反对党就只能强调两党的区分不具有重要意义,反对党的使命就是要终结一切政党,实现无党派的爱国君主统治;而乔治三世甫一即位就敌视一切政党,原来一直执掌政府的辉格党各派别现在被迫处于反对党的位置,他们相应的策略就是坚称辉格党与托利党的斗争依然存在,并且在形式上转换为反对党与政府的对峙。从这样的语境来看柏克当时承担的理论任务,布鲁尔发现《不满》与此前对反对党的所有理论辩护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柏克的反对党是捍卫政党而不是摧毁政党的反对党”,因此,柏克确实声称政党“应当成为政治的持久不变的特征”“而且内在地有益于政治体”(33)John Brewer.“Rockingham,Burke and Whig Political Argument”.The Historical Journal,1975,18(1),Mar.,pp.194-195,p.195.。这样,布鲁尔就大幅修正了自己从前对柏克政党理论创新性较低的评价,表明其重大贡献在于“第一次使那些并不必然是反对党的政党具有了正当性”(34)John Brewer.“Rockingham,Burke and Whig Political Argument”.The Historical Journal,1975,18(1),Mar.,pp.194-195,p.195.。布鲁尔批评欧戈曼没能看到政党的概念与反对党的概念并不必然相同,因而也就错失了柏克观点的新意。布鲁尔强调说,博林布鲁克的政党观是一种末世论的观点(这是弗德的说法),但柏克的政党观却不是末世论的,政党将是政治生态上永恒的风景,因此,柏克与博林布鲁克的政党理论之间还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根本的区别。于是,布鲁尔在批评欧戈曼的同时也就隐含地指出了弗德的错误。在布鲁尔看来,欧戈曼和弗德仅仅关注到了柏克著述的政治语境,而没有深入智识语境的层次,未能辨识出柏克政党论证的与众不同,因而也就误以为柏克的政党观与博林布鲁克雷同。
博克通过对新近被归于柏克之作的一篇新文献《论政党》的分析,进一步确证了柏克在政党理念上对博林布鲁克的超越。这篇文章写于1757年,比柏克阐发其政党学说的两篇主要文献《对近著〈当前国家状况〉的评论》(1769年)和《不满》(1770年)早很多。尽管这篇文章篇幅短小、结构也不完整,但其在政党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上却与柏克后来那些著名的作品有着显著的一致性,而且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该文对博林布鲁克的政党观做出了重要的修正。博林布鲁克把政治力量的分裂和对峙视为无知和迷信的产物,认为需要通过理性(以爱国君主为代表)来加以克服。但柏克却对一个完全根除了政党的政体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非常担心这样的结果会动摇英国宪制的本体,因为缺乏任何的党派对立将会导致绝对政治权威的树立,这会从根本上削弱英国的自由宪制。柏克阐发其政党学说的意图就在于“限制不负责任的主权权力的行使”(35)Richard Bourke.“Party,Parliament,and Conquest in Newly Ascribed Burke Manuscripts”.The Historical Journal,2012,55(3),Sept.,p.632.。柏克的政党要致力于推进英国下议院(作为混合政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事业,为的是以此来正当地反对王权的不恰当行使,从而保全英国的混合政体的性质。柏克在《论政党》中表明,抽象的公众概念是无法动员起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的,只有以伙伴关系的方式服务于既定的政治纲领和目标,才能促成政治合作。因此,柏克的政党绝不是博林布鲁克的末世论式的政党,“在一个自由政体中,政党不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永远有用’”(36)Richard Bourke.“Party,Parliament,and Conquest in Newly Ascribed Burke Manuscripts”.The Historical Journal,2012,55(3),Sept.,p.633.柏克《论政党》的原文,见644-647页。。
博克试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智识语境中来定位柏克的政党论证。他指出,柏克显然赞同休谟关于“政党与自由政府密不可分”的观点,而且他也意识到18世纪通过激进辉格党作家托兰德(John Toland)和莫伊尔(Walter Moyle)复兴了马基雅维利关于派系之争可以产生有益后果的观点(37)关于马基雅维利对党争问题的论述,可参见霍伟岸、谈火生:《马基雅维利论党争》,载《学海》,2018(3);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党争观在18世纪的复兴,可参见Terence Ball.“Party”.In Terence Ball,James Farr,and Russell L.Hanson(eds.).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67-169。,但是这种对于自由与政党竞争之关系的论证仍然没有超出传统的反党争思想范畴,政党最多只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柏克则决心把政党确立为一种全然受人尊敬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克对休谟和博林布鲁克的政党观都做出了显著的修正。博克批评欧戈曼和弗德混淆了柏克与博林布鲁克的政党观的性质,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们没有在政治论证的层次上进行仔细辨析,因而未能充分注意到柏克对于“政党在自由国家中永远有用”这一观点的强调。(38)虽然博克强调在《不满》中,柏克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政党在自由国家中永远有用”这样的观点,但是毕竟柏克在《不满》中没有明确使用过“政党永远有用”这样的表述,至于其他有关表述是否可以被等同于“政党永远有用”的观点,则是一个解读上的问题,至少欧戈曼和弗德就没有朝这个方向去解读。
五、结语
虽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标准教科书中,柏克一般被视为现代政党政治观念的奠基人,但是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知,这种看法首先成型于辉格史观主导下的19世纪,而不是柏克本人生活的时代。到了20世纪,随着对辉格史观的反思日益深入,以及大量柏克私人文件的公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柏克研究热潮中,关于柏克政党理论究竟有多少新意的问题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观察有关争论可以发现,坚持区分隐微/显白教诲和强调古今之争的施特劳斯学派学者不但继续坚持柏克政党观的分水岭性质,而且比辉格史观更加强调其现代意义,当然与此同时也指出其蕴含的危险;那些秉承从政治环境角度解读文本的政治语境主义的学者,总体上倾向于贬低柏克政党理论的新意,尤其反对从柏克带有很强现实政治意图的著述中抽象建构出某种普遍性和体系性的理论,在他们看来,柏克的政党思想与时人的一般看法大体合拍,其新意更多体现在文字表述上,而不是思想内容本身;那些奉行从思想资源和政治论证角度解读文本的智识语境主义的学者,对柏克政党理论之创新性的看法则大都居于前两派学者之间,他们既认为施特劳斯学派学者夸大了柏克理论的里程碑意义,又觉得政治语境主义的解读过分贬低了柏克的理论贡献,他们承认柏克政党理论有相当大的新意,但是又强调这新意主要体现在政治论证上的革新,而不是柏克先知般地预见或预言了一个世纪之后才会出现的以大众民主为基础的政党政府体制。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学者们对柏克政党理论究竟有多少新意的判断只是由其研究方法论决定的,那就犯了过分简单化的错误。一个富有启发的例外是历史学家罗克(F.P.Lock)的观点。
与前述政治语境主义和智识语境主义评论家相比,罗克对曼斯菲尔德的批评最为彻底,他不仅指责曼斯菲尔德关于柏克是第一个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倡导者的观点,是犯了颠倒时代的错误,而且干脆连“柏克有一种政党理论”这一说法也一起否定了。罗克认为,如果谈论“柏克的政党理论”,就相当于陷入了斯金纳所说的“学说神话”的谬误,也就是历史学家不适当地假定每个经典作家对构成其主题的各个话题都阐发了某种学说。(39)Quentin Skinner.“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In James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pp.29-67.“对柏克来说,政党是自由政府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现实,是善与恶之间无休无止斗争的一个不幸的副产品。”(40)Quentin Skinner.“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In James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pp.29-67.在罗克看来,柏克观念中的政党竞争的图景更有可能是“一个具有德性的单一政党对抗由毫无原则的恶棍组成的若干派系”,而不是自由主义者臆想的那种若干怀着不同的美好社会愿景的政党之间的良性竞争。(41)F.P.Lock.Edmund Burke,Vol.I:1730—1784.Oxford:Clarendon Press,2006,pp.295-296.
虽然在方法论上罗克显然是斯金纳智识语境主义的信徒,但在结论上他却比秉持政治语境主义的欧戈曼和弗德走得更远,干脆认为连谈论柏克政党理论本身都是犯了“学说神话”的谬误,既然柏克根本就没有提出过一种政党理论,而只不过是有一些关于政党的零散表达、不成系统的观点,那么讨论柏克政党理论有多大新意就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例外的存在只是提醒我们不要过分简单化地把结论与方法论对应起来,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方法论对研究结论不会产生显著影响。(42)需要说明的是,柏克研究者并不是只有前文专门讨论的这几种方法论,其他比较重要的方法论至少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自然法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柏克研究代表作如麦克弗森的专著《柏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和Harold J.Laski.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Locke to Bentham.London,New York,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0,Chapter 6;自然法学派的柏克研究代表作如Charles Parkin.The Moral Basis of Burke’s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Peter Stanlis.Edmund Burke and the Natural Law.New Brunswick,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58;Francis Canavan.The Political Reason of Edmund Burke.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60。但是这些研究对柏克政党理论的讨论很少,因此本文基本没有涉及。另外,这些研究在奉行政治语境主义和智识语境主义的学者看来都犯了脱离直接历史语境而解读文本的错误。
尽管我们不是在决定论的意义上讨论方法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已经足以让我们意识到,在处理像“柏克政党理论究竟有多少新意”这样的思想史问题时,研究者必须首先对自己采取的方法论有清晰自觉的认知和反省。方法论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关涉到如何抵达真相,甚至是否存在真相,以及真相是何种意义上的真相等根本问题。不同的方法论之间的相互批评既然有认识论乃至世界观上的根源,那么这种多元方法论并存争鸣的状态也就必然是思想史研究的常态了。研究者采用何种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个信念问题。
在方法论自觉的前提之下讨论“柏克政党理论究竟有多少新意”,我们还有必要区分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在柏克自己的意图中他的政党理论有多少新意;第二是在柏克的目标读者群看来他的政党理论有多少新意;第三是在后世的读者看来他的政党理论有多少新意。政治语境主义和智识语境主义更多地是在前两个层次上进行探究,而秉承辉格史观的学者和施特劳斯学派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第三个层次上探索柏克的理论贡献。事实上,后世的读者由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对解读柏克理论的需求不同,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有待解读的研究对象,而本文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这个方向上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