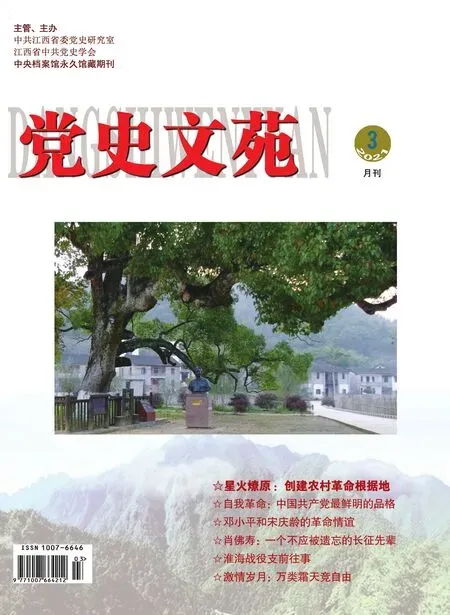『外乡客』的红色传奇
□王 坚

他是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场上负伤掉队的江西籍红军排长,一个在闽赣交界处的深山过着“野人”般生活的外乡来客,也是与反动势力斗智斗勇的地下交通员,更是随时准备献身就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近日,笔者来到长汀县四都镇采访老红军李仰明的后人,追寻一位红军战士用热血和生命谱写的“红色传奇”。
血泪凝成的人生档案
查阅干部档案得知,李仰明原名张天明,曾用名杨振明。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县湖村乡黎家村,1929年任少先队队长,1930年7月被编入方志敏等领导的红十军,参加过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1933年3月,他由戴国旺、洪协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编入红七军团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历任战士、班长、排长。1934年3月29日,在沙县战斗中他的左手和右脚被打断,转入红军第四后方医院治疗。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张天明因战伤未愈不能随队行动,由组织介绍到江西瑞金县陶阳区游击队,陶阳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胡荣佳将其秘密转移到长汀县四都区玉竹杏村群众家中继续养伤,后改名李仰明。
伤愈后,李仰明左大臂肌肉萎缩,右脚行走困难,继续在胡荣佳、彭胜标等领导的中共汀瑞县委和汀瑞游击队工作。1938年春,汀瑞游击队大部分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留下的少数人员在刘国兴、曾玉成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游击斗争,李仰明担任汀瑞游击队的联络员、专买员。1946年3月,汀瑞县委、汀瑞游击队遭敌破坏。李仰明在四都荣坑地下支部的领导下,坚持斗争至全国解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的李仰明积极参加剿匪、反霸斗争,先后担任过民兵队队长、副乡长等职。1957年8月19日,经中共龙岩地委批复,恢复其1933年入党的党籍。1958年,他担任长汀县红楼公社财粮委员、副社长,四都公社工交部部长等职。1959年,他担任红楼乡副乡长。1960年,四都区工委将其上报转为正式干部,享受老红军及老地下党员待遇。
泔水桶捞食的“流浪汉”
现年81岁的李仰明儿子张湖金心情沉重地说:“父亲20岁那年在沙县战斗身负重伤,敌人步步紧逼,红军医院被包围,伤员各自突围。父亲从江西石城转移到瑞金,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进入深山中的若白、陶珠等地,在山寮里藏身。天寒地冻,路上到处都有追兵,父亲一边走一边摘树叶充饥。有一天,他在偏僻的农田里捡到一些谷穗,用石头捣破谷壳,找个烂陶缸煮。刚煮好,敌人又追来了,他赶紧往深山密林钻,敌人的机枪疯狂扫射,幸好父亲没有中弹。父亲翻山越岭来到钟坑的一座山寮里,从附近的田里撸了一些谷串,塞进嘴里干嚼,嚼完再把渣吐出来。有段时间,他一个人在山上漫无目的连走带爬,每天只能吃一点竹笋,最长时间整整44天没有吃一点像样的食物。”
“有一天,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冒险下山偷偷进了陂坑村,挨家挨户在泔水桶里捞食物吃。父亲那时衣衫破烂,头发胡子蓬乱,身上又脏又臭,群众以为来了个神经质的叫花子。过了两天,他在一家泔水桶捞食时,有人出来问他是从哪里来的。恰好主人吴长有是江西弋阳人,比父亲更早一年来到陂坑,父亲讲的乡土话他听得懂。吴长有也是方志敏的老部下,曾经在红楼乡苏维埃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两个老乡战友劫后重逢,抱头痛哭,这时大概是1935年的4月到5月之间。父亲命不该绝,他乡遇故人,总算有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吴长有叮嘱父亲小心藏身,告诉父亲若白村的伪保长张振兴是地下党员,并通过张振兴联系上了汀瑞游击队的胡荣佳和彭胜标等领导。因为父亲的伤势实在太严重,无法随游击队行动,所以组织上通过统战关系,把他留在玉竹杏自然村,作为‘难民’安置,实际上是转入地下工作。”
肩负特殊使命的“木匠”

李仰明的战伤残疾证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下,汀瑞县委在荣坑一带成立了地下党支部,一些失散的红军战士和苏区干部继续开展秘密斗争。中田村由钟同春和赖万和负责,钟同春外号‘丈八筒’;荣坑、陂坑由江西于都人刘腾洪负责,他是游击队副队长;禾上杏由池家香负责,他的外号‘连城佬’。父亲会做木工,大家叫他‘木匠佬’。父亲在红军部队时学过修理枪械,游击队有一支子弹卡壳的长枪,父亲用松脂润滑后,枪膛松开,卡死的子弹退了出来,枪支就可以用了。有的枪支退弹钩坏了、有的木枪柄烂了,无论铁件活、木件活,父亲都能做得有模有样。父亲天天忙着修理枪支,尽管环境艰苦,但心里美滋滋的。”
荣坑地下支部的成员以各种身份为掩护,走村串寨秘密串联。地下支部成员高度保密,他们都在当地结婚成亲,安家立业,活动在游击队的外围,只有刘国兴等汀瑞游击队的主要领导掌握内情。荣坑的伪甲长刘茂良、伪保长刘耀文没有入党,陶朱的保长刘辉山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是“白皮红心”的地下工作人员,利用公开身份为游击队工作。遇到国民党政府征收粮食,就把空谷壳烧毁,应付上面说谷子被游击队烧了,其实是送上山给游击队吃了。接到抓壮丁的通知,就暗中通知青年男子离家躲避。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伪造新四军文件,通知汀瑞游击队空手到西江县领武器,结果前往的游击队队员被敌人重兵包围监禁。一年后,刘国兴组织邹道隆、陈学彬等人越狱成功,回到老根据地重新组建汀瑞游击队。后来,在陂坑山塘坳、银子坵、玉竹杏长窝等地各有一个队,他们从三个人、两条半枪,到1946年发展到有96支枪、100多人。汀瑞游击队被破坏后,地下党支部成员没有受到损失,又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新组建的汀瑞游击队藏在大山深处,所有的生活和战斗物资,都是通过地下支部成员想方设法到各地采购,并冒险运送上山。
“我们在玉竹杏的家是汀瑞游击队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这里距离瑞金的庵子前和荣坑、楼子坝各10余华里。右边山岗可以直下姜畲坑,左边火星岽可以直下陂坑、荣坑、岭背山(属瑞金)等地,前往各个游击队驻扎点可以不通过村庄,以免不测。父亲经常行走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脊线上,往返于各个游击队受领任务。游击队的同志也时常出入我们家,我见过姜畲坑游击分队分队长刘邹和,他是个文化人,瘦高个子,背的是驳壳枪,解放后担任过瑞金石水乡乡长。还有陂坑游击分队的负责人刘腾洪,他是江西于都人,解放后担任过荣陂乡乡长。他们和父亲的感情很好,战争年代结识的生死兄弟,真正是手足同心。”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断绝人民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血肉联系,在革命根据地实行“移民并村”,很多群众的房屋都被欧阳江的白军烧毁。“我们家从最早居住的玉竹杏自然村先后搬迁到楼子坝的洋坪、黄坊、中田、赖坑、瑞金的达陂等地,房屋前后被烧了三次。每次搬家父亲都很无奈,但一有机会,他就会尽快和附近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心里才会踏实,并且想方设法完成游击队交给的任务。”
斗智斗勇死里逃生
“父亲说汀瑞游击队有各种人才,有个外号叫‘鹅佬’的队员是瑞金黄柏乡人,枪法奇准。有只300多斤的野猪在山寮附近出没,睡眼蒙胧的‘鹅佬’听声辨位开枪射击,一枪就把野猪击倒了。还有一个外号‘剃头佬’的瑞金九堡人,也是神枪手,游击队开到瑞金通往赣州的公路上,伏击国民党的运钞车,他一枪就把白军的驾驶员打倒了。游击队不断扩大,需要补充枪支弹药。有一次,‘鹅佬’等人带短枪到濯田采购武器,路过四都区时,按照事先的互不侵犯约定,四都的民团装作不知情,任由游击队员通过。偏偏有个团丁在炮楼上探头探脑,‘鹅佬’以为对方要发难,抬手一枪击中团丁的左眼。
“有一回,游击队副队长刘腾洪和父亲一起到濯田,在墟场上采购了许多牙刷、牙粉、毛巾、电池等物资,夜宿濯田客店时,被反动民团的眼线盯上了。第二天,濯田王猫公为首的反动民团在白沙岭一带设伏。返回途中,刘腾洪发现情况异常,赶紧和父亲互通‘江口’(暗语):‘今天的猪是杀了吃还是吃了杀?’父亲一听心里有数,果断对刘腾洪说不能硬拼。两人拉开距离,走到一处悬崖边,装作拉尿,同时翻身滚下悬崖,抄小路向牛脑屎高峰靠拢。匪徒们追赶了一阵,不敢开枪,害怕等候在牛脑屎的游击队员听到枪声赶来接应。父亲说,这次遇险东西没丢,还捡回了两条命,自己都不敢相信哦!
“父亲逃难到四都,与我生母陈二嫲结婚,母亲20多岁因房屋被烧困在里面窒息身亡。后来,父亲与我后母邹新元成亲。后母也是一位地下交通员,父亲和她约定了许多暗号,比如发现有敌人进村,母亲就会喊:‘仰明啊,牛要吃菜,快去赶开!’家中屋檐下挂竹篮、畚箕,各有不同的意思表达。1946年12月上旬,欧阳江的伪保安团分两路包围玉竹杏。我们家屋后的陡坡长满了茂密的芦苇,父亲当时正在吃饭,见状一头钻进门前土坎下的荆棘丛中。身上的衣服裤子全被锋利的钩刺挂住了,光着身子冲出去了。母亲和招仔、冬秀嫲、永汉佬、高大嫂等人被敌人绑了。白军把母亲吊起来打,用滚烫的香火灼烧母亲的身体,逼她说出游击队的下落。母亲回答说,自己就是一个烧火做饭的农家妇女,什么都不知道。折磨了半天后,敌人要吃饭,才给母亲松绑。机智的母亲杀鸡、切腊肉做饭给他们吃,提了一只烂箩筐装作去地里拔萝卜炖猪肉,转眼从父亲逃命的荆棘丛中也溜走了。敌人在我们家整整住了三天,把家里所有的鸡鸭腊肉白米都吃得精光,弄得满地都是鸡毛鸭毛。离开的时候恼羞成怒,把家里的物件全砸了,往酒缸里拉尿、放鞭炮炸,一把火把我们家的一栋横屋烧毁了。

张胡金出示父亲李仰明遗像
“我和姐姐、哥哥头天就被抓了,看到父母生死不明、其他长辈被绑被打,也吓得半死。白军一个个拷打审问都没有结果,只好把大人们放了。第二天夜里,满脸白须的永汉老公公捡了一点白军吃剩的锅巴给我们吃。随后逃出去的母亲,在山上边走边拍巴掌打暗号,终于在对面山上的一座废瓦窑里找到了父亲。这年我不满7岁,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惊吓,幸运的是父母亲和哥哥姐姐都有惊无难。”
苦难岁月难掩丹心
“父亲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外乡来的难民,在四都山区安家落户。他有木匠身份作掩护,所以在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的时期,仍然可以出入各个村庄。他来到四都不久就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担负起党的地下接头任务。因为这个特殊的使命,我们全家同甘共苦,一起挨过了漫长的苦难日子。
“1943年,家中房屋被反动派烧毁,全部谷物、衣服付之一炬。生母陈二嫲因为出麻疹行动不便,吸入二氧化碳过多中毒而死。家中一无所有,多亏乡亲们帮助料理了母亲的后事,留下四个年幼的孩子。姐姐李秀子8岁,养姐刘长发妹8岁,哥哥李金子6岁,我才3岁。三年后养母来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才开始恢复正常。家中是游击队的接头户,接待往来的游击队队员是常事。为了生存,对待上门的白军反动派,甚至一些流氓地痞也要热情接待,免得生出是非。家里所有的食物,每块肉、每个蛋都要留着,以备急用。我们几个孩子很少有米饭吃,每天中午吃牛角豆,晚上吃‘懒人豆’,或者中午吃玉米,晚上吃豆角煮粥。我没有床铺也没有棉被,一年四季睡在一块捡来的布行招牌匾上,盖的是烂棉袄和蓑衣。我一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穿父亲亲手做的木屐,也从没有穿过棉袄。1953年,姐姐嫁到石门背,姐夫给我织了一双布鞋,我非常开心。小时候,我们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这么狠心,不近人情。长大才知道父亲母亲的苦衷,他们都是有特殊使命的人。父亲聪明好学,平时在家做一些竹木的日常用具,挑到圩场上去卖,有时候去深山的纸槽里打工赚点苦力钱。家中经常断粮,我们每天眼巴巴等着父亲带米回家,可以煮点稀菜粥喝,否则就只能吃蔬菜。尽管家庭生活极为困难,但父母亲从来不抱怨、不消沉,总是教育我们说,‘熬过暗晡见天光’,苦日子总有一天会到头。现在看来,他们才是真正有信仰、有骨气、有追求的人。
“现年86岁的刘长发妹,4岁时抱养给李仰明做女儿。在她的记忆中,养父始终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地下党员:‘听父亲说,他是在打连城的坑子堡时负重伤的,但他从来没把自己当作残疾人。有一次,游击队从瑞金打土豪回来,在玉竹杏我们家歇脚,吃过饭匆匆离开,父亲煮了一些蛋给游击队队员路上吃。他们前脚走,父亲就拿着竹扫把,一拐一瘸上山把路上的脚印仔仔细细地清理干净,然后把家里的泔水挑去喂猪,免得反动派来发现异常。父亲粗中有细,做工作很认真,游击队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很信任他,对我们孩子也很疼爱。有一年冬天,游击队队长刘老三在我们家住宿,我给他端了一盆热水烫脚。他看到我的头发蓬乱打结,责备父亲不关心我,和父亲开玩笑说,再不给我剪头发,他就帮我用火烧了。父亲一听这话,心里很难过,呆呆地很久没说话。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不是不爱儿女,真的是心思精力全部用在游击队队员身上了。作为儿女,看到他去世33年了还有人来访问他,也是对他老人家的安慰呀……”
采访中得知,李仰明和江西老家的哥哥同一年参加红军,上半年哥哥牺牲后,作为红军烈属家庭,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很多照顾,下半年李仰明又自动报名参军。新中国成立后,李仰明、邹新元夫妇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就像山间遍布的翠竹和山茶花,默默地用自己的一生装点人间的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