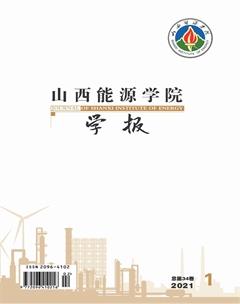探究纪录片创作中的共情性困境
吴茜
【摘 要】 纪录片可以让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观众产生共鸣的基础上,表达一种共同的人性。因此,引起观众的共鸣是纪录片创作者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虽然纪录片创作者经常表现出创造共鸣的想法,但他们经常做不到。本文通过分析南非纪录片《被击毙的矿工》,研究创作者意图与受众共情性之间的差距。从纪录片创作的角度探讨该纪录片共情创作的效果,以及从中获得的创作经验。
【关键词】 共情性;共情传播;纪录片
【中图分类号】 J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21)01-0085-02
本文以当代南非纪录片《被击毙的矿工》为例,探讨纪录片创作者意图与观众共情性之间的差距。之所以选择这部纪录片,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议程,而且明确表示要在国籍南非以外更广泛的受众中传播。
一、研究背景
纪录片创作者常常会陷入这样一个误区,误认为观众的反应会自觉地与自己所预设的创作意图相吻合。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谬误隐含着一种假设,即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观众观影立场的“主导霸权”建构是电影制作的常态。这取决于接收方以发送方预期的确切方式来解释消息的含义,即编码与解码匹配。然而,正如霍尔所指出的那样,观看行为涉及到几种阅读立场,“解码并不必然地从编码中产生”。同样,美国电影学者维维安·索布切克认为,电影是电影制作者和观众之间的对话,因为两者都是观看主体。由于这不是一种对称的关系即电影制作者和观众的认知只会在不同程度上趋于一致,所以索布查克警告说,不要将作者的表达和观众的感知混为一谈,这种假设错误地认为,感知的中心只在文本中。
本文通過两个阶段来探讨在南非纪录片《被击毙的矿工》中,纪录片导演的意图及其影片在唤起观众共鸣方面的不足。首先,需要先评估与纪录片发行背景相关的经验数据,然后通过对纪录片文本的认知分析来假设影片对观众的“实际”影响。第一阶段通过整理实证数据发现,《被击毙的矿工》有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引起人物共鸣的意图也与社会行动主义有关。纪录片制作人在采访和书面声明中公开宣布了他们的目标,同时这些目标也体现在纪录片的预告片、海报和新闻资料袋等副产品中。第二阶段的分析采用艾米·科普兰的高层次共情模型,结合评价理论和人物形象理论,进行文本分析。结果似乎与作者的意图有部分矛盾,揭示了电影未能建立起同理心主要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纪录片创作者偏重于理性的论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叙述,而不是那种可能鼓励共情的情感论证。
纪录片创作者忽视了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性,特别是人物动机与其目标或欲望对象的确立。
本文目的不是要否定这部优秀且有一定影响力的纪录片或者这部纪录片的创作者,而是要提高纪录片创作者意图和观众反应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批判意识,从而产生关于叙事移情和作者身份之间的关系的知识,这可能对纪录片的学者、从业者和教育者都有一定的帮助。
二、纪录片《被击毙的矿工》共情效果分析
《被击毙的矿工》是2014年由编剧兼导演Rehad Desai和制片人Anita Khanna制作的纪录片,由南非公司Uhuru Productions与多家欧洲和日本广播公司合作拍摄。该片的新闻稿将故事概述如下:2012年8月,南非最大的铂金矿之一的矿工为争取更好的工资开始了一场自发式罢工。六天后,警方使用实弹残酷镇压罢工,造成三十四人死亡,多人受伤。影片将三位罢工领袖采访与令人信服的警方录像、电视档案以及在随后的大屠杀调查委员会中代表矿工的律师的采访交织在一起,讲述了这是由于南非新生的民主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断层、长期的贫困和二十年前对所有人改善生活的承诺没有兑现才造成的这一场悲剧。该片自上映以来,在国际上取得了极大的曝光率和好评并于2015年获得国际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
该片制作人Khanna回忆起这一创作过程的开始表示,当时他们决定关注人物,而不是仅仅关注事实和论点。“我们在寻找一个有人物的故事,同时也能拍成纪录片的故事。我们想找一个能在影片中发挥作用的故事。我们并不只是想去某个地方谈论这些问题。”在另一次采访中,导演Desai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利用电影的力量来激起观众的反应,激励他们采取行动。纪录片创作者的目的是讲述矿工的故事,从而引起全球观众对他们的同情。然而,Desai的后一个评论表明了一个平行但也矛盾的议程:纪录片制作者试图通过诱导一种内疚感来震慑观众,让观众觉得自己是大屠杀的同谋。而这种内疚感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观众的立场相对于矿工的立场来说是一种权力和特权。
同理心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电影学者一致认为,这种情感交流也会发生在银幕叙事中的人物身上,高层次的共情取决于三个阶段:情感匹配、面向他者的视角把握和明确的自我与他人的区分。
“情感匹配”表明我们已经成功地匹配了另一个人的情感或情绪;“面向他人的视角把握”则让我们想象自己身处他人的境遇,从他人的角度进行评价;最后,“明确的自我与他人区分”使我们能够与他人进行深层次的接触,同时防止我们忽视自我的终点和他人的起点。如果没有差异化,我们就有可能无法产生共情;相反,我们会陷入自己的情绪中,让我们的想象过程被自我视角所干扰,最终得到的情感模拟但实际上并没有复制他人的经验。关于第二阶段,评价理论认为,情感体验是基于观察者对他人特定情境的评价性解释或评价,这是决定观察者代偿性情感体验(包括移情体验)的关键因素。同理心的前提是观察者的评价等同于主体的评价。因此,如果纪录片创作者想引起观众们的共鸣,就必须确保对其主要人物的彻底描述和主体环境的具体化。
Richard Dyer和Paul McDonald在分析小说主义的人物概念时,举例说明了关于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要素。可信的小说人物拥有诸如特殊性、内在性、圆润性、发展性和动机等特征。如果一个人物没有揭示新的特质,或者没有引发其发展的目标或欲望的对象,观众就不太可能对其进行情感投入。圆润的人物是由多种特质定义的,这些特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圆润的人物容易招致共鸣,因为多种性格特征很可能引起观众的联想,从而激活与屏幕人物所表现的情绪相对应的情感反应。
《被击毙的矿工》的开头是导演Desai的一段旁白,他说南非马里卡纳的事件让他震撼到了极点。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试图发现谁要为此次杀人事件负责的故事。这个戏剧性的问题有助于建立一个叙事情境,影片按照事件的发展顺序一直到最后结局三十四名矿工被警察击毙。该片没有单一的主人公,而是以一群罢工的矿工为统一的主角。然而,Coplan的共情模式需要与另一个个体的心理状态进行情感匹配,而这一点在影片中被其主角集体化效应所抑制。例如,在影片的一开始介绍了三个矿工,其中两个人Tholakele Dlunga和Mzoxolo Magidiwana是受访者,而第三个人Mgcineni Noki则是受害者之一。然而,Dlunga和Magidiwana被设定为“罢工领袖”;他们以参与者和目击者的身份推动了影片的叙述,而不是作为受事件影响的实际个人。无论是通过视觉上的表现还是访谈叙述,影片拒绝让观众深入了解任何一个矿工的精神状态,Dlunga和Magidiwana在事件发生后都接受了采访,但他们没有透露他们在罢工和屠杀之前、期间或之后的情绪状态。在影片中的某一时刻,Magidiwana对着镜头挥舞着手指表示愤怒,事实上,他们除了对所感受到的不公正表示持续的愤怒外,并没有表达任何情感。因此,观众与矿工的情感匹配是很困难的。因为情感被反复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论证、事实的信息和集体对建制派愤怒的固定情绪。这种明显忽视个人化的情境线索而注重对事件和社会不公的描述,抑制了他者视角的观点。
但有趣的是,该片符合Coplan的第三条标准:即自我与他人的区分。大多数时候,矿工们被相对远距离地描绘成一个統一的群体,都表现出一致的性格特征,以及拥有相似的社会和种族身份。尽管如此,仅满足这一标准还不足以产生共情的,这与Dyer和McDonald的圆润性人物概念相矛盾,而圆润性人物是理解多层次个体的重要前提。
自相矛盾的是,虽然矿工必须不断面对不同程度的冲突,但在叙述过程中,矿工并没有表现出发展或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出现发展的实例时,影片并不追求个人的故事性和目标需求,而是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此外,矿工们行动的具体动机仍不明确。他们的宏观动机是追求更多的报酬,以减轻他们的贫困,但他们没有微观动机揭示个人的利害关系,例如他们不稳定的环境如何具体影响他们个人生活和他们的家庭。剧情也缺乏一个设定或引爆事件,比如一个破坏主要人物现状的事件来交代甚至是集体的故事发展。因为当影片开始展开时,观众就已经被推到了戏剧性叙事的中间。这样一来,事件的社会历史重心和政治、社会影响再次被凸显出来,而牺牲了个人的故事性。
三、结论
本文讨论的纪录片共情性的建构上,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叙事情境,都存在一定的不足。《被击毙的矿工》偏重于理性的论证,回避展现人物的情感状态。矿工们通篇都被描绘成一个统一的群体,没有出现一个让观众可以感同身受的个体人物。在这部纪录片中,大部分角色的性格特征极小,人物没有任何成长或变化。此外,他们的个人叙事以及动机和目标都没有被揭示出来,这损害了观众形成那种可以产生情感反应并最终导致同情的评价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物在错综复杂的情境化的故事世界中被悬置,他们被剥夺了圆融的个性,丧失了人物力量。由于缺乏共鸣,尽管纪录片的背景很丰富,也使得纪录片的行动主义和提高认识的目的是否真正实现,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无论是否如此,纪录片创作者鼓励观众认同银幕人物的总体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参考文献】
[1]Coplan, A.Empathy: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Dyer R, McDonald P. Stars[M]. 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9.
[3]Frassinelli P P. The making and political life of Miners Shot Down: an interview with Rehad Desai and Anita Khanna[J]. Communicatio, 2016, 42(3): 422-432.
[4]Hall S. Encoding/Decoding, in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r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J]. 1980.
[5]Keen S. A theory of narrative empathy[J]. Narrative, 2006, 14(3): 207-236.
[6]Livingston,P,Plantinga, C.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and film[M]. London:Routledge Press,2008.
[7]Nls J. The Difficulty of Eliciting Empathy in Documentary[J]. Cognitive Theory,135.
[8]Sobchack V. The address of the eye: A phenomenology of film experience[M]. Americ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9]Wondra J D, Ellsworth P C. An appraisal theory of empathy and other vicarious emotional experiences[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5, 122(3): 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