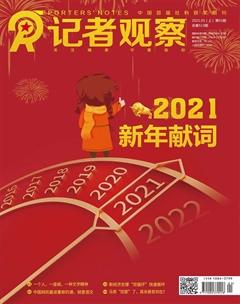一个人,一座城,一种文学精神
王环环
每个作家的笔下,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这些文学空间或许与现实空间相去甚远,但却无限接近心灵的真实。也许是出生的地方,也许是路過的或者长住的地方,作家们总会选择一处作为故乡。有了这片故土,笔下的房屋才会有地基,人物才会有血液。沿着他们书写的脉络,我们可以看见一片土地的千百种样貌:同样,透过这片故土,我们也见证了作家的成长。
沈从文:“故乡是用来怀念的”
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到处充满神秘感的地方,那里的山山水水世俗人情,都是故事,都是诗歌,也都是图画。“(吊脚楼)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脚逐渐进街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自家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等待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
他笔下的湘西没有尘世间的喧哗,从朴实简单的乡村生活以及风俗来体现“人文美”;他笔下的湘西耐人寻味,像一杯浓茶,只有细细品才能品出文中的美,又如同一条长长的古巷,通向梦与美好。
自小生活在湘西的青山绿水中,沈从文对这一片美丽的景色有着深深的眷恋。在他的小说中,常常以饱满的情感描绘湘西绮丽动人的风光,这是一种虽被外来文明侵蚀但仍保存着古老原始状态的自然,镌刻着宁静、质朴与美丽,弥漫着古朴、幽静和祥和的情调,令人心动、痴迷。
在那个新旧交替、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从童年时代受故乡山水滋润,感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到从军流浪,目睹黑暗社会带给自然与生命的不幸,沈从文见证了故乡的变迁,这里已不是他记忆中美好纯粹的模样——他敏锐地察觉到,家乡人的品性被一种“大力”所扭曲。这种“大力”,就是现代性的大潮大浪,它不可抗逆地席卷了黄土地与黑土地,改变了数以千年的乡村形态。
于是,他开始动笔写《边城》,写一条溪、一个女孩、一条狗、一个漫长的梦。这是一种对于似水年华的追忆,对于美好时代的挽歌,对于乡愁的自怨自艾。他知道,乡村的失落不可避免也不可溯回,因此在文学中,他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过去。湘西,成为他内心最柔软的存在。
莫言:在“高密东北乡”自由驰骋
相比于沈从文对湘西的细腻与浪漫,莫言对故乡高密东北乡的感情则多了几分粗犷。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莫言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上演了一出史诗大剧。“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梁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
他形容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极端爱恨都泼进土里,让高密东北乡的人与物,都吸饱了作家的情绪。
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是急切想要逃离的地方,亦是无法抛却的过往。21岁前,莫言一心想逃离这里,因为这里充满了饥饿、孤独、压抑与恐惧。但当他真的离开家乡,才发现那些饥饿与孤独的记忆,为他的写作打开了一扇门。由此,莫言在文学世界里,完成了对故乡的回归,并且超越。
借着“高密东北乡”,莫言进入了与童年经验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环境,在这个没有疆域的文学王国中,他可以自由驰骋,信马由缰。
汪曾祺: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与大风厚土的高密东北乡不同的是,在高邮,硬邦邦的笔杆子都变得水灵灵的,带着湖畔的烟火气。“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见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我上小学,倘不走东大街而走后街,是沿河走的。上初中,如果不从城里走,走东门外,则是沿着护城河走。出我家所在的巷口的南头,是越塘。出巷北,往东不远,就是大淖。我在小说《异秉》中所写的老朱,每天都要到大淖去挑水,我就跟着他一起去玩……”油汪汪的咸鸭蛋,满肚子菱角鲜藕的大湖,薄薄的舟子和垂柳……一代人对于高邮的印象,都从汪曾祺那里来。有人称他的作品是“诗化小说”,淡化冲突起伏,能看见缓缓流动的情绪。
水乡滋养了汪曾祺如水的性格。十九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年近古稀才得以还乡,其间虽饱人间荣辱,但老先生却用一生的沉淀写出了温情脉脉的优雅与情致。早年,他也曾锋芒过,生于轰轰烈烈的年代,师从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先生,笔下的傲气很难掩得住,但也正是因为过尽千帆,当他开始写人间烟火时,才更显从容剔透。
如果用画来作比,那汪老先生的作品大慨是白描,简洁至极,精确至极。他写色彩,写形状,写对话和动作,就是不评价。看的人怎么想?留白给你,随你去想。“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文字活泼之余,不失生动有趣,更是一种豁达与通透。
贾平凹:“商洛是我文学立命的全部”
“我总觉得,云是地的呼吸所形成的,人是从地缝里冒出的气。商洛在秦之头,楚之尾,秦岭上空的鸟是丹江里的鱼穿上了羽毛,丹江里的鱼是秦岭上空的脱了羽毛的鸟,它们是天地间最自在的。我就是从这块地里冒出来的一股气,幻变着形态和色彩。”这片自小成长的土壤,成为贾平凹无法割舍的地方,亦是他的“诗与远方”。
这里的山水草木、阳光空气、世风民情,都始终萦绕于他的心头。无论是《废都》《高老庄》,还是《秦腔》《老生》,在他的每部作品中,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原型有的就是商洛记录,也有原型不是商洛的,但熟悉商洛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商洛的影子与痕迹。“我已经无法摆脱商洛,如同无法不呼吸一样,如同羊不能没有膻味。”
在外游走半生后,对于这片故土,贾平凹仍是满怀赤诚的。“至今,我的胃仍然是洋芋糊湯的记忆,我的口音仍然是秦岭南坡的腔调。商洛也爱我,它让我几十年都在写它,它容忍我从各个角度去写它,素材是那么丰富,胸怀是那么宽阔。凡是我有了一点成绩,是商洛最先鼓掌,一旦我受到挫败,是商洛总能给予藉慰。”
“人人都说故乡好。我也这么说,而目.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起商洛,我都是两眼放光。这不仅出自于生命的本能,更是我文学立身的全部。”
张爱玲与王安忆:“冰冷的上海”与“温暖的上海”
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书写中,张爱玲与王安忆注入的情感色调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冰冷的、异化的。她眼中的上海是一幅阴冷的、孤寂的画面,“那是仲夏的晚上,莹澈的天,没有星,也没有月亮……背后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蓝得一点渣子也没有——有是有的,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
这或与她天然的悲观主义倾向有关。她的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然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轰动一时,却又遭受了痛彻心扉的爱情悲剧;晚年漂泊海外,独自一人生活,直至失去生命。
这样的人生造就了她悲观的思绪,“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电车像曲蟮一样,扭曲的“游走”着,这是一个焦躁的、异化的上海。
同为女作家的王安忆笔下,上海则显得温情许多。她眼中的上海是繁荣的、开放的、包容并蓄的,虽然封建的痕迹仍然在弄堂中存在,但社会已经给予了人们较多的自主权,可以追求自由,获得解放。
在她眼中,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
她痴迷于上海的女人,同样的,也爱上海的弄堂。“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
字里行间,你似乎真的能看到那盏拐角上的灯,带着最寻常的铁罩,罩上生着锈,蒙着灰尘,灯光是昏昏黄黄,下面有一些烟雾般的东西滋生和蔓延……
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不同,是属于两个人的独特人生的特有风貌,没有谁对谁错,更没有优劣之分。她们异曲同工地为后人演绎了一曲海上繁华梦。
每个人都有一片文学的故乡,这个故乡就是心灵的家园、精神的故乡。在故乡的土地上,长出了粮食,长出了草木,也长出了文学。
文学是虚构的,但文学作品所承托的情感是真实的。故乡养育了人,人塑造了文化,而悠久的文化又被记录成一代代文学,哺育了人们纯粹的心灵,搭建了人们精神的故乡,给予人们以内心的“根”和归属感。在时代的变迁和脉动中,在纸上为人们留下一份沉甸甸的乡愁,保存一个精神的原乡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