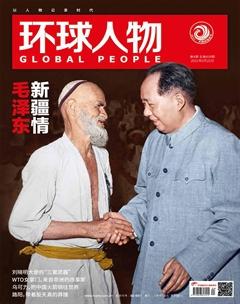戛然而止的桑巴舞
朱东君
往年此时,里约热内卢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狂欢节。有激情四射的游行,有露天表演,有奇装异服的路人……接连数日,这座南美城市陷于昼夜不息的欢闹。
前两年,我都去观看了狂欢节游行。从夜幕低垂至曙光初现,伴着震耳的巴西风舞曲,里约桑巴舞校的队伍依次登场——热辣性感的鼓点女王,设计新颖的花车,以及盛装打扮载歌载舞的方阵,无不宣示着参与者对这场城中盛事的自豪与全情投入。专业评委还会为舞校打分,评选出当年冠军。
巴西狂欢节源于欧洲传统节日,又融入了非洲音乐和舞蹈,自成风格,在20世纪初逐渐流行起来。1928年第一所桑巴舞校在里约建立,其后,更多舞校出现,舞校间的比拼成为里约甚至巴西狂欢节的重头戏。1984年,由巴西著名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设计的桑巴大道落成,里约狂欢节有了永久地标。
桑巴舞校根植于贫民社区,成员基本都是社区居民,获得狂欢节游行冠军对舞校和舞校所在社区都是极高的荣誉。为了这一荣誉,舞校往往要筹备半年甚至更长时间,设计游行主题、情节、舞曲、花车、服饰,再反复排练,只为那一晚的惊艳亮相。
不过今年,因疫情未散,盛景不再。而暂停举行狂欢节活动不仅是文化传统的一次中断,也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里约狂欢节上世纪60年代起有了商业属性,接受私人投资,并售卖舞校游行门票,如今更是发展为利润丰厚的产业。去年狂欢节期间,里约吸引了约210万游客,创造了40亿雷亚尔(约合48亿元人民币)的收入,酒店入住率高达93%。涌入的游客带来了好生意,街头随处可见售卖酒水、食物、饰品和服饰等的小贩。而筹备狂欢节游行,更是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吸纳了一大批作曲家、乐手、编舞、视觉艺术家、场景设计师、裁缝、铁匠、木匠、画匠、玻璃工、化妆师、乐器制作者……
狂欢节停止了,相关从业者也没了收入。40岁的雷娜塔在里约北部租有制衣工作室,年复一年为桑巴舞校制作游行服装。“人们认为狂欢只是狂欢,但它还是收入来源。”往常筹备狂欢节时,雷娜塔的工作室挤满数十名裁缝、設计师和缝纫工。然而疫情之下,无法开工,她只能靠捐助和救济度日。
舞校同样陷入绝望,不再有狂欢节游行转播和门票收入,平日的表演和餐饮服务也不得不停止,无法支付薪水时只能解雇员工。不过危难中,舞校也积极自救,向社会募捐,筹集食品,帮助生活困难的成员;甚至利用手头资源,缝制口罩和防护服,分发给社区居民和医疗机构等。
“没有悲伤可以掩盖这样的喜悦/那些没有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人/那些逃过一劫的人/不用再烦恼/尽情欢笑,尽情玩乐……”1919年里约狂欢节,人们涌上街头,在抛洒的五彩纸屑、彩带和香水中,如此高唱道。那是里约熬过“西班牙大流感”后的第一个狂欢节,那场瘟疫带给里约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约1.5万人死亡。
100多年后,里约人在等待同样的时刻,再次战胜疫情,再次迎来狂欢。“在漫长的疫情之后,狂欢节永远是一剂良药。”为去年狂欢节冠军舞校设计游行情节的马库斯说,“一旦这一切结束,人们将重现1919年狂欢节,同样的狂喜,同样的轻松。”
“下一个狂欢节将是人类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