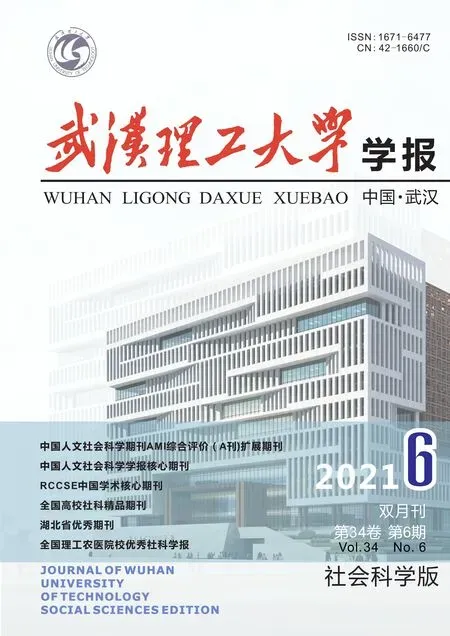造物进化与文化原型的关系互证*
——以中国传统造物为例
熊承霞, 潘长学
(1.上海理工大学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0093;2.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武汉 430070)
对于人类而言,造物(设计)是对“生命、生活、生存”交互世界所有事物的创想和审美化,是文明和文化的重要媒介与载体。设计在传统中国蕴含着“天道、地道、人道、物道”之理念,明代哲学家王艮所说的“百姓日用皆道”可谓是传统中国造物设计的核心指向。1919年德国包豪斯创立了现代主义设计教育体系,这个强调标准和形式主义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中国,成为中国设计的现代主义圭臬。从此,中国的设计范畴被定义为平面视觉设计中的“包装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广告设计”,环境设计中的“展示设计、家具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新媒体艺术中的“动画设计、影视设计、交互设计、媒介设计”,传统美术设计中的“工艺美术设计、染织美术设计、特种工艺设计”等相对独立的“工具理性”指向。然而,现代社会文化传播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设计的概念已经广域化,从国体政策、意识形态到“天网”宇航等,设计可能关涉“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这决定了设计必须重新面对人类文化基因原型,梳理传统文化的精神性和物质性隐喻。传统中国强调“以器载道”“文以化德”,以器物传递和承载人文精神,以器物来成就造物设计技巧、工美、匠心是中国传统的设计维度,以器物扩延人性道德和信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导向。然而,传统造物中的原型基因并未能更好地融合在当代,对历史进程中所展现的文化基因之当代性的研究和现代设计植入尚待提升。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媒体空间语境下,设计不可能局限在功能本位或生物需求,而必须以思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看待设计造物。
当今随着各种新兴媒介的传播,设计产生的“物化”正潜隐在人们的精神世界,而外来的他者文化同样裹挟其设计样态纷至踏来,并影响人们的心理结构。历史向前一路进化,人性化的、智慧的造物文化早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意大利学者克罗齐于1917年提出“谈什么没有凭据的历史就如确认一件事物缺乏得以存在的一个主要条件而又谈论其存在一样”的著名命题[1],便是尊重“物证”从而利于“酌古通今,旁推互证”的例子。正如帕帕纳克在《为真实世界的设计》中所指出的,“设计应该认真考虑地球有限资源的使用问题,应该为保护我们居住的地球和它的有限资源服务。”[2]文化原型作为这个世界上不可复制的人工资源,让这种文化资源得以传承传播并实现新生更是设计界的当代使命。原研哉在《设计中的设计》中提到,“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价值丰富的文化积累。如果能够把它们看成是陌生的东西,加以活用,是比无中生有更了不起的创造。我们的脚下埋藏着巨大的矿脉,我们需要的是发现的眼睛。”[3]显然,设计学已经从解决问题走向对人类命运的构想与规划,设计必须洞察到对历史变迁和民族精神传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清醒地审视“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意义,对于中国当代造物设计工作者、研究者而言,如何让华夏文化原型隐喻的文化文本和价值意义在当代“文以化德”,如何解决广域的普遍意义的“厚德载物”,是我国设计界的共同使命。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求索的“器道”二元文化,一直传续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文化原型的再创造中。然而,在众媒介共存之当代,传统文明的智慧基因及其原型的传承再造尚未普泛性成为现代造物设计的创造性转化资源,为此,论证文明物态与设计的跨时空跨时代传承不仅关乎国家和全球的进步,更关乎当代中国设计体系的民族性传承。本文尝试沿着华夏历史文化遗存和遗产及其出土造物的历史踪迹,以探寻华夏文化原型在当代的“新陈代谢”与创化复兴。
一、 中国早期文化遗存中的规划设计原型
在人类文明的博弈世界中,能否充分运用设计思维,是文化基因传承生存技能的重要逻辑。正如Christopher Pinney所言,“物品作为非人领域的诞生,与人类作为人的诞生是同步的”[4]在现代屏性媒介社会,互联网联系着全球,世界上无论是未开化的土著社群还是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抑或是亟待发展的国家等,都在一体化地共享着地球的资源。造物设计师可谓是这一资源的整理者和分配者,通过设计活动的“格物致知、良知践行”,上可立国,下可化民。也正因为文化设计而造就了世界上唯一持续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这个文明以其高度协同的物质、物品、物性的设计而被载入人类文明进化史。1911年英国人类学传播学派史密斯主张“世界所有文化的产生起源于埃及”,强调人类文化的泛埃及主义思维,认为人类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时间才开始进行与文明有关的创造活动[5]。这显然是一种缺乏全球文化视野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的主观臆测。持与史密斯相同观点的还有佩里的“太阳之子论”。他们都认为古代埃及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后从埃及再逐渐扩散蔓延到世界其它的文化区。这些持“埃及文化中心论”的西方学者的思维体现了直线式的巫术性崇拜心理,而忽视了文化心理产生的多线性进化特点,从而遮蔽了华夏文明、古印度文明和玛雅文明的独特价值。文化的研究必须是整体性的,要从其文化地理、能量供给、技术成因等层面逐层剥离解析,文化与文明的表述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实证物质材料以及对应的文本证据。因此,要驳斥看似明显的文化之谬,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提出确凿的证据。顾颉刚先生曾强调“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在实物证据面前,任何臆想的推论都不足以撼动事实[6]。
2018年5月28日,历时16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实证与证据通报了5000年以前华夏大地上灿如星河、绵延闪耀的文化样态,这些纷繁众多的有计划、有秩序的设计造物,这些辉煌的古代文化中心,都以其独具特色的物质创造提供了文明的证明材料(包括城邑、祭坛和大量的玉器),代表着成熟的物质设计体系。这些古代造物集中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共同心理程序、服从统一的组织机构和宗教习惯,其以造物设计构成实体标志物,从而濡化(enculturation)为文明的内聚力,推进和提升了人类文明的高度。
夏鼐先生曾将“文字、铜器、城市、礼仪祭祀中心等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来探讨文明的起源。”[7]这四者共同呈现出的便是文明的造物设计能力。“铜器和城市”展现了人类对空间、布局、形态的创造能力,随后这两者演化为礼仪祭祀的象征性原型场所,器物和场所共同经营了人类的信仰活动,演变为一种惯习认知,并作为普遍认同的行为,最终从造物物态中迁移而转化为记录人类行为的“文字”文本。其中城市的出现代表文明聚落时空的规范秩序,城邑的构筑展现了早期先民对空间地理水流生态知识的掌握,只有选址布局科学合理,技术和空间相互平衡,才能达成有利于城市和国家发展的文明路径。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河南新砦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例,其宫城与祭祀空间的选址互为“和谐”共生。新砦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命名,“砦”同“寨”,是河南郑州对村落的特殊称谓,是平原地区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叠垒石块围合成的一种聚落建筑形式。考古认定新砦遗址早于二里头遗址但晚于龙山遗址,整个文化遗址包括夏文化经历的三个大的阶段“以王城岗大城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期’遗存(或曰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存”[8]。保存约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文化样貌,贯穿夏朝的起始消亡。其中新砦文化挖掘出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宏大建筑,拥有内外三重城壕,城墙、护城河以及大型建筑分布整齐,城北面建有宗庙祭祀,中部建成宫殿,南面则规划为骨器、玉石手工作坊区。这些建筑遵循在南北垂直的轴线中布局建造的设计规则,经碳14测定,其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所建造,从其层层围合的结构中可以认定为具有早期的城市“设计规划”概念。其将宗庙和宫殿构筑在三重城壕之内,体现母神文明时代的“卵胎”防御式文化原型思维。新砦遗址出土的遗物不仅数量众多,做工精美,而且规格等级较高,反映出新砦城的重要地位。考古专家根据从新砦至二里头时期房址中发现的大量双圈柱洞,判定这些房址在建造前作过一定的规划布局。赵春青、顾万发主编的《新砦遗址与新砦文化研究》一书的“综合研究”部分指出,从新砦至二里头时期房址中发现的大量双圈柱洞,判定这些房址在建造前曾做过一定规划布局[9]。事实上,考古人员在二○○○年前就断定新砦遗址为夏朝遗址,重要依据是城邑的规模和结构,而从造物设计角度看,新砦遗址的规划体现出选址的科学性,其借助北面的天然古冲沟挖筑外壕,城墙沿煤土沟河进行围筑,又以苏沟为内壕。加上南面的双治河、东面的双洎河形成天堑的防御系统,整个遗址恰似一个“瓮城”层叠的围合系统(见图1)。这种选址还体现出美国考古学家金芭塔丝所言的“子宫”母体原型结构,可以看出,夏文化先民城市规划中仍然保留着对孕育式结构的依赖。在后世,这种设计结构一直盛行于数千年的中国城镇乡村选址中。新砦遗址也是早期中国存在城市设计体系的重要依据,华夏文明持续的力量凝聚正是体现在这些造物设计体系中。

图1 新砦遗址规划图
早在新砦遗址前,山西临汾陶寺遗址也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尧舜时期“最早的中国”之雏形,反映的是前4300-3900年的中国,其城址呈“回”字形“双城”结构,面积约280万平方米,遗址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李伯谦先生证实:“陶寺遗址是在聚落分化基础上出现的特大型聚落;陶寺遗址已出现了城壕和城墙等防御设施;陶寺遗址建造有像观象台这样大型宗教礼仪建筑;陶寺遗址存在贵族与平民墓葬的分化……。总之,陶寺遗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完备的王国都城面貌,我们说陶寺遗址是目前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最大的王国是可以成立的、有充分根据的。”[10]这也可以肯定一点,在文明的依据问题上,大型的集中的聚落和方国,意味着有计划有意味的规划设计能力,必须是适应农耕地理风向和河流的特征,展现原始的“堪舆学”能力,符合管子《乘马》中总结的“城郭之制”:“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11]考察这些大批量的早期集中建造活动,可以看出冶炼作坊和工匠合作的组织结构,陶寺出土的板瓦也证明了这一时期陶制建筑材料技术已经成熟。这不仅展现了原始冶炼术的发展,也是中华文明造物科技能力的见证。
除此之外,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公元前3750年)也被考古学界确立为华夏重要的王都,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认为,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宇宙观与王权)、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绿松石龙等,都是‘中国’元素的大汇聚。”[12]以上早期的城市文明都以规划秩序的都邑存在,综合证明先民已经成熟掌握“技术、形态、象征、结构”等造物要素的整体能力。因此,遍布在中国大地各个文化遗址中的人工造物和文明遗存,早已成为华夏文明进程中各具特色的、杰出的物质文明代表。
二、 华夏礼仪祭祀物品中的象征文化原型
如果继续沿着夏鼐所言的“礼仪祭祀中心”推讨文明物证,则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华夏的造物设计文明史。《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传》开篇即云:“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13]那么,是以什么物质行“司”天神和地神呢?很多学者提出,中国早期文明的“玉石时代”观,以玉石礼器作为天地之物象之象征。叶舒宪先生指出:“白玉乃至白色石头,都曾被先民联想到天上的永恒发光体,即日月星辰。按照天人合一逻辑,人类只要效法天上的发光体,或与其符号物相认同,就能通过交感巫术的力量达到永生性。”[14]邓淑苹也提出:“萌芽自新石器时代,以‘精气观’与‘感应观’为主导内涵的‘崇玉文化’成为最初的祭祀媒介”[15]。玉石从劳动工具的制作开始,逐渐从使用工具的惯习中获得文化认知,提取玉石礼器为造物象征,从而实现“国中有玉”的统一思维,以“玉成中国”贯通文明的进化结构,在当代对玉的崇敬已经形而上“玉承”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玉石信仰的同时,青铜器也逐渐作为象征媒介,《史记·孝武本纪》云:“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九鼎从此成为“问鼎中原”“一言九鼎”的民族精神。从玉器和青铜器的制作过程中可以看出,琢磨与冶炼都不只是纯粹的技术问题,更需要提前对形态进行设计规划,同时需要有“文化原型”作为文明语言的意识。仅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石家河文化(前4500—前3300年)玉器进行外观分析(如图2),其对称的人面拥有难以切割的倒钩状轮廓,似乎双凤张翅,五官以线刻组成,眼睛作甲骨文“目”字形,单勾,俗称“臣”字眼,头部和嘴角有装饰纹样,整体造型弥漫着“巫”性,彰显出独具一格的艺术审美。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各种逼真的玉鹰、玉凤(见图3、图4),图3所示的鹰采用几何纹双勾线,双翅饱满、尾羽拖曳,体现了造型的精准和美学规律的设计追求,双鹰的外形与凹空处如同现代设计对比平面构成的经典作品“鲁宾之杯”,可以惊喜地发现史前造物设计所呈现的现代性。

图2 石家河文化出土玉面

图3 石家河文化双头玉鹰(左)鲁宾之杯(右)

图4 石家河文化玉凤
商周青铜器工艺的复杂绝不逊色于玉器,从形态设计到制模为范,同样必须集中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才能完成,更何况中国的青铜器还是一种社会和精神的文化“文本”,代表国家和个体的权势地位,记录方国邦国的各项大事,又称为“钟鼎铭文”,“中国”二字就是从青铜器中发现的,“何尊”内底铸有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记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这说明在文明进化过程中,造物智慧的同时还需要建构对应的话语传播体系。1963年出土于宝鸡贾村的“何尊”,通高39厘米,径28.6厘米,重14.6公斤,是一件落地式盛酒器。纹饰与器身比例和谐,拥有王者之气度,这也是“尊”作为酒器所要展示的精神暗示。从器物造型看,极其符合现代人机工程学结构,口沿外敞,便于倒酒。口沿外由蕉叶纹组成四边扉棱,扉棱玲珑剔透,可增加手捧时的握力,使得由立面观察器身时,每个棱边都是对称的轴中线,构成均衡、严肃的美学。蕉叶侧面装饰有线条云纹,器身图形由三段式构成,鼓腹处饰饕餮纹,似牛头顶着大羊角巨目咧嘴,上部纹饰外部以拱券形笼罩内饰的蚕纹,似乎显示“天”的形态隐喻,底部和细节处用云雷纹衬底。底部呈喇叭型,边沿铸造为圆角,使底边敦厚凝重,为西周早期较为凝练、大方的珍品。整个器物运用的牛羊蚕纹饰展现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礼记·礼器》中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既表示它们是礼器中特别重要的盛酒器,也代表有一套相应的礼制。郑玄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16]“尊”、“卑”不仅形态不同,储酒量也不同,后世依次发展出“尊”“卑”的人格属性,由此可以看出青铜的设计之妙还在于内涵,胜过今天产品造型设计只注重外形而忽略“器以载道”的伦理涵化作用,这是设计与技术协同而显示的国家象征。按照怀特对文化组织的看法,文化被分为三个亚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系统。其中技术系统由生产工具等构成,社会系统则包括亲属、政治、军事和宗教制度等,思想系统由思想、信念、神话传说以及民俗等组成。其中技术系统由生产工具等构成;社会系统则包括亲属、政治、军事和宗教制度等;思想系统是体现思想、信念、神话传说以及民俗等组成[17]。每一件青铜器的设计制作完成可以看出内蕴的文化组织系统的协同,实现这种协同的是设计规划、材料选型和技术合成,这也完全符合现代产品设计的程序。
从“何尊”铭文的排列组合中可以看出现代设计平面构成之均衡美学,单个字形显得刚健质朴、端庄谨严、厚重凝练,横竖欹侧灵动,行间错落有致,体现周公“制礼作乐”以器镇扶社稷之意,每一件青铜器都彰显周人“子子孙孙永宝”之祈愿,因此其铜器的铭文如有“灵魂”般,开创了中国书法艺术中的“人格”表现。书画家李瑞清曾言:“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仅从一件“何尊”中探讨其设计思维,就能够感知西周时期设计体系的完整性(见图5)。

图5 何尊及其“中国”铭文
三、 中华器物中的文字符号及其文化原型
怀特的新进化论或普遍进化论认为:“文化就是人们为了生存下去而适应自然界的一种机制,而没有符号和象征就不会有文化的产生。”[18]因此,维持华夏文明的基因是造物设计文化,这种造物文化也是决定精神行为的因素和转化文明物态的实证。先民依赖造物设计得以获得生计生息、修养保护、外界适应、信仰寄托的文明机制,而中国相对广域的地理空间,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造物结构能力,人们以结构的方式理解自然进化的规律,在自然进化的表象之下,归纳出一种创造的心智,汉字原型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创造合力的见证。解读汉字的深层结构更易于发现隐藏在字形中的文明基因。如果把汉字作为一种文明的持续物态,那么汉字是唯一持续且还将永远持续的物质载体。从汉字中可以反观历史文明,可以找到造物设计的原始依据,因为“当某个汉字以某种文化背景为材料造出来以后,它就会像人的照片一样将作为造字理据的文化背景保存下来,即使后来这种文化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消失了,它也会伴随汉字保存下来。”[19]不仅如此,中国的汉字由于是从其物质形态中转译而来,因此它代表着中国造物的成就,以及造物形意语言的创造性符号转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无法更改的文化原型的证据。

四、 造物智慧显现了整体文明社会的多线进化
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海内斯·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1902-1972)在《文化变迁理论》(1955)中提出文化与其生态环境具有不可分离的功能,它们之间在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中产生影响[21]。也是意识到人类整体生态基因的多线进化作用,中国文明在东西南北广袤的生态地理环境中,通过盆地构成相对向心的地貌结构,有利于统一的文化表述。中国西部高大的山脉和东部的平原反映出自西向东西高东低的地理态势,潜移默化地形成崇高敬畏和追求通达秩序的文化表征。北纬30—35度的两河(黄河、长江)流域为其文明的传播提供了天然的变迁与发展路径,同时联通其境内的不同的生态环境,使文化在相异的人文生态环境中传播并产生近似的文化信仰。正所谓多元聚合而生造物设计的智慧,在造物设计与文明愿景的相互作用下,催生出各种形态的演变。由此,华夏中国在各个历史变迁过程中的设计造物都是其文明的重要标志,且这些造物都与精神、审美、信仰紧密结合。造物设计因生存、财富、掌控等动机而逐渐成熟并走向体系化,最后完整记录在汉字中,显现了华夏文明的变迁,正是设计变迁中不断修订的体系建设成就了华夏文明。
如果以文字出现的先后作为传统文化的分界表征,那么文字出现前的“岩壁刻画、巢居穴卧、玉石琢磨、抟土为陶”,文字出现后的“青铜器物、舟车制造、楼阁殿宇、雕梁画栋、漆器刻镂、陶瓷器皿”等,都可谓是设计体系成熟在文明变迁过程中的文化表征与标识,每一次文明的高峰也就毫无疑问是设计体系的完整宣告。当代文明的进程正迈向人工智能,意味着造物设计成为沟通当代社会经济政治与国际之间的重要桥梁。正如杭间先生所言,“中国的设计学尚在建设途中”。 纵观全球,设计学也同样在建设中,然而只有中国的设计造物体系是同它的上下五千年文明共存续的。当代包豪斯所倡导的现代教育所造成的“文明”,实质上造成了中国设计教育严重的文化心理压抑和社会审美问题。在设计教育中有必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造物设计是其文明生态和社会精神的支撑,去掉历史支撑也就不可能获得当代设计的中国地位。
中国每个朝代的历史文化,其产生的基础都与前朝密不可分。汉之前的秦,唐之前的隋,宋之前的后周,也许都是依靠物质设计立国的成功范例。在中国历史上依靠标准化的造物设计短暂立国的王朝是秦,秦的大国设计方略,文字、道路、兵器、政体、度量衡等,无不体现了其造物设计的标准化和秩序化。然而,其标准化设计却没有渗透在精神与信仰相随的思想体系中,因此秦帝国仅存续了15年的短暂时间,但其文化脉络由大汉承载,并熔铸出儒家的仁礼精神。隋朝开凿了南北运河,改变了中国疆域中大河自西向东的依赖,对改善和平衡我国南北物资运输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唐代,其将诗书画艺术与国家精神多元统一在造物设计中,整体社会文化在看得见的物质中呈现并共享,因而传递出气势恢宏的大国精神。至宋代尽管南北分治,其物质设计却追求一种极致的“尚玉、齐玉”典范,以瓷器的器型设计、色泽美学和烧制技术等元素作为文化原型的整体继承,成为最能彰显“玉成”中国的造物成就,其智慧也永久留驻在瓷器中,并因此在世界上获得“china”代表的国家形象。
在今天,中国龙行天下的“高铁”和凤舞九天的“人工智能”设计正在构筑起大国的当代造物与智造担当,因此亟待中国设计界承上启下创造性活态应用中华文明的造物成就,同时借鉴和创造性转化利用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他者设计文化”,但前提是不能遮蔽或掩盖中华文化原型和基因所代表的物质文化之灵魂。造物设计所提供的物质证据不仅是中华文明长久传承的基石,同时也是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证据。只有在上溯始源启迪未来的设计传承中,才能够更加完整地传播华夏文明,实现全球语境下“天下大同、共享辉煌”的文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