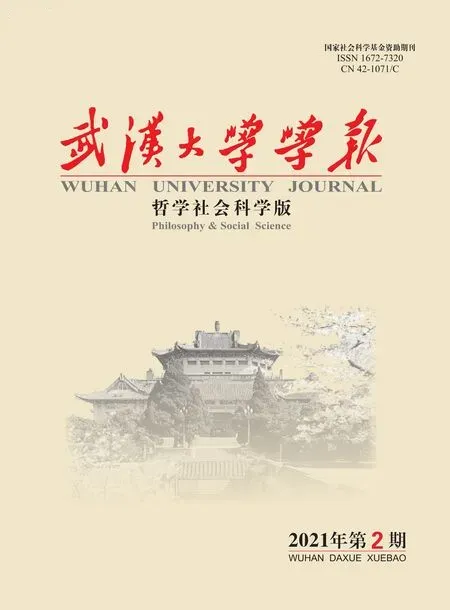子部世界中的欧阳修
——古代经典作家知识结构的一个案例分析
何宗美
受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共同风气的影响,我们对经典作家的研究长期主要在两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即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其中,作家研究又主要集中于生平与思想,作品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创作与审美,由此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不断积累,日益丰厚,使研究得到推进。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深深感到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越是经典的作家,目前的研究越是陷入了困境。有一种学术现象显而易见,即今天以研究某一经典作家而成名的学者已经越来越少,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研究视野已全面拓开使研究格局不断散点化,二是经典作家在失去作家、作品研究的旧路径后一时面临着尚难越过的瓶颈。但这不能归咎于已有研究本身,只是旧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有待突破。毋庸讳言,过去的研究一直存在某种惯性,就作家研究作家,就文学研究文学,条分缕析,格局分明。近年来虽已大为改观,但仍然不能说已经根本找到了经典作家研究的新思路。对此,无疑有诸多潜在性等待研究者探索,但有一个根本点理当作为共识来加以重视,即研究者不可忽视一个基本事实:古代作家的知识结构往往贯通经、史、子、集四部,这一特点在经典作家身上体现得尤其突出。研究古代作家诗文时,人们习惯性地将关注重心放在作家的时代社会生活方面,而容易忽略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四部的经、史、子、集同样是作家思想的重要源泉,本该顺理成章地从经、史、子、集的知识系统中探讨作家作品。经、史、子、集以多种形式进入作家的思想世界,形成不同作家思想情感和文学的多样性。本文以子部的方法路径考察欧阳修的知识、思想和文学世界,便是从传统目录学和古代知识体系来探讨一个经典作家,将文学史与目录学史、著述史、生活史等置于共同场域,以期重新认识欧阳修,重估欧阳修的历史价值,并尝试以子部作为方法的一种学术样式。
一、目录学与古代作家的知识结构
对于传统之学来说,目录学被认为是“一切学术之纲领”[1](P1),“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2](P3)。历来因重目录之学,则目录之著通常视为读书治学之首备,故近人有“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之说[3](P139)。毫无疑问,不具“纲领”,未得“津逮”或“门径”,则学术无以立,学问无由达,目录之学、目录之著的重要性由此可知。
但是,对目录学的重视此前很少与文学研究联系起来。这里将目录学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取决于我们对它与著述史密切性的认识,一方面著述史决定了目录学史,另一方面目录学史也对著述史发挥制约作用,包括定性、定位、取舍等。著述史展开来说,覆盖了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等方面,因此,研究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也就不能忽视目录学和目录学史,这不是仅指作为传统眼光认识到的学问门径、治学津逮或学术纲领而言,而是指目录学、目录学史深刻影响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生成。以文学史为例,目录学或目录学史的影响体现在若干方面:首先,目录学史所形成的经、史、子、集四部,不仅是古代图书目录的一种分类,更是一种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这种结构系统一经形成之后,便为古代作家造就了一个知识场域和知识路径,几乎任何人都不可能离游其外。可以说,目录学的四部分类意味着古代中国系统化知识世界的形成和稳定,它使古代作家具有了可以畅游其间的思想宇宙。其次,目录学中的四部体系是一个古代意识形态体系,四部犹如四纲,但四纲又有区分,经、史为核心,子、集为枝条,其中经为核心之核心,集则为枝条之枝条。这种思想意识和体系结构深刻地内化为古代作家的个体思想意识和知识结构,决定了古代作家的知识基础总是立足于经、史、子或侧重于其中的一个领域,他们的文学思想往往是依经、史而论文,统百家而游艺,从其创作而言,则经、史、子往往成为文学之集的内容和质料,舍经、史、子则难以为文,至少除自然、社会之外的重要创作源泉是来自经、史、子的知识世界,作家身上经、史、子的观念还影响了自然、社会创作源泉的意义生成。通常的情况是,古代的经典作家往往不是单纯的诗文作家,而是在经、史、子或其某一领域造诣颇深,或虽无著述而得其精华,有的甚至本身就是著名经学家、史学家或子学家,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则越是淹通三部、学有根柢的作家,越是作品深厚,意趣丰富,受到推崇,流传亦远。其三,当四部分类和知识体系成为共识以后,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和文学的生成也以四部体系为内在的知识场域,同时四部又各自形成一个次知识场域即经、史、子、集四个场域,每一场域虽亦存在较为清晰的知识边界,但一场域往往与另几个场域的交融映照,存在场域大小、盛衰之差异带来的影响,而生发于其间的任何一个思想、学术和文学作品,皆非单一场域的产物,而是共生的结果。这就形成一种古代中国文学的时代现象,即文学除受到其时代社会场域直接作用外,还受到其时代经学、史学、子学知识场域的深刻制约,既产生经学、史学、子学对文学的挤压,也产生经学、史学、子学对文学的促进,形成较为复杂的场域关系,由此出现此盛彼衰或彼此盛衰与共的情形,其中对于文学来说,子学的情况则具有一定独特性。子学最发达的时代往往是文学最繁荣的时代,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晚明清初以及清末民初,概不例外。唐宋时期佛教的繁荣,也属于子学和子部兴盛的例子。这是因为子学发达意味着思想更为开放,而开放时代的思想场域则更具活力和创造性,思想因素更为多元丰富,同时与经学、史学对文学产生约束力不同,子学本身就包罗万象,这等于给文学提供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世界,为此文学的内在意蕴也变得更为丰富活泼而具个性气质。这便构成一个时代作家的共同知识结构和思想特征。
二、四部知识体系中的欧阳修
四部体系被确立为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这不仅决定了每一个时代知识体系的结构,也决定了每一个士人知识体系的结构。文学领域的作家自然不能例外。所以,从四部知识体系来审视一个作家的思想、知识和文学世界,无疑是更符合事实的。当一个作家进入历史以后,他真正的存在即在于四部体系的知识场域之中,他的四部场域越大则其影响力越大越持久,这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借助了中华民族共同知识体系和知识场域经、史、子、集的存在场及持续力,故能经久不衰,百世流芳。
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欧阳修必然也存在于四部体系之中。撇开其政治影响,如果欧阳修没有在经学、史学、子学方面的造诣、著述和影响,那么他的文学将是另外一番模样,很难产生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欧阳修那样崇高的地位。尤其是自宋代以后,一个没有经、史、子或某一领域杰出建树的作家已很难成为文学主流作家,这一点从苏轼、归有光、李贽、袁宏道、张岱、钱谦益、王士禛以及清代桐城派代表作家何以能取得深刻影响便不难而知,而明代复古派的领袖们在后来的文学史中之所以不能稳居文坛首席地位,一个被攻击的重要软肋就是无学,而所谓学就是经、史、子诸方面的深厚造诣。这种文学认识的思想基础就是从四部知识体系给予的观念中孕育出来的,这可以说是理解宋代以后文学生成、文学批评、文学影响之大端。
四部知识体系内化为古代作家的知识世界并以著述的形式外现出来,不同作家外现的情形不同,这在文学史上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生活在北宋前期集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于一身的欧阳修,恰处于四部知识体系作为那个时代整体同时也作为那个时代个人知识结构建构的重要时期。虽然欧阳修子学一支有的方面诸如佛老等因来自时代的压制而显得较为薄弱,但他已是初步融贯四部且取得著述成就的古代作家,在他之前此类作家还不多见。从这一点看,他是文学史以来自觉构建宏大的四部知识体系并以此进行创作的文学家,此为研究欧阳修和研究文学史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进入经、史、子、集体系的欧阳修并非只以集部作品传世,而是各部皆能见到其人其著,且除其文集外,另有一些著作影响深远,其栖身各部的著作构成共同影响场域,传播力和影响力远胜文学作品单枪匹马的效果。宋人目录学著作《郡斋读书志》收入欧阳修著作9种:经类收《诗本义》15卷,史类收《五代史记》75卷、欧阳修参撰《新唐书》225卷、参撰《崇文总目》64卷,子类收《牡丹谱》1卷、《归田录》6卷、《欧公诗话》1卷,集类收《欧阳文忠公集》80卷、《谏垣集》8卷[4](P66,194,193,402,540,575,601,98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除《诗本义》《新唐书》《新五代史》《崇文总目》《牡丹谱》《归田录》《六一居士集》《从谏集》《诗话》外,还于经之易类收《易童子问》3卷,史之目录类收《集古录跋尾》10卷,《集古目录》20卷则列为其子欧阳棐撰[5](P11,36,102,104,231,232,297,340,496,635,646)。清代目录学集大成者《四库全书总目》叙录欧阳修著述13种,包括收入经部诗类的《毛诗本义》,史部正史类的《新唐书》《新五代史记》,目录类的《集古录》,子部谱录类的《洛阳牡丹记》,杂家类的《试笔》,小说家类的《归田录》,集部别集类的《文忠集》《欧阳文粹》(陈亮编)、《居士集》《欧阳遗粹》(郭云鹏编),诗文评类的《六一诗话》,词曲类的《六一词》,其中《试笔》《居士集》《欧阳遗粹》列为存目,其他皆为著录,收入《四库全书》。这样,在清代官修最大的古代丛书《四库全书》中,收入欧阳修著作就达到10种之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著在各类著述中的经典性。不用说集部的《文忠集》,另如《毛诗本义》之于诗经学,《新唐书》《新五代史记》之于史学,《集古录》之于目录学或金石学,《洛阳牡丹记》之于谱录学,《归田录》之于小说,《六一诗话》之于诗话,《六一词》之于词,都是各个领域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这既反映了欧阳修广泛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建树,也说明欧阳修不只是文学的欧阳修,更是经、史、子、集知识体系和知识场域中的欧阳修,而这样的欧阳修也才是历史上真正的欧阳修。
对于四部知识体系和知识场域中的欧阳修,从著述体系和目录体系去管窥,也只能识其一面。长期以来,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欧阳修,是不是以四部知识体系和知识场域而出现呢?在此,我们先回到北宋的知识场域中加以考察。苏轼的经典评价,可以清楚显示宋人眼中的欧阳修,他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6](P316)这一评价是在为《六一居士集》作序时很正式地归纳总结出的,是“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次而论之”的基本结论,是对欧阳修文学做出的总体判断,但若以比较的视野来看,苏轼的那番评判,与我们文学史通常的定位很不相同。在苏轼看来,欧阳修之为欧阳修,其意义与价值绝不仅仅是文学方面的,不说他的政治作为和为人品格,而就其思想和学养来说则在于“通经学古”这个根本上,讲到“四似”则大体照应经、史、子、集的知识体系,并非只看“诗赋”一端。苏轼接着还说:“此非余言,天下之言也。”[6](P316)据此可知,此论代表北宋人的普遍看法,也就是说苏轼讲的才是曾经出现在那个时代不可替代的欧阳修。
到了南宋,理学家兼文学家的朱熹曾在与周必大的信中很正式地给欧阳修作了一个较全面的评价:“欧公之学虽于道体犹有欠阙,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间,而泝其波流以求圣贤之意,则于《易》、于《诗》、于《周礼》、于《春秋》皆尝反复穷究,以订先儒之缪;而《本论》之篇,推明性善之说,以为息邪距诐之本,其贤于当世之号为宗工巨儒而不免祖尚浮虚、信惑妖妄者又远甚。其于《史记》善善恶恶,如《唐六臣传》之属,又能深究国家所以废兴存亡之几,而为天下后世深切著明之永鉴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说,虽或出于游戏翰墨之余,然亦随事多所发明,而词气蔼然,宽平深厚……”[7](P1690-1691)这里不讨论朱、周二人因政治观念不同而就《范公神道碑》引起的争论,应该关注的是朱熹心目中的欧阳修是怎样的。朱氏心中的欧阳修与苏轼所描述的显然存在共同处,他们都是就思想、知识与文学世界的整体来看欧阳修的,其视野是经、史、子、集知识体系和知识场域,而不单是孤立的文学视野。或者说,欧阳修是拥有经、史、子、集整体知识并有各方面著述和建树的杰出人物,而不仅仅是“文”的成就,即使其“文”的成就,也是基于经、史、子、集知识体系和知识场域的必然产物。
欧阳修这种文化形象,一直延续到清代。清初文坛巨擘钱谦益心中的欧阳修,同样不止是纯粹作为文学家的欧阳修,而是经、史、子、集知识体系中的欧阳修,尤其是作为史学家的欧阳修。在当代欧阳修研究专家洪本健先生整理的《欧阳修资料汇编》中,有关钱谦益论欧阳修的九条材料中,经学一条、史学五条、子学一条、文学一条,另有一条则为论人即由“苏子瞻目欧阳公为天人”谈到“古之君子推前哲”的问题,当然史学、子学的六条同时也涉及文学[8](P641-642)。从接受角度来说,有几个信息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首先,同样是文学家的钱谦益,他对欧阳修的接受并非只是单纯的文学接受,而是包含了经、史、子、集各方面,也就是说钱谦益接受的是整体的欧阳修而非某一局部。其次,史学方面的欧阳修更受到钱谦益的重视,特别是《五代史记》(《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是钱谦益谈论最多、评价最高的,也就是说就影响力而言,史学成就是欧阳修对后世产生影响的重要方面,如钱氏说“六经,史之祖也。左氏、太史公,继别之宗也。欧阳氏,继祢之小宗也”,把欧阳修当作三座史学丰碑之一,并认为自“迁、固之史”以后,“奋乎百世之下,断然以古人为法,而后世有所准绳,则无如欧阳氏矣”[9](P1870-1871)。还有一点,钱谦益对欧阳修的文学评价,通常是从其史著来说的,与今天文学史很大的区别是,他以《五代史记》为欧文的杰作而不是欧集中的诗文。钱氏反复说:“欧阳氏之作《五代史记》也……则史家之法备焉……以欧阳氏之史法,考之迁、固,若合符节。而其文章之横发旁肆,与太史公掉鞅下上,则又其余事焉矣”[9](P1870-1871),“欧阳子,有宋之韩愈也。其文章崛起五代之后,表章韩子,为斯文之耳目,其功不下于韩。《五代史记》之文,真欲祧班而祢马”[10](P1310),“仆初为学古文,好欧阳公《五代史记》,以为真得太史公血脉”[10](P1348)。一般人通常只就欧之文看欧之文,其实不然,欧之史恰恰是欧之文的典范,至少清初的大文豪钱谦益这么认为,而且这种认识深深影响到钱氏的古文修养,这对我们真切认识欧阳修及其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
近千年的欧阳修接受史是复杂多样的,纯粹就文学方面评价欧阳修,也无可厚非,但苏轼、朱熹、钱谦益代表的是更具系统眼光的欧阳修评价,呈现的是四部知识体系中的欧阳修,这与从知识场域来审视作家与文学的当代意识有相通之处。
三、欧阳修的子部著作及其影响
相较于人们对欧阳修经、史、集的研究,其子部方面的研究则颇为薄弱。在诸如黄进德《欧阳修评传》,王水照、崔铭《欧阳修传》,洪本健《欧阳修和他的散文世界》等较为系统研究欧阳修的著作中,欧阳修子部著作皆处于不太被重视或未受关注的状况。近年成书的洪著撰有《欧阳修的笔记〈归田录〉》一节,难能可贵地讨论了《归田录》“创作与传播”“史料价值”“人文价值”之专题[11](P290-316),但这种研究一是十分少见,二是不能改变欧阳修子部著作整体上受到忽略的面貌。欧著中子部原本就显弱一些,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情况也大体未变。不仅如此,在四部之中,相对于经、史、集来说,子部较为特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所谓“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12](P1191)。子书门类杂多,往往游离于六经、正史和文以载道的思想之外,不仅为六经之余,亦为史、集之余,在四部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容易受到整个文化场域的压制、排斥和漠视。
但子部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相对活跃的时代,子部往往异常繁荣。一些地位显赫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子部著述,也能促进子部地位的提升。欧阳修生活在儒学正统地位不断强化的时代,而他本人也是典型的儒家正统主义者,但宋代两种文化倾向促使子部著述的发展成为可能,也让欧阳修在子部方面有所建树。此两种文化倾向,一是宋人的重知识,二是宋人的重闲趣。归结到一点,则是宋代的士大夫文化建构日益强化,并最终定型为较为稳定的人格范式、知识体系和人生趣尚。宋代子部的繁荣,很大程度与宋人的重知识、重闲趣密切相关,即由宋代士大夫文化的兴起所决定。作为思想上严守儒家立场、排斥佛老等诸家异说的欧阳修,之所以能留下像《洛阳牡丹记》《归田录》《笔说》《试笔》《砚谱》之类的子部著作,也与他在知识世界涉猎广博以及作为士大夫对生活情趣的追求不无关系。他的这些子部著作,《归田录》已见专门讨论,《笔说》等主要涉及诗话、书话内容,诗论和书论研究时亦有论之者,这几种著作在本文将搁置不谈,仅以《洛阳牡丹记》为例试加研讨。
《洛阳牡丹记》是欧阳修子部著作代表作之一。今天虽然读之者不太多,但在宋代该著广为流传,影响极大。南宋周必大《欧集考异》载:“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谱》一卷,乃承平时印本,始列花品序及名品,与此卷前两篇颇同。其后则曰叙事、宫禁、贵家、寺观、府署、元白诗、讥鄙、吴蜀、诗集、记异、杂记、本朝、双头花、进花、丁晋公续花谱,凡十六门,万余言……后有梅尧臣跋,盖出假托也。”[13](P131)《牡丹谱》为其别名,从版本而言周必大所载应为假托本,就接受角度来说恰恰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南宋初期欧阳修该著的影响之大,以至士大夫几乎家家有其印本。且凡假托者往往借助两个要素产生,一是“假托”之人为名流,二是假托之著作形式必为当时所流行,如明代假托李贽、钟惺之评点,既是因为钟、李名望之大,也因评点为明代盛行的著作形式。所以,假托现象不但说明了欧阳修名望之大,也说明《洛阳牡丹记》为当时有影响力的著作。影响力的产生,除欧阳修的名望之外,或许与另一个名望同样很高的大家密切相关,此人便是北宋名臣、在书法上称“宋四家”的蔡襄。此前,我们很少注意到在中国古代有深刻影响力的书法当其盛行时对诗、文创作和传播产生的重要媒介作用,当然也包括诗、文对书法产生的同样作用,现在至少在欧、蔡之间我们注意到文学家与书法家、文学与书法互相借重的客观事实。欧阳修《牡丹记跋尾》记载,蔡襄“独喜书余文”。一位是文坛大家,一位是书坛名流,蔡书欧文,原本就是文坛、艺林叹为观止的佳话。这件事从文的角度来看是文以书传,从书的角度来看是书以文传,所以无论是对欧文还是蔡书来说都是扩大了影响力。据欧自言,其文如《陈文惠公神道碑铭》《薛将军碣》《真州东园记》《杭州有美堂记》《相州书锦堂记》《集古录目序》《洛阳牡丹记》,皆由蔡襄所书。其中《牡丹记》为其绝笔,“刻而自藏于其家”,又派人将模本送到任亳州刺史的欧阳修手中,使者在返闽途中,襄却已经去世。时已年过六旬的欧阳修也“老病不能文者久矣”,为此他特撰这篇《牡丹记跋尾》,“书以传两家子孙”[14](P1903)。南宋的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明确记载了蔡襄所书直接促使了《洛阳牡丹记》的盛行:“《牡丹谱》一卷。欧阳修撰。少年为河南从事,目击洛花之盛,遂为此谱。蔡君谟书之,盛行于世。”[5](P297-298)这便真实地印证了文以书传的现象。
《洛阳牡丹记》在宋代的广泛影响,可以得到目录学以及相关文献载录的有力佐证。略早于周必大的郑樵在其《通志》中已确载“《洛阳牡丹记》一卷,欧阳修撰”,并归之于食货之种艺类[15](P784)。与郑樵基本同时的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亦载:“牡丹谱一卷。右皇朝欧阳修撰。修初调洛阳从事,见其俗重牡丹,因著花品,凡三篇。”其归类则置于子类之农家类[4](P540)。稍后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同样载入该著,归类沿袭晁志,亦属农家类[5](P297-298)。该著另载佚名《牡丹芍药花品》七卷,谓“录欧公及仲休等诸家《牡丹谱》、孔常甫《芍药谱》,共为一编”[5](P298)。成书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的左圭《百川学海》,正式收入欧阳氏《洛阳牡丹记》,分《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三篇[16](P402-405),与晁志所载完全吻合。再有一条材料,可以作为《洛阳牡丹记》进入宋人阅读视野的真实反映,即洪迈《容斋随笔》卷二“唐重牡丹”条所引:“欧阳公《牡丹释名》云:‘牡丹初不载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者,彼必形于篇什,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而异也。’……然则元、白未尝无诗,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17](P17-18)洪迈的引文见于《洛阳牡丹记·花释名第二》,文字是节引,虽然对欧阳修原文的意思有误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引用本身反映了洪迈对《洛阳牡丹记》的阅读,也反映了该著在宋代的实际传播。
今天以20世纪以来文学学科和文学史、作品选为基础形成的文学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带有结果主义的局限性。所谓结果主义,就是仅以优秀作品赏析或审美为特色的文学接受,只看作品好与不好及好在哪里等,而忽略了文学之外更丰富的内容。若要认识《洛阳牡丹记》的价值,就要突破审美的结果主义局限。为此,本文将给出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即从著述史、目录学史和生活史、文化史来重新审视这部曾经产生深刻影响的不凡著作。不仅《洛阳牡丹记》如此,中国古代留下的许多著作都需要用这个视角来审视,以便重估其价值。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是影响了著述史的一部书,其独特意义首先在此。而说它影响了著述史,主要是它促使了著述史中兼有农业种植、世人生活和文人闲趣于一体的花谱类著作的形成与发展。虽然他的《洛阳牡丹记》不算最早的花谱类著作,但若翻开目录学集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就能发现“谱录类”的“草木虫鱼”之属的第一种著作就是他的《洛阳牡丹记》。宋代早于欧阳修的此类著作,还有僧仲林《越中牡丹花品》,载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5](P297),因未能传世,影响力有限。在著述史上,“牡丹记”或“牡丹谱”成为一个成员不小的家族,真正的奠定者为欧阳修。今据王宗堂注评《牡丹谱·导读》有关梳理,欧著之后有宋代丘濬《牡丹荣辱志》、张峋《洛阳花谱》、李英《吴中花品》、沈立《牡丹记》、周师厚《洛阳花木记》、张邦基《陈州牡丹记》《洛中花品》、佚名《江都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胡元质《牡丹谱》、佚名《牡丹芍药花品》,元代姚燧《序牡丹》,明代朱橚《朱氏牡丹谱》、严郡伯《亳州牡丹谱》、薛凤翔《亳州牡丹史》,清代苏毓眉《曹南牡丹谱》、钮锈《亳州牡丹述》、余鹏年《曹州牡丹谱》、计楠《牡丹谱》以及赵孟俭、赵世学《新增桑篱园牡丹谱》等相继的作品[18](P7-27)。这些书虽然不少已经散佚,但从现存诸书来看,通常都受到欧著的影响,书中往往有相关交代:
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张邦基《陈州牡丹记》)[19](P15)
于是博求谱录,得唐李卫公《平泉花木记》,范尚书、欧阳参政二谱,按名寻访,十始见其七八焉。(周师厚《洛阳花木记》)[19](P109)
洛花见纪于欧阳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载,载其著于天彭者。(陆游《天彭牡丹谱》)[19](P19)
《洛阳花记》云,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辟霜,亦一法也。(薛凤翔《亳州牡丹史》)[18](P173)
昔欧阳公于钱思公楼下小屏间,见细书牡丹名九十余种,及其著于录者,才二十余种耳。今曹州乡人所植,盖知之而不能言,而士大夫博雅稽古者,又或言之而不切时地。(余鹏年《曹州牡丹谱》)[18](P186)
上述材料包括了宋、明、清三个历史时期,也就说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的影响形成了一条历史脉络,成为牡丹进入知识视野和文化书写的历史。其中,仅第一种没有直接提到欧著,但作者张邦基为两宋之际人,所谓“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19](P15),显然是指又名《牡丹谱》的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或至少首先指的是欧之此著。至于其他数种著述受到欧著影响则是明确见于直接的文字表述,而且有一个事实不可忽略,即“牡丹谱”或“牡丹记”由洛阳而陈州、天彭、亳州、曹州,或者说陈州、天彭、亳州、曹州之有“牡丹谱”或“牡丹记”,完全是受到欧阳修洛阳牡丹书写的直接启发和影响,是一种洛阳牡丹书写辐射现象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有记有谱或有史,便当归于北宋大文豪欧阳修。仅举一例,如张邦基之所以记载陈州牡丹,是他认为,陈州牡丹比洛阳更盛且多,而洛阳牡丹已有花谱载录,而陈州则无,也就是说欧著直接触发了他的写作动机。
从著述史的内在因素来说,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的启发意义或范式意义也是突出的。后来的那些同类著作,多以“记”“谱”“品”为名,明显因袭了欧著“牡丹记”“牡丹谱”和书中“花品序”之“花品”的命名方式,显示了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的直接关系。若具体到书的内容,欧氏影响所及也有迹可寻。丘濬“援引该博而迂怪不经”[5](P298)的《洛阳贵尚录》“事为牡丹作也”,在今存世的《牡丹荣辱志》中作者序曰:“意以荣辱志其事。欲姚之黄为王,魏之红为妃,无所忝冒。”[19](P10)全书内容按“姚黄为王”“魏红为妃”“(牛黄为)九嫔”等结构,这可以从欧著中找到渊源。《洛阳牡丹记·花释名》曰:“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钱思公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19](P4)可见,将姚黄、魏红比为王与妃的立意源于欧著,从作者大体与欧阳修同时①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丘濬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则其生年大体与欧阳修相近。“寿八十一”,则其卒年大体在神宗元丰或哲宗元祐间。、该著略晚于欧著而又“援引该博”以及欧著在当时影响几个因素来说,该著受到欧著的直接影响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著名诗人陆游的《天彭牡丹谱》受欧著影响更是显而易见。“洛花见纪于欧阳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载,载其著于天彭者。”[19](P19)此与张邦基说的有类似之处,而陆著《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的内容和结构,则完全遵循欧著范式。
在中国古代,著述史与目录学史关系十分密切。目录学本身是历史的产物,由著述史决所,但对著述史有制约作用。通常的情况是,著述越丰富则目录学分目越细致多样,也就是著述史对目录学史起着促进作用。花谱或说通俗一点叫花书,目录学分类中最初归于子部农家类,但在《隋书·经籍志》农家类著述仅收《齐民要术》等五种时,自然还见不到这一著述种类的踪迹[20](P679)。欧阳修参与编撰的《崇文总目》于子部农家类亦尚未见花谱之类的著作[21](P146-147),农家类序即出于欧阳修之手,谓:“农家者流,衣食之本原也。四民之业,其次曰农。稷播百谷,勤劳天下,功炳后世,著见书史。孟子聘列国,陈王道,未始不究耕桑之勤。汉兴,劭农勉人,为之著令。今集其树艺之说,庶取法焉。”[22](P1893)后来花谱被归于农家类,正是符合了他说的“集其树艺之说”的界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部农家类著作已上升到27种,较《隋书·经籍志》《崇文书目》皆有增加。该著在《齐民要术》后的农家类叙称“前世录史部中有岁时,子部中有农事,两类实不可分,今合之农家”[4](P527),即旧有目录分类中史部之“岁时”与子部之“农家”至此合为子部农家一类,这是该类书增多的原因,但并非尽然,因为至少有13种著作是宋代新出现的,有的还是《崇文总目》编撰时未有或不见收入的,特别是花木类如欧阳修《牡丹谱》、蔡襄《荔枝谱》都是宋代新兴的著述种类。《郡斋读书志》对农家类著作的认识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即作者提出的“士之倦游”与“农家”的关系问题[4](P527),这对农家类部分著作的创作动因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释,对像欧阳修《牡丹谱》之类的著作何以会演变到农家著作之一类是一个富有启发的回答,如《宋史·艺文志》农家类著作超过一百部,单独花谱如《菊谱》《牡丹谱》《芍药谱》就达到十来部[23](P3463-3465)。
著述史的这一发展,促成目录学史的相应变化,因为宋代以来包括花谱在内的生活类著作的不断增加,在目录学史上一类新的著作类别“食货”开始出现。郑樵《通志·艺文略》于史类列出“食货”一类,下分货宝、器用、豢养、种艺、茶、酒之目,其中种艺之书达到20多部,除少数如戴凯之《竹谱》、王方庆《园庭草木疏》等几部为宋前著作外,多为宋人著作,花谱类除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之外,还《名花目录》《花品》《海棠记》《洛阳花木记》《洛阳花谱》等多种[15](P784)。《通志》在诸子类中另有“农家”之属,收入《齐民要术》等著12部[15](P797)。包括花谱在内的种艺之书从农家类分出,这说明此类著作的兴起足以成为独立的一类。随着该类著作日渐多见,其区别于农家类著作的性质也明朗起来,此在宋前则不可能。这两点应该是促成目录学家调整书目分类的客观原因,是著述史影响目录学史的重要事实。清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仍将花谱之书归于“食货类”[24](P252),体现了目录学史的前后相因。我们注意到,《隋书·经籍志》还不曾设立“食货”的类别,《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亦未见。目录学史上“食货”类别的出现以及该类著述的日渐丰富,可以认为是宋代以后著述更贴近生活的一种迹象。于是,种艺、赏玩也就成了打通宋代以来特别是明代文人生活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方式,由此生活史、著述史、目录学史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勾连。这个勾连得以引发,开其端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欧阳修,一部重要的著作就是他的《洛阳牡丹记》。
《洛阳牡丹记》花谱类著作的兴起,还改变了目录学中“谱系”或“谱谍”类著作的性质。宋人目录著作也有将花谱归于“谱谍”或“谱系”一类的,自此“谱系”“谱谍”名目下装载的内容与以前已不相同。该类著作在目录分类上归于史部,《隋书·经籍志》已列“谱系”,《竹谱》《钱谱》因其书名带“谱”字亦收入其中[20](P667)。《旧唐书·经籍志》称“谱谍”[25](P1363-1364),《新唐书·艺文志》沿之[26](P978-980),但皆未收《竹谱》《钱谱》后世归于“食货”或“农家”之类的书。《崇文总目》则取消“谱谍”之名,替之以“氏族”,原应归“谱系”或“谱谍”的《元和郡主谱》《皇孙郡王谱》之类著作收入此类。《遂初堂书目》沿袭了这种做法,只是名目由“氏族”改为“姓氏”,而其子部仍见“谱录”一类,不过这里所指的“谱录”与《隋书》及两唐书所指已完全两样,收录的是《宣和博古图》《文房四谱》《沈氏香谱》《酒谱》及《欧公牡丹谱》(即《洛阳牡丹记》)之类的生活类书籍[27](P9,16)。《四库全书总目·谱录类叙》:“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12](P1525)这里讲到的“谱录”在目录学史上其实已属“新谱录”,即名目为旧、内容则新。这一变化解决的问题是,像旧有著述《竹谱》《钱谱》有了真正的归属,不用再“寄身”它处,日益兴起的生活类、文化类著述如花谱、酒谱之类都有自己的目录家园。为此,我们看到了目录学史上一种现象,即目录分类的不稳定性,这既表现为新的目录名类的设置如“食货”类,也表现为旧的目录名类的被改造如“谱录”类。这是著述史发展造成的。有时某一著作引发了一类著述的兴起,从而改变了著述史,也改变了目录学史。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毫无疑问是发挥过这一作用的。
今天文学史的历史渊源,有重要的一支实源于生活史发展之结果。现代出版和阅读的世界里,都有一类堪称时尚的读物,就是生活类图书。此类图书之发达,标志着文化步履对社会生活的紧随趋附。这种现象,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砚谱》、蔡襄《荔枝谱》《茶录》之类著作。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华生活经典”丛书数十册,除少数几种为宋前著作外,其余多出自宋、明,宋代收入欧阳修《牡丹谱》、窦苹《酒谱》、朱长文《琴史》、张学士《棋经十三篇》等。2016-2017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艺文丛刊”数十册,主要亦为宋、明、清三代的生活和艺术类读物。单生活类,宋人著作就有蔡襄《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洪刍《香谱》、赵希鹄《洞天清录》、宋达叟《蔬食谱》、林洪《山家清供》、高似孙《蟹略》《砚笺》等。201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博雅经典”丛书20册,同样是生活、艺术、文化类读物,如《牡丹谱》《梅谱》《兰谱》《菊谱》《瓶花谱》《书谱》等,其中《牡丹谱》收宋至清牡丹著述六种,宋有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等四种。2017年上海书店出版“宋元谱录丛编”百余种,包括《茶录》外10种、《北山酒经》外10种、《文房四谱》外17种、《百宝总珍集》外4种、《洛阳牡丹记》外13种、《范村梅谱》外12种等,主要为宋人著作,如《洛阳牡丹记》外13种,除附录五代张翊《花经》外,其余14种即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丘濬《牡丹荣辱志》、张邦基《陈州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胡元质《牡丹谱》、王观《扬州牡丹谱》、周必大《玉蕊辨证》、陈思《海棠谱》、陈翥《桐谱》、周师厚《牡丹花木记》、范成大《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谢翱《楚辞芳草谱》。以上丛书命名不一,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生活经典”“艺文”“博雅”“谱录”包含的这些图书一再出版,说明这些图书内容与现代人的生活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的基础是人对生活、艺术与情趣的追求。二是溯其渊源,生活史、文化史和著述史出现的这种重要现象,全面奠基于宋代,又以明代蔚为大观。宋人于生活、艺术、文化方面的著述,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许多领域或视角都是此前未曾涉及的。虽然有的研究者,将此归因于“宋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并把宋代此类书籍视为“生物种类专门著作”[28],但着眼于“科学技术”不如从宋代社会生活来解释这种著述现象更合理。宋代社会相比它之前的社会,已发生根本变化,宋人生活与前人有了根本不同,这样便使宋人的生活体验和知识视野开始全新的建构。逮至明清,尤其是明代,承宋之余绪,大量生活、艺术、文化类著述涌现,标志着宋代那种文化品格向后代的延伸,体现的是人的生活内涵更丰富,特别是士人阶层日益成为社会中坚,社会生活朝着更丰富、更浪漫、更风雅的方向迈进。三是现代人之所以青睐于宋以来此类著作,阅读和写作都延续了这种文化趣味,意味着著述、文化与生活的一体化是宋代以来的总体倾向,这种倾向既源于生活,带动了著述与文化,又受惠于著述,影响了生活与文化,主要通过文人与文学的媒介得以播散与传承。这是生活、著述、文化共同汇成的一股脉流,宋代是这一脉流的源头,欧阳修是宋代这一脉流的重要发端者。后人特别是士人的生活、著述和文化都因此而有所改变,虽然影响并不能尽归于一人,但欧阳修是重要贡献者则是无疑的。
四、从子部视野重估欧阳修
子部视野能够为欧阳修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路径,子部视野下的欧阳修无疑能扩展、丰富、补充或者说刷新我们已有的认识,从而达到文学史以及思想史、文化史对欧阳修的一次价值重估。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思考:首先,子部建构了欧阳修的思想、知识和著述或创作;其次,同样讲子部建构,每一作家都有其个性,即其子部世界与他人不尽相同,欧阳修的子部世界必然是“欧阳修式”的,恰是这种子部建构的差异性造成了作家的思想、创作及其影响的差异性;其三,欧阳修以其子部著述及创造对子部、子学产生了建构作用,这不仅仅是一个创作问题,而且是一个创制问题。创作是指具体的著述,创制则指对目录学类别的改造或建立。可以说在子部、子学方面,欧阳修的子部创作起到了目录学创制的作用,这是他的重要文化贡献。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便可寻求到解读欧阳修的子部视野。
我们有必要把欧阳修放在经、史、子、集四部体系中来把握其知识结构的特点。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个体系中他无疑是一位以经、史为知识根基的作家,子部虽也是其知识结构的要素,但并不构成他的知识根基,其集部的知识根基也主要是经、史而不是子部,这一点与苏轼是有很大区别的。苏轼的知识根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庄、禅,这在传统目录学归于子部,也就是说子部是苏轼知识根基的重要部分,而在欧阳修则并非如此,这是欧苏异趣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点。再放在子部体系之内来看,子部是一个内容无比庞杂的知识世界,以欧阳修参与编纂的《崇文总目》为例,子部所涉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兵家、类书、算术、艺术、医书、卜筮、天文占、历数、五行、道书、释书,达20类之多。后来《四库全书总目》归为14类,即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这个庞大的知识世界,以其丰富性、开放性提供了古代士人知识遨游的无限空间,也成为培养古代士人于经、史之外思想素养和知识兴趣的重要园地。所以,子部、子学越发达的时代,知识也就越广博,思想则越丰富多样、自由活泼;子部、子学越发达的人,通常也越具个性和创造力,有的甚至被斥为异端,这又使古代思想家对子部、子学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以避免正统思想的非议和打击。子部是认识中国思想史和思想家的一个重要标尺。就一人而言,几乎没有兼赅子部全部类别的可能,这必然造成古代士人子部知识的取舍和分趋,如除归属儒家者最为常见外,又以偏重于道家、释家、纵横家、杂家、艺术、小说家等为多。这一点到了思想发达、子部繁荣的明代中后期最为突出,例如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黄道周等致力于儒学,李贽、焦竑、袁宏道、钟惺等游心于庄、禅,唐寅、徐谓、董其昌、李流芳等放情于艺术,钱希言、陈继儒、冯梦龙、凌濛初等热衷于小说,这就形成了儒家之文、庄禅之文、艺术之文和小说之文等,中晚明著述与创作之大概亦即在此四端。中晚明思想、文化和文学之所以大放异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是子学的异彩,而非经、史之学的异彩,虽经、史之学同样取得了发展,但也是被子学浸染的经、史之学,折射的是子学的光芒。
是否涉猎子部、子学,涉入什么样的子部、子学,决定了古代士人思想和知识的趣向。包罗万象的子部向古代士人开放了无限可能的世界。子部、子学可以依其性质大体划分为四大类型:儒、道、释、法、名、墨、纵横、杂主要属于思想类;兵、农、医、天文算法、术数主要属于实用类;谱录、类书主要属于知识类;小说、艺术属于文化创作类。其中,思想类中的儒属于正统,余则为非正统。杂家、小说家的情况又较为复杂,有偏向于思想的,也有偏向于文献载录的。因此,子部或子学既向古代士人开放思想世界,也向古代士人开放实用知识和艺术创作世界,在思想世界中则既向古代士人开放正统世界,也向古代士人开放非正统世界。对不同世界的选择便决定了一个人子部、子学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趣向。
欧阳修子部知识、子学思想尚属正统儒学和知识类范围,性质是谨慎保守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思想张力,这便注定了欧阳修其人其著思想的丰富性、开放性的不足。这反映了欧阳修作为儒家思想家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特点,也反映了北宋前期儒家思想重建背景下时代知识结构的共同特点,同时还反映了子学发展受到了儒学正统的约束。欧阳修子部知识、子学思想具有两个鲜明的个性:一是正统性,二是知识性。前者体现在他对非正统的道、释、法、名、墨、纵横等思想,非但没有敞开视野,反而持以严厉的批判态度;后者使他向生活世界和文化情趣开始触伸。这两点使欧阳修的子部知识和子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溢出儒家。如果我们按是否排除正统儒家、儒学把子部和子学予以狭义与广义的划分,那么可以说欧阳修的子部知识和子学思想尚属包括正统儒家、儒学在内的广义子部和子学范畴;我们按思想非正统及开放性程度把子部、子学予以核心与非核心的划分,即佛老、庄禅、纵横等异端归于核心的子部、子学,其余思想正统或知识性的则归于非核心的子部、子学,则欧阳修的子部知识和子学思想显然还属于非核心的性质。对核心的即思想异端的子部和子学世界,欧阳修不仅未大胆涉猎,而且持抵制甚至倾力批判态度。在思想史上来说,欧阳修对儒家正统的持守起到了振起儒家的作用,但也限制了他本人的视野。他以其名望和努力,对非正统思想或者说儒家之外的异端思想起了较大的阻止作用。今天的研究者很少有人把欧阳修当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来看待,而实际上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绝不低于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对欧阳修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苏轼《六一居士集叙》有精要的总结:“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6](P316)从孔子、孟子到韩愈,再到欧阳修,以此而论,欧阳修在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就是一千多年历史中的几个丰碑人物之一,可见他的贡献之大、地位之高。宋代思想特别是儒学的转变首先是由欧阳修完成的,早于后来的周敦颐和二程,却往往被思想史研究者所忽视①近年有《中国儒家史》(宋元卷)单列《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一章,可见对欧阳修的高度重视,但并没有对欧阳修在宋代以及整个儒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加以阐释,具体的内容仅涉及“论本末”“论朋党”“论正统”“经学”,没有借鉴苏轼对欧阳修思想及儒学贡献的纲领性评价并加以深刻把握。。苏轼的论述自然是从积极角度评价的。如从消极方面来看,恰是欧阳修严守正统儒学、反对异端思想,使他的知识视野和思想世界受到了极大限制。尽管他强调“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29](P305),又自谓“一生勤苦书千卷”[14](P1514),但其知识面的缺陷至今仍为人诟病。钱钟书《谈艺录》论“学人之诗”,引宋代刘敞讥“欧九不读书”之说,又引清人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所谓“盖代文人无过欧公,而学殖之陋,亦无过公”,并以为“要之欧公不得为学人也”[30](P177)。欧公为后人所讥者,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欠缺子部领域的佛教知识。欧阳修反对佛教思想不遗余力,自然拒绝阅读佛书,而佛学自宋代以后几乎是大多士人的知识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罗大经明确地说:“韩文公、欧阳公皆不曾深看佛书,故但能攻其皮毛。”[31](P195)侧面反映的是韩愈、欧阳修辟佛而不肯读佛书,在知识结构、思想水平上存在严重不足。欧阳修之后的宋人,似乎较普遍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陈善《扪虱新话》卷一一“韩退之辟佛老”条有一段很长的文字,讨论了对思想史产生不小影响的重要公案,并提出新看法:“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于是儒者咸宗其语。及欧阳公作《本论》,谓莫若修其本以胜之,又何必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哉!此论一出,而《原道》之语几废……予闻释氏之论曰:‘欲破彼宗,先善彼宗。’……今之与佛老辨者,皆未尝涉其流者也。”[32](P87)这里记载了欧阳修辟佛之论的广泛影响,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欲破彼宗,先善彼宗”的辟佛新思想、新策略,实际上也就指出了韩愈、欧阳修以及“今之与佛老辨者”知识欠缺的共同问题。人若要成功辟佛,首先必须“善彼宗”“涉其流”,也就是加强佛学修养。陈善还载录了黄庭坚对韩愈辟佛思想的质疑:“毗卢遮那,宫殿楼阁。充遍十方,普入三世。于诸境界,无所分别。彼又安能庐吾居?有大经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尘中,彼又安能火吾书?无我无人,无佛无众生,彼又安能人吾人耶?”[32](P87)黄庭坚、陈善、罗大经的观点,代表了宋人对佛教及韩、欧辟佛立场的共识。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已特别注重佛学修养,佛学造诣甚至相当高。与韩愈相比,欧阳修“修其本以胜之”[33](P513)远高于“火其书”的极端做法,但“不曾深看佛书”韩、欧并无二致。后来的儒者并没有遵照欧阳修的做法,而是如陈善所说“欲破彼宗,先善彼宗”,甚至主张融会佛老、三教归一。欧阳修之后的周敦颐、二程、张载以及南宋陆九渊、朱熹,再到明代的王阳明等,无一不加强了对佛教思想的吸纳。恰因如此,欧阳修在儒家思想地位重振方面,正如苏轼所说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但他不是宋代理学的奠定者,宋代理学以及明代心学的建立,是由一些有佛学造诣的儒家思想家完成的。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北宋中后期直到明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以及不少士人,都是朝着“欲破彼宗,先善彼宗”路子走的,这也就大大改变了儒家知识群体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境界。
五、子部作为研究方法的启示
子部不仅是研究对象,而且可以视为研究方法来运用。作为方法的子部,即是就子部为解决其他领域问题提供路径、视角、启发等而言。这种方法,旨在对作品构成的基本质料加以分析,考察一个作品是由什么写成的,而且主要着眼于构成一个作品的子部成分。
子部可以提供新的路径。以欧阳修为例,可以循子部路径观照欧阳修的文学世界,以解读欧阳修文学创作中受子部知识结构影响而形成的根本特点。例如,借助洪本健先生《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可以运用子部方法于欧阳修的研究:不难发现,欧阳修诗文据经、史者多,据子者少,这是一个基本判断。由这个判断我们大体可以把握欧诗欧文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性质,领会其基本的审美趣向。从引文情况分析,我们注意到欧阳修诗文引用频率高的是经、史或儒家类文献,如《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荀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北齐书》《韩愈集》等,这就基本划定了欧阳修的知识领域及其作品思想场域的边界,一个更加具体化的文学家欧阳修被凸显出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首先,欧阳修的思想鲜明地表现出正统性,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正统性的形成呢?关键之处就在于他的知识结构,不出经学、儒家和正史的范围,或者说经学、儒家和正史支撑了欧阳修的知识结构及其思想的正统性。其次,欧阳修的文风突出体现为纯正性,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纯正性的生成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的知识结构,其知识、思想主要游走于经学、儒家和正史的场域之中,儒家经典和正史不仅是其诗文构成的质料及思想成分,同时决定其诗文思想性质和审美倾向囿于经史之诗文、儒家之诗文。其三,正统性和纯正性固然是欧阳修思想和文学的重要特点,那么,欧阳修是否存在思想和文学的不足,其不足主要又是什么,原因何在?从知识结构来解读,这一问题同样清晰可见。以经史和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知识结构,无疑弱化了欧阳修的思想力度,也影响了其文风。文学上的欧阳修主要是在文法、文气和语言等层面取得极高造诣的杰出作家,而不以思想的自由、开放和创造著称。这一点以他最为传世的名篇就可以印证。拿《醉翁亭记》为例,如果以思想论,它表现的不过是文人的自然情怀和儒家与民同乐的观念,是屡见不鲜的陈旧主题,属于文学史长期以来尤其是古典时期文人诗文创作中常用的共同主题或者说基本母题,不具备个别性和独创性。所不同者在于,作品以文人情怀将儒家观念诗意般地包举起来,又用整散相间、精彩优美的语言和回环往复的文气加以传达和表现,其高妙之处主要在于艺术形式所达到的高度。我们注意到,古代文学中使用共同主题写作是普遍的,特别是儒家思想系统内的文学家,基本属于共同主题的写作者,欧阳修就是属于这样的文学家,而且是典型的一个。他的另一名篇《丰乐亭记》,同样是共同主题的写作,与《醉翁亭记》有大体相同的表达方式,即文人情怀与儒家观念浑然一体。这里的文人情怀仍然是山水之乐,儒家观念则是天下太平、物丰民乐以及“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34](P1018)。从骨子里讲,《丰乐亭记》相当于一篇政治文章,而具有不错的文学性。与《醉翁亭记》稍不同者,《丰乐亭记》主要是议史论世,反映出正史成分是欧文的内核。儒家价值观作为作品的灵魂,则是二文以及欧阳修其他大多数作品的共同特点,其文学的正统性、纯正性正基于此。
考察子部在欧阳修诗文中的构成要素,也可以发现其作品引文、用语出于儒家经典和正史之外者,包括《老子》《庄子》《列子》《抱朴子》等道家类书,也包括《吕氏春秋》《淮南子》《山海经》《西京杂记》《博物志》《世说新语》《搜神记》《拾遗记》《颜氏家训》等杂家或小说家文献。此以《庄子》为例:迄今为止,研究者很少关注到欧阳修与《庄子》的问题,子部路径的研究可以开拓这一方面的视野。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子部中欧阳修诗文引用《庄子》较为多见,可知在欧阳修的知识世界里,《庄子》的存在不可小觑。但我们也注意到,《庄子》在欧阳修诗文中的出现主要是作为微观材料或语料来用的,至多是局部思想而已,庄子思想没有成为欧阳修作品思想的核心。这种情况如《登绛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云:“始疑茫昧初,浑沌死镌凿。”[33](P44)此用《庄子·应帝王》儵忽报浑沌之恩而为其凿七窍之典,是对“其后窜荆蛮,始识峡山恶。长江泻天来,巨石忽开拓”的想象,即描述贬谪夷陵之时所见峡山的险恶,与《庄子》原有思想并无关联。又《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霶霈。”[33](P46)这是借助《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作则万窍怒呺”之风的描述来形容梅圣俞作品文势雄健,气魄磅礴,其旨亦非《庄子》原意。另如《镇阳读书》“有类邯郸步,两失皆茫茫”[33](P57),《鹦鹉螺》“负材自累遭刳肠,匹夫怀璧古所伤”[33](P119),《观鱼轩》“位望愈隆心愈静,每来临水玩游儵”等[33](P463),都属用《庄子》典故之例,比前两例用意进了一层,前为取词,此为取意。遍观欧集,引庄之语和用庄之典的作品略计30余篇,这从比例来说显然不构成其诗文知识含量的主体,更别说构成其诗文思想的核心。
从主观上讲,欧阳修思想的主要价值倾向不是崇庄的,这一点我们从其自编的《居士集》即可得到最起码的认识。《居士集》以古诗《颜跖》篇为全集之首,这种编排并非出自作品时间先后的考虑,而是具有欧集中思想之开篇的作用。从作品时间来说,严杰《欧阳修年谱》系《舟中望京邑》《南征道寄相送者》为天圣五年(1027),当为欧集中诗作的处女作[35](P22)。古诗中,《七交七首》“据题下注,天圣九年(1031)作”[14](P1261),或为欧集该类诗的最早作品。但这几个作品皆不被《居士集》所收,仅见于《外集》。《居士集》中的作品据题下注来看,也未严格遵循时间先后编排,《颜跖》“原未系年,作年不详”系于首篇,《猛虎》“据目录题下注,景祐三年(1036)作”系于《游龙门分题十五首》“据题下注,明道元年(1032)作”之前,《送吕夏卿》“据题下注,庆历二年(1042)作”系于《忆山示圣俞》“如题下注,庆历元年(1041)作”之前[33](P2,3,7,20,21)。这样实有理由说明,《颜跖》居欧集之首,可以看作是欧阳修为其自编《居士集》确立思想基调的主观考虑。该诗以儒家的理想人物颜回与《庄子》所赞扬的盗跖对比成篇,诗曰:“跖身一腐鼠,死朽化无形。万世尚遭戮,笔诛甚刀刑。思其生所得,豺犬饱臭腥。颜子圣人徒,生知自诚明。惟其生之乐,岂减跖所荣?死也至今在,光辉如日星。”[33](P1)这显然是一篇诗形式的人物论,作者集中塑造的两个形象在此代表的是儒、道对立的两种人生范式,欧阳修借此诗篇讨论的是人的生死与不朽的重要话题,一褒一贬、一取一舍之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儒家价值观的追求和对《庄子》价值观的否定。作者将《颜跖》置于首篇,是一种开宗明义的做法,等于为《居士集》确立了整体的思想立场。《居士集》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文本,还是一个体现价值倾向的思想文本。在欧阳修自觉设计的文本体系中,庄子思想所处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不过,庄子思想在欧阳修一生中,也存在隐现不同和前后变化,这又是不可忽视的。在欧集引庄作品中可以寻出蛛丝马迹,借此作为理解和研究欧阳修思想、文学的一个标尺或切入点:如果把《颜跖》视为欧集作品真正的思想起点,那么另一篇题为《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七韵》的长篇古诗则为欧集思想的一个拐点——它与《颜跖》结构相似,同样由两个形象构成其基本内容,其一“地僻与世疏,官闲得身佚”即作者自己,另一则是“轗轲卧蓬荜”的西邻高士,但二者已非隔膜与对立,而是“无言两相忘,相对或终日”[14](P1315)的相融与默契,与《颜跖》篇中两个形象的截然对立已完全不同。诗作于欧阳修贬谪夷陵期间,虽然不能说此时的他已蜕变为一个庄子主义者,但其思想出现了一个显然的特点——相融性,即儒、道浑然一体,彼此不加排斥,由此表现为内在思想、文学形象和语言表达儒、道边界的相对模糊。当然,这种状态并没有一直持续不变,但作为一个阶段的思想与创作心态曾经客观存在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循此便可真切把握贬谪时期欧阳修思想、情感、文学世界中那些深微层面,真切把握欧阳修一生思想、情感、文学的流变。值得注意的是,其后到了庆历五年(1045)所作《镇阳读书》又出现了新的转折点。该诗与《颜跖》《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七韵》一样,也书写了两个形象,一个是文学家、好友石介,一个是作者自己。不同的是,两个形象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二者表现为同道,且前者为后者的榜样。写石介“圣经日陈前,弟子罗两厢。大论叱佛老,高声诵虞唐”,而自己“官荣日已宠,事业闇不彰……却欲寻旧学,旧学已榛荒。有类邯郸步,两失皆茫茫”[33](P56-57),艺术上仍用对比,但属于同类之比。作品提供的思想信号很清楚,随着“官荣”的地位,欧阳修的思想界限再一次明确起来,对佛老完全持对立的态度,所以诗篇虽也有对《庄子》“邯郸学步”之典的引用,但不过是语词借用而已,只形容自己“寻旧学”的无所建树,庄子思想则荡然无存,这又似乎回到了《颜跖》描写的状态即欧阳修早期思想的情形。但往后看,这种思想状态到了其年龄渐老的时期又明显不同,庄子思想再又局部地被容纳进来,与其正统的儒家思想渐又有了浑融相存的关系。此在其人生后期变得越加明朗,所以后期的引庄也出现了新迹象。我们从《鹦鹉螺》《寄圣俞》《鸣蝉赋》《病署赋》《鹘》《憎苍蝇赋》等篇的共同特征,足以形成这样的认识,而《六一居士传》则可作为一个结点来特别看待:如果把这一名篇当成欧阳修晚年文风的代表作,但这种文风代表的显然不是欧阳修一贯的文风。如果以儒家文风与庄子文风来区分,欧阳修的一贯文风显然是儒家的而非庄子的,但《六一居士传》则是庄子似的。这篇自传不仅行文风格似庄,而且内容所及不外“更号”“逃名”“吾之乐”“世之累”以及“累其形”“累其心”等话题,最后结之以“宜去”者三[34](P1130-1132),熟读《庄子》者一看便知,毫无疑问它属于《庄子》似的文学散文。以此而言,后世所谓“六一风神”严格意义来讲就不能排除庄子风神的内涵。
至此,我们不难形成富有启示意义的几点综合认识:首先,欧阳修的知识世界和思想世界在正统儒家与异端佛老对立之外,还存在一个过渡性的“第三地带”——《庄子》与庄子思想,这使他的思想和创作于正统、纯正之中也带有一定的自由和超越,在排斥佛老之时偶又向佛老相近的庄子思想敞开一扇小窗,由此决定他的儒家思想体系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其次,与儒家经典、正史相比,包括《庄子》在内的子部虽然不占欧阳修知识结构的主体,但思想价值不以构成大小而论,庄子思想因其异质性恰恰成为引发欧阳修思想、情感、文学之新变的重要因子。再者,欧阳修存在隐、显两个知识世界和思想世界,整体而言,儒家经典、正史和儒学思想是他知识和思想的显世界,《庄子》与庄子思想则属于隐世界,但隐的知识和思想世界又存在时隐时现的状态,由此构成他知识世界和思想世界的基本特点,也产生一定的可变性和丰富性。最后,欧阳修一生存在前后变化,这种变化看似不那么明显,却有表现深微的一面,变化的外在诱因是其仕途之升迁、阅历之积累,说明欧阳修思想的功利性、世俗性十分突出,而内在诱因则以《庄子》与庄子思想为其重要方面,成为其超功利、超世俗的精神来源。如果把《颜跖》大体看作欧阳修思想起点时期之作,《六一居士传》大体看作其思想终点时期之作,这既显示了他的儒家思想之流变,也显示了他庄子思想之流变,前者由正统、纯正变而相融、通达,后者由隐约、排斥变而明朗、容纳,但变化并非一以贯之,而是时断时续,由此形成一些板块式思想时段,但精神世界总的趋势是由冲突心态到浑融心态。上述几点应该是把握欧阳修思想、情感和文学的关键所在,对中国古代经典作家甚至一般作家的考察不无范式意义。
讨论欧阳修的子部世界及其知识结构问题,除对欧阳修研究有启示作用外,还有更广泛的意义,包括经典作家的个案研究、作家与作家比较研究、文学史特别是断代文学史研究、接受史既包括作家接受史也包括断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等,都可以开拓新思维、新路径。
关于经典作家甚至一般作家的个案研究,本文提出的从知识结构入手的研究途径无疑是有普遍应用空间的。考察作家的知识结构不一定局限于子部,经、史、子、集四部的整体考察会有更宏大的视野,但子部仍然是最具特别意义的一个领域。子部庞杂多元、无所不包甚至离经叛道,是经、史、集不能比的,所以对一个作家子部知识和子学思想的考察,意义就非同一般。从子部考察作家的知识结构,不仅可以为解释一个作家思想、情感、文学是否具有个性,剖析构成其作品的知识成分与思想来源,还可以有效地用于作家的比较研究,判定不同作家因知识结构不同特别是子部知识的差异所产生的思想分趋和文学差异,在此基础上既揭示文学思想产生的知识基础和文学风格形成的知识因素,同时对探讨一个作家何以具有思想创造力和文学创新力的内在动因,从而寻求到文学发展的重要规律。一般来说,子部知识越广博、子学思想越丰富,则意味着被正统性束缚相对较弱,思想的开放、多元、自由、活泼则更突出,创造性则更强,反映在文学则更具有思想情趣和审美情趣。我们从苏轼、李贽、袁宏道、张岱等杰出作家得到有力佐证,甚至更早的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王维、柳宗元等,也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由此上升到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作家特别是能突破正统思想束缚、极大地获得思想创新力的作家,子部就是他们必然要对自己敞开的富有伟大思想意义的知识世界,甚至对未来的中国作家来说,谁的子部知识更深厚,子学思想更多元活泼,谁就可能成为思想更具创造性、文学更具性灵的作家,正如苏轼等人一样。这实际是关乎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规律性认识。
子部、子学深刻影响于文学史是显而易见的。文学的时代性,既由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因素所决定,还由时代的知识结构特别是士阶层的知识结构所决定。子学思想和子部著作发达的时代,往往也是文学繁荣的时代,比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就是文学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这些乱世给包罗万象、思想多元的子学留出了发展空隙,而子学的发展为文学家和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创作活力。归结起来,文学发达的直接原因是子部的发达,而不是乱世本身,因为文学不发达的乱世时代还有不少。子部考察对促进断代文学史和整个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很有助益。以晚明为例,这是子学繁荣促进文学繁荣的典型时代。若仅限于流派、小品文风、地缘、家族等研究,必然会忽视一个基本要领,即这一时代整体的知识结构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子部作为士阶层主要知识构成这一事实。所以,晚明文学的研究,要加强对这个时代子部知识和子学思想的研究,加强对经典作家知识结构和子学世界的研究。这对解决晚明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的一些问题都将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可以从不同历史时期作家个人知识结构和子部知识、子学思想的考察,获得对明前中期与晚明文学之不同的有益解释,探求明代文学演变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因素;可以从不同文学流派的知识结构及其子部世界差异性的研究,把握明代文学流派林立、观念对峙的深层诱因,寻求从台阁体、茶陵派到复古派为什么没有实现文学革新的历史转折,而到了李贽和公安派才完成了文学革新的使命。这种研究路径还可以启发接受史研究。以明代文学而言,从司马迁、李白、杜甫的接受(复古派),到欧阳修、曾巩、邵雍的接受(唐宋派),再到苏轼的接受(公安派),其背后并不是简单的文学崇尚问题,而是意味着对纯粹文艺接受,还是理学接受或庄禅趣味接受的选择。明代心学运动扩大了士阶层的知识世界,培养了他们的思想情趣,故经历了心学运动洗礼、具有广阔知识背景、深邃思想素养的文人不再倾心于纯粹文艺,转而喜欢宋学影响下的宋诗宋文,这是明代文学趣味的一大转变,但这种转变很快被庄禅趣味取代,所以尽管唐宋派在反复古派的道路上进了一大步,而大势所趋则是由冲破理学束缚而以庄禅为思想个性的公安派来最终完成明代文学的根本革新。唐宋派与公安派的区别,可以说就是在于推崇欧阳修、曾巩、邵雍和推崇苏轼的不同,前者是理学的文学,后者则是子学的文学、庄禅的文学、非理学的文学。以此而论,明代文学各流派之不同、各阶段之变迁,归结到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士阶层和整个社会知识结构和思想趣味之变化。走向子学是明代思想的整体趋势,走向子学的文学则是明代文学的整体趋势。这种趋势到了清代被重回经、史的正统之学所打断,明代知识、思想和文学的发展方向便被根本改变。清代文学基本上可以说是根基于经、史的文学,而非晚明根基于子学的文学,这尽管不能说是一种倒退,但可以肯定的是已然为另一种文学,思想活力和文学趣味已远不如晚明。
明代文学及研究可以如是观,其他时代文学及研究也不妨作如是观。作为方法的子部与子学,将开辟文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