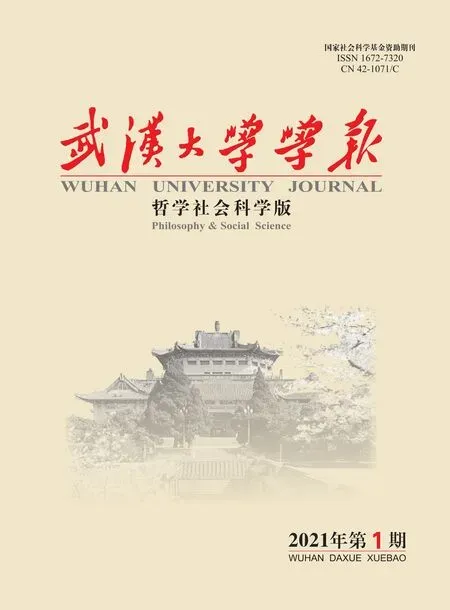俗文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廖可斌
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古代俗文学研究,开启于20世纪20年代,迄今已有百年历史。现在,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研究重心出现向下、向后倾斜的趋势,俗文学研究越来越受关注,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研究高潮。但是,关于俗文学的概念、范围、研究方法、发展方向等问题,人们的认识还存在许多模糊和分歧之处,有必要予以探讨。
一、俗文学的概念和范围
现代以来通行的俗文学概念是郑振铎等前辈学者确立的。它相对于雅文学而言,主要指由下层文人和普通民众创作、以口头创作和表演为主而同时亦以书面形式创作和传播、主要面向普通大众、以通俗白话为主要语言载体的文学作品。
就中国古代到近代俗文学而论,俗文学最根本的特征是语言的通俗性。凡是语言比较通俗的,就可以算是俗文学;凡是语言不够通俗的,就不能算是俗文学。
为什么说只有语言的通俗性才是中国古代到近代俗文学的根本特征呢?
首先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按照雷·韦勒克和奥·沃伦《文学原理》的说法,语言是文学的材料,文学就是特定的语言材料按照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形成的东西[1](P165)。文学与科学、历史学等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学内部各种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于使用的语言不同。“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每一种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词汇的选择。”[1](P186)文学中的雅俗之分,更主要来自它们所使用的语言之差异。
其次,中国古代到近代长时期存在“文言”与“白话”分隔并峙的现象。虽然其他民族的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书面语与口语、雅言与俗言的区别,但可能都不像中国古代到近代“文言”与“白话”的分隔并峙这样突出,这与中国古代到近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有关。中国古代长期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专制君主需要大量官员辅助其治理国家,通过培养和选拔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阶层,这是长期实行封建制的西欧国家中所没有的。“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似乎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似乎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2](P2)这个“士”阶层逐步形成了一种自我确认的群体共识,即以“读书仕进”和“精思为文”为自身的职责与使命[3](P16)。能够写作高雅的文言文,成为这个群体的一种身份标志。他们坚持用文言写作,以与社会普通大众保持距离。不管社会普通语言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们都坚持运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进行写作。中国古代到近代“文言”与“白话”的长期分隔对峙,对中国古代到近代文学的“雅文学”与“俗文学”的长期分隔并峙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现代文学基本上都运用白话文(还有少量作品运用文言文),文言与白话不再是区分雅、俗文学的主要标准,但雅、俗文学的区别仍然存在,现在一般称之为“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主要区别似乎在于前者以探索为主,后者以娱乐为主。但语言实际上还是重要的区别标志。现代“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表面上看来都是运用白话文创作,但运用的具体“语言材料”即“文字词汇”和组织结构是不一样的。
第三,除语言外,前述俗文学的其它特征都是相对的。例如作者,固然俗文学作品大部分都是下层文人和民间作者创作的,但不排除下层文人和民间作者也创作雅文学如诗、文等,而中上层文人也可能创作俗文学。又如读者,俗文学固然主要是供普通民众阅读欣赏的,但普通民众也可能阅读欣赏雅文学,而中上层人士也有可能阅读欣赏俗文学。再如创作和传播形式,俗文学固然较多通过口头创作和传播,但部分俗文学作品(如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也通过书面创作和传播,而雅文学的部分作品(如诗、词、曲)也可以通过口头创作和传播。至于作品的内容,雅文学与俗文学虽然各有偏重,但难以截然划分。雅文学多反映中上层社会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俗文学多反映下层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但雅文学中也有反映下层社会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俗文学也有反映中上层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
所以说,鉴别中国古代到近代俗文学的基本标准,就是用当时相对通俗的语言作衡量尺度。按照这个标准,俗文学包括白话诗词文赋、白话小说(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章回小说)、戏曲、说唱、歌谣杂曲、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笑话、谜语等。其中说唱、歌谣杂曲的文体特征和所包含的具体种类非常复杂。说唱又被称为讲唱文艺、曲艺等,包括变文、诸宫调、俗讲、宝卷、宣卷、道情、陶真、弹词、评弹、词话、说书、评书、评话、子弟书、鼓书(大鼓、鼓词、鼓子词、鼓曲)、琴书、坠子、快书(快板、板书、竹板书)、货郎儿、数来宝、莲花落、木鱼书(木鱼词、木鱼歌)、相声等多种名目;歌谣杂曲也有歌谣、佛曲、俗曲、杂曲、小唱、小曲、曲子、岔曲、俚曲、磨难曲、杂牌子曲、民歌时调、秧歌、潮州歌等多种名目。这里面有些名目之间大同小异,甚或名异实同,只是同一种文学形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不同叫法而已。
关于当代俗文学研究的范围,现在有学者认为,白话诗词文赋、白话小说和戏曲实际上已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雅文学范围,神话、故事以下的各种文体则属于民间文学的范围,而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日益向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靠拢,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因此,最典型的俗文学就是说唱和歌谣杂曲,它们是真正的俗文学。
俗文学究竟包括哪些文体,是现代俗文学研究史的一个老话题。郑振铎撰写《中国俗文学史》时,主张文学分雅、俗两大类,凡是不属于雅文学的都属于俗文学,建构了包括上述各种文体在内的大俗文学的概念。“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4](P1)胡适、周作人、钟敬文等人则认为这种二分法比较笼统,主要问题是郑振铎所称的俗文学种类比较复杂,其间差别较大。因此,他们主张三分法。胡适的三分法是文人文学、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周作人的三分法是纯文学、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钟敬文的三分法是士大夫阶层文学、市民文学(小说、戏曲)和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谭帆《俗文学辨》系统梳理了上述诸家的观点,倾向于抛弃郑振铎的大俗文学概念,而使用胡适等人的三分法概念[5](P79)。
古今俗文学中存在各种类别,其中有些类别之间差异很大。当代俗文学研究出现“三分”的分化也是事实,胡适、周作人、钟敬文等人的辨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谭帆教授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辨析也是必要的。但三分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胡适、周作人两人的说法比较接近。唯周作人用“纯文学”,不如胡适用“文人文学”,因为俗文学不一定就不是纯文学。钟敬文的说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可能是为了突出“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的地位,但其说法中有概念不清的地方。一是市民难道就不是劳动人民吗?二是市民难道就一定没有口头文学吗?三是劳动人民就一定没有书面文学吗?
他们共同的问题,也是三分法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分类的标准不统一。文人文学(纯文学、士大夫阶层文学)和民间文学(劳动人民的口头)是按作者划分的,俗文学却是按作品的审美特性划分的。其次,按作者来分,存在很大局限。古今文人就一定不创作俗文学吗?显然不是的。民间(尤其是民间教育和文化逐步普及的明代以后,特别是现代)就一定没有俗文学,甚至一定没有雅文学吗?显然也不是。其三,把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分开,它们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很难说清楚。有些民间文学(如评书、弹词)与俗文学(如通俗小说)究竟有多大差别?
在确定俗文学的概念、划分俗文学的范围时,应具有辩证观念。
首先,从雅文学、俗文学到民间文学,它们之间固然存在一定区别,但这种区别绝不是界限分明的。在一种文类与另一种文类之间,存在着较大规模的中间形态。我们应该抛弃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方法,而要运用灰色光谱地带的思维方式。有些文学是纯雅文学;有些是以雅为主,而兼点俗;有些是又雅又俗;有些则以俗为主,而兼点雅;有些则是典型的俗文学。在纯粹的雅文学到俗文学两端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灰色光谱地带。所谓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也存在着大量既可称为俗文学也可称为民间文学的东西。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有一定差异,但它们的根本特征是一致的,就是俗,它们总体上属于俗文学,我们没有必要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
将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分割开,还会造成研究中的画地为牢。中国古今俗文学内部各种文体之间本来存在同生共长的密切关系。离开了戏曲、小说,我们很难把说唱文学、民间歌谣杂曲、故事传说等说清楚;离开了说唱文学、民间歌谣杂曲、故事传说等,我们也很难把戏曲、小说说清楚。将它们统一纳入俗文学,有利于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揭示中国古代俗文学发展的本来面目。
其次,有些作品,如白话诗词文赋、古典小说、戏曲,在古代时期,与典型的雅文学如诗、词、文、赋等相比,毫无疑问是俗文学。在现代,它们确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雅文学了。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应该将它们放置在古代历史环境中来观察。在古代曾经属于俗文学的,我们仍然应该将它们视为俗文学。在后来或现代已经不是俗文学了,我们就不再将它纳入俗文学的范围里。如先秦的《诗经》,相当一部分是民歌,比较通俗,在先秦时代属于俗文学。两汉以后,《诗经》变成了经,写作《诗经》四言体诗歌的主要是文人,语言也变得典雅了,那么两汉以后的《诗经》四言体诗歌就属于雅文学,不再属于俗文学了。又如词,敦煌曲子词根本上还属于俗文学,两宋以后的词就不属于俗文学了。我们既不能因为这些文体曾经属于俗文学,而将它们后来的发展形式一直视为俗文学;也不能因为它们后来雅化了,变成雅文学了,而否认它们早期属于俗文学。
根据中国古今俗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基本坚持郑振铎确定的大俗文学的概念,将上述各种俗文学都纳入大俗文学的范围,这可以称为广义的俗文学。同时,考虑到戏曲和小说、说唱文学与歌谣、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等之间确实存在一定差异,研究确实已出现分化,小说戏曲研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典化,特别是民间文学已逐步向民俗学等学科靠拢,我们可以将说唱和歌谣杂曲视为比较典型的俗文学,或曰狭义的俗文学。
二、俗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俗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俗文学本身具有重要价值。雅文学固然是一个民族文学的精华所在,但俗文学也是一个民族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它诞生在下层民间,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反过来又塑造了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是活在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学与文化。
雅文学(精英文学)不等于高水平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也不等于低水平文学。雅、俗主要只是风格特别是语言风格的区别。雅文学(包括当代探索性文学)中也有低水平文学甚至伪文学,俗文学(包括当代娱乐性文学)中也有高水平文学。有的作品能够大俗大雅,雅俗共赏,把娱乐性与探索性完美地结合起来。
在古代和近代,俗文学的地位和影响更为重要。当时识字的人是少数,而不识字或基本不识字的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对大量民众来说,他们与“四书五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相距遥远。他们主要是通过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俗文学获取相关的知识,构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并指导自己的生活。俗文学在当时社会的影响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身处当代社会的人难以想象的。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到近代文学包括俗文学,必须回到历史环境中,充分认识俗文学在当时整个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如果把雅文学比作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那么俗文学则是隐藏在海面以下的巨大存在。海量的俗文学作品,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和生存智慧,也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真实精神面貌。俗文学中所呈现的广大民众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往往与雅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面貌判然有别,甚至大相径庭。我们要真正准确认识中华文化,了解中华民族的特性,吸取其中的宝贵资源,继承其优良传统,同时也认清其中的种种糟粕,都必须高度重视对俗文学的研究[6](P12)。
从文学研究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俗文学研究也是今后最有发展前途的领域。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一个所谓社会史的转向。此前历史研究的重心是政治史、军事史、制度史,此后历史研究的重心逐步转移到社会生活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这是所谓后现代学术的重要特征,根本上是社会进一步趋向民主化平等化的表现。例如,思想史属于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研究重心也发生相应转变,即从以往主要研究精英经典的思想史,到注意研究整个社会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一般知识、信仰和思想世界。按照这种学术理念,精英经典的思想固然代表一个民族的思想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但不能反映民族思想的整体状况和真实面貌。恰恰是整个社会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一般知识、信仰和思想世界,才反映了民族思想的整体状况和真实面目。思想史研究中的这种学术潮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古代思想的认识。中国学术界中,葛兆光教授较早关注到西方学术界的这种潮流,并借鉴其方法,他认为:“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的世界中起着作用。”[7](P13)因此,他撰写的《中国思想史》,就重点关注中国古代整个社会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一般知识、信仰和思想世界,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境界。
中国古代文学界对西方学术界发生的这种转变反应比较滞后,古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人们基本上还是按照五四运动以后确定的古代文学研究基本格局,沿袭人们已经习惯的研究方法。虽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又一次比较大规模地借鉴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如文学的接受与传播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等,但雅、俗相分、以雅为主的格局,以及按照雅文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俗文学的习惯仍然如故。这不仅造成了俗文学研究的严重不足,也造成了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陈旧与局促,造成了选题大量重复、愈趋支离破碎的局面。有那么多俗文学研究的领域任其长期荒芜,无人问津,研究者宁愿挤在雅文学和部分俗文学的范围内徘徊踟躇,陈陈相因。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大胆突破,毅然踏进俗文学研究领域。
有一段时间,我们曾强调学术研究要与国际惯例接轨,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赶上和引领国际学术潮流。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又转而强调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提出要打造中国学术话语,发出中国声音。其实这两者不是对立的。要真正赶上和超越西方学术潮流,首先必须了解、借鉴西方学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果我们不注意了解和借鉴西方,而一味强调中国话语、中国声音,就很容易变成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夜郎自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避免盲目地崇拜西方,迷信西方,而必须坚持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主体性,一方面还得了解和借鉴西方,在此基础上达到平等对话。就文学研究而言,近几十年西方文学研究的潮流是什么呢?就是在继续强调古典、经典研究的同时,加强对民间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从中发现新的材料、新的问题。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研究俗文学是研究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没有多大价值,殊不知这恰恰是符合国际学术潮流的,是具有创新性的,也是具有远大前途的。
三、俗文学研究的方法
俗文学研究如此重要,为什么现在关注的人不够多,成果不够理想呢?除了人们认识上存在误区,观念有待转变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俗文学研究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在一定程度上比研究雅文学还要难。因此,很多人宁愿在雅文学研究的范围里挤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或不敢涉足俗文学研究。
研究俗文学的难度,首先体现在掌握资料难。研究雅文学,文学作品及相关文献往往已经搜集整理得比较齐备,可以直接利用。俗文学的很多文献资料则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调查和完善的整理,已有的相关目录也不完备,研究往往要从搜集第一手资料开始,有时候还要进行田野调查,这样研究的周期就拉长了。许多俗文学文献还存在于一些图书馆的角落、民间收藏者手中和海外,往往是手抄本或比较粗糙的印本,辨识困难。如清代到近代是传统戏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戏曲文献非常丰富,很多保存在各个博物馆、图书馆和个人收藏者手中。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利用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内府剧本、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府及昇平署文献,研究清代宫廷演剧的就比较多,而利用海内外戏曲世家、重要爱好者和研究者及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其他各种戏曲刻本和抄本的就比较少。如国家图书馆所藏吴梅、郑振铎、王孝慈、朱希祖等的藏曲,首都图书馆所藏车王府、北京孔德学校、吴晓铃和许之衡等藏曲,中国艺术研究院所藏傅惜华碧蕖馆藏曲,梅兰芳纪念馆所藏清廷供奉陈金雀、四喜班著名演员曹春山藏曲,上海图书馆所藏周明泰“几礼居”、周越然“言言斋”藏曲,浙江图书馆所藏姚燮《复庄今乐府选》,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清车王府、杜双寿、马廉“不登大雅堂”、清廷供奉陈金雀藏曲等,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赵景深藏曲等,这些就很少人问津。原因在于这些民间抄本,不像清代宫廷文献那样整齐美观,使用方便,而是大多格式凌乱,字迹模糊。保存在更底层的俗文学文献,情况更差,整理使用就更不方便了。
收集到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以后,又遇到掌握俗文学研究资料的另一个特殊的困难,即资料太多,难以把握。研究雅文学,有时只要一册在手,反复阅读,深入分析,就可以基本不假外求。俗文学研究往往面对大量资料,不知从何下手。
这就涉及俗文学研究最关键的问题了。俗文学研究必须有强烈而敏锐的问题意识,要善于在大量语言通俗、结构和情节相当简单、艺术技巧看起来比较粗糙低劣的作品中,发现有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然后围绕问题组织材料,展开论述。研究雅文学,有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有许多现成的概念、范畴、问题,人们可以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研究俗文学,则缺少这样的依凭,要靠研究者自己去发现新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发现有意义的问题呢?一方面是要全面掌握文献,细读文献,从中发现值得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要具备比较宽广深厚的知识面和理论修养,能够见微知著,从微观中透视宏观,在宏观中审视微观,善于捕捉细节中包含的重大问题,在地方性知识中提炼普遍性知识问题,将具体问题上升到宏观高度,揭示其中潜藏的巨大意义。从文献中发现问题,根据问题进一步搜集和组织材料,形成问题与文献的良性互动,这样才不至于在大量俗文学文献面前束手无策。
由于俗文学中包含的往往不是纯文学的问题,而是属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问题,多与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有关,所以研究者需要对多个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有一定了解。善于跨越学科之间的界限,发现不同领域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善于围绕问题跨学科领域搜集材料,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或综合研究。如果能跨语种搜集材料,能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关俗文学现象进行比较,那就更为理想。
在俗文学研究方面,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自叙青少年时代对各种各样的雅俗文学作品都感兴趣,《三侠五义》《施公案》这类通俗小说也读得津津有味,唯独对《再生缘》这种主要为女性读者服务的弹词作品读不下去。直到留学美国和欧洲,了解到口传诗学理论,又接触到大名鼎鼎的希腊史诗如《伊利亚特》《奥德赛》等,才明白《再生缘》这样的作品属于口传文学,与希腊史诗等性质相同。我们应该用口传文学的标准去衡量,而不应该用书面文学的标准来评价。比如它的结构的循环,就是口传文学共同的特点和规律,不应该简单予以否定[8](P1,64)。陈寅恪先生通过研究《再生缘》所提出的这一重要观点,对我们研究俗文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论〈再生缘〉》的意义还不止于此。陈寅恪先生在重新评价《再生缘》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分析了《再生缘》中孟丽君中状元、作宰相、让丈夫下跪、让公公挽车等情节,指出在清朝那个妇女受歧视的时代,《再生缘》作者的这种思想可谓石破天惊,具有巨大的想象力和超前性,可谓难能可贵,振聋发聩。在此基础上,陈寅恪先生深入挖掘,分析中国人过去何以对《再生缘》中这种堪称伟大的思想视若无睹的原因。他通过对中西文化的观察思考,发现中国人过于重视实际,而轻视幻想,因而缺乏突破精神和追求理想的精神。中国人历来对《再生缘》的态度,就是这种文化特征的一种反映。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中西文化的一个显著差异。没有幻想就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就缺乏突破和创新。陈寅恪先生对《再生缘》的研究,就从对口传文学文体的研究,再提升到对整个中国文化特征和中外文化差异的探讨,其见解发人深省。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留学欧美的经历,对口传诗学理论的掌握,对希腊史诗等的了解,以及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有关[9](P93-105)。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俗文学研究的论著都达到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的水平,但他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四、俗文学研究的历程和现状
从中国俗文学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开始了对它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唐宋以后,特别是元明以后,俗文学各种体裁蓬勃发展,相应地涌现了大量记载作者姓名生平、著录作品名目、汇编作品以及进行理论研究与批评的俗文学文献。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文学界开始将俗文学视为可与雅文学媲美的文学,甚至认为它是比雅文学更有生命力的文学,俗文学得到高度重视,人们对俗文学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中国近代以来俗文学研究的一篇标志性文献。梁氏将俗文学的代表文体小说的地位抬升到文学正宗的地位,认为它比雅文学更重要,这对改变人们对俗文学的态度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但梁氏主要是从小说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对当时的社会改良的重要作用来强调小说的地位和价值,他的主要指向不是小说或俗文学本身。其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章回小说考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等,则是从俗文学本身的价值出发,对俗文学进行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50年代,出现了一个搜集、编目、整理、研究俗文学的高潮。除上述几种里程碑式的成果之外,罗振玉《敦煌零拾》、顾颉刚《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其他》《吴歌甲集》、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刘复和李家瑞《中国俗曲总目稿》、郑振铎《西谛所藏弹词目录》、凌景埏《弹词目录》、李家瑞《北平俗曲略》、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宝卷总录》《子弟书总目》《北京传统曲艺总录》、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关德栋《曲艺论集·胡氏编著弹词目订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编《弹词宝卷目录》、李世瑜编《宝卷综录》、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中国古典戏曲理论集成》《古本戏曲丛刊》1-4集和第9集等,也是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俗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进入新时期。在小说戏曲方面,《古本戏曲丛刊》余下各集陆续编印,《全元戏曲》《古本小说集成》《古本小说丛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明清传奇综录》等陆续出版,《全明戏曲》《全清戏曲》编纂正式启动。项楚《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相继问世。在说唱文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编目成果有谭正璧和谭寻《弹词叙录》《木鱼歌、潮州歌叙录》、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李豫等《中国鼓词总目》等。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整理成果有《清车王府藏曲本》《未刊清车王府藏曲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傅惜华藏古本小说丛刊》《传统戏曲、曲艺研究参考资料丛书》《故宫珍本丛刊》(第38-59册收录岔曲、大鼓、连花落、秧歌、快书、子弟书、石韵书、鼓词等多册,第660-718册收清南府及升平署剧本和档案)、《俗文学丛刊·戏剧类、说唱类》《子弟书全集》《中华珍本宝卷》第1-3辑、《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清末上海石印说唱鼓词小说集成》《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清代民歌时调文献集》等。另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曲艺志》(各地方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各地方卷)、《中华文化通志·曲艺杂技志》等大型曲艺志问世。在中国俗文学文献电子化方面,比较重要的有爱如生“典海”平台《中国俗文库》等。少数民族俗文学文献整理方面,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汉文全译本和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大全(藏文本)》的整理出版,是其中的标志性成果。
国外学者历来比较重视对中国俗文学的研究,其中日本学者盐谷温、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大塚秀高、金文京,美国学者韩南,荷兰学者伊维德,俄罗斯学者李福清,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法国学者陈庆浩等,对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研究成果比较重要。在说唱文学方面,日本泽田瑞穗著《宝卷研究》《增补宝卷研究》,稻叶明子、金文京、渡边浩司编有《木鱼书目录:广东说唱文学研究》,俄国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荷兰伊维德著有《孝道与救赎:两种观音宝卷》《包公与法治:1250—1450年代词话八种》等。
上述成果为俗文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居功至伟。但总体来看,对中国俗文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还存在很大不足。
首先,在观念上我们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俗文学已经给予足够重视,但中国古代雅文学的传统特别博大深厚,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其惯性作用超出我们的想象。真正得到足够重视的实际上只是俗文学中那些比较接近雅文学的戏曲、小说经典作品,而大量更为通俗的戏曲、小说作品,特别是众多说唱文学和歌谣杂曲,仍然被认为过于粗糙俚俗而遭到忽视或轻视。许多俗文学文献,时代偏于晚近,不属于善本古籍范围,还躺在某些藏书机构和个人收藏的角落里,任其霉变,无人清理。许多俗文学文献流散海外,调查搜集比较困难。俗文学研究至今未能进入学术研究的主流,依然处于边缘位置。真正全力投入这一领域的优秀学者和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仍然偏少。
其次,上述目录和文献整理大多由某位学者独立完成。但以个人之力,几乎不可能将全国以至海外各地的某类文献收集齐备,不可能对每种文献都手检目验,因此这些编目和文献整理难免存在不全、不准的缺陷。有关文献整理大多就某一地区甚至某一藏书机构所藏某类文献进行整理。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度重视俗文学文献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相继立项“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汇萃与研究”(黄仕忠)、“中国历代小说刊印资料汇考与研究”(程国赋)、“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宋莉华)、“中国历代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纪德君)、“《西游记》跨文本文献整理与研究”(胡胜)、“大连图书馆藏明清小说整理与研究”(李洲良)、“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李永平)等重大项目,有力促进了俗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但这些项目也基本上还是以某地、某馆藏某类文献(或研究文献)为整理研究对象,仍然比较零散,不够系统。
在研究方法上,早期俗文学研究借鉴了西方和日本俗文学研究的方法,注重田野调查,搜集第一手材料;注重运用综合研究方法,将俗文学研究与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研究相结合,取得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一些学者借鉴美国的“口头诗学”等理论和方法,也为俗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10](P120-125)。但总体上看,由于中国雅文学研究的传统极其强大,再加上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仍然习惯于搬用雅文学研究的方法,用雅文学的标准来分析评判俗文学,不能根据俗文学创作、接受和演化的特殊性,来揭示俗文学本身的特点。
五、俗文学文献调查和整理的历史机遇
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对俗文学文献进行全面的调查整理,是推动俗文学研究向前发展的前提。现在,我们迎来了改变中国俗文学文献编目整理不全不准的局面,全面搜集、系统整理中国俗文学文献,展现中国俗文学文献的完整面貌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这就是2013年正式启动的“全国古籍普查”。
在此之前,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中国古籍总目》,收录约20万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约收录6万种。但这两种书目收录仍然不全。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决定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其中一项工作即全面开展全国普查,力图彻底摸清中国古籍的家底。自2013年起,全国2000多家古籍公藏单位联合开展“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普查数据输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发布内容包括普查编号、索书号、题名、著者、版本、册数、存缺卷、收藏单位等内容,系统支持用户按照普查编号、索书号、题名、著者、版本、收藏单位等进行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支持繁简共检,实现了全国古籍的统一检索。用户可在检索结果中按照单位进行导航,从而对其在全国的收藏分布情况一目了然。该数据库所公布的古籍普查数据,是全国各古籍收藏单位通过目验原书,首次按照统一的古籍著录规则完成的普查工作成果,是我国目前最大、最完备的全国古籍书目数据库。截至2018年11月,全国24个省2315个单位已完成普查,共普查古籍260余万条另14500函(藏文),占预计总量之80%以上。截至2019年10月,已累计发布217家单位所藏 772861条、7447203册古籍的普查数据①据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官方网站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预计全国古籍普查和数据发布工作将于近两三年内完成,普查数据将达到300万条以上,著录的古籍有可能达到25万种左右。
除国内古籍外,海外汉籍数量庞大。长期以来,除日本的一些公藏机构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少数机构编有汉籍目录外,其他机构的汉籍收藏情况并不为国内学者所详知。2015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面向国内的“全国古籍普查”相配合,正式启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2016年启动建设“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累计已收录包括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55万条(含子目)书目数据,初步实现海外汉籍的统一检索。
与此同时,鉴于民国文献数量巨大,意义重大,而且已经过数十年,状态堪忧,亟待保护,国家图书馆于2011年又启动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这是继“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之后的又一个全国性文献保护项目。其中的具体工作之一是编纂《民国时期图书总目》,迄今已对全国60余家图书馆所藏民国时期图书普查汇总,共获30余万条书目(含不同版次),《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在编校中。该社配套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已收录民国文献18万种。
随着以上三项古籍和民国图书普查登记工作的展开,大量古籍新品种、新版本被发现,民国时期图书总体面貌得以呈现,许多过去不为人所知、不受重视的俗文学文献重见天日。此轮全国古籍普查所增添的数万种古籍,以清代特别是晚清时期的作品为主,抄本占相当比例,其中许多就属于俗文学文献。如浙江图书馆普查登记目录共收录说唱类文献约650种,据初步比对,其中至少有数十种不见于此前各种目录,如:清抄本《宋誌纪纲安邦后集》弹词十六册、清末石印本《新刻周老龙还披风》曲艺一册、清末石印本《新编月明珠》曲艺一册、清刻本《新刻东调珠蝴蝶》弹词一册、清抄本《酒后茶余》曲艺一册、清刻本《新刻秘本唱口桃花》弹词一册、清刻本《新刻说本唱口玉夔》一册、清抄本《执桂亭》弹词一册等[11]。绍兴图书馆普查登记目录共著录说唱类文献约240种,其中至少有十余种不见于此前各种目录,如清光绪十五年刻《消闲唱曲六种》一册、清宣统三年刻《江南松江府华亭县白沙村孝脩回郎宝卷二卷》一册、清抄本《全讃桃》曲艺一册等[11]。甘肃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共著录小说、戏曲、曲艺类文献498种,含白话小说、戏曲、曲艺340种,其中(清)玉佛园等辑、光绪二十六年刻本小说集《遇佛缘》四卷等,为诸种小说目录未收录。苏州戏曲博物馆对所藏216种宝卷进行了清理,其中就有多种为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所未收,后者是迄今收录最全的宝卷目录[12]。
六、俗文学研究之前瞻
我们可以在文献调查、搜集和整理与研究理论和方法两方面着力,推动中国俗文学研究向前发展。
我们可以依托“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和“民国时期图书总目”这三大普查项目的成果,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俗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排查搜集,力争做到竭泽而渔,修订或重编中国俗文学各种文体的目录,整理出版俗文学文献,改变目前俗文学文献整理各自为战、比较零散的状态,形成系统的目录和资料汇编,全面反映中国俗文学的整体面貌,为学术界和社会提供最完整、最准确的中国俗文学文献信息。
调查整理的范围,一是以古代为主,延及民国。根据民国年间俗文学与古代俗文学联系紧密、民国年间俗文学仍然繁盛、民国俗文学文献也亟待保护等原因,整理研究范围可以古代为主,延及民国,下限到1949年。二是以说唱文学和歌谣杂曲为主,兼顾小说、戏曲。因为说唱文学和歌谣杂曲以往重视不够,在普查中新发现的俗文学书目和文本,也以这两类为主,所以应是关注的重点。至于戏曲、小说,过去已比较重视,有关书目已比较完备,《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集成》《古本小说丛刊》收录比较齐备,《全元戏曲》已出版,《全明戏曲》《全清戏曲》已在编纂中,所以戏曲、小说方面新获信息将不是太多。但在普查登记中新发现的戏曲、小说方面书目和文本,特别是民间的抄本,也要纳入整理研究范围。至于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笑话、谜语等,基本上属于口头文学,已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收集整理已取得较大成绩,可不涉及。三是先搜集整理汉语俗文学文献,同时兼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俗文学文献。各少数民族俗文学文献极其丰富,而且各少数民族俗文学之间、各少数民族俗文学与汉族俗文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它们都是中华民族俗文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本工作步骤,一是筛选分类。先对“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民国时期图书总目”所著录的预计达 400万条以上信息进行全面筛查。这三个数据库基本按普查登记号或索书号上报,没有进行分类,必须将其中所有属于俗文学的条目筛选出来,然后按俗文学的不同文体分类汇总。二是核实信息。可根据筛选出来的分类目录,委托全国各地相关学者分别到收藏图书馆核对。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等工作有奖励措施,按条付酬,调动了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因此上述项目普查比较彻底,漏收的情况较少。但受各种因素影响,收录、著录的讹误难以完全避免。因此必须组织俗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确认或修正。三是补充修订或重编俗文学目录。根据筛选和核实的俗文学文献信息,对现有的各类俗文学目录进行修订或重编。应充分尊重原有目录作者的劳动功绩。可视不同文体目录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对补充信息不太多的目录,向原作者或与其相关的学者提供新获信息,包括著者、卷次、评点者、收藏单位等,请他们对原目录进行补订,仍以原作者名义重新出版,有的在前言、后记中说明补订情况,有的可加上补订者署名;对补充修订条目较多的目录,可组织专家另行编纂“补编”,与原有目录配套,单独出版;对补充修订条目比例较大的文体,则重新编纂目录出版。四是比对、遴选珍稀俗文学文献,分类影印出版。上述大范围普查登记中发现了一批过去不为人所知的俗文学文献,它们分藏各地,相当一部分收藏于地方图书馆或外国图书馆。虽然根据补充修订或重编的俗文学目录,人们已可得知其线索,但阅读使用仍不方便,因此有必要影印出版。首先要将所获得的全部俗文学文献信息,与已有相关目录、已整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比对,筛选出此前没有出版、甚至没有著录的俗文学文献,然后遴选出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按文体分类,编为若干辑,影印出版,弥补以往俗文学文献整理的不足。五是建立数据库。在全面掌握俗文学文献书目、文本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建立中国俗文学文献电子数据库,以便检索利用。
要提高俗文学研究的水平,运用合理的理论和方法是关键。目前国内的俗文学研究,总体上还存在着视野狭窄、观念陈旧、方法单一的问题,很多成果都属于对某种单一的俗文学文献的调查和描述。这样的工作是在为俗文学文献的调查、搜集与整理添砖加瓦,也是有意义的,但价值有限。俗文学研究应该逐步超越文献描述的层面,提升到以问题为核心的层面。应该特别注意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如文人诗词文赋与俗文学通俗诗词文赋之间关系的研究;特别注意不同俗文学门类之间关系的研究,如小说与说唱之间关系的研究;特别注意不同民族的俗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特别注意中国俗文学与外国俗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如印度、中西亚、蒙古、朝鲜、日本、东南亚俗文学与中国俗文学特别是中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俗文学关系的研究。要结合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知识信息,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原创性的俗文学研究的问题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