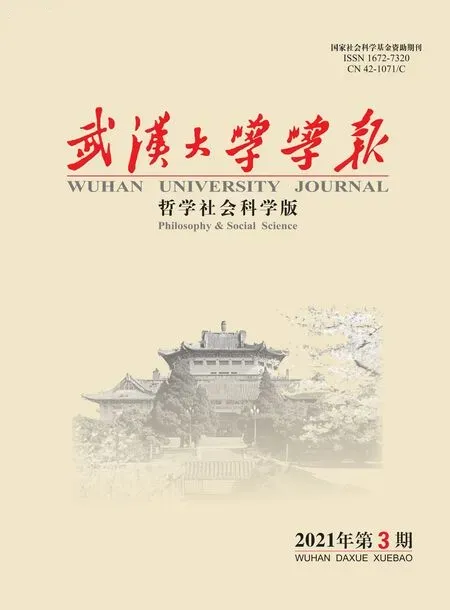神人交互的精神辩证法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机制
陈 赟
身为欧洲文明之子的黑格尔早期即自觉面对如何处理启蒙的视角与基督教视角对西方文明自我理解时的张力问题。彼时的黑格尔面临的是双重的分裂:一方面,宇宙经由启蒙理性的祛魅被解离为两个难以连属的部分——位于此岸的是那已被客体化了的、以机械性物理性为特征的内在世界,它是那种可为纯粹现象主义的因果法则穿透的世界,好像一个无神的庙宇;另一方面,位于彼岸的则是远离内在世界的充盈着神性光辉的绝对,高高在上,俯视尘寰。与此相应的是,人越来越被理解为内在世界的存在者,神性根基则在生存经验的视野之外。伴随着人神分裂的是如下结果:一方面人们浪费在天堂的大量珍宝已经无法转化为内在世界中的生活资源,另一方面被内在世界封闭了与神性关联的人又不得不忍受无根基之痛苦。基督教在人与神、人与世界之间建立的桥梁在启蒙理性之后已经不再有效,无论是古希腊的还是犹太—基督传统的那种朝向神性根基的生存,都无法满足这个降格为现象的内在世界,由此,世俗历史与神圣历史自奥古斯丁以来的张力性结构已经坍塌,黑格尔将自己的使命理解为重新定位理性概念以重建人与神、上帝与世界之间的连续性,从而克服两种历史的分裂:他将启蒙以来的理性贬低为被封闭在使范畴之有序化成为可能的静态知性,以主体与实体的相互涵摄重新定义那被局限在观念中的理性,使之自我运动,走向具体的普遍性。它不再是理解概念和理论的一种主观性的形式,而是具有自我现实化为具体存在的动能。这种理性不仅可以展开在整个人文世界,而且也可以达到对整个人文世界的自我把握。在黑格尔时代,虽然各科学问都有了各自进展,但从文明论的整体上将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并回思人类文明整体,却依然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这项事业自启蒙以来业已发生一种危险,即世界历史被降格为现象层面的文明多元而无法触及纵向性的历史深层演化机制而有中道夭折的可能性。在世界历史的欧洲时刻,黑格尔承付的是化解上述危险重塑世界历史之精神的文明论使命。虽然其后有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克斯·韦伯等接续此一思想劳作,但黑格尔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仍然是难以匹敌的,任何一位走在此道上的哲人,都不能不去面对黑格尔。譬如20 世纪在这个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哲人沃格林,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处理黑格尔。黑格尔不仅是伟大的开创者,更是站在欧洲文明立场上的集大成者,其学问之规模、深度、广度,及其精微高明,可谓罕有匹敌者。黑格尔虽然面向了人文世界乃至文明整体的具体性,但从来也没有遗忘对人类历史文明之普遍性的探寻。在历史哲学的名义下,他所达成的对整个人类文明与西方文明整体的探寻,都被归纳在精神、理性与上帝的辩证运动中。这一辩证运动体现为上帝对世界历史的统治,或者容纳神、人的精神之自我运动,这种运动被构思为世界历史的本质性内容。
一、以理性敞开作为精神的上帝之奥秘
正如卡尔·洛维特业已指出的那样,整个西方近代历史哲学都无法脱离犹太—基督的神学背景来理解[1](P30-47,215-230)。历史哲学的使命自维柯以来就被定位于理解世界历史的天意蓝图,黑格尔接续了这一使命:“上帝的本质是通过基督教显示出来的,所以基督教徒就得到了上帝袒露的奥秘,这样一来,解开世界史的奥秘的钥匙也就提供给了我们,因为世界史就是上帝的本质展示为一种特殊环节的过程。”[2](P28)[3](P40-41)①本文在引用黑格尔此书(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Introduction:Reason in History)时,参考了李荣添的《历史之理性: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述析》(台北:学生书局,1993),李氏对黑格尔此书有选译与评论。世界历史不过是上帝之本质自我展开的环节,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只是这样一种事业,即认识隐藏在世界历史中的上帝之规划或意志,后者构成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哲学要理解的便是这个计划,因为只有从这计划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理性’便是要领悟上帝的神圣工作。”[3](P67)[4](P38)之所以需要建立在理性的地基上,正是因为,唯有理性才使得上帝的认识成为可能②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格尔这里,理性与上帝或天意的关联在于,如无理性,人就无法理解天意;而上帝的显现也必将是一种理性秩序。故而天意、上帝的统治与理性的支配表达的不过是同一内涵:“理性正在支配和已经支配世界,这个命题是以宗教的形式这样得到表达的,即天意掌控世界。”[5](P134),而那些不符合上帝计划者,或者是消极的,或者是毫无价值的。启蒙运动以来的上帝,之所以远离具体个人,远离世界,因而也远离历史,保持为一种无法开启的超验性奥秘,乃是因为以知性去面对它的结果③黑格尔强调:“新时代的‘知性’把‘上帝’变成一个抽象体,把它变成一个超绝于人类的‘自我意识’的事物,从而使‘上帝’成为一堵光秃秃的铜墙铁壁,人们只能对之顿首兴叹。”[3](P106)黑格尔强调:“基督教已经揭示和启示的正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奥秘,即上帝就是人的本性与神的本性的统一。这是宗教之为宗教的真正理念……神的东西与人的东西的这种统一是宗教的真正理念。现时代的知性已使神圣理念成为一种抽象东西,一种在人的彼岸的存在者。”[2](P82)知性的上帝“出自纯粹的无限性,太高大、太非凡,以至于我们的血肉之躯无法蒙受”[6](P397)。;只要实现认识方式的进阶,上帝之奥秘将被敞开。
上帝并非上帝自身之本质,而只是上帝与人的关系,或者上帝对人的显现方式;人在不同的存在层次,上帝便会有相应的对之显现的方式:当上帝对人而言乃是奥秘之际,就意味着我们把握它的方式还停留在感性或知性的样式:
思辨的理念与感性者相对立,也与知性相对立;因此,对于感性的考察方式及知性而言,它是秘密。对于二者而言,它是一个μυστηριoν[神秘、秘密],意即以理性者在其中之所是者为意图而言。通常意义上,秘密并非上帝的本性,在基督教中至少是如此;在此种情况下,上帝已表明可被认识,指明了他是什么,在此情况下他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感性知觉、表象,对于感性的考察方式以及对于知性而言,这就是秘密。①黑格尔强调:感性、知性的研究方式与理性、理念的研究方式对上帝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理念中,诸区别不是被设定为相互排斥,而是仅仅在一个与另一个的相互结合中。这是真正的超感性者,而非通常那应高居于其上的超感性者;因为这同样也是一个感性者,就是相互外在和漠不关心。假如上帝被规定为精神,那么外在性就被扬弃了;所以,对感性而言,这是个秘密。同样,此理念高于知性,对知性而言理念是一个秘密。”[7](P172)现代神学由于诉诸知性,因而上帝成了位居彼岸的超验者,而不是内在于世界之中:“对知性而言,上帝是独一者、诸本质的本质。这种无差别的、空洞的同一是知性和现代神学的虚假产物。上帝是精神,是使自身成为对象性的东西且知自身就在其中,即具体的同一,因此,理念也是一个本质的环节。”[7](P173-174)[7](P171-172)位居彼岸的作为奥秘的上帝,乃是吾人认识分裂之结果,而且,它只能将人的生存引向内在性的某种稍纵即逝的高峰体验,而不是向世界历史中的精神及其实践开放自身:一方面造成人性与神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上帝与世界的对立②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批判的一个要点就在于,基督教对神性的高扬是以对人性与世界的贬抑为代价的,它将拯救托付给个体内在信仰而不是道德伦理生活,是从现实生活秩序中的逃离。“基督教一般不可能促进道德”,“即因人们不把道德而把神祇弄成了这些教义的终极目的,道德的目标便从人们眼前失去了”[8](P127)。,而“对变得如此坚固的对立加以扬弃是理性的唯一兴趣”[9](P10)[10](P11)。黑格尔的新上帝乃是经历了最高分裂之后统一性的重建,这一重建依据的是本身有着神性的理性③黑格尔说:“理性是有着神性在内的,理性的内容及其根据皆在神圣的理念,而理性可说得上是上帝蓝图的本质所在。”[3](P67),其内涵一方面包含着上帝与世界的和解,另一方面包含着神性与人性的统一。这样的上帝被黑格尔理解为自我设定自己、在与他者的差异中回归自身的“精神”,精神将世界历史作为自己的舞台:“‘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只有这一种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④在1822-1823 年的历史哲学演讲里,黑格尔对其历史哲学的总结如下:“整个历史进程是精神的一种连贯进程,整个历史无非是精神的实现过程,而这种过程是由各个国家完成的;国家就是世界历史在尘世中的实现。真的东西必须一方面在纯粹的思想中,另一方面也在现实中作为客观的、得到发展的体系存在。但这必定不[始终是]外在的、客观的,毋宁说,同一个主观精神必须在这种客观性本身中是自由的,并且第三,必须认识到现存东西的内容、这种客观世界精神的内容是它自己的。所以,这种内容是给精神提供见证的精神,它在精神中就是在它自身,就是自由的。重要的是洞见这样的事理,即精神只有在历史和当下存在中才能解放自己和满足自己,现在发生和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仅源自上帝,而且是上帝的作品。”[2](P449)[4](P468-469)
这并不是说上帝不在自然中显现⑤在黑格尔那里,“上帝就是一切之始和一切之终,犹如一切源出于此一样,一切也复归于此;而且,上帝也是一个中心——上帝使一切拥有生命,激励一切,并赋予所有那些形态以灵魂,保持其实存”[11](P1)。上帝作为精神,其历史就是“区别自身、分离、撤回自身的过程”,它有三种存在形式:(1)在思想的要素中,上帝在纯思想中是自在自为的,是启示的但还没有显现;(2)在表象的要素、个别的要素中,即意识囿于与他者的关系,上帝在表象中,这就是显现;(3)在主体性本身的要素中,譬如情绪、表象、知觉的直接性主体,或概念所是的主体性,即思维的理性那里,精神获得了自由。其中在(1)中上帝外在于世界,是无空间的,也外在于时间;在(2)中,作为实存的实在存于世界中,是在完善的定在中的上帝,神圣历史作为过去,原本的历史者而存在;在(3)中,也就是在内在的场所中,在世界中起作用,但同时耸入天界,是直接主体性的精神的现在存在,但作为一种面临完善的当代之现在,其完善性被设定在未来[7](P162-163)。,但在自然中,由于没有人的认识,上帝并不能意识到他自己,它只是作为一种神圣自然而将自身保存为完美的、潜在的但却是不确定的、未能充分发展的存在;只有在精神中,通过人的存在,通过人对绝对者的认识,上帝意识到他自己,并通过人类而充分地完成自己。在这个意义上,精神才是上帝的真正园地⑥黑格尔指出:有限的世界“分解为自然的世界和有限精神的世界。自然只是进入与人的关系中,而非自为地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中,因为自然不是知。上帝是精神;自然不了解上帝。它是由上帝所创造的,但它并不从自身出发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中,这是在它不是知者的意义上说的。自然仅仅处于与人的关系中;在与人的关系中,它是人的依赖性方面所称之者。只要自然被思维认识到,它由上帝所创造,知性、理性在它之中,它就为思维着的人所知;就此而言,当自然的真理已经被认识到时,自然就被设定在与神圣者的关系中……自然对人而言就不仅是这种直接的、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在其中认识到上帝的一个世界;因此,自然对人而言就是上帝的一种启示”[7](P187)。:“惟有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精神才有着最具体的现实性。”[3](P46)进一步的,自然“是为精神和人而存在的自然”,但在更高层次就会看到,自然其实只是精神的较低级形式,即“人的自然性”,通过它显现的上帝是不充分的。上帝是精神,对人而言,自然中的上帝只是被启示出来的;而宗教、艺术与哲学,作为人的活动与精神的作品,才是作为绝对者的上帝的最终完成形态,而世界历史则归属在上帝显示自身或精神自我实现的客观精神阶段,后者意味着主观性在客观性(体制化秩序)中的显现以及二者的相对统一。“上帝统治着世界历史”意味着,“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光从精神的自由的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从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12](P352)[13]··(P473)。必须指出的是,精神(Geist)与智慧(Ⅰntelligence)的不同在于,精神“人人生而皆有”,非由外烁,而智慧则因禀赋的不同在不同人那里而有多一些与少一些之异;而且,人的Geist可以经过社会化过程和学习过程而扩展,因而并不是“一个人固定的、静态的心——Mind”;“Geist是指有目的、有方向的精神动向,与精神好不好的那个‘精神’不同;Spirit大致接近它,但没有含有目的的意思在其中”;因而,Geist实质上意味着“人人都有的、能扩大充实的、有一定意向的精神”,Geist是人之所以能够理解万物之原因;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巨大系统,包括了人类的无数创造物,此大系统代表着世界精神(Weltgeist),“人去理解千万的事物,也就是试着去理解那个世界精神。因为人不断地学习、社会化,所以人的Geist照逻辑来讲也正是Weltgeist的一部分,也反映了Weltgeist”,在这个意义上,“‘Geist’(精神)因此常常可以当作人的‘历史意识’的同义词。强调Geist,其实就是强调历史意识”[14](P129)。
由于只有上升到理性层面上帝才能作为精神呈现自身①“对于思维的理性来说,上帝不是空洞无物者,而是精神”“上帝是精神,是具体的”“上帝不是最高的感受,而是最高的思想”“上帝自在地就是精神”[11](P21,32,44,57)。,因而理性乃是精神的定义性特征。上帝的本质存在于思维之中,至于直观和情感,其实最终只是思维的潜意识或不成熟的形式。理性进入每一个独具特色的人的行为之中,所有的表象形式本质上都是合理性的模式,因而在最终意义上,作为精神的上帝是思想而不是情感的对象,“上帝就是思想,它会在自己里面创造出思想来,就像我们在世界历史里所看到的情况一样”[3](P40)。基督宗教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将作为绝对者的上帝启示给人类,从“感性的精神”到知性之“表象的精神”最终朝向“思想性的精神”发展,上帝的本性在“思想性的精神”中得以彻底真正显现[3](P40-41)。上帝是思想,精神是健动的②黑格尔指出:“精神这个事物是活跃的,健动是它的本质;它是自己的产物,因为它本身即自己的起点而又同时是自己的终点,它的自由并不展现为静态的事物,而是体现为一种不断的否定——精神会不断对那些足以危及到其自由的事物加以否定,精神的目标便是去产生自己,去使自己成为本身的对象,以至于去认识自己。”[3](P48),因而也是不息的,它能够将思想自我实现于它的对立面,即实存中。在这个意义上,精神是理念(Ⅰdea),是那种能够将思想性的概念与时空中的存在统一于自身者,由此,精神本身又是自由的;精神同时还是意识,也是意识的对象,因而它的本性就是自己认识自己[3](P47)。
二、作为神性与人性统一体的精神
黑格尔深刻地看到,上帝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对象来认识的客体之物,只是在与我们的关系中显现自己[11](P31)。精神概念是上帝与人的统一,或者说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在上帝的理念里,那里有着其统一的存在,那是精神的普遍性跟其在个体之意识的统一……在基督教里,神圣的理念乃被展示为神性与人性的统一。”[3](P106)在人那里的有限精神与自然处于对峙中,它还不了解它与自然的最终统一,上帝在自然中的显现与在精神中的显现处在二元对立状态。“当我们将绝对概念称作神性时,精神之理念即成为神性与人性之统一。”[7](P155)充分的精神概念内具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它意味着无限精神(上帝)之下降与有限精神(人)之上升。“只要对人而言上帝不是一个陌生者,人未把上帝作为外在的附加者来对待,而是当人根据其本质、自由和主体性被接纳于上帝中时,人才能知自身被接纳于上帝中……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在自身普遍性中的人,乃是人的思想和绝对精神之自在自为存在的理念。在异在存在在其中自我扬弃的过程中,上帝的理念和客体性也自在地是实在的,即在一切人之中是直接的。”[7](P204)有限者通过扬弃自身的有限性而将自身提升为神圣者之过程的环节,属于外在个别的有限的一切皆已消失,这是有限性本身的升华。“神性与人性之统一的实体者为人所意识,于是人为其显现为上帝,上帝为其显现为人。此实体的统一是人的自在。”[7](P205)在“道成肉身”的象征化思辨中,上帝显现为个别的人,以人为形象,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上帝必须以人为指向,人性的生成本身就是在神之下生存的结果①“基督自称为上帝之子和人子:本应如此理解。阿拉伯人互称为某个部落的子孙;基督属于人类;这是他的部落。基督也是上帝之子;此说法的真正含义,理念之真理,基督对其社团而言之所是者,以及在基督及其社团中的真理的更高理念,亦可注释、表述为:一切人的子女均为上帝的子女抑或应使自身成为上帝的子女,如此等等。”[7](P212);“上帝在基督中被启示了,神性与人性也统一于基督之中。……基督是神人,上帝同时也具有人性”;“神圣的当下本质上与人性者相同一”[7](P214,212)。如是,对上帝的理解也就是对人性的自我理解:“上帝的内容史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史,是上帝向人的运动和人向上帝的运动。”[11](P173)
人与上帝是相互依存的,上帝依存于人类的活动及其自我认识,并通过人类的自我认识最终实现自己。如果没有人的自我认识和行动,上帝在自然中虽然仍在,却是潜在的且不充分的;只有通过人类的活动,才能使上帝真正完善和自我实现。由此,人类活动对上帝的存在乃是不可或缺的,它本身就具有神圣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上帝需要人,依赖人:“上帝只有通过他与自己的中介才会存在;他需要有限者;他自己将有限性设定为某一他者,并借此而自身成为他的某一他者,成为某一有限者,因为他有某一他者与自己相对立。”[11](P140)上帝是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但他不能在自身内部意识到他自身,必须通过一个不同于他的中介,即是从他之中分化出来的另一个他者,尤其是通过那个他者的自我意识来意识自身。在上帝的所有受造物中,人因具有自我意识而能够成为上帝认识并展开自身的中介。通过人类活动,上帝将自己的存在展现在比自然更高、更具深度的层面,通过人对其自身的理解而达成上帝对自身的自我理解。人在这个意义上是上帝之迹,是帮助上帝实现自身的助手;人也因为充当这一助手而将其自我实现提升到超出人类自身的更大、更高维度,启蒙以来被封闭在内在世界中的人由此以升华了的方式被自我克服。对人类而言,以这样的方式参与世界历史、参与神圣存在,又是他的本性的内在要求,因而他的自由作为他的作品而言,又是本性之必然②在早期的《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就认识到:“只有精神才能够认识精神”,“‘神是精神,那些崇拜神的人必须在精神和真理中崇拜’。自己不是精神怎样能够认识精神呢?一个精神与另一个精神的关系是谐和之感,是它们的合一;不同性的东西怎样能合一呢?信仰神只有在这样条件才可能,即信仰者本人也有神性,这种神性在它所信仰的对象里重新发现它自己的本性,即使它没有意识到它所发现的就是它自己的本性。……所以对神的信仰是根源于自己本性的神性。只有神的一个变形能够认识神”[8](P432-434)。。
由此,有限个人若认识上帝,也必须转向人类及其历史自身。因为他自身便是精神。“基督的‘神性’,要由一个人自己的‘精神’来证明——而不是由各种‘奇迹’来证明;因为只有‘精神’认识‘精神’。”[4](P335)上帝的精神对人而言,本质地呈现在人的共同体中,呈现在人与人的相互承认的秩序中,呈现在以国家为中心的伦理生活世界。“对上帝而言,人性者恰非一陌生者,而是异在存在、自我区别、有限性……乃是在上帝自身处的一个环节,当然却是一个消失中的环节。”[7](P220)只有通过将自身提升到绝对精神,精神才真正完成自身。对一个人而言,他必须出生两次,一次是自然的,一次是精神的③黑格尔两次出生的观念也来自基督教传统,譬如奥古斯丁曾说:“第一个人亚当早已去世,在他之后,第二个人就是基督,虽然在这两个人之间有成千上万的人出生。所以从生育的继承中出生的所有人,显然都属于第一个人;正在恩赐的恩典中出生的所有人,都属于第二个人。这样一来,两个人,即第一个和第二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整个人类。”[15](P79)对奥古斯丁来说,从亚当而来的出生是肉身的,这导致了人生而负债,即背负原罪的“束缚”;从基督而来的出生是灵性的,这是将那些根据肉身的方式出生的众人解除他们生来就欠付的债务。;精神的出生不是直接的,它只是像它生于自身那样存在;它仅仅作为再生者存在[7](P237)。而作为通过牺牲而复活的基督之象征,给出了由每一个个人必须自己去完成的道路,自然生命的死亡不再是时间之内的那种褫夺意义的无常,相反,它应该被升华为复活的可能性:“人类的本质就是‘精神’,人类只有在剥夺了他自己的有限性、并且委身于纯洁的自我意识的时候,他才能取得真理。……这一部历史是每个人必须在他自身内完成,然后才能存在为‘精神’,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王国中的公民。”[4](P337-338)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上帝的存在采用了“人格神”方式,而是“指向真正的上帝理念”[3](P106)。相比于早期的黑格尔通过基督教把精神(Geist)理解为既产生于又来自于爱的东西,作为那种自我屈服和自我发现、外在化和内在化的整个过程;成熟的黑格尔不只把精神仅仅看作是两个有限个体之间的爱的经验,而且还发现,只有在有限的自我意识到他们自身是无限的时候,以及在无限通过有限意识到了自身的时候,精神才存在[16](P133-134)。“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力量。”[17](P3)这意味着,精神从人性出发而对人性向着无限性的扩展与提升:既然上帝通过认识人而就是人自身,那么,人通过认识上帝也就是上帝生命本身的环节。耶稣基督受难死亡而又复活的故事,对人类的精神历程而言就具有了普遍意义:“基督——作为人类来说——他一身里表现了上帝和人类的统一,他的死亡和他的全部历史里表现了‘精神’的永恒的历史。”[4](P337)当然,上帝与人由基督教所启示的统一性,“决不可以肤浅地作皮相的看法,以为上帝就是人类,同时人类就是上帝。相反的人类必须将他的‘精神’的‘自然性’和‘有限性’扬弃,并将他自己提高到上帝的地位”[4](P333)时,他才是上帝[18](P324)。黑格尔虽然克服了近代以来将人措置为内在世界中被封闭了神性关联的生存者的取向,但同时也脱离了古典基督教在人神之间设置的张力性结构。
神人之间的生存张力意味着,人朝向其神性根基,人与神相互参与,却并不能达成互构。至于耶稣基督作为“神—人”的象征,并不在人的可能性之内,人无论如何朝向神性根基,永远都无法成为“神—人”。因而,古典基督教所达成的人的位分——生活在人神的居间的位置——在黑格尔那里又被消弭了。“神—人”一旦成为人的原型,最终结果不是人神在分裂之后的参与性结合,而只能是彼此界限敉平之后人对神的取代以及随之而来的无神状态的加剧。卡尔·洛维特刻画黑格尔历史哲学时正确指出:“只有基督教的上帝才既是精神也是人。这个原则是世界历史运转的中轴。全部合理的、理性的和可理解的历史都是‘到此为止和由此出发的’。”[1](P84)沃格林在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中看到的则是神人居间张力的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自我显现对神显的反叛。黑格尔所谓的新教原则,“将神圣理智的世界(dieⅠntellektual-Welt)重新置放在人的心灵之中,从而使‘人能在自己的意识中去看、去认识、去感觉此前曾属超越的万物’”“历史的居间被颠覆为一种辩证的运动”[19](P252)。黑格尔取消了上帝的奥秘,借助“神—人”(theanthropos)将神的显现(theophany)下降为人的自我显现(egophany)事件①黑格尔的基督被沃格林理解为“一位在教义上衍生出来的神一般的人;他出现在‘神性存在变成人’(Menschwerdung des goettlichen Wesens)这一事件中。这是‘绝对宗教的朴实内涵’。这个神性存在‘被认识为精神(Geist)’;这个宗教是‘意识到自我成为精神’……‘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同一,被看见的(angeschaut)正是这个单元(Einheit)’。‘至高的存在能作为一个生存着的自我意识而被看见和听见,这正是其概念的完善’”[19](P359)。,由此,神被自我显现的“神一般的人”或者“超人”替代甚至被谋杀。由于上帝不再是秘密,黑格尔取消神性实在位于神性深处的那个层面,连同对处于居间的生存的意识一并取消[19](P362)。对沃格林来说,上帝或神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旅程的终点,而是旅程的方向,因而与上帝的关联成为永远无法达到终点的朝圣之旅。黑格尔的这一“严重缺陷”,在沃格林看来,便是“将启示的逻各斯化约为哲学的逻各斯,进而将哲学的逻各斯化约为意识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最终取消了人神的分界,可知与不可知的分界;黑格尔的人神和解方案的实质被认为是:“道成肉身不再是上帝进入历史的神秘,而是上帝与人在世界中的同一成为真理的意识。上帝和人在‘精神’中融为一体,启示与理性在‘理念’(Ⅰdee)的展开中融为一体。这样一来,理性为真,合理性成为现实性,就都是合理的了。……借助符号Geist,辩证法的灵知就可以从上帝滑向人,又从人滑向上帝,也可以从两者滑向主体即世界的本质”,这非但无法破解“存在秩序之谜”与“历史人类之谜”,相反,其导致的结果是“哲学家的逻各斯占有存在”[20](P81)。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人性与神性的统一,上帝本身就必然是一个触发人性贬抑的超验机器;如果上帝保持奥秘,永居彼岸,那么正如伯尔尼时期的黑格尔所认识到的那样,此世的人生就变成永无结果的等待,这种无法完成的等待“使人陷入一种备受折磨的不确定状态”②黑格尔指出:“基督教的一种区别于理性的、为理性所不知的教义是那种可怕的非此即彼的抉择:人们在来世所等待的命运不是永恒福祉,便是万劫不复。这是这样一种抉择:假使在此世之后未来的观念对人们来说如同奎宁治疗伤寒确实那么可靠和可信,这种抉择我们也可以说在此世(在此世之后这一恩赐的王国就会结束,无情的正义的王国就将开始)决不会给人以片刻安宁,而是使人陷入一种备受折磨的不确定状态,这种不确定性在其不完善感支配下永远是摇摆在对世界的裁判者的恐惧和对那位仁慈宽容的天父的希望之间。这是一种充满苦痛的状态。”[8](P123),无法舒缓、平息历史性生存的紧张与焦虑。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神的本质虽然向着人性的完成开放自身,但神性毕竟不能为人性所穷尽,神性之下的,并不仅仅是人的精神化生存,还有万物的生存;即便回到具体个人,神性也包含着永远无法被穷尽、永远无法被透明化的内涵,唯有随着历史的展开而日渐显现,但这一显现本身却没有终点;或者说,所有的终点不过是新的开端。
上帝与人的统一,在黑格尔那里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理性的狡计(或机巧)”(die List der Vernunft)。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对其概括如下:“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威力的。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意义下,天意对于世界和世界过程可以说具有绝对的机巧。上帝放任人们纵其特殊情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果,不是完成他们的意图,而是完成他的目的,而他[上帝]的目的与他所利用的人们原来想努力追寻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21](P394-395)在世界历史中,“理性的狡计”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理性在世界历史过程中超脱于主观的情欲和特殊的目的之外,同时又保存自身在这些主观的情欲和特殊目的之内;一方面它引导具体的情欲彼此消耗,自己却丝毫不受损伤,另一方面它通过具体的情欲实现自身①“在世界历史中,特殊的情欲有自己的利益,它是有限的,因而它一定会损伤消失的,在特殊的情欲之间彼此斗争的过程中毁灭自身。然而正是在那斗争中、在特殊事物之毁灭中,那普遍者却由此产生,它自身一无所损,因为并不是普遍理念处在斗争之中,它本身退居幕后,不为所动,不为所伤,没有任何危险,而是指使情欲的特殊利益去相互斗争,去损耗它们自己,这就是人们所称之为的理性的狡计。”[3](P89)。世界历史被视为经线(“神的机制”——普遍性的理性、法则、终极目的、自在的精神)与纬线(“人的机制”——具体个人与民族的主观目的、特殊情欲等)交织而成的作品。在“人的机制”内,善恶、是非并存,难以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但善恶分明、是非井然;然而这是一个具有偶然性的世界,具体的情欲虽然只是追求特殊利益,以个体为中心,甚至是自私的,却是行为之普遍原动力与效用力,倘若没有情欲,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伟大的事业能够被成就,它构成世界历史的主观驱动力,理性正是通过情欲而实现自己②在这里,不难发现黑格尔与康德的如下构思的连续性,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提出“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康德所谓的对抗性正是“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也就是指人类进入社会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又是和一种经常威胁着要分裂社会的贯穿终始的阻力结合在一起的”[22](P6)。这里涉及对恶的处理,在天意支配下的世界历史中何以出现恶,恶在何种意义上是与天意不矛盾而有其自身的意义。康德与黑格尔无疑从基督教传统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处理。。在“神的机制”内,对人而言的善与恶、是与非的对立其实并不存在,“以人观之”而得的偶然也并不构成真理本身的规定③黑格尔指出:“把世界史当作自己的舞台、财产和领地来实现自己的精神,不是一种在玩弄各个偶然事件的外在游戏中四处游荡的东西,毋宁说,它本身就是绝对起规定作用的东西;精神的独特规定相对于各个偶然事件是全然固定不变的,它将这些偶然事件为自己所用并加以驾驭。”[5](P164)。世界历史本身又与个体生命和民族生命处在不同频道上,历史过程并非通过自觉的人类意图就能得到解释,它只有超出了人的精神及其秩序才能得到解释,而精神秩序具有神与人互动相参的层面,历史戏剧中的个人其实并不了解自己在历史中承担的角色;人如果不超越人自身而上升到更大更高的秩序维度界定自己,它就无法成为完全的历史主体。
柯维纲指出,“理性的狡计”意味着,仅仅在主观精神范围内,“激情的辩证法找不到出路”,因为“冲动及激情的冲突反映了内在于主体的两方面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主体自在所是的东西(理性的、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是他实际所是的东西(被一种矛盾的自然性封闭的意志)。解决之道在于“将这种主观性纳入到客观精神的规范性的、制度性的框架内”,作为主体的人对自身所具有的理念过渡到他们所是的理念,并且“作为一个按法构建起来的伦理—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存在”。这意味着:“非强制地将主体融入一种客观秩序中,此秩序的组织及规范无疑对个体的任性施加压力,但它们也为一种在主观上可被体验的自由提供多体系性条件。”由此就有了对客观精神的定义——“在必然性范围内表达出来的自由”[23](P478)。历史主体在世界历史中除了追求自己特殊的目的而言,还必须向神提升自己,“成为理性的目的的一部分,也即是让自己成为目的本身”,而“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目的本身,是因为那内在于他身上的神圣法则,也即我们一直所说的理性”[3](P90)。这就是由人而神,向着那在客观精神中显现自己的神(以国家为中心的伦理共同体)融入自己;唯其如此,人类才能摆脱沦落为理性的纯粹工具的命运,而在世界历史的牺牲和苦难生存中获取意义。面对世界精神为了实现其概念而要以特殊的情欲主体作为手段,“如果我们不把个体仅仅从围绕着他们的行动与特殊目的视角看作为了自己的特殊性,如果不着眼于个体的狭隘的目标,而是以更为具体的观点来考察他们的宗教和伦理生活,这些确切的内容是从理性自身分化出来的,因而具有绝对的成为目的本身的权利。以此方式,一个纯然为手段对应于目的的关系终结了”[3](P92-93)。对“理性的狡计”的探讨①柯维纲指出:对“理性的狡计”的通常解释是,历史名人、伟大人物的激情为一种非人格性的理性服务,为其服务,却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不知道,所以能更好地为其服务。似乎隐藏在理性狡计中的是潜在专制特点,确保概念能够战胜偶然的特殊性。但黑格尔的辩证—思辨理性是为了克服主动性/被动性、主观性/客观性、肯定性/否定性的二分法。“理性的狡计”也不同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那种以自爱(self love),即以一种非有意的方式促进共同福利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因为,黑格尔关切的是客观理性的建构学说,后者借助利己主义的利益与激情的辩证法。和解的力量被引向客观理性、客观精神。简言之,主体间的相互承认,是不能在市场原则下得到处理的,这种相互承认构成黑格尔对精神在其客观化过程的一种界定[23](P482-486)。表明,尽管世界历史无法从特殊性的主观意图加以理解,尽管理性通过情欲而实现自己,将情欲作为工具,但只有从人向着神(精神)的融入与提升,世界历史中的个人才能摆脱仅仅作为手段的命运②拜塞尔指出:“因袭卢梭和马基雅维利的看法,黑格尔批判了基督教把至善放置到超越了世俗领域的天堂的永恒救赎之中。他论证说,古希腊人与罗马人并不需要个人的拯救,因为他们在献身于国家之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16](P267)。问题的另一方面却是,上帝对世界历史的统治是无为的,它本身并不直接行动,而是通过特殊的人的行动而行动,它将自身的无为退藏在人追求特殊利益的有为中,以这样无所作为的方式实现了自己,这是神到人的下降。人的上升与神的下降的统一,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经纬,这一切都指向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内蕴着的连接人与神的潜力。
三、上帝与世界的和解
黑格尔通过精神试图实现的另一和解发生在上帝与世界之间。自从基督教引入古代世界以来,它造成了世俗世界与其神性根基之间的断裂,这个断裂在近代以来形成了普遍分裂的时代状况,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以及与之伴随的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躯体、信仰与知性、理性与感性、智力与本性、绝对主体性与绝对客体性等等的系列对立[10](P11)。早期的黑格尔就在基督教里找到了分裂的根源,其核心就是以耶稣为典范的基督徒生活:“①同世界分离开,并且从世界逃避到天上;②在理想中恢复那遁入空虚的生活;③“亚伯拉罕简直把整个世界看成他的对立物,如果他不把世界看成无物,至少把它看成受一个异己之神支持的……亚伯拉罕,作为整个世界的反对者,除了与他处于对立中的对方外,他找不到更高的存在,因此他也同样受神的支持。也就只有通过神他才与世界有中介的关系,这是他与世界唯一可能的联系。”[8](P356)在每个反抗的人那里,教导对神的回忆和仰望。”[8](P454-455)
基督教朝向天国(Königreich)——在神里面的共同生活,即以灵魂之爱与友谊构筑的精神共同体——的旅程,乃是“出埃及记”(exodus)所象征的逃离世界。在共同体内部爱得越深,对外部“就越具有排外性,越对于其他生命形式抱漠不关心的态度”,“人们在教育和兴趣方面、在对世界的关系方面越是孤立,每个人的独特处越多、则他们的爱越是局限于自己本身。为了具有对于自己的幸福的意识,为了增进自己的幸福,像它乐于做那样,那末它必定要孤立自己,甚至为自己招来敌对”[8](P445-447)。基督宗教社团将外部世界视为异己的、陌生的,这种由于“把爱局限在自己本身、这种对于别的生活形式的逃避”,表达了对世界的坚定拒绝,这种拒绝无论是在亚伯拉罕那里,还是在摩西那里,都有深厚的根基,“只要他看见那个世界还没有改变,他就一直要避开那个世界,并同它断绝一切关系”③[8](P449,451)。由于天国的公民与地上秩序被对立起来,地上的国家又不能被取消,因而基督教只能将天国保持在心中,“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他必须逃避一切现存的关系,因为那些关系受到死法规的束缚”,“所以他只能够在空虚里找到自由。因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束缚住了。因此耶稣把他自己孤立于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和亲戚之外。他不要爱妻子、不要养小孩、不要成为一个家庭的父亲、一个国家的公民,以便同别的人一起享受共同的生活”[8](P453)。一言以蔽之,基督宗教的天国生活是以拒斥内在世界的伦理共同体作为始点的,只有真正脱离、舍弃甚至牺牲这个世界,才有进入天国的可能性。而对世界的拒绝的核心就是拒绝人间社会的伦理生活,黑格尔引用了《马太福音》中如下言述:“谁要是爱他的父亲或母亲、儿子或女儿多于爱我,他就不配作我的门徒”(10:37)“我来到地上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宝剑。我是来把儿子分裂出来反对父亲,把女儿分裂出来反对母亲,把新媳妇分裂出来反对她丈夫的亲人”(10:34-35)①其实在《马太福音》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类似的言述:“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10:21)“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10:36)。[8](P453-454),以彰显基督教“脱离生活”,或者说,“过着一种与世界分离的生活”:“一个与现实相对立并与现实相隔离的社团,只有在信仰中才能联合起来。所以这种[与世界的]对立乃是固定了的,并且是这个盟社的原则的一个主要部分。”[8](P455)
基督的福音被黑格尔理解为一种爱的伦理,但它被视为更适合一个教派,而不是共同体整体,这种超越人间社会所有关系和脉络的普遍之爱其实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因而不可能向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共同信仰的人开放。放弃了伦理生活和国家秩序,将拯救转移到内心的天堂,这是一种逃离世界的形上学,以此为基础的精神生活,只能囚居在灵魂世界,而无法将自身客观化,无法引导人们与他人一道生活。上帝因而也是在世界之外、之上,而不是内在于世界之中的奥秘体。古希腊世界所构想的cosmos(有序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巨人(macroanthropos),即人的放大②在《蒂迈欧篇》30d,33b中,柏拉图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单一可视的活物”,“一个包含所有活物在自身之内的活物”,据此自然的一切都是人的类似物,即一个巨大的人(macroanthropos)。,正如希腊的城邦世界被构想为大写的人③柏拉图的《理想国》368c-d中,可以看到一种构思,“城邦是一个大写的人”。沃格林写道:“这个原理必定已永久性地被植入认为社会所代表的正是宇宙真理这一观念中,在今天来得与柏拉图的时代一样彻底。一个存在中的政治社会必须是一个有序的小宇宙,但不能以人为代价;它不仅应该是一个微型的宇宙(microcosmos),还应该是一个巨型的人(macroanthropos)。柏拉图的这个原理,将简称为人学原理(anthropological principle)。这个原理的两个方面必须加以区别。一方面,它是用来解释社会的一个普遍原理;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24](P66),在那里,很难发现一个位居彼岸的超越性上帝,然而基督教给西方文明带来了内在世界与超越性上帝的对立或分裂。
黑格尔将自己的工作视为近代以来这一基本分裂的和解。黑格尔将基督教语境中具有逃离世界与伦常生活的爱的经验视为精神生活的初级形式,它只不过是精神的“直接的实体性”的表现,它必须被整合到在内在世界中相互承认的精神秩序中,经历差异、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新统一,才能上升到精神生活的理性形式。黑格尔把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视为精神辩证法的环节,耶稣受难即上帝之死,其实是“上帝之子”的死亡,它是对那个逃离世界的神性之否定,是要在超验性的放弃中获得重生的可能性,伴随着重生的是上帝与世界的新型关系,即在通过受难而经历了分裂之后的重新和解,上帝成了世界中的上帝,成了我们之中的精神。通过十字架上的死亡,神性才从他与个别的人的外在和有限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上帝之子的死亡,伴随着基督化身为有限之人而在他身上设定的种种对立和分裂的扬弃,死去的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复活的则是哲学家的上帝,它是作为最高理念、最高现实的神,作为先行放弃自身进入世界、并在内在世界中重回自身的精神[25](P295-296)。“上帝通过死使世界和解,并使世界永恒地与自身和解。”[7](P218)黑格尔的上帝也就不再仅仅以爱,而是以理性界定的精神为核心规定,世界的和解只有通过精神的辩证法达成,而与传统基督教中上帝的奥秘所关联的奇迹在这个辩证法中不再重要。道成肉身的教义被理解为上帝放弃了超验性而下降成为人,并进一步通过受难死亡而放弃其人的存在形式的运动过程④黑格尔以为:“宗教的另一种方式是无限东西与有限东西的统一,上帝与世界的统一……这在基督教中是很纯粹的,在那里,神的本性与人的本性的统一是以基督表现出来的,这种统一让上帝以他的圣子表现出来,使人们这样达到对这种统一的意识。然而这种人神同形同性的本质不是以有失体面的方式得到描述的,而是这样得到描述的,即它导向真正的上帝理念。属于真正的上帝理念的是不存在一个彼岸,意识在它之外,在它之上,与它对立。”[2](P83)。
对这样的上帝来说,世界及其历史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世界史中有对这样的和解性认识的一种更大要求”[5](P135-136)。不可能存在没有世界的上帝:“真理和理念,完全只作为运动而存在,因此,上帝就是自身中的这种运动,而且,只是因此,才独自是活生生的上帝。但是,有限性的这种持久存在不必保留下来,而应加以扬弃:上帝是向着有限者的运动,而且因此作为有限者趋向自身的扬弃;在自我(作为有限的自身扬弃者)中,上帝复归于自身,而且只有上帝才作为这种复归而存在。没有世界,上帝就不是上帝。”[11](P141)上帝并非出于对世界的爱、对我们的爱而成为精神,而需要世界,真理恰恰在于上帝的本质就在于成为精神,认识自己,他只能在人间、在世界上才能充分达成其本质。“精神的一切行动只是对于它自身的一种把握,而最真实的科学的目的只是:精神在一切天上和地上的事物中认识它自身。”[26](P2)由于人类存在本身就是有限精神,故而人的社会存在及其世界历史在上帝把握自己的过程中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上帝只有就其知自己本身而言才是上帝;进而上帝的自知就是上帝在人里面的自我意识和人对·于·上帝的知,而人对于上帝的知则进展到人在·上帝中·的自知。”[26](P379)
对处于基督教文明背景中的黑格尔而言,“上帝只有被认为是‘三位一体’以后,才被认为是‘精神’”[4](P328)。“三位一体”并不是上帝在不同视角里呈现的三个维度,而是被理解为精神在其辩证运动中的不同阶段。靠着这个精神的辩证法,可以将死亡与重生设置为精神在自我分裂之后的重新自我统一。由此,基督教的对世界及其历史、对世界秩序之核心的伦常与法规的逃离,就转变为精神在某一个阶段的自我终结、自我死亡,这就是黑格尔在“上帝之死”——其实质是“圣子之死”——中看到的东西,只有圣子的死亡,作为精神的上帝才能在新的阶段——圣灵阶段——再生。于是,犹太—基督宗教对世界的逃离转变为对世界在新的维度上的敞开的必经阶段。“基督死了;只有死了,他才高升到天堂,安坐在上帝的右边;只有这样,他才是‘精神’。”[4](P334)而精神本身也被提升为在世界中实存化自己并通过民族精神的兴衰更替来表现自身历程,并在此中认识自己的世界精神,后者的历程正是从精神汩没于自然之中开始,经过与自然分离而达到特殊性的自由意识,最终到达经由纯粹普遍化而抵达的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①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进程总结为四个依次更替的原则:一是世界精神以实体性精神的形态为原则,单一性沉没在本质中,没有自为存在的权利;二是实体性精神的自为存在,即优美的伦理的个体性;三是认知着的自为存在在自身中的深入,以达到抽象的普遍性;四是精神的上述对立面转化,并在精神的客观性中达到和解[13](P477-478)。[4](P59)。正因如此,“三位一体”被黑格尔提升到世界历史的高度:“这个新原则是一个枢纽,‘世界历史’便在这枢纽上旋转。‘历史’向这里来,又从这里出发。”[4](P328)通过“三位一体”,黑格尔找到了世界历史中化解无常体验与超越意识对峙的核心,他将世界历史视为精神的辩证进展,这个内在世界则被视为精神的自我训练(Zucht),只有通过世俗历史的训练,精神才能死后复活。这样,在《但以理书》视角里被视为毫无意义的帝国更替、文明兴衰、个人沉浮,便不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被理解为精神的受难,精神通过这种受难牺牲自我复活,以跃入更高阶段。黑格尔借助基督教又摆脱了基督教持有的整个世俗历史毫无内在意义的观点,他将整个世俗历史看作精神的“受难地”(Golgayha),它构成精神自我成长的环节。譬如,作为历史事件的十字军东征虽然充满征服与杀戮的残酷,但通过它,精神向人们启示的是其真理并不在圣地、圣寝等废墟之中,也不在圣餐、圣礼与圣歌之中,而是在主体性原则(principle of subjectivity)之中,“在心灵的深处,在内心的绝对理想性中寻找”精神自身,“使外部东西屈从自己的主体性”[2](P429,427)——以十字军东征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而后才有路德“因信称义”的新教真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成为黑格尔处理世界历史的不同纪元及其连续性的架构,这一架构同时也把世界历史作为一种“神正论”,即对神的正当性之证明,这种神正论要求上帝与世界的深度和解。
上帝与世界的和解,意味着上帝在世界精神中显现自己。精神虽然最终是思想性的精神,但它并不将自己停留在思想中,而是将自己客观化在实存的世界中,以有限的客观精神面貌出现。“‘世界精神’是精神通过人类意识在世界中彰显出来的……世界精神亦是从上帝之精神而来,后者也就是绝对精神。”[3](P52)世界精神如果要显现自己,又必然落实到特殊性里,这就是在国家及其伦理生活所展现的民族精神中显示自己。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其实是指那些已经自行理性地组织起来并建立了国家的民族,这样的民族能够形成一种普遍的意识,此意识涵摄了整个民族的全部目的及其利益,由此其成员追随其指令,而该民族的法律、习俗、宗教、体制等皆由此普遍意识而来,形成整体,并对渗透在这个整体中的民族精神形成意识[3](P51-53,95-96)。世界精神要通过民族精神的兴衰更替来展开,而民族精神就体现为特定的国家及其承载的文明,一个文明体的核心就是宗教与国家,在精神层面而言,宗教与国家并非对峙之物,而是有所差异:“‘宗教’之所以为宗教,乃是心灵和心的‘理性’——它是上帝的‘真理’和‘自由’从而出现在概念界的一座堂庙;至于‘国家’却同为‘理想’所控制,但它是人类的‘自由’同现实的知觉和意志相关的一座庙堂,这种现实的内容,甚至于可以说是神圣的。”[4](P345)如果说精神在宗教中采用了情感与表象的样式,那么世界历史中的国家则是精神在内外全部现实中的现实性[13](P473)。
上帝与世界的和解最终将人带入国家之中。“国家自在自为地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国家是立于世上的精神……在世上行进的神,就是国家。”[13](P387-388)精神通过国家而使自己充分客观化,人向着神的上达,并不是超越此世,而是融入国家。“只有在国家里人们才有着理性的存在。所有教育的目的都在于确保个体不会停留在主观阶段,而是要在国家里成为一个客观的存在。个体固然可以通过国家去达成其私人目的,但只有当每一个体都克尽本分,能够摆脱那些非本质性的枝节,才是真理。人们要把其所有成就归功于国家,只有在国家里他才可以成就自己本质性的存在。所有个人的价值、所有精神的实在性,都是由国家所赐予。”[3](P94)但黑格尔的国家并不是一台权力部件构成的复杂机器,而是现实的伦理生活与理念之内在法则的统一体,是普遍的、本质的意志与主观的意志的统一体,作为这一统一体成员的个人,获得了伦理性的生命[3](P94)。国家的本质是精神在其他各个具体方面之枢纽——法权、艺术、伦理、生活情趣等[3](P93),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可以视为文明有机体,它不能理解为机械钟所体现的机械模型,象征有机体的花园模型虽然更为接近,仍不足以充分表达它,国家将文明的精神弥漫在其人文宇宙的每一个角落①黑格尔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无他,不过是精神的概念实现其自己的过程,也就是精神将其自己灌注到那些分化出来的不同领域:国家、宗教、艺术、法权、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所有这些都是精神的概念在它自己那里的自我实现”,在国家里,“一个民族的宗教、法律、伦理生活、知识状况、艺术、司法,它的其他特殊技能倾向、满足物质需求的工业、它全体的命运以至于战时与平时跟邻邦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密切地联结在一起”[3](P101-102)。,从而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围绕着共同善的统一整体,每个人的特殊性权利在其中得以保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促进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整体的利益。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可以视为围绕着共同善而旋转的希腊城邦伦理共同体与现代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的综合,其综合的成就便是其伦理生活(Sittlichkeit),在其中国家的客观意志与个人的主观意志得以相互协调,以至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相互嵌入、交相构成的关系样式超出了手段—目的的层次②黑格尔说:“国家并非为了公民而存在的,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国家是目的,而公民则为其工具,但在这里,目的与工具的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合适的,因为‘国家’并非站在公民的对立面而成为一个抽象事物;相反,他们就像有机生命那样,只是分属不同的环节,在国家那里,无所谓谁是目的,也无所谓谁是手段,‘国家’的神圣法则就是‘理念’,就是理念要在人间社会去彰显其特性。”[3](P94-95)。个人的独立只有在与国家对立而又被置于其下——唯有在这种个人与国家对立统一的吊诡情况下,理性生活才到达高度发展的阶段,这样的国家才是神圣的,它是人与精神的统一体[3](P97,101)。通过国家的伦理生活,个人提升了自己:“个体都是归属于这个精神性的全体,每一个人都是其民族之子,并且,只要其国家仍按照概念的规定而发展,他就同时是时代之子……精神性的存在就是其存在,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由之而生于斯,亦由此而居于斯,每个成员身上都构成了客观性的内容,其余的一切都是其形式。”[3](P103)这就是追求着特殊利益的现代个体重新在文明论的国家中安身立命,与客观精神达成和解,而个体与客观精神的和解可以视为上帝与世界和解的内容之展开形式。在客观精神阶段所能达到的和解意味着,“精神王国从它的天国实存下降为尘世的此岸和平庸的尘世,下降在现实和表象中,——尘世王国则相反把它抽象的自为存在往上塑造为思想,塑造为那种有理性的存在原则与知识原则,成为礼法与法律的有理性。”[13](P481)精神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意味着主观精神“对制度性条件的承认,制度性条件为主观性的自由要求赋予坚实存在及现实性,缺乏这些条件,主观性的自由要求将停留为空虚的要求”[23](P479)。无论是宗教自身的历史转进,即从自然宗教向精神个体性宗教再到绝对宗教的进展,还是法的必然抽象化原则的现实化历程,等等,都构筑了精神在文明中自我展开的历史进程。当然,在有限精神(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层面,精神“无法最终克服诸多主观的与客观的(社会性的)激情在自身领域中所引发的张力”,和解的可能性在绝对精神学说,必须转向思辨,“即概念的肯定性的发展活力”[23](P486)。
四、历史作为精神的辩证运动
综上所述,上帝统治下的世界历史被理解为精神通过产生自己及其对立物、并在对立的扬弃中再度自我统一的辩证运动。黑格尔一方面将上帝引入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则以思辨理性改造了基督宗教的超验上帝,并以独特的方式促成了内在化世界历史与超验性上帝之间的和解,排除了在世界及其历史之外的彼岸化上帝,从而建构了一个内在于世界但其意义又不能为世界内事物所穷尽的作为绝对者的上帝。上帝作为唯一的绝对理念,乃是世界历史的(内在)目的因。从启蒙之前“已经有过一个所有知识都是关于上帝的科学的时代”到启蒙之后“知道所有的东西和每一个东西,知道无限多的对象,只是对上帝毫无所知”的智识状况的变迁,尤其是康德哲学传统宣判的“对上帝的认识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被看作是最高的洞见”[11](P24-25)的时代氛围里,黑格尔依然接续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天意”主题,并将自己的历史哲学自我界定为“神正论”[4](P16)。尽管黑格尔对传统基督教进行了一系列改造,譬如以世界历史进程代替救赎,以历史审判代替最后的审判,以理性机巧代替神意。这些代替的一般意义在于将一种特许的价值赋予作为精神承载者的人[23](P103),但卡尔·洛维特还是正确地强调黑格尔历史构思的神学前提:“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在本质上是基督之前和基督之后的。只有在作为真宗教的基督宗教的前提条件下,黑格尔才能够系统地建构从中国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他是最后一位历史哲学家,因为他在根本上是最后一位其宏伟的历史感还被基督教传统规定和限制的哲学家。在我们现代的‘世界历史’中,基督教的纪元成了一个空洞的图式。它虽然还被接受为通行的标准,并被运用于形形色色性质各异的文化和宗教,但是,这种实质上的多样性却缺乏一个像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那样合理地安排各种文化和宗教作为出发点的统一中心。”[1](P84)
黑格尔历史哲学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中的普遍历史规划,将本来是过去的历史的焦点置放在未来,因而重点不再是以古鉴今,即从历史的过去来理解当下和未来,而是从未来(既在历史过程之内又在历史过程之外)理解过去。如此一来,“历史本质上成了未来对当代人的催促”[27](P100)。历史未来化的实质,是以未来照亮过去,即以未来的名义“赋予过去意义的视角和终点目标”[27](P100)。这一历史意识依然是以基督教末世论为基础的,其“前提条件是,这种真理是建立在基督教西方的宗教基础之上的。从以赛亚(Ⅰsaiah)到马克思(Marx)、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从约阿希姆(Joachim)到谢林(Schelling),基督教西方的历史意识是由末世论的主题规定的。对作为‘边界’(finis)和‘目的’(telos)的一个最终终结的这一展望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具有不断进步的秩序和意义、能够克服古代对‘宿命’(fatum)和‘命运’(fortuna)的畏惧的图式。‘末世’(eschaton)赋予历史进程的不只是一个终点,它还通过一个确定的目标划分和完成了历史进程。末世论的思想能够克制时间的时间性(Zeitlichkeit der Zeit);如果不通过一个终极目标富有意义地限制这种时间性,那么,它就会吞噬掉自己的创造物。与给我们指出空间中的方位,并使我们能够征服空间的指南针相似,末世论的指南针指向作为终极目标和终点的上帝之城,为我们在时间中指出了方位”[1](P46-47)。洛维特正确地揭示了西方的普遍历史观念与犹太—基督宗教的末世论的深刻关联。而普遍历史筹划所立身的普遍性正是由这种末世论思维赋予的:“只有在对历史程序的这种末世论的限制范围之内,历史才成为‘普遍的’。它的普遍性不仅以信仰一个全能的主宰为基础,而且以这个主宰一开始就通过把人类历史引向一个终极目标而赋予它一种统一为基础。”[1](P47)
对黑格尔来说,尽管上帝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世界的上帝,但世界历史领域依然被视为“外在的普遍性领域,在此领域中,法的抽象概念最终现实化了,也就是说它最终被伦理—政治性地客观化;正是借助历史,并且正是在历史之中,理性的现实性才逐渐地并且以一种困难重重、但仍然还不是最终的方式显示出来”[23](P122)。换言之,在历史进程中并通过历史呈现的世界精神并不是精神的最后完成,精神的完成虽然发生在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但它最终将超越时间和历史,并以某种非历史性的成就作为时间和历史过程的完成。“世界精神(Weltgeist)仅仅是一个‘外在普遍的精神’;换言之,它只是绝对精神在时间中的外在化的表现(此时间是概念的定在,但仅仅是它的定在)。在历史的时间之外,存在着概念的时间,它是将时间扬弃(Aufhebung)在如下在场中的时间,即作为绝对知识的思想对自身的绝对在场。”[23](P122)世界历史唯有在对时间的扬弃中才能抵达最终的完成——这就是内蕴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哲学中导致历史终结症候的根本——如果没有对时间与历史性的瓦解,历史本身就仍然还在时间的支配下,无常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兴衰荣枯的节奏就将继续主导历史,因而,生成中的历史世界必须通过一种历史完成性意识的引入,并使之弥漫在每一个当下,而得以获取通往精神的绝对永恒之企望,同时又以此充实历史性生存的每一个当下。一种以扬弃时间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在犹太教—基督教的弥赛亚信仰与末世论中有其深刻的本根,但这恰恰是其历史意识的非历史性的吊诡之处——历史意识完成于历史的取消。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尤瑟夫·耶鲁沙尔米(Yosef Yerushalmi)在其《铭记》(Zakhor)书中提出的问题就是尖锐的:“犹太教历经许多世代,始终都浸润着强烈的历史感,但为何历史著述在犹太人之中顶多只占辅助地位,而更常见的情况是根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在犹太人经历的各种考验中,关于过往的记忆始终至关重要,但历史学家为何不是这一记忆的首要承载者?”[27](P xvi)这一问题同样适合基督教。
黑格尔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历史的完成只是阶段性的,而且每一次完成意味着精神运动的一个周期,这个周期的终点只是下一个周期的始点。从一个周期到另一个周期的更替,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开始[28](P502-503)。精神的这种纪元性的自我运动,是精神在实存中外化自己而后又在其既有实存的破碎中回到自己,如此循环的上升运动。“那个通过这种方式而在实存中塑造起来的精神王国构成了一个前后相继的序列,其中的每一个精神都把前一个精神取代,每一个精神都从前一个精神那里接管世界的王国。这个序列的目标是使深邃内核启示出来,而深邃内核就是绝对概念本身。”[28](P503)在此,历史被理解为精神与其在时间中的外化之间的张力性的和解。“一方面,把那些精神当作一种自由的、显现在偶然性形式下的实存保存下来,就是历史;另一方面,把那些精神当作一种已经得到概念式把握的组织机构保存下来,则是以显现出来的知识为对象的科学。两者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已经得到概念式把握的历史,构成了绝对精神的回忆和骷髅地(Golgatha),构成了绝对精神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和确定性。假若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将会是一种无生命的孤寂东西,唯有——看到他的无限性翻起泡沫 溢出这精神王国的圣餐杯。”[28](P503)历史被视为绝对精神的受难所,这意味着精神从一个形态、一个王国到另一个形态、另一个王国,或者从一个纪元到另一个纪元的展开,被象征化为受难之后的复活。
这样,世界历史就展现为双重向度,即人的机制的维度与神的机制的维度,精神则贯通二者:“正义和德行、不法、暴力和罪恶、才能及其成就、大大小小的激情、罪责与无辜、个体生活和民族生活的辉煌、国家和单个人的独立、幸与不幸,所有这些都在所意识到的现实性领域中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并在其中找到它们的判断和正义,虽然只是不完善的正义。世界历史则发生在这些观点之外;在它之中包含着世界精神之理念的那个必然环节,即当下就是它的阶段,具有它的绝对权利,有活力的民族生活在这个环节中,则能顺利实施其行动,获得幸运和荣誉。”[13](P474-475)经历兴衰荣枯之更替的是精神在其历史中的外在化实存,这些实存不可避免地在经过它与精神的短暂婚姻后,注定坍塌,只能成为精神的记忆,成为滋养精神走向更高的下一个纪元的营养,内蕴在薪尽之中的却是不熄的火传,它通过健动不已的实存化运动将自己化身在世界历史与人文宇宙之中,而后又否定这实存宇宙,回到纯粹内在性的自己,重新再将自身实存化①“精神已经向我们表明,它不仅仅是自我意识之退回到自身内的过程,也不仅仅是指自我意识沉浸在实体之中,各种差别荡然无存,毋宁说,精神是自主体的这样一个运动:自主体一方面脱离自身发生外化,沉浸在它的实体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主体摆脱实体,并返回到自身之内,把实体当作对象和内容,因为它扬弃了客观性与内容之间的差别。”[28](P500)。这样自主运动的精神就是神的内涵,这是黑格尔在启蒙之后的新时代建立以精神为中心的新宗教:“‘精神’是一个最崇高的概念,它属于近代和近代宗教。”②博德指出:“《精神现象学》的宗教是近代宗教”,“正是这种对宗教(引者按:指的是旧宗教)的排斥是近代的宗教”[29](P306,305)。戴晖教授指出,近代宗教是精神对自身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近代特征在于意识,换句话说《精神现象学》里的宗教是精神的自我意识[30](P28-39)。[28](P16)。仅仅从人的机制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作为神正论(theodicy),似乎证成的只是上帝的行动合理性。奥斯维辛之后的本雅明,从关切有限者的生存着眼,其《历史哲学论纲》对黑格尔的评价完全被翻转了:将历史设置为上帝手中的牵线木偶,而人不过是其工具;对人类而言,黑格尔的历史荒原实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渺小与荒凉的悲剧性感觉。但对黑格尔而言,只要我们还局限在人的机制内,历史就不可能具有绝对目的或终极目的:“把历史事件当作外在偶然故事来看待,特别是那些在历史进程中的衰退没落者,它们只能够以不确定标准来评价事物之优劣,于是最后只能讲出世界历史发展之相对目的,而达不到其绝对目的。”[3](P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