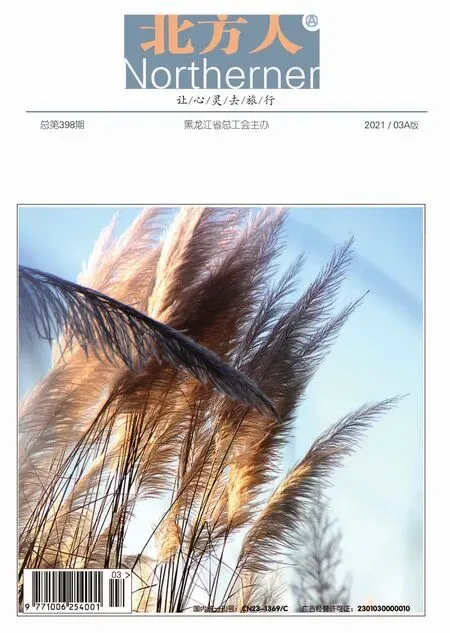智者倪匡
文/沈西城
认识倪匡近半个世纪,当年我们年轻、天真,彼此性情相近、言谈无隔。我们都是上海人,用上海话沟通,倍觉亲切。倪匡二十二岁来港,舌头发硬,学不好广东话。他不承认,说:“跟舌头硬没关系,我天生有言语障碍症。”这是真话,倪匡这个人除了弄笔杆儿,其他物事啥都不懂。洋泾浜英文 ,只 会“So what”和“Who cares”,就此走遍美国。他不独学话蠢,方向也辨不来,走进菜馆再出大门,便分不清东西南北。可以说他做什么都笨,只有写作灵光——南来六十余年,一根原子笔管吃饭,赚了不少钱。
倪匡一生交友无数,知己仅一人,古龙是也。古龙嘛,人人竖起大拇指,直夸“绝顶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掉进创造的角色里,把自己看成陆小凤、楚留香,千金散尽还复来,怕啥?倪匡自小明白“千金散尽有日不复来”,于是赚得的一半,呈奉贤妻,自己花其半,于是晚年无虑。自诩老白脸吃软饭。软饭吃得名正言顺,怕人不知,还通过传媒告示天下。

20世纪80年代前,倪匡坚持原则:“小叶,阿拉文人,要保持神秘感,勿可以露面。”作家一露面,少了头巾气,人家瞧不起。身为小阿弟,只好有样学样,连照片也藏起,不敢曝光。90年代初,倪匡来个大变身,居然做电视节目了,搭档是鬼才黄霑、食神蔡澜,三人行,顶呱呱。节目叫《今夜不设防》,访超级明星,嘴巴子活。蔡澜能文不善言,倪匡善言,粤语却人人听不懂,只好打字幕,说话的仅黄霑一人。要命的是,这个综合性节目居然红火爆灯。
后来做电视不过瘾矣,倪匡视而优则影,跃登大银幕,在《群莺乱舞》里,粉墨演嫖客。朋友劝之谨慎为要,别坏声名。他三声大笑:“谢谢!顶对我胃口,我就是做自家呀,驾轻就熟!”众友笑至喷饭。
90年代,倪匡居然移民旧金山,买了幢圆形玻璃怪房子,房间一个,夫妇相依。倪太住不惯,回港小休,独留倪匡孤居。打电话与他聊天,他居然说忙至不可开交。一个老头子忙啥?“小叶,你又搞不懂,我忙得要死。早上起来写小说、看报纸。下半日剪花除草、洗衣裳。黄昏要到附近超市储备食物,回来煲鸡汤,哪有时间?”什么,大作家竟当上家庭主妇?倪爷当是一种乐趣。倪匡有项天大的本事,非人人所能为,就是化枯燥为乐趣。人视为畏途,落到他手,变成好玩。套用他的口头禅,就是“邪气好白相”。
倪匡性格怪:一是痴,一是绝。先说痴,恋上某事物,痴缠到底。70年代初,我到他铜锣湾海宁街的寓所做客,那时他正在收集贝壳,捧出给我看,我根本不懂,只好装着看。他随手拿起一块,道:“小叶,你猜多少钱?”我为难,不敢言少:“五千!”“再说一遍!”“一万!”“不,不对,五万!”倪匡纠正。吓坏我!未几生厌,贝壳全送人,一片不留。改玩音响,十万、二十万一套山水牌器材,硬要我听。我听了,一个感觉:跟我家的卡式录带并无二致,而其价钱仅港币三百元。后他又转去养鱼,什么金鲤、黑魔鲤、七彩神仙鱼……总计九缸,自号“九缸居士”。鱼缸,放诸餐桌,日观夜赏。不旋踵,厌了,毫不犹豫送友人。最后爱上旅游,一月出门数次,东闯西逛,不亦乐乎,之后返璞归真,闭户静思。
倪匡做人也有个大优点:说一不二,答应别人的事,就算赴汤蹈火,也决不推辞。他说写作配额用完,就是用完,你即使开出千字一万,他也不会心动,仍一字不会写。镇海倪匡,诚硬汉子也。
讲真的,我从不以为倪匡是什么作家,他听到了,气得瞪小眼睛:“我写了这么多的书,还不是作家?”他板着脸,吓唬我。我腰板直,胸膛挺,轻描淡写:“侬是智者,远比什么作家高明!”听得这样说,他怒气全消,脸上现出笑容,如初夏朝阳。号称智者,何以见得?援引倪匡的语录以见其概:“小说只有两种:一是好小说,二是坏小说,好小说能看下去,坏小说不能看。”“写作没得教,全然靠天分。没有的话,去干别的事。”“要写就写,千万别拖!”“医生要我听话,我问听话是不是不会死?医生说不会呀!我说那我干吗要听你话!哈哈哈!”凡此种种,皆智慧之言。
最近倪匡说很多配额都用光了:喝酒配额完蛋了,生命配额也差不多耗尽!千万别为智者倪匡悲伤,他视死如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