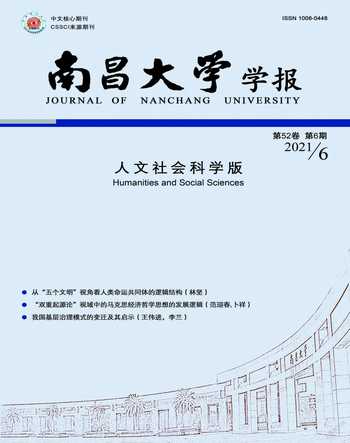乡村责任共同体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优势
杜姣 刘尧飞
摘 要:乡村关系是国家治理进入乡村社会的通道。新时代背景下,对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而言,广泛出现于税费时期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关系模式和存在于部分发达地区的乡村行政共同体关系模式不具有存续的空间。赣西G镇通过村治主体的中农化、片组制度的设置以及积极与村干部进行情感互动实现了乡镇两级基于治理责任的连带和捆绑,将村干部吸纳至乡镇的工作任务框架中,建构乡村责任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这一乡村关系模式不仅强化了乡镇治权,而且维系了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模式,保存了村民自治空间,较好地解决了下达至乡镇的国家工作任务向村庄社会的落地问题,化解了乡镇对村干部的动员难题,实现了乡政与村治的有效衔接。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模式可成为中西部地区乡村关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乡村关系;乡村责任共同体;中农治村;片组制度;情感互动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21)06-0083-09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确立了我国农村“乡政村治”的基本治理架构,乡村两级分属不同的治理体系,即乡镇政权作为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组织,隶属于国家行政治理体系,而村级组织则隶属于自治体系[1](P26),这客观造成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内在张力,并为乡村两级之间互动形态的多元化赋予了空间,乡村关系也构成理解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围绕乡村关系,学界大体形成了两种研究视角:
一是规范视角。即以制度规定的乡村关系模式为标准,对照分析实践中乡村关系出现的各种偏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是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诸多学者发现,实践中的乡村关系表现为行政化乡村关系[2](P1),乡镇政府将村委会视为自己的下属层级或是派出机构[3](P56);二是治理视角。该视角着重关注特定的乡村关系形态所造成的治理影响,其抛开制度文本对乡村关系的限定,直接深入到农村实践中考察乡村关系的运作过程[4](P5)。有学者重点探讨特定乡村关系形态对村庄治理的影响,认为乡村关系从过去的二元结构向乡村一体化关系的转变是造成村级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5](P48)。部分学者立足乡镇落实国家工作任务的目标,重点探讨乡镇在乡村关系建构中的主导作用,认为近年来乡镇通过制度型支配这一乡村关系模式的构建强化其对村级组织的控制,以贯彻国家意志[6](P69)。吕德文认为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工作共同体兼顾了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效应对了治理负担急剧加大所带来的挑战[7](P78)。
在新时代背景下,伴随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改造,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下沉至乡镇,需要乡镇贯彻和落实。近年来,比较常见的工作任务包括精准扶贫、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殡葬改革以及土坯房改造等。此外,许多原来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的事务也被吸纳至国家的工作任务之中,并以行政指令的方式下达至乡镇。当前整个农村基层社会普遍进入国家化治理时期,国家目标和意志越来越凸显。作为国家最末端的基层政权,如何有效地贯彻落实国家目标和意志是乡镇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其中,乡村关系是影响国家目标和意志贯彻程度的关键一环,而核心又是处于不同治理体系下的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动员问题。鉴于此,本文将遵从治理视角,立足乡镇落实国家工作任务的目标,结合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于2021年4月在赣西G镇为期15天的调研经验,剖析当地以乡镇为主导的乡村关系建构模式,并总结该乡村关系模式的治理优势。
一、乡村关系的实践类型与乡村责任共同体转型
乡村关系是乡镇政府与村庄治理之间关系的简称。立足乡镇落实国家工作任務的目标,乡村关系又主要表现为隶属于国家行政治理体系的乡镇政府对隶属于村民自治体系的村干部的动员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关系是国家治理进入乡村社会的通道[8](P181)。根据历史和区域经验,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乡村关系类型:一种是通过利益动员而形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一种是通过行政动员而形成的乡村行政共同体。前者广泛出现在税费提取时期,后者则以当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部分乡村最为典型。然而,这两种乡村关系的实践类型都有其特定的条件限制。对处于新时代背景下的中西部地区乡村而言,需要实现乡村关系的转型。赣西G镇的乡村责任共同体的建构模式可成为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乡村关系的发展方向,其高度适应了基层治理国家化时期乡镇有效贯彻国家工作的任务需求。
(一)税费时期的乡村关系:乡村利益共同体
从时间维度来看,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从19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9](P1)。面对西方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挑战,中国所走的必然是一条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等各方面都带有突出的国家主导特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便承担了对农村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重任。国家被视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其中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为了获得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源,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资源汲取型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昭示着税费提取时代的到来,并最终随着2006年全国农业税费的全面取消走向终结。税费时期,乡镇政权作为国家在基层的最末端政权,其主要工作任务是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由于乡镇干部的人力限制以及乡镇干部客观存在的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难题,致使其必须依靠村干部来帮助完成税费收取任务。然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意味着村干部与乡镇政权分属于不同的治理体系,村干部是完全由村民选举产生的自治性公共治理主体,而非由国家任命或授权的行政性公共治理主体。乡镇政权与村干部之间出现了体制断裂,乡镇政权无法对村干部进行体制动员。作为自治主体的村干部具有不执行或消极执行乡镇工作任务的空间。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对农民税费提取的力度空前增加,为完成国家税费收取任务的乡镇工作目标与农民利益出现严重失衡。村干部往往倾向于不得罪村民,而对乡镇下达的税费任务持消极应付的态度。受压力型体制的驱动,乡镇政府通常会采取体制外利益方式来动员村干部[10](P46)。比较常见的做法是,乡镇政府会默许村干部对农业税进行加码以及增加村级征收提留来让渡一定的农业剩余索取权。这部分体制外利益构成乡村重要的灰色利益空间,此时的乡村关系亦呈现为一种利益共同体关系[11](P163)。乡镇通过利益诱导将处于自治体系中的村干部吸纳至乡镇的工作任务框架中。然而,这样一种利益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也造成了严重的治理后果,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好人”村干部不断退出村级治理领域,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强烈利益攫取取向的狠人村干部的上台[12](P409)。干群关系空前紧张,甚至有学者用世纪之交的“三农危机”[13](P1)来描述这一时期的农村情形。
(二)东部发达地区的乡村关系:乡村行政共同体
从区域维度来看,虽然我国农村普遍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乡政村治”是乡村社会的基本体制结构,但实践中的乡村治理体制却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化,尤其表现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分化[14](P110)。综合笔者近年在全国多地农村的调查经验发现,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乡村仍然保持了“乡政村治”的体制结构,而部分东部发达地区乡村则呈现为“乡政村政”的体制结构,村级组织已经完全行政化,成为乡镇行政治理体系在村庄社会中的延伸。“乡政村政”这一乡村体制结构形塑的基本目标亦主要是解决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工作动员问题。这一体制结构使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行政动员成为可能,其可通过采取行政手段防止村干部出现偏离乡镇意志的行为。因此,这些地区的乡村关系模式属于行政共同体模式。乡村行政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的构建主要通过对村干部职业性质的改造来达成,使村干部的切身利益都需要依托乡镇政府实现。具体改造举措如下:
一是提高村干部工作待遇,将村干部职业化。上海农村支部书记一年的工作收入高的能达到15-16萬元,低的也能达到9-10万元。其他村两委成员一年的工作收入多在7-8万元左右。珠三角地区村书记、村主任每月的基本工作收入在5 000元左右,副职村干部为4 500元左右,一般村两委成员为4 000元左右。除去每月的基本工作收入外,村干部每年还会有3-5万元的绩效奖励。将珠三角地区村干部一年的所有工作收入加总,基本都在10万元左右。苏南地区村干部的工作收入水平也普遍处于10-20万元之间。这三地的村干部收入水平远在村中一般普通农民之上,在村庄中处于中上水平。此外,他们还都有数额不低的退休工资保障。与村干部不低的工作收入相对应,当地政府对村干部提出了脱产要求,并严格执行坐班制。这一举措直接改变了村民自治体系下村干部的兼业性质,在当地人看来,村干部俨然成为一份体面的职业。
二是构建较为完备的村干部职位流动与晋升体系。在村民自治制度中,村干部是由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也是最能体现基层民主价值的环节,它确定了村干部权威来源的社会性。上海、珠三角、苏南等地的地方政府则通过设置制度化的村干部选任机制弱化民主选举,将民主选举形式化,从而强化村干部选任中的乡镇意志。与之相应,村干部也彻底转变为一种稳定且具有流动和晋升空间的职业体系。这一方面体现在村干部位置呈现为明显的职位进阶特征,比如上海农村村干部一般都是通过村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这一后备干部制度的方式进入村级治理体系,并遵循从助理到一般村两委成员,再到村主职干部的晋升路线;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村干部可实现向乡镇干部(主要是事业编干部)的流动,比如苏南地区根据村干部任职期间的工作情况以及工作年限等综合因素有选择地让优秀村干部转成事业编。只要是进入村干部岗位的村民,他们都有稳定的职业预期。职业预期的实现与乡镇政府的意志存在紧密的关联,村干部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政府设定的科层轨道中展开。
(三)乡村关系实践路径转型:乡村责任共同体
不论是税费时期的利益共同体,还是东部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行政共同体,最终要解决的都是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动员问题,使村干部成为国家下达至乡镇的各项工作任务在村庄社会中的有力担纲者。但这两种乡村关系模式对当前的中西部地区乡村而言则面临着客观的条件限制,而不具有适用性。
常见于税费时期的利益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乡村灰色利益空间的存在,乡镇通过对灰色利益空间的运作和支配实现对村干部的动员。灰色利益空间的存在主要源自制度体系的不健全和权力运作体系的不规范,这赋予了乡镇较大的自主操作空间,其中默许村干部对农业税进行加码以及增加村级征收提留便是典型的灰色利益的分配形式。近年来,随着农村基层制度的愈加完善、各种议事决策程序的健全和各种监督督察体系的建立,乡村灰色利益空间受到极大压缩,乡镇权力的运作也越来越规范和透明,这直接瓦解了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建构基础。
普遍存在于东部发达地区的行政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则改变了以“乡政村政”还是“乡政村治”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政村治”体制,确立了“乡政村政”体制。然而,“乡政村政”体制的建立需要有强大的公共财政做支撑,是高度资源依赖性的治理体制。不论是将村干部职业化后的工资成本,还是各种规范和约束村干部治理行为的制度运行成本,都需要由政府公共财政承担。我国绝大多数地处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普遍面临着地方政府公共财政资源比较匮乏的处境,不具备构建以“乡政村政”体制为基础的行政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的资源条件。同时,中央财政还很难承担各地方进行“乡政村政”体制改革成本的能力。
此外,从具体的实践效果来看,利益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和行政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都有其固有的缺陷。前者会致使村治主体出现从“好人”向“狠人”的更替,造成干群关系的急剧恶化以及乡村治理的灰黑化,影响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后者则突破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限定,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基本治理体制,进而存在一定的制度风险。综合上述多重因素,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工作任务下达至乡镇,为了有效地动员村干部,地方政府亟须实现乡村关系转型,突破利益共同体与行政共同体这两种乡村关系建构模式。赣西G镇则作出了有益探索,构建出一种新型的乡村关系模式,即乡村责任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不仅实现了下达至乡镇的工作任务在村庄社会的有力贯彻,而且还有效规避了乡村利益共同体模式和乡村行政共同体模式潜在的治理风险。
二、乡村责任共同体的实践逻辑
乡村责任共同体指乡镇政权与村干部之间形成了一个对农村基层治理责任具有一致认同的体系,强化村干部对农村基层治理责任的认同,实现对村干部的动员,将村干部整合进国家下达至乡镇的工作任务框架中。村干部对农村基层治理责任的认同以及将此种认同转化为行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依托以乡镇为主体所主动进行的各种机制的建构来达成的。从赣西G镇的经验来看,其主要通过三方面的举措实现乡村责任共同体的建构,分别是对村治主体的有效选择、片组制度的设置以及与村干部进行积极地情感性互动。G镇版图面积为96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10万亩,耕地面积为1.7万亩,水域面积为7 035亩。全镇辖10个行政村及2个居委会,4 449户,总人口15 816人。G镇政府机关有行政在编人员12人,事业编在编人员28人。这40人构成乡镇治理的主要体制性力量。
(一)中农治村:乡村责任共同体的村治主体基础
在责任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建构中,村治主体的有效选择是关键一步,这涉及隶属于自治体系中的村干部对国家工作任务与目标,包括对乡镇政权权威的认同问题。实地调研发现,在乡镇政府的把关与指导下,G镇形成了以中农为核心的村干部队伍结构。贺雪峰将“以适度农业规模经营为主体的,主要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且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又可以保持家庭生活完整的农户”称为“中农”[15](P3)。刘锐对“中农”概念进行了细分,将之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经营部分土地、兼做其他行业,但居住于村庄,主要社会关系和主要利益在村庄;二是经营中等规模的土地,主要社会关系在村庄[16](P24)。
在上述两重定义的基础上,本文将“中农”界定为因各种原因无法外出或不愿外出而依托乡村社会内部的经济机会空间获取收益的农民群体。在当前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的制度背景下,村书记、副书记或副主任和村会计被称为“村三大头”,并主要承担村级治理之责,其他村两委委员只是在必要时给予协助。G镇几乎每个村的“村三大头”都是因各种原因没有离开乡村的中农群体,在乡村中都有自己的产业。比较常见的产业类型有,经营20-30亩的土地、进行一定规模的生猪养殖、开农资店或是在本乡镇开办砖厂。这些产业内生于乡村社会,属于乡村经济机会空间的一部分。中农群体的不离乡特征为其担任村干部提供了可能,他们也构成G镇村干部的主要来源。由中农群体担任村主要干部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村干部可获得的制度性收益对中农群体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中农群体对村干部职位的重视能够保证其切实履行村级治理职责,这也为乡镇政府实现对村干部的责任吸纳提供了载体。之所以说当村干部获得的是制度性收益,主要指这部分收益是为正式制度认可的规范性收益,以区别于乡村利益共同体时期的灰色收益。这部分制度性收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村干部每月可获得的工作收入。近两年,中西部地区农村村干部的工作收入已经有明显提高,G镇村干部每月的工作收入在2 000元左右。此外,到年终,村干部还有各种奖金收益,平均到每个村干部大概有3 000-5 000元。当村干部所有可获得的收入加在一起,一年能有2-3万元。较之于部分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村干部的年工作收入,2-3万元的收入并不高,但对在乡村有经营产业的中农群体而言,这无疑是一笔额外收入,并能成为其家庭收入极为重要的补充;二是当村干部可获得的社保收益。大约在2006年左右,G镇所在地方政府开始陆续为“村三大头”购买社保,政府与个人承担的费用比例为6[BFZ]:[BF]4。连续交满12年,“村三大头”到达退休年龄后,便可获得每月1000多元的养老金。这有效化解了村干部离任后的后顾之忧。而且,当村干部还能进一步拓展中农群体的社会关系,进而起到润滑其产业经营利益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农群体的社会特征使其更容易认同国家下达的相关工作任务以及政策目标,并将落实和贯彻国家工作任务、政策方针视为自身的责任。在服务型政府转型以及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国家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而是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并且会颁布各种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民富裕和振兴乡村的政策。国家目标与农民利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由于中农群体长期生活在乡村,并且利益和社会关系都深度嵌入村庄,这使得担任村干部的中农群体必须要将有利于农民和乡村建设的国家任务和政策切实有效地执行下去,实现国家目标与农民利益的对接,以获得村民的认可,从而帮助其更好地实现其个人产业利益和维系社会关系。中农群体利益和社会关系在村的这一社会特征使其与乡镇的工作目标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即乡镇作为最末端的基层政权,贯彻与执行国家任务和政策是其必须履行的工作职责,中农群体对国家任务和政策目标的价值认同则为乡村责任共同体的建构奠定了心理条件。
由此可见,G镇对村干部选择的中农群体导向是其能够建构乡村责任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进而形成对村干部以执行贯彻国家任务和政策目标为指向的责任动员的村治主体基础。
(二)片组制度:乡村责任共同体的体制条件
中农治村是建构乡村责任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的村治主体基础,乡村责任共同体的具体落实还需要相应体制条件的推动。G镇则通过片组制度的设置对乡村两级进行治理责任的连带与捆绑,将乡镇干部与村干部整合进乡镇的工作任务体系之中。片组制度指乡镇政府将镇域范围内的村居分成若干片,每个片由3-5个村居组成,除乡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之外的其他班子成员、乡镇各站所的负责人以及一般工作人员根据各自的性格特质以及工作能力分组搭配至相应的片中,形成以片为单位的治理小组,负责其所在片区村居的所有治理事项。职位排名靠前的班子成员担任片长,其他班子成员担任副片长,其他站所长以及乡镇一般干部则以驻村干部的身份下派到各个村居,他们将处理本职业务工作之余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驻村,协助村干部处理相关事项。
G镇12个村居共分成四个片,人大主席、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镇长以及纪委书记分别担任各片片长,其他班子成员被分配到各片担任副片长。片长与副片长一般情况下不下村,只有在重大工作推进时或是村中的疑难问题依靠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无法解决时,才会下村联合驻村干部与村干部一同处理。日常工作中,片长与副片长只是对村庄工作给予统筹、安排和指导。驻村工作主要由驻村干部负责,G镇每个村一般安排2-3名驻村干部,多采取老少搭配的形式,蕴含着以老带新锻炼年轻干部的意味。从镇级层面来看,片组制度是一种责任分包制度,将乡镇工作在乡镇干部中进行划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片组制度是乡村责任共同体得以落实的体制机制,也是鄉村责任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机制。它通过对乡镇体制内人力资源的调动利用,尤其是借助驻村干部机制将乡镇体制内的治理力量下沉至村庄来实现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责任捆绑的目标。
乡镇重要班子成员担任片长有助于强化治理责任向村干部传递的效力,他们可通过对村主要干部职位,尤其村书记职位的政治控制实现治理责任向村级组织的传递。中农村干部对村干部职位的在意和重视使乡镇重要班子成员对村干部主要职位的政治控制具备一定的威慑力。此外,G镇政府将驻村干部的利益与工作高度嵌入村庄之中。这体现在:一方面,驻村干部的考核、绩效和奖励都与村庄工作的好坏挂钩;另一方面,驻村干部被赋予突出的村庄治理主体身份,他们与村干部一起参与到村庄实际工作的处理当中,由此实现驻村干部工作向村庄的嵌入。比如驻村干部需要与村干部一道参与村内矛盾纠纷的调解、乡镇常规工作以及重点工作在村庄中的推进以及各种文字档案等规范性材料的制作等等。驻村干部与村干部形成国家任务与政策在村庄执行过程中的紧密协作与配合关系,二者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产生对乡镇工作任务的一致认同,并形塑出基于共同工作认同的责任连带。因此,片组制度在实现乡镇治理力量向村庄下沉的同时,也是乡村责任共同体得以切实展开的重要体制条件。
(三)情感互动:乡村责任共同体的润滑机制
在“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下,乡镇政府与村干部不存在直接的行政控制和管理关系,因而乡镇政府也无法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让村干部协助乡镇工作的开展。要形成稳固的乡村责任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乡镇干部还需要对村干部辅以积极的情感互动来进一步润滑乡村之间的责任共同体关系。通过形塑村干部对特定乡镇干部,尤其是其所在片的片长、副片长以及驻村干部的情感认同来强化村干部对乡镇权力以及乡镇工作任务的认同,进而使村干部主动承接乡镇下达至村的工作任务,增强乡村两级干部的凝聚力以及治理合力。
G镇的重要领导以及其他乡镇干部,尤其是驻村干部都特别重视与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的交流与互动,他们会借助各种方式来与村干部建立情感联结,塑造村干部对乡镇干部的情感认同。在让村干部产生情感认同之前,乡镇干部首先需要确立其在村干部面前的权威形象,让村干部对他的工作能力形成认可。这是村干部对乡镇干部产生情感认同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干部(特别是驻村干部)一定要在重大且疑难的治理问题面前展现其工作能力。再者是乡镇干部还要通过各种媒介,比如开座谈会或者是私下与村干部沟通、谈心的方式主动与村干部交流,并从内心里真实地认可村干部的工作价值以及理解村干部在工作任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难处,并能给予积极的情感回应。有些乡镇干部甚至将这种情感关系延续到二者的日常交往中,比如相互之间的人情往来之中。一旦村干部产生对特定乡镇干部的情感认同,那么只要是该乡镇干部出面分配的工作,村干部都会全力地去执行,由此实现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的润滑与巩固。调研中一位村书记这样说道:“士为知己者死。领导对我的肯定,对我知冷知热,这是我为他工作的最大动力。能理解我,认可我,关心我,不对的时候指正我。不把工作做好,我对不住他。领导交办事情,我会想尽办法去办好。”
三、乡村责任共同体的治理优势
建构责任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成为农村基层灰色利益空间被极度压缩的背景下公共财政资源较为稀缺的中西部地区实现乡镇政府对村干部有效动员的重要路径。乡镇与村干部在实现治理责任捆绑的情况下,二者的积极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并呈现出多重治理优势,在增强乡镇治权的同时,也维系了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面向,保存了村民自治空间。
(一)增强了乡镇治权
乡村基层治理研究主要将治权与资源相联系,将资源视为治权的重要生产机制。吉登斯较为系统地揭示了权力与资源之间的关联性,认为资源是重要的权力再生产机制,并将资源区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17](P7)。受吉登斯的启发,申端锋将乡村治理资源划分为物质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物质性资源指乡村组织所拥有的物质,权威性资源指乡村支配农民的手段与制度[18](P14)。
从乡镇治理的角度来说,乡村关系同样构成乡镇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治理的顺利展开离不开村级组织的有效配合。因此,良性的乡村关系是增强乡镇治权的重要因素,它具体体现为乡镇政府对隶属于村民自治体系中村干部的整合与动员能力。责任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通过对村治主体选择的中农群体导向、片组制度的设置以及乡镇干部对村干部进行积极地情感性互动等多重体制机制的建设极大地实现了乡村两级基于农村治理责任的捆绑,将村干部吸纳至乡镇的工作任务框架中,形成村干部对乡镇工作目标的认同,进而实现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有效整合和动员。在这种情况下,以村两委干部为主体的村级组织俨然成为乡镇政府的治理资源和治理支撑,起到了增强乡镇治权的效果。
(二)维系了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面向
“简约治理”概念最先由黄宗智提出,用来指涉中华帝国时期县级以下治理中广泛采取的半正式行政方法,由社区提名的准官员是半正式行政的实践主体。黄宗智认为,“简约治理”的重要遗产还被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现今的改革时代所承继[19](P10)。“简约治理”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一种低成本的治理模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约治理”模式的制度基础是基层组织的非政权属性,即基层组织是半正式化的治理组织。治理主体的“准官员”身份意味着其并不是完全由政府公共财政供养;二是依托半正式化的治理组织,整个村级治理活动的开展主要是运用人情、面子等乡土治理资源,而非依靠政府供给的正式制度和体制资源[20](P81)。责任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维系了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内涵,具体体现在这一乡村关系模式并没有额外增加治理成本。
首先,村干部依然保持了兼业特征,并没有成为职业化村干部,村干部在从事村庄工作的同时也经营自己的家庭生产活动。村干部的兼业特征具有类似于黄宗智提出的“准官员”性质,地方政府在动员村干部承接乡镇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只需要给予数额不多的误工补贴。村干部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也较少倚仗乡镇政府的正式治理资源,而主要利用乡土治理资源。只有在超出乡土治理资源的治理限度时,村干部才会寻求乡镇政府的帮助。其次,在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模式中,镇级层面也未增加新的治理成本,而主要依托片组制度将乡镇既有的体制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和调动,使乡镇既有体制资源的治理效能得到充分释放。因此,责任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在不新增治理成本的前提下,通过充分撬动和利用既有的治理资源,维系了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面向,适应了中西部地区地方公共财政有限的现实。
(三)保存了村民自治空间
责任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延续了“乡政村治”的基本治理架构,保存了村民自治空间,有助于村干部充分进行群众动员式治理。村民自治不仅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的重要方式,也是乡镇治理的重要工作方法和手段。乡镇工作任务在村庄执行的过程中,还需要借助村民自治的方式来完成。具体来说,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工作任务。
其一,具有政策模糊性的工作任务。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不规则性,这类任务往往很难在国家统一的政策领域中给出清晰的和标准化的执行标准,因而需要采取动员群众、利用村民自治的方式生成工作任务的执行规则。这类工作任务常见于针对农民的资源和利益分配领域中,比较典型的是农村低保资源的分配。根据制度设计,我国主要根据农户家庭收入标准来确定低保对象,但农民的家庭收入通常难以做到量化核算。一方面,农户家庭收入呈现为多元化特征,并表现为传统农业经营收入、务工收入、政府转移性收入以及出租房屋等财产性收入并存的收入来源结构,由此可能产生农户隐瞒收入的问题,而无法对其家庭收入进行精准核算;另一方面,农户家庭还有很多无法货币化的隐形收入,比如其用于自我消费的粮食、家禽等。此种情况就需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效能,利用村民彼此之間的相互熟悉将村中的绝对贫困群体筛选出来,形成全体村民所认可的低保评选规则。
其二,基层公共服务类的工作任务。基层公共服务类的工作任务一般是面向所有村民,且多发生在村民间相互重合的公共领域。但是在地方政府治理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村内的大部分公共服务不可能都由政府承担,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还需要在村庄社会内部消化,由村民共同承担。就目前来看,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涉及范围比较广泛。其中,最基础的环节是村内环境卫生的长效保洁,而这离不开村民的广泛参与。只有形成村民内部的自主管理与自我监督,才能降低人居环境整治成本,也才能增强村民的环境卫生意识,避免形成村民对政府的过度依赖,进而构建出一种可持续的环境卫生管理机制。
乡村责任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充分保存了村庄社会的自治空间。乡镇政府通过将乡镇工作任务转化成村内工作任务实现“乡政”与“村治”的有效衔接,极大激活了村民自治资源。
四、结论与讨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乡村治理现代化则蕴含在这一改革目标之中,并且乡村治理现代化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问题。其中,乡村关系是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具体表现为隶属于国家行政治理体系的乡镇政府对隶属于村民自治体系的村干部的动员关系。在良性乡村关系模式的构建上,赣西G镇作出了有益探索,当地形成的责任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不仅增强了乡镇治权,而且维系了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面向,并在“乡政村治”体制架构的基础上,充分释放了村民自治的治理效能,保存了村民自治空间,契合“人民获利”[21](P172)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最根本目标。
当然,乡村责任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仍存在一定的治理限度,主要体现为它不是一种具有高度动员效力的常态化乡村关系模式。在长时间段内,当乡镇下达至村庄的行政工作任务过多,担任村干部的村民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在村庄工作中并严重影响其参与自身家庭生产经营活动的投入时间时,隶属于村民自治体系中的村干部就极有可能出现消极应付的行为。这意味着在责任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中,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动员强度是受到限制的。因此,乡镇政府需要切合实际需要,尽量减轻村干部不必要的行政任务负担,避免对村干部形成过度动员,挫伤村干部落实乡镇工作任务的积极性,确保责任共同体式的乡村关系模式的可持续运转。
此外,乡村责任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正不断经受各种改革措施的冲击:一是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思路下,各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引进外来资本流转乡村土地,发展乡村旅游,进行田园综合体打造。外来资本的涌入直接占据了乡村社会本不充裕的经济机会,形成对中农群体生存空间的挤压,迫使其不得不离开乡村,去城市寻求务工机会;二是对村干部选拔标准的年轻化与学历化要求。比如部分地区对新进村干部的年龄限定在18-35周岁,且需要大专及以上学历。与之相对应,则是将村干部的工作待遇大幅提高,否则既有的工作待遇根本无法吸引年轻且高学历的村民。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村干部的选拔方向实则是对中农村干部的替代。上述两种改革倾向都会造成村庄社会中农村干部的缺失,从而使乡村责任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的建构失去村治主体基础。我们需要对当前出现的上述两种改革倾向有所警惕,为乡村责任共同体这一乡村关系模式的构建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张厚安.乡政村治——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J].政策,1996(8).
[2]项继权.乡村关系行政化的根源与调解对策[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4).
[3]金太军,董磊明.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關系的冲突及其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2000(10).
[4]贺雪峰,苏明华.乡村关系研究的视角与进路[J].社会科学研究,2006(1).
[5]桂华.论村级形式主义的体制性成因——基于乡村关系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21(9).
[6]邹建平,卢福营.制度型支配:乡村治理创新中的乡村关系[J].浙江社会科学,2016(2).
[7]吕德文.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工作共同体的建构逻辑[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
[8]韩鹏云.乡村关系的运行机制与改革发展方向[J].甘肃社会科学,2016(2).
[9]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10]赵晓峰.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演变逻辑——兼论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的变异逻辑[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9(3).
[11]贺雪峰.试论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J].中国乡村研究,2007(4).
[12]陈柏峰.“有才无德”村干部:悖谬及原因[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13]温铁军.八次危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14]杜姣.村级组织建设路径的地区差异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中西部地区村庄为经验基础[J].中国行政管理,2020(4).
[15]贺雪峰.论中坚农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16]刘锐.中农治村的发生机理[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17]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8]申端锋.乡村治权与分类治理: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换[J].开放时代,2010(6).
[19]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2).
[20]赵晓峰.公域、私域与公私秩序:中国农村基层半正式治理实践的阐释性研究[J].中国研究,2013(2).
[21]蔡伏虹.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基于城镇化三重结构矛盾的省思[J].河北学刊,2020(3).
The Practical Logic and Governance Advantages of Rural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G Town in Western Jiangxi Province
DU Jiao1,LIU Yao-fei2
(1.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Nah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wnship and village is the channel for the state governance to enter the rural society.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period,for the vast number of rural area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interest community between township and village,which widely appears in the tax period,and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administrative community between township and village,which exists in some developed areas,have no spale for survival.G town in western Jiangxi Province has realized the joint and binding of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middle peasants as village cadres,the grouping system and the positive emotional interaction with village cadres.It has absorbed village cadres into the work task framework of township government,and constructed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between township and village.The model of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between township and village not only strengthens the governmental power of towns,but also maintains the simple governance model of rural society and preserves the space of villagers’ autonomy,better solves the problem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work tasks assigned to township to village society,solves the problem of the mobilization of village cadres by township government,and realizes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ownship government and village governance.The mode of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ownship and village can become an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ownship and villag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Key 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township and village;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between township and village;village governance by middle peasants;grouping system;emotional interaction
(責任编辑
陈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