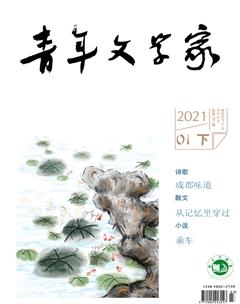《呼啸山庄》的文学文体学分析
摘 要:《呼啸山庄》在批评界一直遭受异议,但进入二十世纪,评论界对这部作品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已有评论界虽已有从文学文体学这一角度的分析,但角度比较受限,且分析不够深入。本文在对这部小说进行细读的基础上,从视角转换、会话分析,以及文本类型出发,在语言层面分析的基础之上对其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使用的这些写作手法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本所蕴含的生态观念这些方面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
关键词:《呼啸山庄》;文学文体学;视角转换;会话分析
作者简介:马越(1997-),女,汉族,陕西西安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3--02
学界对《呼啸山庄》的文体学分析多从其叙事角度出发,对于语言层面的分析较少。如张琳在《语言情态的人际意义研究——以<呼啸山庄>中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对话分析为例》中,对于情态动词的使用进行了細致的分析,以深入了解人物性格特点及内心情感。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界定“‘文学文体学特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为目的的文体学派。”[1](p76)本文将从叙事学的视角转换,语言学中的会话分析,以及这部小说的文本类型出发,对文本进行多方位的分析,以探究其所蕴藏的潜文本。
一、视角转换
“叙事作品文体分析中受MickShort和其他文体学家关注最多的是叙述视角和人物话语表达方式。”[2]从艺术结构来看,《呼啸山庄》中的嵌套式叙述方式是其显著特征之一。初读《呼啸山庄》,读者也许会对故事中的事件及发生的时间感到困惑,但这一安排却另有深意。关于叙述方式,我们借用奥地利学者斯坦泽提出的“叙述情景”这一概念对文本进行分析。
人称叙述情景指的是由一个叙述者将自己的故事讲给其他人,而小说中的洛克乌的叙述显然属于这一情景。他的日记中不仅有自己的所见所闻,也囊括了其他人物的叙述。他是现在这个时间的见证人,透过洛克乌的视角,我们看到屋里年轻凯瑟琳的冷漠,屋外“烈风和猛雪卷起可怕的漩涡,把天空和山岗全都搅混了”[3](P17)。房客洛克乌是现在这个时间的见证人,他给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奇怪的,冰冷的家庭氛围,这引起了读者的好奇。我们不禁会好奇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这些人物身上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但“书中的‘我不是可以提供可靠信息的全知叙事者,而是和读者一样需要从头认识周围环境和人物。”[4]这就使得读者继续追随洛克乌的脚步去探索事情发生的原委,而这是洛克乌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因此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叙述者。
人物叙述情景指的是通过故事中人物对于故事发展的观察来呈现故事,洛克乌、伊莎贝拉、纳莉的叙述都是人物叙述情景,他们分别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于过去、现在的故事发展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呈现。奈莉承担的是过去发生的故事的叙述者,现在与过去使得这个故事变得完整。而顺叙、插叙与倒叙的使用使得整个故事变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也使得读者与作品中的人物的关系若即若离,给人以不同的体验和理解。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不仅能读到房客洛克乌的带有主观色彩的叙述,也能读到参与过去事件发生的人物的叙述。洛克乌和奈莉不仅承担了叙述者的角色,也在其叙述的过程中承担了传话人的角色。这不仅仅是艺术结构上的大胆尝试,更是使得读者与作品的关系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此类叙述的不可靠性值得我们注意,因为除了在叙述的过程中带有个人立场之外,回忆的过程中也不可能每件事都能清晰无误的记录下来。选择性视角的局限性使得我们在接受信息时充满了多种可能性,因而也给读者留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和阐释空间。
二、会话分析
“文体学虽可划归应用语言学的范畴,但其本身是将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交叉学科。”[5]通过对文本中词汇的选择,我们便可以深入了解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态度和情感色彩。
《呼啸山庄》中故事的核心虽然是希克利和凯瑟琳的爱情,但是对于这两个人在一起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却并不多,小说中第十五章是两个人最后的会面,这个场景俩人的言语行为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分析。希克利和凯瑟琳最后会面的场景是“strange and fearful”,凯瑟琳脸上的表情是“a wild vindictiveness” 和“a bloodless lip and scintillating eye”,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矛盾的凯瑟琳。在她的身上既有一种愤怒,又有见到爱人的那种激动与兴奋。这时的她十分虚弱,但透过这些词汇我们还是能深切地感受到她对希克利的强烈的感情。此时希克利“while raising himself with one hand, he had taken her arm with the other; and so inadequate was his stock of gentlenes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her condition”[6](p124),这里动词提前起到了强调的作用,突出了希克利想要靠近凯瑟琳的急切心理。但希克利并没有温柔地对待孱弱的凯瑟琳。倒装句的使用也起到了强调的作用,突出了希克利的粗暴。
“‘Are you possessed with a devil, he pursued, savagely”[6](p124)
希克利对凯瑟琳的评价也是与常人对于相爱之人的定位是大相径庭的,希克利竟说她身上有着“devil”,并且用到的副词是“savagely”。这些词汇的使用都使得这两个人的关系让人觉得很费解,但细细品味我们会发现凯瑟琳的死亡使得希克利即便是活着也要经受着失去爱人的折磨。我们可以见到的是希克利和凯瑟琳两人之间强烈的,超乎常人的感情的爱恋,看似疯狂却又让人感动。
“文体学除研究作家或流派的文笔风格外, 通过语言特征来更好地揭示某一作品的审美价值或主题意义。”[7]尽管希克利和凯瑟琳之间的爱释放的非常激烈,他们没有对自己的感情加以控制,但是他们追求的灵魂上的契合才是两个人对于彼此的定位。他们之间没有你我之分,这种超越了肉体的精神上的结合使得他们的爱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三、虚构现实主义
19世纪是英国小说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各具特色。不同于伊恩·瓦特的形式现实主义,不同于乔治·艾略特的心理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狄更斯的外部现实描写,艾米莉所呈现的是一个想象的现实空间。“如果说《呼啸山庄》纯熟精到的写实部分构成了有生活实感的基本层次,那么非写实的部分就凸出了作品的思想层次或哲学层次。”[8]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对小说中所呈現的现实与非现实因素进行分析。
艾米莉酷爱自己故乡的荒原,在那里“山上杂草丛生,树木稀少。绿色的山坡上,有时覆盖着成片黛绿紫褐的低矮植被。”[9]而透过小林顿的视角,我们在原野中央石楠丛生的高坡上也能感受到这片荒原的气息。在艾米莉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生长的荒原的影子,感受到这片荒原的气息。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这两个虚构空间的截然对立呈现出了一个虚构的空间。“读者对艾米莉在约克郡生活细节和风景的印象和小说中这些因素的部分缺失的区分,是艾米莉对虚构现实主义和明显的虚构进行平衡的结果。”[10]艾米莉使用虚构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现实与想象区分开来,使得读者和作品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不至于陷入小说中那种疯狂、扭曲的爱恋。因此便可以在凯瑟琳和希克利的爱恋的背后,去探寻另外一个潜文本,寻找《呼啸山庄》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
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在向我们讲述一个几近疯狂与变态的爱情故事,在这个文本之下还有另外的潜文本,蕴藏着更加深刻的思想和理念。在这暴风雨般的爱情与复仇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注。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人的心灵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与自由,人的生存环境才能真的有所改变。艾米莉这种前瞻性的思考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19世纪英国的社会状况,而且能够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存产生启发。
结语:
《呼啸山庄》中主题的呈现与其叙述技巧、语言的选择,以及作者使用的虚构现实主义手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通过这一多角度分析,我们深入体会到了故事中希克利和凯瑟琳超越肉体的精神契合,以及艾米莉本人的生态观念。在现在这个物质生活不断提升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正确面对和处理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各种欲望,不能耽于物质享受,应该多接触大自然,调整自己的身心。
参考文献:
[1]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申丹. 《语言与文体》评介[J]. 外语研究, 2013(06): 104-108.
[3](英)艾米莉·勃朗特著. 呼啸山庄[M]. 方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4]刘进.“观望者”的故事——《呼啸山庄》叙述层次研究[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3): 100-103.
[5]申丹. 跨学科角度的叙事分析——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J]. 江西社会科学, 2008(02): 26-32.
[6]Bronte, Emily. Wuthering Heights[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847.
[7]封宗信. 叙事小说的语言形式与文学意义[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0(04): 75-77.
[8]金琼. 绝对时空中的永恒沉思——《呼啸山庄》的叙述技巧与结构意识[J].外国文学研究, 1993(02): 39-44.
[9](英)夏洛蒂·勃朗特, 艾米莉·勃朗特著. 勃朗特两姐妹书信集[M]. 孔小炯译. 河北: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10]Margaret Homans. Repression and Sublimation of Nature in Wuthering Heights[J].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78(93): 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