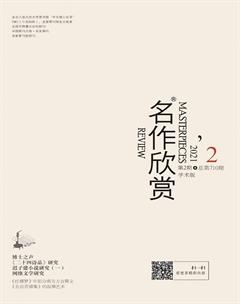葛水平小说创作中的民俗元素探析
摘 要:通过阅读葛水平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她总是习惯用与民俗有关的内容来丰富和演绎小说。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浏览和分析文本,将在其几篇代表性小说中所发现的民俗元素为切入点,来明确一个选题方向和独特的写作角度,探析民俗元素在其小说文本中的分布和分类,及其对文本的影响和作用;并由此开拓思维,试图为当下对其作品的研究进行丰富、填充,乃至可以提供另一个分析的角度和路径。
关键词:葛水平 民俗元素 口头文学
葛水平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之一,其创作路程的起始相比于更多的文学作家来说是较晚的,但是她的文学作品却得到了高度认可,成为山西文坛的重要作家。通过阅读其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她总是习惯于用与民俗有关的内容来丰富和演绎小说,本文便以葛水平的小说为例来说明。正是因为有了众多民俗元素的运用和对民间生活的真实书写,作者笔下的内容才更显真实细腻,呈现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真实的人物生活,同时能够充分显示乡土社会的封闭性和传统性。葛水平对乡土气息的极力渲染,在小说叙事中突出的文化标志,形成了其作品的特色。因此,对其文学作品中的民俗元素进行研究就更加有意义与可解读性。
一、神像信仰与人物命运
(一)炎帝像
《活水》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神像信仰,这篇小说延续了她一贯的乡土写作风格,其中的神像信仰以炎帝像为代表。炎帝庙是小说中多次描写的民俗元素:“炎帝对山神凹人来说是一个大道理,你可以不予接纳,但必须予以尊重,炎帝庙是山神凹的大是大非。”小说由此引出了全篇的第一个民俗元素,关于它的描写还涉及多次,此处不再赘述。
(二)人物命运
作者笔下的人物似乎总是逃脱不了悲剧的结局,如《活水》中的一系列人物:李夏花的丧子之痛、申小满的余生忏悔、申芒种的憨傻等。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不仅让读者看清了人性的善与恶,而且一次次地体会到悲剧带给人们的心灵震撼。其中,申芒种的悲剧也是最离奇、讽刺的。
这一人物的悲剧要从他和炎帝庙的缘起说起。炎帝庙和炎帝像是镇土一方的保护神,是山神凹人的根,申芒种与山神凹这片土地相伴生长。由一开始的天真淳良,到对申小满的盲目追从,再到最后对炎帝庙的不敬和毁灭,变卖神像,在人性和神力的对抗中,他失去了对自我生存价值的思考,也忽视了炎帝庙存在的意义。失了根本,生命就沒了意义;丢弃信仰,他终得报应,成就悲剧。
首先,拆毁神像,是对山神凹地物风貌的破坏。山神凹不再有山神庙,从此失去了信仰的标志和符号,这是人与自然的悲剧冲突。其次,他对神像的破坏与山神凹人对神像的敬仰相违背。这是对人情伦理的对抗,造成人与社会的悲剧冲突。再次,他没有自我意识,不受伦理道德原则的约束,失去自决能力和自我选择,最终只能彻底丧失精神自由,这是人与自我的悲剧冲突。作者在这样的悲剧中,揭示了主体自我意识和人性美的重要性,以及生命力的伟大。也是在这样的悲剧中,作者表达了对土地、神像、信仰、生命意识乃至悲剧等的敬畏之心。
(三)同类型情节
在《天殇》中,上官芳和王安绪订婚,两人的生辰八字被一起放在水缸里的两只碗中。春香看见这一幕,出于嫉妒,拨散了两只碗,没想到就打着旋沉了底。她惊吓着了,伸手去捞却再不能回复原有景貌,就得溜走,迎头撞上了婶娘,一下重重地摔倒了,便傻了……春香失去自我理性的行为让这种信仰被破坏,最终,王安绪和上官芳相继殒命,这场婚事不得圆满。
如此荒诞、突然的悲剧效果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既可笑又可怜。由此,一个悲剧暗示着另一个悲剧。这种悲剧意识无形中渗透在之后的每一段情节里。这其中的人文思考就是人性的真诚善良,守得根本。对神灵的亵渎、对信仰的不敬,暗示了人物命运的结局和走向。这不仅让读者理解了民间信仰的神圣,而且抒发了作者的生命意识。
所谓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另一方面来说,抛开事物的价值,任何事物都是正反的对立与结合。当好与坏、善良与罪恶、美好与丑陋交织在一起时,复杂的个体自然要被道德准则批判或者承担悲剧。当个体和悲剧之间存在不平衡时,实则会更让人悲叹。申芒种以一个奇异又真实的形象面对读者,而后因人诱骗自食其果;春香对爱情的懵懂、执着无可厚非,可也因为偏执而起异心。他们不是肉体毁灭型的悲剧,而是更深刻的精神损伤型的悲剧,他们本质单纯,天真无害,却承担了过分的惩罚。作者以一种特殊的生命悲剧的美学形式来构建文本,营造了悲痛和怜悯交织在一起所生成的悲凉语调,表达了“人性本善”的美好愿望。
二、民俗事象与文化意象
(一)喊山
“《喊山》是一篇读来令人震撼的充满现实感的作品,一个被拐卖的女人被以极为野蛮的方式剥夺说话的自由达十年之久,整日生活在沉默和恐惧中,最后终获解脱和自由。《喊山》以‘声音为主题,在民间生活的丰厚质地上展现心中艰巨的大义和宽阔的悲悯。它在艺术上显示出极为成熟的风格:作者通过诗意的语言、鲜活的细节和耐心的叙述,彰显了一个与尊严和自由相关的主题,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这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评委会对其作品的评语。
“喊山”一词在小说中出现三次,被作为一种民间习俗运用在小说中。与文学创作艺术性地融合在一起,就不会再是原来简单的民俗意象,它在文学作品中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位哑女对山另一头的回应,看似是在喊山,实际已由最初的沟通方式,或者驱赶野兽的民俗意象,转变为对自我情感的宣泄和抒发。这是主人公对自己命运的坎坷不公、生命的悲惨痛苦、生活的无奈寂寞的呐喊,是她对挣脱枷锁、获得自由的呐喊,对生存欲求的呐喊,是对低贱、荒诞、脆弱的生命的反抗。这一声呐喊引起了我们对现实生活中弱势女性群体的关注,也唤醒了我们的怜悯向善之心。最简单的文化表述都是有意识的创作,小说中作者所表达的生存、安全、恐惧、死亡等意识也都是其女性意识的倾泻而出。对喊山这种民俗的描写,能够让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重新审视道德的底线,对女性这一角色重新进行认知、反思和确认;由底层社会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来看当代社会性别平等的问题,能产生价值认同上的共情度。阎开振曾言:“葛水平在对生活和艺术的体会和体验中形成了自己对生命意识独有的感知与理解,然后将这种生命意识倾注于作品之中,用艺术展现她对生命本质与价值的思考,形成自己的生命哲学。”
(二)甩鞭
葛水平笔下另一篇小说《甩鞭》,依旧以女性为主人公。一生以放羊为生的鐵孩,面对王引兰却爱而不得。在占有欲的驱使下,他的心理逐渐扭曲,于是,他害死了王引兰的两任丈夫。但也是这个男人,让王引兰在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甩鞭,才有了盼望春天的希望。然而,在甩鞭的绝响中,王引兰的希望最终破灭。
“鞭声不沾尘土与落雪交融,王引兰觉得心开了,血沸了,这时听到遥远处有一声雷响,生生滚了地气,在天地邈远之中,浩浩荡荡传来。紧接着是大片雷声从漠漠旷野中急速滚过,仿佛来自浩渺天宇惊雷般的鞭声,竟让王引兰的灵魂战栗了,她觉得有一种东西从此就嵌进了她的生命,是什么呢?她现在明白了,是鞭。鞭声是一种昭示:她王引兰的生命里会有春天吗?”a但最后知道真相的王引兰,亲手杀死了这个给她带来希望又给她带来绝望的男人,也打破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她渴望的真正的春天来了,只一眨眼,她发现她看到的依旧是一片暗,是一种没有半点生机的死亡颜色,一个聒噪的世界里,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已经离她而去。原来她的生命里是没有春天的。她听到血滴成阵,落地如鞭,干巴巴的成为绝响。”b
她等到春天,看到的却不是春天的颜色,这种颜色是灰色的,是血色的。人生有了希望,而希望又破灭,永远是绝望和死亡的交替。在甩鞭这样的民俗形式中,文化意象其实是一种隐喻性的书写,象征了人物生命和节气轮回的契合,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天人合一的精神。小说起始的背景是在冬天,麻五死了,一个人的生命在这样一个肃穆的季节里消失了。此后一段插叙回到过去,王引兰的身世、他和麻五的缘起、婚嫁后的生活伴随着一轮季节的轮回而自然发生。在这一段回忆性的描写里,甩鞭和它的意义在王引兰心里萌芽。随后,小说又回到现实的冬天,开始了向春天的过渡。这是甩鞭的季节,意味着春天来了。她喜欢看铁孩甩鞭,这也是她对希望的追寻。春天万物重生,欣欣向荣,与王引兰这个人物的心理是十分契合的。气候开始好转,人物也度过了生命里的坎坷,看似迎来了希望,但她还是在等来的春天里死了。人与自然共生,和谐舒展,人物的命运却迎来了悲剧,这不能不让人悲叹。
这里的甩鞭与喊山一样,都是一种民间习俗。但它不仅仅是一种习俗,还是春天来临的标志,象征了人物对重获新生的企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我尊严的守护,以及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其中的文化意象和内涵在作者的笔下更加厚重,既是对男权统治下女性悲惨命运的书写,也表达了作者对女性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三、民间文学与口头传统
(一)民间音乐
1.小调
三毛钱买了一杆铜烟袋/红绸布袋绿飘带/有人问我谁做的/嚎嗨,是我表妹叫改改/满窗子玻璃明晶晶/观看二哥进大门/炕上坐个无事人呦/嚎嗨,不想给我腾空空/越思越想越生气/拿起扫帚扫脚地/满家灰尘难睁眼/嚎嗨,看你没事不走开 (《活水》)
这是一段对韩谷雨出场的描写,他看到山神凹每一户窑垴上的炊烟,唱起了小调。他觉得哪里都没有山神凹好,唱着凉腔走调,缭绕到最后那一丝尾音上,眼泪掉下来了。小调中真实的生活场景描写、人物描写、诙谐的语调给人一种轻松活泼的乡村画面感,让读者得以体味其中的世俗情调。
这种自白式的叙事歌,在叙述个人经历的过程中,插入社会事件,演唱者在演唱时使用了装饰音和传统民歌重章复沓的形式。这样,歌手个人的声音就能变成真正的民俗音乐,演唱者所呼吁的个人要求到了听众那里,就变成了社会性的集体选择。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他们所置身的社会环境,是当代“社情”的一部分。歌词中的文化观念,是现实生活和低消费的传统生活的结合。小调民歌不仅是乡民社会交往的工具,也是乡民性的流露。他们生活在传统、粗犷、原始的乡村文明中,形成了粗野放荡的性格,找到了发泄心情的最好方式,保证了乡民的自我存在。
2.儿歌
月明月明光光/闺女下河洗衣裳/洗得小手白光光/蒸好馍馍你尝尝(《活水》)
李夏花丧子之后一人在戏班子里生活,孤独和自卑感让她时常想念死去的儿子。在经历了精神困境和心灵折磨之后,她的性格发生了蜕变,于是唱起这首儿歌,回想从前遭遇的不善、痛苦和寂寞。她在自责中只身一人求生活,无人安慰的悲哀不免让读者感受到这个女人的不易和不幸,也让读者看到了这位女性主体的精神成长。
(二)民间戏曲
春光不用银钱买/春花年年为我开/与父春山把猎打/相依为命十数载/老爹爹进城去把兽皮卖/为什么日过午还未回来
作者在小说文本中多处运用戏剧这一民俗元素,并且用大量的笔墨细致具体地描写戏剧内容,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娱乐性,让文本充实自然,情节更加真实丰富。读者在欣赏小说的故事情节之外,还能体会到更多的乡村文化。用这样一种描写戏剧表演的文学方式来反映晋东南地区的文化特色,对人物、情节、语言风格的塑造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方言俗语
1.琴花马上就变了一个腔:“水流千里归大海,人走万里归土埋,活归活啊死归死,阳世咋就拽不住个你?”(《喊山》)
2.“油菜花亮汪汪,坐了花轿奔哪方,绿望绿黄望黄,嫁了男人不想娘……”(《甩鞭》)
3.黄皮子叫道:“一双落了草(死了),都是真汉子。”(《天殇》)
葛水平小说中对民间口头文学的运用造就了她语言上简洁精练、质朴淡雅、通俗平易、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让文字因地方方言的使用而具有感染力,让小说更具乡土气息,更具“俗”味,也让读者真切地体会到地方人情风物的特点,完成了民间口头文学对小说风格的第二次塑造。这得益于作者的语言功底,对晋东南人文气息、风俗文化的感悟和自身独特的气场。
葛水平的小说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将乡土文学和地缘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是具有较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小说。它裂变为乡土写实和乡土抒情,注重人与“乡土”关系的原初性、自然性和精神性,表现了一种集知识、信仰、道德、习俗、人际交往、价值观于一体的文化形态。葛水平用文字的形式与自然沟通和交流,构造了一个完整的礼俗社会,让读者感受到了文化撰写中的美感和痛感、反抗和超越。如此一个广泛涉猎民间文化的作家,将文字和民俗互补,让民俗成了会说话的文化;同时,作者用原生态的语言描写,让读者看到晋东南地域的生活场景和文化意蕴,并慢慢沉淀为其笔下细腻真实的民间立场和善意的表达。
她借助一种现实与文化相融合的描写方式来表达其中隐喻和象征的部分,用笔下的文字来理解生命的价值与人性的善恶,看待等级社会和平权社会。她试图用每一部作品来描绘乡土生活的画卷,通过乡村风俗来解读生命的意义,并将其中的封闭性和传统性表达得淋漓尽致。因此,葛水平小说中的风俗、文化符号,以及其他细节都是值得被剖析和解读的。
ab 葛水平:《甩鞭》,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第221页。
参考文献:
[1]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 葛水平.守望[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4.
[3] 葛水平.吴玉杰.有一种气场叫善良——葛水平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1(4).
[4] 高长江.乡情·乡俗·乡音——中国乡村文化语言的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
作 者: 牛莹,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俗文化。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