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根书简》:欧洲名医与中国土茯苓
1543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5月,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德国纽伦堡出版;6月,维萨里的《人体之构造》在瑞士巴塞尔出版。对中国读者而言,维萨里的名字可能比较陌生。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比利时人,解剖学家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御医。《人体之构造》出版前,欧洲知识界对身体的认识以公元1世纪罗马医生盖伦(Claudius Galenus ,129—199)的《解剖学》为准,盖伦在动物解剖基础上构筑的解剖学思想被中世纪医生奉为圭臬,容不得半点质疑。欧洲医学界封盖伦为“医圣”,与维萨里同时代的医生大多数是盖伦信徒。维萨里的著作以人体解剖与活体观察为主,批评了盖伦学说中的错误,同时配制了精美的人体图像以描述正常的身体构造。如果说《天体运行论》调整了人们看世界的眼光,找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那么,《人体之构造》则修正了人类对自己身体的认知,使人们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以一种创新的方法彻底颠覆了盖伦的学说。西方史学家认为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启开了欧洲的科学精神之路,1543年标志着欧洲的科学知识走出了中世纪。在西方科学史上,维萨里则被认为是西方古典医学的终结者,在学术贡献上是与哥白尼齐名的科学家。
《人体之构造》与《中国根书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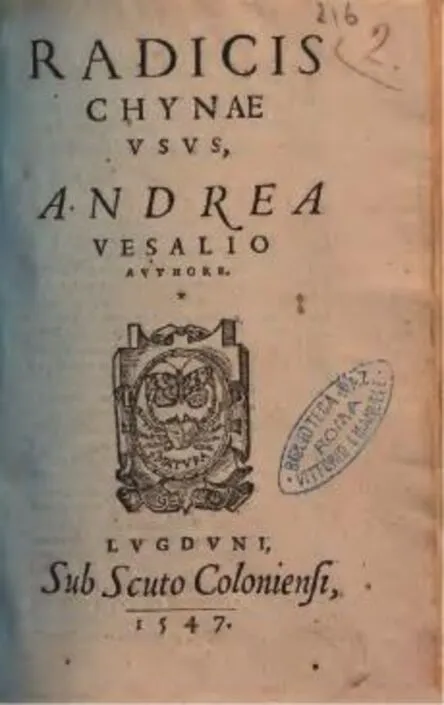
1547年出版的《中国根书简》
维萨里出生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医生世家,其曾祖父在鲁汶大学教授医学,祖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皇室御医,父亲安德里斯(Anders van Wesel)是马克西米连的药剂师,后任查理五世的贴身侍从。父亲鼓励维萨里延续家族的习医传统,1528年,维萨里进入鲁汶大学修读美术,1533年去法国巴黎大学学医,他追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德国籍医生安迪拿其(Johann Winter von Andernach,1505—1574)和法国著名的解剖学家西尔维乌斯(Jacobus Sylvious,1478—1555)学习。求学期间,维萨里表现出对解剖学的浓厚兴趣,他时常去巴黎的圣婴公墓研究人体骨骼。1536年,他移居威尼斯,后就读意大利帕多瓦大学,1537年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了帕多瓦教授外科学和解剖学。同时,他还被邀请去博洛尼亚大学和比萨大学作解剖学讲座。当时欧洲教解剖学的教授或听解剖学的学生都学习过盖伦的理论——以动物的解剖来进行说明——但没有人试图去验证一下盖伦的理论。维萨里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他使用解剖工具亲自演示操作,学生则围在桌子周围观察学习,面对面的亲身体验式教学被认为是唯一可靠的教学方式,也是中世纪解剖教学实践的一个重大突破,《人体之构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人体之构造》出版时,维萨里才28岁。书甫一面市,便受到医学生们的欢迎。然而,维萨里公然否定盖伦学说的做法,威胁到了欧洲各国医学院中被称作为盖伦学派的解剖学家们,其中,维萨里在巴黎大学求学时的解剖学导师、著名的解剖学家西尔维乌斯尤为愤怒,他在课堂上批评维萨里的言辞是“无礼”而“浮夸”的,指责维萨里对盖伦学说提出疑义是“不忠”的行为。同时他利用自己在学界的影响让朋友和同事疏离维萨里。面对权威的攻击,年轻的维萨里烧毁了自己的手稿和为研究所收集的素材,离开了大学。在宫廷药剂师父亲的斡旋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御医。即便如此,欧洲解剖学界也没有放过维萨里、停止对他的攻击。
1546年1月,维萨里收到好友、比利时医生阿希姆·多米努斯(Joachim Roelants,1496—1558)转来其儿子由法国寄来的信件,叙述了巴黎医学界对《人体之构造》的反应。1546年,维萨里修正盖伦解剖学知识的新书在瑞士出版,有意思的是,该书的名称是《中国根书简》(Radicis Chynæ),全信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回答“中国根”的问题;第二部分是直接回应西尔维乌斯的批评,对《人体之构造》中反盖伦的内容作详细说明。
“中国根”是什么?为什么维萨里在回答批评者的意见时,会将这两部分内容合在一起,并采用了一个与中国相关的书名?
查理五世迷信的“中国根”
16世纪的欧洲社会,困扰人们的两大疾病是痛风和梅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受痛风困扰多年。1546年,维萨里随查理五世到布鲁塞尔,皇帝的病情再次发作。维萨里和宫廷第一御医一同参与对查理的治疗,但皇帝并不相信御医们提供的治疗方案,而是想自己寻求“灵丹秘药”。此时,一种名为“中国根”的异域草药进入查理五世的视野,该药主要对付痛风、结石和梅毒。梅毒是16世纪初在欧洲突然出现的传染性疾病,主要在皇家权贵名流圈内传染。对欧洲医生而言,梅毒是一种新型传染病,一时无法对症下药,只能采取传统的方法——汞剂治疗,若用量掌握不好,便会导致患者“生结毒,鼻烂足穿,逐成痼疾,终生不愈”。可怕的症状和疾病传播方式的特殊性,梅毒一时被“污名化”,让患者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锁。后来,医生运用北美输入的愈苍木和菝葜等草本药物治疗,有些医生采纳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从东方带回的“中国根”,煎制成汤剂让患者服食,有效地对付梅毒。

手绘的土茯苓插图
“中国根”在民间流传已近10年,口碑甚好。此时,西班牙贵族竭力向查理五世推荐此药,认为它比御医们常用的愈苍木疗效要好许多,查理五世对“中国根”抱有极高的期望,特命维萨里按宫廷医规配制汤剂,按时饮服,深信其效;不仅如此,查理五世还亲自颁发药物许可证,让“中国根”进入正规流通渠道。
“中国根”是医用拉丁文Radicis Chynæ的译名,它的中文学名是“土茯苓”,中文医籍第一次出现“土茯苓”的名称是在1522年出版的《续医说》,专用于治疗梅毒。1525年,土茯苓被引入欧洲,其功能是促进排汗和排尿,与西方体液医学理论正好契合。1535年在欧洲成为治疗梅毒的特效药,但主流医生并不十分了解,也不愿接受这种来自异域的新药物,同时代的西方药物学著作中未见提到土茯苓。当欧洲诸国王室的御医和显贵的医疗顾问获知“中国根”得到了皇帝的青睐和许可后,一时趋之若鹜,纷纷向维萨里咨询“中国根”的泡制方法和治疗方案。1546年1月比利时御医多米努斯致信维萨里,询问“中国根”的情况,在1546年6月13日这天,维萨里开始给多米努斯父子写回信,这封写在精美的羊皮纸上,信长达60页,花了他两周的时间,在信中维萨里解答“中国根”的问题并对西尔维乌斯的批评做出回应。
欧洲名医笔下的“土茯苓”
维萨里写的“中国根”内容,与其说是一封书信,还不如说是一篇严谨的科学论文,内容包括:学术名称的甄别,药物进入欧洲的来龙去脉、植物特征与特性、炮制方式、治疗方案以及与其他相关药物的比较,维萨里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临床案例对土茯苓的疗效做了科学分析。成功地示范了如何科学地观察研究“新事物”,客观地评估“新药”的效果和价值。
1536年,维萨里在威尼斯作临床实习生时,亲历了“中国根”引进的过程,他切身体会到当地医生对“中国根”的热情与期望。据维萨里考证,土茯苓在欧洲有多种称呼:“Chyna”“Chynna”“Cyna ”“Echina ”或者“Achyna”, 维萨里则简称之为“Chynæ”。16世纪欧洲流行的“中国根”是葡萄牙商人通过海路带回的,因此欧洲人就将“中国根”与海和海员联系起来,甚至认为该植物是长在海边沙滩上的。维萨里则从欧洲的商业贸易路径上考察,认为土茯苓可能来自印度或是美洲新大陆。在信中他仔细描述了“中国根”的形态:巨大、粗糙、参差不齐的碎片,质地上更像木质,“长得很像真菌”。土茯苓是根块状的物质,“新鲜的根多汁”,运到欧洲后的土茯苓干燥有虫。维萨里很清楚“中国根”(土茯苓)与美洲的菝葜属性相近,但还是略有不同。这一认知与16世纪中国的本草界将 “土茯苓”“菝葜”和“萆薢”混为一谈的情况相近。
书信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如何炮制“中国根”,维萨里手中有一份意大利文的炮制法和一份片段的西班牙文方子,他将其译成拉丁文介绍给他的朋友。
“每天取24盎司的土茯苓,分为24份做成新鲜的汤剂。药材要提前一天准备,切割成小块,切得越细小越好,然后注入少许水浸泡,第二天再煮。将土茯苓和浸泡的水放进新锅里,再倒三壶泉水进去,煮沸之,直到水蒸发掉1/3。锅的开口要确保蒸煮的药汤不会溢出,还要盖上盖子以免汤汁溢出。一旦药汤煮好,便要从火上移开,然后用大毛巾盖住保温。药汤要每天要炮制新鲜的,否则,时间长了药剂就会变酸。如若病人服药后,未能产生作用,在每份水里加入1/2盎司的芹菜根和中国根一起煮。”
如何饮服“中国根”?欧洲医生制定了严格的方案,首先,医生会因人而宜地确定医嘱。该疗程分为前、中和后三个阶段执行,服药前先清肠,第一阶段24天,早晨空腹饮用后要卧床两小时,静待发汗,注意避风;第二阶段减量,再服8天左右,若效果不佳的话,则继续服24天,第三阶段清肠。患者因梅毒身体有溃疡,或痛风产生的疼痛,可用浸润药剂的毛巾敷贴,也可用药剂清洗痛处。服药期间,患者还要遵守各种规则,有诸多食品和生活方式的禁忌。比如,不能有性生活,不能吃鱼,减少外出,在室内作适当运动,出门一定要避风保暖,回屋后即敷上药浸毛巾等。
维萨里对土茯苓的处理和饮用,从今天的角度看与中国医学的治疗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否能说明当时的西医受到了中医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证实。考虑到16世纪的欧洲,西方医学处在古典的体液学阶段,草本药材的使用,排汗、利尿的医疗方案基本符合那个时代的医学理念,但从当时药物学书籍和医生经验的考察,这个来自异域的药材——“中国根”——炮制和使用,则是新方法和新技术。事实上,对“中国根”的使用效果,当时的医生褒贬不一。在书信中,维萨里通过在安特卫普亲见两个失败案例,对土茯苓的疗效做出了解释,他表示当时患者病入膏肓,医生根本无法救治,医疗失败并非土茯苓的缘故。
“中国根”为西医创新辩护
维萨里的信,从科学角度对土茯苓的临床应用做了全面阐述,类似“中国根”的说明与临床使用指导。很快,此信就以抄本的形式在比利时医学生手中流传开来,维萨里的弟弟从朋友处获得一份抄本,发给瑞士出版商,1546年8月书信集在瑞士出版。尽管“中国根”的部分只占全书1/5篇幅,主体内容是维萨里阐释他在《人体之构造》中未尽之思想,反驳西尔维乌斯关于盖伦不会有错的观点,但最终出版时却定名为《中国根书简》。土茯苓与人体解剖学两者间风马牛不相及,为何维萨里要将两部分内容合在一起,且最终选择“中国根”作为书名?维萨里的弟弟在序言中代其作了解答。
“该书收入一种新药,尤其是中国根药剂的炮制法,以及其他一些药物,同时附加了解释,这很容易让追求真理的信徒思考盖伦的学术,这位著名的解剖学家教授,他并没有解剖人,只是描述许多人与动物不同处。”
“追求真理”是《中国根书简》的核心价值所在,显然,维萨里想通过解读新药“中国根”的方法为自己反盖伦经典、创建自己的新观点作辩护。正如后来研究者的评论:“在同一封信里他讨论中国根,同时又对盖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因为他受到了不信任权威而相信科学解释的启发。”
维萨里是西方医学由古典向近代医学转型的领路人,《中国根书简》记录了他与盖伦和以西尔维乌斯为首的盖伦信徒间的新学——科学医学——与经典医学之间发生的学术争执。 在这场“新”与“旧”的直接较量中,新药“中国根”起到了药引子的作用,催化了科学新思想的产生。维萨里在“中国根”的最后部分讨论了解剖学与药物学之间的关系:“那些认为手与医疗工作无关的人的判断是非常扭曲的……就好像一位被认为是真正的医生的人最终会成为一名医生;如果一个人在医学的某一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他就会对其他的医学知识产生抵触情绪。”
《中国根书简》正确地示范了什么是科学的方法和思维,如何展开对旧理论的批评和接受新事物。首先,科学的态度与认知,面对世人对土茯苓的追捧,维萨里清楚这是因为皇帝背书“中国根”的效应,对此,他指出查理五世饮服“中国根”是他自己的决定,并非来自医生的建议,言下之意查理对土茯苓疗效的吹捧,完全基于他个人的经验,不代表医生的专业意见。他的批评直指跟风的医生,“以专家身份跟随在王子们的后面,在公开的场合享受到人们的赞扬,而把自己的研究远远抛在脑后。”维萨里既反感医生追随权贵的风气,又反对盲目相信学术权威。其二,以观察和实证的方法,重新检视古典学术的内容,在《人体之构造》中,维萨里认识到自己最初是“盲目相信”盖伦的结论,他对科学真理的认识与发现是通过观察、亲手解剖、准确绘制和阅读比较盖伦的著作,逐步建立起来的。他通过调查、分析和比较的实证方法阐释了新药“中国根”的真实效果;他坚持人体解剖,描述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身体结构,以事实批评盖伦的错误。其三,欧洲医学界信奉希波克拉底所谓“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但长期以来,是维萨里第一个将解剖学与临床医学的相关性做了解释。其四,如何对待“新”知识、方法和新药物。维萨里信中说自己是第一个通过对真相调查而对盖伦学说提出挑战的青年人,相信同时代博学者们会为后生超越的努力而骄傲。
《中国根书简》是第一部,并且唯一部以土茯苓的研究并命名的西文专著,1546年拉丁文第一版在瑞士巴塞尔出版,从1546至2015年,该著作共计出版13个版本,语言涉及拉丁语、法文、荷兰语、德文、西班牙文、英文,有完整的译文、也有碎片,或者只译了第一部分。有意思的是大部分再版或译文只有“中国根”部分,而没有解剖学的内容。尤其是在17—18世纪,《中国根书简》的译本主要是用以指导土茯苓治疗梅毒。
如果说,维萨里以《人体之构造》向盖伦学派的古典医学发起挑战,那么,《中国根书简》就是通过对“中国根”的分析与研究,深化对盖伦解剖学的批评,创建了医学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将西方医学从古典领进了文艺复兴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