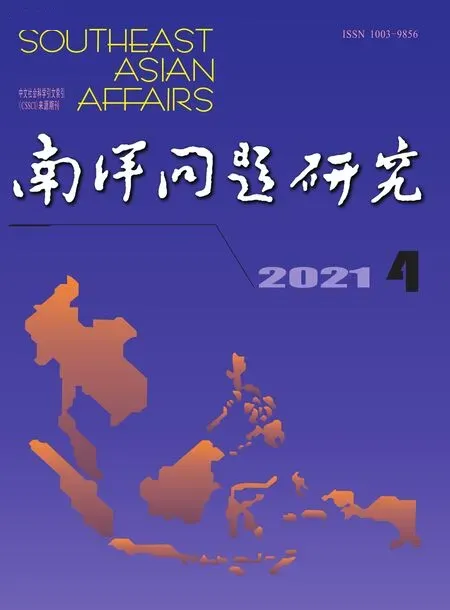南海生态环境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角色
任远喆,王 晶
(外交学院 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北京 100037;同济大学 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92)
近年来,全球海洋安全研究的议题不断扩展,国际上相关的学术讨论也日益丰富。英国知名的国际问题类期刊《国际事务》相继刊发了多篇文章,讨论海洋安全研究新议程。这组文章共同呼吁,除了有关海权和海洋治理法律结构的传统议题,海洋安全亟需关注不同威胁和议题之间的连通性,海洋治理和海上秩序的新样式,以及通过国家海洋能力建设实现的安全议题扩散。[1]长期以来,关于海权兴衰等传统安全议题一直占据学术争鸣的主导地位,如今越来越多的海上非传统安全议题业已进入核心议程。
这一研究趋向在南海问题上亦有鲜明体现。在南海地区岛礁主权归属、主张海域重叠、海洋资源分配等传统争端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下愈演愈烈的今日,海上非传统安全议题的牵引作用和溢出效应日益凸显。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已展开较为广泛的讨论。[2]这些研究大体可以归为3类。一是议题导向,就南海地区存在的海盗、环境污染、非法捕鱼、海上偷渡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进行详细梳理、归类和分析,或聚焦某一议题或框定多个议题,并就这些问题的解决出路进行探讨。总的趋势来看,海盗、海上走私等传统跨国犯罪问题受到的关注程度一直较高,而对于海洋环保、非法捕鱼等议题的讨论也日益增多。[3]二是制度导向,侧重从功能主义出发,在海上非传统安全议题讨论的基础上,对多边合作和制度建设进行探索,涉及机制拥堵、机制协调与地区制度构建等方方面面。这已成为国内南海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中国在推进南海合作中一直坚持朝着机制建设方向努力。该方面研究既有南海非传统安全整体机制的探讨,也有就不同议题机制建设的分析。[4]非传统安全方面的规则、规范与制度建设无疑已经成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南海地区海洋治理的关键。[5]总体上,在南海地区难以形成统一的安全机制和行动规范的背景下,非传统安全机制建设无疑成为了“试金石”和“推进剂”。三是效果导向,着重分析中国在海上非传统安全中的政策主张和实践特点,探讨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于中国拉近同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南海当事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有学者强调在广泛的海洋合作机制仍然无法建立的情况下,可借助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适度缓解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的传统安全困境、促进政治层面的国家间信任措施的建立以及危机预防管控机制的良性运作。[6]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之后,也有学者将与东南亚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视为经济和软实力之外中国运用的第三种策略,但认为其效果有限。[7]
最近几年,生态环境保护议题在中国南海政策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加凸显。在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非法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以及2016年7月12日仲裁庭发布的“最终裁决”中,涉及了渔业捕捞产生的环境影响、岛礁建设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环境影响评价这三大法律争议点。“南海仲裁案”海洋环保问题的多层面议题,折射出南海海洋环境治理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长期面临的困境。[8]此后,一些国外学者开始以中国的海上活动破坏了南海环境为由炒作指责,注脚新一轮“中国威胁论”。[9]尤其是不少美国研究机构和媒体近年来明显加强了以南海生态环境安全为借口,大肆宣扬“环境破坏论”“渔业资源枯竭论”等,对中国的形象进行抹黑。[10]可见,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南海非传统安全的关键议题,既是各国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成为海上博弈的焦点所在。近年来,围绕这一议题建立的合作机制尽管数量不少,但是成效难言显著。尽管如此,中国始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南海地区生态环境合作与机制建设既是化解当前南海地区合作僵局的有利抓手,更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鉴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当前南海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状况,分析现有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面临障碍,明确中国在其中的定位和角色,并思考未来南海地区生态环境机制的发展路径。
一、南海地区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挑战
南海对于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平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全球最大的大型海洋生态系统,是浅海热带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区域,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多样性程度最高的浅水海洋。[11]南海拥有着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和上升流等典型生态系统。倘若南海的海洋环境遭到破坏,会导致包括多种珍稀生物在内的大范围生物死亡,浅海热带生物多样性将会因此撕开缺口,随之带来的是全球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打破,食物和药物供应安全受到冲击,进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南海周边国家需要在环境保护方面践行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后代的利益着想。[12]
当前,对于海洋环境保护涵盖的范畴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海洋环境保护涵盖了与环境安全相关的议题,既包括保护海洋资源免于受到非法捕鱼或污染的侵害,也包括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挑战。海洋环保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的安全等其他向度密不可分。[1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条第4款将“海洋环境的污染”定义为:“人类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其中包括河口湾,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类健康、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损坏海水使用质量和减损环境优美等有害影响。”[14]根据这一普遍定义,结合南海的地质特征,可从空间及污染原因等角度将南海生态问题分为气源、陆源和海源3类。
(一)气源问题:由气候变化导致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统计数据显示(如图1),全球陆海年平均温度自1977年以来异常升高。大气层对海洋生态的影响主要是由温室效应引起的,直接影响为海水酸度、温度和海平面均升高三项,间接影响体现在南海地区主要包括以下4项:
第一,南海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型海洋生态系统,有硅藻和甲藻等浮游植物486种,桡足类和水母类等浮游动物505种,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等大型底栖生物972种,[15]海水温度升高导致一些对温度敏感的生物死去,其中便包括对海洋生态极为重要的造礁珊瑚,珊瑚礁出现“白化”现象,许多以珊瑚礁为栖息地的生物相继死亡。
第二,贝类、螺类、珊瑚等生物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海水酸度升高使碳酸钙溶解,温度升高加快溶解速率,抑制生物生长,甚至会造成珊瑚格架坍塌,一些以贝类、螺类为食物或者以珊瑚礁为栖息地的其他生物进而受到影响。海洋生物是粮食和药物的来源之一,人类生存与海洋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
第三,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促进了光合作用,藻类生物生长迅猛,藻华减少了水下光照度,抑制其他海洋植物生长,藻华死亡腐败大量消耗氧气,导致海洋动物窒息死亡,部分藻类产生藻毒素,通过食物链传递,可能造成麻痹性贝毒中毒等事件,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16]
第四,海平面上升使得一些岛礁被淹没。有学者预计印度尼西亚将于2030年失去2000个小岛。[17]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领海宽度从基线量起不超过12海里”的规定,海洋权益争端可能由此激化。海平面上升还会加快海岸带侵蚀,造成海岸带脆弱。

图1 1880—2020全球陆海温度异常统计图
(二)陆源问题:由人类活动导致
人类对渔业资源和油气资源的不科学、不合理开发,将处理未达标甚至未经处理的垃圾排入南海,以及频发的交通事故,是主要的陆源污染。
一是酷渔滥捕。南海约有2300余种渔业资源,是其沿海77%人口的蛋白质和工作收入来源。[18]有评论家指出:“南海争端实际上是争夺渔业资源,而非石油天然气。”[19]酷渔滥捕造成渔业资源锐减、失业人口增加。部分失业人口可能被海盗、恐怖主义组织、贩毒团伙招募,实施海上跨国犯罪活动,从事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IUUF)。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国际劳工组织(ILO)与欧洲海事分析和行动中心(MAOC-N)统计,IUUF本身与毒品贩运、人口贩运、现代奴隶制和恐怖团体有广泛联系。[20]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规定,IUUF不仅涵盖公海地区,也包括主权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地区。[21]为了限制IUUF,南海沿岸所有国家都颁布了相关的法律和条例,但是在主权争议海域难以界定IUUF,因此为IUUF的限制带来了挑战。
南海沿岸国家过度捕捞是渔场趋于枯竭的重要原因。如图2所示,中国的人均渔获量是最小的,菲律宾约为中国的2倍,越南约为中国的3倍,马来西亚约为中国的4倍,印度尼西亚约为中国的6倍。虽然均值上文莱比中国略高,但是近年文莱的人均渔获量飞涨,从2016年起,每年约为中国的3倍。

图2 南海各国2008—2018年人均渔获量统计图
二是能源开发。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估计,南海拥有约190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和110亿桶石油;而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估计,南海拥有约160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和120亿桶石油。[22]因此,南海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是海上石油开采的密集区域,也是溢油事故的多发区域。在我国因海洋石油开采引起的41起溢油事故中,有22起发生在南海。[23]
欧洲空间局(ESA)公布了图3新加坡东北部海域、图4马来西亚东海岸附近海域和图5婆罗洲西海岸附近海域的遥感图像,图中深色条纹是浮油污染。我国每年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状况公报》也测量了南海海域石油类污染物年受纳总量。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南海海域石油类污染物受纳总量为89.7吨。[24]

图3 新加坡东北部 图4 马来西亚东海岸 图5 婆罗洲西海岸
三是垃圾排放。由于海域广袤,南海成为“天然垃圾场”,单是2020年1年,排入南海的污水量就高达136,019万吨,石油类污染物89.7吨,氨氮污染物1373吨,总氮污染物10,281吨,总磷污染物794吨。[25]
对于因人为排放垃圾造成海洋污染的后果,历史上有过惨重教训。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西方国家曾将索马里海岸用作垃圾倾倒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计算:“这样清除有毒垃圾的成本非常低廉,由每吨670英镑降至1.70英镑。”2005年海啸导致有毒物质漂上海滩,造成了数千名索马里人病倒、数百人直接死亡的惨剧。[26]南海周边国家应吸取教训,停止将未处理或处理未达标的垃圾排入南海。
四是交通事故。南海是欧洲—东亚航线的必经海域,是非洲供应商与亚洲市场间的最短航线,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中转站之一。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全球有超过30%的海洋原油航运经过南海,约1500万桶/天。此外,约140万桶/天的原油在途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的海峡时进行精炼,以石油产品的形式经过南海。[27]由于过往船舶众多,南海及附近海域频发交通事故:2004年,巴拿马籍“现代开拓”号与德国籍“地中海伊伦娜”号两艘集装箱轮船相撞,导致后者燃油外溢;[28]2008年,韩国籍货轮“宙斯”号翻沉溢油;[29]2009年,巴拿马籍“圣狄”号搁浅;[30]2012年,韩国籍化学品船舶沉没;[31]同年新加坡籍“达飞巴莱利”号搁浅;[32]2014年,一艘沥青船在南海发生泄漏事故;[33]同年“茉莉快乐”号船发生油污泄漏。[34]这些船舶事故导致大量污染物输入南海,对南海生态造成了严重后果。
(三)海源问题:由地质条件导致
南海既是半闭海,又是边缘海。作为半闭海,海水交换速率较慢,导致污染积聚;作为边缘海,海床陆壳较薄,导致海岸带脆弱。
其一,作为半闭海,水体交换速率慢导致污染积聚问题。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6年第4期会议)认为,由于闭海、半闭海面积小且与邻接海的水体交换条件差,遭受各类污染的危险日益严重。[35]半闭海性质决定了南海污染易长时间积聚,造成愈演愈烈的海洋生态问题。
最新数据显示,在南海的70个入海河流国控断面中,水质断面一类0个,二类24个,三类31个,四类12个,五类2个,劣五类1个。化学需氧量、总磷及氨氮不同程度超标。[36]截止2019年5月,南海海面漂浮微塑料密度高达1.8×108个/km3。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海洋研究中心认为,海洋微塑料只有1%漂浮在海表,99%处于深海之中。[37]因此南海可能存在比海面漂浮微塑料更严重的底栖塑料堆积问题。这些污染物质的积聚使南海生态进一步恶化。
其二,作为边缘海,陆壳薄导致海岸带脆弱问题。边缘海的陆壳较薄,在海水的侵蚀作用下,海岸带易出现不同程度的侵蚀现象。海岸带是海陆交互作用的地带,对陆地和海洋均能产生影响,因此同时会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海岸带主要有防淤积和防冲刷两大地质作用,受到侵蚀后,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海岸带的生态承载力明显下降;海水的自净能力下降,水质恶化;珊瑚群落白化、海草床草场面积减少、红树林植株稀疏矮小;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船舶航行、养殖业以及旅游业可能会受到影响。
二、南海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历程与现有机制
南海生态环境保护政府间合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74年启动了针对全球闭海和半闭海的“区域海洋项目”(Regional Seas Program),其中的“东亚海洋行动计划”(The East Asian Seas Action Plan)涵盖了南海生态环境保护。不过,该计划主要由以国家主导的小型研究项目构成,反映出此时的南海生态环境保护带有零星、自发性和利己主义的特点。直到90年代,南海地区才出现系统性和切实的海上合作。[38]2002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下称《宣言》)对包括海洋环保在内的低敏感领域合作做出了相关规定,各方不断落实《宣言》的重要体现就是开展各个层次的生态环保合作。从范围来看,迄今为止的海上生态环保合作机制横跨全球、区域和双边等各个层面,参与主体包括国际组织、相关国家官方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涉及议题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海洋防灾减灾、海洋资料交换等方方面面。已有的重要合作机制如下:

表1 重要的全球机制

表2 重要的区域机制

表3 重要的双边机制
构建南海海洋环境合作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形成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合作机制。[39]上述合作机制的发展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于应对南海生态环境挑战的多方尝试,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相关难题。然而,南海地区迄今并未建立起规制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的专门组织,也尚未形成具有拘束力的区域性公约或协定,而是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40]对于环境治理上的“碎片化”问题,学界早有研究。[41]这里的“碎片化”是指南海生态环境机制主体的多中心化、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例如,从上表可以看出,现有的合作机制大体可以分为国际机构推动、东盟和地区国家联合推动以及中国与南海相关国家双边推动三类。国际机构推动下的机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全球环境基金共同发起题为“扭转南中国海及泰国湾环境退化趋势”的项目。这是由南中国海周边七国——中国、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共同发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织实施,全球环境基金提供资助的海洋环境保护大型区域合作项目,内容包括红树林、珊瑚礁、海草、湿地、渔业资源与陆源污染控制六大领域,项目旨在摸清南海现有生态环境资源及其污染破坏程度,找出海洋环境污染与破坏的原因,制定一系列海洋与海岸带环境、生态保护行动计划。通过该项目,各参与国之间协调行动,使南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得到可持续协调发展。在最初合作中,参与国的科学家们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联合行动,项目进展顺利。然而之后不久,中国和东盟国家出于不同的政治考量放慢了合作进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主要的战略就是促使环境合作“去政治化”,并在其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然而,南海地区的环保合作从来都不仅是单纯的技术和环保议题。[42]
总的来看,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合作机制,其推进速度和治理成效都不太尽如人意,普遍存在“议而不决,决而难行”的问题。如今,南海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未根本扭转。该地区每10年就会失去30%的海草床、16%的红树林和16%的活珊瑚。[43]自然环境演变和人类活动导致的南海生态环境挑战日益增多。更令人担忧的是,受南海地区局势起伏的影响,各国之间原有的积极合作势头也有所减缓,合作机制存在的缺陷暴露无遗。
三、南海生态环境机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障碍
如前文所述,尽管经过多年努力,南海生态环境合作机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了域内外国家针对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经常性交流与对话,形成了合作的习惯,提升了合作意愿,但是机制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4个方面的主要障碍:
(一)现有合作机制效果不佳
区域性法律和合作机制的缺失,客观上影响了各国在海洋环保方面的合作效果。[44]一直以来,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有效性饱受质疑。现有合作机制虽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但功能重合度高,彼此之间缺乏协调,机制的有效性和行动效率很低,达成的协议很少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诸多一轨半和二轨机制并没有形成可以影响政策制定的成果,没有真正实现机制设置和建立的初衷。[45]尽管从全球到双边,南海地区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机制林林总总将近几十个,但是大部分机制比较松散,缺乏约束力,缺少充分的法律支撑和完善的机构设置,机制的定位比较模糊,功能也多有交叉,权责不够明晰,因而可持续性往往不足。
就区域合作机制而言,亚太经合组织等机制虽设立了海洋和渔业工作小组,但是缺乏对海洋环境与油气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监督机制,无法监测和反馈海洋环境的实际治理效果,也没有明确的应对争端解决机制,当成员国之间就海洋环境保护发生利益冲突时,无法给出妥善的解决方案。东盟国家在南海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一方面在资金和技术上存在不足,措施执行乏力;另一方面域外大国的介入导致相关合作日趋复杂化。除此之外,由于缺少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不同区域机制的目标和任务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这样的重叠既浪费参与国有限的资源,也会损耗南海生态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就双边合作机制而言,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一些双边协定的“点对点”式方案无助于解决南海生态环境危机。[46]目前所达成的合作协定大多仅适用于非争议水域,并且绝大部分是以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存在,其约束力极其微弱。除此之外,双边合作大多是针对油气资源开发所达成的,着眼于生态治理的极其有限。
除此之外,现有机制的法律约束力也十分有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国际防止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使用的是根据“各国良好意愿”和“国内立法情况”等措辞,加之南海周边国家以“选择性定位”“选择性加入”以上各项全球性公约,致使这些公约对于维护南海生态环境和维持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软约束”再次大打折扣。
(二)互信缺失导致各国难以协调一致
国际关系中信任的缺失普遍存在,这在东亚地区体现得尤为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东亚一体化进程和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47]更何况南海问题涉及到领土归属、海域划分等敏感议题,“信任赤字”体现得尤为明显。南海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一直面临着互信缺失的掣肘。美国海洋法学家马克·瓦伦西亚(Mark J. Valencia)早就指出,“南海地区多边海洋管理体系建立的最大障碍是领土主权归属和海域划分的冲突以及一些当事国之间互信的缺乏。解决或搁置管辖海域争端或许是促成其他方面问题达成合作的先决条件。”[48]澳大利亚退役海军准将沃尔特·塞缪尔·贝特曼(Walter Samuel Bateman)也提出互信缺失是南海地区环境保护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即便是在渔业管理、海洋环境保护这些建立互信的重要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没有互信,合作寸步难行。”[49]
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普遍遭遇“安全化”和“政治化”。南海地区主权争端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进一步增加了南海地区生态环境合作的复杂性和达成一致的难度,一些国家加大力度将环保议题“政治化”,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一些环境保护举措污名为“寻求海上的扩张”。例如中国一年一度在南海相关海域实施伏季休渔制度,就往往遭到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指摘。而这是中方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权利、履行相关国际义务的正当举措,有利于南海渔业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南海周边国家出于保障国内渔业供给的需要,激化了在渔业问题上的紧张态势。[50]对于中国采取的“碧海2020”等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也有人将其解读为“是中国更广泛的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实际控制争议海域,将其主张合法化”。[51]
(三)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和干扰
近年来,美国南海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介入南海问题的程度不断加深,对海上合作的破坏性也日趋加大。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更多地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法主张和维权行动视为对美国区域军事存在的直接挑战,甚至视为对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的破坏。[52]2019年以来,美国借口中国在南海地区进行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开始派遣海岸警卫队等准军事力量到南海活动。这是美国对南海地区的“灰色地带”策略的重要方式。[53]多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一直向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南海沿岸国提供装备,开展培训和联合训练,保持紧密联系,增强力量投射。打着渔业执法合作的旗号,以新的手法介入南海事务,对冲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挑战中国在南海的固有权利和主张,可能是今后美国政府南海政策的重要选项。[54]美国还不断炒作中国在各大洋所谓“非法捕鱼”活动,并强调要与沿岸国开展合作,以更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打击非法捕鱼。这些行动势必对各国的渔业以及其他方面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带来冲击。
不仅如此,2020年7月13日,美国时任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Michael R. Pompeo)就南海问题发表了政策声明,这意味着美国今后的南海政策从“选择性干预”到“全面性干预”的战略转变。[55]美国已经成为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地区稳定的最大障碍,为南海地区合作制造了重重障碍。2020年,美国等域外国家舰机更是多次非法闯入中国领海及有关岛礁邻近海空域,单是美国开展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就多达九次,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合作的良好势头,弱化了南海生态环境合作的势头。一些智库不断炒作中国利用“疫情”扩大在南海地区的优势,并妄称中国在南海的活动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认为中国全然不顾这一领域的国际规则,损害了自然资源的管理。[56]这些恶意挑拨和单方设限都为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蒙上了阴影。
(四)政策对接和管理协同难度较大
一直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由于涉及领域广,介入部门多,机制性合作的实施需要各国国内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同样要求与各国国内法相一致,普遍存在各国国内立法错位和对接不畅的问题。[57]在南海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这一困境也有所体现。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各国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政策重点有很大差异,甚至相互矛盾。例如,尽管南海周边国家在生态系统保护和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和执行高度集中,都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但是涵盖范围和侧重点则有所不同。如针对南海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海草床,南海周边国家仅有印尼和马来西亚有专门的立法保护,而对于珊瑚礁的特别立法则被普遍忽视。总的来看,南海周边国家在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要优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58]这使得在南海“争议水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执法难以统一。
另一方面,南海周边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的能力建设方面并不均衡,在合作议题排序、资源投入等方面差异较大。中国倾向于搭建起涵盖各个领域、拥有多项制度安排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合作架构,而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和多边非传统安全合作具有注重单一问题领域(例如反海盗等)而不追求多领域综合合作及能力有限的特点。[59]近年来,东盟各国为保护海洋环境纷纷设立海洋保护区,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和机制保障,海洋保护区仅有10%—20%得到有效管理。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海洋保护区数量迅速增长。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建立271个海洋保护区,大多分布在近海,总面积约12.4万平方公里,占管辖海域面积的4.1%。[60]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已在重要海域开展大量监测、科研及保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海洋保护区的有效管理远远超出东盟相关国家的能力。管理模式和管理能力的巨大差别,导致南海生态环境合作协调不易。
四、南海生态环境合作中的中国角色
中国是最早进行海洋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也是在海洋环保领域投入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非常重视南海地区生态环境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参与了现有几乎所有合作机制,针对南海生态合作存在的障碍,中国从理念贡献、产品供给和制度设计等方面发挥着负责任的大国作用。
(一)合作理念贡献者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安全维护、海洋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绩,并提出了要建设“海洋经济发达、海洋科技先进、海洋生态健康、海洋安全稳定、海洋管控有力的新型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内涵应该包括认知海洋、利用海洋、生态海洋、管控海洋、和谐海洋等五个方面”。[61]这5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对于海洋资源、海洋能力和人海关系的全面认识。其中综合管控,建设生态海洋既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参与国际海洋环保合作的指导思想。在2017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海洋大会会议上,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与各国、各国际组织积极构建开放包容、具体务实、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海洋面临的挑战”。[62]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面向世界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海洋领域的生动体现,反映了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价值追求,也为推动新形势下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海洋指明了方向。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含义和价值目标可以分为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5个维度。其中,在生态上的目标是通过保护海洋环境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系统,实现“和谐海洋”理念倡导的人海合一目标,进而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目标。[63]生态海洋、蓝色伙伴关系、海洋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从中国自身的海洋生态建设、到与伙伴共同维护海洋生态、再到建立全球海洋生态治理体系3个层次,为南海生态环境机制构建提供了思想引领。
(二)公共产品提供者
2011年,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启动了中国—东盟环保合作论坛,同年设立了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基金支持建立海洋科学研究、环境保护方面的专家小组,也推动了多项海洋环保方面的务实合作。2012年和2016年,中国先后颁布了《南海及周边海洋国家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2015)》、《南海及周边海洋国家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6—2020)》,得到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已牵头组织发起并实施了30多个合作项目;向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提供了4个海洋观测站的仪器设备和环境预报系统。中方开展的东南亚海洋环境预报及减灾系统等项目,为南海及周边国家提供海洋环境预报公益服务。[64]此外,中国和印尼共同建立了海洋与气候联合研究中心和海洋联合观测站,和泰国共同建立了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与马来西亚、柬埔寨分别建立了联合海洋观测站,与越南开展了“北部湾海洋环境管理与保护合作”等项目,起到了增信释疑、维护稳定的作用。[65]海上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充分体现在了中国参与南海生态环境合作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缩小南海各国海洋能力建设的差距,提升了政策对接和管理协同的程度。
(三)机制建设引领者
长期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南海生态环境保护的机制建设,将其视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海上合作的长期保障,近年来不断提出机制建设的新主张。在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呼吁借鉴与南海相似的其他闭海或半闭海地区沿岸国合作机制,在南海建立沿岸国合作机制。“在防灾减灾、海上搜救、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安全等领域进行具体的、务实的、机制化的合作”。“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如能成功构建,将有效整合目前已呈“碎片化”的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机制。[66]原外交部边海司司长易先良也表示,在构建开放性的南海区域合作机制过程中,要以开展海洋生态和环保合作为范例,推动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加强地区国家渔业政策协调、资源养护及海洋联合科考合作等。[67]
在2017年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中国强调要面向东南亚国家和南海地区,建立中国—东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与行动计划框架下,推动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合作。2017年11月13日,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了《未来十年南海海岸和海洋环保宣言(2017—2027)》,强调“南海当前的情况要求有关各方共同行动起来,才能保护海上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这体现出南海周边国家共同打造整体性海洋环保机制的信心和决心。此外,中国还与东盟国家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等多边合作机制中,开展具体的环保合作,引导区域合作方向。
当前中国与东盟正在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并就单一磋商文本达成一致。“准则”的最终达成将为南海地区的长治久安提供规则支撑。在“准则”中也包括海洋环境保护等很多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具体议题。中国与相关国家可以将南海环保合作的机制构建纳入“准则”谈判的诸多方案之中,为在其他敏感领域达成共识开个好头。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会分论坛上,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海洋可持续发展方兴未艾,推动蓝色经济合作成为国际潮流,中国积极开展海洋生态保护、科技创新、防灾减灾等领域国际合作,正同东盟探讨建立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中方愿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同各方积极开展蓝色经济合作,共同抢抓发展先机。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他认为,“有关争端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聚焦功能性领域的合作,推进南海生态环境、航道安全、渔业资源保护等议题的治理与合作。特别是针对资源衰竭和生物多样性退化、海洋塑料垃圾等区域性挑战,沿岸各国可借鉴世界其他地区海洋治理的成功经验,协商签订‘南海环保公约’,建立促进南海可持续发展、打造蓝色伙伴关系的制度性机制。”未来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的建立无疑将涵盖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诸多内容,“南海环保公约”等新倡议也为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尝试。
当然,尽管中国始终不懈地推动南海生态环境的机制化建设,尽力克服相关障碍,形成南海合作的早期收获,但伴随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和地缘博弈的加剧,南海进入新一轮的动荡期,美国等域外大国的不断介入干扰,一些南海周边国家以巩固既得利益为导向的单边行动持续增多,区域生态环境合作出现了“进一步、退两步”的状况,弱化了已有的合作成果。原本应与中国一起成为“双引擎”的东盟国家受限于协商一致的议事规则和自身能力的不足,并未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海洋环保地区规则,单独或与中国联合发布的官方声明呈现软约束和“碎片化”的特点,签署的一些合作计划并未真正落实。这些因素都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角色的提升。
五、南海生态环境机制建设的前景
当前南海地区秩序正处在转型过渡期,海上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但总体上稳定可控。解决南海环保挑战的急迫性不断上升,各国对南海生态环境合作和机制建设仍有巨大的需求和持续的动力。特别是在南海传统安全矛盾难以调和并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海上生态环境合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不可替代。未来南海生态环境机制建设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一)在广泛借鉴的基础上突出区域特色
不少人主张应该在南海地区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方面更多地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世界上有闭海、半闭海合作的大量实践。我们可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加强研究、深入探讨,为南海合作提供有益借鉴。”[68]例如,可以综合并借鉴北极理事会的模式与经验,设立南海合作理事会,推动南海地区的合作与发展。亦有人提出可学习地中海区域的合作实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地中海有着复杂的地质地理环境和极具差异化的沿岸国家,几乎体现了半闭海区域海洋合作可能包括的所有问题,在海洋生物资源管理、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有成功的经验。[69]还可依托国际组织,展开环保专项治理。南海沿岸国可以探讨在国际海事组织的支持下,建立地区性合作机制,以预防船舶和航行造成的南海污染。[70]新加坡智库建议南海周边国家应建立起海洋环保的地区协同机构,推动沿岸国海警等执法力量合作,共同开展海洋科学研究,并充分动员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等力量。[71]这些讨论都为南海生态环境合作机制的建设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路径。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广泛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南海地区的特殊性。南海区域内各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异很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迥异,利益分歧突出,因而在机制建设中需重点考虑合作目标的可及性、合作途径的适宜性和合作规则的普适性,充分照顾到各方的舒适度,秉持包容性原则,将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合作进程。同时,形成“核心合作机制+辅助性合作机制”的模式,确保生态环境合作的多样多速共进。
(二)通过务实合作不断累积互信
在海上非传统安全机制构建中秉持合作安全观,通过更多的对话合作促进海上安全,增进战略互信,培养起合作的习惯。充分发挥中国与东盟之间不断增强的经济纽带,加强利益融合,推动经济合作势头溢出到海上生态环保领域。2020年疫情期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逆势增长,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全年贸易额6,846亿美元,同比增长6.7%。(1)《2020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简况》,驻东盟使团经济商务处,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01/20210103033653.shtml(登录时间:2021年4月20日)。这大幅提升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合作的信心,强化了合作共赢的基调,也有利于为海上合作营造良好氛围,增进各国的合作意愿。
以务实合作击破将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政治化”“安全化”的图谋。疫情期间,中国与南海相关国家的双边务实合作也取得积极进展。中菲有条不紊地推进落实《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按照“政府对政府、企业对企业”的双轨并行思路稳步商谈南海共同开发。中越依托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和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机制,就同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和南海共同开发等不断深化共识。[72]毫无疑问,这些进展对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发挥了示范效应。
同时,还要在合作中加强各国的法律对接和制度协同。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推进合作项目的契机,将沿线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聚拢在南海环境保护的议题之下,将政策沟通等理念运用于南海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建设中,进一步挖掘已有合作机制相关机构的潜力,为相关合作框架公约和议定书等的执行提供有力支撑。
(三)尽力消减传统安全的负面冲击
未来南海地区在相当长时间里仍将保持紧张态势。美国无疑是背后最大的“推手”。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继续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施压,带动地区局势的持续紧张。与特朗普政府如出一辙,拜登政府仍将南海问题作为“印太战略”的优先事项和关键议题,在进行全面评估后制定新的南海政策。美国务院、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对南海当前态势、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以及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规划进行全面评估后,在数月内形成系统性的战略框架,在延续前任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密集军事行动和威慑施压的同时,具体操作手段更加隐蔽化、集团化、多样化,对地区稳定的冲击更大。除此之外,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也纷纷介入,毫无疑问又增加了南海局势的复杂性,也会影响相关国家推进海上合作的意愿。
对此,既要看到南海局势面临的新挑战,也要善于发掘海上合作的新机遇,努力实现“化危为机”。美国新政府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态度转变还是为包括南海在内的生态环境合作带来了契机。2020年底,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同美国亚洲协会举行视频交流中指出,中美在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保护海洋环境、开发海洋资源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双方可以就此积极探讨并开展合作,围绕海上问题形成中美良性互动,为中美整体关系注入积极因素。拜登政府也已释放出了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与中国合作的意愿。毫无疑问,中美之间在南海环境保护上的合作可以为动荡的南海局势注入不可或缺的正能量,打开一扇南海生态环境合作的新窗口。
注释:
[1]Christian Bueger and Timothy Edmunds, “Beyond Sea Blindness: A New Agenda for Maritime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Affairs, Vol. 93, Issue 6 (2017), p. 1294.
[2]Mely Caballero-Anthony,NegotiatingGovernanceonNon-TraditionalSecurityinSoutheastAsiaandBeyo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85-112; Wu Shicun and Zou Keyuan (eds.),Non-traditionalSecurityIssuesandtheSouthChinaSea:ShapingaNewFrameworkforCooperation, London: Ashgate, 2014, pp. 207-276.
[3]洪农:《论南海地区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基于海盗与海上恐怖主义问题的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1期,第36—52页;李聆群:《南海环保合作路径探析:波罗的海的实践与启示》,《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45—58页;Ahmad A. Amri, “People Smuggling in South East Asia: Trends, Challenges and Way Forward”,AustraliaJournalofMaritimeandOceanAffairs, Vol. 7, No. 2 (2015), pp. 132-151; Elizabeth R. Desombre,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Fisheries”,InternationalAffairs, Vol. 95, Issue 5 (2019), pp. 1019-1035; Katja Lindskov Jacobsen and Jessica Larsen, “Piracy Studies Coming of Age: a Window on the Making of Maritime Intervention Actors”,InternationalAffairs, Vol. 95, Issue 5 (2019), pp. 1037-1054; Wu Shicun and Zou Keyuan (eds.),Non-traditionalSecurityIssuesandtheSouthChinaSea:ShapingaNewFrameworkforCooperation, pp. 207-276.
[4]杜兰、曹群:《关于南海合作机制化建设的探讨》,《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83—95页;李志斐:《南海非传统安全的现状与应对机制分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4期,第69—80页;李忠林:《南海安全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及其解决路径》,《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第77—88页;祁怀高:《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第129—152页。
[5]吴士存、陈相秒:《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4期,第25—36页。
[6]任远喆、刘汉青:《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中国的角色》,《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3期,第80—95页;Li Mingjiang, “China and Maritime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 Vol. 19, Issue 64 (2010), pp. 291-310.
[7]Gong Xu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Indo-Pacific Geopolitics”,InternationalAffairs, Vol. 96, Issue 1 (2020), pp. 29-48.
[8]刘丹:《南海海洋环保合作的困境与出路——兼及对“南海仲裁案”相关仲裁事项的辩驳》,《外交评论》2017年第5期,第115—117页。
[9]Amiel Ian Valdez, “Beyond the Arbitral Ruling: A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Asi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 Vol. 9, Issue 2 (2019), pp. 251-274; Leland Smith,Peter Cornillon,Don Rudnickas and Colleen B.Mouw,“Evidenc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Caused by Chinese Island-Building”,ScientificReports, Vol. 9, No. 5295 (2019), pp. 1-11; Nguyen Chu Hoi and Vu Hai Dang,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gal Obligation and Cooperation Drivers”,InternationalJournalofLawandPublicAdministration, Vol. 1, No. 1 (2016), pp. 8-23.
[10]Abhijit Singh, “A Looming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ugust 12, 2016, https://amti.csis.org/looming-environmental-crisis-south-china-sea/#:~:text=Over%20the%20past%20two%20decades,%2C%20dynamite%2C%20and%20detonating%20cords (登录时间:2020年12月12日); Jackie Northam, “One Result Of China’s Buildup In South China Sea: Environmental Havoc”, September 1, 2016, 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6/09/01/491395715/one-result-of-chinas-buildup-in-south-china-sea-environmental-havoc (登录时间:2020年12月12日); Matthew Southerland, “China’s Island 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amage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mpl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pril 12, 2016,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China's%20Island%20Building%20in%20the%20South%20China%20Sea_0.pdf (登录时间:2020年12月12日); Rachael Bale, “Giant Clam Poaching Wipes Out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July 13, 2016,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6/06/south-china-sea-coral-reef-destruction/#:~:text=More%20than%2040%20square%20miles,new%20analysis%20of%20satellite%20imagery.&text=Carving%20up%20a%20reef%20leaves%20it%20barren%20of%20life (登录时间:2020年12月12日).
[11][19]Amiel Ian Valdze, “Beyond the Arbitral Ruling: A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Asi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 Vol. 9, Issue 2 (2019), pp. 254-257.
[12]Zou Keyuan, “Realizing Sustain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Wu Shicun and Zou Keyuan (eds.),Non-traditionalSecurityIssuesandtheSouthChinaSea:ShapingaNewFrameworkforCooperation, p. 223.
[13]Christian Bueger,Timothy Edmunds and Barry J.Ryan, “Maritime Security: the Uncharted Politics of the Global Sea”,InternationalAffairs, Vol. 95, Issue 5 (2019), pp. 973-974.
[1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汉英),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29页。
[15]《2018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9年5月29日,http://www.mee.gov.cn/ywdt/tpxw/201905/t20190529_704840.shtml(登录时间:2020年3月30日)。
[16]于仁成等:《中国近海有害藻华研究现状与展望》,《海洋与湖沼》2020年第4期,第774页。
[17]Robin Warner, “The Portents of Changing Climate: Maritime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in Wu Shicun and Zou Keyuan (eds.),Non-traditionalSecurityIssuesandtheSouthChinaSea:ShapingaNewFrameworkforCooperation, p. 247.
[18]Jianwei Li and Ramses Amer, “Closing the Net Against IUU Fish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s Practice and Way Forward”,JournalofInternationalWildlifeLaw&Policy, Vol. 18, Issue 2 (2015), p. 139.
[20]Gregory B. Poling and Conor Cronin,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a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November 2, 2017,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71102_Poling_IUUFishing_Web.pdf (登录时间:2020年12月19日).
[21]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at is IUU fishing?”, http://www.fao.org/iuu-fishing/background/what-is-iuu-fishing/en/ (登录时间:2021年2月12日).
[22]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South China Sea Energy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https://amti.csis.org/south-china-sea-energy-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 (登录时间:2020年12月19日).
[23]《中国近5年发生海洋溢油污染事故41起》,中国新闻网,2011年10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10-11/3378675.shtml(登录时间:2020年2月8日)。
[24][25][36]《2020年中国海洋生态状况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部,2020年5月26日,http://www.mee.gov.cn/hjzl/sthjzk/jagb/202006/P020200603371117871012.pdf(登录时间:2020年6月8日)。
[26]“Somali Piracy”, https://www.globalpolicy.org/component/content/article/205/39506.html (登录时间:2020年12月19日).
[27]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More than 30% of Global Maritime Crude Oil Trade Move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August 27, 2018,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36952 (登录时间:2020年4月23日).
[28]《“现代开拓”和“地中海伊伦娜”轮碰撞溢油事故》,中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2018年5月12日,https://www.sh.msa.gov.cn/copcfund/sgal/503.jhtml(登录时间:2020年12月21日)。
[29]《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2008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9年12月7日,http://www.cnemc.cn/jcbg/zgjahyhjzlgb/200912/t20091207_647007.shtml(登录时间:2020年12月21日)。
[30]张辉:《南海生态保护引入特别区域制度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37页。
[31]张丽娜、王晓艳:《论南海海域环境合作保护机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43页。
[32]《2012年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年10月,http://www.cnemc.cn/jcbg/zgjahyhjzlgb/201706/W020181008686433905504.pdf(登录时间:2020年12月21日)。
[33]《2014油轮溢油事故数据统计》,国际油轮防污联盟,2015年1月,https://www.itopf.org/fileadmin/data/Documents/2014_Stats-CHS.pdf(登录时间:2020年12月21日)。
[34]《2014年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5年7月,http://www.cnemc.cn/jcbg/zgjahyhjzlgb/201706/W020181008686377029520.pdf(登录时间:2020年12月21日)。
[35]Budislav Vukas, “The Mediterranean, An Enclosed or Semi-enclosed Sea?”, in Budislav Vukas (ed.),TheLawoftheSea:SelectedWritings, Lei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4, p. 282.
[37]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grove Forests Trap Floating Litter”, May 13, 2019, https://phys.org/news/2019-05-mangrove-forests-litter.html (登录时间:2021年1月19日).
[38][42]Sulan Che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actors, Actors and Mechanisms”,Ocean&CoastalManagement, Vol. 85, Part B (2013), pp. 131-140.
[39]李聆群:《南海环保合作路径探析:波罗的海的实践与启示》,《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55页。
[40][64]薛桂芳:《“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国—东盟南海海域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的构建》,《政法论丛》2019年第6期,第77、79页。
[41]Fariborz Zelli and Harro Van Asselt, “The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sponses”,GlobalEnvironmentalPolitics, Vol. 13, No. 3 (2013), pp. 1-13; 王明国:《机制碎片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第7—17页。
[43]Si Tuan Vo, John C. Pernetta and Christopher J.Paterson,“Status and Trends in Coastal Habita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Ocean&CoastalManagement, Vol. 85, Part B (2013), p. 162.
[44]王腾飞:《以海洋环境保护促成南海合作》,《世界知识》2020年第16期,第62页。
[45]李志斐:《南海非传统安全的现状与应对机制分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4期,第77页。
[46]姚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现实需要、理论驱动与中国效应》,《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99页。
[47]包广将:《东亚国家间信任生成与流失的逻辑:本体性安全的视角》,《当代亚太》2015年第1期,第38—62页。
[48]Mark Valencia, “Regional Maritime Regime Building: Prospects in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OceanDevelopmentandInternationalLaw, Vol. 31, Issue 3 (2000), p. 240.
[49]Sam Bateman, “Building Cooperation for Managing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out Strategic Trust”,Asia&ThePacificPolicyStudies, Vol. 4, Issue 2 (2017), p. 254.
[50]Laura Zhou, “Beijing’s South China Sea Fishing Ban Threatens to Raise Tensions with Rival Claimants”, May 8, 2020,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83572/beijings-south-china-sea-fishing-ban-threatens-raise-tensions (登录时间:2020年6月7日).
[51]Yinghui Lee, “Pay Attention to China’s ‘Blue Sea 2020’ Project: Is China Quietly Securitizing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une 29,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6/pay-attention-to-chinas-blue-sea-2020-project/ (登录时间:2020年6月7日).
[52]杜兰:《中美竞争背景下的美国对东南亚安全政策》,《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3页。
[53]陈永:《精准修正主义与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期,第56—64页。
[54]《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行动的法律边界问题》,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2020年12月24日,http://www.scspi.org/zh/dtfx/1608796586(登录时间:2020年12月26日)。
[55]朱锋:《美国南海政策的危险转型》,《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5期,第22页。
[56]Daniel F. Runde,Conor M. Savoy and Janina Staguhn,Post-pandemicNaturalResourceManagementintheIndo-Pacific, October 9,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ost-pandemic-natural-resource-management-indo-pacific (登录时间:2020年11月6日).
[57]任远喆、刘汉青:《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中国的角色》,《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3期,第90页。
[58]Mohd Nizam Basiron and Shelley M. Lexmond, “Review of the Legal Aspec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Gulf of Thailand”,Ocean&Coastalmanagement, Vol. 85, Part B (2013), pp. 258-260.
[59]韦红:《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架构与中国的策略思考》,《南洋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第3页。
[60]《<中国海洋保护行业报告>:我国已建立271个海洋保护区》,新华网,2020年10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energy/2020-10/13/c_1126600371.htm(登录时间:2020年12月26日)。
[61]刘赐贵:《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6日,第13版。
[62]侯丽维、张丽娜:《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南海“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南洋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第61页。
[63]金永明:《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6页。
[65]徐贺云:《改革开放40年中国海洋国际合作的成果和展望》,《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6期,第21—22页。
[66][70]祁怀高:《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第140、151页。
[67]易先良:《构建开放性的南海区域合作机制》,《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4期,第7页。
[68]高之国:《南海地区合作机制的回顾与展望——兼议设立南海合作理事会的问题》,《边界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2期,第5—10页。
[69]张颖:《半闭海制度对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的启示》,《学术论坛》2016年第6期,第69—70、140、151页。
[71]Lina Gong and Julius Cecar Trajano, “Advancing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ovember 26, 2018,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8/11/PR181126_Advancing-Marine-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the-South-China-Sea.pdf (登录时间:2020年6月19)日).
[72]吴士存:《关于构建南海新安全秩序的思考》,《环球时报》2021年3月3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