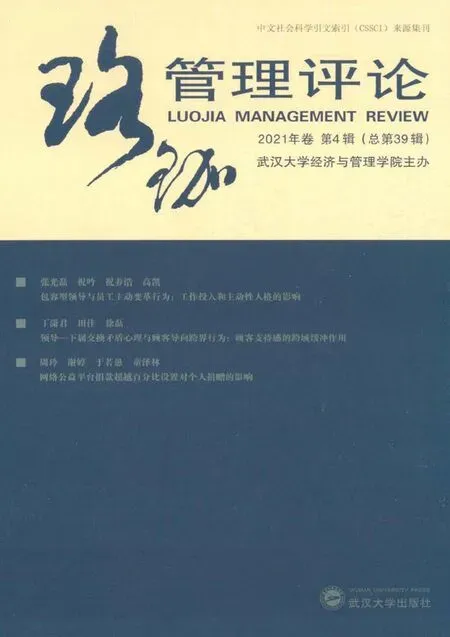女性高管、竞争惯性与企业绩效*
——来自中国家电行业的实证检验
● 林晓真 邓新明
(1,2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1.引言
在动态竞争领域,研究的核心视角是在一个真实的竞争情境中调查企业行为(Chen, 2009),进攻—回应的对偶视角成为调查中的基本单元(Chen & Miller, 2012)。然而,现实中企业不是严格按照单一进攻与回应的对偶逻辑参与竞争,而是通过执行一系列的行动组合展开竞争(Connelly, 2017)。因此,考虑更长时间和更多方面的行动序列是一个更受关注的趋势(Connelly, 2017)。也就是说,整体层面的竞争行动才构成了一家企业的竞争决策(Ferrier & Lyon, 2004; Miller & Chen, 1994),通过企业所执行的一系列组合性的竞争行动,可以分析该企业长期坚持的竞争模式(Chen & Miller, 2012)。Miller等人(1994)引入竞争惯性这一构念来考察企业整体竞争行动的一致性水平,从而研究其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这是文献上最早也是迄今为止少数尝试从竞争视角来评估惯性的研究之一,因为以往文献大多关注程序惯性、结构惯性和战略惯性,而很少关注竞争情境中的惯性(Miller & Chen, 1994)。但是在实际的竞争情境中,企业有可能保持各项行动的一致性而仅对竞争行动做出很小的适应性调整;也有可能试图通过出其不意的创新性行动以改变竞争格局(Miller & Chen, 1994)。不同的竞争模式会给企业及其业绩带来不同的影响,但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家都忽略了企业在参与竞争时普遍存在的“适应性努力”倾向(Miller & Chen, 1994)。Miller和Chen虽然关注到了这种倾向,但将其归结为组织和环境驱动,忽视了背后隐藏的人的影响(Connelly, 2017)。因此,动态竞争领域的学者们也将高阶理论运用到动态竞争情境中,并由此展开了实证研究(Hambrick et al.,1996)。正如陈明哲等人所指出的,现实中企业的竞争行动只有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才能实现(Chen & Miller, 2012),Connelly(2017)也呼吁学者对隐藏在竞争策略组合背后的决策者特征进行深入研究。
在研究高层管理团队(TMT)特征的众多文献中,性别是常被学者们讨论的因素之一。随着女权运动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对女性参与企业管理的呼声日渐高涨,中国经济舞台上也涌现出一批以董明珠、杜鹃等为代表的优秀女性高管(1)据Deloitte 统计,中国2016年女性董事平均占比为10.7%,女性CEO平均占比2.3%,我国内地企业女性高管的比例正逐年增加,而没有女性高管的企业比例也在持续下降。文献来源:Women in the boardroom:a global perspective[EB/OL]. [2016-11-21]. https://www2.deloitte.com/br/en/pages/risk/articles/women-in-boardroom.html.。女性高管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术界对女性经理人的关注也越来越多。研究表明,由于认知与偏好的性别差异,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将影响企业决策(熊艾伦等,2018,2019)。比如,女性高管具有更强的风险规避意识(Khan & Vieito, 2013),当这种意识被带入竞争决策,可能表现出更稳定的竞争风格,进而使企业的竞争行动组合嵌入一种竞争惯性。现实中,创维集团在女性高管比例高于30%且由狄慧女士担任CEO的2012—2014年,每年发动的竞争行动类型几乎一致且高度集中于推出新产品、营销和媒体互动,表现出稳定的竞争风格;而女性高管占比不足15%的小天鹅公司发动的竞争行动类型每年都有较大的变化。我们认为,这些由性别差异导致的不同一致性水平的竞争行动会给企业绩效带来差异化影响。同时,心理学家指出两性性格在一些情景下差异较大,而在另一些情景下差异较小(Lippa, 2010),我们认为女性管理者偏好对竞争决策的影响在不同情景下也有差异。首先,女性高管对竞争决策的影响受其决策权大小的约束,即女性高管想做什么(偏好)受她能做什么(权力)的限制。由于女性CEO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比普通女性管理者更强(Lee & James, 2007),本文还考察在CEO由女性担任的情况下女性高管对竞争惯性的影响强弱是否会发生变化。其次,Gneezy 等人(2009)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竞争意识上的差异受环境的影响。由于产业环境影响管理者的注意力配置,从而影响高管的战略选择(Nadkarni & Barr, 2008),本文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当高动荡水平的竞争环境要求企业必须采取适应性调整时,女性管理者有没有可能降低对稳定的偏好而采纳创新性的竞争行动。
综上所述,本文以中国家电行业为背景,研究女性管理者对企业竞争惯性和绩效的影响,同时关注女性管理者的实际话语权和注意力配置对竞争决策女性偏好显示程度的约束。本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贡献:
(1)这是运用高阶理论解释动态竞争领域中竞争惯性的一次有效尝试,凸显了企业竞争决策组合背后人性因素中女性因素的影响,为动态竞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2)拓展了对女性高管的研究内容。首先,我们呼吁关注女性领导对竞争决策或竞争行为的影响,为今后对女性高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且有意义的方向。其次,我们同时考察了女性高管的数量和质量(职位与职权)对其实际影响力的作用,对领导团队中女性人数的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有了新发现,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
(3)结合社会认知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来考察女性高管对企业决策的影响边界,是高阶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一次有意义的融合。
(4)丰富了动态竞争领域对竞争惯性的研究。在前因变量上,补充并检验了管理者因素这一惯性来源;在结果影响上,本文在线性关系之外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倒U形关系,是对既有研究的补充和完善;在测量上,将非市场行动纳入考察范围,拓宽了竞争惯性的研究范围。
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女性高管与企业决策
高阶理论认为,作为战略决策的主体,高管团队的个人特征是影响企业决策行为和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由于企业管理者是有限理性的,高管团队的心理特征和人口学特征会影响对信息的获取、处理和筛选能力,从而带来不同的战略选择和组织绩效(Hambrick & Mason, 1984)。决策者最终评判所筛选的信息不仅受个体认知能力的限制,还受主观偏好的过滤(Hambrick & Snow, 1977)。由于男性和女性的偏好具有显著的差异,在关于高管的众多研究分支中,对女性高管的关注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热点。其中,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直是女性高管研究体系中最主要的研究主题,但现有研究结论却迥异甚至互相矛盾。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归咎于女性高管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而是先影响企业的某些方面。例如,Davis 等人(2010)研究表明,女性高管因为有更强的市场导向能力而使企业表现得更好;Boohene 等人(2008)则证明女性高管通过价值观和企业战略作用于企业绩效。
不可否认,直接将性别等管理者个体特征与企业绩效相关联确实存在因果链过长的问题(熊艾伦等,2019)。所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和探究女性高管相对于男性高管的领导风格和决策偏好差异,并透过这些差异研究女性高管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熊艾伦等, 2019,2018)。虽然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女性高管决策偏好及其对企业的不同影响,却少有文献探究女性领导者这些不同于男性的决策偏好如何影响企业的竞争决策和竞争行为。随着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竞争对每一家企业而言都是不可避免且至关重要的。应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以怎样的风格发动竞争行动才能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和良好绩效,则是每一位企业管理者必须做出的抉择。研究已经证明,每一个决策者都会将自己的一些“偏好”带入特定的决策情景(Bowen & Siehl,1998)。因此本文认为,女性高管会将其决策偏好带入竞争决策,影响企业参与竞争的方式和发动竞争行动的模式——竞争惯性,进而影响企业绩效。事实上,动态竞争领域的研究已经在竞争行动(包括进攻与回应、行动的特征和竞争行为组合即竞争策略组合等)和企业绩效之间建立了关联(Miller & Chen, 1994; Ferrier & Lyon, 2004)。据此,我们认为企业竞争惯性所反映的一段时期内发动的竞争行动策略组合特征,也会影响企业的后续表现。
2.2 女性高管与竞争惯性
根据Miller等(1994)的定义,竞争惯性指的是一家企业在改变自身的竞争态势时所显示出来的活动水平(level of activity),是一家企业在某一年度的整体竞争行动的一致性程度,它反映了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一系列竞争性活动的决策组合。与类似的竞争对手相比,若焦点企业很少改变其竞争做法,则它具有较高的竞争惯性;反之,则具有较低的竞争惯性。根据高阶理论(Hambrick & Mason,1984),企业的竞争行为是高层管理者认知、判断和决策的结果。由于管理者是有限理性的,在无法对所有信息有完全的认知和掌控下,竞争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决策者自身主观偏好的过滤(Hambrick & Snow, 1977)。因此,本文认为女性高管会将其迥异于男性高管的决策偏好带入竞争决策情景,从而影响企业一段时间内的竞争决策组合。首先,女性高管具有更多的规避风险特质,更加厌恶风险(Khan & Vieito, 2013),这种偏好将使企业决策趋于保守,在竞争决策中表现为稳健、审慎的风格,使企业竞争行动更多活跃于已知的安全范围内而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其次,女性高管对竞争行为具有排斥心理(Niederle & Vesterlund, 2007; Gneezy et al., 2003),不愿意直面竞争或发起激烈的竞争行为,这使她们在竞争决策中显得被动而较少发起积极主动的创新性竞争行动。最后,性别异质性本身增加了管理团队达成一致性的难度(Pelled et al., 1999),而在这种更难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具有强共识取向的女性高管又追求团队成员达成一致共识(Bart & Mcqueen, 2013),这降低企业在竞争行为上做出改变的可能性。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女性高管会增加企业的竞争惯性。
2.3 竞争惯性与企业绩效
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惯性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惯性被视为一种停滞或超稳定状态,以至于组织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动而危害绩效(Miller & Friesen, 1984)。后来的研究将惯性的定义修正为“抗拒根本性政策方向的调整”(Tushman & Romanelli, 1985)。也就是说,带有惯性的组织还是会做出改变,只是这些改变需要与组织的核心策略一致。事实上,组织本身就是在一套规则下运行的有机体,组织内部策略的制定与执行都遵循着一定的行为方式,而从中体现出的惯性实际上有助于实现组织内部的协调与控制(Hambrick et al., 1993)。因此,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惯性给组织带来的许多益处(Hannan & Freeman, 1984)。
本文认为,企业一段时间内竞争行动精简所反映出适度的惯性是有利的(Miller et al., 1994)。第一,惯性有利于降低企业竞争决策的搜寻成本。事实上,每一个组织都会受到一定程度惯性力量的控制,表现为保持当前的做法或模式不变(Hannan & Freeman, 1984)。惯性可以为组织提供一致性的操作指南、程序和习俗(Bourdieu, 1990),为企业竞争行动的选择和实施提供借鉴而不需要每次重新搜索,从而有效降低搜寻成本。第二,竞争惯性可以提高企业的学习效率,使管理者有时间思考自身的竞争行动,更多专注于最重要的决策和他们最擅长的行动(Miller & Friesen, 1984),降低变革时犯错的概率(Hannan & Freeman, 1984)。第三,竞争惯性可以避免干扰客户和竞争对手,使企业能维持产品和服务的稳定性,避免客户因为不愉快的异常体验而疏离(Hannan & Freeman, 1984),同时避免因采取过多竞争性攻击而受到对手不必要的报复。
然而,不足或过高的竞争惯性会约束企业获取并维持竞争优势,从而不利于企业绩效。这是因为:首先,竞争惯性不足说明企业在竞争决策中需要频繁地重新搜寻、筛选和判断信息,这一方面产生高搜寻成本,另一方面容易贻误战机,因为错失最佳的进攻或回应时机而损害绩效。其次,过度的竞争惯性使企业失去灵活性,削弱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能力(Levinthal & Myatt, 1994),不能很好地应对竞争对手的挑战,也无法为消费者提供精确的服务,从而削弱其竞争优势。再者,组织惯性发展到极端就会导致老化和惰性,严重阻碍内部企业家精神的发挥(Sull, 1999),使企业在竞争中缺乏创新和探索,甚至导致竞争近视错失一些发展机遇。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竞争惯性与企业绩效存在一种倒U形关系,即适度的竞争惯性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改善,而不足或过高的竞争惯性则会抑制企业绩效的提升。
2.4 女性高管、CEO性别与竞争惯性
尽管已有大量文献肯定了女性高管对企业的影响,仍有学者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怀疑女性管理者在企业管理中的实际话语权和影响力(Erkut et al., 2008;Westphal & Milton, 2000)。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为保持团队认知的一致性和协调性,群体中往往是少数服从多数;当团队内发生冲突时,社会障碍降低了少数群体影响团体决策的可能性,而占多数的一方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从而对决策影响更大(Westphal & Milton, 2000)。虽然女性高管占比逐年提高,但女性在高层管理团队中的比例仍远远低于男性(2)文献来源:The CS gender 3000 report 2019: diversity and company performance[EB/OL].[2019-12-22].https://www.credit-suisse.com/about-us-news/en/articles/news-and-expertise/cs-gender-3000-report-2019-201910.html.,限制了女性高管在企业竞争决策中的影响力,这种现象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可能尤为明显。由于性别歧视和偏见的存在,女性担任企业高管并不被人普遍接受,女性高管在男性占主导的情景中不得不模仿男性同行以获得下属的尊重和认可(Hoyt & Murphy, 2016),从而减弱女性管理者决策偏好在企业战略选择中的影响痕迹。
再者,在中国,有一些女性是凭借豪门家属的身份才进入企业高管团队,比如在2011年胡润女富豪榜上的50位中国女富豪中,10位与其家族联袂上榜,11位与其丈夫同享殊荣。这类女性高管所拥有的更多是一个身份或一份荣耀,所在的职位往往也非企业的关键决策人。而在西方国家,性别机会平等或代表性平等被视为良好公司治理的一种表现(Burke, 2000),若女性高管比例过低,企业甚至会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质询。迫于制度压力,许多企业在高层管理团队中加入了女性,但只是为了获取合法性而做的表面文章,而不是增加管理团队异质性的真诚尝试 (Konrad et al., 2008)。可以预见,以上类型的女性高管对企业决策的实际影响力不强。有学者指出,在研究女性高管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时,应该对其职位与职权加以区分,因为管理层级差异影响女性高管实际话语权的强弱,从而给企业带来不同的影响(Dezso & Ross,2008; Lee & James,2007; 熊艾伦,2018)。我们借鉴Dezso和Ross(2008)以及Lee和James(2007)的方法,通过区分CEO和非CEO来研究女性高管对企业竞争决策的不同影响。由于CEO是企业的一把手和掌门人,每一家企业都极为重视CEO的人选。正是因为该职位的关键性,能担任CEO的女性一般不属于象征型高管,而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关键决策者。当企业的关键决策人由女性担任,女性高管由于人数劣势或性别偏见导致的决策参与劣势得以缓解。因此,由女性担任CEO企业的决策将更多受到女性管理者决策偏好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女性CEO会增强女性高管对竞争惯性的正向作用。
2.5 女性高管、环境动态性与竞争惯性
本文认为,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在自身偏好和环境要求之间不断权衡。虽然女性管理者在竞争决策中偏向于稳健而使各项竞争行动保持一致,但当企业所处环境快速变化时,为了适应环境,她们也必须做出改变。一方面,高阶理论肯定了高层管理团队个人特征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Hambrick & Mason, 1984);另一方面,企业注意力基础观认为,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不仅由个人特征决定,还受管理者所处组织环境及其对环境之理解的影响(Ocasio, 1997)。组织想要保持优势就必须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管理者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也就必须做出正确的决策以使企业可以应对环境的动态性特征。环境动态性是指产业环境中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和绩效因素的不稳定性(Dess & Beard, 1984)。由于企业收集有效信息的能力和资源是有限的,管理者会将其注意力分配到环境的各个板块,哪一个板块的不确定性越强,管理者便对该板块越关注(Hough & White, 2004)。在环境较稳定、不确定性较弱的环境下,管理者会做出较少的改变(Hough & White, 2004),这时,管理者在竞争决策中更倾向于使各项行动保持一致,女性高管决策偏好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将得到增强。相反,在环境快速变化、不可预测性较强的环境下,管理者会搜寻额外的信息以提高决策的精准度,使决策更加适合变化情景的要求(Eisenhardt, 1989),这时女性高管偏好对竞争惯性的影响会被高环境动态水平削弱。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环境动态性会削弱女性高管对竞争惯性的正向影响。
3.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编码
本研究以中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也将几家与家电行业密切相关的配件制造企业考虑在内。理由如下:本文的核心构念“竞争惯性”依附于那些已执行的、公开的决策,即企业所实行的利益相关者可观测到的重大具体行动(Miller et al., 1994)。因此,需要选择一个竞争行动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并且可以被观测到的样本企业为实证背景,家电行业很好地满足了这个要求。本文基于多种信息来源采集所需要的数据:通过CSMAR数据库获取家电企业的运营数据和高管团队信息;通过中国家电网(www.cheaa.com)、51家上市企业的官网以及百度实时新闻三个主要渠道搜集企业竞争行为的信息,三个渠道的信息相互补充,能为本文提供较为全面的企业行为数据。最终,以2013年1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为时间窗口,我们共搜集到51家上市企业5年内的4957个行动数据,其中市场导向的行动3086个,占比62.26%;非市场行动1871个,占比37.74%。可见,在企业的竞争行为中,非市场行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Quasney, 2003)。
我们以搜集到的竞争行为信息为分析单位,用结构化内容分析法辨识和划分这些竞争行为,该方法是获取企业行为的一个重要工具(Quasney, 2003)。首先,借鉴既有文献(Connelly et al., 2017;田志龙等,2007;Ferrier & Lyon, 2004)的做法,确定了11种市场行动类型,即研发、调整生产规模、推出新产品、进入新市场、进入新行业、并购、合作联盟、渠道布局、改进服务、价格调整(降价与涨价)和营销,以及5种非市场行动类型,包括企业家政治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官员视察、媒体互动和参与公益项目。接着,为保证最终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我们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进行初始研究,组员包括动态竞争领域的教授1名、博士生2名和硕士生3名。在正式编码之前,研究小组先进行预编码,每个组员先各自阅读企业行动报道的内容,然后分别独立地对每一个行动进行归类。为确保分类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当信息模糊不清时,我们请动态领域的专家进行指导,实在无法确定便剔除该信息。一段时间后,研究小组进行正式编码,发现一致程度高达0.87,表示前期的研究足够可信。
3.2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
(1)女性高管参与。在现有的研究中,对女性高管参与的测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构造一个虚拟变量,若企业存在女性高管,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Abdullah et al., 2016)。二是使用女性管理者的参与比例,即女性高管人数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例(Lyngsie & Foss , 2017)。本文以后者进行研究,而以前者进行稳健性检验。
(2)竞争惯性。Miller等人(1994)最初仅通过市场导向的竞争行动来研究竞争惯性,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开始关注企业的非市场竞争行动(田志龙等,2007;Quasney, 2003)。本文通过对中国家电企业竞争行为的长期追踪发现,大多数企业在发动市场行动的同时也发动非市场行动,比如慈善捐助、媒体互动、官员视察等,这符合我国转型经济的制度特征,也反映了中国情景下企业管理的特殊性(田志龙等,2007)。因此,本文将非市场行动纳入竞争惯性的研究范围,根据不同类型行动的平均数量差异进行加权调整。借鉴Miller等人(1994)的研究方法,竞争惯性的测量方式具体如下。
先分别计算第i家企业(i=1,2,…,51)第t年(t=2013,2014,…,2017)采取第j类型行动(j=1,2,…,16)的决策数,记为xi,j,t。由于每一j类型行动整体的平均决策数量存在较大差异,而不同类型的同一数量行动对企业而言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在本文的样本中,营销活动的平均次数为每年5次,而进入新行业的平均次数仅为0.17。企业i若每年采取2次营销活动只是一个很小的频数,但要是每年进入新行业2次就算非常多。因此,为了避免经常采用的活动类型权重过大,本文将所有样本企业、所有年份内的每一j类型行动得分标准化,即由xi,j,t减去行业均值再除以标准差,记为zi,j,t。这个标准化分数zi,j,t给予那些数量虽少但意义重大的行动较大的权重(3)比如进入新行业2次,将得到一个很高的正数;而给予那些经常做的日常决策相对较低的权重,如营销活动2次,将是一个小于零的负数。。然后,将每一j类型行动的标准化得分zi,j,t加总得到企业i第t年的活动指标(activity index)。为了使不同规模企业的指标具有可比性,我们将活动指标得分除以企业规模的对数值。为使该变量呈现正态分布,本文对活动指标再进行自然对数运算。
(1)

(2)
最后,由于本文使用了16种行动类型来测量企业的竞争惯性,我们又通过SPSS来分析这16种行动类型的内部一致性,结果显示它们的信赖系数Cronbachα为0.73。
(3)企业绩效。本文使用市场类指标TobinQ值来测量企业绩效。
(4)调节变量。第一,CEO性别,构造一个虚拟变量,若企业i在第t年由女性担任CEO,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第二,环境动态性反映的是产业环境中影响企业决策和绩效的不稳定性(Dess & Beard, 1984)。本文关注企业层面的环境动态水平,借鉴Ghosh和Olsen(2009)的方法,对于每一家企业,用其前5年的销售额对前5年的时间变量做回归分析(OLS),本文的研究窗口为2013—2017年,因此每家企业做5次回归分析。具体回归方程如下:
salesi,t=α+β·year+ε
(3)
其中,salesi,t是企业i前5年的销售额,year为年度变量,若观测值是当前年度的,year=5;若观测值是过去第1年的,year=4;以此类推,若观测值是过去第4年的,year=1。模型(3)的残差标准误除以企业前5年的平均销售额,即得到未经行业调整的企业环境动态性,记为A;而每一年度未经行业调整的企业环境动态性的中位数即行业环境动态性,记为B。最后,将A除以B即得到企业层面经过行业调整的环境动态性水平。

表1是变量汇总。

表1 变 量 汇 总
4.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我们的统计结果显示,在2013—2017年,样本企业的平均女性高管占比为15.74%。然而,女性高管占比为0的企业平均有15家,占比高达29.41%,说明女性进入企业高层仍有较大的空间。另外,观测时间内有5家企业出现过女性CEO,占总体样本企业的9.80%;但由于有女性CEO在观测时间内中途换届,女性CEO占比仅有6.25%。
表2报告了本文模型中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系数。总体来说,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全部小于普遍认为的0.8阈值,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很小。进一步,本文对各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分析(VIF),发现最高膨胀因子为1.59,平均膨胀因子只有1.24,均低于临界值10,所以本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接下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表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4.2 回归分析
本文最终得到中国家电行业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检验提出的假设,由于样本数据属于大N小T的短面板,可能会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问题,故选择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为避免因果倒置,将所有解释变量做滞后一年处理。同时,为避免在调节回归中出现共线性,我们将自变量做中心化处理。以上数据处理的结合使用有助于减轻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最终的回归结果见表3和表4。模型2显示女性高管对竞争惯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H1得到验证。进一步,模型3加入女性CEO与女性高管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即女性CEO增强了女性高管对竞争惯性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H3。同样,模型4加入环境动态性与女性高管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即环境动态性削弱了女性高管对竞争惯性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H4。

表3 回归分析一

表4 回归分析二
为更直观地观测女性CEO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我们进行绘图说明。图1绘制了由女性担任CEO和由男性担任CEO情况下女性高管对企业竞争惯性的影响,发现在由女性担任CEO的情况下,女性高管对企业竞争惯性的正向影响更为陡峭,说明由女性担任CEO的企业的决策和行动带有更明显的女性色彩。图2绘制了高环境动态性和低环境动态性情况下女性高管与竞争惯性的关系变化,发现当企业的环境较为动荡时,女性高管对竞争惯性的正向影响更为平缓。说明女性高管在竞争决策时一方面受自己决策偏好的驱动,另一方面也关注和回应环境的变化,并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环境动态性减弱了女性高管对竞争惯性的正向影响,但女性高管的影响系数始终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即使在较为动荡的环境中,女性高管的竞争决策风格仍然是谨慎稳健型。这有可能使企业在多变的环境中错失发展机遇,但也很有可能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使企业平安渡过危机。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曾有舆论认为如果当初的“雷曼兄弟”变成“雷曼姐妹”(5)文献来源:http://bigthink.com/women-and-power/lehman-sisters-wouldnt-have-failed.,或许有可能避免破产危机。

图1 女性CEO的调节效应图

图2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图
表4的模型6显示了竞争惯性一次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系数并不显著,说明竞争惯性与企业绩效可能不存在线性关系。模型7加入了竞争惯性的二次项,结果显示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都是显著的。特别是竞争惯性二次项与企业绩效成显著的负相关,并且倒U形曲线的顶点0.3428(0.4782/(2×0.6974))落在竞争惯性[-2.5637, 2.0835]的区间之内,竞争惯性对企业绩效的倒U形关系通过检验,假设H2得到支持。为了进一步检验竞争惯性与企业绩效之间倒U形关系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方法,加入竞争惯性的三次项再次进行回归。表4的模型8发现竞争惯性三次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说明竞争惯性与企业绩效不存在S形关系。为了更加直观地观测竞争惯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画出两者的倒U形关系,见图3。虽然二次项系数仅有10%的显著性水平,我们仍然认为这种影响不应被忽略。适当的竞争惯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改善效应,而过低或过高的竞争惯性对企业绩效则产生抑制效应,这符合现实的竞争情形。

图3 竞争惯性与企业绩效的倒U形关系图
4.3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替换关键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使用女性高管虚拟变量和滞后两年的竞争惯性来检验假设H1、H3、H4和H2,结果见表5。模型9的Fem1是女性高管哑变量,若企业存在女性高管则取值为1,否则为0。结果显示,女性高管对竞争惯性并没有显著影响。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样本中有些女性高管对企业决策的实际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这种有限的影响力在只有1位女性高管的情形下尤为明显。事实上,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已经指出,董事会中是否有更多的女性成员决定了女性董事能否真正发挥作用(Erkut et al., 2008)。另外,也有其他研究证明,董事会性别多样性能为企业带来的许多好处,只有在女性在领导层打破单一代表时方能实现(Jia & Zhang, 2013)。因为仅让1位女性进入领导层可能只是企业为应对制度压力和取得合法性的象征性举措,难有实质上的影响 (Konrad et al., 2008)。对此,西方有媒体做出评论:“一个是显然不够的,一个只是象征。”(6)文献来源:https://money.cnn.com/2018/08/30/pf/california-women-company-boards/index.html.可见,以是否存在1位及以上女性高管来考察女性高管对企业的影响是有偏差的。

表5 稳健性检验
因此,本文以是否存在2位及以上女性高管为标准重新构造一个虚拟变量Fem2,然后再次进行回归。模型10显示,女性高管对竞争惯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与前文的结果一致,验证了假设H1。可见,在企业高层管理团队中,女性只有在人数上取得一定优势后才能对竞争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模型11和模型12分别检验了该测量方法下,女性CEO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与模型3和模型4相比,两个交互项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假设H3和H4的结果是稳健的。接着,将竞争惯性和其他控制变量做滞后两年的处理,以考察竞争惯性对企业绩效是否有持续性影响。模型13与模型14显示,假设H2的结论也是稳健的。
最后,本文还分别对女性高管与市场行动惯性和非市场行动惯性关系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女性高管显著增强两类竞争惯性,但当环境动态水平较高时,女性高管对非市场行动惯性的影响被显著削弱,而对市场行动惯性的影响,虽然不显著却得到一个正的系数。这说明,当环境不确定性很强,女性高管倾向于避免与竞争对手在产品市场上发生猛烈的冲突,而更多将压力转移到非市场行动,比如战略性政治参与和公益项目参与等。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没有对这部分的回归结果进行汇报。综上,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5.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融合了高阶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社会认知理论,探索了女性高管对企业竞争惯性的影响及其边界,并研究竞争惯性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最终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女性高管提高企业的竞争惯性。女性高管将规避风险、排斥竞争的决策偏好带入企业的竞争决策,使企业的竞争行动更多活跃于已知的安全范围内,从而表现为谨慎稳健的竞争决策风格。
第二,女性高管对企业竞争决策的作用受CEO性别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具体包括:(1)女性CEO加强女性高管对竞争惯性的正向作用。女性CEO作为企业的关键决策人,可以减弱女性高管作为少数群体的社会障碍,使她们更多地将规避风险、厌恶正面竞争等偏好带入竞争决策情景,使企业的竞争行动更为稳健。(2)环境动态性削弱女性高管对竞争惯性的影响。动荡的环境要求企业做出改变才能保持竞争优势,此时女性高管更多关注环境,将对竞争决策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整。这说明女性管理者虽然在竞争决策中追求经验和稳健,但仍保持警惕性和灵活性,因此可以对变化的环境要求做出相应的响应。
第三,高层管理团队中仅有1位女性成员只是一种象征而无法对竞争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至少需要2位女性代表才能真正发挥女性管理者的作用。一方面,该结果回应了Jia和Zhang(2013)等人的研究,表明管理团队性别异质性为企业带来的许多影响,只有当女性在领导层打破单一代表时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本文对管理团队中女性领导影响企业决策的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提出了新见解。西方学者普遍认同女性董事能对企业决策起实质性影响的临界规模为3人(Konrad et al.,2008),但本文得出的结果为2人,与现有研究结论不同,可能的原因为:首先,中西方情景差异。西方国家多通过颁布法案以提高董事会中的女性比例,西方企业在让更多女性进入领导层上面临更大的制度压力,也直接导致更多象征性女性领导进入董事会。而中国女性能进入企业领导高层更多凭借自身的才华和能力,淡化了象征性意义。其次,前面所述临界规模研究的是董事会中的女性,而本文关注的是高层管理团队中的女性,这可能也是产生偏差的原因之一,说明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中女性的临界规模可能存在区别。
第四,竞争惯性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适度的竞争惯性对企业是有利的,可以降低搜寻成本、提高组织学习效率,使企业专注于最重要和最擅长的竞争行动,而稳健型决策风格也可以降低经营风险。然而,竞争惯性不足将产生过高的搜寻成本和较低的竞争决策效率,从而损害绩效;过度的竞争惯性使企业在竞争中失去灵活性和动态能力,甚至导致竞争惰性和近视,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本研究对企业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女性参与企业管理不应只是企业获取合法性或家族控制企业的一种象征性举措,而应将其视为提高高管团队异质性、改善企业绩效的有效途径之一。重视女性领导者稳健型决策风格在降低企业竞争风险方面的重要意义,尤其当经济下行时,企业决策应尤为谨慎。
第二,企业应帮助女性管理者培养适当的冒险精神,使女性领导更富于创新。事实上,中国女企业家协会曾于2016年对2505位女企业家进行问卷调查,统计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最缺乏的能力是创新与冒险,只有28.9% 的女性企业家对自身的管理创新比较满意。可见,女性领导需要在这一方面有更多培训。
第三,要真正发挥女性高管对企业的作用,应当使管理团队中至少存在2位女性,或者给予女性高管足够的话语权,因为孤身无援的单一代表难以产生实际作用。
第四,企业在竞争中要保持适度的惯性,将更多精力集中于最擅长、最有效的竞争行动,使自己在竞争场上有规划、有章法、有聚焦,而非“东打一拳,西踢一脚,胡子眉毛一把抓”。但在竞争决策上又要保持一定的动态性,密切关注竞争对手、市场和环境的变化,以在竞争行动上做出必要的改变,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或抓住某些发展机遇。
虽然本研究取得了有意义的结论,但仍有其局限性:
(1)本文基于决策偏好的逻辑研究女性高管对竞争决策的影响,但仅使用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代理变量,未来研究可以结合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从高管的人格因素、心理特征和认知角度出发,进一步探究女性高管决策的内在规律和机理。
(2)高层管理团队的女性人数是否存在一个最优解以及这个最优解为多少是本文没有研究的问题,是今后一个有潜力和价值的研究方向,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关注女性高管对企业其他竞争策略组合特征的影响。
(3)研究设计上,本文仅在一个5年窗口内对单一行业展开研究,虽然这是动态竞争领域学者们的普遍做法(Miller et.al., 1994;田志龙等,2007),但不可避免地给结论的普适性带来约束,未来可以在更长的时间窗口和其他行业开展类似的研究,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