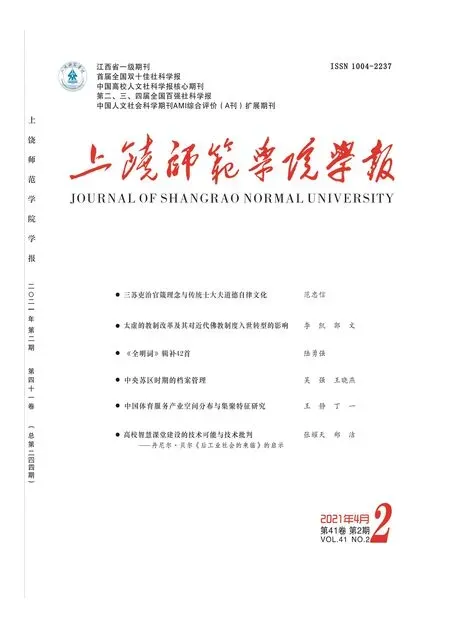高校智慧课堂建设的技术可能与技术批判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启示
张耀天,郑洁
(1.湖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435002;2.武汉晴川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204)
“后工业化社会”一词最早由丹尼尔·贝尔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启用。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预言,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将从能源经济时代进入到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线也将由此发生偏移,他将未来时代称为“后工业时代”。1973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一版出版时,丹尼尔·贝尔就指出,后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是“知识居于中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1]4,同时天才地预言未来社会制定相关决策要依靠“智能技术”[1]4。诚如丹尼尔·贝尔所构想,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本世纪初开始广泛地应用到高校教学改革领域:从最初Web1.0时代高校教学技术改革启用简单的PPT教学、视频播放为开端,信息技术一路凯歌,挺进高校校园。从微博教学、QQ教学,再到慕课、翻转课堂、混合课堂等信息教学形式纷纷登场,一直到今天的智慧课堂,我们可以发现,高校教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过度依赖于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信息技术的力量以强势的工具理性,对高校教学人文价值取向肆意倾轧,高扬工具理性势必导致教育过程中对价值理性的漠视,这种现象既是教学技术进步产生的负效应,也是大数据时代数据权力全面渗透的一个缩影。《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当前审视高校智慧课堂技术提供了经典视角和批判立场。
一、大学取消到大学重建:智慧课堂的技术可能
传统大学的价值在于通过传播和继承人类的知识、经验,实现文化传承、精神传递和人才培养。《大学》中讲到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4,很好地诠释了大学的精神和基本功能。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大学应成为“经验重组和价值观整理的核心”[1]395,因为大学建设的初衷是要弥补传统社会的“信息匮乏”。传统社会环境中,人们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中,凭借祖辈积累的经验就可以逍遥自在地生活,但要了解经验之外的艺术世界、文化世界和政治世界,就需要在学校里进行系统化的学习。大学校园内由此而形成的师生关系、教学关系、传授关系等,也是建立在“信息匮乏”的基础上的——教师由于掌握了大量的知识而被赋予绝对的权威,由此也可以理解传统大学教学氛围缘何以“填鸭式”教学为主。按照贝尔的界定,传统大学是基于社会“信息匮乏”的需求,并由信息屏障而筑建大学的高墙。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几千年来大学营造的知识壁垒已被互联网的浪潮击溃,传统传媒、互联网传媒和今天的大数据传媒,为观察世界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窗口,大学生求知、问学的路径不再局限于大学之内。以智慧课堂为例,它对传统大学的教学实践主体、教学实践场景、教学实践全程、教学实践管理等,均产生了根本性、颠覆性的消解作用。
首先,传统教学实践明确了师生教学相长的主体导向,师生二元关系的互动主导着教学实践的展开。智慧课堂教学实践则改变了这种场景,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师生二元关系之后,教学关系演化为一种新型的“人机交互”型的教学关系——技术力量逐渐呈现,传统的教师主导身份被技术逼退[3]。其二,传统教学实践往往注重场景教学、氛围教学。大学的场景、氛围,不仅是历史积淀的象征,也对学生思想道德的养成、价值观的塑造产生着积极、正向的影响[4]。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直接被腾挪到大数据技术塑造的“赛博空间”,师生的教学实践直接发生在虚拟空间内,解构了传统大学的氛围教育和场景教学。其三,传统教学实践的全程,教学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均处于教师的控制之下。智慧课堂则实现了教学全过程的无死角数据监控,教师的教学设计、教学备课等信息需求,学生的复习备考、学习信息收集等,均能被智慧课堂技术满足。其四,传统教学实践中最令教师头疼的教学管理工作,被智慧课堂轻松化解。考勤管理、成绩管理、评估检测等教学管理工作,都可以在智慧课堂的系统内“一键搞定”。
智慧课堂借助大数据技术重建的数据围城和赛博空间,击溃了传统大学的象牙塔结构,大数据技术以数据整合、数据重塑的方式,把传统大学腾挪到智慧课堂的虚拟空间,以海量的信息弥补了传统大学教育信息陈旧的短板,以形象的图景构建了全新的教学模式——海量信息与知识经验相融合,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结构,也改变着大学教育的内涵。传统大学教育是一种知识型教育,它把人类历史上积淀的文明成果、智慧经验,形成知识教学的范式并在大学内展开相关教学实践。但“知识”不能简单地和“教育”划等号,“知识必然是一种权威,而教育则是铸造权威性判断的过程”[1]397。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人类的知识是一种天然的权威,大学教育则是把知识的权威过渡到教学的权威,事实上两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异。由此也导致传统大学教学过程中知识陈旧、学术垄断等问题。
智慧课堂则更类似于后工业时代大学概念,它突破了教师对知识权威的垄断,天然具有“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基因:一方面,传统大学的教学实践在面对大数据技术冲击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与大数据技术融合;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冲击着传统大学的围城,大学传统功能日益消解。大数据语境下的大学更像是一座信息交流、经验沉淀、理性反思的象牙塔。丹尼尔·贝尔对技术力量可能带来的大学教学方式的重建保持了警惕,并指出,未来大学不应是固定的知识交流的场所,“大学的作用就是联结意识探索的各种模式”[1]397,重塑价值观和整合自我意识,应当成为其主要功能。
传统大学有关批判、思辨的精神,有关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思维,有关价值观培育和自我意识塑造的实践,都被保留下来。以智慧课堂为代表的大数据技术,则重塑了教学实践的新模式,把传统大学的教学实践拖拽到新的数据空间。
二、空间孤立到时空超越:智慧课堂的翻转自由
智慧课堂教学源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初开始,在线学习、移动学习、混合学习等各种依托于信息技术的学习方式,给传统的大学教学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可否认,这种翻转式的、混合式的学习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教与学的效率,线上和线下的双向互动,促进着知识的交流和情感的认知。智慧课堂很大程度上把教师从繁琐的课堂管理中解放了出来,真正实现了教育自由,也把学生从填鸭式的学习方式中解脱了出来,在明确个体学习兴趣的同时,真正做到了个性化、自主化的求知。智慧课堂较之于传统大学教学,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它以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概念、云计算理念和VR视觉模拟技术的综合应用为基础,既全真模拟了传统教学的全过程,实现了实景教学的技术再造,也拓展了传统教学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智慧课堂对于大学教学而言不亚于一次哥伦布式的探险——它把原本封闭于每个大学校园内的知识纳入信息技术的新航道,把原本相对隔绝的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融汇到技术时代的新场景。人类正在利用今天的大数据技术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虚拟的赛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机器和信息真正地融为一体,实现了崭新的数据化生存的新生态[5]。无论是数据技术搭建的教室、图书馆、操场、健身房、实验室等校内基础设施,或是可供大数据搜索的电子图书、电子专利、数据信息、云端计算,都意味着传统大学的围墙被大数据技术野蛮地推倒。智慧课堂是一种技术的翻转,这种翻转带来的是根本性的、颠覆性的、破坏性的教学革命。
这种颠覆性的教学革命,在丹尼尔·贝尔的理论系统中,被描述为“空间自由”对“空间孤立”的取代。前者是指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每一个大学都保留着自己的学风和独树一帜的价值标杆,保留着传统的学术血统和学术派系的山头,这固然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尊严所在,但也意味着每一所大学都在刻意地规避人类文明融合的源流,以空间孤立的方式而特立独行。后者则意味着大数据到来之后,赛博空间内的每一所大学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脉络,都被无情地转化为电脑和手机显示屏上一个个跳跃的字符和智慧课堂控制后台的基础数据。从某种意义上讲,“空间孤立”是一种无奈于大数据时代潮流的“光荣孤立”。“空间自由”意味着大学教学改革被裹挟进强势的大数据潮流,自由的代价则是以牺牲人的主体价值而换取与技术理性的妥协[6]。智慧课堂的到来,实现了从“空间孤立”到时空穿越的过渡,并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社会人格到数据人格的过渡。“新一代的通讯基础结构强调互动和参与,用数以百万次的互联极大地丰富了传媒”[1]43。智慧课堂的交流方式,一改传统大学教学场景中语言交流、文字交流、情感交流的方式,把现实的社会交流转化为数据语音、数据文字、互联网表情包等符号交流。在智慧课堂的交流平台上,无法寻觅到真实的、生动的人格表现,师生之间的交流转化为各种数据信息和数据符号的交流,真实的人格被数据化,转化为数据人格:教师成为一个兼具“信息守门人”和“信息传播者”双重身份的新数据人格形象,学生并不会关注教师的真实教学心理和教学水平,只会关注智慧课堂平台上象征教师的数据符号所推送的相关教学信息。教师也无法走进学生的人格世界,在智慧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只能看到操作平台上跳跃的学生形象。智慧课堂的交流方式,能够屏蔽掉传统大学教育中教师对知识传授的人格影响,“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人类的文明资源变得易于获取”[1]43,但却忽略了知识被技术“祛魅”之后仅留存数据信息的尴尬和窘境——当教学的人格之魅不再,也意味着人文世界的失落。
其二,从经验教学到数据教学的过渡。传统教学体系是建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文明积淀基础上的,这种教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信息的传递,也是智慧经验的沉淀。如亚里士多德指出,大学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哲学教育,所谓的哲学,就是“爱智慧”,爱是一种追求而非占有。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就指出,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物种不同,人类说到底是一种群居性的、社会性的动物,人人都有求知的欲望,但求知不是目的,而是获取智慧和幸福的手段[7]。从这个角度出发,智慧课堂反而是强调技术、否定智慧的教学方式,传统教学实践则真正地保留了“智慧”的内涵。所以,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哲学先贤一样,都强调培育人的德性人格,把人格成长的培养视为实践智慧,指出国家的善治最终要通过社会个体具备实践智慧,践行个体德性,才能实现教育的真谛与价值[7]。这种回归智慧本义的思考,在《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中有也反思:纯粹的技术性学习,尽管带来了海量的信息,但“随着知识的指数增长和领域(兴趣)的倍增,个人所能获得的有关事件种类或只是跨度方面的信息必定会相对缩减。随着时间流失,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少”[1]441。
其三,从情感交流到数据交流的过渡。传统大学教学通过讲台艺术综合地表达教师的人格魅力、学术修养、人生智慧等综合教学能力,它有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有“程门立雪”的尊师重教传统,也有“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革命创新勇气。情感交流是教学场景中师生交流的一条主线,师生之情也是大学毕业生回忆象牙塔“乡愁”的精神象征。而在智慧课堂的场景中,师生的交流被异化为数据化的符号,或为教学任务、教学管理在智慧课堂系统中的呈现,或为戏谑化、符号化的网络语言。传统大学教学注重情感体验、注重氛围教化的传统,被数据技术消解。由此也暗含着,教师手中的教学权力被新的数据权力夺取。丹尼尔·贝尔所警惕的数据权力,表现于智慧课堂带来的权力转移过程。
三、知识话语到信息话语:智慧课堂的权力转移
权力正义问题,不仅是社会管理学要考察的核心问题,也是大学课堂教学实践展开的核心问题。如前文所言,知识传授的过程,不仅意味着人类理性思考、历史经验的传递,也综合地表达着教师的个人情感、生命体验。纯粹理性的、技术性的“祛魅”,在教学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实现。即使是纯粹的、理工科的教学活动,不同的教师也会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究其原因,就在于教师本人在知识传授过程中的主导价值发挥。这也意味着,传统大学教师既是知识的象征,也因这种象征而享有课堂话语权。
在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内,教师享有知识话语的地位被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文化演化为“去权威化”的利器:师生在大数据环境内,享有同等的知识信息获取渠道,甚至在某些领域,教师掌握的信息量远不及学生。以笔者自己的教学经历为例,笔者担任了全校的通识必修课教学,某次多班大课堂以“明星薪酬与社会贡献”议题展开讨论。课堂氛围极其活跃,同学们纷纷提供各种明星薪酬信息,笔者提供的信息显得苍白无力:既没有同学们的信息丰富、翔实,也无法有力论证自己的论点。笔者的真实感受,如同一个第一次见到智能手机、手足无措的世外之人。更让作者感到挫败的是,这些信息冲淡了教学的主题、冲淡了价值的探讨。课堂氛围固然活跃了,却不能实现信息穿透、寻求价值批评的教学目的。教师对课堂的主导权力更无从谈起。智慧课堂不仅打造了脱胎于现实社会的“赛博空间”,更打造了信息公平传播的乌托邦,在大数据技术面前,师生都享有公平的信息权力,也就意味着传统教学实践中的信息壁垒被打破,知识话语营造的权力伴随着信息话语的冲击,成为光辉的历史。知识也开始被信息取代,新权力结构在智慧课堂环境开始逐渐形成。
“每个人都想让所有都围着自己转,要拥有所有,至少是掌控所有,但凡违抗他的,他就让他消失。”[8]283当信息、数据等技术产物衍化为权力的依据时,信息话语从课堂管理的后台走向了前台,课堂的权力分配系统开始重新整合:首先,技术平台的权力高扬,传统的师生二元话语交流结构转化为师生和技术平台的三元交流模式。技术成为新兴的权力型力量,开始主导课堂权力的展开:“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强调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组织新技术、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的一条中轴”[1]107。其次,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中,象征着技术力量的技术人员高度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不仅负责技术协调、数据关系协调,而且参与到教学管理、课堂管理中来,“技术人员还是当权者及其追随者不可或缺的行政参谋”[1]342。某种程度上讲,智慧课堂对技术人员的高度依赖,已远远超过了对教师的依赖。第三,教师如若要适应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只能接受信息权力的规训:一方面要学会适应海量信息介入教学实践的现实,从容应对信息权力主导课堂的新局面;另一方面要接受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碰撞的现实,主动改变思维方式。智慧课堂以技术力量撕裂了传统教学实践中的权力主导模式,在改变教学生态的过程中,不断吞噬着教师的主体价值,并且改变了传统教学的内容主线,实现了由知识传授到信息传播的转型。无论是教学权力的转移,抑或是教学内容主线的转型,都意味着传统大学教学生态的颠覆性变革,当然这也内含着技术变革可能带来的隐患。
四、数据鸿沟与人文思考:智慧课堂的技术批判
与其他技术乐观主义者一样,丹尼尔·贝尔对新技术怀着热情的向往:“交通和通讯革命把世界各个社会联结成一个巨大联合体。这意味着古老的地区性文化走向解体,而世界各地的艺术、音乐和文化汇流入一个全新的兼容并蓄的容器,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它,也有义务推动它”[1]179。大数据技术实质性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和大学教学的方式,给大学教学实践带来了创新的力量和变革的动力,但不可忽视的是,大数据技术业已给整个社会带来新的阶层分化,以之为基础的智慧课堂也可能带来“数据鸿沟”。
“数据鸿沟”一词最早出现于1995年美国商业部电信局(NTIA)发布的《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9]。所谓数据鸿沟,是指互联网时代因技术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分化现象:技术落后地区的族群,因无法融入大数据时代而逐渐被社会遗弃;新技术娴熟且能融入大数据潮流的发达城市族群,则能够因大数据技术而获益。数据鸿沟的出现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的“马太效应”:“后工业社会为地位和权力之基础、获得途经增加了一个新的标准,技术竞争力成为实施权力的条件之一,高等教育则成为获得技术能力的手段。这使得权力的金字塔出现一种位移,在关键机构中技术竞争力成为最首要的考虑”[1]400。
在大学信息化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数据鸿沟现象十分明显,以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为例:青年教师能够娴熟地使用各种课堂软件,中老年教师在大数据时代则显得黯然无光,除了极少数强调人文积淀的学科教学交流外,大部分中老年教师早已远离了教学实践交流的“赛场”。鉴于各种教学活动均能在智慧课堂上展开,青年教师也不再向中老年教师请教教学经验,只要能熟悉智慧课堂的操作系统,它就能提供人工智能化的教学流程——青年教师能否上好一堂课,仅需要向技术人员请教即可。掌握技术的人成为教学的主导者,远离技术的教师被隔绝于数据鸿沟的另一侧。这或许是当前大学教学信息化、技术化改革必须正视的新问题。
依托于大数据技术的智慧课堂,把技术的力量带入到大学实践中,演化为一种重建大学课堂的新力量。它把内在的数据逻辑和数据算法转化为控制教学的新力量,数据权力成为渗透性的、内化的控制性力量。教师被湮没于技术的背后,数据技术从后台走向前台,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地掌控着智慧课堂环境中教学实践的展开。师生的人文身份不再被关注,但凡能适应智慧课堂的就能继续自由地展开教学,但凡不能使用智慧课堂的就会被技术排斥成为另类。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及他对教学实践的观察:学校的铃声本身是一种声音的传播,但进入到学校氛围之后的师生,只要听到铃声响起,就会自觉地接受学校纪律的管束[10]170。铃声异化为鞭策、规训师生的控制性力量:认同铃声,就意味着认同学校的教育;反之,则被视为违反纪律。学校场景构建的本质是要实现教书育人的功能,而学生服膺的不只是教书的先生,还有课堂的铃声。智慧课堂的教学场景中,技术的力量如同铃声一样,接受了它的规训,才能展开教学实践;反之,则被技术权力所淘汰。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能者统治与平等”一节中,丹尼尔·贝尔引用了英国社会学家《能者统治的出现》这则寓言。寓言讲述英国进入“技术能者”的统治时代,“所有的才智之士被提升至一个共有的精英阶层,居于下游的人们对自身的失败无可辩解;他们被贴上受排斥的耻辱标签,是人所共知的低能者”[1]384。寓言中讲到2034年的英国爆发了一场民粹主义的革命,革命者认为“生活不能由数学方法来治理,每个人应当发挥多样化的功能来主导自己的生活”[1]384。这种忧患,可以启发大学教育者对智慧课堂技术的反思:技术的发展应当造福、服务大学教学,如今却演化为异化的控制性的力量;大学教育中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传统人文精神,被技术消解。智慧课堂的技术弊端也带来其他隐患,如师生的隐私保护、智慧课堂背后互联网公司的商业诉求等,这些都意味着唯有回归到大学教育的人文初心和价值诉求,明确智慧课堂等大数据技术服务教学的从属地位,才能在大数据时代保留大学教育远离物化、崇尚人文的象牙塔清安。丹尼尔·贝尔警惕地认识到了技术进步对传统社会的撕裂和可能导致的全面技术异化,以他的立场反观高校智慧课堂的建设,可以为当前信息化教学实践的深入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批判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