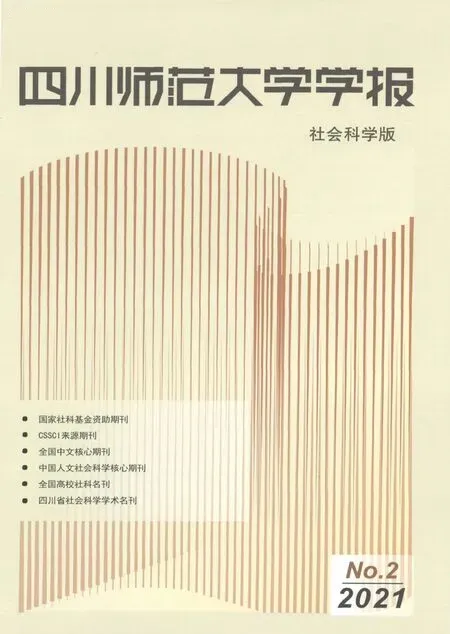科幻英雄的神话之旅
——论《一无所有》中的仪式思维
肖达娜
神话英雄的主题和古老仪式的思维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地潜藏于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文学艺术作品之中。无论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还是歌德的《浮士德》,都一遍遍地重复着神话英雄人物在追求永生和真理途中所经受的考验、苦难及跋涉的故事,演绎着原始成人礼仪中新员(novice)们在时空和主体上所经历的隔离、边缘和聚合的仪式过程。坎贝尔曾明确表示原始信仰中的仪式思维是其英雄之旅思路的来源:“神话英雄历险之旅的标准道路是成长仪式准则的放大,即启程-启蒙-归来。”(1)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28-36.坎贝尔在其著作《千面英雄》中多次提到原始信仰中的仪式思维是其英雄之旅思路的来源。成长礼仪,作为最重要的过渡礼仪,为弗雷泽的古代仪式案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的梦的精神分析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分析等都提供了原始理据。而成人礼仪,作为原始社会中最重要的过渡礼仪之一,完美呈现出从分隔(Separation)到边缘(Marge),再到聚合(Agregation)的仪式结构(2)〔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xiii页。。
美国当代科幻作家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的巅峰之作《一无所有》(TheDispossessed),同时包揽了星云奖及雨果奖两项科幻界最高奖项,是20世纪70年代幻想文学复兴的重要标志。小说虚构了阿纳瑞斯(Anarres)和乌拉斯(Urras)两个截然不同却原本是同宗的星球世界。除了物质的运输和交换以外,两个星球之间没有人员往来,对彼此的认识都还停留在一百多年前所存的录像带画面。小说主人公谢维克是阿纳瑞斯星球的一名物理学家,他试图突破传统的时间观念,打通序时(the sequential theory of time)和共时(the simultaneous theory of time)两种时间概念,推算并发展出一套“通用时间理论”(a unified temporal theory)。由于在时间物理学方面的天赋和创见,他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受邀赴乌拉斯星球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的阿纳瑞斯人。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以讨论共时原理为主线的科幻星际旅行小说,其科学理据建立在仿连续性的物理学(simulsequentialist physics)之上。从结构和内涵上看,它却是建立在古老仪式思维基础之上,以原始社会的成人礼仪为雏形的神话英雄之旅的现代重释,是超越故事的故事。
一 启程——隔离
在神话语境中,英雄往往会被命运选中,受到历险之旅的召唤。在进入陌生世界接受挑战与考验之前,他首先需要告别过去的身份,并与先前的环境相分离。这是神话英雄启程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原始成人礼仪的第一阶段:隔离。
范热内普对原始部落或族群所举行的成人礼仪进程做了细致的考察,发现“新员被与先前的环境分隔,相应地成为死人,以便被聚合到新的环境——他被带到森林,受到隔离、清洗、鞭打、被棕榈酒灌醉,最后进入麻醉状态”(3)〔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第85页。。 此类现象反映出隔离的象征意义,表现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处境或状态(state)之中分离出来,为进入到另一处境或状态做准备。因为,在原始人看来,如果不先脱离凡俗的境地,就不可能与神圣世界建立亲密联系。可见,隔离的作用在于净化,并最大限度地为未来世界腾出空间。通过这一净化过程,新员获得了进入神圣世界的资格。他们原先的世俗身份和待遇都被剥去,连名字也被统一的称呼所取代,同时还象征着新员身上原有的差异被彻底消解,将在绝对平等的新环境中被重新塑造。
(一)被选中者:命定的英雄
神话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往往都具有区别于凡人的特殊身份: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阿伽门农和智勇双全的奥德修斯都是宙斯的后裔,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阿喀琉斯则是阿耳戈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之子。他们都是被神选中的英雄,具有过人的胆识和才华,与先前的环境相隔离,踏上历险之旅。作为天赋异禀的时间物理学家,谢维克因发表“共时理论”的学术创见受到母系星球乌拉斯的邀请,成为第一位迈入乌拉斯星球的阿纳瑞斯人。他的特殊身份、才能使他成为命定的英雄,而对“奧多主义”(4)奧多主义是小说中阿纳瑞斯人的宗教信仰,源自两百多年前最初起义者奧多的思想。信仰的笃定和坚持,则是他开启英雄之旅神谕般的指引。
在成人礼仪中,新员凡是想要加入某组织,或是进入某一新的社会阶段,往往需要“穿戴不寻常的衣饰,举止犹如神经不正常,借此,他表现出他与众不同”(5)〔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第87页。。小说突出描写了谢维克在幼年求学时期另类的课堂表现,与同学们一起恶作剧时内心的犯罪感与道德感的矛盾交织,孤僻的性格与世俗环境的格格不入,以及29岁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西奥·奥恩奖得主等,都从侧面烘托出他的与众不同。另外,谢维克一方面对祖先的行为和信仰坚信不疑,时刻奉行“奧多主义”理念,尊崇其“女性化”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潜心于科学理论研究,具有相当成熟的理性思维,崇尚科学世界中的“阳刚”之力。他的身体和思想内部存在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与矛盾、斗争与统一,是神的双面性特征的体现(6)神话故事中神的本性中总是交替甚至同时存在着对立和统一:光明与黑暗、冬天与夏天、战争与和平、创生与毁灭、男性与女性、仁慈和残暴……因此,对立与统一是一种神的原型模式。。
种种迹象表明,谢维克自幼的特立独行和过人才华,以及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神性与人性的对立统一,使他成为“被选中者”(the selected),即命定的英雄(7)伊利亚德在对“神显的结构”进行分析时提出:“所有这些神显和力显表明有某种挑选,被选中的事物被认为就是强大的、灵验的、令人敬畏的或者是多产的,即使该物‘被挑选’出来是因它与众不同、新奇或畸形。” 参见:〔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姚蓓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他所致力研究的“共时理论”,看似这次旅程中的世俗使命,实为一把开启神圣回归之门的钥匙。
(二)历险的召唤
英雄一旦被命运选中,将会接受历险的召唤,背离故土,踏上陌生的征程。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科学理性让谢维克明确地认识到两个星球之间的差距。录像带里母系星球的影像不断激发着他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与乌拉斯科学家的通信交流令他兴奋不已,并渴望亲身参与学科前沿的研讨和对话;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惯于剽窃他人观点的伪学者萨布尔署名发表,触发他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情绪……那个未知的世界——乌拉斯,一直吸引并召唤着他,各种有待探索的疑问和被压抑的欲望在他内心发生着摩擦、碰撞和升温。如同英雄受到命运的召唤,“熟悉的生命范围被突破,旧有的概念、理想和情感模式不再适用,超越阈限的时刻即将到来”(8)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47.。谢维克不再满足于阿纳瑞斯星球为他提供的研究条件,更不甘于继续忍受萨布尔势力对他学术自由的干预和限制。相反,乌拉斯星球的学术氛围和条件让他心动,促使他迫切地想要逃离现状、抛下陈旧的自身,去尝试、体验围墙之外的他者文明。
在原始社会中,当一个个体被认为进入了社会成熟期(9)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一书中将生理成熟期礼仪与社会成熟期礼仪进行了区分,本文中的成人礼仪意指不单纯以年龄和生理变化为标准的社会成熟期礼仪。,人们将会为他举行相应的成人礼仪。一旦被认定,他将被带到陌生的环境,或森林,或单独的房屋,或其他神圣之地,与先前的环境相隔离。此时的新员往往会表现得如同婴儿一般,对即将进入的新环境既好奇又恐惧,既向往又担忧,多种情绪复杂交错。谢维克也一样,等待着他“越墙”行为的,将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里充满了诱人的新知,隐藏着未知的危险与考验。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谢维克出格的跨界行为,他被故土的居民们认为是叛徒、杂种、逃逸者。在迈出代表国界的那一堵“墙”,踏上星际飞船之前,他遭到了本国人民的唾弃、谩骂和攻击,手臂被石头砸中,受了重伤,精神也处于极大的恐慌之中。谢维克的行为颠覆了传统,违背了同胞们的意愿,一方面象征英雄脱离熟悉的环境,与过去彻底决裂;另一方面也暗示这是一次历险的召唤,前方的道路布满了荆棘与危险,迎接他的,将是一段通向未知的、艰难的磨砺之旅。
(三)赤裸的主体
赤裸的主体,是英雄在进入历险之旅接受考验之前,与过去诀别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以伊阿宋为首的阿耳戈英雄们为了取得金羊毛,航行于迷宫般的大海,他们身上原有的各种代表权势、地位、威望的标签被摘除,以赤裸的新员身份面对陌生的岛屿、森林、气候、怪兽和女妖。英雄必须以赤裸的主体迎接全新的旅程,这一要求突出体现了原始成人礼仪中分隔礼仪的核心思想——净化。涂尔干在考察澳洲土著部落的仪式过程时发现:土著人要被允许参加仪式,就必须脱得精光,赤身裸体。初成年者必须离开他始终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甚至要离开一切人类社会(10)参见:〔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20-425页。。可见,在成人礼仪中,对新员进行鞭打、清洗、模拟死亡,将其带离先前的生活环境等,都是为了使其与旧的、世俗的世界告别,以便为进入新的、神圣的世界做准备。
“我什么也没带。”(11)Ursula K. Le Guin, 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 (New York: Harper Voyager, 1974), 13.谢维克独身一人、两手空空地开启访问乌拉斯之行,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对书名“一无所有”最直接的呼应。在去往乌拉斯的星际飞船上,他呕吐、昏迷,沉睡许久之后醒来发现自己被锁在客舱内,原有的衣服也已经被拿走。“他把自己全身上下都洗了一遍。”(12)Ursula K. Le Guin, 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 10.在原始社会的各种成人礼仪中,青春期的男女必须接受时间和空间上的隔离,遵守诸多禁忌,清洗自身之后,才被允许进入社会和下一个人生阶段。因此,新员往往被假扮成已经死亡的状态,所以常常都是裸体的。为了让新员看上去更像是已经死亡的人,他们的身体有时会被涂成黑色、白色或者红色,有些部落甚至会在新员的身上涂满鲜血。他们还需要割断亲情的纽带,与母亲、姊妹彻底分隔,或被单独安置于某个偏僻的房屋内,或身无一物地独自走入森林。
在踏上新的征程之前,谢维克拒绝了与自己母亲和解的可能,被隔离在陌生的船舱中,赤裸主体,清洗全身。这些都是英雄接受净化、脱离过去的象征。在隔离阶段,谢维克原有的一切特征和属性都必须被清除,包括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甚至固有的观念及信仰。他两手空空、主体孤独,为进入陌生世界吸纳新的思想和经验腾出空间,敞开自身去迎接未知的机遇和挑战。
二 启蒙——边缘
英雄一旦启程,将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进入一种迷宫般的阈限状态。他原有的认知和经验完全失去效用,在神谕的指引和全新的实践中接受启蒙。因为“处于阈限阶段的初次受礼者必须是 tabula rasa,即一块白板,而其所属群体的知识与智慧将被刻在上面”(13)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这种一无所有的状况是阈限阶段的重要特点,范热内普将它称为边缘:“凡是通过此地域去另一地域者都会感到从身体上与巫术-宗教意义上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一种特别境地:他游动于两个世界之间。”(14)〔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第22页。成人礼仪中的边缘阶段往往相当长,因为新员需要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去学习成长、挑战危机。他遵行积极的教导,由神父-巫师指导,说特别的语言,吃特别的食物,学唱神圣的歌,了解社会的秘密,学习秘技或得到必要的知识(15)在《过渡礼仪》中,范热内普调查并梳理了诸多民族志资料中的成人礼仪过程,发现新员在进入“边缘”阶段后,会接受来自自然或人为的各种形式的启蒙。。边缘提供了一个凡俗与神圣、同质与同志的混合体,使新员得以被重新塑造,并被赋予额外的能力,去适应生命中的这一新阶段。依照沃林格的说法,“一切呈现出界限的东西都成了一种暂时的过渡”(16)〔德〕威廉·沃林格《抽象与移情》,王才勇译,金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146页。。穿越阈限,实际上就是穿越边界,创造过渡到对方世界的一种可能。
从谢维克踏出阿纳瑞斯的那一刻起,他就进入了边缘,成为两个世界的局外人。当星际飞船离开故土,他感受到了“无所属”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他现在失去了周遭的一切,剩下的只有自我”(17)Ursula K. Le Guin, 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 6.。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脱离了那个曾经熟悉的环境,即将进入却又还未进入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之前,他的那种不属于此、也不属于彼的孤独感愈发强烈。他游走于两个世界的边缘,接受了来自物质、性和生命的各种极限的考验,际遇了不同的引路人,由此获得新的经验和体悟,实现精神和认知的双重升华。
(一)物质诱惑——在物欲中迷失
阿纳瑞斯和乌拉斯两个星球原本是同宗的。两百多年前,由于宗教信仰的冲突,奥多主义者们起义离开乌拉斯,来到沙漠般贫瘠但矿产资源丰富的阿纳瑞斯星球,开创自己的新世界。这里物资匮乏,环境恶劣,没有一片绿叶,没有一种陆地动物,只有人类、鱼类、虫和霍勒姆树(一种生长在沙漠地带的灌木)。与此相反,录像带里的乌拉斯却是另一番景象:男人们整天躺在沙滩上,等着无产阶级的人为他们献上食物,女人们连肚脐眼上都装饰着五光十色的珠宝。
来到乌拉斯,谢维克受到来自上层社会的贵宾待遇。他参加各种高端学术会议,被众人崇拜称赞,游历城市名胜,享用美食及奢华套房,为乌拉斯的美景和各种现代化设施所折服。在乌拉斯商业街上,奢侈的珠宝礼品琳琅满目,连糖果及生活用品的包装都无比精美,这是阿纳瑞斯人在录像带里才能看到的东西。现在,谢维克就置身于这个繁华世界之中,被这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所震撼。他在奢华的富人区购物、用餐、散步,与美丽的女伴享受浪漫的约会……面对梦境一般的乌拉斯,他产生了烦躁和叛逆的情绪,羡慕并嫉妒乌拉斯人拥有的一切。他的奧多主义信仰发生了动摇,甚至开始质疑祖先们两百年前离开乌拉斯的决定是否正确。很明显,“他已经爱上了乌拉斯”,然而,“他在这里是孤立的,因为他来自一个自我放逐的社会”(18)Ursula K. Le Guin, 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 89.。
天堂般的乌拉斯吸引着他,将他拽入了物欲的漩涡。他在物欲的迷宫中徘徊,渐渐忘记了自己是谁,来自哪里,将去向何方。这一现象反映出新员在原始成人礼仪中进入到边缘阶段所呈现的状态。无论是新员受到鞭打至暂时失去意识,还是被要求跳舞直至昏厥,又或是被棕榈酒灌醉昏迷不醒、被迫喝烟叶汁而“发疯”,其目的都是使其进入麻醉状态,以便顺利过渡到边缘期。
(二)酒后狂欢——女神的诱惑
爱与性,无论从古老的神话学,还是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看,都是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机遇与危险的象征。神话中的女性可能是代表爱与奉献的母亲、姐妹、情人、新娘,也可能是代表引诱、邪恶甚至毁灭的女怪或妖妇。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总是一方面受到如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佛洛狄忒等女性神灵的暗中帮助和指引,一方面又会遭遇像邪恶的魔法女巫喀耳刻,又或是以甜美歌声引人走向覆灭的塞壬女仙等女妖的引诱与祸害。在南美洲大多数神话中,主人公往往也会遇到两个女性人物,一个是食人女妖,代表黑暗;另一个则是太阳之女,代表光明。这种昼夜的对比也符合宇宙间的二元结构。
可见,“遇到女神”,是英雄必须经受的重要考验和获得启蒙的方式之一,也是新员在进入到边缘阶段后,与神圣世界相结合的象征。“女神”就是神的化身,她诱惑、引导、命令英雄突破自身的羁绊,如果他能配合她的启蒙,那么两个人——求知者和知晓者都能摆脱各种局限(19)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100-110.。
谢维克在英雄之旅中经历了与两位“女神”的邂逅与结合。一位是纯洁的、奉献的、正面的女神塔科维亚。她陪伴谢维克成长,给予他无私的爱与帮助,对他的人生具有引导和启蒙的作用。另一位则是魔性的、索取的、引诱他犯错的邪恶女神薇阿。薇阿的身体对谢维克具有极大的诱惑,她女性化的、时尚的装扮,各种妩媚的姿态、神情,一切都充满了挑逗的意味。用塔科维亚的话来说,薇阿就是身体投机分子的终极代表。在薇阿举办的家庭晚宴上,酒精的驱使,薇阿裸露的双乳,缀满珍珠的脚趾,挑逗的神情,使谢维克彻底陷入了性欲的迷狂。他感觉一切都变得阴暗起来,不可抑制地沦为性的奴隶。直到精液喷涌而出,他才羞愧地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肮脏的傻瓜”(20)Ursula K. Le Guin, 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 232.。
“猥亵的攻击所具有的巫术力量广受赞美,甚至在高度发达的祭祀仪式中也会发生。”(21)〔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第353页。谢维克对薇阿的性侵犯是典型的猥亵行为,这是在迷宫和考验阶段英雄试图打破陈规,获得性自由的表现。在酒精作用下,他射精、晕厥、呕吐……在此过程中,谢维克经历了狂欢、颠覆,重新体验了世界创造之初的混沌,回归到无形、无差异的前宇宙存在形式,旧的自我死去,新的自我复原再生,英雄将重新创造世界,给混沌带来秩序。
(三)直面死亡——生命的考验
在神话语境中,死亡不仅带来重生(《金枝》中的“死亡-复活”仪式就是典型例证(22)〔英〕J. G. 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汪培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4-28章中关于“死亡-复活”的仪式。),还将世俗升华至神圣和超越历史的层面。仪式中的“假死”(23)原始仪式中的“假死”,又常称为“仪式性死亡”或“模拟性死亡”,是一种象征性的死亡。,使“死亡”成为过去式。“死亡不再是即将到来的潜能,而是存在的过去,是它的基础、它过去的现实”(24)〔意〕马里奥·佩尔尼奥拉《仪式思维——性、死亡和世界》,吕捷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9页。。
当谢维克逐渐从物欲和性欲的迷醉中挣脱出来,迎接他的,是来自生命终极层面的挑战——死亡。乌拉斯下层社会向他发出邀请,仆人艾弗尔对他讲述了关于这个富饶美丽、繁华光鲜的星球的另一面:老鼠、兵营、精神病院、救济院、当铺、死刑、小偷、出租房、失业、阴沟里的死婴,等等。天堂般的乌拉斯,原来只是一个包装盒,而谢维克自己也被包于其中。这时他才意识到,乌拉斯是上等人的天堂,却是下等人的地狱。这些来自又一个陌生世界的召唤不断地吸引着他,指引他冲破乌拉斯上层社会的精美包装,走入下层贫民区,继续历险之旅。
乌拉斯星球的贫民区被形容为迷宫,有其深刻的寓意。“迷宫”最原初的含义和功能,包含着守卫一个“中心”的意思。进入迷宫,就相当于一次入会礼仪,一次对英雄般的、或者神秘的旅程的征服。所以,谢维克在贫民区的迷宫经验,是英雄在获得新的启蒙之前的又一轮净化和隔离。在原始仪式中,“触摸下等级人、吃他的饭、在他的床上躺下或进入他的房屋,可以使该成员自动失去原来的等级身份”(25)〔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第106页。。谢维克进入迷宫般的贫民街区,体验他们的生活,参与他们的起义,并成为演讲者之一。然而,飞机的轰鸣、武器的咆哮,还有人群的躁动,融混成巨大的噪音,使他感到眩晕。他不清楚自己说了什么,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在一片骚乱中再度失去了本来的身份。在这个陌生的迷宫深处,他既不属于上层社会,也不属于下层民众,又一次进入了“边缘”。
“暂时死亡的思想是巫术与宗教加入礼仪的普遍主题”(26)〔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第112页。。起义到达高潮时,在一阵枪林弹雨中,谢维克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挣扎求生,与受枪伤的同伴进入地下室,亲眼目睹同伴一步步走向死亡,自己也在恐惧中陷入昏迷。这是来自生命的考验,在混乱和模糊之中,谢维克体悟了死亡,最终穿越阈限,成功地将“死亡”置于死亡的境地,把它视为新的出发点,从而跨越死亡,获得重生。
三 回归——聚合
当英雄完成启蒙,他需要带着象征智慧的神秘符号或金羊毛返回人类的国度,将在神圣世界获得的恩惠用于复兴社群、国家、地球或大千世界(27)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179.。特纳在研究通过仪式的阈限阶段特征时发现,“新员在阈限时期获得的秘密知识或‘神秘直觉’改变了新入会者心底的本质,好比在蜡上打印一般,在他身上打上了新状态的特征。这不只是取得了知识,而且是存在本身的转变”(28)〔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35页。。通过边缘阶段的考验,旧的自我随着仪式性死亡而成为历史,前方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和全新的生命历程。这一过程包含了双重含义的过渡与回归。一是地域上的过渡与回归。通过从一地域到另一地域的过渡,新员从先前的社会群体、环境聚合进入另一社会群体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二是精神上的过渡与回归。通过与神圣世界的交流,新员获得了新知,被赋予了神性,实现了自我的成长和超越。他冲破阈限,与神圣世界分隔,再以全新的身份回归到正常环境之中。在这两层含义之间,我们还可以看到仪式思维中所蕴含的重要过渡,即新员通过空间上的过渡实现了精神上的过渡。
(一)地域上的过渡与回归
在与乌拉斯下层民众一起游行的过程中,谢维克亲眼见证了两组对抗势力(全副武装的上层军事势力和贫苦的下层民众)的较量和打斗,仪式性地体验了死亡。这与原始仪式中的农业庆典或新年庆典中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的“狂欢”所要表达的意涵和要达到的目的一致,那就是要打破规则、消除界限,回归宇宙原初的黑暗与混沌。这也是神话英雄历险的终极目的——抵达世界的中心。那里有代表神力和永生的圣杯,有代表智慧的知识树。然而,通向中心的道路却困难重重、艰苦卓绝。“只有那些英雄才能注定战胜所有艰难困苦,杀死通向不死之树和不死之草、金苹果、金羊毛,或者诸如此类东西的道路上的魔鬼”(29)〔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第371页。。
阿纳瑞斯的国界,也就是小说开篇出现的那一堵墙,将墙内和墙外划分为互不兼容的两个世界。“整个星球被圈在了墙内,由此变成一个巨大的集中营,一个孤立于其他星球和其他人类的隔离区”(30)Ursula K. Le Guin, 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 2.。边界的形式可能是一座里程碑、一堵城墙、一尊塑像或是一座桥梁,它代表一种可见的界线,同时也象征着不可见的心灵的、文化的、信仰的界线。因此,跨越边境,不仅仅是地域上的穿越,更重要的是它背后隐藏的巫术-宗教意义。这面墙既是谢维克跨界之旅的出发点,也是在一个环状的过渡仪式结束之后的回归之地。
神圣的礼仪具有中枢性的作用,当开始一次征程并发现身处陌生地域时,新员便进入了神圣界域。谢维克开启这场英雄之旅的初衷,是推倒阿纳瑞斯与其他星球之间的文化隔离之墙。所以,跨越边界背后的巫术-宗教意义对他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他跨越边界,穿越时空,进入长久以来向往的理想世界。对于谢维克而言,跨出那道墙,自己便进入了神圣的界域,与新的世界结合在一起,靠近了世界的中心,同时把他先前所在的世俗世界隔离在那堵石墙之内。通过在神圣世界的过渡,他获得了特别的巫术-宗教特质,再次进入边缘,体悟死亡,然后再与当地神圣的环境分隔,重新向正常的环境聚合。
向正常环境的聚合,不止于空间维度上的过渡与回归,同时还意味着向新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聚合。因为,地域过渡的真正目的,不是鼓励人们去寻找或是创造一个完美的新世界,而是通过各种颠倒和破坏,让人们看清事物的对立面,重新认识和塑造自我,由此来达到将过去曾视为世俗的环境神圣化的目的。小说的副标题“暧昧的乌托邦”同样反映出这样一种理想。乌托邦理想是人们在一个充满变数的不确定世界里用以表达对确定、安稳生活的向往的一种文学想象。仪式是人们用有形的、固定的方式去把握和操控自然界中那些无形的、令人捉摸不透的神秘力量所做的尝试和努力。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原始仪式和乌托邦理想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因此,真正源自伊甸园神话的那个完美的乌托邦世界在空间上并不存在,它既不是贫瘠的阿纳瑞斯星球,也不是富饶的乌拉斯星球,而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暧昧的理想之域。谢维克的出走与回归架起了沟通两个世界、两种时空的桥梁,还原了原始成人礼仪的过渡和中介作用:将差异和矛盾纳入一个模棱两可的中介地带。在此处,两个世界之间的文化隔离之墙被推倒。双方清空了既有的傲慢与偏见、敌意与冲突,为彼此腾出接纳对方的空间,继而模糊了两个世界的边界,解除了彼此的误会和对立,实现了差异间的相互试探、学习与交融。
(二)精神上的过渡与回归
在勒奎恩塑造的这个现代神话中,英雄历经重重考验和磨难,突破阈限,最终成长为最真实、平凡的人,而不是万能和永生的神。小说开放式的结局为英雄的未来赋予了多种可能。通过穿越迷宫、模拟死亡等仪式行为,一切既有的、有形的观念与形式又重新融为一体,成为无形、无差异的统一体,使得全新的创造得以再生。
作为文化英雄,谢维克在边缘期的“狂欢”中冲破了信仰、国界、阶级、性别等重重障碍,从墙内和墙外两个对立面重新审视和认识世界,在差异和矛盾中看到了对立的统一,也正是在这充满对立与统一的混沌之中,孕育着无休止的生命力,显现着神圣的真实。这场成人礼仪帮助他最终推倒了无形的心墙,重新认识和理解了奧多主义的精神。他结合奧多著作中的核心思想,对健康社会的定义和功能进行了全面分析,对个人在社会中应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深刻反思。跨界之旅让谢维克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并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奧多主义者。他最后仍然两手空空,以凡人的身份返回自己的星球,去面对等待他的各种未知。只是此刻,他已经历过阈限的考验,完成了精神和心灵的修炼,实现了自我的成长与超越。
聚焦谢维克这一人物本身,我们还会发现许多巫师的特质。在原始巫术仪式中,巫师的责任和义务是沟通神圣与世俗两个世界,他本人需要重复经历如迷狂、昏厥、死亡、灵魂升天、与神交流、返回等一系列备受折磨的过程,最后将从神圣世界所获得的知识和神秘技能应用于特定的对象(如疾病、灾难等)。谢维克跨越边界,与陌生世界结合,成为沟通世俗与神圣的中介;计算出时间物理公式,拥有把握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学会陌生世界的语言,亲身体验异国文化生活;参与下层民众的游行,唱诵圣歌,发表演讲,体悟死亡。这些都是常人所不具备的非凡本领,也是原始仪式中巫师所特有的才能。
作为跨界者,谢维克勇敢的跨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精神实质和现实追求,与原始仪式中巫师为了集体的团结、大众的福祉、族群的繁衍所做出的自我奉献和所追求的世俗目的是一致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商汤为民祈雨、以身为牲祷于桑林的仪式(31)《吕氏春秋·顺民》,《诸子集成》(第六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6页。,还是人类学著作《金枝》中各种“杀死神王”仪式或是其他以人牺献祭的替代仪式(32)〔英〕J. G. 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第437-477页。,都体现出这样一种伟大的个人牺牲精神。谢维克为了推倒阿纳瑞斯与外界的隔离之墙,以身探险的行为也是这种仪式精神的再现。作为中介者,谢维克的回归还承担起两个世界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的任务。他将神圣性带回到世俗世界之中,为世俗世界的矛盾和疑问寻求解答。同时,他的回归还影响了墙外其他星球的探险者,激发了他们了解和探索这个封闭多年的阿纳瑞斯星球的勇气。在返回阿纳瑞斯的星际飞船上,一名海恩人执意要与谢维克一同着陆,和他一起面对舱外的敌人和朋友,袭击或拥抱。他的这一决定打破了历史陈规,模糊了阿纳瑞斯星球与外界之间绝对的隔离之墙。这次英雄之旅是连接两个星球的一场重要成人礼仪。它一方面帮助谢维克从精神上走向成熟,从心理上理解、接受并真正融入一个集体,另一方面还促使两个截然对立的集体在两性关系、政治主张、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颠覆和换位,赋予彼此试探、体验、交流、学习、借鉴的可能。
四 结语
仪式的意义,不在于改变或操控现状,而是作为一种中介,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铺设一条通道,发挥过渡的作用。从这层意义看,科幻叙事就是一种现代巫术仪式,它为变幻不定的世界拟造出一幅幅抽象的图景,用有形的手段和形式来对其加以干涉或定型。科幻模拟可能到来的未来(死亡或灾难),表现对种族存亡和人类命运的担忧,承载着对生命乃至宇宙的重大关切,是严肃且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人们正是在这种模拟当中,将未来根植于当下,或将它演绎为即将过去的历史,来实现一种提前运作未来的可能。
《一无所有》中谢维克的乌拉斯之行,“目的就是想要动摇一些事情,惹出点儿事情来,打破某些旧有的习惯,引导人们提出问题”(33)Ursula K. Le Guin, 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384.。他最终体悟出奧多思想的精髓——终点并不存在,过程即全部。这既是奧多主义者的坚定信仰,也是原始仪式的核心精神,即仪式的目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从结构中被释放出来之后,仍然要回到结构之中,而他们在边缘地带所经历的交融,已经为此时的结构重新注入了活力”(34)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130页。。小说开放式的结局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一场磨砺,一段过程,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超越结果,为我们提供更多自由的选择,创造更多的可能,引导我们在差异和矛盾中反思、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