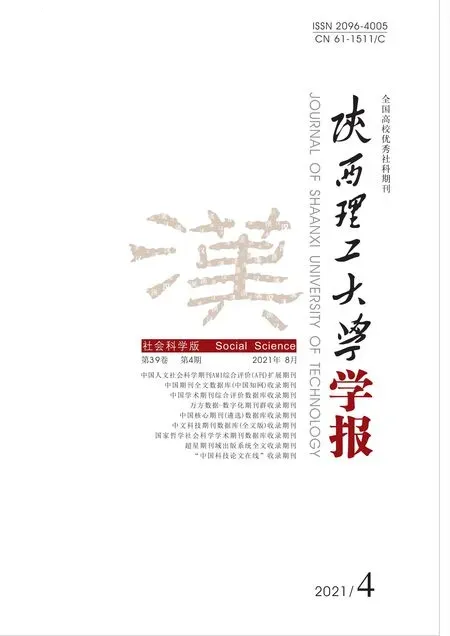唐金堂长公主晚婚原因及寡居生活新探
郭海文, 远 阳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金堂公主是唐穆宗的第四女。在《新唐书·公主传》中只有寥寥几笔的记载:“金堂公主,始封晋陵。下嫁郭仲恭。薨乾符时。”[1]3670
2010年金堂公主与驸马郭仲恭的合葬墓被发现。2013年《唐郭仲恭及夫人金堂长公主墓发掘简报》[2]16《唐郭仲恭及金堂长公主墓墓志考释》[3]52-53公开发表。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金堂公主研究的进程。但是,这两篇论文都是将驸马与公主放在一起研究,而且重点还是放在驸马身上。金堂公主的一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她晚婚的原因是什么?金堂公主守寡30余年,她是如何养育她的儿子、女儿的?本文就以这些问题展开研讨。
一、金堂公主生平简考
(一)公主的父母
据墓志记载:金堂公主生于宪宗元和六年(811),卒于僖宗乾符二年(875),享年64岁,父亲为唐穆宗,《新唐书》记载:“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讳恒,宪宗第三子也。母曰懿安皇太后郭氏。”[1]221穆宗有女凡八人,金堂公主为其第四女。母亲为郑才人,《新唐书·后妃传》录有“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贞献皇后萧氏、懿安皇后韦氏”[1]3506-3507,《公主传》载:“义封公主,武贵妃所生。淮阳公主,张昭仪所生。”[1]3669金堂公主母亲为郑才人,可补史阙。
元稹文集录有《郑氏封才人》,可大致了解郑才人生平。
郑氏封才人
敕:古者天子设六宫以诏内理,是以《关雎》乐得淑女,忧在进贤,将听《鸡鸣》之诗,岂惟鱼贯之序。郑氏,山东令族,海内良家。每师班女之文,尝慕樊姬之德。桃姿焜耀,兰行馨香。爰用择才,冀无伤善。勉当选进之重,无忘和平之心。可才人。[4]625-626
从中可看到郑氏出身山东令族,有一定的学识与道德修养。
可惜的是,“凉国以长庆元年(821)初封晋陵公主,开成中(837)改封金堂,母曰郑才人,寻殂”。也就是说,郑才人在金堂公主婚后不久就去世了。
(二)公主的丈夫
金堂公主于文宗开成二年(837)26岁时下嫁郭仲恭,“以开成二年十二月降归于我将作少监、驸马都尉、赠工部尚书郭公讳仲恭。尚书即中书令、尚父、汾阳王曾孙,左散骑常侍、驸马都尉、赠太师讳暧孙,剑南、西川节度使、司空、赠太尉讳钊之爱子”,[2]17-18此年公主26岁。(1)本文之后所引用公主墓志原文皆以此为准,不再额外注释。
郭仲恭,两《唐书》无传。据其墓志可知“曾祖子仪,有大勋力于王家,为中书令二十余载,封汾阳王,位称尚父,赠太师。祖暧,拜骑省左常侍,尚升平公主,为驸马都尉、赠左仆射。父钊,策司空、兼太常卿、赠太尉。公即太尉第五子。太夫人沈氏,驸马都尉、兵部尚书宇之女也。”[5]299《郭钊墓志》亦云“仲文,詹事府丞;仲武,鸿胪寺主簿;仲礼,光禄寺主簿;仲词,京兆府参军;仲恭,左司御率府参军,皆公侯令嗣,必复光显”[5]262。墓志与《新唐书》记载一致。子仪有子凡八人,“曜、旰、晞、昢、晤、暧、曙、映”[1]4609。其中第六子郭暧“以太常主簿尚升平公主”[1]4611。“初,暧女为广陵郡王妃……四子:铸、钊、鏦、铦”[1]4611,“(郭钊)子仲文、仲恭、仲词……给事中卢弘宣奏:‘钊妻沈,公主(长林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孙,其子仲词尚饶阳公主’……仲恭历詹事府丞,亦尚金堂公主”。[1]4612
驸马一家“姻连帝戚,内外一同,华毂朱轮,寰海无比”,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宪宗的后妃,穆宗的母亲,敬宗、文宗、武宗、金堂公主的祖母——懿安皇后郭氏,“尊居国母,凡四叶,位称太皇,实公之姑也”。也就是说郭氏是金堂公主的祖母,是驸马郭仲恭的姑姑。她其实是连接郭家与皇家的纽带。
据驸马墓志“以会昌四年(844)八月廿一日寝疾,薨于京师长兴里之私第,享年卅一”[5]299,可推算出郭仲恭生于813年,比金堂公主还小3岁。所以公主结婚时26岁,驸马23岁,但这与唐人法定婚龄“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6]1529相比,他俩都属晚婚。
二、公主晚婚原因探微
(一)唐代后期“公主难嫁”现象的影响
公主墓志做了一些暗示:“先是国家富有六合,卑视汉魏。主第或恃大宠,宣骄炽横。朝庭百吏不敢问,士人畏惮羞薄,难肯议婚姻者。”关于公主难嫁的问题,学术界早有讨论,雷巧玲从“公主婚礼有悖礼仪,使夫族陷入窘境。公主婚姻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公主和舅姑异居与习俗相乖。公主居傲纵态、残忍奸淫”[7]92-94等方面,讨论了唐人畏尚公主的原因。程国赋“从服丧制度、门第观念以及多数公主不修妇礼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士族之家不乐国婚的原因”[8]112-114。王力平则提出新的观点:他认为:“所谓‘唐代士族之家不愿娶公主’,应为进士之家不愿娶公主。”[9]116进而进一步说明:“公主婚姻发生困难一在宪宗时期,一在宣宗时期。而正是在这个特殊的阶段,进士科成为选拔高级官吏的主要途径,进士子弟的社会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到了进士群体的择婚取向,进而波及了皇室公主的婚姻大事。联姻皇室固然可以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但对于那些名闻天下的科场状元来说,既可享受庇护一门、不差不科的优复特权,高官美色自然也不难猎取,而一旦身为驸马,必然要受到公主及其身后皇室的挟制,接受诸多约束,失去许多自由。因此,在权衡利害得失后,进士子弟借‘国戚’为门户的热情必然大大衰减,他们之所以‘不乐国婚’,恐怕也就不难理解了。”[9]116
总之,因为公主不修妇礼,导致当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循规蹈矩的科举士人的畏婚是晚唐公主难嫁的原因之一。其实相对于唐前期的太平公主、安乐公主来说,晚唐时期的公主即使再嚣张跋扈也不可能比过她们,那么为什么反倒是中晚唐公主难以婚配,焦杰在《中晚唐公主“难嫁”原因新探——从太和年间的公主入道现象说起》一文中给出了解答:“中晚唐公主难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公主婚姻政策发生了改变,择偶对象由勋戚子弟开始转到士族子弟,更重要的是政局混乱,礼会院不修,李唐皇室无睱顾及,再加上宫廷政变频发,很多公主在成长过程中缺少正常的家庭关怀,由此导致她们不能适时出嫁,甚至至死未嫁。”[10]126
生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堂公主也难免受到影响,公主的父亲唐穆宗在公主13岁时就去世了,母亲位份仅为才人,也很难在公主的婚姻中提供助力。且当时政局不稳,与入道的妹妹安康公主和义昌公主相比,金堂公主幸得祖母懿安皇后郭氏的帮助,将其下嫁郭仲恭,但此时公主也已经26岁,属于晚婚了。
(二)武则天、太平公主时期女性意识的遗存
有学者认为:“从唐代高宗朝到睿宗朝的历史中,出现了女性政治人物试图提高女性地位的行动。这些行动绝对没有构成可以和现代女性主义相比拟的女权思想。不过它们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意图和含义或隐或显;至少我个人从中看到了某种‘女性主义的冲动’,一种要为自己和其他女性争取更高地位与更多权益的想望。”[11]166-167随着太平公主被杀,玄宗朝以后再未出现女主的痕迹。晚唐儒教复兴,正如金堂公主墓志所说“宪宗持礼法,变天下风俗,先去宫壸之弊,勑其爱□歧阳主家,无得骄杜氏。宪主亦能率妇道,变贵戚风俗”。此事《旧唐书》记载颇为详细:宪宗为长女岐阳公主择婿,“遂令宰臣于卿士家选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唯悰愿焉。”[12]3984因为杜悰乃宰相杜佑孙,但他却不是进士出身。进士出身的从弟杜牧还因此不服气。史载:“牧字牧之,既以进士擢第,又制举登乙第……牧从兄悰隆盛于时,牧居下位,心常不乐。”[12]3986从中就可以明白“无得骄杜氏”“变贵戚风俗”的原因了。
但在宫廷和民间还有女性意识遗存。比如吕温赞扬上官婉儿“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13]18晚唐女诗人鱼玄机在及第题名处发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14]111的感慨。金堂公主晚婚就可能与其女性意识有关。再结合金堂公主后来不同寻常的30年孀居生活,就可看出公主具有较强的女性意识;而她的不改嫁,则可以说是晚唐儒教复兴的结果,从而可以推知金堂公主的抗争与妥协。而且郭仲恭也不是进士出身。正如研究者所说:“‘安史之乱’以后,唐代政权中形成了一批以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家族为主的新的功臣群体,至中晚唐时期,其二代、三代以后的功臣子孙通过门荫、科举及与李唐皇室的姻亲关系等途径得以入仕。从郭氏家族中郭子仪第三代孙郭仲恭及其兄弟仲文、仲辞等人的入仕途径来看,可窥其一斑。”[3]54
三、金堂公主卅年寡居生活探究
婚后“凉国能用宪皇遗训,执蘋藻之礼,躬服澣濯,琴瑟宜家,自是主第,咸仰以为则”。然而好景不长,婚后7年,驸马郭仲恭“以会昌四年(844)八月廿一日寝疾,薨于京师长兴里私第,享年卅一”[5]299。此时,金堂公主刚刚33岁。他们的三个女儿“哀哀稚女,婉婉淑人,恸哭南野,悲□□邻”[5]299,还未成人。然而金堂公主并没有被中年丧夫的悲剧所击倒,而是在晚唐时期的日常生活中,继承与发扬了北朝妇女“妇持门户”[15]35的作风和武则天、太平公主的女性意识。
唐代后期,“虽然士大夫对于妇女贞节的提倡并未形成潮流,贞节观也并未大众化和普及化,政府对于节妇也并无特别实际的奖赏,但经济制度的变化,妇女经济地位的降低,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中对于礼教的重视和儒学的复兴都对妇女贞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6]899“三十年间,岁时出入中禁,入则为天子姑,姊妹尊重优渥;出则俭静,无贵勋戚之态。”所以,金堂公主三十余年间的寡居生涯在唐后期公主并非个案,她的出现进一步说明了“唐朝后期,由于纲常礼教的加强,男尊女卑的社会模式和男性对女性控制的思想模式逐渐笼罩全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逐步下降,女性又向传统角色复归”[17]77。
除此之外,与金堂公主几乎同期的唐顺宗女西河公主却是二嫁,《新唐书》载“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翚。薨咸通时”[1]4613,“铦,性和易,累为殿中监,尚西河公主。鏦(郭鏦)卒,代为太子詹事、宫苑闲厩使。长庆三年(823),暴卒。太后(郭皇后)遣使按问发疾状,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铦无嗣,以沈氏子嗣。”[18]211所以唐代后期并非没有公主改嫁,可见金堂公主孀居除了是受到了晚唐时期传统礼教回归的影响,还可能是前文提及到的公主的自主选择,是对武则天、太平公主时期女性意识余绪的继承。
1.亲自操办亡夫的丧事
丧葬礼属于凶礼,是被记载在正史礼仪志里的。皇亲国戚的丧葬礼都由国之重臣来操办,是属于男主外的范畴。驸马英年早逝后,金堂公主“既孀,尽以车服器用之有无,手庀丧事”。一个主内的女子承担主外的重任,可以看出公主非凡的魄力。正如福柯所说,“政治仪式是一种权势的炫耀、一种夸大的和符号化的‘消费’。权力通过它而焕发活力”[19]47。
2.寡母教女
有学者说:“我们在梳理历代母教史料的过程中发现,那些教育偏严的母亲,往往是在父亲的缺席的情况下,母亲身兼父、母两职,所以严慈兼具。或偏于严,历代的寡母教子多遵此道。”[20]253金堂公主也不例外,“视子弟严过于慈,家人缩缩,屏气不敢大语”。唐代公主教育孩子内容即“女子主要学习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女工技能等,而对男子主要从建功立业方面引导”[21]154。金堂公主亦是如此,“有女三人,年皆冲幼,明慧和淑,四德备焉”[22]61。“四德”是女子须遵从的道德规范,金堂公主不仅自己恪守“四德”,教育女儿也要遵从“四德”。“但她的贡献应止于‘齐家’。女性的行动领域被限定在家内和私人间,其生活中的地位是向心的”。[21]154由此可见传统儒教对金堂公主及其女儿的影响。
3.收养义子
有学者认为:“对于女性而言,相比较于与丈夫之间的脆弱关系而言,生育的完成使得她还获得了与儿子之间牢固的血缘关联,不仅意味着她由此拥有了丈夫父系血统中的一个男性成员的母亲身份,在生前可以得到儿子的尊敬和孝顺,而且也意味着她在死后也能够作为家族的成员而在祖庙里面获得被祭祀的席位,从而找到最终的人生归宿和来世生活的安全。”[22]61据金堂公主墓志记载,“有子二人,女三人,女皆淑顺有先范。长子曰缋,温和秀茂,邦族称为重厚长者,官太府寺丞。次曰元鐬,殿中少监、兼通事舍人。”然郭仲恭墓志仅载:“有女三人,年皆冲幼,明慧和淑,四德备焉”[5]299。另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录有太子家令郭缋为郭曜房下曾孙辈,通事舍人郭元鐬为郭暎房下曾孙辈。[1]3120-3121可知兄弟二人或为家族中过继者。子仪凡子八人,“曜、旰、晞、昢、晤、暧、曙、映”[1]4609,所以郭缋与郭元鐬确为郭子仪嫡系一支,为郭仲恭子侄辈。
所以可知公主与驸马仅育有三女。二男是驸马死后,公主收养的。虽然收养的二子与公主没有血缘关系,但收养子嗣是延续家族香火的主要途径,“促进这一家族体系的延续和兴盛成为她应当承担的重要责任与人生目标”[22]161。这样的大事情,公主是在驸马亡后,一个人完成的,可见其在家庭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4.代子求官
公主墓志:“三十年间,岁时出入中禁(2)“中禁”当为“禁中”之误。“禁中”,皇帝所居之处。:入则为天子姑,姉妹尊重优渥;出则俭静,无贵游勋戚之态。”但公主具体做了什么,墓志语焉不详。
《颜氏家训》有这样的记载:
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15]35
从中可看到金堂公主“持门户”的影子。如果再结合公主收养的二子在官场上的发展,“兄弟二年间,特恩赐朱绂银章,时人荣之。元鐬倜傥多智略,弱冠升朝,能用贤善老成人交。外则罄□奉宾□,居则幹□□员箎,雍睦晏如也”,就可推知公主出入禁中与代子求官有很大关系。难怪墓志感慨“呜呼!可谓贤明德度,有母仪矣。”也就是说:“只有当对父系家族体系的稳定秩序和顺利传承并不构成某种现实的威胁,或者是作为对男性缺席时的一个重要‘补充’的时候,女性跨越‘内’的界限,参与外在事务的作为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并最终获得主流文化传统对于她的最终承认和尊重”。[22]47
所以,金堂公主去世时能获得赠谥并享有鼓吹,就不令人费解了。
所谓“谥号”,就是用一两个字对死者的一生做一个概括性评价,“是丧礼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既是对死者在天之灵的追思悼念,又是带有浓厚政治性的宣传。因为谥皆采用对死者生时的行为活动作出政治性的结论”[23]87。赐谥取决于“圣裁”,充分体现了皇帝“悼往推恩,旌椒兰之懿行,传美名于千古”。金堂公主逝后,被册封为“凉国大长公主”,其中,“凉国”是金堂公主死后,僖宗为其所赠的封号,也是一种尊称。“大长公主”指明了公主与僖宗的人伦关系。唐制:皇姑为大长公主,正一品。另还定谥为“定康”,《逸周书·谥法解》曰:“定”即“大虑静民”“安民大虑”“安民法古”“纯行不二”;“康”即“丰年好乐”“安民抚民”“令民安乐”[24]678。从这些字眼中,可以了解公主美好端庄的品性。《新唐书》中对公主的封号、谥号等未有明确的记载,可补史阙。
至于鼓吹,本为一种用鼓、钲、箫、笳等乐器合奏的一种器乐合奏曲,汉初边军用之,以壮军威,后渐用于朝廷。《唐会要》记载:“鼓吹之作,本为军容。”[6]691-692韦后《妃主给鼓吹表》曰:“自妃主及五品已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请自今婚葬之日,特给鼓吹,宫官准此。”[25]10458-10459她的提议遭到太常博士孙绍的反对,足见唐代对于丧葬使用鼓吹的资格有着严格的限制。金堂公主之所以享用“鼓吹”,是因“长达30年的寡居生活,使她在家内领域拥有了自由和受人尊敬的空间”[21]227。
金堂公主通融于内外界限之间,集中体现了受教于道德儒家学派中的女性所拥有的可能性和限制。
金堂公主志文向我们展示了唐代后期公主生活的面貌,作为一位经历宪、穆、敬、文、武、宣、懿、僖八朝的公主,她因为唐代后期“公主难嫁”现象及武则天、太平公主时期女性意识遗存的影响等原因晚嫁,又备受晚唐时期传统礼教回归的影响,囿于家庭藩篱,无法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甘作贤妻良母,孀居30余年。金堂公主在抗争与屈服中走完了自己64岁的人生,最终葬于郭氏家族坟茔,唐后期皇室公主的生活面貌或由金堂公主墓志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