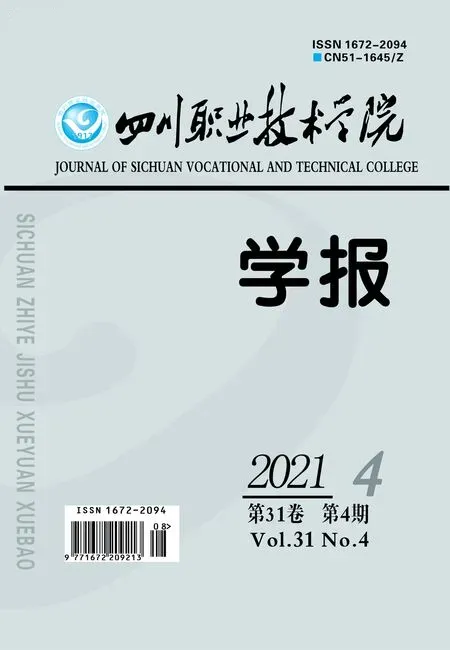论斯捷潘诺娃《记忆记忆》的后现代叙事特征
王雪婷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昆明 650500)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Mapия Степанова),当代俄罗斯诗人、作家、记者、编辑、出版人,1972 年出生于苏联一个犹太家庭,著有十部诗集和三部散文集,主办俄罗斯独立文艺资讯网站colta.ru,月访问量近百万。曾获德国传媒大奖“斑比奖”“帕斯捷尔纳克文学奖”“安德烈·别雷奖”。斯 捷 潘 诺 娃 的 代 表 作《 记 忆 记 忆 》(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是她的第一部小说,该小说于 2018 年一出版便夺得当年俄罗斯文学界三大奖:“大书奖”“鼻子奖”及以托尔斯泰庄园命名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之“读者选择奖”,随后迅速被译为德、英、法、意、瑞典、芬兰等多国语言。《记忆记忆》被出版社定义为融合了历史、哲学与文学的新型复合小说。小说由两条线串起:一是作者追寻家族先人的足迹,从自己犹太家族几代人的生命故事中,回溯俄罗斯近代史中的自我家族史,并对历史进行反思;二是作者由家族先人的旧物、文献引发思索,同时将二十世纪欧美文艺界纳入其中,对这些试图“回忆”的人们作了文学与哲学的思辨。《记忆记忆》这本有着全新体裁的跨文类写作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后现代叙事特征。
一、碎片式:消解文学体裁界限
碎片式叙事是后现代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不同于传统的小说以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之线性结构来展开故事的情节,“后现代主义者不以追求有序性、完备性、整体性、全面性、完满性为目标,而是持存于、满足于各种片段性、凌乱性、边缘性、分裂性、孤立性之中。”[1]他们在创作时常常“有意消解故事、消解小说独特的叙述方式,同时也消解文学中不同类别的体裁的界限”[2]。斯捷潘诺娃创作《记忆记忆》也颠覆了传统叙事模式,使得作品在结构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出碎片式特征。
首先,《记忆记忆》结构形式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碎片化倾向。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各个章节可以相对独立,由此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呈现出碎片化特征。《记忆记忆》全书分三部分共二十二章,另外斯捷潘诺娃将家族中亲人的部分原始文件(日记、书信)作为“插章”放入其中,共有六个“插章”。作者以每一章节论述的主题作为章节标题,各个章节之间的关联性不是很强。同时每一章节内部又被作者分为若干片段,统一于章节主题之下。如第一部分第三章《若干照片》,作者用二十个片段分别描述了二十张照片。然而,这种看似杂乱的文章结构布局其实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所有的“碎片”实则都统一于“记忆”的主题之下,恰似一个文字的“康奈尔盒子”。各个章节表面上看似独立,实则如康奈尔制作的盒子,“都并非单个作品,而是一整个系列,由众多相互补充的作品完成”[3]258,这些不同质地形状、不同大小类别的作品,在文本的方寸之地中,组合成了一个微观而宏深的世界,为自我家族史在近代史中的呈现创造了一个可以使之显形的空间。
其次,《记忆记忆》在内容上的拼贴也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反体裁倾向。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具有“元小说”的性质,文本中的内容更多时候展现的是叙述者由一系列人、事、物引发的关于记忆的思考,颇具意识流色彩。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不断插入其他不同种类、不同文体的作品,这些内容多为分析、研究、评论,其中甚至有关于记忆的考据性学术文字。小说的前两部分,作者对祖先的原始文件(日记、书信)、照片的描述和日常生活用品的描述相互交错,形成个人档案与宏大叙事交错的叙述模式。同时,为了填充记忆的“康奈尔盒子”,斯捷潘诺娃将二十世纪欧美文艺界的许多人物纳入文本,而且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群几乎被一网打尽,从本书译者的二百余条注释中,可看出其中不乏作家、诗人、摄影师、画家、艺术家。斯捷帕诺娃就他们关于记忆、物品、过去与未来的观点作了文学与哲学上的思辨。其中包括关于拉斐尔·戈德切恩、弗朗西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赛巴尔德(W.G. Sebald)、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敖德萨(Odessa)等人,关于老照片、“冰人夏绿蒂”(frozen Charlottes)陶瓷娃娃、夏洛特·萨洛蒙(Charlotte Salomon)的画作集《人生?如戏?》(Life? or Theatre?)、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的代表作《翠尔比》(Trilby)等物和许多地点的随笔。这些内容和故事互相说明,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拼贴”式叙事,使得小说成为各种文类“拼贴”的万花筒,从而消解了文学不同类别和体裁的界限。
斯捷潘诺娃以碎片方式消解文学体裁界限,此举之动力显然源于作者拯救和保存的愿望,她所讲述的自己家族的人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只是俄罗斯-苏联社会剧变中隐隐绰绰的存在。而《记忆记忆》便是斯捷潘诺娃为族人建起的记忆的纪念碑,斯捷潘诺娃自己也谈到:“我在写作《记忆记忆》时并不觉得是在写一部小说,它更像是一个总和:不同体裁、不同形式都在其中共存并被重塑。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份家族研究、一部成长小说、一本旅行之书、一篇文章、一片展示的空间……我感觉最后这个定义直击核心:在与悲剧时代的大叙事有着内在关联的各种故事和遗物间,我希望自己建筑起了一个空间,我的家族故事和家族残留都安全而自由地储存于其中。因此,没有必要按顺序一章章地来读这本书,你可以从任何一页开始读起。这不是一本能很快看进去的书,但如果它能成为一个‘时间转换器’,我会很高兴”[4]。
二、互文性:文本的互动联通
自从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互文性”便在在意识形态及诗学领域都占据了重要位置。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5]。也就是说文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是与其他文本或社会背景进行互动联通。实际上,“互文性召示了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6]因此,任何作家的写作都必定会与前文本构成指涉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开放而且流动的文本空间,由此,文本的含义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且非静态的扩展状态,并未文本与文本之间也呈现出对话状态。在《记忆记忆》中,不同于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以“记忆”为主要叙事方式对“过去”进行的重塑与想象,斯捷潘诺娃以“互文性”策略,与“留住记忆”的写作方式对立,指出记忆未必可靠,而是应该“饶过记忆”。
首先,小说《记忆记忆》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回忆录《说吧,记忆》(Speak, Memory)在题目及创作方式上呈现互文性。《说吧,记忆》的题目以记忆女神自行发声为名,纳博科夫用以证明时间不存在。其开篇“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7],纳博科夫从降生前育儿室中的空摇篮开始讲起,空空的摇篮之下是无底深渊,这令他心生恐惧,坚决不肯把常识中的出生视做生命的起点。作品最后以一家人踏上驶向美国的巨轮时间戛然而止,从1903 年到1940 年时间跨度为三十七年,地域上从圣彼得堡到圣纳泽尔。斯捷潘诺娃的《记忆记忆》题目以记忆作为纪念,其写作跨越三十五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本档案到另一本档案”[3],地域上从俄罗斯到俄国,作者探寻家族先人的迁徙版图,搜集了许多带有记忆痕迹的物品,试图复原出先人的生活图景。但最终,她不得不承认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记忆未必可靠,所以靠记忆拼凑起来的也未必就是历史的真相。
在创作方式上,纳博科夫在将自己的这段生活进行剪辑,组成几个各自独立、彼此又相互联系的主题。同时,在处理这些主题时,纳博科夫更注重强调各部分间的非线性关系。另外,纳博科夫在每个主题之下的事件安排上以事件在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为基础,或是根据事件在记忆、回忆过程中形成的新型关系,对其进行艺术的重组。以事件相同或人物相同为主题编排过往生活碎片。如在第六章中纳博科夫围绕蝴蝶详细叙述了他对捕蝶的兴趣,及由捕蝶引起的许多误会。在《记忆记忆》中,如前文所述,文本呈现的碎片化叙事与《说吧,记忆》具有相似性,由此可见《记忆记忆》在题目上与《说吧,记忆》具有相似性,在创作方式上是对《说吧,记忆》这一“前文本”的模仿与改写。
其次,《记忆记忆》与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阿莱夫》(The Aleph)在喻说意象呈现互文性。正如巴赫金指出的“文学作者写作,不仅从语言系统里选用词句,还要从过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传统中选用情节、人物原型、喻说意象、叙述的方法、文学类别特征,以及某些词句”[8]。巴赫金认为文学文本间的对话是根本性的,巴赫金的观点对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思想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记忆记忆》中的喻说意象瓷娃娃“冰人夏绿蒂”便指涉了博尔赫斯《阿莱夫》中的喻说意象“阿莱夫”,二者形成“对话”关系。在希伯来文中,“阿莱夫”是第一个字母,博尔赫斯在同名小说中赋予“阿莱夫”以神秘力量,它包含着世间的一切,是“空间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点”[9]189,独成为一个宇宙,当凝视“阿莱夫”时,便已明晰这宇宙中隐藏的秩序。而斯捷潘诺娃则于莫斯科古玩市场上邂逅一个白色瓷娃娃,并将其买下,由此她意识到:“这次讲述的真正的‘阿莱夫’,已经被装进了我的口袋。”[3]66作家终于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一个中心喻体。
“阿莱夫”出现在《记忆记忆》封面上,是一个残缺的白瓷小男孩,光着身子,一头卷发有点像丘比特。然而它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市场上,它们不仅数量繁多,而且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大都带些残疾。这白瓷娃娃吸引斯捷潘诺娃的是女摊贩对它的介绍:这些造价低廉的瓷娃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作为货物运输中的减震垫,以免贵重物品在运输途中相互磨损。换言之,这些瓷娃娃生来就是为了牺牲的。此时,斯捷潘诺娃清楚地知道,她已经为这本书找到了的结尾:“这个瓷娃娃有多重寓意:首先,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可以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不是脚会受伤,就是脸会刮花;其次,空白和缺陷是生存的必然伴侣、隐秘发动机和加速装置;再次,只有伤痕将我们从批量产品变成独一无二的单品;最后,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瓷娃娃,20 世纪集体灾难的批量产品,同时也是其survivor 和被动受益人,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3]67斯捷潘诺娃后来在收集家族史资料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关于瓷娃娃的信息。它们出产于德国图林根地方的霍伊巴赫小城,从19 世纪80 年代开始大批量生产,大约生产了半个多世纪。为了节省成本,只在正面上釉,一两个铜板的价格,使得它们在欧洲随处可见。既可以放在玩具屋当摆设,也可以裹进馅饼里看看谁有运气,似乎还可以放在茶杯里代替冰块——所以在英语世界现在有一个统一的称谓:frozen Charlottes(冰人夏绿蒂)。然而在一个落雨的傍晚,这个残破的瓷娃娃摔碎了,作者哀叹说:“原本他还好歹诠释了家族和自我历史的完整性,突然间却变成了一个讽喻:历史无法言说,任何东西都无法保存,而我,完全无法从他者过去的碎片中拼凑出自我,甚至不能将其据为己有。”[3]68而博尔赫斯也在看到阿莱夫之后说到:“看到无数眼睛像照镜子似地近看着我,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镜子,但没有一面能反映出我。”[9]194《阿莱夫》中的“我”所感到悲哀的是窥见了永恒之后无趣的生活,自身的存在只是虚妄的真相,最终因遗忘而得以救赎。而冰人夏绿蒂则喻意:没有事物是完整、永恒,幸存者的象征,幸存记忆的象征,是残缺的,微小、不美、背对我们,随时可能湮没在时间深处。
三、历史编纂元小说:边缘性主体的被动“失语”
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琳达·哈钦(Linda Hutcheon)在《历史编纂元小说:对历史的戏仿与互文》一文中提出了“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概念,以此来指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欧美文坛涌现的一股将现代主义实验创作与历史以及社会语境车合起来的创作潮流。哈钦认为这类小说既有强烈自我指涉的元小说特征,同时又穿插和影射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采用近乎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对历史叙事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加工。《记忆记忆》具有历史编纂元小说的特征,斯捷潘诺娃通过回溯俄罗斯近代史中的自我家族史,对历史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再加工,同时也反映出边缘主体的被动“失语”。
首先,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一个特点是它的自我指涉,即小说对自己文本的虚构性进行揭露,揭示具有某种元小说(metafiction)的特点。《记忆记忆》是一部“元小说”,作品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叙述,“我”兼叙述者与作者斯捷潘诺娃同名。在第一部分第二章《无数缘起》叙述者揭示了创作这部作品的缘起,这些叙述都是作者本人在现实中的一些思路,并使这种叙述成为小说整体的一部分,这种叙述就是“元叙述”,而具有这种元叙述因素的《记忆记忆》就是一部元小说。
其次,斯捷潘诺娃对历史重新思考与再加工。《记忆记忆》以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作为历史语境,而事实上1972 年才出生的斯捷潘诺娃,对于二十世纪前期的记忆又从何谈起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十世纪的过往对于斯捷潘诺娃而言只能以一种被加工的方式被知晓,因为她不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但与此同时,作为拥有犹太血统的战后一代,斯捷潘诺娃始终感觉历史如幽灵一样与她如影随形,她认为自己“侥幸成为了整个家族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会向外界发声的人”,有责任与义务为不曾被国家集体记忆讲述的人发声,她要完成一部家族之书,“必须讲述他们,为他们发声”[3]20。因此斯捷潘诺娃引入了家族中人的许多真实历史材料(虽然也无法确证):物件、照片、日记、书信、文件……尽管如此,对他们还是不够了解。斯捷潘诺娃由此将二十世纪俄罗斯公众文化即文学人物引入文本,试图以类比的方式从这些人物在二十世纪的写下的文字中还原当时的情景。从而将家族的个人记忆与二十世纪风云变化的大历史串联起来。
然而,在讲述的过程中,斯捷潘诺娃发现“祖父母辈的很大一部分努力恰恰是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为了变成透明人,隐身于家庭琐碎之中,与充满宏大叙事、动辄百万人口误差的大历史保持距离”[3]20。斯捷潘诺娃的母系一方,祖上都是地方的犹太商人、资本家和企业主,在新政权下纷纷失去财产,或沉寂落寞、或不知所终。这个家族的百年经历与资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大清洗、二战、冷战、苏联解体相始终,外加排犹引发的一系列惨案。家族先祖为了自保,有意隐藏记忆,闭口不提历史中的事件。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廖吉克参军,二十岁牺牲于前线,却只能在一封封家书里写“一切都好”,实际却与之相反。而爷爷科里亚十六岁加入共青团,一直做到部队政委,最后在大清洗中险些被波及。在后半生里回想起这些经历还是讳莫如深。斯捷潘诺娃的父亲斯捷潘诺夫参加苏联建设,但是当斯捷潘诺娃想发表他当年的家书,却遭到父亲的坚决拒绝。
因此,充满悖论的就是普通人无法汇入历史的宏大进程,而只能是作为历史的边缘性主体存在。与大人物共同经历时代遭遇,但是是不曾被叙述的,是被动“失语”的。二十世纪,也许每个国家的悲剧都并不相同,各个国家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试图消化他们的灾难,于是世界文学中充满了创伤、苦难以及回忆录文学。但是对于俄罗斯而言,如斯捷潘诺娃指出的,是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是一种“创伤性渗透”[10]。一系列的灾难让国家和其人民无暇停下来思考发生的事情,没有时间哀悼死者,似乎只有继续前进才不会意识到周围的苦难。所以,家族中的人,甚至是众多的普通人,对这些生活在动荡时代的人来说,他们都不愿意回忆过去,甚至于在某些时刻会开始选择遗忘,有意无意地重写现实。也就是说,“家族记忆中的空白、缺失与抵牾,是在民族记忆、社会记忆与国家记忆场域下的被动失语或主动删除”[11]。
总体来看,《记忆记忆》的后现代叙事特征体现在:首先,《记忆记忆》颠覆传统叙事模式,在结构形式和内容上体现碎片式特征,消解了文学体裁界限。其次,在题目、创作方式及喻说意象方面分别与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构成互文性。最后,《记忆记忆》具有历史编纂元小说特征,斯捷潘诺娃以元叙事方式回溯家族故事,对二十世纪历史进行重新思考与再加工,动荡时代家族记忆中的空白、缺失与抵牾,实则是边缘主体被动失语或主动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