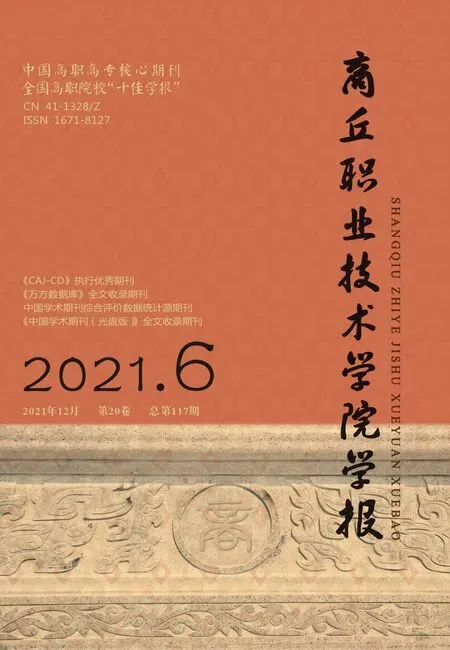性别与身份认同的张力结构
——中西语境中的“姐妹情谊”研究
赵思奇,聂平均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姐妹情谊”是伴随着女性意识觉醒、女性在男性话语的镜像下的一种话语回归建构。相对于男性的逻辑性、秩序性和等级性的话语,女性话语建构者认为,女性有普遍的属于女性的隐秘体验、特殊的言说方式和书写方式,而这则可以作为建构“姐妹情谊”的基石[1]376。这种设想的“缔结女性共同体”,为女性主义的身份认同和女性解放的基础带来了希望,但是这种脆弱的联盟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和短暂性,其最终是否会导向乌托邦式的“幻象”是值得深思的[2]。作为一种设想,“姐妹情谊”是一种女性联合体,是要跨越种族、身份、肤色和阶层的,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地“跨越身份界限”[3],这里其实是存在着一个性别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结构的。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女性的从属是‘结构性的’”,尤其是早期的女性主义者的研究就会把注意力放在女性受到的“共同压制”上面,而忽略了由于身份认同(种族、肤色、阶级等)带来的“差异”上[4],从而也会使理论指向乌托邦。但是,如果在尊重身份认同的情况下,彼此体谅对方的“差异性和独立性”,也未尝不可相互促进,结成稳固的女性同盟势力,来共同对抗来自父权和男权话语的压制,开创属于女性的话语空间并最终走向女性解放之路[5]。所以,对性别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结构的揭示和研究,可以很好消解“姐妹情谊”理论自身固有的乌托邦指向,为建立新型的“姐妹情谊”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
一、“平等”与“差异”的张力:西方女性诗学中的“姐妹情谊”
女性主义诗学是与女性主义纠缠在一起的,而女性主义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平等与差异”问题,当强调“性别平等”就会导致“差异”被抹杀,而过分强调“差异”就会造成“多元立场”“内部分化”[6],这是女性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背离或者悖论。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强调“差异性”的,这种男女的差异仅仅是一个方面,还有女性内部的种族、阶级和人生阅历的差异。如果抹平“差异”追求“平等”,那么“平等”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比如男女平等、女性平等等。这些问题启迪了女性诗学试图尝试构建“女性传统”“女性气质”和“姐妹情谊”理论来解决女性内部的一致性问题。从前面的分析得知,“姐妹情谊”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带有抹平女性内部“差异性”的倾向,“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是阻碍女性团体团结的主要障碍[7]74。所以,“姐妹情谊”在有些研究者看来就指向了乌托邦,也只有在共在的“集体情感”中才有可能克服这种乌托邦性质[8]。也有学者通过对胡克斯的研究表明,“姐妹情谊”构建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才有走向理想未来的可行性[9]。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分析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和温切西尔夫人的时候,用“两人都沉溺于诗,又都因此而形容憔悴”“打开公爵夫人的诗集,你会看到同样的躁动”[10]来描述女性作家有着相通的体验和烦恼。此外,伍尔夫进一步分析了女性作家在创作时会面临的困境,比如说相同的经济困扰、阻力和障碍,以及来自男性话语的诘难。这种女性的共通性到了肖瓦尔特时,女性就从开始讲述“她们”的故事,变成了《她们自己的文学》,这条在伍尔夫手中还不是很清晰的路线图已经清晰可见了。“女性传统”作为文学史中的“亚特兰蒂斯”被重新发现,也就是说在整个文学史当中,由于女性文学当中“某些循环出现的类型、主题、问题和形象”构成了文学史当中的“亚文化”[11]。女性的亚文化在肖瓦尔特看来是由女性共同的生理经验和共同的社会经验所形成的需要掩盖的“秘传知识”,所以,女性作家从一开始就具有“隐秘”的团结和“共谋”,而这种由于建立在共同女性经验基础上的女性团体之间的身份认同就是“姐妹情谊”[12]。比如简·奥斯汀和夏洛蒂·勃朗特对笔下人物伊丽莎白和简·爱的刻画,都不约而同地从她们不顾世俗的偏见,敢于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的角度展开,简·奥斯汀和夏洛蒂·勃朗特之间的这种跨时间的亚文化身份认同,可以作为肖瓦尔特理论的注脚。
这种共同的女性经验在爱丽斯·沃克看来其合法性就非常值得怀疑,因为黑人在女性传统理论中是缺席者,黑人仅存在于白人理论的注脚里,这让她萌发了追寻属于黑人的女性传统、风俗的理论追求[13]47-52。爱丽斯·沃克认为,黑人女性的传统是祖母传给母亲再传给女儿的,是一种在种族压迫、阶级压迫和男性压迫下的艰难处境。在赫斯顿的《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和爱丽斯·沃克的《紫色》中,就穿透着这种传承性,前者用“驴子”来形容黑人女性在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的双重压迫下的处境,而黑人女性的解放则寄托在一种纯粹的乌托邦世界中,相反,后者中的夏格则敢于挣脱男性世界的束缚,并鼓励自己的姐妹塞莉跳出藩篱。前者塑造了珍妮和菲比,后者刻画了夏格和塞莉“姐妹情谊”关系,而这种在种族关系上的身份认同就比白人女性的那种抽象的建构更加牢固。
在胡克斯看来,如果女性主义不将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纳入其中,其实质就是一个抹杀黑人女性,一个纯粹的白人女性用于自娱自乐的“非人化的过程”。胡克斯举例说,白人女性在发言的时候不仅不考虑黑人女性的利益和诉求,在讲话的时候也不会考虑其他女性的感受。在胡克斯看来,这种能够处理女性理论内部“差异”的能力是决定女性是否能够团结起来对男权社会进行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所在[7]65-69。来自阶级底层和受压迫的种族的女性,当她们在白人女性家中做女仆和奴隶的时候,跟她们提“姐妹情谊”这种完全忽略受压迫阶层利益和诉求的口号,只能是一种没有任何可能实现的泡影。
梳理英美较有代表性的批评家的“姐妹情谊”理论,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英美哲学当中的经验主义影响深远,理论当中充斥着感性和经验性的感受和描写。相比较而言,法国女性主义则比较偏重于“以激进的态度,将语言作为性别与权力斗争的一个场域,试图以与女性身体相结合的女性写作来拆解父权文化象征秩序”[14],更侧重从文本、语言学、语义学以及心理分析等方面的理论建构工作[15]126。波夫娃的女性理论是建立在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批判上,她认为,“若每个人都能够坦率地承认他者,将自己和他者相互看成既是客体又是主体,那么超越这种冲突便会成为可能”[16]。 女性的形成在她看来是与男性世界和男性话语的“他者”凝视密切相关,而语言和神话结构则是环绕在女性头上的另外一层束缚。在波夫娃的笔下,女性是具有相同的形成过程,“她”是被社会所规训、所凝视、所教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存在。但是,她写出了女性的形成、处境和生存之境,在她的笔下,女性的“差异”还不是很明显,她还企图构建男女平等的理想愿景,但是没有人继承她的衣钵[15]128。
尽管如此,得益于波夫娃对于主奴辩证法的批判和解构主义者对能指和所指的解构,西苏就首先选择从解构语言结构开始,她认为,写作是女性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写作才能让女人跨越前俄狄浦斯阶段,感受到未被男权污染的纯净的世界。但是,如果使用男性的语言结构进行创作就会再次掉入男权中心主义的窠臼中,唯有借助于“身体写作”才能给予女性“洞察力和力量”[17]。而西苏所指的女性“是指那些不可避免地要与传统的男人做斗争的妇女,还包括了必须使妇女觉悟起来,争取她们的历史地位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妇女主题”[13]397,西苏和波夫娃虽然没有承认“姐妹情谊”,但是她们的理论相对比较侧重于女性的“共性”。西苏并不否认“差异”,但是借助于“身体写作”挖掘女性身体的潜意识可以让女人之间产生一种共鸣。到了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那里,主体被消解掉了,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文本间性”,处在主体位置上的“是文本间的对话”[18],换句话说,主体是一种“流动性的过程主体”,是对父权象征秩序致命的解构。解构之后的主体的流动性让整个文本世界呈现出一种随意流动和无目的、无秩序的状态,但是,如果没有主体,谁又为文本提供了流动的场域和“语境”呢,这在克里斯蒂娃这里是一个永恒难解的谜。也就是说,到了克里斯蒂娃,“女性”这个概念也是不存在的,“女性气质”和“姐妹情谊”都是遭到严重质疑的概念。
二、“女儿国”原型视域下的中国女性诗学中乌托邦式表征
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女性诗学是以中国传统的“女儿国”原型为文化基底,以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为镜像,通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镜像的交互,才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诗学。“女儿国”作为中国诗学中女性生成和存在的空间,是文学作品中主要表征“姐妹情谊”原型结构,在中国女性诗学中分别有三种乌托邦:第一种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原生态的中国古典式“姐妹情谊”的乌托邦;第二种是以《方舟》《兄弟们》为代表的初步启蒙(有性别认同但是没有自觉身份认同)的乌托邦;第三种是以《一个人的战争》《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为代表的“同性之爱”的乌托邦。其中,第一种为未经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镜像浸染过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古典形态,后两者则是以中国文化为基底,又积极汲取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有益成分,在中国女性诗学中的表征形式。
(一)原生态中国古典式乌托邦
从神话学的角度讲,“女儿国”可以追溯到《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对“女子国”的描述,其后在《淮南子》《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皆有类似的记载。《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则来源于《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行记》中对印度附近的“女子国”的记载[19]。《西游记》对“女儿国”的描写就比较成熟了。小说当中的“女儿国”,是为了衬托唐僧取经的坚定所设计的妖魔化的女性王国,这个王国里面虽然已经有女性当家做主的影子,只是完全借用了男权社会的权力而设计的,里面并没有“姐妹情谊”。《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则是对现实的倒置——男性主内而女性主外,男性穿裙子、梳妆打扮、裹足,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受到的一切压迫都让男性去承担,颇具有启蒙意义。到了《红楼梦》中的“女儿国”(就是贾宝玉所居住的“大观园”),里面的一系列女性人物才具有中国意义上的“姐妹情谊”雏形:一种相互扶持、相互体谅和相互尊重的姐妹表征。
原生态的中国“姐妹情谊”,首先是高度审美化的,因为这群姐妹是没有生产和生存的现实需要的,她们过的是吟诗结社的生活,人物形象是婀娜多姿的,性格是多姿多彩的,气质是藻雪精神的,气氛是圆融和谐的;其次是高度理想化的,因为这群姐妹都是完美的,都是可人的,都是让人怜惜的,都是不占尘埃的。基于此,她们的结局注定是悲剧的,她们之间的“姐妹情谊”最终导向了乌托邦。究其深层次原因,一方面是她们的女性意识尚未觉醒,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根源是封建父系社会和男权制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她们的自我身份认同。比如,香菱是个被买来的丫头,虽说被薛宝钗当作妹妹看待,但毕竟身份不同;林黛玉虽说是主子的身份,由于双亲皆不在身边,始终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再加上与贾宝玉之间暧昧的关系,与薛宝钗等人始终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姐妹关系等。在传统意义上的“女儿国”空间中,在塑造原生态的“姐妹情谊”中,曹雪芹不自觉地把性别与身份认同二者的张力结构表现了出来:一方面作为女性,她们与男性和男权社会划清界限,在乌托邦幻象的“大观园”中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她们又不得不屈从于封建男权社会。曹雪芹囿于时代和历史的限制,显然无法超脱出来,所以,他精心营造的“大观园”最终走向了衰败和没落,这既是他的悲哀,又是时代的悲哀,更是女性的悲哀。
(二)以《方舟》《弟兄们》为代表的初步启蒙的乌托邦
张洁在《方舟》中描写的三个女性同窗好友:荆华、梁倩、柳泉,各自有其不幸,但都不愿意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共同挤在“方舟”上,组成三个人的“女儿国”。这个“女儿国”对于女性共同面临的困境,比如婚姻问题、孩子问题、工作问题以及与男人交往过程中受到的骚扰、侵略以及欲望的或者蔑视型凝视都有比较认真的细节描写。虽说她们想象着如果各自问题解决后,大家要好好“出去玩一玩”,可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她们是绝望和无奈的[20]。王安忆的《兄弟们》中“老大”“老二”和“老三”三个姐妹基本上被作家切断了与社会联系,作者把她们放在一个校园内,可以算是一种乌托邦设计了。 三个姐妹在校园中产生了纯洁的友谊,只是这种“姐妹情谊”无法经受现实的考验和冲击。王安忆比张洁犀利的地方在于,王安忆让三个姐妹离开了乌托邦空间。“老三”一毕业就不能抗拒自己丈夫的压力而跟随丈夫回到小县城;“老大”回去后也很快生了孩子,这也算是背叛了她们之间的约定和诺言;“老二”虽坚守的时间最长,但因扛不住那种外在的无形的压力最终决定要孩子,也算是没有坚守住承诺。
这种形态的“姐妹情谊”,主要关注的是凝视问题,主要集中于异性的欲望的凝视、外在权利的凝视以及身份认同的自我凝视。它不仅仅是一个“看与被看”的问题,而是一种欲望的投射、权利的压力和自我的异化的一个问题。女性在男性为主导的场域中,欲望的凝视是她们首先会遇到的问题。一方面,欲望的凝视会给女性造成困扰,另一方面,有些女性为了赢取权利和地位通过塑造自己的气质和外貌等[1]357来迎合这种欲望的凝视。比如《方舟》中魏经理对柳泉的凝视就是这种欲望的凝视,实际上还混杂着权利的凝视。柳泉可以对抗甚至无视魏经理欲望的凝视,但是却不能忽略他带有权利的凝视,尤其是涉及具体的工作。前两种凝视会形成一种外在的镜像对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产生强大的不自觉的自我凝视,而女性一旦不自觉地屈从了外在的对于角色的定位要求,很快就又会从觉醒状态划入未觉醒状态。这是在多重凝视下的女性“姐妹情谊”会导致乌托邦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在王安忆的《弟兄们》中有非常明显地体现。
(三)林白、陈染“同性之爱”的乌托邦
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南丹的存在“总是使我返回我的原来面目,这是她对我的意义”[21]。由于南丹的追求,才让她有了做女人的感觉,在南丹闯入她的生活之前,没有男生对她有兴趣,她同样对男生没有兴趣。在这里,南丹的性别实质上被倒错了,南丹虽然性别为女性,但是,其扮演的却是一个闯入主人公生活的“男生”,一是作者把南丹与男生类比,二是作者让南丹做了只有男生才会做的事情——主动追求主人公多米。在多米眼里,南丹用只有男性才拥有的欲望,凝视着她,她最终融化在了南丹的柔情之中。
与《弟兄们》类似的是,戴二也有两个小姐妹,也曾经相约不嫁男人,甚至到了一周不见就会思念的地步。当小姐妹缪一和麦三相继与自己的男友结婚和同居之后,她们三人的“姐妹情谊”也就烟消云散了。尤其是当缪一怀孕之后,戴二明显感觉到由于身份认同的原因她们之间的隔膜越来越严重了,甚至到了打通电话两人无话可说的地步[22]。在另外一部小说中,陈染描写了戴二在不堪重负的母爱下与伊堕人之间的“同性之爱”,伊堕人拥有戴二另一面的气质,也可以算作是戴二的自我分离、自我分裂,她与伊堕人之间的“同性之爱”甚至可以看作是戴二的自我复位,是一种自我追寻和自我双性同体的一种复归。伊堕人曾经对戴二说:“没有男人肯于要你,因为你的内心与我一样,同他们一样强大有力,他们恐惧我们,避之唯恐不及。”[23]79母亲对戴二的爱,在戴二看来是一种窒息的令人发疯的爱,是一种监视式的牢笼的爱,是一种窥视和怀疑式的爱。但是,在戴二的母亲看来,她对戴二的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不受伤害、不受欺凌,尤其是不让女儿堕入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不正常的女性之间的关系之中去[23]83,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同性之爱”的另外一种版本呢。
林白建构的“姐妹情谊”,其中一个女性会自然而然地将自我的性别认定为“男性”,当性别认同倒错之后,她会用一种男性镜像式的自我凝视要求自我身份认同。她们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他者的凝视,她们该如何面对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如何面对外在的和内在的焦虑和不安。当性别倒错了之后,她们该怎样对自我的身份进行定位和认同,这是一个棘手问题。陈染的“姐妹情谊”更像是一种自我的心灵投射,与其说是为了“同性之爱”,不如说为了一种自我的心灵安慰和心灵慰藉。与林白不同的是,陈染有意模糊性别的界限,她不认为“同性之爱”是一种性别倒错,而是试图通过女性的私人化描写来展现女性独特的体验和经验,而且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这种“同性之爱”的“姐妹情谊”是一种不可靠的、随时都会由于身份认同瓦解的不稳定结构。陈染的“女儿国”的乌托邦是由于在“母亲”过于沉重之爱的压迫下,在母亲和自我的双重凝视下,对于异性的警惕和自我情感的投射下所导致的。由于母亲的警惕和窥视,无论是“同性之爱”抑或者异性之爱都被破坏,而也正是由于母亲的监视和刺探,戴二与母亲之间这种母女之间的爱也被破坏,最终全部导向了乌托邦。
三、结语
在西方和中国的早期建构中,理论和践行的先行者都只注意到了女性话语的性别意识,却不大注重对身份认同的研究,这就导致了“姐妹情谊”具有非常明显的乌托邦性质。在西方,“姐妹情谊”是由于阶级、肤色和民族问题所造成的性别与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中国,“姐妹情谊”则是由于受到“女儿国”原型的影响,往往会把人物设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对性别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认识不够。即便是被增添了身体书写、雌雄同体以及母女关系问题的探索,由于“姐妹情谊”对身份认同所造成的社会复杂性认知程度不够,所以,从简单的人物性别、人物独特的心理感受以及人物独特的生理体验出发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导致理论的乌托邦性质。那么,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利用中国古老的“和而不同”的智慧,也许会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将是我们下大功夫努力研究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