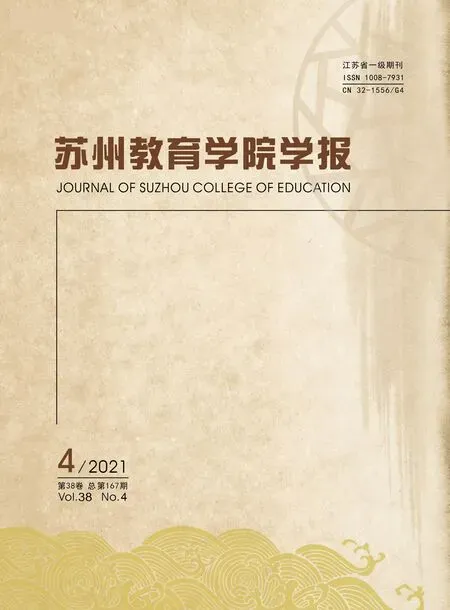《田汉全集》未收的八则启事
金传胜,席 媛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在搜集田汉生平文献的过程中,笔者陆续发现了田汉发表于民国报刊上的八则启事,鉴于它们未被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田汉全集》所收,对此有必要加以介绍,并对其所涉事件的缘由略作梳理与考证,以期丰富对田汉生平创作的研究。
一
1926年5月19日,上海《新闻报》第一版刊有《欧阳予倩 田汉 唐槐秋启事》,内容如下(原刊无句读或标点,笔者酌加整理):
阅连日新申两报载,民新影戏专门学校招生广告,署名者为校长、教务长、教授,而鄙人等贱命亦在教授之列。按,予倩受民新影片公司之聘主任编剧,并非该专门学校教员。汉与槐秋现竭全力进行南国剧社,无暇他图。虽以友朋之谊,不妨为精神上之互助,但并未受该校校长、教务长之聘为该校教授,自无随同所谓校长、教务长者对外启事之理。该校招生广告所云,殊乖事实,特此声明,以免误会。
本启事5月20日亦刊于上海《申报》第一版,“新申两报”,即《申报》《新闻报》。该年的5月10日,《申报》“本埠增刊”第二版刊载《民新影戏学校之发起》之广告:“上海民新影戏专门学校(西文为C. S. Cinema Academy),为民新影戏公司独力经营之事业,以提高银幕的艺术,养成国产影戏专门人材为宗旨。现已推定侯曜君担任校长,徐公美君担任教务长,欧阳予倩、田汉、唐槐秋、芳信诸君分任各科教务,业由校长聘请邹鲁、谢英伯、黎锦晖、郑振铎诸君,担任讲演。闻已组织就绪,不日将登报招生。”[1]该广告已经提到欧阳予倩、田汉、唐槐秋等人为该校教员。5月17日起,《上海民新影戏专门学校招生广告》陆续刊布于《新闻报》《申报》广告栏,欧阳、田、唐三人均被列为该校教授,因此,欧阳予倩、田汉、唐槐秋见报后马上发表上述启事,以消除误会。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申报》登载该启事时,其右侧仍原封不动地刊有民新影戏专门学校的招生广告。
二
1929年7月18日,无锡《橄榄报》第一版刊有《南国社旅锡公演启事》,落款人为田汉,全文内容如次(原刊为句读形式,笔者酌加标点):
汉来锡多次,或在梅园花放之日,或在惠山雪满之时。此次藉暑期行旅,率数十同志赴京演剧,归途勉如此间教育界之请,又作短期公演。然而波上风清,枝头蝉唱矣。顷过旧游,因怀故友,写《太湖的黄昏》一剧以寄无锡。公演两日,短剧六篇,游人归,未尽如意。诸惟此间公众与以严正之批判,幸何如之。第一日:《古潭的声音》《南归》《颤栗》《湖上剧悲》,第二日:《南归》、《垃圾桶》(新作社会剧)、《一致》(表现派社会剧)、《太湖的黄昏》(新作诗剧)。售券地点及时间:每日上午十时起至下午四时止在城中通俗教育馆发售,过时不候。每日只限五百张,过限停售。定价一律小洋六角,附赠《南国特刊》一份。开演时间,本月十七、十八两日,下午八时起。[附注]孩童概不招待。南国社委员长田汉谨启。
据张向华《田汉年谱》记载,1929年7月17日,田汉“所撰之《南国社话剧股旅锡公演》广告载无锡各报,说:此次‘顷过旧游,因怀故友,写《太湖的黄昏》一剧以寄无锡。’(剧本未发表)”[2]。笔者没有找到当日的《锡报》和《新无锡》两报,从年谱引述的语句可知,所称广告应即《南国社旅锡公演启事》。其中,《湖上剧悲》(按:应作《湖上的悲剧》),因饰演主角白薇的王素女士被父亲强迫不许登台,该剧最终并未在无锡上演。《垃圾桶》《一致》《太湖的黄昏》是田汉为旅锡公演而特意编排的新剧。《垃圾桶》《一致》两剧经整理后发表于《南国周刊》,而《太湖的黄昏》剧本未见发表,今已不存。
三
方育德、陆炜编《田汉著译目录(1913—1968)》(收入《田汉全集:第二十卷》作为附录)中曾著录:“敬告《田汉戏曲集》读者上海《文艺新闻》47期(1932年2月1日)。”[3]642本文实为声明性质,张向华《田汉年谱》对此有记载,但《田汉全集》却未收录。现将《文艺新闻》上的这则启事照录如下:
鄙人虽曾与现代书局有发行《田①原文漏一“汉”字。戏曲集》之约,但为尊重自己艺术的良心及他局的版权起见,对于过去各剧非经仔细改正及一定之排列不愿出版。重以年来生活变动,故至今只发行过四、五两集。而第四集原稿及序亦经该局任意移换改窜,非复原有形式,复更闻该局有整本翻印《咖啡店之夜》及与他剧为第三集之讯,曾去缄嘱尊重作者意思,该局置不理。今更见诸出版豫告,该局而有此种行为殊不足怪,而作者对于读者负疚已深。鄙人穷甚,无法登广告,敢藉文新余白敬告亲爱的读者及公众勿受其骗。田汉。[4]
现代书局于1927年成立后,与田汉和南国社多有往来。1929年,田汉主编的《南国周刊》《南国月刊》均由现代书局发行,现代书局还与田汉达成合作意向,将田汉的剧本结集出版,发行《田汉戏曲集》。早在1930年《现代书局出版目录》中就已刊出《田汉戏曲集》(共十集)的“发售预约”广告:“田汉先生的戏曲,是最受读者推崇和欢迎的。但田先生生平的作品甚多,分登各种杂志,读者每以不能全读为憾。敝局本促进戏剧运动之旨,特替田先生出版戏曲全集,并由田先生改篡一过,以飨读者。”[5]由于田汉忙于南国社社务,这一工作实际进展缓慢。1930年6月,现代书局发行了《田汉戏曲集》第五集,1931年4月出版了第四集,1932年1月,该局又发行了《田汉戏曲集》第三集,收入《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乡愁》《获虎之夜》《落花时节》《一致》《林冲》等七个剧本。但据上述启事可知,该书局事先并未征得田汉的允许,而是擅自将他的旧作编印成书。田汉致函现代书局,对方却置之不理。此前,现代书局在出版第四集时,其实也没有完全尊重作者的意思,对原稿与序言作过改动。抱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田汉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该启事,这既对读者有所交代,又对现代书局的做法表达了不满与愤慨之情。
1933年2月,现代书局出版了《田汉戏曲集》第一集、第二集。在《田汉戏曲集》第一集的自序中,田汉再次声明:“在这里得声明的,是我迄现在为止只编辑过四、五集,第三集完全是别人负责编的,其中除了整个翻印我在中华书局发行的《咖啡店之一夜》外,甚至连在《南国周刊》上写的京戏《林冲》的残稿都给收进去。这一种行动我想不是每一个著作者所乐从的。好在现在发行书肆方面已应许将该集毁版,我才着手重新编定一、二、三集。在这三集中我不预备专收过去的作品,而以思想发展及题材关联为标准,充分容纳今日以前我对于中国剧坛涓滴的贡献。这第一集中如《咖啡店之一夜》、《姊妹》(原名《午饭之前》)两篇虽为旧作,但均经重大的删改,无论在内容形式相信都已焕然改观。”[6]《田汉戏曲集》第一、二集的迟迟问世,一方面因受到当局的审查,另一方面,缘于田汉想对旧作进行大幅度修改。实际上,田汉自编的第三集最终并未印梓。除去擅自翻印的第三集,现代书局发行的《田汉戏曲集》共有第一、二、四、五集,以及1934年5月收有15个剧本的《田汉戏曲集》(改订本)。
四
1935年11月6日至8日,南京《新民报》第二版广告栏刊有《姜济寰先生门人公鉴》,落款者共有八人,田汉居首。该文如下(原文无标点或句读,笔者酌加整理):
姜师作古,同深哀悼,拟联合在湘在粤及门者举行公祭,份金二元起至一百元止。倘蒙赞同,请于九日以前送交实业部谢宝树、唐升节、罗敦伟代收登记,十日上午十时齐集莫愁路仁孝殡仪馆行礼是盼。田汉 罗敦伟 唐升节 欧阳翥 姜心曙 刘维柱 谢宝树 陈常 仝启
姜济寰,号咏洪,亦作运鸿,湖南长沙人,国民党左派人物。1912年与徐特立共同创立了长沙师范学校,从事教育事业,后从政多年,任长沙县知事(县长)、财政部委员等职,1935年10月病逝于南京。田汉于1935年11月8日写下《旧师之死—悼姜济寰先生》,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长沙求学与身陷南京狱中期间姜济寰给予自己的关怀与照顾:“姜先生做过三任长沙府知事,其后又保有许多更大的官衔,但我们认识他的,与其是作为政治家的姜先生,毋宁是作为教育家的姜先生。他在长沙师范校长时代的讲学,特别是关于阳明学的阐扬,对于学生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一部分的同学该记得姜先生念‘险夷原不滞脑中……’等名句时的神态吧。至于我,所负于姜先生的又不仅一般的启迪了。我在长师时有一学期的膳费即系姜先生代出。系金陵狱时,姜先生适居曾公祠,家母及素斐来京探狱,必访姜先生。姜先生也必定多方地帮忙。”[7]490同时提到门人的公祭活动:“本月十日上午十时在京同学拟公祭姜先生于莫愁湖之殡仪馆。”[7]493与上述启事恰相印证。据11月11日《新民报》载,姜济寰灵柩于10日下午出殡,“政军各界,及姜氏学生前往执绋者不下数百人,极为严肃”[8]。田汉显然在执绋者之列。无论是发起公祭活动,还是撰写专文悼念,田汉对这位恩师的爱戴与哀悼之情令人动容。
五
1935年夏秋间,因黄河决口,苏北发生严重水灾。为支持女演员黄侯、黄今、黄美三姊妹赈灾公演,田汉曾创作独幕剧《陆沉之夜》。此剧曾被学界认为已佚失,直至2019年才被发现①黄爱华:《新发现的田汉独幕剧〈陆沉之夜〉》,《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第157—162页。。该剧在世界大戏院上演前,曾在1935年11月8日的南京《新民报》第八版刊出广告,有“明日骄矜大贡献”“戏剧名家田汉先生编剧导演”“意调特殊,别开生面,千载一时”等宣传语。第二日,该报第五版刊发了一则《田汉启事》:
鄙人前虽曾为黄氏姊妹赈灾公演写一短剧《陆沉之夜》,但鄙人病体未愈,亦素不会导演,且生平最恶夸张之习,从不敢妄称“无敌”,更无可“骄矜”,阅世界大戏院广告令人汗下。此等广告鄙人绝未与闻。合亟申明,敬希各方鉴谅。
可以想见,田汉在看到报上《陆沉之夜》的广告后,对世界大戏院的夸张用语与不实宣传甚为不满与反感,因此马上驰函报馆,公开声明。只是同一日所刊的演出广告,“导演”两字虽已消失,但依然有“今日骄矜两大贡献”之语,甚至还出现了“牺牲色相”这类抓人眼球的字眼。相信田汉见到时,心中恐怕仍不是滋味。不过此则启事还是发挥了作用,该月10日以后的广告,“骄矜”“牺牲色相”等夸大之词终于没有了。
六
方育德、陆炜编《田汉著译目录(1913—1968)》收录了田汉1936年的两则启事,分别是“田汉启事 上海《大晚报》,1936年9月5日”[3]648与“田汉启事 南京《新民报》日刊,1936年9月12日”[3]649。然而不知何故,两篇全文均未收入《田汉全集》。经查,第一则1936年9月5日载上海《大晚报》副刊《剪影》,内容如下所示:
近阅南京东海书店出版之《文化新闻》常登载汉所为诗文。如前期之《旧诗新作》实汉舅父易梅园先生旧作,并非出自汉手,凡此皆未得本人同意。其编者林适存先生虽为汉同乡,但一再为之,殊违其见爱之意,且非汉所能负责,特此声明。
《文化新闻》是南京东海书店出版的杂志,创办时间不详,目前仅能见到1936年9月11日出刊的第四期。林适存是该杂志的编辑。由上述启事可知,该刊曾多次登载田汉的诗文,但刊发《旧诗新作》前并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上一期(从时间上推断,当是第三期)所登《旧诗新作》实际上并非田汉手笔,而是田汉舅父易梅园(又名易象)的旧作。田汉发现后有所不满,特意写下此则启事并投诸报端。
第二则启事,于同年9月12日载南京《新民报》第7版,这是以书信的形式撰拟的,全文如下(原文无标点,笔者酌加整理):
敬启者:昨因友人林适存先生主编之《文化新闻》登载拙稿事,在上海《大晚报》上有所声明。意思只是希望适存先生于采登拙稿前有所通知,俾便负责而已。阅九月十日《大晚报·剪影》,不图又有狂丝先生一文对于林先生作过当之责备,甚至有“文坛不肖子”等语。此则大反汉之态度,以适存登载拙稿虽手迹稍欠,并非出于恶意。而汉生平和不肯糟蹋自己一样,也从不肯糟蹋别人。除已去缄《大晚报》更正外,并作此简单声明,向林先生表示非常歉意。田汉,九月十一日。
可见,两则启事内容紧密相关。查1936年9月10日《大晚报》副刊《剪影》,确有一篇署名“狂丝”的文章《戏剧界两条大汉在南京》。该文章主要讲述作者狂丝在南京结识华汉(阳翰笙)、田汉两位戏剧家的情形。狂丝通过其兄的介绍认识了华汉,并与华汉同去拜访了田汉。文章透露,田汉发现《文化新闻》未经其允许刊载自己作品,对这一做法他颇为生气,并表明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于是狂丝写下了这一事件的经过,田汉看到了该篇文章,甚觉不妥,立即写了第二则启事。
狂丝文中有“田先生说:拿人家来卖牌子干什么啦,这似乎可以称之为文坛的不肖子了”[9]的表述。田汉认为狂丝的记述不符合自己的原意,遂向林适存表达歉意。据朱绛《不尽的哀思,难消的悲痛》①苏州大学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会:《艰苦的探寻续集》,内部资料,1992年,第187页。一文记载,狂丝是江菊林的笔名。江菊林,江苏常熟人,毕业于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爱好文艺,经常握笔弄文,读书时曾与同学汪藻香、卢显和朱绛在无锡《国民导报》上创办文艺副刊《湖风》,后来常为《新民报》副刊《新园地》《大晚报》副刊《剪影》等报刊撰稿。
七
桂林《大公报》1941年12月27日第一版刊有一则《战区长官部托招平剧宣传团团员启事》,落款人田汉。全文如下(原文无标点,笔者酌加整理):
汉奉命南来视察本部团队,经恩施黔江谒陈长官,深以平剧宣传实验剧团停顿为惜。陈长官在政治部部长时代,于该团极为支持,亦嘉许其成绩,于汉等歌剧改革计划亦甚赞同,曾嘱以代招一平剧队,但以鄂西贫苦,道路阻隔,必须能耐劳苦之“戏剧兵”,待遇既薄,又不许带家眷。汉来湘桂,曾以此意告之旧队员同志,托其相继组织并购置衣箱。经迭电陈长官,承允照办,计前后由长官部副一课及湖北省文艺委员会汇寄万四千。除衣箱之购置添制修补管理共费万一千元左右,所剩三千元用于团员之招集训练。在衡桂两地集合者,共达三十人,一月以来,备极艰苦,但彼等克苦耐劳,不为利动之精神,亦难能可贵,经于前日□②□:为原刊漫漶无法辨识之字。以下同,不另注。鄂并面呈李主□□潮先生。在车辆旅费未到以前,拟令暂在此间高升大戏院公演《岳飞》《土桥之战》等剧,以在湖北省文艺委员会管理下暂称“文艺歌剧团”,已将组织经过缄呈本市党政军各方。计刻□报到之团员为李迎春、郑亦秋、杜淑云、马俊峰、姜竹轩、戴宝彪、吕剑春、陈剑秋、陈世忠、陈绘纭、于海山、杨瀛洲、田云卿、吕信田、秦福禄、熊素云、季振芳、李河山、鲍世雄、梅金奎、孔玉山、傅得良、鲍顺□、沈守威、笪善臣等。一俟规模略具,当向战区移动演出,以期扩大抗建宣传并实验新歌剧之理论。谨此公告。田汉敬启 十二月二十六日
启事中的“李主□□潮先生”疑为“李主任任潮先生”,即时任西南行营主任李济深,他与桂林时期的田汉颇多交往。“陈长官”即陈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是田汉的上司。1940年第六战区重建后,陈诚任长官司令,辖鄂西、鄂南、川东、湘西地区。陈氏委托田汉组织平剧宣传队(后易名“平剧宣传实验剧团”),对田汉的戏曲改革实验给予了支持。剧团解散后,田汉在旧队员的基础上组建了“文艺歌剧团”,由湖北省文艺委员会管理。关于此段史实,田汉在1942年的长文《岩下纵谈—艺人的行路难》中曾述及:“文艺歌剧团是以陈长官的嘱托而组织的。辞公把这团体交给湖北省文艺委员会管理,所以命名为文艺歌剧团。他们一共寄来了一万四千元。购买衣箱、添置各物费去万二千元,以剩下的这一两千元着手团体的恢复。”[7]577-578这里提到的经费总额与上述启事一致,分项费用则互有出入。因启事成文时间较早,可信度似更高。1941年3月,田汉在重庆黔江谒见陈诚,二人就湖北文化建设问题作了交流。临别时陈嘱托田汉招募能吃苦耐劳的“戏剧兵”。来到桂林后,田汉计划“补充阵容,加强训练,多排几个合用的抗战剧本,以便在文化种子比较稀薄的□①原刊如此。战区展开戏剧宣传”[7]578,于是他发布了本则启事,以招募平剧宣传团团员。
结语
上述八则启事或由田汉单独落款,或系田汉与他人联合署名,依学界惯例,皆属于田氏的著述文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田汉全集》收录的启事寥寥无几,不能不说是遗憾的。虽然启事是一种公告性、实用性的应用文,但不难发现,在田汉笔下,这种文体有时不乏文学性(如《南国社旅锡公演启事》),既具备较高的文献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