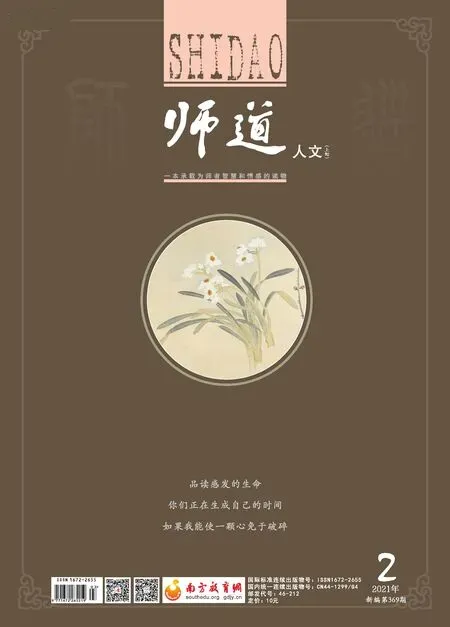海外撷片
格言说: 诗人的智力或职业的标志是对语言的激情, 这种激情被认为是对语言最小沟通单位——对词语的发狂反应。 诗人被认为是不能充分理解 “血红色” 这类词语的人。 但我的经历并不是这样。 从四岁, 或五六岁的时候, 我最早开始读诗,最早开始把我所读到的诗人当成我的同伴, 我的前辈——从一开始,我就偏爱最简单的词。 让我着迷的是上下文的多种可能性。 我所回应的, 在书页上, 是一首诗如何借助一个词的安排, 通过时间设定和节奏的微妙变化, 解放这个词的丰富而令人惊讶的意义分布区。 对我来说, 似乎简单的语言最适合这种创新事业; 这种语言, 作为一个类别, 其个体词语的内部往往包含最大、 最戏剧化的意义变化。 我喜欢刻度, 但我喜欢它变得无形。 我喜欢那些在书页上如此之小、 但在心灵中变得伟大的诗歌; 我不喜欢那种虚张声势、 但逐渐变小的诗歌。并不奇怪, 我为之吸引的那种句子, 是反映了这些心灵趣味和本来习惯的句子, 是悖论, 它具有的增强的优势能恰到好处地将固执的本性从一个正变得过于道德化的修辞体系中挽救出来。
我出生于最不可能被给予这种偏见的家庭。 在我所出生的环境里, 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有权将其他人的句子补充完整。 像这个家庭的大多数人一样, 我有强烈的说话欲望, 但这欲望经常受到挫折: 我的句子, 如果被打断, 就彻底被改变——被转换, 而不是被解释。 悖论的美妙之处在于其结果无法预期: 这就应当确保听众全神贯注。但在我家里, 所有讨论都以单一的配合语气进行。
我很早就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如果不能精确、 清晰地说出观点, 说话就没有意义。对我母亲来说, 说话是社交中可以接受的那种唠叨形式: 其功能是用持续不断、 令人安慰的声音填满房间。 对我父亲来说, 是表演和掩饰。 我的反应则是沉默。 阴郁的沉默, 因为我一直渴望得到满怀敬意的关注。 我专注于个人特征, 在我头脑中, 这是与制作句子相联系的。
…………
我阅读开始得早, 所以, 反过来, 从很小年龄起就想对人说话。当我儿时读莎士比亚的诗歌, 或是后来读布莱克、 叶芝、 济慈和艾略特的时候, 我并没有被流放、 成为边民的感觉。 我反而觉得这是我的语言的传统: “我的” 传统, 正如英语是我的语言。 我的继承。 我的财富。 甚至在它们被经历之前, 一个儿童就能意识到那伟大的人类主题: 时间, 它哺育了失落、 欲望、世界的美。
——摘自 [美] 露易丝·格丽克著: 《诗人之教育》, 柳向阳译,《四川文学》 2017 年第1 期
“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你就会轻松自在”, 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箴言。 它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 因为几乎所有的事情——荣誉、 骄傲、恐惧, 在死亡面前都会消失。 有时候你会患得患失, 提醒自己快死了, 是我知道的避免这些的最好办法。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你没有理由不去跟随内心的声音。
大概一年前, 我被诊断出癌症。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活切片检查, 医生将一个内窥镜从我的喉咙伸进去, 用一根针在我胰腺的肿瘤上取了几个细胞。 我当时是被麻醉的, 但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 当医生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细胞时他们开始尖叫,因为这些细胞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可以手术治愈的胰腺癌症细胞。我做了这个手术, 现在我痊愈了。
那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候, 我希望这也是以后的几十年最接近的一次。 从死亡线上又活过来, 我可以更肯定地对你们说: 没有人愿意死, 即使想上天堂, 也不会为了去那里而死。
但是死亡是我们共同的终点,没有人逃得过。 这是注定的, 因为死亡可能是生命中最棒的发明, 是生命交替的媒介, 送走老人们, 给新生代开出道路。 现在你们是新生代, 但是不久的将来, 你们也会逐渐变老, 被送出人生的舞台。 抱歉讲得这么戏剧化, 但是这是真的。
你们时间有限, 所以不要将它浪费在重复他人的生活上。 不要被教条束缚, 盲从教条就是活在别人的思考结果里。 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的心声。 最重要的, 你要有勇气去听从你直觉和心灵的指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 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当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本振聋发聩的杂志, 叫做 《全球目录》。它是我们那代人的圣经之一。 在最后一期的封底上是清晨乡村公路的照片, 照片之下有这样一段话:“求知若饥, 虚心若愚。” 这是他们停刊的告别语。 “求知若饥, 虚心若愚。” 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那样,现在, 在你们即将毕业, 开始新的旅程的时候, 我也希望你们能这样:
求知若饥, 虚心若愚。
——摘自 [美] 史蒂夫·乔布斯著: 《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 张勇译, 《世界教育信息》 2012 年Z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