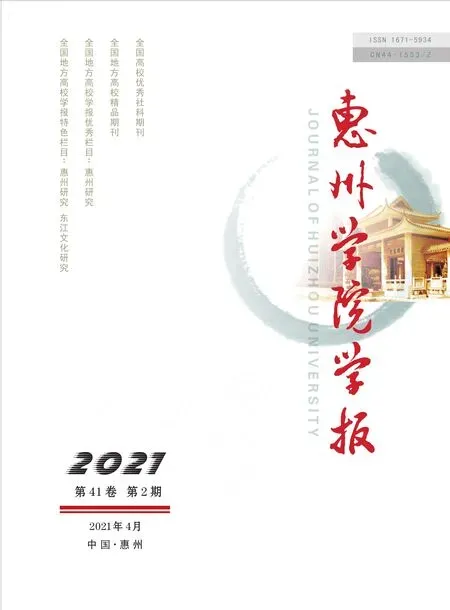罗浮山游记论略1
史素昭,梁 琳
(1.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516007;2.阳西县方正中学,广东 阳江529500)
作为全国道教“十大洞天”中“第七洞天”,罗浮山以岭南著名文学景观的形象,一直活跃在文人的诗文歌赋里。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载:“考罗浮始游者安期生,始称者陆贾、司马迁,始居者葛洪,始疏者袁宏,始赋者谢灵运”[1]89。在葛洪、袁宏、谢灵运之后,历代不少骚人墨客、高官名士都曾畅游罗浮山,并有名篇佳作传世,其中包括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罗浮山游记。本文罗浮山游记的研究对象,以清末民初罗浮山游记的四本专辑为主,即:民国时期酥醪观圆镜道人钟玉文编撰的《罗浮山游记汇刊初编》,共刊宋、明、清时期赵汝驭、祝允明、李时行、欧大任、李孙宸、陈恭尹、谢兰生等十四位名人的罗浮山游记;清人马俊声编撰的《罗浮游记》;清人陈青槐编撰的《罗浮纪游》;清末民初陈伯陶编撰的《罗浮指南》。此外,还有清人潘飞声的《罗浮纪游》,以及苏轼《游罗浮提名记》等零散游记。
目前学界对罗浮山游记关注不够,资料整理较多,学术研究极少。只有李若晴的两篇论文《罗浮山旅行与纪游诗画——以嘉道年间广东名士谢兰生为中心》和《浮山崛起——嘉道年间罗浮山的重新发现与实景山水画创作》涉及了少数几篇罗浮山游记,不见其他研究成果。因此,笔者对罗浮山游记做一番整体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罗浮山游记独特的山水品味
罗浮山游记记录了文人名士看山、寻水、赏石、观瀑、访胜、寻芳的踪迹,体现出不同寻常的山水品味,流露出人与自然山水的亲和。
(一)气韵生动的罗浮山水
罗浮山游记,看山是重点。祝枝山笔下的罗浮山雄秀奇诡:“望山色异甚,状亦绝诡。奇山横互,盘盘如巨屏,略无林樾。然而神气岌岌,若与天为徒。高处峰崖,接次不断”[2]10。雨中的罗浮山更是令人痴迷不已:“云气弥漫塞路,远近峰峦如出没银海,飞泉琅琅,喷射涧壑。而四山桧竹,挟风雨与泉声相乱”[2]20(郭子直《今雨奇游·序》)。这样的描绘充满了诗情画意。苏轼可能是最早留下游记的罗浮旅客[3]19。苏轼在《题卓锡泉记》写罗浮山泉:“近度岭入清远峡,水色如碧玉,味亦益胜。今日游罗浮,酌景泰禅师卓锡泉,则清远峡又在下矣”[4]159。苏轼在《游罗浮提名记》中写朱明洞洞幽水琅:“坛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锵鸣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4]158。如葛洪所说“阴洞冷冷,风佩清清,仙居永劫”[4]211,置身于此,如同置身于仙境,忘怀了尘世的喧嚣,闲适惬意!罗浮山不仅洞幽水琅,山石也皴皱如画:“潭上有亭,俯瞰潭底,石皆绉叠,色如水银,显露龙形,两山中划,均作大斧劈皴”[5]6。“雨霁,藉山僮导游蛤蟆潭。潭中砥石层垒如叠巘[2]62”(颜薰《游罗浮琐记》)。罗浮山的瀑布闻名遐迩:“(华首)寺后泉石益奇,有合掌岩。巨石中空,下广上锐,如合十爪。有瀑布落悬崖,注于平潭,飞流四射,如倾万斛珠,坠潭面辄跃起数尺,最为壮观”[2]43。潘耒曾评价王士性的《五岳游草》说:“先生夙植灵根,下笔言语妙天下,兴寄高远,超然埃壒之外……刻画意象,能使万里如在目前”[6]20。此言用来评价潘耒本人《游罗浮记》的这些精彩文字也非常合适。谢兰生《游罗浮日记》叙及访胜经历:“吾三人趺坐石上,久之,乃遍游石城,见壁上镌字深入分许,字意如以刀作笔,半楷半隶,云:‘朝吴暮粤,水天一色。长啸归来,山青月白。’不书姓名,真是仙笔”[2]56。罗浮山留下很多前人题字,诗意和书法均功底深厚,增加了罗浮山山水景观的人文底蕴。宋代赵汝驭担任惠州知州时曾游览罗浮山,访胜寻芳,并写下《罗浮山行记》。他笔下的景色野趣盎然:“与客步自冲虚,东行数里,泉声潢然出丛翳中,其上则洞口也。由洞口而南有岩,双壁宛若门然。从门以入,歘然见寒梅于藤梢棘刺间,崎岖窈窕,皆有古意,顾者不甚见赏。问其地,则赵师雄醉醒花下,‘月落参横,翠羽啾嘈’处也”[2]8。怒放的寒梅保持着古朴自然的生长姿态,枝干倔强地横斜在朱明洞口丛生的荆棘藤萝中。“泉声潢然出丛翳中”,加上隋人赵师雄醉憩梅花下遇佳人的美丽传说,有一种“妙处难与君说”的愉悦感和幽美的神秘感,以至于让作者产生了“若与抱朴子、桃椎子相期于缥缈”[2]9的幻觉。
(二)人与自然山水的亲和
罗浮山游记体现了人与自然山水的亲和;这种亲和关系,一则表现为一种对山水的天然亲近,二则表现为把山水放在与人同等的地位,视山水为自己的知己朋友。
明代学者黄汝亨说:“我辈看名山,如看美人,颦笑不同情,修约不同体,坐卧徙倚下同境,其状千变。山色之落眼光亦尔,其至者不容言也”[7]1112。有当代学者评价袁宏道游记说:“他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超出了人对自然的欣赏品味,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他亲近大自然时的那份痴恋情怀”[8]73。罗浮山游记何尝不是如此。罗浮山游记对山水的亲近,首先表现在对自然美景发自肺腑的赞叹和情不自禁地感慨。潘飞声在《罗浮纪游》中叙写其深情款款地远眺罗浮:“江上静悄,月明如昼。忆陈兰甫先生语余云,昔游罗浮,仅得‘罗浮睡了’四字,欲续为词,久而未成。起从天际望一抹遥峰,真觉先生此四字为传神之笔也”[5]6。颜薰在《游罗浮琐记》赞叹飞瀑的动人心魄:“玩锦屏峰,峰下左岩石,题曰‘飞云溅雪’,右题曰‘听涛百尺’。飞泉直注平潭,潭畔洗衲石湍激,如倾万斗珠,令人魂怡魄荡”[2]63。罗浮山的山水美景更需慢慢欣赏细细品味,所以谢兰生在《游罗浮日记》中写道:“向闻此径松石茂美,不让西湖之灵隐韬光。惜夜行,遗却佳处,凡事见地容易,到地不容易。今日罗浮君既为予祛除云雾,露全身,其中秘奥,岂令人一日揽尽乎?”[2]50对罗浮山水的那份痴迷爱恋以至于让谢兰生产生了卜居之兴:“此地深不过幽,奇不尚险,有泉石可莹心神,置室屋可安眷属。近与仙观比邻,远有云峦遮护,花竹草木,种自前人,田原陂塘,筑之由我。江夏子有志卜居,园亭若成,游偃终身。岂复思出山乎?”[2]55罗浮山的山水美景常常让游记作者喜不自禁、浮想联翩;读者也仿佛置身其间,获得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9]198。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10]193。
罗浮山游记还把山水放在与人同等的地位,视山水为自己的知己朋友。《徐霞客游记》开篇写道:“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陈函辉评徐霞客游记“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11]110。罗浮山游记亦是如此。谢兰生《游罗浮日记》写道:“晓行数里,江面群峰,上有大山雄秀特峙。如仙子被霞裳立水际,肯舒眉与凡士接者,心讶之”[2]50。在作者的笔下,罗浮山就像披着霞裳等待自己的红颜知己,令他惊喜不已;这种写法与袁宏道《华山别记》中“是日也,天无纤翳,青崖红树,夕阳佳月,各毕其能,以娱游客”有异曲同工之妙。谢兰生写罗浮山小蓬莱:“江道人称小蓬莱,岂以其地静穆,有怀葛风欤。然小蓬莱浮山之总称,前人诗云:浮山浮海自东来,嫁与罗山不用媒。合体真同夫与妇,生儿尽作小蓬莱”[2]54。浮山、罗山和小蓬莱,就如同人间的一家人,亲切自然,富有生趣。类似人与自然山水灵犀相通的描绘在罗浮山游记里比比皆是。“抵博罗界,罗浮岿然在目。江浅流清,薄暮明霞。互空五色照映,疑玉女、麻姑辈于峰头相招[2]34”(欧必元《游罗浮山记》)。“入观门,老梅数支,老桂一枝,方作花时。诸院梅俱残而此方盛,岂留以欸客者耶?[2]54”(谢兰生《游罗浮日记》)“麻姑峰下,夕照含山,秋荫到地。回望孤青、玉女、老人,恍若翘首垂鬟,依依相送[2]151”(陈青槐《罗浮纪游》)。“有门曰‘梅花村’,芳眼疏明,皆迎人笑[2]9”(赵汝驭《罗浮山行记》)。有学者说《徐霞客游记》“是表现一位名士与山水自然作心灵对话的记录,是人与自然的情感交流史”[12]52,此言用来评价罗浮山游记亦十分妥当。
二、罗浮山游记与罗浮山山水画
罗浮山游记不仅诗意地模山范水、漫记风光,而且在自然美的发现和观照中,体现出十足的画意。罗浮山游记与罗浮山山水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浮山山水画的创作深受罗浮山游记的影响,有的山水画作直接取材于罗浮山游记的纪游描述文字,增加了罗浮山景观的文化韵味。
广东名士谢兰生的罗浮山纪游画作与其《游罗浮日记》互为映衬,相得益彰。谢兰生罗浮山游记及其相关的罗浮山山水画创作问题,当代学者李若晴在《罗浮山旅行与纪游诗画--以嘉道年间广东名士谢兰生为中心》一文中有比较中肯的阐述,笔者深以为然,本文有关论述参考李若晴先生的观点[13]86。谢兰生《艮泉图咏》(纸本水墨,28.5×500cm,1814年,广州美术馆藏),便是根据其《游罗浮日记》文字忠实地绘描艮泉周围的风光:“沿山后双髻峰,下觅艮泉……明潭澄绿,洞照肺腑,诧为奇特。上潭即艮泉,有瀑流右落,左折一激而注。潭旁有丹灶及丹井,潭中石凡两重,势皆圆抱。其下为琉璃潭,似束方势。皆天然结就,石色净滑。如日有人为洒扫然者……谂以步蒙子曰:‘予入山,始见此奇’”[2]54。谢兰生《罗浮烟雨图》(绢本设色,91×42cm,广州艺术博物院藏),作者款识曰:“入合掌岩,修路逶迤,奇石异卉,夹道幽秀。有石两片,如人合手礼佛,岩罅通透,倏阴乍阳。小径蛇蟠,徐起而伏。岩口左侧,瀑泉巨奔而落。大石中起,若与之拒,即洗衲石也。尝为汤贻汾守戒,写一小幅,甚肖似。”这一段文字,即是谢兰生《游罗浮日记》中的原句[2]52。谢兰生最有名的罗浮山山水画,是于道光元年所作《茶山飞瀑图》(绢本水墨设色立轴,116×43.5cm,1821年,广东省博物馆藏)。此画远景横断丛山,云雾缭绕;近景杂木葱郁,溪流潺潺;意蕴幽深闲适,宁静致远。对照谢兰生《游罗浮日记》的文句:“入茶山。高松拂天,云凝不流,松罅白练横飞,环山上下雷转,动人心魄。山顶小祠,肖黄仙像……其旁小屋数椽,依崖而立,最后峭壁撑空,一瀑直注,凝为深潭。潭旁黝石数方,位置高下,恰如人意。坐以观瀑,神清体安。两崖多植山茶、梅、桃、杂花,落英纷馥。入山来始一豁双眸也”[2]54。这一段话,就是对《茶山飞瀑图》构图、景物、人物、设色、意境的如实而又诗意的完美解说。《茶山飞瀑图》款题“茶山飞瀑。辛巳小春。茶山瀑布自山顶飞下数百尺,潴为潭,又由松阴数十折,而后赴壑。吾尝欲与步蒙子结屋山椒,筑塘二顷,灌田养鱼,可以终身倘佯其间,非惟擅林泉之胜也。因赋西江月小词一首以申前盟:四壁云岩积铁,中间天乐鸣绞。冥心坐向水天中。看见本来真面。松下筑塘二顷,厓前架屋三椽。饥餐渴饮困时眠。仙矣何劳修炼。里甫居士识”,与上述《游罗浮日记》文辞异曲同工水乳交融,画作、款题、游记文句均是谢兰生超俗之心灵世界的流露。《游罗浮日记》为谢兰生的罗浮山山水画提供了蓝本和素材,而谢兰生的罗浮山纪游画作又使其《游罗浮日记》中的仙景仙境得到直观的呈现,赏心悦目,愉人心智。二者交相辉映,相互成就。
罗浮山山水画与罗浮山游记互为印证的情形,在作者相异的画作和游记里也常常存在,使罗浮山盛名远扬,底蕴深厚。清代黄鼎《罗浮春色图》(绢本设色,60.3×43cm,广东省博物馆藏),作者题识曰:“昔游岭南,值木棉花放,荔树生叶,红绿相间,开遍野塘。粤东春色如此,乃江左所无,追忆旧游,写罗浮春色,以应西斋学长见教。黄鼎,时戊申春二月七日也。”黄鼎以罗浮山景致代表南方山水,融绘于《罗浮春色图》中;湍流的清溪、青绿的山石与红色的树木相映成趣,密繁中见疏落,朴茂中见旷远[14]20。对比陈青槐《罗浮纪游》所述:“至于石龙,溪水清浅可涉。水中石齿艮艮,每遇山环处,即淡折成潭,鱼皆悬空可数。溯溪行四里许,忽睹棕榈数株,亭亭可爱,是为浪头。踰溪小憩野店山庄,颇有幽趣……天香室为憩赏之所,种木棉绕屋。而环分霞岭种松、梅、桄榔千万树……木棉几株,清香远溢。桄榔松竹,薄荫交垂”[2]152。见字如见画,画作、游记,二者情境何其相似!黎二樵1767年作《罗浮观日图》[15]154,所绘之景暗合赵汝驭《罗浮山行记》所写“罗浮山观日”:“及披衣起,天际已明,及上则暗。久之,火轮由暗中射飞涛以出。向所谓浑沌,又若造物者,始判清浊,而六合晖新也。林霏一开,负寒凌澌,变而明岚暖翠,凡岭南之山川,隐显背向,咸无遁形”[2]9。陈璞《茶山下叠瀑》(纸本水墨,册页,26.5×37cm,广东省博物馆藏),又可视作欧必元《游罗浮山记》所观瀑布的写意画:“诸子俱往,稍近望之……悬崖千丈,轰轰下泻,澎湃百状。飘者如雪,断者如雾;缀者如梳,挂着如篇。散入山足,森然四口;涌若沸汤,奔苦跳鹭。其声蕴隆,日久不绝。诸山之水,此为最奇”[2]39。
三、罗浮山游记与罗浮山旅游资源开发
有学者指出:“(人们)深爱罗浮山的群山高峰、林木花草、珍禽异兽。罗浮山的道教文化、罗浮山的仙景仙境、罗浮山的朴淳民风,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罗浮山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谐相生,令人叹为观止”[16]10。罗浮山成为岭南旅游胜地,固然有赖于其天然美景、仙山盛名和文化底蕴,但罗浮山游记对罗浮山旅游资源开发的作用不容忽视。
罗浮山游记对开发罗浮山旅游资源提出整体规划,以赵汝驭《罗浮山行记》和潘飞声《罗浮纪游》等为代表。六朝时代的罗浮山曾为道佛胜地,之后逐渐寂寥。潘耒《游罗浮记》写道:“罗浮非难游,苦无栖息地”[2]42。南宋赵汝驭任惠州知州时,深感重建罗浮山、恢复其盛名势在必行。从赵汝驭《罗浮山行记》可见,由于景区配套设施跟不上,“路转山腰,舆者已痡,道士亦倦”也找不到休憩场所,所以“皆将兴尽”;赵汝驭只好独自登顶:“登伏虎岩,至朝真石,视众山于薆葑之罅,已培嵝然矣。过分水凹,迄逦历平圹,如坞如坳。忽然若凭虚上腾以凌空,云气变态,不可名状,犹天地浑沌如鸡子未判时。”虽然一睹云雾仙境却“恨无庐可托以伺日出”;因此,赵汝驭决心开发罗浮山旅游资源。一是开辟旅游线路:“捐缗粟,命道士从所取道辟焉。”二是整体规划:“以目行心画者指授之曰:某地宜门,某地宜亭,又某地宜庵。属博罗令赞其事。”由于赵汝驭是惠州知州,握有实权,他的规划第二年便已落实好:“山之麓有门,曰‘屐云’,表飞云之屐,如从足下也。向所谓洞口,有亭曰‘仙春’,迩青远白,佳趣现前。向所谓顾者不赏,有门曰‘梅花村’。芳眼疏明,皆迎人笑。向所谓兴尽欲返,有亭曰‘横翠’。依崖据胜,可眺可休。向所谓薆葑之罅,有亭曰‘拂松’。镜石琴风,景象轩豁。向所谓无庐可托,有庵曰‘见日’。卓然三千六百丈之上,审曲面势,大约如指授。”自然美景融入适当的人为点染,游客倦怠之时随时有暖心憩所,罗浮山旅游条件大为改观,以至于由先前“荒凉萧条”至于现在“游客如织”:“山行者累累若鱼贯。”有学者认为,由这篇游记可见,赵汝驭称得上是开发罗浮山的一大功臣,是宋代重建罗浮山游览区的设计师[17]。笔者很是赞同。此外,潘飞声在《罗浮纪游》中写道:“使建铁轨于陆路,借仙人之飞车,作长房之缩地,不逾数刻可履洞天门阑矣。瑞士、意大利称西土名山,自筑路以来,林木茂密,田亩丰穰,市尘畅盛,民游乐国,暴寇不生,楼台可泽金银,云霞新其绚绮,此仙城宝界之犹有待于后人也”[5]9。这可谓是一个开发罗浮山旅游资源的宏伟构想,眼界开阔,见识不凡,启迪后人。
当代学者李若晴曾指出,谢兰生的《游罗浮日记》和各种山志一样,成为后人游览罗浮山的指南[13]97。笔者认为,很多罗浮山游记也有这样的作用。民国罗浮山道士张学华给钟玉文编撰的《罗浮山游记汇刊初编》作的序文,先叙名士畅游足迹:“邹师正《指掌图赞》由宝积寺后之二石楼,层累而登。当时谓之云路,今已断行人。宋赵汝驭则自石洞开路而上;明刘克平则自金沙寺上;清潘耒则自华首台上。又明欧大任、李孙宸曾登飞云顶,攀陟险阻,所历之境又不尽同,并详所作游记”[2]3。再叙罗浮山游记风物考证和导游之作用:“(罗浮山)上下数千百年,仙山灵迹,不可胜纪。而径路之变迁,祠宇之建置,或昔险而今夷,或昔存而今毁,赖此互相考证。其有裨于掌故,固多抑可为游者之先导焉”[2]3。此为确论。陈伯陶的《罗浮指南》写到自己每至一处,都按前人游记一一考证。比如:“资福寺在华首台下。李时行《游记》:‘华首台前有资福寺。’则明中叶尚存”;“宋季赵汝驭则自石洞开路而上。详见赵汝驭《登山记》,李昂英《飞云顶开路记》。明刘克平游记则自金沙洞上”[2]168。类似的表述比比皆是。罗浮山游记不仅对罗浮山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启发,而且为罗浮山水景观注入人文底蕴,如张学华道士序文所言“或足为名山增重也”[2]3!
罗浮山游记促进了浮山(罗山和浮山合称罗浮山)旅游资源的开发。当代学者李若晴指出:“从宋代到清初的罗浮之行,大体以罗山为主,浮山几乎没有文人的足迹履及。如果从广州乘船而至,罗山游览相对方便,浮山则较为幽僻……其游屐多止步于罗山南麓,而未能深入浮山”[2]22。何仁山在《书罗浮览胜图卷诗后》写道:“罗浮二山,浮胜于罗,而游者罕到”[18]183。可见,古代对浮山的开发是非常滞后的。不少罗浮山游记记录了名士们的浮山之行,描绘了浮山的奇峰异景,使得浮山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罗浮山游记的作者认为罗山与浮山难分高下。谢兰生《游罗浮日记》写道:“諗以步蒙子曰:‘予入山始见此奇,人言浮胜于罗,斯言信否?’步蒙曰:‘不然!二山皆栖真之所,佳境俱在深处。高处如罗之百花径、大石楼、君子岩、朱明洞、飞云顶、上界三峰,实离尘绝俗,非此不足栖息仙灵。惜乎!子之未见。即如艮泉,初时壅翳无路,予斩荆入,乃获斯胜,未可于两山分轩轾也。’此洵不磨之论”[2]54。陈青槐的《罗浮纪游》亦云:“大抵罗之胜在雄奇,浮之胜在幽奥,二山几难轩轾。弟雄奇者危峰峭石,拔地倚天,其险怪也固足骇;幽奥者复巘重峦,浓描淡抹,其飘渺也尤可欣。至若灵踪异产,怪怪奇奇,二山各擅其胜。”不少罗浮山游记还认为浮胜于罗。潘耒《游罗浮记》曾言:“然吾观罗浮二山,横亘数十里。秀岩深壑,以千百数。浮在罗之西北,尤大而长”[2]46。潘飞声在《罗浮纪游》中写道:“而子居复有渐粗恶之言,不知浮山较罗更高,山皆峻岭,浓绿古翠,磅礴雄尊,自异罗之秀峭”[2]9。潘飞声还深入浮山游览:“阅《浮山志》载佛子凹鸟道百盘,行者喘息,然巨灵设险,所以限俗士之游踪,待高人之芳躅。又忆陈元孝句‘神地于今路亦难’,余独游至此,诚一快事”[2]10。罗浮山游记记录了文士们游历浮山的所见所闻所感,深得山水兴味;嘉道之后,浮山日渐成为名士文人旅游罗浮山新的热门路线,游罗浮山不至浮山,会被笑话为“浅尝辄止”[3]36。所以,陈青槐《罗浮纪游》写道:“往阅吴谷人《游泰山记》谓:‘游泰山不游黄华,不如不游也。’余谓‘游罗不游浮’亦然”[2]152。张其淦在《历代罗浮山游记汇刊·题词》亦云:“好月人间第一秋,既到罗山应到浮”[2]4。可见,浮山之所以被不断关注、重新发现并得到相应的开发,有多种原因,但罗浮山游记的作用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