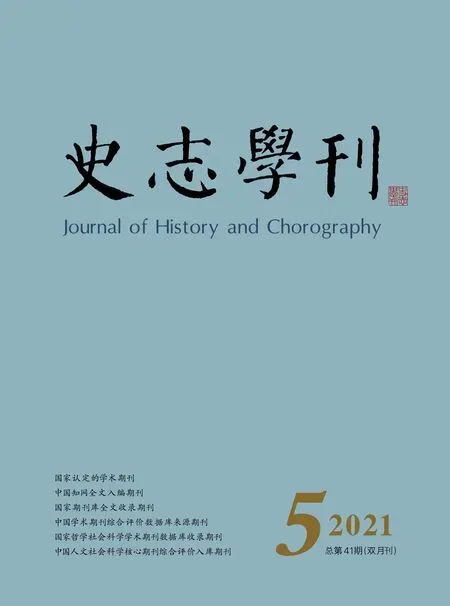东晋初年南北士族共生模式与义兴周氏兴衰
杨恩玉 刘文兴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义兴周氏作为江南极具实力的武力强宗,其兴亡史实历来颇受史家关注,如陈寅恪先生提出:“王导在利害关系上总是设法避免与东吴士族的冲突,笼络义兴周氏为王导笼络吴人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环。”[1]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黄山书社,1987.(P157)川胜义雄先生亦说:“江南土著豪族第一次受到北来亡命贵族的压制,首先发生在314年阳羡大豪族周玘之子周勰的叛乱过程中。”[2](日)川胜义雄著.徐谷梵,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P158)而义兴周氏的势力变化是在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本文拟从东晋元帝和明帝时期的侨旧共生模式变迁入手,探讨义兴周氏的兴衰历程及其历史背景,并进一步探究东晋时期南北士族间的关系。
一、渊流:南北地域的传统关系
中国南北方之间的关系自三皇五帝时便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形式:一方面两者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并引发大规模战事。西北地区凭借黄河流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产劳作方式等优势,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而东南地区由于经济和文化的滞后自三代以降便逊色于西北地域,故而娄敬向刘邦献策时便主张定都关中,并将之比作“咽喉”所在;张良也说:“夫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以制东面诸侯。”[3](西汉)司马迁.史记[M].卷 55.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59.(P2044)西晋统一孙吴之后,这种地域上的冲突和歧视仍未消弭,西晋时武帝策试秀才华谭说:“吴人趑雎,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博士王济亦曾嘲讽华谭:“君吴、楚之人,亡国之馀,有何秀异而应斯举?”[1](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52.华谭传.中华书局 ,1974.(P1450-1452)作为东吴名臣陆逊之孙的陆机,成都王司马颖任命他为河北大都督后,小都督孟超挑衅地说:“貉奴能作督不!”[2](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54.陆机传.(P1480)由此可见,当时南北士族间的矛盾之尖锐,这也是后来司马睿入镇建邺之初江东士族不予合作的历史原因。
南北方之间的另外一层关系是:在北方战乱时南方会成为北方人民的避难所,两者会在此种特殊的情况下取得共生的机遇。在商汤灭夏后,“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3]逸周书[M].第66.殷祝解.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P74)。据《史记正义》,南巢在庐州(今合肥)巢县。作为中华民族主宰的北方文明群体虽与南方士民常有冲突,然而在他们遇到战乱、生活窘迫时常选择前往南方避难,不仅是先秦时代,在三国战乱时孙坚、孙策父子前往东南地域创建东吴并臣服山越亦是此种情况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南北方自半信史时代开始,便有着冲突与共生的双重关系。这种地域之间的共生关系也为后来永嘉南渡和东晋南北士族关系的演变提供了历史渊源。
二、兴起:建康政府草创中的义兴周氏
周玘三定江南为江左政权的草创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在太安初期(303),张昌部将石冰率领的农民武装攻破扬州,周玘联络“江东士人”、共推吴郡顾秘统领扬州讨逆诸军事,消灭了石冰势力,此为“一定江南”。此后广陵相陈敏企图割据扬州,并拉拢江东世家豪族,他们因为陈敏是出身低微的寒庶不愿与之合作,故而周玘与“顾荣、甘卓等以兵攻敏,敏众奔溃,单马北走,获之于江乘界,斩之于建康,夷三族”[4](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58.周处传附周玘传.(P1572)。此为“二定江南”。在陈敏之乱时吴兴人钱也曾起兵讨伐,司马越任命其为建武将军,但他不久反叛,“杀度支校尉陈丰,焚烧邸阁,自号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劫孙皓子充,立为吴王,既而杀之。来寇玘县[4](P1573)”。周玘“复率合乡里义众,与(将军郭)逸等俱进,讨,斩之,传首于建康[4](P1573)”。此即“三定江南”。周玘之所以能够三定江南,在于义兴周氏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号召力和宗族实力,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王导在利害关系上总是设法避免与东吴士族的冲突,尤其是义兴周氏是他联合东吴士族的重要环节,这主要源自于江东士族本身的强大实力[5]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0.(P157)。
在“三定江南”过程中参与人员的身份是有变化的,这里便隐藏着永嘉南渡后南北士族实力增减和共生状态的变迁。司马睿是在永嘉元年(307)担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石冰之乱的平定是在太安二年(303),时隔四年,这四年的时间在江南占主导地位的是陈敏和江东诸士族,晋朝政府由于八王之乱和汉赵的建立(304)无暇顾及江南,江南几乎没有足够的势力尤其是军事力量来保障对东吴故土的有效统治,所以石冰能轻易攻破扬州。“一定江南”的大多是江东人士,吴郡顾氏作为江南士族领袖承担了此次平叛的领导者。平定陈敏之乱的则是汝南周氏的周馥,“(周馥)出为平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代刘准为镇东将军,与周玘等讨陈敏,灭之,以功封永宁伯[1](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61.周浚传附周馥传.(P1663)”。周馥屯驻寿春,在江东驻守的时间还要多于司马睿,是“江西诸军”的实力代表。在此次平乱中顾荣曾私言于甘卓:“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事败之日,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题曰逆贼顾荣、甘卓之首,岂惟一身颠覆,辱及万世,可不图之。”[2](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68.顾荣传.(P1813)可见顾荣等江南士族对于江西诸军势力的忌惮。为实现江南豪族地主利益的最大化,以顾荣为代表的江南土著文化士族选择拥护司马氏。正因如此司马睿和王导在进驻建康后才能站稳脚跟,草创江左政权。
晋怀帝永嘉元年九月琅琊王司马睿至建康,当时的情形是“吴人不附,居月馀,士庶莫有至者”[3](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65.王导传.(P1745)。在王导的策划下,“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王)敦、(王)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3](P1746)”。川胜义雄先生曾对此提出异议,说当时琅琊王军事实力几乎为零,而王敦此时未在建康,故不足取信[4](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P144)。实际上即使此记载不够准确,但当时江南名望拜于道左应是事实,因为江南土著文化士族对于北方士族虽有矛盾,但对于其文采风流和传统礼仪文化是极为赞同和倾慕的。东晋葛洪说:“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犹其小者耳。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令忽然无复念之情……曰:‘此京洛之法也。’”[5](晋)葛洪著.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M].下册.中华书局,1997.(P12-17)江东士族对于北方京洛文化的尊崇和倾慕是南北士族迅速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司马睿“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6](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6.元帝纪.(P144-145)”。这体现出三吴土著文化士族与北方南渡士族的融合趋势,而其中没有义兴周氏、吴兴钱氏等武力强宗。但在这种形势下“江州刺史华轶不从,使豫章内史周广、前江州刺史卫展讨禽之[6](P144)”。周广是华轶的部将,他临阵倒戈,导致华轶战败被杀。周访为汝南周氏,先祖汉末时避乱江南,在庐江地域生活。平定江西诸军时司马睿本人并无直属兵马,仍要借助于江南地域士人的协助。吴兴人钱起兵,王敦在得知“环环会阴欲杀敦,藉以举事”[7](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58.周处传附周玘传.(P1573)时,行为是“奔告帝”。由此可见,王敦此时虽居扬州刺史,然在面对钱环环会叛乱时却拿不出足够的制衡力量,只能前往建邺,而后还是周玘借助乡里武装平定此次叛乱。
综上所述,由于琅琊王司马睿坐镇建康时武力的不足,以吴郡顾氏、义兴周氏为首的江南土著豪族为了自身权益联合起兵,并在司马睿和江西诸军进行争夺时选择了司马睿这一政治势力,最终完成了建康政权的草创。但由于义兴周氏本身的强大实力和江左政权对它的忌惮和歧视,江南武力强宗与琅琊王集团实际上已经有了裂痕,由此引发了周勰之乱。
三、转折:南北士族联合过程中的义兴周氏
司马睿在江南武力强宗支持下消灭江西诸军,标志着江南土著豪族也倒向了司马睿;即使如此司马睿的军事实力仍很微弱,在此情形下江南武力强宗就成了江左政权不得不依靠的力量。江南武力强宗试图通过自己的武力积极推戴司马睿并拥护晋王室的权威,然后在这一姿态下,努力打造一个实质上属于自己的政权[1](日)川胜义雄.徐谷梵.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P158)。这样的诉求在“三定江南”的过程中的确得到了满足。所以桓彝在渡江后对周顗说:“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2](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65.王导传.(P1747)这时已经是永嘉五年(311),距离司马睿渡江已有四年,在此期间虽依靠王导和江南士族取得联络,但中州士族在南北关系中仍处于劣势地位,这种状态在同年六月发生了变化。随着永嘉之乱发生,晋怀帝被匈奴大将刘曜俘虏,司空荀藩传檄四方,推举琅琊王司马睿为盟主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江南士族企图创建符合自己利益政权的愿望落空,琅琊王已经有了名位,也有了威权和号召力,北方流民势力开始向其身边汇集,而此时江南士族则逐渐开始居于劣势。不过这只是初现,并未完全得到实现,讨平江州刺史华轶事便是证明。华轶是江西诸军的代表,与周馥属同类势力,都与江南士族分庭抗礼,对于司马睿的建康势力一直处于漠视状态,故而“帝承制改易长吏,轶又不从命”“(北中郎将裴)宪自称镇东将军、都督江北五郡军事,与轶连和”[3](北齐)魏收.魏书[M].卷 96.僭晋司马睿传.中华书局,1974 年.(P3092)。司马睿“遣左将军王敦都督甘卓、周访、宋典、赵诱等讨之[4](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61.华轶传.(P1672)”。此次战争王敦虽然身为都督,但实际发挥作用的是周访等南方士族代表。虽然司马睿承制将北方流民和士族武装聚集到自己身边,但司马睿、王导并未改变联合江南士族的政策,只是在人员类别上有了改变。他们吸纳和联合的多为如甘卓等文化士族,对于义兴周氏等武力强宗则开始予以排斥,以致后来平定江西诸军时并未任用“三定江南”的周玘,而是任命属于汝南周氏的周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原因就在于祖逖等北来流民团体的加入壮大了司马睿的势力。
八王之乱后的西晋政权处于分崩离析的态势,各地的士族、百姓为了自身的生存除流徙避祸外,多选择结壁自保并逐渐演化成了武力集团。“及京师大乱,(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5](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62.祖逖传.(P1694)“(邵)续去县还家,纠合亡命,得数百人。”[6](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63.邵续传.(P1703)“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李)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7](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63.李矩传.(P1706)”。这些武装势力在北方与匈奴、羯族势力的战斗为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政权缓解了北方的压力,又稳定了建康集团的北部。后来祖逖北伐时被任命为豫州刺史,邵续死后仍抚慰其众,虽然职务、实权上有很大折扣,也表明北方武力流民势力开始有所上升。“于时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周)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周玘为挽救这种颓势便开始密谋叛乱,结果事泄,周玘抑郁而终,他去世前对其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8](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58.周处传附周玘传.(P1573-1574)“伧”字是吴人对北方侨民的蔑称,这显示出二者之间的矛盾,由此引发了周勰之乱。“勰因之欲起兵,潜结吴兴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矫称叔父札命以合众,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吴兴徐氏、义兴周氏、孙皓后裔联合举兵,周勰欲借助其叔父周札的实力,然“札以疾归家,闻而大惊,乃告乱于义兴太守孔侃”[1](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58.周处传附周勰传.(P1574)。此时司马睿的应对策略也可以看出当时建康集团的实力状况。
“元帝欲讨之,王导以为‘兵少则不足制寇,多遣则根本空虚。(周札兄子)黄门侍郎周莚忠烈至到,为一郡所敬。意谓独遣莚往,足能杀续。’”司马睿接受了这个建议,顺利平定了叛乱[2](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58.周处传附周莚传.(P1577)。由此可以看出,为进一步提高早已承制但军事实力仍显衰弱的琅琊王集团的实力根基,北迁士族在进一步坚持王导联合江南士族政策的同时,开始将流民帅势力引入政府并将之作为北部屏藩,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又使得江南的武力强宗产生了分化,一部分进入了建康集团,另一部分因为受到排挤而爆发了叛乱。也正因此时司马睿军事实力的不足,对于武力强宗仍要有拉拢和联合的姿态,故而对于周勰的处理便有了与周馥、华轶明显的不同。“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勰为札所责,失志归家,淫侈纵恣,每谓人曰:“‘人生几时,但当快意耳。’终于临淮太守。”[3](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58.周处传附孙勰传.(P1574)周勰作为叛乱的首谋没有受到惩治,司马睿对他抚之如旧,原因就在于义兴周氏势力强大。
四、衰亡:王敦之乱中的义兴周氏
元帝太兴四年(321)四月发布诏书:“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4](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6.元帝本纪.(P154)这一诏书将原属士族的部曲奴隶解放为国家直属民,以扩大兵源。对于以义兴周氏为首的江南武力强宗来说,这是不小的打击,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在已知单凭自身实力难以改变局面时便开始寻求第三方势力的帮助。
位于长江中上游荆州地域的王敦在消灭华轶后势力逐渐增强,之后与陶侃、周访等人联合平定了荆州杜曾之乱,并随之安定湘州,成为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强藩。随着王敦势力的增长,他与陶侃、周访间的关系也逐渐恶化。陶侃与王敦的矛盾是在平定湘州杜弢叛乱时埋下的,“王敦深忌(陶侃)功。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廙为荆州[5](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66.陶侃传.(P1772)”。“初,王敦惧杜曾之难,谓(周)访曰:‘擒曾,当相论为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职,诏以访为荆州。敦以访名将,勋业隆重,有疑色[6](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58.周访传.(P1581)”。面对陶、周两方势力的威胁,王敦也有着引入他系势力的诉求,故而江南武力豪族和王敦之间便有了合作的基础。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沈充和钱凤。“沈充,字士居。少好兵书,颇以雄豪闻于乡里。敦引为参军,充因荐同郡钱凤。凤字世仪,敦以为铠曹参军,数得进见。知敦有不臣之心,因进邪说,遂相朋构,专弄威权,言成祸福。[1](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98.王敦传附沈充传.(P2566)”由于司马睿废除奴籍招致江南武力强宗的不满,故而他们希望依靠王敦在政治上出人头地[2](日)大川富士夫.六朝前期的吴兴郡豪族——特别围绕武康沈氏.立正大学史学会编.宗教社会史研究[M].熊山阁出版社,1977.(P537)。由于近似的利益诉求,先前反对周勰之乱的周札也倒向王敦,“王敦举兵攻石头,札开门应敦,故王师败绩[3](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58.周处传附子札传.(P1575)”。《魏书》亦载:“札潜与敦书,许军至为应。”[4](北齐)魏收.魏书[M].卷 96.僭晋司马睿传.(P2094)义兴周氏的倒戈使得本身军事实力不足的元帝被王敦控制,元帝也因此抑郁而终。为扭转这一严峻局面,明帝开始召引流民帅进入东晋政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郗鉴。
郗鉴在战乱时没有立刻随中州士族南迁,而是选择结社自固。元帝承制后他逐渐进入仕途,拥众数万。“明帝初即位,王敦专制,内外危逼,谋杖鉴为外援,由是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5](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67.郗鉴传.(P1797)”除郗鉴外,朝廷召集的流民帅还有刘遐、祖约和苏峻。“王含反,遐与苏峻俱赴京都。”[6](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81.刘遐传.(P2130)明帝召引流民帅的结果,可从元、明时期应对王敦之乱时的人员配置上考察。元帝时,“征征西将军戴若思、镇北将军刘隗还卫京都。以司空王导为前锋大都督,以戴若思为骠骑将军,丹杨诸郡皆加军号。加仆射周顗尚书左仆射,领军王邃尚书右仆射。以太子右卫率周莚行冠军将军,统兵三千讨沈充……刘隗军于金城,右将军周札守石头,帝亲被甲徇六师于郊外。遣平南将军陶侃领江州,安南将军甘卓领荆州,各帅所统以蹑敦后[7](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6.元帝纪.(P155)”。明帝时,“加司徒王导大都督、假节,领扬州刺史,以丹杨尹温峤为中垒将军,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以光禄勋应詹为护军将军、假节、督朱雀桥南诸军事,以尚书令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以中书监庾亮领左卫将军,以尚书卞壸行中军将军。征平北将军、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北中郎将、兖州刺史刘遐,奋武将军、临淮太守苏峻,奋威将军、广陵太守陶瞻等还卫京师。帝次于中堂[8](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7.明帝纪.(P161)”。元帝时戴若思、刘隗为元帝心腹,王导、王邃为中州士族,其余的除周顗是南渡流民势力外皆属江南豪宗,故而周札倒戈后元帝无军事实力依托而战败。明帝时,温峤与应詹陶侃同属北方侨民,郗鉴、祖约、刘遐等皆是流民帅,即这次战争东晋政府已摆脱了江南土著武力豪宗的影响,这从其后对周札的处理中也有所体现。
“事下八坐,尚书卞壸议以‘札石头之役开门延寇遂使贼敦恣乱,札之责也。追赠意所未安。懋、莚兄弟宜复本位’。司徒王导议以‘札在石头,忠存社稷,义在亡身……臣谓宜与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书令郗鉴议曰:‘今周、戴以死节复位,周札以开门同例,事异赏均,意所疑惑……今据已显复,则札宜贬责明矣。’……鉴又驳不同,而朝廷竟从导议,追赠札卫尉,遣使者祠以少牢。”[3](P1576)对于义兴周氏的处置,卞壸、郗鉴和王导各有不同的见解,其优劣暂不置论,此时郗鉴和卞壸能够反驳优待周氏之议说明此时随着流民帅势力的增长和王敦势力的覆灭,东晋政权的南北士族侨旧共生模式已经由原来的南北文化士族联合压制、利用江南武力强宗变成了中州文武士族联合左右朝堂,以郗鉴为首的流民帅势力已经取得很大话语权,故而在明帝驾崩时其遗诏中会将流民帅出身的郗鉴作为顾命大臣与王导、外戚庾亮并列。“召太宰、西阳王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杨尹温峤并受遗诏,辅太子[1](唐)房玄龄等.晋书[M].卷 7.明帝纪.(P164)”。江南土著豪族代表只有吴郡陆氏的陆晔一人,这表明江南文化士族在此时由于流民帅势力与中州士族的结合逐渐边缘化,在南北士族关系中已呈现出弱势状态。
综上所述,东晋元帝至明帝时期的侨旧共生模式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永嘉之乱前即311年之前南北士族在江南地域一直是合作联合状态,甚至于南方士族势力一度凌驾于中州士族之上,镇守建康的司马睿因实力的薄弱只好依靠江南的强宗豪族巩固自身实力,义兴周氏势力达到了顶峰。而随着永嘉之乱爆发,司马睿承制,北方流民往来依附者日益增加,中州士族和江南文化士族共同开始排斥义兴周氏为代表的武力强宗,最终导致了周勰之乱,强宗豪族如钱凤、沈充、周札等为摆脱这种困境开始依附王敦。而晋明帝为平定王敦之乱召引流民帅,郗鉴、刘遐等人得以进入建康集团,逐步压制江南的武力强宗并在此后还保持着对江南豪族的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