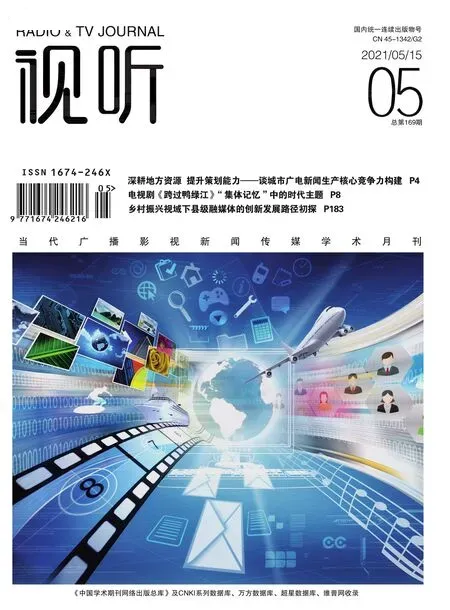官方媒体时政新闻亲近性转向研究——以央视新闻B站短视频新闻实践为例
□ 何东颖 刘 祎
在舆论引导工作要求下,为了在新媒体环境下维系宣传体系,官方媒体传播范式开始背离传统宣传主义,建构了一种吸纳专业主义、煽情主义等不同范式元素的杂糅化形态①。随着网络技术的变革,传统媒体改革逐渐深化,作为内容承载体的新兴短视频平台成为传统媒体变革的又一关键切入点。官方媒体作为舆论引导的主导力量同样加入了新闻短视频战场,寻求与社交媒体平台的深度融合。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陆续进驻抖音和哔哩哔哩等视频平台,补全了官方媒体社交媒体矩阵中的视频板块。视频媒介形式本身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与接近性,相较于之前的文本,体现出亲近性的不同面向。
亲近性新闻(intimate journalism)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新闻实践,它强调对普通人日常心理与生活的记录,倡导对平民化报道的实践经验总结。作为新闻实践的亲近性新闻是对“新新闻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题材选取的平民化与记者介入的理性化②。作为新闻价值的亲近性则是接近性在心理上的深化与延伸,报道的关注点从新闻本身转向关注新闻中信息与人的关系,以及受众在情感、认知、信仰等方面的心理认同③。从具体文本分析来看,亲近性指的是文本的表达方式与文化解读者的符号表达方式、思维方式、解读心理、时空相一致④。
一、官方媒体时政新闻的亲近性转向
(一)叙事情感化:从告知到讲述
与传统电视新闻相比,短视频新闻凭借平台特质打破了组织生产限制和政治符号限制,实现了从告知向讲述的转向。由于短视频新闻是官方媒体的革新尝试,媒介内部的生产限制得以打破,其作为主体电视节目附属补充的角色同样免除了官方媒体的政治符号属性。
以《主播说联播》栏目为例,主持人以口述、点评、呼告等方式进行报道或点评,呈现出情感化和倾向性特点。例如在母亲节当天推出的视频中,新闻联播主持人海霞红着眼圈讲述了李静芝母子通过央视认亲大会成功团聚的故事,其中包括大量的情绪表达、个体感受与价值评价,如“我也是一个母亲,李静芝这些年的锥心之痛,对我来说恐怕连想都不敢想”。与传统新闻客观性报道规范所要求的“新闻与评论分离”不同,短视频新闻允许甚至促成个人情感与价值的介入。
从叙事框架来看,短视频新闻采用“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情感”架构,将小人物的情感和利益与宏大的国家利益和布局联系在一起。例如在5月20日推送的“有爱的日子不仅是你侬我侬,更是家国平安”中,叙事逻辑将个体婚恋圆满引向疫情下的家国团结。从叙事文本来看,短视频新闻吸纳非正式语汇与网络热词,实现语言上的亲近性。例如报道北京新发地疫情的视频名称为“热干面挺过来了,炸酱面也会好起来的”,在报道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时将其描述为“胖五”“刷了个大火箭”“V5”。
(二)媒体人格化:从媒体品牌到个人品牌
广电媒体在视频制作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但其源媒体特征仍然突出,新闻短视频中主持人的存在感也仍然较强⑤。《新闻联播》长期以来作为政治性仪式存在,主播作为节目的发声者也被附着了浓厚的符号色彩。央视主播在外形(视觉符号)和声音(听觉符号)的塑造上力求纯正完美,但随着传统媒体改革和短视频新闻实践深化,作为“门面”的央视主播开始走下神坛,从精英化、去情绪化、去个性化的静态形象转变为网红化的、可接近的、人性化的动态形象,从“声音传递者”变成了“声音发出者”⑥。
《主播说联播》栏目从立意上就凸显了主播的个人价值判断,将受众感知的“发声者”从宏观的国家体制缩小到具体讲话者,从最直观的标题设置上突出主播的发声者姿态,如“康辉为美国某些议员补课”。在短视频中,央视主播从语言符号到非语言符号都突破了程式化限制。在语言符号上,口语化叙事、情绪化表达和网络词汇得到大量使用;在非语言符号上,主播拥有丰富的肢体语言,如点赞、摊手、摇头等动作,随着具体新闻内容的变化,主播的声调与情感也会相应改变。通过这种形式,受众在观看过程中仿佛置身对话环境,主播所传达的国家意识形态则被看作讲话者的个人化观点。
在接近性上,央视主播的曝光也不再囿于新闻节目。2019年11月推出的“康辉Vlog”集中体现了央视对个人品牌的打造,在评论中有网友戏称“第一次看到康辉腰部以下”并获得了四万多的点赞,排在第一位,这充分说明了此前央视主播印象塑造的刻板化与模式化。在破除符号化形象之外,央视新闻还借用了饭圈话语,将康辉与朱广权、撒贝宁等人气主持人称为“央视Boys”,塑造社交媒体上的“网红”主播。通过这种形式,媒体被赋予了人格化的特点,拟人化的传播促进了传受关系的平等,央视主播、外交部发言人等个体元素共同构成了媒体的性格特质。这是央视新闻亲近性转向的重要一步,也是媒体品牌向个人品牌转变的过程。
(三)后台透明化:从中心到边缘
电子媒介融合了不同的媒介场景,为了解释场景融合后交往行为的折衷风格,在“前台”“后台”的概念基础上,梅罗维茨将场景混合之后在新场景中产生的新行为称为“侧台/中区行为”⑦。
从2019年底“康辉Vlog”推出以来,央视新闻已经将Vlog作为常规化的短视频新闻报道形式,在后续的两会报道、疫情报道里都广泛采用。目前央视新闻的Vlog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新闻工作人员记录自己的日常工作,表现了生产后台的透明化;另一种是记者探访采访对象的日常生活,体现了内容后台的透明化。对新闻内容后台的揭露强化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对中心议题的侧重是由重要性和显著性决定的,但相比于宏观的新闻价值,具有接近性的边缘议题往往更加接近生活,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四)平台接近性:从媒体中心到受众中心
短视频形态本身具有很强的平台依附性,B站作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社群,从符号意义上来讲与主流文化相对。官方媒体入驻B站,不仅完成了对青年亚文化的收编,也实现了官方媒体的形象重塑。由于短视频的平台依附性,B站的平台属性、社区文化构建了央视新闻短视频新闻创作的底层逻辑。B站的社交媒体平台定位及其独特的弹幕文化确定了平台视频的社交属性,这就决定了央视新闻短视频更多是以平等的对话姿态呈现,并且具有一定的互动性。从社区文化来看,B站具有显著的青年亚文化属性,央视新闻也进行了迎合,例如嘻哈文化视频“朱广权新rap央视新闻来B站了”。
B站的文化与规则是用户和受众在长期的亚文化实践中形成的,央视新闻对B站的依附实际上是对受众习惯与喜好的接近与迎合。此外,主流媒体对亚文化社群的收编行为本身就是亲近性转向中的关键一环。从引导公众接收主流话语、接受官方媒体,到主动迎合网络话语、接触网络文化和社区,央视新闻通过平台的接近实现了由媒介中心到受众中心的转向。
二、官方媒体时政新闻亲近性转向的效果
如果从国家意识形态领导的要求来看,官方媒体时政新闻的亲近性转向无疑是成功的。首先,入驻视频和亚文化平台的行为本身就代表着亲近性转向,有助于扩大受众范围;其次,短视频与文字相比是一种无门槛的阅读方式,将时政新闻以可视化、流行化的形式推送则降低了阅读和理解门槛,激发了公众对严肃时政新闻的兴趣;最后,虽然这种亲近性本质上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的一种体现,是官方话语向民间话语做出的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是央视新闻在B站400多万的粉丝数量证明其传播效果的成功。不过这种亲近性转向也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一)严肃议题娱乐化与碎片化
短视频的时长限制、移动观看的媒介特质决定了传播形式的轻松化和娱乐化。央视新闻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要新闻播送窗口,时政新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央视新闻的适应性调整易造成严肃议题的娱乐化与碎片化。这种片段式、碎片化的时政新闻无法帮助公众深入了解事情全貌,最后只能浅尝辄止、浮于表面。
(二)亲近性无法完全替代公信力
公信力是媒体通过长期新闻传播实践与受众和社会建立起的信任关系,媒体的公信力应当来自于其生产的新闻产品。在亲近性路线下,受众不再关心新闻的内容,而是关注媒体以何种形式进行呈现。媒体对受众阅听心理的迎合无法从根本上获得公众信任与媒体公信力,只能获取暂时的、情绪化的反向接近。此外,央视新闻的短视频中出现了大量带有强烈倾向性、观点性的内容,这反而会对公信力造成削弱。
(三)迎合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加剧意识形态极化
近年来,文化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极化呈现加剧趋势,在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和官方宣传的“大国崛起”叙事下,网络空间面临进一步撕裂的风险。“大国崛起”叙事是当下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导框架,它迎合了民族主义者的想象与偏好。央视新闻短视频中存在大量以“大国崛起”为母题框架的内容,虽然这是由国家整体宣传话语和其官方主流媒体定位决定的,但短视频因为时间限制只能呈现部分事实,大部分新闻背景都被省略,只保留了事件冲突或高潮。“听说你们爱看‘外交天团’?赵立坚40秒高能限定”等视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视频只剪辑了外交部发言人的强硬回击合集,但没有针对具体事件,也没有交代发言背景。这类短视频共同形成了官方话语的“爽”文化,迎合了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助长了网络空间“后真相”风气。
注释:
①龙强,李艳红.从宣传到霸权:社交媒体时代“新党媒”的传播模式[J].国际新闻界,2017(02):52-65.
②吴飞,卢艳.“亲近性新闻”:公民化转型中的新闻理论与实践[J].新闻记者,2007(11):52-55.
③易艳刚.“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标准之变——以“罗尔事件”为例[J].青年记者,2017(04):17-19.
④杨保军.创制亲近性文本:跨文化有效传播的重要基础[J].国际新闻界,2001(06):59-63.
⑤殷乐,高慧敏.传统媒体新闻短视频发展现状与传播态势[J].当代传播,2018(06):45-50.
⑥周勇,黄雅兰.《新闻联播》:从信息媒介到政治仪式的回归[J].国际新闻界,2015(11):105-124.
⑦刘娜,梁潇.媒介环境学视阈下Vlog的行为呈现与社会互动新思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11):4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