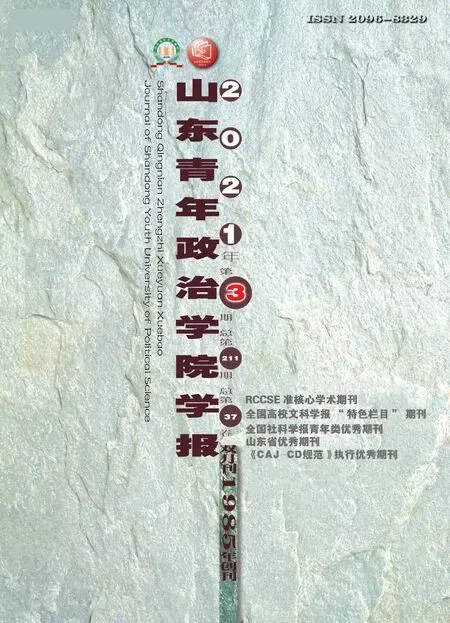毛姆《月亮与六便士》生命意识的叙事呈现
李 磊,楚金波
(佳木斯大学 文学院, 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月亮与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ence)是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发表于1919年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相对于以往的作品,这部小说在叙事方式和结构模式上具有重要变化,并呈现出现代主义的叙事特征。在此基础上,毛姆从不同角度对生命意识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以尝试回答人为何存在及如何存在的问题。生命意识在文学创作与鉴赏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者们也对其进行相应的阐释。杨守森认为:“生命意识,是具有了意识活动能力的人类,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1]詹福瑞认为:“生命意识不同于生命哲学或生死哲学,它是人对生命的感性认识,具体说,就是对于生命的感受、体验与感悟。”[2]在这部作品中,毛姆通过多重视角及多维空间的叙事手法展示了主人公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下文简称“查尔斯”)“非理性”的生命意识,即超脱人云亦云、枯燥乏味的生活,并在不甘平庸生命理念的指引下,勇于追逐理想的人生,而这也有助于当代人重新审视其生命意识,以探寻更有意义的人生。
一、多重视角下图绘生命意识的外在轮廓
毛姆通过故事中的“我”串联了故事线索,并将人物线、地点线和时间线编织成一个网络体系,以勾勒整个故事图景。作为整个故事的牵引者,“我”以伦敦、巴黎和塔希提岛为中心,“将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与特定的情境相关联”[3],并在多重视角下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在主人公与众人生命意识的碰撞中,在宏观层面图绘了众多生命意识的外在轮廓。
在伦敦,“我”主要通过萝丝·沃特佛(一位女作家)、艾美(主人公的妻子)和麦克安德鲁上校(艾美的姐夫)等人的视角呈现查尔斯的社交及家庭形象。但毛姆以外聚焦的视角限制了叙述者的权力,即“叙述者只能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4]因此,叙述者在都市男女对查尔斯“主观且片面”的描述中,勾勒了查尔斯生命意识的外在轮廓,进而展现了人们之间虚假、伪善的关系。查尔斯出走前,在萝丝·沃特佛眼中,“查尔斯在城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好像是股票经纪人。他这个人很无趣。他话很少,对文学和艺术一点兴趣都没有。艾美也认为查尔斯无趣且不文艺,但在她的言辞中并未包含贬义且还透露着很深的感情。”[5]宴会上的人们认为查尔斯“无聊且不文艺”,之所以如此,只因查尔斯没有像大家一样侃侃而谈以显示其“博学多识”。显然,这一看法反衬出宴会上男女宾客的虚伪做作,宴会俨然成为他们彰显身份、炫耀学识、展现优越感的“舞台”,而宴会上的种种也成为当时伦敦社会环境的缩影。查尔斯出走后,“我”是在众人推测式的言语中得知查尔斯抛妻弃子,放弃美好生活的“原因”的。沃特佛“本能”地将查尔斯与茶馆年轻女孩的出走两件事关联在一起,捏造了一场在当时伦敦见怪不怪的私奔“丑闻”,并在其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同样,艾美与麦克安德鲁上校也都认定查尔斯与人私奔。人们臆想了一个“无聊且不文艺”“冷漠”“道德败坏”的查尔斯形象,这表现了城市环境中人与人间信任感的缺乏,且善于猜忌、怀疑。此外,毛姆以“我”的口吻道出主人公“美满”生活本身的矛盾性。正如“我”在文中所言:
无数的夫妻一定都是这样度过一生,而这样的人生模式有其朴实之美……但我在这样大多数人度过的人生中,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我知道这种人生的社会价值。我了解这种井然有序的幸福所在,但我血液里有一股放浪不羁的狂热。这种轻松简单的快乐,对我来说似乎含有某种令人心惊的特质。我心中有着向往冒险的欲望。如果能有所改变——改变与前方那为之的刺激,对于尖锐崎岖的礁岩与危机四伏的浅滩,我并非丝毫没有准备。[6]
显然,查尔斯的出走与理想与现实、个体与家庭间的矛盾有关。对主人公或毛姆来说,他的出走是偏重于理想化的精神追求,这是一种追求“至善至美”的生命意识,与此相反,则是伦敦中上层社会所维系世俗化的物质追求,这是一种倡导“及时行乐”的生命意识。这两种生命意识虽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们之间,或是对于人本身来说是一个不断平衡的持续过程。此外,查尔斯与毛姆也看到了个体与家庭之间存在的矛盾。按世俗观点,人们应该以某种相对保险的方式循规蹈矩的生活,毛姆也看到了这种人生模式的“朴实之美”及“社会价值”。同样,他也意识到人有另一种充满不确定性、近乎丛林探险、艰难无比且少有人涉足的人生路。可见,查尔斯选择了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路,而这就区别于侧重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的生命意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意识究竟是不可调和,还是能够和谐共处,这需要不同的个体去探索。
在巴黎,毛姆仍以外聚焦的视角来展示人物的动态,并在“我”的观察下进一步凸显人们眼中的查尔斯,进而呈现多元化的生命意识。首先,“我”受艾美之托到巴黎寻找查尔斯,并发现他不顾一切地抛妻弃子以及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就为了实现儿时的梦想——画画,而支撑着他走下去的是一股无形又强烈的力量,而不是人们口中的物欲驱使。其次,感知到这种“力量”的是德克·史特洛夫,一个籍籍无名的画家,却有极高的艺术鉴赏才能。在德克看来,查尔斯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并说到:“美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美奇妙而不可思议,是艺术家的灵魂受尽折磨,从那混沌的世界里一手打造出来的。而他创造出来时,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你必须走过艺术家奋斗的历程,才认得出它来。”[7]最后是布兰琪·史特洛夫,一个被这种“力量”伤害的女子,在布兰琪看来,查尔斯是一个“混账没礼貌”且不知感恩的人。令人诧异的是,布兰琪竟对查尔斯萌生了爱情,并在被冷落后自杀。毛姆通过“我”、德克和布兰琪等人塑造了查尔斯的巴黎形象:“我”认为他是抛妻弃子且冷漠、不知感恩的男人;德克觉得他是创造美的艺术天才;他是布兰琪又爱又恨的恋人。毛姆以这三个视角结构这一部分有其独特用意:“我”是伦敦家庭线的延伸,德克是艺术线索的发端,布兰琪则是爱情或家庭线索的展开。相比于伦敦环境中的人物视角,毛姆在巴黎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展示了人们眼中的主人公形象,“我”、德克和布兰琪都对其予以最大的包容,或者说,这里的人们更希望主人公成为他们眼中的查尔斯,即他是一位合格的现代都市人,并在符合时代风气和社会规范的情况下过着他们眼中差不多的“美好生活”。查尔斯对这种“美好生活”却有极其抗拒的心理,而这背后隐藏着毛姆对天才与庸才、人与本能欲望矛盾性的探讨,这也是毛姆从宏观层面理解生命意识的尝试。查尔斯对德克种种不礼貌的言行,实则是天才与庸才间的矛盾,而其中也掺杂着理想与现实、经典与非经典的矛盾。查尔斯是天才的化身,但是他的艺术超越了所处时代人们能够理解的范畴,在不被认可的情况下,天才又不得不面临现实生活中“柴米油盐”的困扰,是坚守还是放弃,背后是由或理想或平庸的生命意识所影响的。德克则是庸才的化身,查尔斯对其画作不屑一顾,这种画“全都虚有其表、缺乏诚意而且粗制滥造”。[8]然而,德克的画却大受欢迎,而查尔斯的画却在当时处于滞销的状态,这又与查尔斯成名后画作畅销形成鲜明对比。这就牵涉到经典与非经典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既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宏观因素有关,又与主流与非主流、个人化与非个人化、自由与非自由等微观因素有关。而这因素显然更多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这需要借助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上述问题。布兰琪的形象显然有个体与家庭矛盾的成分,但毛姆笔下的布兰琪是欲望的化身,其中潜藏的是理性与本能欲望间的矛盾,而这欲望却以各种样态与人纠缠,它或是被动的,或是相对和谐的,或是主动的状态。人无法绕开它,但又不得不克制它。可见,对于毛姆及查尔斯,曾经的艺术殿堂——巴黎也被充斥着物欲的生命意识所环绕,显然,这并不是他们要驻足的地方。
在塔希提岛,“我”是在尼克斯船长、柯恩、提亚蕾、布鲁诺船长和库特拉斯医生等人的只言片语中大致勾勒了查尔斯余生的画面。尼克斯船长是查尔斯离开巴黎、去往塔希提岛前的见证人。在尼克斯船长的描述中,查尔斯与其在马赛共度过了四个月左右风餐露宿、食不果腹的患难生活。查尔斯离开马赛就来到了塔希提岛,他第一份工作是商人柯恩给的,柯恩出于对艺术家的同情对其工作要求不高,他也有足够的时间画画。在柯恩的回忆中,“查尔斯只待了几个月。他赚够了买颜料和画布的钱之后就离开了。那时候他已经被这地方给擒获了,他只想遁入丛林中。不过他偶尔还是会见到他。他每几个月就会现身帕皮提,待上一阵子;他会从别人身上搞到钱,然后就消失不见。”[9]柯恩因借给查尔斯两百法郎而获赠一幅画,对这幅画作“柯恩根本摸不着头脑。他这辈子也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这距离那画卖出三万法郎已过去很多年。”[10]在浮花旅店店主提亚蕾的描述中,她时常接济查尔斯,并为其介绍了在塔希提岛上的妻子爱塔,而“我”在与其的交谈中也了解到查尔斯初到塔希提岛的内心活动:“我抬起头来,看见岛的轮廓。那一刹那我便知道,那是我寻寻觅觅一辈子的地方。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我似乎认得这个地方。有时侯我四处闲晃,到处都感觉很熟悉。我敢发誓我曾经住过这里。”[11]查尔斯去世后不久,“他十几张未裱框的画作大多以五六块法郎、少许顶多以十块法郎被卖掉。”[12]在布鲁诺船长的描述中,查尔斯“不问世事也被世界遗忘,在他住所的阳台上躺卧着三四名本地人……一名年约十五岁的女孩在编织漏兜树叶做帽子,一名上了年纪的女子屁股着地抽着烟斗。爱塔正在喂刚出生的婴孩喝奶,脚边有另外一个全身赤条条的孩子在玩耍。查尔斯也与本地人一样,身上只围了一块花布,他很开心地邀请布鲁诺船长进屋,他已经彻彻底底成为本地人了。”[13]在库特拉斯医生描述中,查尔斯身患麻风病,他对此表现的很平静,除了专注于绘画之外,查尔斯还会关心身边人,并赠予医生一幅画以表达其带来“重要消息”的谢意。大约是三年后,他见到了病危的查尔斯及其旷世奇作。“他不懂绘画,但这些画有种撼动他的特质。墙面从地板到天花板盖满奇异而精妙的构图。其美妙和神秘难以形容。他为之屏息。心里溢满他自己也不了解、无法分析的情绪。他感受到一个人目睹世界诞生时的那种敬畏和喜悦。气势宏大、感官敏锐、热情奔放,然而其中也带着一种可怕,令他感到恐惧的元素……”[14]相比于伦敦和巴黎城市环境中人们臆想及希望查尔斯成为或扮演某种社会角色,在毛姆看来,塔希提岛上的人们以真挚的情感和强大的包容心走近独立人格支撑下的查尔斯。虽然他们并未理解查尔斯的艺术及生命画卷,但起码他们做到了彼此信任、理解与认同,即尼克斯与主人公的患难情、柯恩的知遇之情、提亚蕾与布鲁诺的友情、爱塔的真挚且纯洁的爱情以及库特拉斯医生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这些是不掺杂功利心且无比珍贵的情感,区别于工业资本支配下人们相互妒忌、怀疑、压迫等异化状态。这种异化状态可在经济与文化,即消费与文化的裂痕处探究原因。也就是说,当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到消费资本主义阶段,经济与文化貌合神离的状态愈发明显,经济披上文化的外衣,并借助信息传播媒介大肆“招摇逛骗”,催生各种形式的“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消费文化产业,而“消费文化”的本质是以收益为中心,而忽视真正具有人文关怀的文化对人的反哺作用。显然,人在周而复始的劳作及“文化消费”中消磨掉本真的“七情六感”,失去爱人的能力及同理心,成为没有感情的“工具人”“消费机器”。可见,毛姆及查尔斯在经济与文化的裂痕中预先感知到经济发展对文化发展的反噬作用,从而呼唤具有真善美生命意识的复归。
由上可知,毛姆从理想与现实、个体与家庭、天才与庸才、理性与本能欲望及经济与文化等多组矛盾中识别出宏观生命意识的多样态及外在轮廓,在此基础上,毛姆表达他对生命意识的理解,即“去伪存真”“崇尚理性”“呼唤真情”。
二、空间构筑中复刻生命意识的内在肌理
同样,毛姆也通过叙事空间的场景化叙事对各种生命意识进行微观细描,加深了其对生命意识的理解,进一步探寻了人为何存在及如何存在的问题。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毛姆构筑的空间对塑造人物形象及复刻生命意识的内在肌理具有重要作用。正如龙迪勇所说,“空间表征法不仅以公共空间表征某些人物的‘共性’或‘群体性格’,还可从私人空间表征单个人物的‘个性’或‘独特性’。”[15]毛姆不仅借助伦敦、巴黎与塔希提岛等公共空间展示了特定群体性格,他也以私人空间的装饰呈现单个人物的独特性格。值得注意的是,毛姆亦通过人物言行及外貌来烘托空间氛围,进而凸显群体或单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伦敦是查尔斯逃离的现实空间,毛姆以“我”的视角呈现了伦敦中上层社会的空间景象及群体性格,进而展现不同的生命意识。首先,萝丝·沃特佛是文艺人士中的“典范”,“她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她把人生看作是给她写作小说的机会,而一般大众便是她的素材。假如这些芸芸众生对她的才华表示欣赏并不吝赞美,她偶尔会邀请他们来她家做客。他们的缺点在她眼里有如狮子的猎物,并以带着好笑的心情轻蔑视之,不过她会合宜得体地在他们面前扮演知名女作家的角色。”[16]同样,“我”对宴会上男女作家的刻画,亦能展示文艺人士的“共性”特征,即“有关女性,她们常作奇形怪状的打扮、声音轻柔眼神贪婪而锐利……有关男性,他们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作家……并且总是有点疲倦且很不真实。”[17]在毛姆看来,宴会上的文艺人士隐匿真情实感,虽然他们想要表现其“博学”“高贵”“优雅”“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但在其言行中却透漏着虚荣、做作、趾高气扬且颇具优越感的本性。这是毛姆通过人物言行反向烘托出伦敦上层宴会场景“虚假”的艺术氛围,进而凸显宴会上文艺人士善于伪装、精神文化匮乏的生命状态。其次,“我”对主人公家餐厅风格的观察值得深思:“墙上有大片的白色木材护壁板,还有镶着工整黑框的绿色底纸,上头印着惠斯勒的铜版画。直条条挂着的绿色窗帘是孔雀图案,而地毯上有淡色白兔在枝叶茂密的树丛中嬉戏的花样,处处显现出威廉·莫里斯的影响。壁炉台上摆着蓝色的戴夫特陶器当时装潢一样的餐厅,在伦敦特定有五百间之多——风格简朴、雅致而无趣。”[18]从家具色彩来看,白色、黑色、淡色、绿色及蓝色等富有现代轻奢风格的家装色彩显示出房屋主人的前卫意识;从家具装饰品来看,房屋主人将铜版画、地毯图绘和陶器作为装饰物,处处显示其颇具古典气息的“艺术修养”。从餐厅风格来看,趋同化的内部空间也暴露了房屋主人盲目从众的心理。最后,在查尔斯出走之后,“我”对主人公住所的描述颇有意味,即“房间里没有鲜花,夏天时收起来的装饰品也没放出来;以往气氛亲切的会客室,如今有股惨淡拘束的意味。”[19]在这一空间里,既没了鲜花装饰,缺了生机活力,又没了装饰品的装点,缺少了往日房屋现代化和艺术的氛围,反而是尽显“惨淡拘束”。这一压抑和冷清的空间景象既衬托出艾美伤心的情绪,也表现出查尔斯出走打破其“美好生活”假象之后的失落、迷茫与无奈。由上述论述可知,毛姆一方面通过展现以沃特佛为代表的文艺人士的言行,表现了这一群体善于伪装、精神文化匮乏的生命状态,同样也构筑了一个充满谎言、缺乏真情与真正艺术气息的现实空间;另一方面,毛姆对室内环境及装饰的描写反衬了人们生命力匮乏及理想信念缺乏的状态。可见,毛姆通过叙事空间的场景化叙事对伦敦中上层社会世俗化的生命意识进行了细致刻画,这与查尔斯理想化的生命意识形成鲜明对比。
巴黎是查尔斯追逐的艺术空间,毛姆仍以“我”的视角构筑了这一空间景象,并在空间构筑中塑造着人物形象,并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进而凸显查尔斯独特的生命意识。首先是查尔斯初到巴黎的住所,“从外部来看,它是一幢老旧的大楼,并有一种邋遢破烂的气氛,两侧的房子相较之下都显得干净整洁。从内部来看,查尔斯的房间很小,塞满了法国人称之为‘路易·菲利浦’风格的家具……所有东西都肮脏破旧……”[20]由房屋内外部环境可推断出,查尔斯并非人们口中与人私奔,且过着奢华堕落的生活。从塞满“路易·菲利浦”风格家具的房间可知,这是一种流行于19世纪前半期偏复古主义风格的家具样式。但到了20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的兴起,欧洲设计界更偏爱现代风格的家具,相对忽视复古风的家具。也就是说,当时的巴黎存在着古典与现代两种艺术形式。但古典主义风格的绘画在巴黎还占据一定的势力范围,这也就说明查尔斯偏现代化的绘画风格不能立即被巴黎当时的主流艺术圈所认同。其次是查尔斯在巴黎五年后的住所:“这间公寓极小,一半是房间,一半是画室,里头只有一张床、面对墙壁的画布、一座画架、一张桌子,还有一把椅子。地板上没毯子。没有火炉。”[21]如果对查尔斯五年前后的住所条件进行对比,也会对其生活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如住所面积由“很小”变得“极小”,住所陈设由“塞满了”家具到如今的屈指可数,且绘画工具占据了空间的大半面积。由此可知,查尔斯在巴黎的生活更加贫苦,这不仅与其绘画材料开销大有关,同样也与其“冷漠”“无聊”“单纯”甚至“感情用事”的性格有关,而这种性格也决定了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存在人生观与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进而体现在艺术理念上,自然其作品也遭到主流艺术圈的否定。最后是德克·史特洛夫的画室,毛姆以“我”的视角简单介绍了德克的画室,“房间里摆了两张衬垫厚实的扶手椅和一张大长沙发……斯特里克兰德(查尔斯)决计不肯靠近那些椅子……在‘我’看来,他从不认识像查尔斯这样对环境毫不在乎的人。”[22]毛姆对德克画室的呈现不仅是要表现查尔斯不注重物质的侧面,还要表现他极力逃离一切带有世俗情感及复杂人际关系环境的一面。显然,毛姆通过主人公住所空间不仅表现了现代艺术在“传统”艺术之后呈现了新的话语表达,即现代艺术贴合现实语境以及立足于人本真的想法,在形式与内容的双重创新中表现了现代人或消极或积极的全方位情感,它区别于“传统”艺术局限于形式与内容且颇具意识形态性质的表达。更为重要的是,查尔斯及毛姆还在文艺呈现中看到了“人的存在”,而这也是其生命意识最核心的部分,即人应挣脱现实与理想、新与旧、物质与精神等矛盾的束缚,在立足于个体生命最本真需求的基础上,从珍视生命、注重生命体验及精神世界构建的角度去寻找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塔希提岛是查尔斯的理想空间,其中包含着生存和艺术空间,而这两种空间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并与城市的喧嚣拉开距离,最终践行着其淡泊宁静的人生旨趣。毛姆仍以“我”的视角构筑了塔希提空间。首先是对塔希提全景式的俯瞰:“这是一座高耸的碧绿岛屿,地表层层叠叠的深色绿意,可以想见岛中蕴藏的寂静山谷;在其沉郁的深邃里有种神秘,潺潺流泻着沁凉的溪水,在那些荫蔽之处的生命自亘古以来便依照着远昔之道生生不息。”[23]此处散文式的景物描写,将自然的“静”与生命的“动”完美结合,从而将涌动着“神秘”力量的塔希提以颇具意境的“山水画”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也是查尔斯重获新生的神秘力量,它区别于伦敦和巴黎等环境中所形成的压抑并禁锢着人的力量,它更纯粹、更自由、更充满活力与温情。其次是查尔斯的住所,“这是一座未上漆的木材搭成的小屋,里头有两个小房间,外面有一个充当厨房的小屋。屋里除了权充床铺的垫子外别无家具,此外就是门廊上的一把摇椅了。”[24]相较于查尔斯伦敦和巴黎的住所来说,这是一座极其简陋与狭小的屋舍,但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我”不仅以一个“小”字展示其空间,还以“一”为数量单位展现其极简的居住环境,这些都延续了查尔斯不注重“环境”的一贯作风。在这里,他不仅会画画、读书,还会去捕鱼、抓龙虾、去溪里沐浴,甚至参加邻居们的宴会。可见,查尔斯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他不再被都市宴会的“繁文缛节”所扰,在这里他是自由的、真实的和充满温度的人。正如“我”听布鲁诺船长所感叹的那样,“我真希望能让你亲眼看见那地方的魅力,那是个遗世独立的角落,抬头是一片蓝天,身旁是葱郁茂密的树林,有如色彩的飨宴。而且芬芳馥郁,气候凉爽。言语无法形容那海角乐园的美妙。他就住在那个地方,不问世事也被世界遗忘。我猜在欧洲人的眼里,那里一定看似邋遢不堪。房屋残破也不甚干净。”[25]此处,在“我”的知觉体验下,塔希提的自然风光给人以疗愈的功效,它使人忘却追名逐利的现实世界,尽享大自然给予的视听盛宴。最后是布鲁诺船长记忆中的塔希提夜景透露着这个岛屿的与世无争:“我(布鲁诺船长)无法形容那夜里的寂静有多强烈。我在波摩图斯的岛上,夜里不曾有过如同这里的万籁俱寂……但在这里却无声无息,空气中夜里的白花暗香浮动。那一夜美得叫灵魂难以承受肉体的牢笼。感觉灵魂仿佛就要随着虚空婆娑而去,死亡的面容竟如挚友般可亲。”[26]可见,塔希提静谧的夜竟有种使人置身于忘“我”境地的力量,它已然使人超越生与死,从而站在更宽阔的视角去审视世间万物。也正是有此开阔的心态,人才能返璞归真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查尔斯及毛姆来说,塔希提的“静”唤醒了潜藏在生命意识深处的“动”,这种“动”不是都市环境中充斥着消费物欲的“冲动”,它也不是一战后创伤未平的“躁动”,而是富有生命能量的“动”。显然,毛姆与查尔斯将生命能量熔铸在富有生命张力的文艺表达上,而这生命张力一方面在平衡人与自身、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也在驱除人们生命意识中腐朽、麻木且死气沉沉的部分,以重新唤起富含生命力、充满希望及可能性的部分。这种生命能量是生命意识的滋补剂,它有助于人追寻富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
由上可知,毛姆通过叙事空间的场景化叙事对各种生命意识进行微观细描,他既看到了伦敦空间中精神文化匮乏的生命意识,还察觉到“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因话语体系革新所诞生的新生命意识萌芽,也探寻到塔希提空间富含生命能量的生命意识。显然,毛姆推崇的是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富含生命张力的生命意识。毛姆对生命意识的理解,也为当代人思索生命意识为何与何为的问题提供思路。
三、余论:生命意识的为何与何为?
毛姆展示了多样化的生命意识,在不同视角和空间构筑下将内在的意识外化,并通过人物、事件、场景等单一因素或综合体呈现出特定生命意识的本质特征,进而凸显特定生命意识指导下的生存模式,即有人执着于名与利、有人憧憬小富即安且现世安稳、又有人甘愿在坎途中寻找心之所向的身体和心灵的栖息地等等。人在现实生活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易潜移默化地接受机械化、程式化及固定化的生活模式,而这类模式是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造就的,能够对人的言行及思想产生影响,尤其是资本极度膨胀之时对人的生命意识具有很强的塑造性。这类生命意识面临着空洞感和虚无感的危险,而这又会波及到人的多重社会关系。正如徐葆耕先生所说:“20世纪以来,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西方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中的全面异化和心灵畸变有更加深入的广泛的揭示。西方人的孤独感、灾难感、陌生感、无聊感得到更加细致入微的表现。”[27]可见,毛姆在其时代背景下,他不仅要展示形态各异的生命意识来呈现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观,还要在这些观念的差异性和变异性中思索生命意识样态、形成路径及影响后果等为何的问题。但毛姆并非只在生命意识为何这一问题上止步,而是在此基础上探索了生命意识何为的问题,即寻找适合的生存之道,并找寻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毛姆笔下的“月亮”与“六便士”分别寓意梦想与世俗生活,然而,在怎样的生命意识指导下的人生才算是理想的、有价值的,显然,毛姆并未直接给出答案。但毛姆在生命意识的表达上,显示了其理想性及矛盾性:毛姆一方面屏蔽了查尔斯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国家等现实关系中的责任,凸显了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另一方面也无法规避现实对理想的冲击,进而在理想与现实间产生矛盾性。而这矛盾性又与“自由”与“不自由”这一二律背反的问题相关,显然,这一问题与康德、黑格尔的“自由观”不无联系,理清他们在自由问题上的关系,有助于分析毛姆生命意识“何为”的问题。
毛姆生命意识观与康德自由观中的“先验性”构成了各自观念的理想性。尽管毛姆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城市环境中人们缺乏生命力的生命意识进行了批判,并在理想空间中找到符合其人生诉求的生命意识,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富含理想色彩、个别的、理论上、先验性的生命意识(或自由观)。而康德自由观也是预设了“先验的自由”(die transzendentale Freiheit),通过实践层面的“自由意志”(der freie Wille),即“不受感性的干扰而逻辑上一贯地使用理性,使理性本身具有了超越一切感性欲求之上的尊严,以获得真正一贯的、永恒的自由。”[28]也就是说,康德对“永恒自由”的追寻显示了其理想化的成分,而在这理想化中也能让人看到其对“真正一贯的、永恒的自由”的苛求。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言:“康德对自由的‘消极’意义的理解是就其局限于‘应当’而排除一切感性的前因后果的考虑这一点而言的。这种理解本身也有两方面:其一,在原因上它不受自然必然性所决定、所束缚;其二,在结果上它不在乎现实的后果是否是它所想要的,即它不掌控现实的后果。”[29]显然,毛姆生命意识的“理想化”与康德自由观中的“永恒”具有同构性,二者都是在先验性假设的基础上,追求着“不计现实后果”的生命状态。这一状态有其合理性,即人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被束缚,想要在对的时间及空间中将自身价值最大化,以获得理想化的生命状态或是“一贯的永恒的自由”。但其不合理之处在于过于理想化及绝对化,而忽视了现实的诸多因素。这只是一种假想的、理论上的生命意识或自由,它无法通过自身规避掉理想与现实间的种种矛盾,因而缺乏现实实践性。
黑格尔对康德自由观的改进,缓和了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性,这也有助于解答毛姆“生命意识何为问题”。黑格尔自由观规避了康德自由观中“不计现实后果”的问题,即“他不仅使自由观念本身具有了逻辑层次,还使自由观经过了历史主义的根本改造。”[30]黑格尔的自由观经过“历史”的“洗礼”,展示出了强大的现实适应力。也就是说,自由或不自由,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背景,甚至不同年龄、性别对于自由的理解不同,这也就决定“自由”是相对的,而不能绝对化、永恒化。正如邓晓芒所言:“真正的自由就是由人的现实的激情所推动的历史的必然运动,在这种历史运动中,任意性必将上升为自律,而必然性则不再是外在的机械必然性,而是自由本身的一个现实环节,自由也不再只是内在的一种抽象观念或主观消极的不受束缚、不动心,而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客观现实行动,它所体现的就是历史理性 。”[31]可见,黑格尔自由观贴合了“现实历史性”,这样就扩大了自由的适用范围,显示了其应用价值。虽然毛姆也曾赋予其生命意识“先验性”(或理想性)的意味,但这是其在处理城市空间中人与城、人与人之间矛盾时所采取的“消极”、现实性不足的做法,然而也具有“破而后立”的意味。显然,毛姆也试图解决生命意识过于“理想化”及现实性不足的问题,并在塔希提空间中找到了“生命意识何为”的答案,即毛姆将生命意识放置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来理解,并综合现实及历史诸多因素对不同生命意识作宏观层面及微观层面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他既承认生命意识的多样态性,在一种“去伪存真”“感性与理性结合”“呼唤真情”的现实氛围中追求以人为核心的富含生命张力的生命意识,而又反对僵化、模式化状态下只注重物欲追求、精神文化匮乏的生命意识。可见,毛姆生命意识显示了其强大的包容心,这对于当代人的存在与发展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