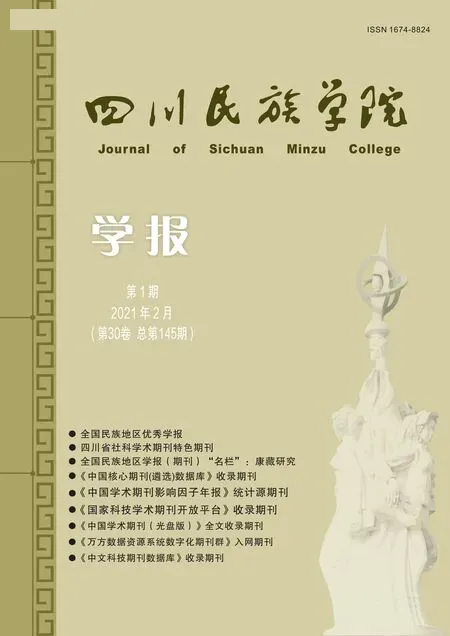阿来作品的生态审美三维透视
余忠淑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生态审美是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以生态意识为引领,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渗透、依存为研究视角进行的审美活动。生态审美摈弃了人与世界对立的“主客二分”认识,主张主体间性,形成人与世界交融的审美模式。生态审美强调“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主张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兼顾。生态美学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在《沙乡年鉴》中提出保护生态的美学思想,开启了生态美学的理论前奏。加拿大学者约瑟夫·米克(Joseph W.Meeker)在《生态美学构想》一文中首次提出生态美学概念,提出了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的主张,开启了世界美学界的生态美学潮流。我国学者对生态审美学也进行了思考,徐恒醇在《生态美学》中认为,生态审美是一种将生态理念作为价值取向的审美意识,“不是主体情感的外化或投射,而是审美主体的心灵与审美对象生命价值的融合。”[1]盖光在《论生态审美体验》中认为生态审美强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共存、共生、共荣”的包容性关系[2]。反映人类生产生活的文学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给予高度关注,并注重创作中的生态审美的体现。美国生态文学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其1962年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中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成为生态文学产生的标志。
法国生态哲学家加塔利(Flix Guattari)在其《三重生态学》一书中提出了医治环境问题的“三重生态”理论,构建起了“自然-社会-精神”三维合一的生态审美模式:自然生态维度打破“主客二分”的传统美感模式,构建人与自然统一模式,彰显自然生命进程和生态公平;社会生态维度下推进人类社会关系因差异性和多样性而走向“和而不同”的局面,重建人类社会和谐与公正;精神生态维度在多元价值逻辑下重塑精神价值体系并趋向艺术化生存。三重生态维度相互作用,使外在生存环境和内在生命本体智慧通达,和谐统一,实现人类生态的美学救赎[3]。三重生态的审美思想引发了生态文学创作者与文学评论者的共鸣。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生态文学常常体现了三重生态:以自然界为描写对象,主张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以人类社会中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等为主要描述对象,主张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生态;以人的内在情感、精神生活为刻画对象,主张实现精神价值维护、重塑的精神生态。“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自身的关系,”[4]三重生态和谐统一,实现人类生态整体发展。三重生态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内在机理。社会生态学创始人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在《自由的生态学》中指出:“无论你喜欢与否,几乎所有的生态议题都同时是一个社会议题……差不多所有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失衡问题都有着社会失衡的渊源。”[5]生态文学作品毫无疑问反映了社会生态问题与人类生态危机的关联性,正是人类社会问题导致了对自然的破坏。实际上,精神生态对所有的生态危机的形成具有本质的影响。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强调正是人类的精神危机才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从而提出生态审美中精神生态性的问题。他认为人类的精神是世界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变量,是客观存在的一心向着完善、完美、亲近、和协的意绪和能动理性。生态文学中也常常体现了人类精神生态的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具有的本质影响作用。
曾繁仁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中认为生态美学应“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关系,最后落脚到改善人类当下的非美的存在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存在状态。”[6]这实际道出了生态文学倡导的三维合一的生态审美意蕴:自然生态要维持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社会生态要实现人与人融合共生的关系,而精神生态要实现精神家园守望,从而实现自然、社会和精神和谐相融的生态审美状态。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关系,所要试图建立和实现的主要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生态文学作品常常从自然、社会和精神三重维度进行审美书写,着力于促进人与自然生态的良性发展,期望创建人类美好家园的生态图景。
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中的藏民族尤其重视生态,藏族文学自然少不了对生态的关注。阿来是具有代表性的著名藏族作家,在创作的《空山》《大地的阶梯》《蘑菇圈》等大量作品中高度关注生态。本文从生态审美视角透视阿来作品中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的书写与反思带来的启示,将利于人类和谐生态的构建。
一、阿来作品的自然生态审美
阿来出生在青藏高原以东群山层叠的峡谷之中,一直生活到36岁时才离开。在阿来看来自己就是一个自然之子,对藏地的山水草木倍感熟悉和亲切,其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在其文学作品中,必然要对藏地美丽的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书写,为自然山水赋予生命,人化自然,呈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性。在《大地的阶梯》中他谈及嘉木莫尔多山是战神的化身,人们对其顶礼膜拜获得勇气和智慧。《天火》中描写了有一个冰冻的色嫫措,一对金野鸭飞来,引来阳光后坚冰融化,四周变得温暖湿润,森林变得茂密,鸟兽得以生长,人类繁衍兴旺。机村的村民都认为是金野鸭保佑了他们风调雨顺,粮草丰饶,于是主动维护着色嫫措湖优美宜人的自然风光。阿来认为人与自然互为环境,自然赋予了人生产生活的环境,人类应倍加呵护自然,改善自然环境。正如阿来所说:“我突然觉悟,觉得自己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还应该有人的环境——不只是人与人互为环境,还有动物们植物们构成的那个自然环境,它们也与人互为环境。”[7]在《狩猎》中他写道,猎人在营地发现了哺乳的獐子,却放弃了获取麝香的机会,“没听说过哪个真正的猎手要杀喂奶的东西。”[8]放走了母獐和小獐子是不滥杀生灵的狩猎规则。在《天火》中他谈道,人们有规律地砍伐木柴烧火做饭,在维持生存的同时也保护了森林。巫师多吉用传统的方式烧毁草场上多余灌木,让下年牧草长得更丰盛,喂养更多的牛羊,维持草原特有的生态平衡。庄子认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9]阿来在天地自然之美书写中充满着深沉的理性认知与真情感悟,透射出天地万物的演变与发展之道。阿来对自然审美的体悟是通透清澈的,是温和亲近的,在自然描写中感悟人生的道理,在与自然沟通中唤醒着人与自然原初的天人合一的记忆。
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人类中心主义盛行,对自然进行了贪婪的索取,自然环境遭到了无情的摧残。在人类的眼中,自然成了征服的对象,对此阿来表达了深深的隐忧。在《遥远的温泉》中,他说这里有像梦幻般的措娜“神泉”,这里碧波涟涟,绿草连绵,鸟鸣婉转,优美的环境给人们带来神秘美好的幻想和诗意般的生活。温泉还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贡波斯甲就用温泉治好了脸上的皮肤病。但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幌子下,人们在措娜温泉上粗暴地修建了现代建筑,美丽的温泉变成了污浊不堪的臭水池。小说中还写到,为了获得大量电力,增加财政收入,人们在机村附近大肆开发水电站,破坏了河流及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美丽的自然风光消失,村子被淹没,许多动物也失去了生命或家园。在《随风飘散》中他谈道,为了修建万岁宫之类的建筑,机村人精心挑选挺拔的白桦树,大肆砍伐,一车车拉出,让茂密森林面目全非,令人嘘唏。砍伐并未结束,人们继续砍伐树林深处的红桦树,并从高山密林中滚落下来,对森林形成碾压破坏。在大肆砍伐下美丽的森林渐渐消失,留下的只是满山疮痍,也给村子带来了泥石流,导致村庄的毁灭和生命的死亡。在《已经消失的森林》中描写了在森林砍伐下,村子四周的山峦变光秃了,裸露的灰黄岩石在泥石流冲刷下泛出格外显眼的痕迹,茂密的森林和众多溪流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故乡童话般的色彩不复存在,动物也受到了伤害。《达戈与达瑟》中描述道,麦田收获了,猴群会在田间捡丢落的麦穗,过去机村人认为将麦穗留给猴群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为了卖毛皮和骨肉获得暴利,人们举起了猎枪射杀与村庄有千年和平相处契约的猴群,将其剥皮剔骨。人们砍伐森林,捕杀动物,也没有放过大地中金子之类的东西。在《金子》中他谈及人们开始淘金后,山坡上森林砍伐殆尽,泥石流频发,河水变得浑浊;村庄被毁坏,人们被迫迁徙;庄稼被淹没,长满了杂草;镇子的城墙也变得破烂不堪,人类在贪欲下摧毁了自己的家园。
传统的自然审美是人作为主体对自然环境客体的主观表象,将客体对主体的取悦程度作为美与丑的判断,属于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阿来作品中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审美,认为将其他自然生命当作工具,将人类作为唯一有价值的生命存在是荒谬的。阿来痛惜环境的破坏,呼吁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整体主义不单将人类的利益,更是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护整体生态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作为衡量人类活动标准[10]。生态审美认为人的生命和自然的其他生命一样平等存在,存在的生命都需要家园,而自然环境就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栖居的家园,人不过是家园的栖居者。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共生、共荣美好状态是真正生态审美下的美好状态,是人栖居于自然之中,了解自然、理解自然、关心自然的审美。可见,在对自然的生态审美中,人们不是关注自然的工具形式,而是关心自然的生命存在;不是把自然当作环境对象,而是把自然当作生命的家园;不是把自我当作自然的观光者,而是把自我当作家园的栖居者[11]。阿来在作品中写道,政府开始推进退耕还林,人们开始植树造林,自然生态恢复充满了希望。阿来发出了呐喊,希望全面摈弃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生态整体主义,将自然环境作为人的家园,将人作为栖居者,关爱家园,守望家园,让人与自然形成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二、阿来作品的社会生态审美
社会生态关注人类的政治、经济等活动状况,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的恶化构成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破坏最重要的直接根源。阿来在其作品中对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运动和经济利益驱使下人与人相对淳朴关系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大量书写,对这种变化给人与自然生态失衡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生态审视。
在政治运动下,人们充满了政治热情,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充满了政治元素,人与人充满了政治关系。阿来在《随风飘散》中写道,因为要修建万岁宫,显示出对政治的忠诚,人们打破过去有限砍伐木柴满足烧火做饭的规律,狂热砍伐成片的白桦林,用卡车拉出山谷,整个现场热闹极了,森林最后被砍伐殆尽。在《天火》中他描述道,当大火蔓延,按照传统的方法就应赶紧救火,但在政治运动下,上面下来的救援人员还要开动员会,表面形式工作完成后,失去了最佳扑火时机。机村民兵排长索波是积极要求政治进步的青年,为了获得机村领导人地位,与队长格桑旺堆发生了矛盾,为表现自己,盲目带人扑火,最终大火失去了控制,植被大面积被烧毁。植被破坏后,泥石流频发,水土流失严重,惨重的饥荒降临到机村人头上。在《荒芜》中,机村村支书林驼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强制要求全村大搞积肥运动,结果过度施肥烧死小麦,导致粮食绝收,机村人被迫去觉尔朗峡谷开荒救命,拉开了饥荒岁月的序幕。在《蘑菇圈》中阿来谈及在“人定胜天”号召下为了增产,过度施肥,结果粮食减产,机村人家缺粮后挣扎在死亡线上,社长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上吊自杀,蘑菇等野菜成了大家救命度日的食物。在《遥远的温泉》中描述了贤巴为了政治升迁,积极表现自己,成立旅游局对措娜温泉大肆旅游开发,最终在为了职位的短视行为中让美丽的温泉毁掉了。对过去政治运动或政治决策失误中带来的生态危机,阿来在其作品中充满了深深的忧虑和反思。而在《三只虫草》中,阿来对当下社会问题进行了批评,表达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的愿望。阿来论及政府调研员贡布假借调研虫草及学生逃学情况之名,大肆廉价收购虫草,用以行贿来晋级升迁。文中虫草成为层层升迁的助推工具,刺激了虫草的过度挖掘,加剧了虫草生态圈的破坏。
在经济活动的物质利益驱使下,人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金钱物质关系,严重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阿来在《天火》中写道,当大火燃起来时,机村的人们参与上级部门组织的救火活动,看到大量下发的食物,许多人不去救火,却忙于将食物一罐一罐搬回家。在《金子》中他谈道,为了获得金子,男人抛弃了妻子和女儿,母子反目,女儿堕落,人的亲情荡然无存,人与人充满了仇恨。在《三只虫草》中他谈及政府实施退牧还草政策后,搬到定居点的牧民们没那么多地方放牧,一家人的用钱都指望着短暂的虫草季。于是挖虫草成为人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就连小学生不上学也去挖虫草,大家对虫草的过度挖掘破坏了生态。在《自愿被拐卖的卓玛》中这样描述,在商品经济推动下,人们都忙着把许多东西变成商品卖掉换钱,人们四处走走看看,“林子里什么东西就又可以卖钱了”“砍木头换钱还是犯法的,但是,男人们就喜欢挣这样既作孽又犯法的钱”,卖了钱人们就到镇上喝酒闹事。到镇上卖蕨菜的卓玛也被卖掉了,机村人感兴趣的是她到底把自己卖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卖到什么样的地方去了之类的问题,而对卓玛的安危和生命的尊严没有太多的关心。在《轻雷》中写道,改革开放初期,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许多人头脑里充满了金钱利益观,更秋家的六兄弟买通了木材检查站的人,不断盗伐盗卖木材挣了大钱。拉加泽里看到挣钱机会后,放弃了高考也开始盗卖木材,于是许多人也开始加入盗伐木材的活动中,就连那些最初反对大面积伐木的村民也成了技术娴熟的伐木工,因为砍木头获得的收入远多于庄稼地的收成。阿来哀叹道,祖祖辈辈敬惜树木等生命的宝贵传统不复存在了。树林被砍伐光了,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泥石流频发冲击了村子。
阿来作品中大量的描写反映了社会生态发生了异化,引发了自然生态破坏的问题。阿来感叹道:“每个人的心肠都变硬了,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多了几丝刀锋一样冷冰冰的凶狠。”[12]阿来的内心充满了忧虑,也充满了改变人类行为的期冀。在《空山》中他写道,看到村民肆意盗伐倒卖木材,崔巴噶瓦老人将五彩经幡挂满树枝,虔心祈愿人们能良心发现,改过自新;在《荒芜》中写道,看到伐木工们大肆砍伐森林的行为,协拉顿珠老人默默地拿走了锯子和斧头,他们在用实际行动希望矫正人们的行为。阿来在其作品中还写道,砍伐森林的拉加泽里最后关进了监狱受到了惩罚,受教育后幡然悔悟开始植树恢复生态,与他有过节的秋家老五不再找他复仇,与他和解参加了植树活动,预示着社会向着和谐发展方向转化。政府开始实施退耕还林等政策,人们开始自觉植树造林,人与自然关系在逐渐修复。这些书写体现了阿来内心充满着构建良性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的期盼,充满着推进人与人和谐相处,修复人与自然生态关系,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祈愿。
三、阿来作品的精神生态审美
精神生态关注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反映人与自身的关系,精神生态良性发展对推进自然和社会生态良性发展具有内在本质的作用。丹纳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3]阿来出生并长期生活在藏地,创作中的许多精神文化来源于本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熏陶。阿来说:“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的是从藏族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取营养。”[14]这些文化包含了藏地民族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反映出藏族先民对各种自然现象的朴素认识,蕴含着对自然的热爱和对家乡的赞美,表达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真挚愿望。阿来作品中体现了藏民族精神生态的智慧哲理判断,指出正是精神生态的问题带来了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危机。
人们对政治的敬畏和权本位思想由来已久,政治欲望的刺激让一些人失去了起码的理智。在《遥远的温泉》中阿来写道,贤巴为了得到升迁大搞政绩工程,粗暴地在措娜温泉上修建了大量现代建筑,那曾经与自然天然一体的湖水被冰冷的建筑阻隔,碧草连绵、鸟鸣婉转、波光流转的自然景观消失,美丽的温泉成为遥远的记忆。阿来描写了在曾经的政治运动强力裹挟下,人们的精神生态发生了异化,人们要么充满政治热情,要么茫然不知所措,阿来反思和批判了这种政治运动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在《天火》中他谈道,机村青年索波是一名积极上进的民兵排长,瞧不上谨慎小心的队长格桑旺堆,一心想在运动中表现自己成为机村的领导人,面对大火不听队长的安排,擅自带领机村青年人鲁莽灭火,结果大火烧毁了森林草地。而先进青年央金对炸掉色嫫措湖有所疑惑,但出于对组织的拥护,心头一直缠绕的神秘传说浮现出来时,很快就被组织的思想所取代并积极服从,眼看着色嫫措湖被人们盲目行动破坏掉。[15]在《随风飘散》中他认为,这本是一个破除迷信的年代,所有被破除的东西,什么山妖水魅,鬼神传说,实际又复活了。阿来认为人们过度迷信政治,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敬畏和理性判断,实际进入了另一个迷信圈中,对此他不由唏嘘,感到遗憾与痛心,希望积极推进政治生态文明建设,在理性的生态审美意识浸润下,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注入人们的精神意识中,构建起良性的政治生态观念,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
阿来在《随风飘散》中写道,在新科技浸入的影响以及物质欲刺激下,人们的精神发生了异化,如机村栖息着金野鸭的色嫫措湖过去一直被人们信奉为神湖,如今一些人认为是非科学的封建迷信。新奇先进的物品进入到机村,刺激了人们获取的愿望,人们不惜打破与猴群订立了千年和平相处的契约,向猴群痛下杀手,获取毛皮和骨肉去出售,获得金钱,换取这些物品。正像魔鬼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一般,突然之间,机村的人们好似没了羞耻之心,一些人吃饱了后,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犹豫开始偷窃,将食品、半导体收音机、斧头、手锯、锉刀、手电筒、马刀等放入怀里拿走。在《大地的阶梯》中他描写了森林被大肆砍伐后的景象,感叹道:“我目睹了森林的消失,也看到了更加令人痛心的道德的沦丧。”[16]在现代物质的诱惑下,机村人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意识显得脆弱不堪,人们举起了猎枪和斧头,在自然毁坏中获得了眼前的金钱和物质,却遗落了美好的心灵家园,失去了美丽的栖居家园。其在《蘑菇圈》中描述到,阿妈斯炯守护蘑菇圈,小心翼翼采摘蘑菇,感恩大自然的馈赠,懂得要和鸟儿分享,干旱时节为蘑菇浇水,与蘑菇保持了互助的关系。但许多村民在贪欲下大肆采摘蘑菇而破坏了蘑菇圈,阿妈斯炯痛心哀叹:“人心成什么样了!”阿来痛惜环境的破坏和传统精神的异化,对传统习俗的非美变迁充满了深深的忧伤。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是人的精神危机泛滥的后果。改变人们的精神观念,回归质朴的人性家园,成为阿来内心深深的祈愿。
阿来在作品中不断反思人们的精神生态的变化,认为人们在一些曾经的政治运动、现代科技文明、经济物质利益冲击下带来的精神生态的变化,是一种对传统思想虚无主义的外化。他对故土一些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消逝感到痛惜,对当前人类的许多生态意识淡漠和古老生存模式的渐行渐远表现出无奈。他谈道:“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17]在《达戈与达瑟》中他写道,达瑟是文化的守护者代表,在“文革”中人们烧毁书籍时,他偷偷抢救书籍,并认真学习,规劝达戈不要残杀林中的动物。在《空山》中他谈道,面对精神生态失衡带来的生态问题,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索波褪去了狂躁的政治热情,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毅然决定到觉尔郎峡谷去守候鹿群。因砍伐木材进入监狱的拉加泽里经过罪与罚的洗礼后,幡然悔悟,意识到破坏森林的罪过,回到机村后带着一种救赎和回归的愿望开始在机村植树造林,他的行为得到村民的尊重和效仿。秋家老五从拉加泽里的转化中受到教育,放弃了与他之前的仇怨,摈弃了藏地千百年来宗族复仇的文化陋习,和拉加泽里一道去恢复生态环境。人们保护自然生态精神和行为的转变预示着机村人心灵家园的回归,寄托着阿来对人们的精神生态良性发展的美好祈盼。
结 语
藏文化基因中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观,以及合理向自然索取,可持续利用的发展观,这种生态意识也深深地植入了阿来文学作品中。当生态系统被破坏后,他说,风不再湿润,水不再浸润,动物消失,而人类有勇气消灭这一切,却没有勇气和森林、流水一道消失。他悲愤地说道:“先是鸟失去了巢穴,走兽得不到荫蔽,最后,就轮到人类自己了。”[18]阿来在其创作的作品中对人类中心主义充满了批判,积极倡导整体主义,希望实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和谐统一,着力推进自然生态的良性发展。他对生态的破坏感到隐忧和反思,对人们逐步端正认识,改变行为,推进生态和谐发展充满了期冀。正如他所说:“当作家表达了一种现实,即便其中充满了遗憾与抗议,也是希望这种现状得到改善。但作家无法亲自去改善这些现实,只是诉诸人们的良知,唤醒人们昏睡中的正常的情感,以期某些恶化的症候得到舒缓,病变的部分被关注,被清除。”[19]当前,生态失衡,灾害不断,社会问题频发,精神道德滑坡,人类非美之处颇多,制约了人类前行的步伐。阿来作品的生态审美意识对推进生态安全、社会和谐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人类向往的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