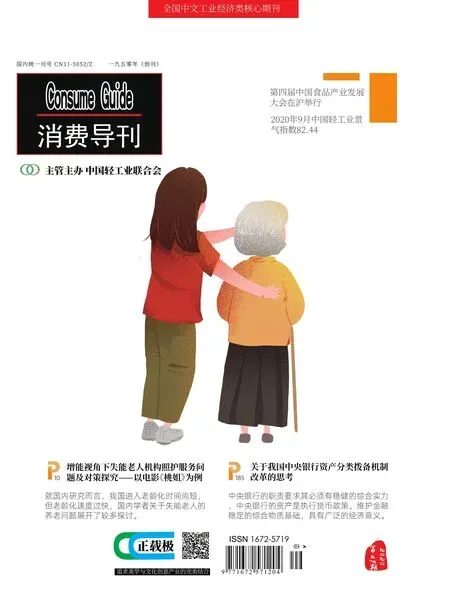数字技术、普惠金融与商业银行
韩石 苏州大学
一、引言
联合国把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定义为能有效和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系统(焦瑾璞等,2015)。近年来在我国,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余额宝等新型互联网金融产品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使我国普惠金融的受众广度得到了极大提升。
以互联网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为代表的新型数字金融业务无疑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上起到了质的作用。数字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模式给传统金融系统带来深刻的影响(谢平等,2012;刘澜飚等,2013)。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为,在我国大力推行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之中,数字金融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交易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对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又有哪些冲击。
二、交易可能性集合拓展
谢平、邹传伟(2012)提出,互联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逐渐降低,金融交易可能性集合拓展,原来不可能的交易成为可能。这一点与数字金融在提高我国普惠金融受众广度中的巨大作用相契合。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创新型的数字金融可以克服传统金融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具有更大的地理穿透力和低成本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金融的很多模式只要能超越一定的“关键规模”(critical mass),就能快速发展,从而取得竞争上的优势(Varian,2003);反之,在竞争上就会处于劣势。
我国数字金融显然已突破“关键规模”点,其影响力使交易可能性集合拓展成为现实。本文将苏州市2012~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信贷业务与苏州银行个人贷款量对比,这两组数据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反映的分别是数字金融与以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为苏州市民提供个人金融服务的发展情况。明显的,虽然商业银行的个人贷款业务量也在逐年上升,但支付宝等数字金融增长的速度更快。
相比于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具有拓展金融交易可能性和网络效应优势特征,这使得数字金融在开发新的受众市场的过程中受阻力较小,并且为信贷、保险等业务带来潜在客户,使交易可能性集合拓展。
三、金融抑制与存款竞争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存在投资工具稀少、投资渠道狭窄、市场进入壁垒高和资金配置过程中银行独大等特点(郑联盛,2014;郭品和沈悦,2015)。在此背景之下,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对资金持有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投资渠道的扩展。
参考邱晗等(2018),本文沿用Dinger and Hagen(2009)的做法,本文选择各银行在银行间市场的净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即银行同业净负债)作为衡量银行负债端结构的被解释变量。该指标先是用银行的同业负债减去银行的同业资产,再除以总资产。如果指标越大,则说明银行的同业需求相比于同业供给来说更高,银行越依赖同业资金。
将2011~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Q)与我国26个上市银行(剔除紫金银行、青农商行等10家银行样本的非平衡数据)的银行同业净负债(NIL)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负债结构与指数呈正相关,即随着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增大,数字金融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渗透性越强,则商业银行负债端同业间往来业务占比更多,商业银行对同业间批发行融资的依赖性就越强,从而证实数字金融降低了银行的吸储能力,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资金。
四、结论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规划的重要内容,其意义不仅仅是有助于政府改善民生,对商业银行及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来说,普惠金融是它们在当前金融环境之下扩展市场、提高业务水平和综合实力的关键出口。基于数字金融使可能性集合拓展以及网络效应理论,本文提出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趋势之下,数字金融扩展了交集可能性集合,较传统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交易模式来说更具优势。此外,我国仍存在金融抑制,这使得社会资金出口仍然狭窄,由此形成电子金融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存款竞争,传统金融机构吸引客户存款的能力下降,在负债端将更依赖于银行间拆借等批发行融资业务。
这些结论有助于对各金融机构在新金融环境下意识到数字技术对金融交易带来的巨大改变,并定位其在金融服务链中的新位置。